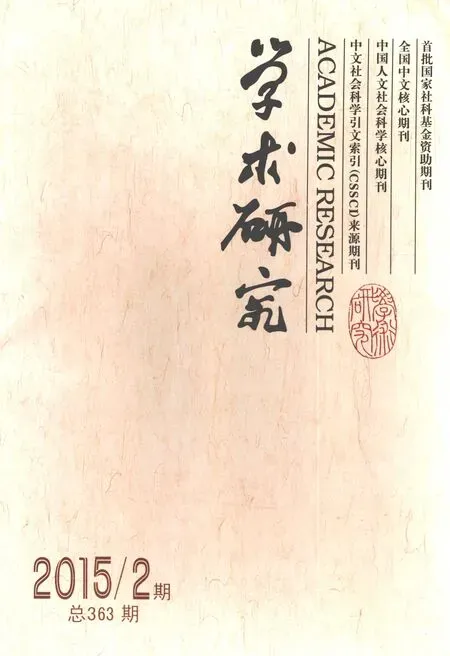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2015-02-25刘永祥
刘永祥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刘永祥
民国时期,国史馆设立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国史馆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民国时期 国史馆 建制沿革 史料搜集与纂辑
中国史学发展一直呈现官修、私撰双线并行的基本格局,“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1]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拥有官方制度化、组织化的史学活动,正是中西方史学的主要区别所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性质的逐渐转变以及中国史学的日益现代化,官方史学的存在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地位也一落千丈,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对于这一重要史学现象及相关机构,目前学界尚未给予足够关注,而有关民国时期国史馆的研究尤为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及主要成绩略作梳理、总结,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教。
一、国史馆设立始末及设馆理念的嬗变
中国古代之所以高度重视设馆修史,其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是掌控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从深层次上说,则是中华民族发达的历史意识使然。民国时期,国史馆继续存在并随时代发展产生新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复杂曲折的设立过程及设馆理念的嬗变上。
民国成立不久,胡汉民、黄兴等97人联名请设国史院,一方面要求延续设馆修史传统,一方面严辞批判旧史记载范围狭窄、维护君主统治等弊端,强调史书编纂应以社会、民族、国家等为书写主体和服务对象,从而标志着这一与政统、学统息息相关的文化制度开始转型。[2]因当时处于权力交接时期,参议院无暇顾及。袁世凯窃权后,表面上维持共和制度,将各项官制咨送参议院审议。议员们围绕国史馆应否设立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梁孝肃、蒋举清等坚决反对设馆修史,认为必 “蹈专制时代之覆辙,
重政府而略国民”。[3]事实上,历代史馆虽与皇权密切关联,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行政职权方面,还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直书精神和信史理念上。在中国文化传承和史学发展中,官方修史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谷钟秀就反驳说,国史馆 “不但不碍于私史,且可以为私史之参考”。[4]最终,这一理性观点赢得多数议员赞成。1912年12月11日,袁世凯任命王闿运为馆长。 “闿运久不至,欲改任章炳麟,藉以羁縻,炳麟不受。”[5]1914年5月25日,国史馆正式成立,然有名无实、形同虚设。1917年4月18日,段祺瑞呈请将国史馆暂行停办,“由教育部派员接收,另筹妥善办法”。[6]
随后,国史馆被降格为国史编纂处,于1917年6月30日并入北京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宣告当局对修史权的放弃,折射出官方史学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趋势。国史编纂处虽仅存两年,但成绩颇为可观,主要得益于对权力干预的剥离和对学术精神的贯彻。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对学生的回护引起当局不满,校长职务被免除,国史编纂处也被收归国务院。1919年9月1日,新国史编纂处成立,涂凤书任处长,在长达8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像样成果。1927年9月21日,张作霖以该处 “规制简略,职司未备”为由,下令重设国史馆,任命柯劭忞为馆长。[7]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垮台,国史馆随之解散。南京政府成立后,薛笃弼建议 “现有之部院……可以兼掌国史者,添设一处,专责编纂国史之责”,[8]未被采纳。首都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建议设立国史馆,并特别强调与中共争夺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从而将历史编纂纳入到政治斗争范畴。钮永建亦呈请设立国史馆,其出发点虽非党争,更侧重对官方修史传统的继承,但实质是以 “史权”塑造大众价值观,同样带有明显政治色彩。[9]可见,随着中国政权格局的变更,国史馆的政治意义逐渐被发掘。1931年5月11日,南京政府通过设立国史馆案,并成立了国史馆筹备处。然时隔近3年后,国史馆依然未能成立,引起国民党部分元老的重视。1934年1月,邵元冲等联名提交重设国史馆案并获通过。提案将设馆修史置于世界文化范围内加以讨论,认为它造就了中国文化特色,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不应为政治体制所累。[10]这种以保存民族文化为宗旨的主张的提出,正反映出处于日寇侵略威胁下爱国思想的高涨。
1939年1月27日,张继等提出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的提案,获得通过。提案强调设馆修史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认为 “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并极言蔑弃修史的严重后果,指出 “亡史之罪,甚于亡国”。[11]尤其是,提案明确划清国史、党史编纂界限,认为 “二者性质迥不相同,必不可混而为一”。[12]同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决议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以下简称筹委会)。筹委会虽名义上负责筹备事宜,但实际上已承担国史馆早期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1946年9月,筹委会迁回南京,10月23日,张继等呈请将筹委会改为国史馆,获得通过。[13]此时抗战结束,国史馆政治属性再度得到强化。提案在措辞、主旨及内容上均充满复古色彩,意欲以接续治统、道统之名,行专政之实,将 “民国史撰修成为一部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 ‘钦定’正史”。[14]1947年1月,国史馆正式成立,张继任馆长。张继去世后,戴季陶、居正先后被特任为馆长,但均未到职。其间,虽网罗诸多史学人才,但终未能取得具体编纂成果。1949年,国史馆撤往台湾。
二、国史馆的建制沿革
从制度层面来说,史官制度于汉魏时开始向史馆制度演变,至唐初而成定制,此后不断发展,至清达鼎盛,形成多馆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纂修体系,是传统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君主专制被推翻后,史馆虽得以保留,但因无法真正融入新的政治系统而迅速萎缩,原先多馆合作记载、编纂国史的格局发生变化,转由国史馆独力承担,加之时局动荡、政权多变,国史馆几经更张,其建制如史馆地位、职责范围、组织系统以及人员构成等也随着时代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特点。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官、私修史都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史馆在旧有政治体制内大致保持着行政上的相对独立地位。这一理念在民国时期基本得到继承。孙中山批复胡汉民等人提案称:“中国历代编纂国史之机关,均系独立,不受他机关之干涉,所以示好恶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笔者据事直书,无拘牵顾忌之嫌,法至善也。”[15]袁世凯当政后,参议院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大部分议员同意
政府提案中将国史馆与国务院平行、馆长 “直隶于大总统”的做法,认为可以使 “修史者立于独立地位”。张华澜等人则主张 “各省省议会公举”馆长,并建议将国史馆建设为 “合议制机关,非独裁之机关,为公开之机关,非职官专定之机关”,试图将修史之权从官方转移到私家领域。[16]这一反映民主观念而又偏于理想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因为国史馆所拥有的权力偏于文化范畴,而非具体的行政实权,不过却充分反映出官、私史学之间的张力。国史馆附设北大后,行政地位急速下降,而史馆性质的转变则带来纂修自由度和独立性的大幅提升。此后,国史编纂处被收归国务院,又经张作霖撤处设馆,国史馆的行政地位最终得到恢复,并一直延续下去,南京政府时期的筹委会和国史馆都直隶于国民政府。[17]只是,这一看似显赫的地位徒具形式,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与古代史馆的政治分量不可同日而语。
在职责范围上,国史馆起初 “掌辑民国史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18]但被北京政府收归国务院后,就不再承担编纂通史任务,而专门负责民国史纂修和相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在组织系统和人员构成上,袁世凯当政时期,国史馆设有馆长、秘书、纂修、协修等职,[19]馆员多为王闿运同乡,并包含清代翰林院一些守旧人物,他们对编纂民国史并不热心。[20]国史编纂处设有处长、纂辑股主任、征集股主任、纂辑员、特别纂辑员、名誉纂辑员等职,主要由 “中国史学门教员兼任之”。[21]在蔡元培和张相文的合力主导下,一个史学理念更为先进的队伍承担起修史重任。[22]他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或多或少接受了世界意识、进化史观、社会视野、民史等新观念。史馆风气随之一变,政治淡化、学术凸显,并依据研究方向进行分工,既便于发挥各自专长,又与原来工作保持一致。后来,又成立史学讲演会,“以北大学校史学门学生及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名誉征集员为主体”。[23]新国史编纂处设有处长、总编纂、主任编纂、编纂等职,馆员大多为清末进士。[24]南京政府时期的国史馆则设有馆长、副馆长、纂修、协修、助修等,后又增设特约纂修一职,并成立史料审查委员会,以确保编纂的政治倾向,[25]馆员多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史哲学者。[26]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国史馆在规模上明显趋于简化,并受政权更迭影响而无法保持一以贯之的运行机制和相对稳定的编纂队伍,这是它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史馆在发展过程中虽步履蹒跚,却也随着现代性元素的增加而呈现新面貌,特别是筹委会成立后,很多馆员对传统官方修史活动进行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勇于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史馆制度,尤以朱希祖所论最具系统性和创新性。他撰写 《国史事例杂议质疑》等一系列文章,提出诸多建议,立意高远、创见迭出。比如,他将档案上升到 “国宝”高度,呼吁设置档案总库,主张依据档案性质和种类采取不同的保存手段并设置相应的阅读权限;主张现代史官应具备文章雅洁、考订精确、识见高深等能力且必须通晓社会科学,并提议在史馆中特设储才馆;[27]等等。这些独到见解不仅继承古代设馆修史的优点,而且饱含浓厚的现代意识,有力推动了史馆的进一步转型。
三、搜集纂辑史料成绩举隅
从最终成果来看,国史馆尽管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通史或民国史,但在史料搜集、保存和纂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应一笔抹杀。概括来说,除袁世凯当政时期国史馆 “形同虚设”[28]外,其他阶段均在理论或实践层面做出贡献,尤以国史编纂处和筹委会较为突出。
国史编纂处成立之时,北大已在蔡元培大刀阔斧的改革下渐由充满官僚习气的旧式学堂转变为研究高尚学问的新式学校,学术氛围浓厚,馆员们用不到两年时间就 “纂辑稿件约二百五十五册,征集中东西文各书报约七百八十余种,计五千五百六十余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纂辑过程中,严格遵循客观原则,“专纪事实,不参议论”,而这正是史料长编工作的核心要求。[29]在搜集史料方面,国史编纂处最初采取官式做法,但在复杂权力格局下收效甚微。随后,张相文提出 “众擎共举”主张,在北大创设征集会,发动学生收集史料,并以报刊为媒介将征集范围扩大到全国,很快便汇集大量史料。[30]上述工作得到当局充分肯定:“该处……广罗名宿,实事著述,积极筹办,成绩斐然,至堪嘉许。”[31]
筹委会成立于抗战期间,由于时局艰难,原定庞大计划无法全面落实,遂将工作重心转移到 “史料之编辑与采访”。[32]在史料纂辑方面,筹委会编成 《民国史料长编》、《金石志稿》、《民国大事日历》、《国
史拟传》等,以前两种最为重要。[33]《民国史料长编》由傅振伦、蒋逸雪等摘录当时报刊、公报、档案及私家记载,以月为单位,用按日系事的方法编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国史馆开馆后,将其作为重要参考,编年组总纂柳诒徵称:“正其虚实,补其缺略,当不失为一良好之依据。”[34]《金石志稿》由王献唐呕心沥血编纂而成,是民国时期国史馆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现代学者评价其为 “一部极其罕见的、以个人力量系统地编撰清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未曾著录的出土金石资料的重要著作”,[35]“更加明确地反映民元以来金石方面的考古成绩,在中国金石考古之学的发展史上有其重要意义”。[36]
在史料搜集方面,筹委会制定 《征集史料简则》,并特别规定 “延请当过勋贤及熟谙掌故之时彦为史实之讲演,或派员前往访问,录存参考”,[37]已经意识到口述史料的重要性。1941年3月29日,张继等又以 “历代史馆秉著其所取材……亦皆出于政府”[38]为由,呈请国民政府令各机关将废存档案移交筹委会保存,获得批准,并制定具体实施方法,从而标志着一套适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史料收集和输送制度得到初步确立。据不完全统计,筹委会共收集、接收各类档案达几十万宗。[39]上述工作使大量珍贵史料得以在战乱中保存下来,不仅为民国史编纂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
南京政府成立后,直至抗战爆发前的10年间,当局对于国史馆虽筹而未设,也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在理论上充分意识到档案的重要性,认为 “今日在国史整理上之需要从事者不在国史馆”,[40]而在于档案史料的保存与整理,并联合中央研究院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法。[41]古代设馆修史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史料输送制度作为支撑,当这一制度随着民国政治体制的转变而消失后,国史馆的运作必然困难重重。因此,上述政策可谓抓住了问题核心,成为国史馆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孟森就曾评论称:“今闻人言政府不主张即设国史馆,而谋设保管档案之所,是即悟史有原材矣……有欲谈国史者,今日官制之下,尚无集中史材之法,则国史无由生,即国史馆何由设乎?”[42]
当然,史料纂辑工作必须遵循一定体裁体例,否则便无从着笔。在体裁上,国史馆大致沿用了带有综合性的纪传体,并加以改进。比如,国史编纂处将民国史长编分为 “年表、大事记、志及列传四类”;[43]新国史编纂处将 “国史体例,凡分五类,即纪、表、志、传及纪事本末”。[44]虽具体做法不同,但改造纪传体以成新的综合体裁是纂修人员的共识,尤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优点,解决通史撰述中的主干问题,使历史发展大势得到清晰再现,这也是近代以来史书体裁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此外,近代史学在产生时以批判 “无数之墓志铭”[45]的革命姿态出现,致力于探寻历史演进规律,造成 “人”在历史编纂中长期以来的缺位,而国史馆对列传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四、影响国史馆运作诸因素
从性质上说,国史馆不是单纯的学术机构,而被赋予文化和政治双重功能,是当权者掌控 “史权”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决定了其发展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在民国时期,这种影响除了时局动荡、政权更迭外,还表现为北京政府对修史的漠视和南京政府对国史馆政治属性的强化。
袁世凯设立国史馆只是 “承旧案,应故事……故视为冷衙闲曹,无足轻重”,[46]不仅造成官方历史记载的一度中断,而且使国史馆地位迅速下降。国史馆在政府机构和学校部门之间的随意转换,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导致北大学人的工作几乎 “前功尽废”。[47]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国史馆虽在文化和史学传统影响下得以保留,但面对复杂多变的政局时难以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就无法进入当权者的政治视野,因此这种延续往往流于形式,其重要性更多停留在理论或政策层面,始终游离于新的政治、权力体系之外。梁启超批评说:“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纪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48]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史馆的政治意义逐渐被发掘,并渐有强化之势。筹委会成立之前,林森等就曾呈请将党史编纂委员会改名为国史编纂委员会,试图混淆党史、国史之间的区别。[49]抗战胜利尤其是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诸种手段维护独裁政权,国史馆也被纳入其中,成为与中
共进一步争夺史学话语权的工具。在国史馆第一次纂修会议上,馆长张继就强调说:“今日修史,当维持中国之正统,以期继往开来……必以三民主义,为吾今日撰述之依据。”[50]随后,顾颉刚提议创办 《国史馆馆刊》,旨在打破官、私修史之间的屏障,指出:“史料贵于研究,而研究所得,尤贵供诸社会,故希望吾国史馆能倡办一研究近百年史之刊物,以供世人阅读。”[51]但张继对馆刊内容予以制约,再次强调说:“中国国民党为缔造中华民国之唯一政党,故自国父建党以来之一切活动,实居中华民国历史之主要地位……本馆受命纂修国史,应坚守三民主义之立场,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52]
此外,民国时期,战争频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不仅一度中断国史馆的筹备工作,而且使纂修人员经常面临危险,严重影响史馆正常运转。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诘朝诣歌乐山史馆,经重庆大学,礼堂、图书馆皆被震毁,路旁断木纵横,瓦砾满目,为状至惨……同史馆同人避于宽仁医院之防空洞,久之敌机未入市空,午后三时警解返馆。”[53]然而,恰是在这一时期,国史馆建设突破政策层面,正式转入实质性筹备阶段。其直接原因,是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感促使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进一步意识到国史编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间接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撑,则来源于历史记载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存灭的观念。这一观念由龚自珍明确提出,后经梁启超 《新史学》赋予其近代意义而广为知识分子所接受。
再者,时局的动荡造成社会生产力低下,政府财政紧张,加之 “国家之财赋,皆集中于军事”,[54]国史馆常常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北京政府之所以将国史馆降格为学校部门,目的正在于节省经费。段祺瑞在呈文中称:“值此财力支绌之时,与其长此因循,徒糜经费,曷若即行停止,徐图更张。”[55]江瀚曾呈请将国史编纂处收归国务院,但未被采纳。当局回复说:“方今世界文化日进,史学列为专科,文明各国纂集史事,多由最高学府典领,以期贯通学术,发扬国光……原定国史馆官制,系专设机关,规模宏备,需款甚巨,应俟竟来查察情形,再行斟拟规复。”[56]显然,若非 “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并无意收归国史馆,而借世界通行做法之名,行节省经费之实。筹委会在抗战时期的境遇则更为窘迫:“仅以开办费二千元之数,筹备成立……三十年后,物价日见腾涨……经济益见拮据,不得不一再紧缩。”[57]凡此种种,皆造成国史馆的发展举步维艰。
五、结语
民国时期,设馆修史的传统虽得到延续,但繁荣不再,实已步入曲折和萎缩阶段。在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国史馆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它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缺失政治土壤的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因素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透过历史的沧桑,我们可从中总结出诸多十分值得珍视的思想观念和学者的执着追求,尤其是,中华民族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在民国动荡的年代却一直产生回响,显示出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孙中山、蔡元培等杰出人物,对于修史如何反映新的时代特征和坚持直笔传统,提出了鲜明的主张,掷地有声;许多具有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学人,如张相文、邓之诚、傅振伦、王献唐等,都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为修史或纂辑史料付出坚韧努力,做出成绩;还有,像朱希祖、金毓黻、但焘等学者,都对修史中如何发挥优良传统和切合时代需要提出了具有卓识的主张。以上各项,就是我们梳理和审视这一曲折历程所应得到的有益启示。
[1]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胡汉民、黄兴等九十七人请设国史院呈》,《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1912年3月17日。
[3][4]《参议院第八十三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81号,1912年10月29日。
[5][20][24][40][46]逸雪:《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
[6][28][55]《国务总理关于暂行停办国史馆致大总统呈》,《政府公报》第459号,1917年4月18日。
[7]《大元帅令》,《政府公报》第4101号,1927年9月24日。
[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第126页。
[9][26][37][49]许师慎编:《国史馆纪要》(初稿),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年,第84-86、152、126、117页。
[10]《邵元冲居正方觉慧等提请重设国史馆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中国档案史参考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41页。
[11][12][13][17][18][19][25]国史馆编:《国史馆成立始末》,南京:国史馆编印,1946年,第6-15、6-15、19-20、23-25、2-3、2-3、23-25页。
[14]孔庆泰:《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史撰修概述》,《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15]《临时大总统批示》,《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1912年3月17日。
[16]《参议院第八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82号,1912年10月30日。
[21]《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简章》,《政府公报》第526号,1917年6月28日。
[22]《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职员录》,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
[23]《国史编纂处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7日。
[27]朱希祖:《国史事例杂议质疑》,《史馆论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9]《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呈报纂辑、征集工作清册》,《教育公报》第6年第5期,1919年5月。
[30]张至善:《张相文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1]《教育部指令》,《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6日。
[32][33][39][54][57]国史馆编:《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结束报告书》,南京:国史馆编印,1947年,第14、20-21、24-37、38、1页。
[34]《编年组会议记录》,《国史馆馆刊》1947年第1期,馆务。
[35]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 〈国史金石志稿〉整理札记》,王文耀校,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
[36]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王世民序》,王文耀校,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
[38]《拟请国府通令所属以废存档案移交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保存案》,《浙江省政府公报·公牍》1941年第3307期。
[41]《筹设国史馆之四办法》,《教育周刊》1934年第193期。
[42]孟森:《国史与国史馆》,《独立评论》1935年第135号。
[43]《国史编纂处纂辑股编纂略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6日。
[44]金毓黻:《旧京史馆述闻》,《国史馆馆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4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47]萧一山:《蔡孑民先生事略》,《非宇馆文存》卷1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41页。
[4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5页。
[50][51]《国史馆纂修人员第一次座谈会记录》,《国史馆馆刊》1947年第1期,馆务。
[52]《馆刊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国史馆馆刊》1947年第1期,馆务。
[5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565-4566页。
[56]《教育部咨呈国务总理详陈国史馆附设北京大学校办法》,《教育公报》第6年第4期,1919年4月。
责任编辑:郭秀文
K207
A
1000-7326(2015)02-0119-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09AZS00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4CZS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2014T70628)的阶段性成果。
刘永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山东 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