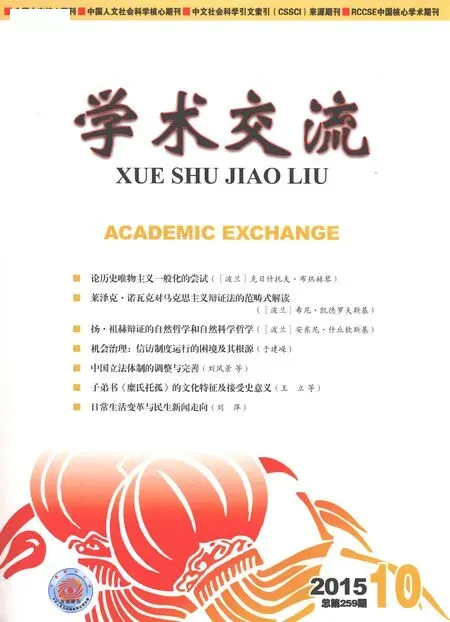超越正义回归多元良善生活
——阿格妮丝·赫勒正义理论解读
2015-02-25魏金华
魏金华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超越正义回归多元良善生活
——阿格妮丝·赫勒正义理论解读
魏金华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赫勒认为,我们不能仅从正义本身去研究它,不能局限于宏观的视域。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正义,回归微观的良善生活,而良善生活的三个构成要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超越正义的目标。
超越;正义;良善生活
正义是一个亘古恒新的话语,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关乎人类美德的价值尺度,是关乎人类未来状态的理想意境。 从古希腊开始直到今天,人们从未放弃过对正义的探索。但由于人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情境的不同,在对正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诸多争论。卡尔曼海姆说:“我们应当首先看到这一事实:同一个术语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1]245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赫勒的《超越正义》一书在对传统和现代正义概念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评论的基础上,认为所有关于正义的诉求都源于“自由”与“生命”等其他价值追求,而不是正义本身。赫勒得出结论认为,当未来每一个个体都是道德的人、理性的人或是“人的本质”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学习养成正义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做不正义之事,当正义可以充当良善生活的先决条件之时,这种良善生活就超越了正义。
一、传统社会的静态正义
赫勒从静态的或形式的特征来理解传统社会的正义理论,指出传统社会的正义理论涵盖正义全部类型的所有特质,不仅涉及正义的全部规范而且涉及理想类型中抽象出来的正义。正如赫勒所说:“形式的(或静态的)正义概念之所以被界定为形式的(或静态的)是因为它涵盖了所有类型正义的共同特性,因此,它不仅是从正义的全部规范的内容、标准和程序中,而且也从某些(有限的)理想类型中抽象出来,这可以通过内容、标准和程序的不同结合方式而得到合理的理解。”[2]1通过批判亚里士多德“平等与不平等”的二元视角和佩雷尔曼 “形式的或抽象的”的视角,赫勒认为在解读形式的正义概念时不能仅仅使用规则,还应该使用规范和规则。因为规则是具体的,而规范存在具体和抽象之分,如果用“规则”代替“规范和规则”就限制了人们对复杂性的理解。赫勒通过对规范和规则的区分重新界定了形式的正义:“形式的正义概念意味着那些应用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各种规范和规则能够连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适用于该社会群体内的每个成员。”[2]5通过形式的正义概念,赫勒旨在说明一个群体是由运用于该群体中的规范和规则构造而成的。
赫勒把静态正义描绘为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因为正义是客观、公正的,公正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够追求物质利益,不能够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不能够热情、嫉妒和羡慕,也不能够有一颗善良的心。公正就是应该连续不断、持之以恒适用于相同的规范和规则,而不应该考虑个人的物质利益,不应该掺杂个人的情感。静态正义有时是一种冷酷的美德,甚至是残酷的,无论是温和还是残酷,实际上正义都有赖于规范和规则本身。由于静态正义观以极度的一致性公平地或适当地对一切不合乎静态正义标准的“非正义”施以责难和处罚,赫勒认为如果在塑造社会群体时采用这样的静态正义准则,将会产生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在此基础上,赫勒通过批判卢梭的“公意”概念来表达她对静态正义观的反感。赫勒认为在卢梭那里正义就意味着实现了的公意,公意又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静态的公意中,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的规则和习俗永远也不会受到挑战而变得僵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志,就会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有这种意志,便是专制主义。而在动态的公意中,政治规则为政治成员提供了自由挑战社会规则和规范的空间,并鼓励他们这样做。”[3]101卢梭的静态的公意和动态的公意所反映出来的是静态的正义观和动态的正义观。静态的公意——静态的正义的实现,必然导致权威的滥用,所以卢梭指出只有通过法律的普遍性才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卢梭的法律概念在尼采看来只是表明了它对“那种新的、独一无二和无可比拟的事物”的偏见。因此,把公意作静态的理解只能导致把欺骗性的平等与普遍性强加于人的行为,为了实现这种公意不得不依赖于服从和同一,不得不消除冲突和异议。最终导致卢梭的公意概念不得不求助于强制和束缚的概念。
赫勒认为静态正义要求社会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必须连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遵守特定社会群体的各种规范和规则,寻求的是一种普适性的正义观,但这种正义观也会带来社会冲突,这些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种情况是个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强权即正义;第二种情况是为适应静态正义的适用范围而对社会群体进行削足适履;第三种情况是内外集团之间的不对称使同样的正义规则造成了不平等。赫勒认为静态正义的黄金规则内含于所有的社会冲突中,静态正义的黄金规则即是“我对你所做的就是希望你对我所做的”[2]21。这是一个形式规则,这一规则只适用于规则可以作明确解释的相互关系,即黄金规则只适用于对称性的关系,而不适用于非对称性的关系。只有当人类的关系是对称性的,只有在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是平等的时候,黄金规则才能发挥指引人们所有行为的作用。赫勒认为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被抛进一个固定化的、以目的论的方式建成的等级社会的某个阶层中,它在成为生命个体的同时必须顺从其命运。“如果一个人是作为奴隶而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就必须成为他生而要成为的那种人——一个好的完美无缺的奴隶。”[4]84赫勒认为遗传先验不会注定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等级降生。遗传先验是被放进信封里,而信封被寄往等级制社会的一座城堡。由于遗传代码的“信封”被抛进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个人所行使的职能被镌刻进他的社会地位之中。弗洛姆对人生的此种状况作了描述:“封建社会早期,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机会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阶级。从地理位置来讲,他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镇迁到另一个镇,或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他必须从生到死待在一个地方,甚至连随己所好吃穿的权力都没有。”[5]29尽管每一次出生都是一次偶然,但一个人却在获得生命的同时接受了他(她)的命运。赫勒用金字塔来比喻传统社会格局,在金字塔的各层及其居民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相互关系,金字塔一层一层地垒造,一层一层描绘并规定着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等级中的“指定位置”,底下宽、顶上窄。在金字塔的顶端总是站着一个男人,扮演着支配者和统治者的角色。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是不平等的。因此,静态正义的黄金规则不适用于非对称性的传统社会的人类关系。
二、现代社会的动态正义
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动态正义在现代社会或国家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说明现代性不是被否定摧毁,而是通过它繁盛地生长。人们开始质疑传统,质询和检验被证明是真实、神圣、理所当然的信念。曾经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如今被证明是虚假的;曾经被认为是正确而加以接受的东西如今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加以批判的,不再有什么是稳定地、一成不变地被一致接受的。动态正义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就会越迅速地转变为不正义。昨天的正义是今天的不正义;今天的正义是明天的不正义。“正义就变成了一个相反的变色龙:它总是呈现不同于其周边环境的颜色。一旦环境类似于其颜色,正义本身就变化颜色。”[2]235在任何地方,对一切事物都存在不同的意见,因此,以正义的名义所发起的挑战几乎从不会来自同一个角落。无论对错我们都可以大声愤怒地呼喊,说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应该用更多正义的制度取代它。因此就会出现一部分人控诉制度的不正义,一部分人认为制度是公平而正义的去捍卫它,由此引发双方的冲突,但他们运用的是同样的动态正义概念。赫勒认为现代性的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也取决于有关正义的争论。社会阶层的不同导致正义的准则和要求差别很大。一个阶层认为是正义的,另一个阶层可能认为是不正义。对一个阶层来说是正义的成分多些,对另一个阶层来说是不正义的成分多些。因此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有关正义的争论不仅会推动社会与政治格局朝一个单一的方向改变,而且在被朝一个方向推动后,它们完全有可能被推向另一个方向。
赫勒认为动态正义关注规范和规则,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作出评判。赫勒列举了与现行规范和规则相矛盾的,以使现行规范和规则失效的四种规范性标准:特定的原则、道德规范和实践准则、实用准则以及实质性的价值。其中实质性的价值是最终的、最根本的。在现代这个时代,最终的实质性价值就是普遍价值。赫勒认为“无论是通过使用特定原则、道德价值或准则或者实用性准则都会使不正义的规范和规则失效,对每一个规范和规则系统的摒弃最终都是根源于实质性的价值。在现代,所有的原则或准则都来源于这两个普遍的价值:自由和生命”[2]127。自由和生命被先验地设定为普遍的价值,一个社会只要能确保公民的自由和生命,就是正义的。在动态正义概念中,正义必须诉诸自由和生命的实质性价值。赫勒认为在现代性中只有两个普遍的价值,所有的因其不公正而使规范和规则失效的那些原则,在最终的意义上都要诉诸这两种价值。自由和生命的价值必须得到平等的满足,否则任何目标和原则都不能被视为具有普遍性,都可以质疑其正义性。只要动态正义得到应用,那些试图否定一项规则和法律之正义性的人总是要么求助于自由,要么求助于生命,更确切地说,共同求助于自由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那么毫不奇怪,在现代性中这两种价值(自由和生命)都变成了普遍、动态正义的准则。“持续的正义论争表明,人们总是以这两种价值的诸多解释中的一种为参照。”[4]286
动态正义视角下的社会冲突及政治冲突是在检验与质疑规范和规则本身正义性与否的过程中出现的。我们在正义感的指导下完成的对不正义的规范和规则的摒弃,并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当我们声称这些规范和规则是不正义的时候,是想改变或者废除这些规范或规则,或者由其他的规范和规则替代;当我们声称这些规范和规则是正义的时候是想捍卫它们。赫勒提出的理性建议:所有社会及政治的冲突都起因于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对特定的一种正义要求的抑制会产生社会或政治的压迫,而对某些规范和规则的正义或不正义方面的妥协会产生社会和政治的妥协。赫勒认为社会政治冲突的动力即社会冲突中的组织和个人是受正义理想激发的,对团体和个人而言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赫勒认为社会政治冲突同样还受利益激励,在静态正义下受既得利益激励,在动态正义下受动态利益激励,而特殊的社会冲突是通过激情获得最终动力的。社会政治冲突产生于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每一次我们会因为正义或不正义而使规范或规则生效或者失效。自由和生命作为普遍的价值,只有在现代才能成为最终的价值,在每一个社会或政治冲突中,某些产生效应或者失效的价值观、原则或假言命令被嵌入自由或生命的一种特殊的解释。对于每个人而言,自由应该减少的主张是自由的正义论争,这是社会的冲突而不是政治的冲突。所有关于正义的论争是有关自由的、要求自由的、抨击自由的特殊解释,是典型的政治冲突。对于每个人而言,生命机会应该减少的主张是政治的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冲突。因此,赫勒得出结论,“如果基于自由而驳斥正义,冲突就是政治的;如果基于生命而驳斥正义,冲突就是社会的。”[2]150也就是说,政治冲突产生于自由原因,社会冲突产生于生命机会原因。无论在动态正义还是静态正义角度下结论都是相同的:如果事关生命机会的规范没有持续不断的应用,可能会发生社会冲突;如果事关自由的规范没有持续不断的应用,可能会发生政治冲突。
三、后现代社会回归良善生活世界
赫勒通过评析传统社会的静态正义和阐释现代社会的动态正义,最终要寻求的是通过正义程序运作的、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这一世界是良善生活的历史条件。赫勒认为我们不能设计良善生活的模型,只能关注构建良善生活的要素。赫勒认为良善生活体现在三个方面:“正直、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及才能的运用和个人联系的情感深度。”[2]285良善生活的三个方面是对正义(静态正义和动态正义)的全面超越。
良善生活的第一个构成要素:正直的人。赫勒在《一般伦理学》《道德哲学》和《个性伦理学》三部著作中提出并回答了一个关键的基本问题:“正直的人存在,但他们何以可能?”什么样的人是正直的人?亚里士多德把正直定义为美德的总和,这一定义没有把所有良善生活的具体要素抽象出来。康德把正直定义为善良意志,表面看起来很抽象,但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定义只是在正直的人的形象中包含形式主义的元素,但却不包含伦理和行动本身。赫勒认为最好从康德回到柏拉图式的定义,即“正直的人是宁愿忍受不义(邪恶)也不愿践行不义(作恶)的人”[2]291。赫勒认为这一定义足够抽象,这一定义很好地概括了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正直,却没有涉及良善生活的任何具体方式;这一定义不是要求对每个人做好事,而是对任何一个人不应该做坏事,并且当干坏事是唯一的选择时应该忍受邪恶。这一定义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它既适用于很少规范和规章的社会,又适用于很多规范和规章的社会。这里正直被定义为对一个行动(恶行)的容忍,而不是定义为行善。不对任何人作恶,就在消极的意义上履行了善。在多元的文化世界里,尽管生活方式不同,但正直的人拥有最高程度的道德自主,这是正直的人的共同特点,即他或她的道德品质没有屈服于社会强制。赫勒认为正直的人存在是道德哲学的重要理论前提,“没有‘好人存在’是真实的这一理论前提,就根本没有道德哲学。”[6]47什么样的人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的品质特征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总能发现正直的人确实是存在的。赫勒认为正直的人不能被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对这些人来说忍受不义好过践行不义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存在自觉和自我意识的关系,并且如果他或她的行动始终如一且持续不断地遵循这一关系的话,那么他或她便是正直的。我们生活在多元的、规范化的道德世界中,存在许多可以被任意选择的规范,我们凭借自己的口味、利益和愿望选择规范,并且为我们自己的行动给出心理的理由,而非道德的理由。为了在几套规范中进行选择,为道德理由使自己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必须从道德视角来检验自己的规范和行动。为此我们必须在善恶之间作出实存选择,实存的选择是通过一系列适时的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选择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优先考虑道德理由的人,成为一个由实践理性指导的人,成为一个宁愿忍受邪恶也不践行邪恶的人,只有这样的选择才是成功的。赫勒把存在的选择区分为差异性范畴下的存在选择和普遍性范畴下的存在选择,指出后者是一个抉择于善恶之间的历史范畴。“如果一个人在普遍的范畴下选择了自我,那么他就在伦理上选择了自我。如果一个人选择成为他所是并且如他所是,那么他就从伦理上选择了自己。通过选择自己的决定,一个人使自己自由地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我注定成为好人的人。通过选择成为一个好( 正直的) 人,他就在善恶之间做出了选择”[7]17。
良善生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将天赋发展成为才能,即自我的构建。赫勒认为道德规范是压制性的、非理性的。它削弱人的个性,抑制人的本能和愿望,因此仅仅通过道德因素是不能将我们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的。由于社会政治规范和规则是压制性的,导致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抑制性的,在未来要超越正义,超越抑制,就是要超越所有社会政治规范,进而超越道德规范,在所有的人类本能和欲望都可以存在和付诸实施的框架内构建社会政治制度,这就要求创建由“美”或“自然”规范构成的非社会的、非政治的和非道德的生活方式,从而确保自我在爱和友谊的纽带中得以构建。自我的构建不是一个快乐的旅程,而是一个痛苦的劳动。赫勒认为自我的解构与自我的“毁灭”等同于权威的解构与毁灭,我们越从所有规范中“解放”自我,就越在进行自我毁灭,也就变得越不自由。由正义程序建立的社会政治规范要求价值商谈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将生命和自由诉诸最高价值,只要发现某个特殊的规范或规则是不公正的,每个人都可以再一次从头开始。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在社会中,一种类型的社会-政治规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欲望、倾向和需要自由地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生活方式不同,在一种单一的社会政治团体中,道德规范可以有所不同,但大家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政治规范。由彼此互惠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多元文化世界提供了把我们的天赋发展成为才能的最大可能性,最佳的社会政治世界为良善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强化了不同的才能,一个人可以根据他或她的需要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才能。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社会互动不涉及相互的主宰,因此不存在不被允许发展成为才能的天赋。如果社会政治的规范和规则不是压制的,如果正义的商谈程序符合伦理的要求,如果人们遵守的仅是提供人类的最广泛合作的社会政治的框架而非具体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自我就完全地构建起来了。
良善生活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个人联系的情感深度。一个具有自主的道德自我的人,是将各个社会或制度的所有道德方面以及所有与道德相关的行动模式予以同质化的人,可以将他或她的一些天赋发展成为才能,从而将他或她自己建构成为创造性的自我。创造性的自我虽然只有相对的自主性,这种相对的自主性受社会理解矩阵的指导。创造性自我越有自主性,过良善生活的机会就越大。创造性的自我在进入个人的联系时会选择他的相对他律。将个人的天赋发展成才能当作个人幸福的领域,追求个人幸福是贯穿于情感纽带和联系中的,是与自我创造的社会规范和法律之中的公共幸福同质同源的,也就是说,个人联系的情感强度与我们所服从的道德准则同质同源,我们促使我们自己服从于人际关系。一个诚实的人的个人联系并不违背道德准则,在进入个人的联系时一个人会选择他的相对他律,个人联系的情感强度在社会的上下级关系或心理上的上下级关系中是他律的,即使在心理和社会的两种上下级关系全都不存在时,我们也会在这种联系中发现相对的他律,只有在缺乏社会和心理的限制时,相对的他律才可以被自由地选择。从人类条件中消除他律或者使其退化,是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已经初步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情感的全部限制,甚至于情感淡漠。进一步的解决方案是贬低爱,进而自我放弃,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使唯一的或者至上的爱的目标绝对化。自主和他律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赫勒看来对完全自主的恳求已经降到了使情感自我毁灭的程度。由情感投入所创建的他律被当作一个本质上为善的事物来体验,每个人都知道个人联系中如果没有任何情感强度的生活就不可能是美好的,也是不值得生活的。再多的尊重,再多的承认也不能代替被爱的需要的满足。只有对人的爱才能满足爱与被爱的需要,才能构建和重建人际关系,每一个宁愿忍受邪恶也不愿践行邪恶的人都是通过他(她)对所有人的行为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是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诚实的人在善良的庇护下主动承担人际关系、普遍团结的关系。自我作为人类的一个完整成员,幸福依赖于其他人的快乐、安宁或者仅仅是存在。自我通过与一个人的联系,从而与人类完全地联系起来。个人联系是人际联系的微观缩影,诚实则是它的宏观世界。在个人联系中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他律,使自己服从于爱的力量,使自我发展成为一个仁慈的和完全的自我。
综上所述,通过评析传统社会的静态正义和阐释现代社会的动态正义,赫勒要说明的是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和观点不同,价值观具有多元性,但良善的生活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良善生活的条件仅是正义的程序,正义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不能设计良善生活的具体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认为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良善生活即:正直、从天赋到才能的发展及才能的运用和个人联系的情感深度,最终将使我们超越正义。
[1] 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M].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70.
[2] [匈]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M].文长春,译.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 [英]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尼采的道德—政治思想研究[M].宗成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 [匈]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5] [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6] Heller A. General Ethic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7] Heller A. A Philosophy of Morals[M].Oxford:Basil.Blackwell,1990.
〔责任编辑:余明全 杜 娟〕
2015-03-13
魏金华(1970-),女,吉林梨树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B089
A
1000-8284(2015)10-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