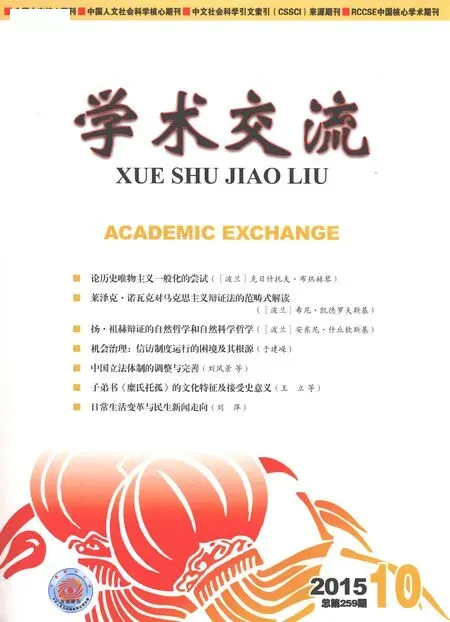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民族精神论析
2015-02-25郑忆石
郑忆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外国哲学研究
·俄罗斯哲学专题·
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民族精神论析
郑忆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民族精神在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中体现为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救世主义及爱国主义。它强调民族文化对俄罗斯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而它对俄罗斯独特性的注重,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具有强调自强自立的斯拉夫主义特质。它重理想轻欲望、重精神轻物质,对精神价值的强调,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弥漫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它透过人的内在生命和心灵世界去研究外部现实,对自由、道德、生命意义的关注,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它强调只有通过宗教信仰,才能唤回人类的自由和拯救世界,而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情怀,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充满了救世主义元素。它崇尚集体、崇拜国家,追求精神完整性、聚合性、完整性,而它对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认可,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倾注了爱国主义活力。
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救世主义;爱国主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伴随东正教的复兴,传统宗教哲学一度成为学界的新宠。进入21世纪后,出于经济发展、国家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等需要,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家、企业家及相当部分民众,开始厌弃和冷落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但社会并未否认反而强调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强国梦的意义。挖掘和阐释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中的民族精神元素,不仅是当下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取向和社会发展所需,也对当下中国学界,如何通过正确辨析自己的民族哲学文化传统而提升民族精神,走好自己哲学的未来之路,具有借鉴意义。
民族精神作为一国文化中意识、性格、信仰、价值观等的历史积淀,无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它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民族的复兴注入持久的活力。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包括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救世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它们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景观,影响了包括政治、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在内的诸多社会意识形式。同样,它们也在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身上刻上了深深的印记。
一、斯拉夫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基质
象征着俄罗斯本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俄国的特殊性,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我们不能直接断言斯拉夫主义就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但斯拉夫主义对于俄罗斯“独特性”的强调,蕴含了俄罗斯注重自我和强调独立的民族精神。
作为代表和象征俄罗斯本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纵向”*与之相应的,是俄罗斯的西欧派,被称为俄罗斯文化的“横向”脉络。脉络兴起于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主要的、集中的任务,在于寻找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作为对西方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和恰达耶夫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回答,斯拉夫主义者们断然指出,俄罗斯的历史、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民族意识,也就是整个俄罗斯文化,不能被归于其他的,与它不一致的模式之中。俄罗斯文化拥有自己的生活价值、自己的前景”[1]。从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出发,斯拉夫主义反对俄罗斯文化的西方化和“世界主义”思想,而它的强调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复兴的主张、强化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努力、传承俄罗斯民族精神遗产的行动,构成了那个时代“俄罗斯思想和文化的‘向心线索’,‘其特征是全部世界观、所有的创造和研究的努力,全部的价值观念的纵向取向’”[2]。与之相应,斯拉夫主义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对于俄罗斯哲学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构建俄罗斯哲学的“必要因素”[3]前言1。
在俄罗斯传统哲学中,斯拉夫主义特质最为鲜明地体现为俄罗斯宗教哲学蕴含的,与俄罗斯民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东正教传统。这种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历史传统的东正教传统给予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在契合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既有东方色彩的同时,坚持“哲学认识是用完整的精神去认识,在这种精神中理性和意志、感觉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唯理论所作的割裂”[4]157,表明了俄罗斯宗教哲学重直觉体悟而轻理性推导、重生命体验而轻知识经验、重情感信仰而轻思辨分析、重道德价值而轻物质利益的特征。而它提出并力图论证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的独特性观点,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具有精神优势,而“德国哲学不可能在我们这里扎根。我们的哲学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发展起来,应当从当前的问题中,从我们人民和个人生活的主导利益中创造出来”[5]的观点,强调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以反对西方思想的方式来寻找自我和确定自我”[4]157的思想,更是在创建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中,表明了它对传承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民族独立精神的重视。
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的民族精神,还通过语言形式体现出来,具体体现为通过挖掘俄罗斯民族语言的潜力,表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与俄罗斯哲学具有的斯拉夫主义特质相应,19世纪40年代—60年代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成为俄罗斯社会思想的时代性标志的同时,斯拉夫主义者在强调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特殊性中,十分强调俄罗斯语言对于确保俄罗斯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由于语言形式是民族个性最真实的“物化形式”,是社会集体心智的“形式化结合手段”,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形式化表现手段”[6],因此,它是民族性记忆和精神性体验的标记。在斯拉夫主义者看来,俄罗斯语言同样如此: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而言,它是其体现形式,发挥着民族自我认识的作用;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而言,它同样是其体现形式,发挥着充实民族精神财富的作用,“民族精神不可能具有语言结构形式以外的其他结构形式,因为不存在任何没有语言的精神力量”[7]。
斯拉夫主义者们对语言形式及其本质的关注,对俄罗斯语言对于民族意识崛起、民族精神跃升价值性的强调,在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应,便是将精神价值的寄寓所在置放于东正教的传统文化观,将哲学的关注点置于精神的绝对性作用。这种“精神的绝对性”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尽管是自己的内在信念与直觉基础的融合,并且各有特点,但强调精神的实在性、注重生命与世界的完整性、宣扬应有的理想性等,却是其共同特征。这种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立足于俄罗斯语言之上的斯拉夫主义“团契性”思想。
尽管强调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本土特色的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俄罗斯哲学保有独创性和特色之根,也是俄罗斯哲学提升民族自尊自信之源。然而,对哲学民族性和本土化的过分强调和片面追捧,又容易造成民族自尊的过度和泛化,导致哲学的封闭保守。在俄罗斯哲学发展史上,从具有独立形态的近代宗教哲学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保守性虽然程度不同,但却是一以贯之。而这又与其“斯拉夫主义”特质一脉相承。 当今世界,全球化挟带着资本指令与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汹汹来袭。这一切,向今日俄罗斯提出了许多深层思考的课题。如何既坚守传统,弘扬独立自我的民族精神,又面向世界,为民族精神注入开放多元的时代元素,在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为“强国梦”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对当代俄罗斯哲学而言,如何在传承斯拉夫主义民族精神遗产的同时,使这一精神在富含时代气息中得以升华,是其不能不深思的问题。
二、理想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基调
对俄罗斯民族而言,其文化的民族精神含义十分丰富,既饱含高度道德感,崇尚理想追求,又渴望真善美,致力变革求新。但“重理想轻欲望、重精神轻物质”[8]的理想主义,却是其文化中民族精神的基调和底色。这种理想主义对精神自由、道德、价值、信仰等超越物质经济因素的东西,有着独特的关注,“在俄罗斯民族中深藏着比有着较多自由和受过较高教育的西方民族更大的自由精神”,“巨大的自由是俄罗斯民族的最主要的本原之一”。[4]44这种对精神价值的独特关注,使得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特质中,弥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认为“一切都应当建立在信任、爱和自由的基础上”,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于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中,“斯拉夫主义者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他们认为生活从一开始就超出权力之上”[4]50。这种对精神价值的独特关注,使得俄罗斯民族形成了道德、精神刺激等因素“在事业的成功中起重要作用的传统”,这种传统“培养出了俄罗斯人特殊的生物节律、道德伦理和劳动纪律”[9]336。这种理想主义在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中,通过文学作品中众多文学大师塑造的诸如“多余人”“新人”“特殊的人”等形象;通过现实生活中一些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出于憎恶农奴制、同情怜悯民众苦难境遇,掀起的“到民间去”运动;通过“十二月党人”,出于忧患焦虑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甘冒奉献生命的义举,等等,而表现出来。
在俄罗斯传统哲学中,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理想主义特质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俄罗斯宗教哲学蕴含的浪漫性。这种浪漫性表现为:鄙视世俗生活,视现实世界为“奴役和堕落”的世界[10]63;注重未来世界,将自由、价值、理想的实现希望寄于天国和上帝;注重人类救赎,轻漫个体私欲,注重主体感受,厌恶规则约束,将人的崇高品质归结为“自由、意义、创造性、能动性、整体性、爱”[10]32,将艺术、宗教、哲学视为解决人生、社会问题的真正途径。
俄罗斯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彰显了俄罗斯民族精神中一种可贵的气质。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为实现理想目标而奋斗。然而,俄罗斯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重理想轻现实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主义,一旦遭遇生活的拷问和民众的不满,它便会遭遇民众的抵触和拒绝。这一点,我们从苏联解体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滑铁卢”,俄罗斯宗教哲学面临的新“危机”*无论学界还是政界,其态度都在“降温”,都对它能否引领俄罗斯社会走出精神困境,表示怀疑。中便可看到。进而言之,当这种理想主义将俄罗斯文化的“传统”视为驶出现代文明苦海的风帆时,这种“传统”则在表明其保守封闭的同时,与其渴望“吸取先进”相去甚远;当这种理想主义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浪漫性”,视为脱离现代文明沼泽的路径时,这种将文学、诗歌、艺术、乌托邦与现实、世俗、生活,视如冰炭相克的“浪漫性”,则在表明其空幻化的同时,与“回归现实”的愿望咫尺天涯。
当今世界,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追求崇高和崇尚理想的传统价值取向,正面临渐行渐远乃至全面败落的命运。这一切,向今日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极具困难的课题,即如何既不被世俗文化的平面化、单面化、功利化的浪潮所裹挟,在坚守理想追求信仰中,存留一份民族精神的心性,又在追求终极、崇仰至上的同时,成为生活世界、现实生活的航标路灯,这一极具困难的课题。
三、人文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内蕴
沙俄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社会,似乎没有人文主义立足的地盘。然而,作为广泛存在“村社制度”的传统社会,俄罗斯人尤其是广大农民,又因长期生活在“温暖的集体怀抱”和融入“惬意的生活环境”,使其宗教信仰在带有集体精神特色的同时,富有人文主义色彩。至于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们,则毫不崇拜西方式的“冷漠的公正”,对他们来说,“人高于所有制原则”,“道德评价决定了对农奴制政权的抗议”;对他们来说,同情弱者、仇恨暴力、蔑视特权,走向民间,为民众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4]87-88,才是体现自身价值的正确选择。因此,尽管在精神层面,俄罗斯没有出现文艺复兴,“没有体验过西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然而,“人性毕竟是俄罗斯具有的特征”,是“俄罗斯思想之最高显现”,它“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道德”,也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家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而人与人之间不应是狼“而是兄弟”[4]86-87的口号,则最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俄罗斯人信仰上帝的原初激情根据所在。作为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又深受基督教人本主义的影响。视人为上帝的臣民,但又在赋予人的“原罪”的同时,将人置于原始平等的地位,并以上帝之名挖掘人的生存、发展价值,是基督教人本主义的理论主旨之一。“人人皆兄弟”的基督教教义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中人文主义的契合,在彰显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对俄罗斯宗教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人文主义,体现为将“人”视为探究世界本原的重要方面,将人的精神自由、道德价值、生命意义等视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以致每一个宗教哲学家“总是透过人的内在生命来研究外部现实,以‘从深处’、‘从内向外’的眼光看待世界”[3]前言3,体现为将人的心灵视为外部世界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体论的基础。为此,它认为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文明是“野蛮”文明,“给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世界观以及人和文化的人道主义理想,带来了可怕的打击”,因而“就其本性而言,是反人道主义的”[11];它指责科学技术是割裂人与世界的罪魁,“只证明了一切‘进步中的’人类所达到的目光狭隘、麻木不仁和冷漠无情”[12]192-193;它认为科学因其“不能解决心灵的所有的疑问”,因而“在理论思维领域却几乎没有任何建树”[13]。为此,它要求文化“赋予人类以生命本身的内在内容”,与人类生命建立“与活生生的精神的有机联系”[14];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能帮助人们“寻找人的精神家园、确定历史发展的新方向”,能使人成为“自己的生活的创造者”,永远告别那“把人变成螺丝钉”的“唯物主义”。[9]338
俄罗斯传统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无疑充满了对人的深切关怀。这一点,使得它无论对于人类认识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还是对于人类认识现代性的弊端,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当这种人文主义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人本性”,视为祛现代文明、科学理性的利器时,这种视传统文化为精神文明、人文精神而视现代文化为物质文明、科学理性的“二分”理论,则在表明其褊狭的民族心态的同时,与其“多元文明”的初衷渐行渐远。而它浓厚的前现代化色彩,则无论对于正确认识人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关系,还是对于正确理解人的精神世界本质,都明显具有局限性。
当今世界,尽管传统的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现代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围猎”面前,似乎不堪一击,甚至面临崩溃的命运,然而,以现代文明、现代民主为特质的现代人本主义,又不能不以现代的科学理性托底。因此,对当代俄罗斯哲学而言,如何在弘扬传统人文精神的同时,正确看待以现代人文价值为核心的现代科技理性,如何在批判传统工具理性的同时,吸取以现代科技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人文主义元素,在实现人文价值性与科学理性的融合中,提升俄罗斯哲学传统人文主义的水平,是它不能不面对的理论考验。
四、救世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底色
与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理想主义相伴随的,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救世主义,“如同欧洲的民族一样,弥赛亚说也是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4]32,它既是理想主义的延伸,又是宗教情结的折射。这种源于“第二罗马,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拜占庭帝国陷落之后,一种意识——意识到俄罗斯、莫斯科政权是保留着世界上唯一的东正教的政权和俄罗斯民族是东正教信仰的唯一承担者——在俄罗斯民族中苏醒过来”[15]的救世主义,强烈关注人类命运,视俄罗斯民族为上帝的选民,认为俄国是“唯一负有使命而否定整个欧洲的国家”[16],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民族负有拯救人类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在俄罗斯历史上绵延千余年的救世主义,到19世纪成为贯穿俄国思想史的主线,为俄罗斯文学抹上了浓墨重彩。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世界文学巨匠的作品中,无不表现出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注的救世情怀,弥散着“对拯救全人类的艰苦思考”[17]气息。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情怀,同样“呈现出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的某些特点”[4]58-59。
在俄罗斯传统哲学中,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救世主义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它要求“从宗教的高度俯察人世”[18]135,认为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使人“加入上帝的生命、人在上帝的生命之上确立自己的生命”[12]193-194,唤回人类精神中最宝贵的精神——人的自由的实现。而它强调只有弘扬东正教理想,才是摆脱西方的科技、社会、生态等消极后果,才是拯救世界唯一良方的理论,则是对俄罗斯宗教哲学中“救世主义”最为集中的折射和最为充分的体现。当这种救世主义与宗教意识相逢时,它便在“寻找上帝”*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尼·别尔加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瓦·罗扎诺夫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家发起的新宗教运动,揭开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序幕。而他们出版的《路标》和《自深处》文集,则在由反对暴力、呼吁放弃乌托邦思想、强调精神新生中,转向了呼唤上帝,从人的内心深处与上帝对话,以寻求心理解脱。中,致其哲学在传承俄罗斯文化浓厚的宗教传统之时,使救世主义与宗教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结合形式,即无需外部物质力量而只需内在精神自由,便可以实现人类的救赎。于是,“白银时代富有叛逆精神,寻找上帝,热衷于美,就是今天它也不会被遗忘。……这最好地说明了传统得到了继承”[19]。当这种救世主义转向对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时,它便在反映俄罗斯民族心智特点的同时,表达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通过“俄罗斯向何处去?”的拷问,而体现了拯救俄罗斯的使命感。
俄罗斯传统哲学中的救世主义,既是俄罗斯民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感、使命感的体现,又极易沦为大国沙文主义的理论温床,“成为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9]136和心理依据。在俄罗斯历史上,俄国军队大败拿破仑大军而拯救欧洲,苏联红军战胜纳粹德国而拯救世界,这类历史功绩既强化着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怀,也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扩张心理注入了养分。因此,历代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二战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战略,实质上都是以救世主义为根源的泛斯拉夫主义历史传统的延续。而俄罗斯哲学中的救世主义,又在无形中成为这类扩张行为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理论依据和辩护工具。例如,近代俄罗斯统治者往往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万物统一论”中,寻求俄罗斯民族在精神方面对世界的使命,自认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移至俄国。苏联时期的当权者们,也善于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统一论”“结构系统论”中,找寻苏联“老子”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子民”们的权利,“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论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20]。当这种救世主义与宗教性相结合,或具有宗教性特征时,它便极易导致自我与依附的奇妙组合、幻想与现实的急剧冲突。
当今世界,全球化在淡化和抹平地区、民族、国家之间差异,又强化和催生出新的民族主义,造就了世界多极化态势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现状。昔日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今日经济、政治、社会面临的现实困难,促使俄罗斯不得不重新审视其现实处境和在世界中的地位,因而淡化了传统民族精神中的救世主义。然而,对当代俄罗斯哲学而言,如何既肯定传统救世主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又否定和消解其扩张意识和包打天下的独尊心态,在实现所为与不为、担当尽责与尊重包容的协调中,净化俄罗斯哲学传统救世主义的内涵,是它不能绕过的坎。
五、爱国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主旋律
与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中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救世主义等文化传统相应,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浓厚的爱国主义气息,是上述特质的集中体现。由于俄罗斯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互相帮助、村社精神、劳动组合以及相应的号召并准备为共同目标牺牲”[9]336,所以集体主义是其社会精神的支柱,个人依赖于集体,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历史上的俄国,“国家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18]141,它往往作为集体的代表出现,依赖集体就是依赖国家,热爱集体就是热爱国家。因此,个人对集体的崇尚,又与对国家的崇拜紧密相连。爱集体就是“爱国家”。这个“国”,虽然随着时序更替、改朝换代而名称会变,但人们对它的热情和依恋,却矢志不移*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苏俄时期,大批俄罗斯杰出的哲学家、作家、作曲家、音乐演奏家、画家离开祖国,是出于被驱逐出境的不得已。这些知识分子们虽然身在他乡,但其作品中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念,表达的仍然是浓郁的爱国情怀。“1923年,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移民美国多年之后返回祖国;在30年代,先后返回祖国的作家有斯基塔列茨、酷普林和茨维塔耶娃”。([俄]Т.С.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36页。)。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密不可分。这就是俄罗斯人浓厚爱国主义情结的来源。
贯穿于俄罗斯历史的爱国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主线。19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思想理论上存在巨大的对立和分歧,尽管斯拉夫主义者把俄罗斯“当作母亲”,西方主义者把俄罗斯“当作孩子”,但这不能改变“两派都热爱自由,两派都热爱俄罗斯”[4]38,都关心俄罗斯的前途命运,都对俄罗斯的民族发展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都致力于寻求一条适合俄罗斯发展的道路,都是爱国主义者的基本事实。爱国主义作为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更是从古至今始终如一。从俄国古代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到18世纪罗蒙诺索夫的抒情诗《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从19世纪俄国文学大家们那些对黑暗专制的无情揭露鞭笞,对民众悲苦命运的哀思叹息,对自由的极其渴望,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到苏联时期文学家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尽情讴歌,从中都能发现和体会俄罗斯文学家们浓烈、深沉的爱国主义之情。
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占据俄罗斯文化传统主导地位的东正教“完整性”原则,不仅决定了“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价值”[21],而且“极权性和追求完整性”还成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独创性特征”[4]158。“精神完整性”“聚合性”“整体性”,这些蕴含集体主义性质的价值原则,与爱国主义可谓一脉相承,且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体现在具有斯拉夫主义思想,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优势,强调创造发展新哲学思想,应当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并将其视为创造新哲学原理关键的思想家们如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的理论中;这种爱国主义,同样体现在具有西方主义思想,但又赞同斯拉夫主义提出的建立“俄罗斯独特哲学”,并在批判西方哲学缺陷,总结和清理其积极因素的同时,致力于实施这一纲领的思想家如索洛维约夫等人的理论中;这种爱国主义,还体现在那些远离祖国但仍然对祖国充满感情的思想家们的理论中*弗兰克、别尔加耶夫等人的理论中,处处显示出这种二维特点。,他们既批判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狭隘性,又赞颂它的纯朴性,既批判西方科技理性的弊端,又承认西方文明因科学理性支撑而显现出“灵魂”是“理性的、有序的”,是俄罗斯文明走出“野蛮阶段”的必经之路[22]。因此,如同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救世主义、人文主义都有双重性一样,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同样既是民族向心力的凝固剂,又在历史上因夸大渲染其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的根源。
当今世界,全球化在淡化国家和民族之间差异的同时,也使各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面临着新挑战和新问题。然而作为俄罗斯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见证,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无论对于今日俄罗斯走向富强,还是对于当代俄罗斯哲学走向新生,都是极其重要的精神动力。因此,对当代俄罗斯哲学而言,如何在弘扬传统爱国主义的激情一面,以适应俄罗斯公众的大国情结和怀旧意识,又赋予其具有普世意义的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在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对接中,使这一精神顺应世界潮流,焕发时代活力,是它不能不探讨的问题。
[1] Галактионов А 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XI - XIX веков [M].Изд-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89:283.
[2] Кондаков И В.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M].Изд-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1997:245.
[3]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俄]尼·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Критика и эстетика[M].1979:68.
[6] 隋然.俄罗斯早期语言哲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俄语教学,2006,(1).
[7] Рамишвили Г В. Вопросы з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языка[M]. Тби лиси.:Мецниероба,1978.
[8] 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
[9] 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神人精神性基础[M].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11]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1.
[12] [俄]弗兰克.人与世界的割裂[M].方珊,方达琳,王利刚,选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
[13] [俄]舍斯托夫.深渊里的求告[M].方珊,方达琳,王利刚,选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129.
[14] [俄]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M].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87.
[15] [俄]尼·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
[16] [俄]尼古拉·别尔加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汪剑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
[17] Бердяев Н 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M].1990:63.
[18] 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9] [俄]弗·阿格诺索夫,主编.白银时代俄国文学[M].石国雄,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07.
[20] Хорос 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ерекрестке[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2,(6).
[21] [俄]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徐凤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20.
[22]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M].汪剑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1.
〔责任编辑:余明全 杜 娟〕
2015-05-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11BZX004)
郑忆石(1954-),女,浙江温岭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
B512;B976.2
A
1000-8284(2015)10-0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