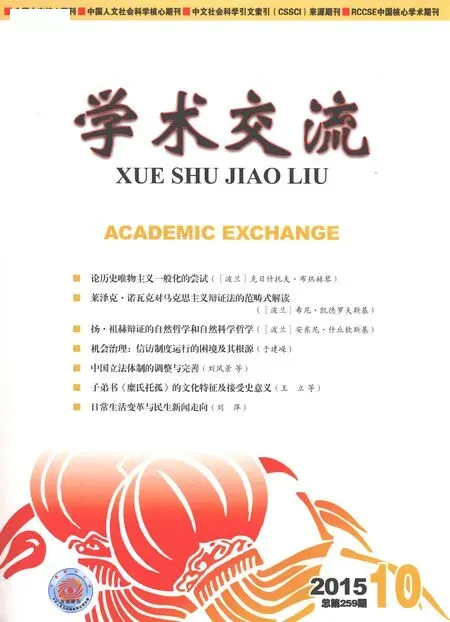莱泽克·诺瓦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
2015-02-25波兰希尼凯德罗夫斯基KrzysztofKiedrowski
[波兰]希尼·凯德罗夫斯基(Krzysztof Kiedrowski)
温 权 译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专题(三)·
莱泽克·诺瓦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
[波兰]希尼·凯德罗夫斯基(Krzysztof Kiedrowski)
温 权 译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诺瓦克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稿》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中系统地阐释了他的辩证法思想,而他在《面向一种范畴式的解读》等书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可视为一种科学认知的哲学式建构的尝试,主要方法是理想化与具体化,主要内容涉及客观性和主观性、主体论和认识论。
辩证法;新马克思主义;范畴式解读;莱泽克·诺瓦克;本体论;认识论
本文旨在概述莱泽克·诺瓦克(Leszek Nowak)的辩证法思想,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稿》[1-2]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FoundationsofMarianDialectics)中被系统阐释。《面向一种范畴式的解读》[3]亦构成本文的基础。从类型学角度看,对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categorial interpretation)似应纳入时下经典的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它既涉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关乎马列主义[4]。
一、辩证法范畴式解读的哲学假设
辩证法范畴式解读的主要来源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以恩格斯为主要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解读;本体论本质主义的相关假设。在诺瓦克看来,辩证法的一般路径依托两种假设:一是将辩证运动等同于这个词通常意义上所指的运动,即事物变化的质、量、度;二则意指辩证运动法则的普适性,一般被理解为合理性,即它应涉及这些法则的有效性范围。对诺瓦克来说,这些假设无益于修正,且导致对辩证法的庸俗理解。通过考察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的内在深层意蕴,“运动”和“普适性”概念应重新解读。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之第一个假设表明,运动无关乎事物,而是指向其本质及制约它们的规律[3]10。在第二个假设中,诺瓦克预设:“所有针对辩证法的高水准解读必须遵循两条一元性规则:其一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其二则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3]10举例来说,第一个假设意味着用以描述自然现象之本质运动的多样性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领域。鉴于此,“普适性”被理解为,对自然与社会领域的转换均适用且通过外部现实的运动法则得以描述[3]8-11。
本体论的本质主义理论发轫于诺瓦克对方法论的反思。他从60岁开始研究理想化与具体化方法,而对它们的最初使用,他则归结为马克思[5-6]。该方法只有在现实的本质被多元化且本质与现象(规律)间的关系具有可变性时,才有使用的必要。因此,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可视为一种科学认知的哲学式(辩证的)建构的尝试,其主要方法是理想化与具体化的方法。[7]
下一个议题在辩证法之本体论类型的范畴式解读的基础上与可接受性密切相关。诺瓦克采用了以下类型的本体论观点:(1)还原主义的本体论(reductionistical substantialism)。其作为哲学的基础,将诸事物当作唯一的本体论类型。该论点的例证是科塔宾斯基所提出的具体主义(reism)[8]。(2)普遍主义的本体论(universalist substantialism)。这里能够标识出至少两种基本的本体论形式,其一就是诸事物。(3)还原主义的反本体论(reductionistical antisubstantialism)。只有一种本体论形式至关重要,但并非诸事物(譬如罗素的事件主义[eventism][9])。(4)普遍主义的反本体论(universalist antisubstantialism)。至少承认两种本体论形式,事物从它们当中衍生出来。
这表明诺瓦克的本体论是立足于辩证法范畴式解读之上的集合论的本体论(一种普遍主义本体论的变种),该观点认为所有的本体论形式,特别是诸要素(量[magnitudes])、事实(情境)、关系以及性质,都能被还原为特殊的项和相应的集合。诺瓦克认为,该论断对集合论之本体论的接纳实则是通过接受当代标准的经验科学而实现的[3]19-31。
正是以上假设才使得诺瓦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作出特有的解读。从这个角度看,最普遍的理论莫过于在一般意义上作为现实的结构及其运动法则的辩证法。因此,它构成标识外部现实之规律的辩证本体论与描述思想现实之运动的辩证认识论的双重核心。鉴于此,当后两者基于现实的适当领域组成辩证思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具象化结果时,即凭借外部现实与思想现实间彼此统一的假设,它们分别获得了各自的特定性,故而辩证法比本体论和认识论更具普适性。一旦以这种方式进行解读,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法,或简称为辩证法,便构成主观性与客观性范畴之结构与变化的理论。
倘若外部现实包含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辩证本体论就构成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如此一来,遵循社会现实与自然现实彼此统一的假设,我们不得不囿于一种确定、普遍且被标识的唯物主义框架。一方面,基于自然现实或社会现实,它涉及对客观辩证法理论的解读;而另一方面,它还是对本体论的“非辩证”理论(自然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适当诠释。因此,上述提及的法则捕捉到了客观的自然与社会范畴之共同结构与动态。由给定现实的特定性所探寻的领域的补充则是系统阐述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3]37-40。
按照类比方法为诺瓦克所发展的学科层次构成辩证的认识论。它的具象化最终形成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对于这些学科而言,它们都揭示了与经验性学科(自然科学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共有的核心(自然知识的辩证法,社会知识的辩证法)。只有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具有合法性,对辩证认识论的研究在诺瓦克看来才是对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必要完善[3]40-41。
二、客观性范畴
(一)客观性范畴的结构
除客体概念(一种个体性客体,事物)之外,对于客观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而言,它隶属于要素与作用的概念。从集合论的本体论出发,要素(量)意味着从被确定关系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一系列客体中抽象出的类(类的共同体)。[1]48-49一旦假定要素概念,现象就能通过一种给定的属性而被描述为诸多属于量变范围之子集的关于客体的值(程度)。另一方面,作用(本质性)的概念被直观地界定为“倘若要素A的变化导致了要素B的变化,那么要素A无疑对要素B发生作用”[3]52,该作用通常与已被描述的要素之范围相关联。给定要素的范围是所有以确定程度拥有该要素的客体之集合,并且,在确定范围内,关于给定要素的诸本质性要素范围,是在给定要素的范围中具有作用(本质性)的诸要素之集合。与此同时,基于作用的强度,本质性要素的场域也被组织起来。如此一来,对给定的要素而言,就形成了具有不同作用强度的要素层次,该层次在确定的范围中被视为关于给定要素的一种本质性结构。具有同等本质的诸要素之特定层次,乃是本质的层次。从中可以区分出只包含对给定事物而言最为本质性的要素(关键要素)的内在层次和容纳所有在本质层次中的第二性要素(次关键要素)的表观层次[3]52-55。因此,现象的本质就是所有关键要素的集合,后者以给定的属性,凭借该属性范围内的客体,产生一定程度的作用。总而言之,一定范围内给定要素的本质性结构,可视为对彼此等价的本质关系进行抽象的类的集合。例如,在范围Z中要素F的本质性结构(一系列要素之本质的层级化对于范围Z中的属性F是本质性的)如下[3]55:
(k-1) H1, …, Hn, pk
……………………………
(1) H1, …, Hn, pk, …, p2
(0) H1, …, Hn, pk, …, p2, p1
此处(k)是本质性的内在层次,(0)是表观层次,Hn是关键要素,pk是第二性要素。
存在可资选择的不同的本质性结构:(a)等价——要素的集合与其本质性次序相同;(b)基本相似——内在本质(关键要素的集合)相同;(c)基本不同——作用于其上的关键要素不同。
彰显了符合相应现象之要素层级的本质性结构,是客观性范畴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规则性结构所揭示的在诸要素与该现象的程度性特质之间出现的附属区域,以下是其确定序列[3]71-74;[1]56-58:
(fk) F(x) = fk(H(x)),
(fk-1) fk-1(H(x), pk(x)) = gk-1[fk(H(x)), hk-1(pk(x))],
………………………………………….
(f0) f0(H(x), pk(x),…, p1(x)) = g0[f1(H(x), pk(x), …, p1(x)), h0(p0(x))]
如果x∈Z(程度F的范围),那么上述提及的要素F的本质性结构就被假定了(对事物关键性要素之集合界限的简化)。当(f0)被视为表观的附属区域时,附属区域(fk)作为一种内在的附属区域,等价于范围Z中的程度F的规律,并且它仅代表一种在给定范围中关于确定属性之关键要素的作用。至于之后的附属区域,则揭示了该规律以何种方式通过次关键要素的作用得以调节。因此,仅次于关键要素H的次关键要素pk,在作为规律(fk)的首要表现形式的公式(fk-1)中得以考量。与之相反,新要素的作用通过两种函数被揭示:校正性函数(hk-1)揭示了有关程度F的次关键要素pk的作用,方向性函数(gk-1)则表明关于程度F的次关键要素的作用以何种方式调节规律。进而可得出,取决于表观附属区域(f0)的附属区域,具有相应的类比性结构。在确定范围内,对给定程度具有决定作用的上述附属区域的序列于该范围中形成了对这一程度的规则性结构。
上述观点赋予辩证法的传统概念以重要的特征,即什么是个体性,什么是特殊性与一般性,以及什么是与个别客体等价的个体性存在。此外,就什么是特殊性而言,一种解释将属F(genera-F),即在程度F范围内的诸客体之集合,视为被决定的某一本质性结构[1]60;与此同时,对于什么是一般性来说,种F(species-F)是“在程度F范围内所有客体的集合,它以同等的关键性要素,相对于各种本质性结构的种类”[1]60。综上可知,如果从属于相同种F的不同属F具有不同的次关键要素之集合,那么对程度F产生作用的不同种F,其关键性要素的集合也不尽相同。
与客体的某一种类以及与之相应的规则性结构相对,本质性结构组成确定现象的客观性范畴。它揭示了何为关键与第二性要素,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客体的某一种类,而后者无疑呈现为一种给定属性的恰当值。因此,对现象之完备知识的诉求意味着在标示出这些客体要素的决定性层次的同时还要揭示这些要素针对给定现象的作用方式(规则性结构)。
(二)客观性范畴的运动
通过对上述关于现象之客观性范畴概念的采纳,可以认为区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节点首先被现象之客观性范畴的变化所承认。鉴于此,变化除涉及纯粹的现象之外,还指向决定它们的规律。形而上学预设规律结构的恒常性,如此一来,规则的非历史性铁律就钳制了世界(现象)的变化性[3]103-109。
变化性观点使处于恰当的本质层次之现象、本质性结构及附属区域暂时相对化。于是,从现在起,对变化性问题的探讨,能够指明隶属于给定存在的暂时性环节。
在时间段t~t+1中,能标识出两种关于给定程度的变化[1]77-80。(1)活动。鉴于现象的本质性与规则性结构在t或t+1时刻相等同,变化就只与程度F相关联。(2)本质性变化。程度F的变化与现象之本质性结构的变化相关联。①量变。立足于次关键要素范围内的本质性结构的转变,即它们的集合不是扩大就是缩小,或其与次关键要素的作用强度的变化相关联。②质变。与关键性要素范围内的变化相关联。a)质变形式一,至少一种在时间t中关于程度F的关键性要素在时间t+1中成为次关键要素;b)质变形式二,时间t中任何一种关于程度F的关键性要素都不是时间t+1中的关键或次关键要素。
根据上述研究,由于辩证法的主体是本质性变化,形而上学的主体就是诸运动的事件。
从理解变化概念的方式来看,现象的客观性范畴要经过两种样态的形变:发展和改变。客观性范畴的发展构成次关键要素之集合的变化,即除内在层次外,至少有一种本质性层次发生变化。于是,该本质与这一给定范畴的规律在t瞬间与t+1瞬间彼此等价;然而,在t~t+1时段的变化之下至少有一种形式的规律表现样态。利用此前的术语,在t瞬间与t+1瞬间符合给定现象的本质性结构基本相似。可见,客观性范畴的发展构成一种量变的等价物[3]111-125。
可以区分出下列关于范畴发展的形式:扩张(t瞬间的本质性结构通过一种附加的次关键要素在t+1瞬间得以丰富,后者比t瞬间的结构具有较少的本质性),缩略(通过t瞬间本质性结构之本质的最低层次,t+1瞬间的本质性结构愈发贫乏),以及绝对的转变(t+1瞬间本质性结构的次关键要素之集合或序列处于变化状态)。对范畴外延的恰当组合,是倾向于扩张抑或缩略的改变[3]119-122。
作为客观性范畴运动的次重要形式,改变构成一种给定现象的本质的变化。在瞬间t至t+1中的范畴的本质性结构也因此而大相径庭。我们区分出两种形式的改变:改变形式一,在t瞬间,它至少存在于一种关于范围Z内的程度F的本质性要素之中,且t+1瞬间仍然具有该程度的本质性(由于t瞬间与t+1瞬间的本质性结构的内在层次不同);改变形式二,t瞬间与t+1瞬间的范畴之本质性结构完全不同,即它们不具备共同的要素[3]125-132。
客观性范畴的运动被理解为发展或改变。发展被视为一种弱转变,这是由于现象的核心在变化的过程中保持恒定,且决定它们的规律也是如此。而强转变则使其成为本质性结构之内在层次的其他内容,和与之相应的其他规律。在这些改变中,人们能够进一步区分出具有历史性特质的变化,其中不断变化的范畴之各种本质性结构拥有一种共同的元素(要素),而非历史性特质的变化在这里也与一种给定现象的要素之本质性集合的所有交换相等同。
对每一个范畴的转变,人们能冠之以不同的类别(发展或改变)。t瞬间原初范畴的分裂(质的分离)被我们称作诸范畴的类别并出现在t+1瞬间,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原初范畴的转变。在t+1瞬间的一种范畴集合具有一元性的情况下,我们讨论退化的分裂。与退化的分裂相对立的范畴的分裂意味着在时间段t~t+1中某一范畴之本质性结构及其规则性结构的变化[1]95-96。
客观性范畴之运动的一般性历史是同一原初条件下的所有范畴之转变序列的集合,而范畴转变的个体性序列则被视为一般性历史中给定的局部性历史。对一般性历史而言,直到所有分离的部分都严格对立,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反例则是无规律的历史。倘若一般性历史的所有部分趋于退化,其临界个案是普适性历史。这种历史(退化的)只包含一种局部性历史,其中现象的本质性与规则性结构不发生任何变化[1]97-99。在这种情况下,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显而易见。按诺瓦克的说法,形而上学宣称所有的一般性历史都是退化的,而辩证法则认为至少有一些一般性的历史是真实且非退化的。
客观性辩证法为任何要素的普适性历史提供了运动的法则。鉴于此,一些一般性的历史不具可能性,换言之,它们与对辩证法基本法则的范畴式解读相违背。客观性范畴运动的法则有两种形式,不是对客观性范畴之运动的描述(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法则,否定之否定的客观法则),就是揭示该运动的作用机理(普遍运动的法则,矛盾的普遍性法则)。(1)对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之范畴性解读,表明一种范畴的变化在时间上先于一系列范畴的发展。如果我们把客观性范畴量的变化(范畴的发展)称为范畴的进化式转变,而把质的变化(范畴的转变)称作革命式转变,那么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则证明范畴的进化式转变实际上导致了范畴的革命式转变。举例来说,作为一种结果,它只排除了构成发展(进化式转变)或转变(革命式转变)的所有一般性历史。当以这种方式解读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时,在作为转变的原初范畴的第一种改变中,它通常无法以一般性的历史形式存在[1]105-106。一般性历史运动的下一条法则是否定之否定的客观法则。出现在所有一般性历史之每一局部历史中的适当转变,是该转变的第一种形式。因此,范畴的非历史性改变是没有可能性的,所有客观性范畴实际上都是先于范畴的本质性要素的变化。上述规则决定了所有一般性范畴的基本历史图景:它们构成一系列最终是转变的第一种形式的原初范畴之发展,后者随后又成为一系列范畴的发展以及第一种形式的转变,如此等等[1]106-107。(2)另一方面,普遍运动的法则表明矛盾是范畴改变的基础。这里,我们区分出内在矛盾与外部矛盾。当现象被彼此对立的关键性要素决定时,它就是内在矛盾。一种要素的作用越强劲,另一种的作用就越被削弱。一旦经过一个确定的临界点,次关键的要素就转变为一种从属性的存在。外部矛盾指的是通过彼此对立的从属性要素对给定现象产生的作用。与之相反,决定性因素的可变性导致在从属性要素范围内本质性结构的变化。由此可见,内在矛盾引发质的变化(一种给定的客观性范畴之转变),而外部矛盾则导致量的变化(给定客观性范畴的发展)。普遍运动的法则连同矛盾的普遍性法则引出如下结论:所有客观的历史都包含一种矛盾性的范畴,因此,它必然处在运动当中。鉴于此,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1]108。
三、主观性辩证法
(一)思想性范畴的结构
辩证法的第二部分涉及认识主体(探究者)的认知能动性,后者旨在对现象进行解释。而任何解释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具有可能性,它被理解为符号与规则的系统。以本体论集合的假设为基础,我们认为事物、关系以及要素(情境)在语言层面足以构成个体性表达、谓词乃至语句。这表明,一种特定种类的语言表达(例如个体性表达)只能代表一种特定的本体论形式(比如事物)。伴随着对恰当句法(以及本体论的)形式的选择,主体完成了对世界的结构化,这是源于人们进行基本反思的诸重要形式中的象征(在范畴辩证法的基础上它们是事物和集合)。因此,对语言(句法形式)的选择是决定被描述世界的本质与内容的首要且基本的哲学方案[1]110-113。
认识主体着手进行的下一环节,就是将表征集合与事物的程度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并建构本质分化的规则,从而指出哪种形式的程度能够对其他形式的程度产生作用。该方案为本质分化的秩序性规则所补充,后者在程度的一种确定形式中,按诸要素对隶属于程度之其他形式中的要素之作用(本质性)的强度使其层次化。因此,对于程度的某一确定层次,分化规则能够建立要素的层次性与本质性秩序的体系[1]113-114。该体系的相关方面是本体论关系的积极与消极性法则,它描述了要素间关系的可能与不可能形式,而后者则处于被研究体系与程度的不同层次当中。本质分化的法则与本体论关系的法则共同构成被认识主体所采纳的本体论观点[1]115-116。
针对认识主体,就给定客体范围内与人们兴趣点相关的本质性程度之区间而言,本体论观点构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恰当领域。对它们的考察则通过本质性分层假设的构想得以实现,后者在某一确定范围及其经验限度内是给定要素对所研究对象的作用。只有当认识主体所提出的范围未被准确确定或对作用进行了错误阐释,分层假说才会失效。在一定范围内,对人们所指认的、关于被研究的程度而言具有本质性的所有要素的建构,将产生出一种关于特定范围内被研究程度的本质性程度区间的假设性范围图景[1]117-118。本质性程度区间的图景能够存在于有关本质性要素自身区间的各种关系之中[1]118:(1)这些集合具有共同的排他性,分层假说所提出的要素都不是本质性要素之区间的元素;(2)这些集合彼此等价;(3)关于区间的图景是符合该区间自身的一个子集;(4)本质性范畴的区间构成其图景固有的子集,本质性要素之后往往是非本质性的要素。
在下文中,基于假定性要素之给定层次的作用强度,本质性程度区间的图景经过了层次化。鉴于此,认识主体草拟出受制于经验限制的秩序性本质的假说。经过审度的秩序性假说产生出一种关于形式之确定范围中被研究程度的本质性结构图景[1]118-119:
(n) B
(n-1) B, qn
……………………
(1) B, qn, …, q2
(0) B, qn, …, q2, q1
在个体性语言构成的该结构之本质性层次中,(n)是内在层次而(0)是表观层次。
本质性结构的图景与该结构自身的关系可以归结为[1]119-120:(1)彼此等价,这必须具备假定性范围与真实范围相等同、本质性要素区间的图景与该区间自身相等同、图景的本质性秩序与该区间相同这三个条件;(2)基本相似,本质性结构的内在层次(关键要素的集合)等价于其图景的内在层次;(3)基本不同,本质性结构与其图景具有不同的内在层次。
需要补充的是,被认识主体采纳的本体论观点决定了整个本质性结构之图景的类型,也即本质性分化图景的给定层次与本质性假设的层次彼此相应。既然本体论观点是哲学反思的结果(一种先验特质),那么本质性结构之图景就在认识主体的本质性假设所设定的经验性体验的基础上被产生出来。
本体论观点对哲学界限的正确设定,不只是为了构想出能够建立本质性结构之图景的本质性假设,更在于提出有关存在于本质性之特定层次的要素之间关系的假设。这一理想化论断采取了一种条件性形式[1]122-123:(t) U(x) ∧ q1(x) = 0∧…∧qn(x) = 0 → F(x) = knB(x)。其中,U(x) 作为一种现实性条件表征本质性结构图景的范围,而qi(x) =0则是理想化假设。理想化假设只涉及次关键要素,并且在本质的一定层次还预示了给定要素的作用被加以悬置。这些假设具有反事实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在现实(本质性结构的表观层次)当中,所有要素都对被研究的属性起作用[1]122-123。
含有之前理想化假设的理想性观点,被近似值,即不同本质性层次中的各种次关键要素的作用在技术上(在科学发展的给定阶段)的合理还原所检验。当认识主体建构出不甚准确的关系(kn)或提出有误的本质性结构图景时,理想性观点就无法通过经验考量。现在,能够降低之前所有次关键要素的作用且具有经验确证性的理想化理论,当其之前的关系(kn)被认识主体视作规律时,它就被称为科学的法则。如果被该理论界定的关于程度之本质性结构图景与程度自身的本质性结构基本相似,则可以说理想化观点本身就代表规律,即关于法则的构想。当被研究要素的本质性结构及其图景彼此等价,就能将该理论称为法则。因此,每一个法则都是关于法则的构想,而非其他。作为科学的法则,被我们称作在一定时期内为认识主体所掌握的法则[1]123-127。
法则或其较无说服力的认识论形式涉及本质性结构图景的内在层次。逐次考虑本质性连续(低级)层次中次关键要素的作用,并且说明这些要素以何种方式在更高级的本质性层次对要素的作用进行调整,叫做具体化运作。作为对观点(t)具体化应用的结果,以下是对观点(t)的第一次具体化[1]128:
(t) U(x) ∧q1(x) = 0∧…∧qn-1(x) = 0∧qn≠ 0 →
→ F(x) = kn-1(B(x), qn(x)) = g(kn(B(x)), h(qn(x)))
h(qn(x))是一个校正性函数,它界定关于被研究程度之次关键要素的作用,而g(...)则是基于附属性要素之作用而展示法则变化的方向性函数。至少恢复了关于被研究程度之本质性要素作用的最终具体化(最后的具体化),建构出不以任何理想性假设为前提的事实性理论。
一系列科学理论为认识主体所公认,其中第一位的是科学性法则,最后一位的是事实性观点。如果第一种观点作为法则的措辞,那么我们就在谈论一种理论性方案;而当第一种观点作为法则,并且它全部的具体化分别代表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就在应对一种理论。科学理论连同本体论假设的观点构成一种理论性定位,而被我们称为一系列科学理论的科学性指向则预设了相同的本体论观点[1]129-132。
总之,以辩证法的范畴式解读为基础的认知过程生成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理想性阶段),认识主体尝试建构一种本质性结构图景,后者立足于分类性与秩序性的本质性假说之上。其次,通过建构科学性法则并对其进行具体化,人们构想出科学性理论(具体化阶段)。如果提出的理论无法解释被考察的现象,那么它将作出相应的修正。它按照所作修正的重要指向进行,也就是说,它始于不会对所有科学理论的核心造成影响的变化。因此,如果它是必要的,该修正经过下列环节:校正性函数,科学性法则,次关键要素,关键要素,以及本体论观点的预设。所有修正都意指一种新的科学性理论,而后者在对以上种种进行描述的方式中,则作为经验确证性的主体[1]132-136。
客观性概念与主观辩证法之间具有一致性,客观辩证法之本质性程度的区间、本质性结构、规律、规律的表现形式、规则性结构诸概念分别对应主观辩证法之本质性程度的区间之图景、本质性结构的图景、科学性法则、具体化、科学理论诸概念。[3]224这里并未考量借助本质性与规则性结构而界定的客观性范畴的概念。而被称为本质性结构与科学性理论之图景的思想性范畴则认为,通过认识主体,它被一系列客体(范围的图景)的假设所限定。这种理解思想性范畴的方式不仅反映出认知过程的结构,而且还指出该过程的两种基本指向:对本质性结构与被考察现象之规则性结构的重建[3]224-225。
为了说明客观性范畴与思想性范畴之间的关系,诺瓦克指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区别。代表规律或其(除了表观层面的)诸表现形式的陈述叫做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则是代表表观的表现形式的陈述。以上界定伴随着相对真理的多元性和绝对真理的唯一性。绝对真理指出关键要素及其对被考察现象的作用方式,然而,通过具体化,它们必然被次关键要素及后者的作用所补充。相对真理则是法则或对法则的构想,它是与绝对法则相对立的事实性理论,即法则最终完全的具体化[3]226-228。
对思想性范畴而言,当且仅当本质性结构图景与该结构自身相等同、范围与其图景相等同,并且所有关于科学性理论的观点表征一种对规则性结构的适当依赖时,它才是对客观性范畴的一种观念性忠实反映。以上关系将导致如下结果: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相同形态出现在具体化关系与表现关系之间的法则,该法则是相对真理,而事实性的观点则是绝对真理。但是,观念性忠实反映的关系只构成思想性范畴与客观性范畴的理想性关系。关于忠实反映的关系则更具有真实性,其中,本质性结构图景只与结构自身,以及科学性法则和给定规则结构的规律基本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性法则是关于法则的构想(而不必然成为法则),而事实性理论也不必然成为绝对真理,如此等等[3]228-230。
一旦预设了观念性忠实反映的关系,思想性范畴的结构与客观性范畴的结构就彼此等价。鉴于此,如果人们假定知识主体是能够完全建构思想性范畴的独立的认识主体,那么其所建构的理论,就能复写出现实自身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性能够对理论的内容与结构产生影响。而该情况,则是真实认知过程的中立且理想性的模型。
(二)思想性范畴的运动
对思想性范畴之运动的考察涉及时间(理论表述的阶段性),后者是对前一阶段的抽象。由于与之前理论的事实性观点相左,对素材的积累将引发相应的修正。在之前的时间T、之后的时间T’两种理论之间存在两种形式的关系,即根本的一致性关系和派生的一致性关系[3]231-234。在根本的一致性关系中,后一种理论立足于一系列相同的关键要素及其相应的法则,而次关键要素和以其为基础的法则的具体化则是变化的主体,关于被考察现象之本质的观点及支配它们的规律得以维持,因此本质性结构图景在根本上相类似。至于两种理论的区别,则是认识主体凭借理想性观点所发现的规律展现形式。当T和T’理论所假定的本质性结构图景从根本上不同,它们就停留在派生的一致性关系中,也就是说,在后一种理论里,被考察程度之关键要素的集合处在变化当中。这里,T’理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构想出被考察现象的本质以及规律,但在涉及的本质性要素里至少有一种应当在之前理论的本质性结构图景的框架中予以考量。凭借辩证一致性的概念,能够理解根本一致性与派生一致性之间的关系。
就之后有关思想性范畴之概念的理论之间所具有的上述关系而言,人们能够指出变化的两种形式——发展和转变[3]234-241。对于思想性范畴K的发展而言,我们把由范围的后一种思想性范畴图景所假定的思想性范畴K’称作之前范畴之范围图景的一个子集,与此同时,构成思想性范畴K’的科学性理论从根本上与前一阶段的科学性理论保持一致。而思想性范畴K能够以两种方式转变为K’,转变形式一以前后理论间派生的一致性关系为基础,转变形式二则不以前后理论的辩证一致性为基础,二者的不同首先应归结为前后思想性范畴的本质性结构图景在根本上是有所不同还是完全不同。因此,在被考察程度之本质性要素的范围中,基于一种连续性,转变形式一具有历史性特征;一旦后一种思想性范畴与之前的思想性范畴趋于完全分离的状态,转变形式二则被视为一种非历史性的改变。
理解了思想性范畴之改变(变化)的发展或转变的内涵,我们就能说思想性范畴的运动构成其转化为他者的基础。处于占主导地位的认识主体之认知过程中的该运动,最终为各种客观性范畴所激发。对于真正的认识主体(历史性主体)而言,客观性范畴的运动不单是对思想性范畴的转变起作用的要素,纵然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3]239-241。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给定的思想性范畴而言,其转变的属性具有一种完整的层次。这些转变能够同时被客观性范畴自身的运动以及认知理性所激发,譬如作为尝试对之前思想性范畴进行修正的结果。我们将之后观念性范畴的分层称为思想性范畴的分裂,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思想性范畴的转化。当一种思想性范畴只转化为一种其他范畴时,称为退化的分裂[3]242-245。
对于一种共同的原初范畴而言,我们把思想性范畴转变的所有序列称为有关程度F(思想性历史F)的思想性范畴之运动的一般历史,而转变的个别形式则是给定的一般历史之局部的历史。思想性历史的任何更为深刻的区别都与之类似,而后者则被视为客观的历史。故当一般历史不包括任何退化的分裂时,它便有规律可循;否则我们就是在讨论一种无规律的历史。无规律历史的一个特例,是一种包含局部历史的思想性范畴的普遍历史(退化的)。真正的历史则涵盖非退化的局部历史。
在理想的认知环境中,思想史的结构与主观性历史的结构具有相同的形式。也就是说,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对思想性范畴的转变以客观性范畴的适当转变为前提。如此严格的适当性以明显的排他性的形式存在于认知过程之最为理想的形式中,并且它还符合客观辩证法之法则的类比性(量变到质变的主观性法则,否定之否定的主观性法则)。因此,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只能接受以下形式的观念性历史,其中,思想性范畴的任何转变都以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发展为先导,此外,唯一能被接受的转变,都是第一种形式的转变。鉴于此,每一种思想性历史都具有历史性特质,这就意味着所有理论之间都具有彼此一致的(根本的或派生的)辩证关系[3]250-253。如此一来,就不单是思想性范畴的结构与客观性范畴的结构相等同,而且是这些范畴的发展也彼此同构。其有力佐证,是关于思想性范畴、客观性范畴以及客观与主观辩证法的法则之运动的类比性概念。这样,对存在与思维相统一理论的范畴式解读就能被理解了,我们可以从以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中找到答案:“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译者注。
四、辩证本体论与辩证认识论
对辩证法的建构是众多理想性条件的要求。它们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本质,即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得以区分。对存在论与认识论特性的考察,与理想性条件的持续消解及构成辩证法范畴式解读之适当部分的较具体类型相关联。
(一)辩证本体论
诺瓦克指出三种有效的理想性条件,从而本体论的第一种类型被建构出来(客观辩证法):(Z1)物质性客体只经历本质逐渐分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属于一定种的客体,将来还会隶属于一种或多种属;(Z2)就其本质而言,物质性客体是简单的事物,这表明它们自身及其成分是关于要素之相同层次的作用的主体(它们从属于相同的属);(Z3)如果一种要素是另一种要素的本质,那么后一种要素对前者就不具有本质性[2]9-10。这些条件的陆续消解将导致本体论的第二至第五种类型被建构出来。
Z1条件的消解引发对范畴集合趋于统一的思考。在第一种类型中,范畴只作为分离——在特殊性况下它将是一种退化的分离——的主体。在第二种类型中,与转化相反的统一通常允许本质性同一。如此一来,客观性范畴的运动就构成分离或统一,并且包含统一性的一般历史,就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历史。关于本体论之第二种类型的基本理论,是关于运动之不平衡性的理论,其中,“为物质性客体所界定的各种要素,它们的客观性历史完全不同,此外,与之相关的时间也不尽相同。”[2]23历史的完全分化意味着历史的最后阶段比最初阶段涵盖更多的范畴,而对于时间性历史的非均质性而言,范畴的转变则以不同的节奏出现。因此,物质性现实的任何转变,主要构成以不同节奏出现的本质性分化。上述有关运动的非均质性观点,只有当Z1条件对Z2与Z3条件的消解持续有效时才能被给出[2]11-24。
本体论的第三种类型对Z2条件的消解使得关注以下事实的观点得以构建:客体的复杂性对本质的相关问题来说意义非凡。对于这种情况而言,相同客体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本质性结构为特征。由此,在该类型中,部分、整体及其之间关系的概念构成分析的主题,客体复杂性的问题依据其之后层次的关系被解读为决定性因素。因此,第三种类型的核心概念就成为结构及历史性结构的概念,而该类型的一个主要论断为:随着客体复杂性程度的提升,其本质性与法则性特征也就愈发变动不居[2]25-51。
在本体论的第四种类型中,条件Z3也经历了消解。与此同时,通过简化该类型,条件Z2得以重构。第四种类型构成对总体关系之辩证观点的范畴式解读。范畴间的相互作用,使该类型的基本概念成为有关体系的概念。而这是客观性范畴的范围及本质性结构互相交叉的结果。我们在此区分了封闭的体系(诸要素不产生单向的作用)和开放的体系(至少有一种要素产生单向的作用),积极的体系(至少有一种要素从单方面决定不属于该体系的要素)和消极的体系(没有要素单方面作用于体系之外的要素)。第四种类型的主要观点为,现实(普遍的样态)是兼具封闭与消极特征的体系[2]52-68。
本体论的第五种类型为自然与社会现实提供了正式的起点。所有上述提及的理想性条件在其中均被消解了,这就是呈现于此的现实性图景同时考虑范畴运动的多元化、与客体复杂性相关联的结构的发展、在本质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体系性基础这三种观点的原因所在。该类型的核心概念是世界性的历史,它囊括了各种层面的物质运动,其中体系的发展及物质运动的形式是体系性转变的结果。我们称这一具体的总体性为世界性历史的积极且真实的片段[2]69-82。
(二)辩证认识论
作为辩证认识论基础的理想性条件有本体论条件和具体的认识论条件两种形式,前者即上述Z1-Z3。这些条件的共性源自为所有认识论所假定的确定的世界观。因此,随着现实图景(第二到第五种类型的本体论)趋于复杂化,认识论的客体通常也愈加繁复(认识论的第二到第五种派生类型)。辩证认识论的第一种类型显然是上文所述的主观辩证法。一旦唯独与认知过程相符合的条件具有合法性,该类型通常就会被重新建构。诺瓦克列出四种条件,它们的消解能够使认识论的第六到第九种类型被概念化:(Z4)认识主体为自身确立的目标是只解释一种要素;(Z5)认识主体具有关于其所指认的次关键要素是如何作用于被考察程度的某种信念;(Z6)认识主体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对现象的解释;(Z7)认识主体占主导地位[2]84。
消解条件Z1所产生的结果是,对思想性范畴之转变概念的理解方式处于不断的扩展中。在认识论的第二种类型里,思想性范畴的统一性通常可以反映主观范畴之本质同一性过程。在该过程中,思想性范畴运动的历史之统一的范围通常得以扩大,此外,认知运动的结构与被认知现实的运动结构彼此等同。与运动的非均质性理论相等同的真理的具体性法则表明,就时间性而言,所有思想性历史都完全不同且彼此不同步。也就是说,有关任何时间中的所有客体的普遍性理论是不可能成立的。对经验之不同领域的认知为不同的理论所描述,它们的变化以客观性范畴的变化为基础[2]86-93。
以消解Z2条件为前提的第三种类型的辩证认识论没有产生重大的认识论结果。基于客体结构的派生性,物质性范畴也彼此区分,于是思想性范畴的第一法则适用于客体的第一层次。因此,通过逐渐被认知的结构复杂性趋于相对化,思想性结构的历史得以充实。而对条件Z3的拒绝(同时重建条件Z2)将促使对涉及现实的第四种类型认识论的建构,其中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得以显现。该情况为一种共轭理论所阐释,后者关注对他者来说具有本质性的要素。根据要素具有关键性或次关键性,我们能够探讨理论的强耦合性(所有要素都是关键性要素)、弱耦合性(所有要素都是次关键要素),或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的强关联性、弱关联性。我们称理论性体系为理论的集合,其中每两种都互相关联。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不外乎分析(对非矛盾性理论集合的建构)与综合(对独立要素的拒绝和对理论的修正),它们构成具体方法的等价物,并在建构个体性要素时使用。总体关系的本体论法则通常以真理体系法则的形式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其等价物,即,除非关于其他所有要素的真理得以确立,否则针对给定要素的绝对真理无法成立。故,真理只能在体系(理论性)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在认识论的第五种形式中,先前与世界历史相关联的被消解的本体论条件Z1-Z3由物质运动的相关形式(基于时间与结构)组成。物质运动形式之概念的认识论等价物是关于合理秩序之基本科学的概念:“一种表征合理秩序之物质运动形式的理论体系,该体系中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包含一种关于运动形式中被描述要素的绝对真理,与此同时,通过该体系中的诸理论,运动形式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得以描述”[2]101。
现在,关于世界历史知识的概念构成世界历史概念的等价物。世界历史知识由一系列基础科学所构建,其主体则是物质运动之后的形式。如此一来,科学的分类就不是一种任意性过程,而是根植于本体论基础之上。这是(辩证的)认识论假定辩证本体论的又一佐证[2]93-102。
辩证认识论的更深层结构构成对认识的理想性条件理论(Z4-Z7)之合理性的持续消解,而作为对类型的简化,条件Z1-Z3被重新构建。因此,认识论的第六种类型构成第一种类型的具体化。
对Z4条件的拒斥通过一种内在的理论性知识完善了认识主体的认知情况。仅次于本体论观点与体验,它构成相应的理论基础,认识主体试图从中提炼出被考察要素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知识无法以演绎的形式提炼出其中被考察的理论,那它只能以第一种类型中的形式来建构该理论。因此,为第六种类型所建构的理论结构不仅通过具体化的关系,而且还依托与结果的关联被描述,故而以该类型为基础,我们讨论的是理想性的复合理论。其发展的额外途径是通过塑造其他领域中的相应理论而建构一种简单的理想性理论。认识主体的最终目的(以第六种类型为基础)是提出在确定层面被考察要素之层次的理想性复合理论(不证自明的体系),并且整理出其抽象的层次。而第一种类型中简单的思想性范畴概念通常要经历具体化过程。要素层次的理想性复合理论包括一种被考察集合中要素的本质性结构图景的层次,而要素的理想性复合层次则源于被预设范围的集合。需要强调的是,在此类型中,复合的思想性范畴将不再与主观性范畴同构。但在被反思的类型中,思想性范畴运动的图景无法被修正;尽管复合的思想性范畴是变化的主体,但描述它们的规律保持其在第一种类型中的形态[2]103-119。
认识论的第七种类型以对Z5条件的消解为基础,它导致认识主体无法在有限的具体化中构想事实性观点的结果。其中,人们运用了能够构想出事实性论断的近似值运算,而后者为额外的变量即近似值的标准及其阈值所决定。与认识主体知识的欠缺相关,对作为理论之核心步骤的近似值的运用,是调节确定的次关键要素的方式。我们将简单的近似性理想理论视为理想性观点的等价物,它首先是一种法则,而后是其自身的具体化,最后是理想性观点之前的近似值。在被反思的类型中,主体认知状态的改变使人们尝试使用不同种类的近似值运算,也就是说,在人们处于本质的更高层次并作为修正理论的主体之前,他们赋予近似值的标准和阈值以不同的价值[2]120-128。
对Z6条件的消解,涉及理论科学(基础科学)之外的事实,其最终目的是解释相应的现象。实践科学致力于展现事物的理想状态,它通常认为所有充分发展的基础科学都具有与其规则相对应的应用性。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之间的基本区别应归结为前者是关于经验标准(对被经验事实的解释)的意识,而后者是有效性标准——“它们试图解释给定社会的价值如何在最高程度被现实化”[2]129。事实的精确性构成基础科学的基本标准,而对实践科学,该标准需符合为社会所决定(需要)的价值[2]129-140。
与Z7条件的消解相关,第九种类型中存在一种在知识发展问题范围内意义非凡的修正。发轫于辩证认识论第一种类型的条件,其必然结果是关于思想与客观性范畴运动之间一致性理论。对现实性的预设表明“在所有相互矛盾的理论指向中,认识主体对何为次关键要素中的确定性保持清醒的认识”[2]147,与思想性范畴的集合相一致的个别客观性范畴的运动包括以复合的近似性理想观点为基础的理论指向。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科学性过程,即相对真理向更为充分的真理的转化,而后者生发于社会实践。因此,实践的有效性将成为对被考察现象之本质进行准确认识的实践理论之基础的直接佐证。在科学中,理想性条件的消解通常导致认识主体之认知积极性的共同结果以逻辑矛盾的形式出现。进而,通过介入具有经验合理性且与真理更加接近但彼此矛盾的理想性理论,它构成科学中过程的基本要素。同时,第九种类型还展现了为第一种类型所采纳的存在与思维相统一的法则,纵然其对现实的观念性忠实反映不具有可能性,但它仍存在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以该类型为基础可知,不仅科学理论的结构,甚至其运动的法则都不是人们任意行为的结果,它们是对现实之本体论结构的反映[2]141-156。
五、结论
辩证法范畴式解读的各个方面都构成被批判的主体。在其他人那里,诺瓦克受到以下质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符合对辩证法的这种解读[11];对辩证法的“一般性”解读的批判毫无根据[12];就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形式而言,该方案的可接受性有待商榷[13];对辩证法的承认意味着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14];在分析运动的概念时,从中抽象出心理时间[15]。诺瓦克针对所提出的体系,以及他认为的对范畴辩证法来说是致命问题的共同内在类型的缺乏(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分裂),都作了相应的修正与完善。这些批判成为诺瓦克最终的体系性概念的来源之一,即消极的一元形而上学[16-18]。以上述形而上学为前提的一元论与属性论似乎是把握范畴辩证法基本内容的正确领域,并且该概念自身又是关于辩证法范畴式解读之恰当的哲学起点。
[1] Nowak L. Wykdy z filozofii marksistowskiej, tom I: Dialektyka[M]. Poznań Wyd. UAM,1976.
[2] Nowak L. Wykdy z filozofii marksistowskiej, tom II: Ontologia i epistemologia[M]. Poznań Wyd. UAM,1978.
[3] Nowak L. U podstaw dialektyki Marksowskiej. Próba interpretacji kategorialnej[M]. Warszawa: PWN,1977.
[4] Bocheńki J M. Lewica, religia, sowietologia (opr. J. Parys)[M]. Warszawa: Wydawnictwo AWM,1996:45-50.
[5] Nowak L. U podstaw Marksowskiej metodologii nauk[M]. Warszawa: PWN,1971.
[6] Nowak L. Zasady marksistowskiej filozofii nauki. Próba systematycznej rekonstrukcji[M]. Warszawa: PWN,1974.
[7] Nowak L, Nowakowa I. Idealization X: The Richness of Idealization (Poznań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vol. 69)[M]. Amsterdam/Atlanta: Rodopi,2000.
[8] Kotarbińki T. Dziewszystkie. Ontologia, teoria poznania i metodologia nauk[M]. Wrocw/Warszawa/Krakó: Wydawnictwo Polskiej Akademii Nauk,1993:101-232.
[9] Russell B.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47:861.
[10] Engels F. Dialektyka przyrody[M]. Warszawa: PWN,1979:316.

[12] Krajewski W. Voice in the Debate[M]// Kmita J. Zania teoretyczne badań nad rozwojem historycznym. Warszawa: PWN,1977:127-128.
[13] Aleksandrowicz D. “Substancjalizm” i “relacjonizm”[M]// Kmita J. Zania teoretyczne badań nad rozwojem historycznym. Warszawa: PWN,1977:129-131.
[14] Magala S. O miejsce praktyki w marksizmie[M]// Kmita J. Zania teoretyczne badań nad rozwojem historycznym. Warszawa: PWN,1977:132-135.
[15] Mejbaum W. Czas rzeczywisty i urojony[M]// Kmita J. Zania teoretyczne badań nad rozwojem historycznym. Warszawa: PWN,1977:136-138.


[18] Kiedrowski K. Zarys negatywistycznej metafizyki unitarnej[M]. Poznań Wydawnictwo Poznańkie,2010.
〔责任编辑:余明全〕
2015-09-15
希尼·凯德罗夫斯基(Krzysztof Kiedrowski,1985-),男,波兰人,哲学博士,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教师,从事辩证法及古典和现代形而上学研究。
[译者简介]温权(1987-),男,山西太原人,助理研究员、讲师,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B513;B023.2
A
1000-8284(2015)10-0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