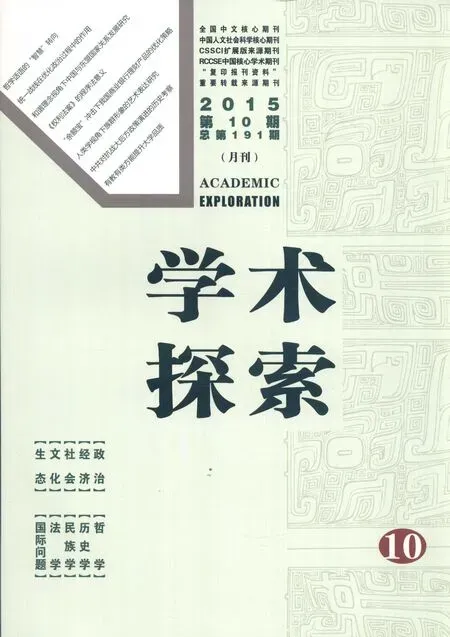《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考
2015-02-25滕汉洋
滕汉洋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考
滕汉洋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白居易任职盩厔县尉仅一年半即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由低级官吏升任清望朝官,这一快速升迁的经历不同寻常。一般认为白居易是因讽喻诗创作而为宪宗所发现并召入翰林的,但白居易此前只创作了十几首讽喻诗,也并无讽喻诗创作的自觉意识,不可能因讽喻诗的创作受到提拔。他在任职盩厔尉时期因创作《长恨歌》而名动天下,此诗所展示出的文学才华及其题材与宪宗本人关注点的契合,才应是白居易被宪宗发现并提拔的真正原因。
白居易;盩厔县尉;翰林学士;《长恨歌》
《长恨歌》作为白居易的经典名篇,其意义似乎不仅仅是为诗人赢得空前的声名,更在于对其仕途迁转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学者静永健在考察白居易《长恨歌》与《新乐府》五十首的关系时指出,《新乐府》中的《骊山高》《李夫人》《上阳白发人》等诗,都是以其之前创作的名篇《长恨歌》为样板的。他认为这是白居易在有意突出自己《长恨歌》主的身份。[1](P101)笔者以为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意义。《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白居易时任盩厔县尉。在创作了这首长诗后不久,白居易即受到唐宪宗赏识被召为翰林学士。而《新乐府》作于元和四年,白居易时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正是深得宪宗宠信之时。从这一点来看,白氏以宪宗为预设读者的《新乐府》中的若干作品选择以《长恨歌》为样板,说明白居易得宪宗赏识并被召为翰林学士很可能与其《长恨歌》的创作有很大关系。以下通过对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情况的考察,说明《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之关系,庶几有补于我们对《长恨歌》巨大影响力的认识。
一、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的相关情况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参加制举,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旋授盩厔尉的职务。但他任职盩厔的时间很短,元和二年秋即调充京兆府进士考试官,试毕帖集贤校理,十一月六日又入朝为翰林学士。在被召为翰林学士不到半年,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四月又改官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由县尉成功跃升为“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2](P20)的清望朝官。关于白居易的这段迅速升迁的经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据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志铭》记,白居易参加元和元年制举,“对宪宗诏策语切,不得为谏官,补盩厔尉。”[3](P1808)李商隐此文是应白居易嗣子白景受之托而撰,所言当有事实依据。白居易本年的制策现载其集中,其首云:“臣闻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是时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2](P2844)可见,白氏实是在效仿贾谊上书汉文帝切谏的行为。在策文中,他又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兵兴寇生、赋重人疲以及君臣异位、上下道殊等问题加以论述,以为这些都是君王政德不修、待人不诚所致,并要求宪宗“敬惜其时,重慎于事。既往者且追救于弊后,将来者宜早防于事先”,颇类耳提面命,连白居易在策文中也屡屡称自己是“狂直”“过言”。而这很可能会引起宪宗及宰臣们的不满。白氏登科后授予盩厔尉一职,恐与此有关。今按《唐大诏令集》所载元和元年《放制举人勅》: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次等元稹、韦惇,第四等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第四次等崔韶、罗让、元修、薛存庆、韦珩,第五上等萧俛、李蟠、沈传师、柴宿,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第五上等陈岵,咸以待问之美,观光而来。询以三道之要,复于九变之选。得失之间,粲然可观。宜膺德懋之典,或叶言扬之举。其第三次等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书门下即与处分。[4](P545)
唐中后期制举,第一、二等例不录人,第三等实即第一等,第四等实即第二等。按照排名的先后顺序,元稹为本年的敕头,韦惇次之,二人获得“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的待遇。其中元稹除左拾遗;韦惇当是“韦淳”之误,即韦处厚。《新唐书·韦处厚传》记:“中进士第,又擢才识兼茂科,授集贤校书郎。”[5](P4674)可知韦处厚及第后授集贤校书一职。第二等第一名的独孤郁,据韩愈为其所撰墓志,制举及第后拜右拾遗。[6](P484)以上排名白居易之前的诸人,除了韦处厚以刚刚进士及第又中制举,所以授官不高外,元稹与独孤郁排名高于白居易,任职也都好于他,这不难理解。排在白居易之后的诸人授官情况,也多可考知。其中韦庆复制举登科后“诏授京兆府渭南县主簿。”[7]罗让“应诏对策髙等,为咸阳尉。”[8](P4937)萧俛“登贤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遗。”[8](P4476)沈传师“贞元末举进士……联中制策科,授太子校书”。[9](P924)从以上排名白居易之后的诸人授官情况来看,白氏的任职与同等第的韦庆复和第四次等的罗让相当,但如萧俛是第五上等,排名白居易之后,却被授予右拾遗,则显然是第一等的待遇,要好过白居易。从这一点来看,白居易制举及第后的处分并不算好,相反,他被授予盩厔尉的职务,正如李商隐所言,一定程度上具有忤旨下放的性质。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何白居易又在短期内复受宪宗青睐并得到提拔重用呢?
其二,唐制,集贤校理、翰林学士等乃是一种兼职或差遣,白居易在元和三年被授予左拾遗之前,其系禄之官仍是盩厔尉。虽然如李肇《翰林志》所言,翰林学士“下自校书郎,上及诸曹尚书,皆为之”。[10]在白居易之前也曾经有校书郎、县尉一类低级别官员充任翰林学士的先例,但考虑到中晚唐时期翰林学士职位清贵,号称“天子私人”“内相”,仅任职盩厔尉约一年半时间的白居易即被召为翰林学士,这一跨度依然是相当大的。即从其元和三年方改官左拾遗来看,其盩厔尉的任职时间尚不到三年,这在唐中后期守选者多而官缺少,县级官吏往往有长达五年、六年乃至更长时间不得调的情况下,白居易被提拔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之快。而由县尉跃升为左拾遗翰林学士,这也是唐人十分钦羡的转任途径。如《唐语林》卷五记:“议者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11](P447)白居易由畿尉一跃为皇帝之近臣,可谓是比“佛道”“仙道”更好的待遇。而从与白氏同登本次制科并也曾有任职翰林经历的独孤郁、萧俛来看,独孤郁元和五年四月一日入翰林(后因岳父权德舆为相,为避嫌,于九月辞职出院),萧俛次年四月十二日入翰林,二人虽然制举登科后被授予右拾遗,除官要好于白居易,但入翰林却都晚于白居易。那么,白居易有何超出同侪的过人之处而受到超次拔擢呢?
综上所述,白居易先是由于对诏书语切而不得为谏官,嗣后则迅速地由县尉升迁为左拾遗翰林学士,虽然品阶提升不大,但由于是皇帝近臣,职位却比之前重要得多。白居易这段快速升迁的经历在中晚唐时代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这其中的原因,颇耐人寻味。
二、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的转任与其讽喻诗创作无关
对于白居易迅速升迁的原因,他自己并未提及,同时代的人也未留下任何记载。而《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却做了肯定回答。《旧唐书·白居易传》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阙,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8](P4340~4341)
又《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十一月”记:盩厔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12](P7646)
《通鉴》之说当是承袭了《旧唐书》的记载。根据上述记载,白居易是因为此前的百余篇讽喻诗“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阙”,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甚至流入宫廷,最终为“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宪宗所发现并加以“非次拔擢”的。
白居易受到宪宗亲自拔擢有事实根据,《新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5](P4302)
由宪宗所谓“是子我自拔擢”一句看,白居易之任职左拾遗、翰林学士,与宪宗对他的赏识有直接关系。而且白居易在得到升迁之后,也多次对宪宗的提拔任用满怀感恩。白氏后来“五年为侍臣”期间屡屡上书进言,与其说是左拾遗、翰林学士职位的使命感使然,毋宁说是对于宪宗的报恩思想使然。因此,《旧唐书》说其“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大抵符合白居易的心理。
然而《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认为白氏得宪宗赏识是因其讽喻诗的创作这一说法,恐与事实不符。首先,白居易在入翰林之前并无所谓“箴时之病,补政之阙”的意识。白居易先是于贞元十九年任秘书省校书郎,正式走上仕途,再是元和元年制举及第任盩厔尉,这两个时期的白居易或得意闲适,或牢骚满腹,并无强烈的用事之心。如在作于校书郎任上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诗中,白居易说自己的校书郎生活是:“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2](P269)与校书郎时期的闲淡无事相比,白居易“结绶畿甸”的生活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如其《盩厔县北楼望山》云:“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2](P740)《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寄》云:“低腰复敛手,心体不遑安。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2](P503)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摧眉折腰的风尘小吏形象。即使是在后来回朝任职左拾遗翰林学士后,白居易仍然耿耿于怀的回忆道:“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归家不自适,无计慰心神。”[2](P469)这些屡次的表白,代表了白居易在任职盩厔尉时期辛苦失落的真实心绪。
其次,唐人文集留存至今者,《白氏文集》最称完璧,然就目前留存的白集来看,白氏作于元和三年任职左拾遗、翰林学士之前的诗歌约有四百首,但他自己编在讽喻诗一类的仅有十余首,而非如《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所谓的“数十百篇”“百余篇”。数量如此之少的讽喻诗断然无法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更不可能形成“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的传播效果。此前的诗歌创作,白居易自己的评价也不高,他有意识的创作讽喻诗并产生社会影响实际上是在入朝任职后。关于这一点,其在《与元九书》中有明言。白居易明确树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意识是“自登朝来”,也就是任职左拾遗、翰林学士之后。另外,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会宪宗皇帝册召天下士,乐天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喜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13](P923)说明白居易早期讽喻诗的代表性作品如《秦中吟》等,也是在任职翰林学士之后创作并产生社会影响的,之前并无有意识创作大量讽喻诗并产生影响的事实。
综上,白居易入翰林后,因为对宪宗的知遇之恩满怀感激,所以“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开始有意识并集中地创作了大量以宪宗为第一读者的讽喻诗,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而此前的白居易既无强烈的讽谏意识,也无较多的讽喻诗创作实践,更没有创作出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讽喻诗名篇。因此,他受到宪宗关注并由盩厔尉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不可能是因为讽喻诗的创作。前引《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说法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三、《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之关系
据前文,白居易入翰林前既无强烈的用事意识,也无大量创作讽喻诗并产生影响的事实,那是什么使他得到宪宗的赏识并得到提拔的呢?此前的白居易“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2](P2793)其先后的低卑的任职经历亦无所谓的政绩可言,因此他不大可能靠自己的政治才干或与朝廷显贵的交往而接近权力中心。他所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文学才华。既然《旧唐书》中所谓的“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的不是白居易的讽喻诗作品,那么当是其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对此,我们不得不提到白氏创作于盩厔尉上的,为其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千古名篇《长恨歌》了。因为从社会影响来看,白氏此前的诗歌只有此篇具有“流闻禁中”并得到皇帝赏识和提拔之可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长恨歌》的题材、内涵与宪宗本人关注点的契合以及中晚唐帝王因诗文选用人才等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长恨歌》是以唐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为题材的,唐人对此事的关注度颇高,尤其是玄宗与杨妃之事,不仅史家进行记录评价,文人形诸小说、诗歌,统治阶层也并不避讳谈及此事,相反却往往将其作为探讨治、乱之源的一个极好案例。相关话题,在具有极强的中兴意识的宪宗朝廷,曾不止一次得到讨论。宪宗本人对于本朝治、乱之事颇多留意。《旧唐书·宪宗纪》上记:十二月……丙辰,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8](P423)
此事在宪宗即位初期的元和二年,所谓“朕览国书”,可见其对本朝历史的关注。元和四年七月,宪宗又“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是月,出书屏以示宰臣,李籓等表谢之。”[8](P423)这十四篇书于屏风的前代君臣事迹,想来当包括宪宗所关注的本朝君臣之事。在这其中,宪宗对玄宗朝由治而乱的发生过程尤其关注,并多次与臣下讨论玄宗朝的政治得失。如《旧唐书·李绛传》和《旧唐书·崔群传》中记载着,宪宗在位期间不仅常读《玄宗实录》,而且好言开元天宝间的政事,且主动与群臣探讨。从李绛、崔群二人所言来看,对于开天政治得失,宪宗君臣有清醒深刻的认识,而且往往引以为鉴戒,作为指导本朝政治的反面教材。以上所引李绛事发生在元和四年,崔群事则发生在元和十四年,虽然时间都非宪宗初即位时,但这种讨论也很可能发生在宪宗即位早期。李绛元和二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崔群于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以右补阙充翰林学士。这二人皆以敢于直言极谏称于时,而且颇得宪宗重视。史称李绛自元和二年入翰林至元和五年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8](P4285)崔群任职翰林期间“数陈谠言,宪宗嘉纳,因诏学士:‘凡奏议,待群署乃得上。’”[5](P5080)李、崔二人在宪宗即位早期即为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他们与宪宗可能经常讨论开天治乱的话题。宪宗处二人为翰林学士,嗣后更是经此而拜相,也很能见出宪宗的用人态度。
白居易之《长恨歌》以开天轶事为题材,一定程度上与宪宗本人的关注点是契合的。而《长恨歌》“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2](P659)的创作目的,也符合元和君臣以开天之事为鉴的历史意识。从这一点来看,作为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诗歌作品,《长恨歌》受到宪宗的关注,作者白居易受到宪宗的赏识,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次,唐代翰林学士是具有帝王私人秘书性质的官职,其职责之一就是出纳王命、撰写诏敕。因此,从唐玄宗设翰林学士始,所选之人如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所言,乃是“朝官有词艺学识者”,[14](P4684)文学才华是翰林学士最为重要的素质之一。在唐代翰林学士选任的考核中,主要的测试内容是制诏、诗赋。白居易元和二年入翰林院所考核的内容,据其自己的《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记载,包括制诏三篇,批答一篇,诗一篇。[2](P2868)可见重点考察的是他的文学才华。这说明,白居易之所以能有入翰林的机会,起码首先是其文学才华得到认可。而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因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作品得到帝王赏识并直接提拔者,不乏其人。韩翃因《寒食》诗为德宗所用,元稹因《连昌宫词》为穆宗引擢,即是显例。
《新唐书·韩翃传》记:“翃,字君平,南阳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罢,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复辟之。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时有两韩翃,其一为刺史,宰相请孰与,德宗曰:‘与诗人韩翃。’终中书舍人。”[5](P5786)对此,《唐才子传》卷二所记更为详细:德宗时制诰阙人,中书两进除目,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同姓名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15](P20)
《新唐书》及《唐才子传》中所言,本于唐人孟棨《本事诗·情感》篇中的相关记载,虽是小说家言,但唐人记此事并非一例。姚合《极玄集》中亦言韩翃“以《寒食》诗受知德宗,官至中书舍人”。[16](P551)以上可知,韩翃以《寒食》诗为德宗擢为中书舍人,实有其事,非仅道听途说。
又《旧唐书·元稹传》记: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嫔妃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8](P4333)
此处所记元稹一事本于白居易所撰《元稹墓志》,白居易言:“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2](P3738)《旧唐书》与此处所记在时间上虽稍有不同,但元稹以文学创作而得穆宗赏识并拔擢是可以确定的。
以上两例,一个发生在德宗朝,一个发生在穆宗朝,韩翃、元稹二人皆是以诗名得到重用乃至执掌王言,足见是时帝王选任秘书班子人员,文学尤其是诗歌才华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宪宗来说,他虽不以文雅著称,甚至未有一首诗歌留存于世,但是这并非说其对于文学不关注。今存唐人选唐诗有令狐楚编《御览诗》一卷,傅璇琮先生据书中所题令狐楚“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的官衔,考定此书的撰进当在元和九年至元和十二年之间,乃是令狐楚应宪宗之命而编选的。[16](P363)此书选大历至元和诗人三十家,诗二百八十九首。从这一选本来看,宪宗本人对于本朝诗歌尤其是元和朝诗人的作品是颇为关注的。上引穆宗东宫嫔妃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一事也可说明,其时著名诗人的作品甚至可以在宫廷传唱。因此,白居易之产生巨大影响的《长恨歌》流入宫廷也就是完全可能的,宪宗可能就是因此而发现了白居易并提拔他为翰林学士的。
综上,笔者以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元和元年十二月创作于盩厔尉任上之后,迅速产生影响,再加上有陈鸿《长恨歌传》一篇与其并行,其传播的速度应是相当快的。且盩厔作为畿县,离政治中心的长安非常近,《长恨歌》在完成不久之后即可能传入长安。那么这首取材本朝事的长篇歌行,既表现出了诗人的出世之才,又与宪宗本人对于开天之事的关注相契合,其流入禁中,得唐宪宗注意也是完全可能的。而白居易不久后就由于宪宗的拔擢由盩厔县尉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当与其因《长恨歌》创作所获得的巨大声名有关。
[1]静永健.白居易写讽喻诗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安迪.韦应物一家四方墓志录文[N].文汇报,2005-11-04(8).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
[9]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洪遵.翰苑群书[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14]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erlasting Regret and Bai Juyi's Promotion to Hanlin Academ ician
TENG Han-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Yancheng,224002,Jiangsu,China)
BaiJuyi‘s promotion from deputymagistrate of ZhouzhiCounty to be a Hanlin Academician took noly one year and a half.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his promotion was due to his satirical poems being discovered by Tang Xianzong.In fact,Bai-Juyi had had no conscious idea to write satirical poems and had only created notmore than a dozen before his promotion.On the contrary,itwas his creation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when he worked as the deputymagistrate of Zhouzhi County thatwon him great fame.This poem displayed Bai Juyi's brilliant literary talent and the theme it expressed corresponded with Xianzong's then attention,which is the real reason of Bai Juyi's promotion.
BaiJuyi;the deputymagistrate of Zhouzhi County;Hanlin academician;The Everlasting Regret
I207.22
:A
:1006-723X(2015)10-0097-05
〔责任编辑:黎 玫〕
滕汉洋,男,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隋唐五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