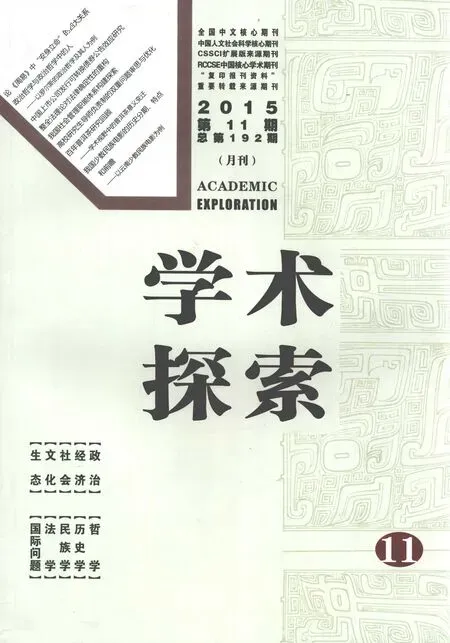晚明园林文化与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2015-02-25李玉芝
晚明园林文化与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李玉芝
(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摘要:晚明园林文化从着重道德伦理的追求到闲雅自适的自我超脱,从素朴的自然园林到追求奢靡世风的富贵园林,从幽远静谧的山泽湖滨到喧嚣热闹的市井社会。园林文化是文人审美心理的重要载体,晚明园林文化的变化直接反映了晚明文人在审美心理上的变化:对物质欲望的追逐和及时行乐的末世心态。晚明文人在审美心态上的变化使得晚明成为中国古代园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关键词:晚明;园林文化;审美心态
作者简介:李玉芝,女,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
晚明是园林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一个转折期。这个时期,文人在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从外到内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反映在文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园林文化上。晚明时期的园林文化关注个体的价值,具有鲜明的世俗生活色彩,可以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体现,这和晚明社会对享乐和休闲生活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一般是“仕”和“隐”。隐居与出仕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两面,“出”与“入”对于他们来说,一直是个颇为艰难的选择题。从唐代的白居易开始,文人可以说找到了调和的办法,即“中隐”,或者说是“通隐”。“中隐”的说法来自唐代白居易的同名诗歌《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园林可以说是文人“中隐”生活的最好载体,而文人园林发展和唐代文人的“中隐”思想有密切联系,后来又历经宋元的发展,尤其是在元代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文人大多在政治上难有作为,或隐于艺术,或是耕读隐居,或者是大隐隐于市。文人远离政治的同时,在园林文化中可以说是找到了精神栖息地,而元代尤其是元代末年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兴盛期。
明代初年,园林文化一改元代的兴盛态势,整个园林文化走向岑寂。究其原因,一是战争的破坏,使得元代很多著名的园林都成为废园。比如江南名园钱氏南园,其传到元代已经历经百年,这个时候也因为战争的原因成为废园,诗人高启就有诗作《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专门缅怀这座曾经历经百年沧桑的江南名园。二是政治原因。太祖时期颁布了《营缮令》,对造园的规格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明史》卷 68《舆服志》)在历经洪武、永乐朝的严酷统治以后,明代政治进入“仁宣之治”,这个时期朝廷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开始实行宽仁的德政。这体现在园林文化上,首先是明代初年颁布的“营缮令”随着两京大规模地修建宫廷园林而变得名存实亡,由于园林文化的兴盛,园户甚至成为工匠户中的热门。其次,尽管重农抑商一直是国本,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文明的发展,商业文化的发展已经不是朝廷颁布几纸诏文就可以控制。在城市商业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文人的人生选择上也有了更多方向,加之明代科举道路随着科举应考人数的大量增加变得异常拥堵,不少文人都自觉选择闲居园林,或是醉心禅道,或是醉心艺术,总之,出仕不再是文人的必然人生选择,尤其是“仁宣之治”后,明代政治环境逐渐恶化,园林隐居成为更多文人的自觉选择,园林文化也因为文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再次兴盛,其发展到晚明,可以说是达到极盛。一方面园林是文人致仕后显示声望和影响力的完美地方,另一方面,明代社团众多,其活动基地多是在私家园林中进行,著名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私家园林中进行。这一时期园林的位置和功能也发生了不小变化,文人的身份角色定位也借此发生转变, “进”可以打开大门迎客,这时候园林作为文人社交文化的中心,可以借园林及其文化活动提升社会声望;“退”,文人可以关上园林大门,在艺术活动和清玩古物中优哉度日,晚明可以说是明代园林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
一、明代园林文化的变迁
(一)君子攸居到逸乐之园
明代初年由于朝廷对士人道德的严格要求,文人造园一般都有一个雅正追求,或者说是必须有一个符合道统的追求,其多为耕读、致学、养亲等。园林的题名上也显示文人向传统园林审美趣味的回归。这个时候的园林主人大多是有志于躬身耕读的高洁之士,其园林题名多是要含蓄表达文人隐身山野的高风亮节,所以或是从稼穑、渔猎、耕读、修身、养亲等方面选题立意,或是以菊、梅、松、竹等主题植物来象征其高远志向。以苏州如意堂来说,其筑园目的就是园主杜琼侍母尽孝之用。汤克卫修建奉萱堂的目的和杜琼的一样,是为回报母亲:“其父曦仲早世,母李(氏)鞠之成人,克卫既克有立,且幸母之寿康,乃作堂以备养颜之”。[1](P168)(徐有贞《奉萱堂记》)还有常熟人陈符的驻景园也是侍亲之用:“诸子恭勤孝养,营园池,杂植花卉奇树,作二亭其中,以奉之翁”。[2](P318)(吴宽《瞻竹堂记》)吴门画派的第一代领袖沈周家资殷实,但是其园林“有竹居”却是朴实无华:“近习农功远市哗,一庄沙水别为家。墙凹因避邻居竹,圃熟多分路客瓜”。[3](P662)(沈周《乐野》)正是因为明代初年对园林文化的追求大多是有着雅正的道德意蕴,所以其园林多为自然之园,其中孕育的是自然宁静的审美气质,在园林境界的追求上更注重宁静致远的审美风格。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晚明时期,园林文化的核心在经济富饶的江南地区,这个时期的江南园林没有北方园林一览无余的开阔与放达,又大都是城市园林,讲究的是造景设计上的精巧与细腻,在审美追求上自然多了几分深远的曲径幽深之美。在园林建造上,叠石成山是大部分江南园林必备的功夫,以致叠石师傅在当时大受欢迎。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当时主持造园的很多都是当地有名的画家,所以园林文化讲究画面的纵深感和意境的层次感。江南多水,咫尺山林中又密布沟壑,进一步展示园林的幽深曼妙之境。晚明园林在审美功能上道德意义逐渐淡去,休闲逸乐的意义突显。首先文人在选址上不再刻意避开城市,而是要“大隐隐于市”,尤其是江南文人和城市文化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休闲审美生活的重视,使得他们将“市隐”变成一种普遍的休闲人生模式。其次园林是文人雅集宴乐的主要场所,尤其是晚明,享乐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追逐所在,文人将大部分的生命投注在园林的各种逸乐生活中,明代有大量关于游历私家园林的文学作品,加之明代社团文化发达,园林是文人雅集的重要地方。明代赏玩文化发达,很多园林主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园林文化中对逸乐活动的追逐,使得园林在空间和建筑构造上比起明代初期有了很大变化,园林中越来越多的高大建筑和日益精致奢华的布置格局可以说是逸乐休闲文化在园林中的投影。晚明一改明代开国之初的简朴自然,在园林文化上对繁缛富丽风格的追逐成为时尚。在园林面积上,成华年间苏州最大的园林是东庄,面积大约是六十亩,到了嘉靖年间,王献臣的拙政园面积就达到两百亩,适园和薛荔园则是圈山围湖乃至填岛造园,可见园林规模之大。明初园林多是自然之园,园内建筑物很少,成化以后,江南园林不仅是面积上的扩大,在园内建筑上也是高楼林立,密布景点,以拙政园来说,从文徵明的记载来说有三十一景,每一景都可以独立成景,而各种盆景、花木、假山、奇石、博古清玩更是园林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由于奢侈之风日盛,本来只是在宫殿、庙宇中常见的雕梁画栋在私家园林中普及流行开来。正德年间文人顾璘祝贺同僚乔迁之喜就有说道:“雕梁画栋相鲜地,最爱诗题素璧光”。[4](P439)(顾璘《吴太宰新堂初成有鹊来巢》)可见私家园林在内部装饰上的奢华做派已经不为人所惊讶了。
(二) 自然素朴到富贵逼人
(三)从归隐山泽到喧嚣的通隐
明代有着庞大的山人群体,但是后代对于明代的山人文化多有诟病。最能够代表明代隐逸文化变化的是陈继儒。陈继儒可以说是明代最为有名的隐士,曹臣《舌华录》卷一《名语》篇记载: “吴鹿长与诸友闲谈天下名士,及某某等, 吴曰:云间陈眉公,以艺藏道, 吾敬其道;毗陵刘少白,以道藏艺,吾敬其艺。天下名士,不难于知显,而难于知隐”。[7](P23)可见当时眉公的隐士之名就备受推崇。眉公自己也以隐士自处,其在《芙蓉庄诗序》中说:“吾隐市,人迹之市; 隐山,人迹之山。”(《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6卷十二》)但是眉公之隐,不是要清静无为,而是热闹很,其生活不是“长日避门以求闲”,而是人情应酬样样少不得。吴梅村《陈征君西佘山祠》说他:“通隐居城市,风流白石仙。地高卿相上,身远乱离前。客记茶龛夜,僧追笔冢年。故人重下拜,酹酒向江天”。眉公如此热闹的隐居生活在清代以后多次被人指责,其中以乾隆诗人蒋士铨的指摘最为严厉:“妆点山林大架子, 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 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 蝇营锺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 飞来飞去宰相衙。”眉公的隐居方式不是一个个例,应该说是当时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而眉公在当时的备受推崇,正好说明了晚明在隐逸文化上的普遍态度:心怀隐志,身在尘世。
二、晚明文人审美心态的变化
明代园林文化审美上出现的诸多变化,体现了明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变化。
(一)文人审美理想的世俗化
前面我们讲到,园林文化是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载体,园林文化的发展和隐逸文化的发达有着密切关系。明代山人文化发达,明代小品中表达归隐志向的文字比比皆是,但是《明史·隐逸传》只收录了十二人,明代最有名的隐士陈继儒被后人贬为“云中雁”,可见对于明代山人文化的精神内涵后人都是不大认可的,其重要原因在于明代山人这个特殊群体的世俗化价值取向对传统隐逸文化精神的破坏。传统意义上的“山人”是有着比较严格的道德要求的,通常是指那些隐居在山泽的高洁之士。明代山人除了不出仕这点外,其生活方式和传统的隐士相去甚远,“山人”一词在明代沦为贬称,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里说他们是:“有明中叶以后, 山人墨客, 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 下则厕食客之班, 上则饰隐君之号。”山人群体对传统隐逸文化的消费和利用,使得承载隐逸文化价值的园林文化在审美上也是普遍世俗化,园林的功能可以说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耕读、求志、侍亲的雅正追求上逐渐变成文人在现世的温柔富贵乡,其中也有追求乡野之趣的,比如:“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阱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留连忘反,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足道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但是更多的是如徐应秋《自奉之侈》里面讲到的:“国朝王文恪子大理寺副延喆,性豪奢。治大第,多蓄伎妾子女,斥置珠玉、宝玩、石尊、罍、窑器,法书名画,价值数万。尝以元夕宴客,客席必悬珍珠灯,饮皆古玉杯,恒醉归。肩舆至门,门启则健妇舁之,后堂坐定,群妾筓而盛服者二十余。列坐其侧,各挟二侍女,约髪以珠琲,群饮至醉,有所属意,则凭其肩,声乐前引入室,复酣饮乃寝。晚年益豪奢,自喜宠姬数十人,人设一院,左右鳞次,而居院设一竿,夜则悬纱灯其上,照耀如昼。每夜设宴,老夫妇居中,诸姬列坐,女乐献伎,诸姬以次上寿,爵三行,乐阕,夫人避席去,乃与诸姬纵饮为乐。最后出白玉巵进酒,此巵莹洁无瑕,制极精巧,云是汉物,宝惜不轻及人,惟是夜所属意者,则酌以赐焉。婢视巵到处,预报本院,院婢庀榼温酒,以待房老掌灯来迎,诸姬拥入院,始散去。余纱灯皆熄,惟本院存,各院望见竿灯未熄,知尚私饮未寝,啧啧相羡”。[8](P29)所谓的园林之乐完全不见明代初年文人园林的境界追求,弥漫的是在声色酒气中不加掩饰的末世狂欢。晚明世风日渐喧嚣,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奢华的审美风格流向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极度颓靡的地步。整个社会对财富、对享乐、对欲望的毫无节制的追求使得这个时期的园林文化不但抛弃了明代初年对雅正文化精神的追求,也撕去了文人所谓“中隐”的遮羞布,园林成为文人纵情声色,角逐名利的重要地方,末世之习泛滥。园林文化的耕读和隐世传统消退,园林成为晚明文人狂热的消费欲望的重要象征。园林建造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进入全盛时期。仅就苏州一个地方来说,魏嘉瓒在《苏州历代园林录》中指出,在晚明时期修建的园林大概就有130多处,尽管这个数据并不是说非常准确,但是估摸可以反映当时的造园之盛。在审美境界的追求上,园林作为隐士文化的符号意义显然已经名不副实。在审美理想上,园林的富贵气象显然要承载的不是传统的雅正道德气象,其审美趣味已经深度世俗化。园林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繁复的华丽效果:造景上的密集、华丽高大的园内建筑、华丽繁复的装饰、奇异名贵花草树木的种植移栽等等,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才能达到的,其背后浸染的是明代人浓烈的物质欲望。
(二)自放逸乐中的末世心态
晚明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以园林文化最为发达的苏州地区来说,其可以说是消费经济主导下的城市文明。对财富的狂热使得整个晚明的人文环境显得极为颓废,在奢华的表象下是失去灵魂的浮躁:“彯缨挟弹谁家子,跕屐鸣筝何处娃。不惜钩衣穿薜荔,宁辞折屐破烟霞。万钱决赌争肥羜,百步超骧逐帝騧。落帽遗簪拼酩酊,呼卢蹋鞠恣喧哗。只知湖上秋光好,谁道风前日易斜。隔浦晴沙归雁鹜,沿溪晓市出鱼虾。荧煌灯火阗归路,杂沓笙歌引去槎。此日遨游真放浪,此时身世总繁华。”(申时行《吴山行》)晚明文人在这样奢靡的末世人生面前,其自放逸乐的生活理想中所希望包蕴的对独立人格和精神价值的追求逐渐消退,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文人对现实逸乐毫无节制的追逐,尤其是对物质的占有和追逐到了病态的地步,《吴风录》就有对当时古玩之风引发的掘墓之风的记载:“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若陆完神品画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铜器万件,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自正德中,吴中古墓如城内梁朝公主坟、盘门外孙王陵、张士诚母坟,俱为势豪所发,获其殉葬金玉古器万万计,开吴民发掘之端。其后西山九龙坞诸坟,凡葬后二三日间,即发掘之,取其敛衣与棺,倾其尸于土。盖少久则墓有宿草,不可为矣。”(《吴风录》)清玩古物是园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园林主人或是自己收藏赏析,或是与三五好友共赏,本来都是清雅之事,但是从时人的记载来看,这些清玩古董背后由于交织了太多物质利益,市场上对清玩古物的追逐,早已经不是为了满足文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生财敛财之道,这是因为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才会引发市场的热情,以至于掘墓之风盛行。
(三)“受用清福”
晚明是文人重新定义生命价值的重要时期。其中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理想生活图景颇具代表性。高濂以为人生应该“逍遥余岁,以终天年……受用清福”,所谓“受用清福”,化自民间传统的“五福”观,一般来说,包括寿、富、贵、康宁、子孙众多,实际上这是建立在现世享乐基础上的世俗生活理想,和文人“兼济天下”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它强调的是生活本身的安逸自在。能够实现文人受用清福理想的最佳空间就是私人园林。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文人在价值追求和审美心理上的个人转向,园林不是文人失意仕途之后的暂居之地,而是文人安身立命所在。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文人将个体的生命价值视为意义本身,所以园林生活对于文人来说不是余事,而是正事,东林名士高攀龙就有提到:“仕宦者每借山林为口吻,实以官爵为性命,盖不自知其性命也。如弟稍自识性命,养性命者必以山林为宜,但世间浊福易知,清福易蹉耳。”这里已经是将养护自家性命作为意义的来源了。理解了这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晚明文人对生活本身的意义如此重视,园林生活作为个人“受用清福”的载体,自然成为文人用心经营的地方,甚至不少文人在致仕后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园林的建设中,出现了大量反映园林生活的园林小品文。
大家无法直接感受到手表平时所承受的力,有一个数据可供参考,玩过山车时的重力加速度是6G,但人在挥手时,戴在手上的手表会受到8G的重力加速度;轻轻拍手时大约有10G,热烈鼓掌时就会达到80G。平时我们应该不会想到手表居然要经受这么大的冲击吧。
结语
晚明园林艺术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园林文化的集大成者。古代园林文化发展到明代,一方面是文人园林文化中本来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程式的审美原则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晚明社会审美思潮的多元化也使得其园林文化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色调,晚明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是一个末世的开始,但是对于艺术审美文化来说,则是一个盛世。园林文化在道德功能和教化伦理意义上的弱化,园林主人在审美上普遍体现出来的世俗化、对感官文化和物质文明的追逐,是对传统园林文化审美的破坏,也可以说是新的时代声音的回应。明代是生活美学发达的时代,明代文人对生活本身意义的重视是促成明代审美文化心理变化的重要原因,这一变化又直接体现在园林文化的变化上,也就是说,文人在园林文化生活上的种种变化,是晚明审美思潮的语境之一,笔者相信,站在园林和审美文化的角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晚明社会。
[参考文献]
[1]徐有贞.武功集(第4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吴宽.家藏集(第37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沈周.石田诗选(第7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顾璘.息园存稿诗(第13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元好问.元好问全集(第33卷)[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6]黄省曾.吴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曹臣.舌华录[M].合肥:黄山书社,1999.
[8]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第3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Garden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 Mentality of the Literati
LI 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Zigong,643000,Sichuan,China)
Abstract:The garden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had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on in its pursuit, from moral and ethics to elegance and self-detachment, from naive natural landscape to rich garden of extravagant ethos, from remote and tranquil lake to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noisy society. Garde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the literati.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garden culture directly reflected subtle turning of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the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doomsday mentality of chasing material desires and making merry while one can. The change of the aesthetic mentality in the scholars made late Ming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Keywords:late Ming; garden culture; aesthetic mentality
〔责任编辑:葛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