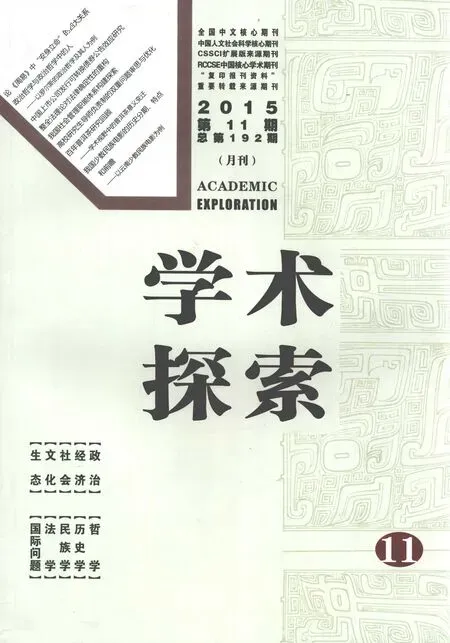孔子的“为政以德”及其思想基础
2015-02-25孔祥安
孔子的“为政以德”及其思想基础
孔祥安
(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山东曲阜273100)
摘要: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是对周公“以德配天”政治观念的继承、转化和提升,孔子倡导的“政者正也”“道之以德”“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等政治主张是对周初“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治理理念的借鉴和发展。孔子将为政之“德”贯穿于其设计的政治生活的诸方面,彰显了其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和特质,存有道德决定论和理想主义的倾向。至今仍在以德治国、党员干部执政素质、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德政;思想;基础
作者简介:孔祥安,男,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儒家伦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KS052);贵州省教育厅基地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
春秋时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以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失序现象层出不穷,周天子天下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孔子面对这样一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的“无道”社会,以“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的强烈使命感和悲天悯人的“济众”情怀,高高擎起“为政以德”的旗帜,极力“主张用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现实人际和社会政治问题”,[1]并毕生不停地思考和探索治平天下的政治良策,进而建构了一套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一般学界将其视为伦理政治思想,有学者也称之为“道德的政治”,[2]或“教化的哲学”。[3](P4)只因孔子的政治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思想文化遗产,而且是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应予以借鉴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故不揣学识浅陋,尝试对其“为政以德”的命题做点诠释,并对其产生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雅方家。
一
《礼记·礼运》篇论述了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和理想的小康社会,《礼记·中庸》篇则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概括孔子政治思想的渊源。“大同”之世是孔子对尧舜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向往、憧憬和概括,“小康”社会是孔子对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认可、赞许和总结。正是基于对“公天下”和“家天下”政治观念和人文思想以及春秋晚期各国政治现实的理性检讨和深刻反省,孔子才提出了早期儒家的一系列政治命题、概念以及观点、主张。综合而论,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或总纲应当是“为政以德”,因为他所有谈论政治的议题都是围绕“为政以德”这一总纲来进行的。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为政以德”是治国理政的策略和方法,“众星拱之”是为政治国所要达到的功用和目的。整体来看,它体现了方法和目的的有机统一。在孔子那里,为政以德的“德”大体有两层意义: 一方面是指为政者应实行有德之政,关注天下百姓的疾苦,体恤民众,实施惠民之政;一方面是指让有德者为政,让为政者做民众的表率,率先垂范,从而突出为政者的示范作用。但是,两者的前提基础是执政者必须有为政之德。实际上是“为政以德”的观点回答了何者为政和为政为何这两大问题,即为政者必须是“修己”成德之君子;为政是为了安乐天下百姓。[4]综观孔子的“为政以德”,其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者正也。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在这里,孔子把“政”界说为“正”,主要表现在“正名”和“正己”两个方面。“正名”,强调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即“复礼”;“正己”,突出为政者的表率作用,即“克己”。但是,这都是对为政者而言的。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即是说,为政者只要率先垂范,民众就会主动效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风气。
首先,孔子认为“正名”是为政治国的首要任务。“正名”就是让人们找准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承担所应该担负的职责和义务,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遵循“亲亲”“尊尊”的原则,保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秩序。这既是社会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活动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否则,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的无序现象。
其次,孔子认为执政者的“正己”(正身)即率先垂范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显然,这要以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为前提。所以孔子提倡“君子怀德”(《里仁》),倡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P4)同时,也强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等等。可见,孔子是把为政之德的着眼点和重心放在了规范和约束为政者的德行上,希望为政者通过自身的美德和善行影响民众,进而带动社会大众道德境界的提高,扩大人们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孔子政治思想的重心不是在“治民”,而是在“治官”,这与一般传统意义上说的“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6]
再者,孔子提倡贤人政治,倡导有德者有其位,主张“为政在人”“政在选人”。如孔子对鲁哀公讲为政之道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5](P28)当仲弓向孔子请教如何从政时,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然而,在季康子向孔子问卫灵公昏庸无道而为什么没有败亡时,孔子回答说:“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宪问》)孔子认为卫灵公有贤才辅佐,所以才国泰民安。但是,如何选人?孔子认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可见,“孔子在谈论政治问题时是把政治美德放在第一位……对政治美德的重视导致了儒家贤人政治的理想。”[2]
第二,道之以德。孔子提倡执政者应用礼乐道德来教化百姓,并将德礼放在为政治国的第一位,把政刑放在第二位,原因是礼乐教化比政令刑罚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即是说,用政令引导民众,用刑法禁止民众,虽可以使民众不犯错误,但民众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来教化民众,用礼仪来约束民众,民众才会有羞耻之心,才能自觉地改正错误,进而达到“使民日迁善而不知”的理想效果。可见,在孔子那里,“德政”教化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孔子提倡礼制,并没有排斥刑罚,而是主张礼主刑辅,礼刑兼用。孔子说:“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孔子家语·刑政》);“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同时,也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目的就是使政治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治理效果。可见,孔子的政治目标不仅要建构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而且要建构一个有道德乃至“至善”的“大同”社会。就孔子“道之以德”的政治思想来看,这就如同今人所说的“以德治国”,它突出强调了道德教化对政治治理的理想效果和优越性。
第三,爱民利民。孔子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7]把惠民富民放在为政治国的重要位置。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即是说,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所以,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杨氏认为:“‘因民之所利’的思想,就是向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着想,因而使他们有利。”[8](P210)鉴于此,孔子首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博施予民而能济众”(《雍也》)以及“恭、宽、信、敏、惠”(《阳货》)等爱民利民思想。其次,孔子主张薄赋敛,反对执政者聚敛钱财,反对贫富悬殊。尤其对战争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明确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战争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痛苦和死亡,所以“子之所慎:斋、战、疾”(《述而》)。再者,孔子十分注重以义导民,避免民众掉进利欲的“窠臼”。孔子认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赞同人们追求富贵的愿望以及获取正当物质利益的需求,但也反对“不以其道得之”的做法,并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这种用道德原则指导物质利益关系的做法,不仅是孔子仁爱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而且也发展为后世儒家“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为政思想和治国原则。
第四,取信于民。孔子认为治国为政必先取信于民。因为民众是历史的主宰者,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而孟子则有更深刻的认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为此,孔子把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重:民、食、丧、祭”(《尧曰》),主张“使民如承大祭”(《颜渊》)等。当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在这里,孔子面对子贡“不得已”情况下的一次次追问,认为可以先去掉“兵”,再去掉“食”,但“民信”是不可去的。因为“民无信不立”,否则,国家就保不住了。
综观前述,孔子为建构其所理想的社会秩序,将“为政以德”视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把为政者之“德”作为治国理乱的关键,旨在通过“以德导民”和“德政利民”的政治实践,实现治平天下之目的。这一政治思想,尽管有理想化的倾向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7]
二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朱熹注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5](P37)孔子称赞古代圣王尧、舜、禹的盛德,并对“制礼作乐”的周公推崇备至。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同时,明确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为政以德”的直接思想来源应是西周“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
周得天下,事实是作为附属国的“小邦周”取代了处于盟主地位的“大邦殷”。王氏曾评价殷周之变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之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9](P453)其实,刚刚取得政权的周初统治者虽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荣耀,但也存在着无穷的担心和忧虑:一方面需要对殷遗民解释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使之接受管理;一方面需要拿出一个治理国家的策略,避免政权的得而复失。
周初统治者为达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的政治目的,总结了殷商天命得而复失的经验,吸取了三监和武庚政治叛乱的教训,增强了政治忧患意识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周公对政权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警惕性,他把殷商“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失政原因反复告诫召公。同时,提醒康叔“唯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可是,如何永享天命?这成了周初统治者必须做出回答的严肃政治问题。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周初统治者明智地将问题聚焦在了执政者的政治道德这一关键环节上,进而明确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的天命观念。即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的,能否得到天命的眷顾,关键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德”。那么,统治者之“德”不仅成了承受天命的先决条件,也是永享天命的决定条件。这样,周初就变革了殷商“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否认了“皇天有亲”的政治观念,把殷商的“以祖配天”转变为周初的“以德配天”,使对外在性的天神崇拜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自觉。这一观念的形成,不仅决定了此后中国哲学的思维向度,而且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周初“以德配天”政治观念的确立,不仅给周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也使周统治者确立了“敬德”“明德”的政治理念。然而,这个“德”落实到政治实践就是如何“保民”。另一方面,周人也从商纣因“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而失败的历史事实中,对民众的力量和价值有了历史性的新认识。如“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尚书·康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等等。换而言之,在周统治者看来,民众不仅成了周初统治者之德的体验者和监督者,而且民众对统治者政权的得失也有了对天的建议权,对周王“政德”的评价也就成了天对“王德”的考察依据,民众自然成了周人“以德配天”的关键。那么,“敬德保民”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初政治的核心问题。
周初“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观念,虽是从关乎周初政权安危的角度来设计和提出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使周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保民、惠民、爱民的措施和手段,进而推动周初确立一个以德为原则的新的管理模式。鉴于民众是周统治者“政德”的监督者,所以他们就必须思考“以德治民”的政治问题。周公认为,治国既要德刑结合,也要慎用刑罚。言以蔽之,即“明德慎罚”。“明德”,即倡导教化、以德化民;“慎罚”,即慎用刑罚、依法行政。
周初为推行治理国家的新理念,对治国思想、原则、方法等进行了制度化,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它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宗法制、封建制、等级制等。一是周初明确规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嫡长子继承制;二是封邦建国,以蕃屏周;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等级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其中人分为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这样,虽体现了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的原则,但从侧面也反映出周初社会的有序性。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非常关注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政治的根本性问题。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对此,孟子解释得比较明确。如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回答说:“天与之。”(《孟子·万章上》)即是说,是天把天下授予舜的。孔子之所以十分赞成这种政权更迭的正当性,原因是这些先王有为政之德,天接受了他们,才授予天下让他们管理。可见,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的思想是赞同和肯定的。
孔子继承了周初“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认为天命是尚德的并以德作为评价政治甚至转移天命的依据。换句话说,也就是谁具有了高尚的人格品德,也就拥有了治国理政的资格和权威。因而,孔子面对“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为建构“天下有道”的有序社会奔走并高声呐喊“为政以德”。但是,孔子政治思考的重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而是如何做好人间的社会治理问题,即人间的君王和天下苍生之间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秩序而设计政治规范和原则问题。简单地说,君主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品德直接决定了国家政治的前途和君民关系的命运,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贤明帝王为政。
孔子将周初的“以德配天”转化为“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不仅肯定了 “德”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意义,而且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及其重要价值作用,而天命、鬼神在孔子那里存而不论,并失去了支配一切的主宰地位,人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体。于是,孔子就把全部热情转向社会人生即“人道”方面的思考和考察,并提出一系列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政治概念和命题。[1]首先,孔子提出了“政者正也”这一实践性的政治命题。一方面强调为政者的“正名”“修己”,突出为政者的道德素养、发挥引领和表率作用;一方面强调“为政在人”“选贤使能”,突出“贤人政治”“学而优则仕”。可见,周初那种浓厚的宗教性的政治色彩在孔子那里已经退去,呈现的却是充满人间温情的人文道德理念。
其次,孔子借鉴和发展了周初“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了“道之以德”“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等政治主张。在孔子那里,德刑关系是一种体用、本末关系,刑罚虽可以使人们逃避犯罪,但不能让人心悦诚服,只有用道德教化,才能使人有耻辱感,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避免犯罪,实现“无讼”的目的。但是,孔子没有否定刑罚的作用。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服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孔子这种德刑兼施、礼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思想,与周初的“明德慎罚”可谓是一脉相承。同时,孔子倡导使民以时、节用爱民、轻徭役、薄赋敛等一系列的爱民惠民思想和措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孔子也认为仅仅做到爱民还是不够的,还应依靠民众,尤其要取信于民。否则,政权的稳定问题将受到质疑。可见,在孔子的“德政”思想中,既是对周初“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其的发展和超越。
再者,孔子十分崇尚周初的“礼乐制度”,认为“德”不仅是周政的核心,也是周公“制礼作乐”所注重和强调的,代表的是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正是因周统治者“失德”而体现的“天下无道”、社会失序,所以孔子希望恢复和发挥西周礼乐的教化功能,主张以主体道德的内在自觉来改变这种无序的社会现实,还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良性状态。尤其通过执政者为政之德的提升即“克己复礼”,进而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状态。
综上所述,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不仅是对周公“以德配天”政治观念的借鉴和继承,更是对该观念的一种转化和提升。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虽不被当时社会所接受,但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汉代以后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存在理想主义和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以及历史的局限性,但能切中治国理政的要害、反映为政治国的要旨,对提高执政者的能力和水平,倡导廉政、德政、仁政,制约乱政、恶政、暴政,推动政治改良,促进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唯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0]可见,当今十分有必要探索和研究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这对促进当前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提升党员干部执政素质和能力、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孔祥安.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价值根源[J].广东社会科学,2013,(3).
[2]陈来.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J].天津社会学,2010,(1).
[3]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4]陈卫平.孔子为政以德的理论内涵[J].江南大学学报,2013,(1).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裴传永.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J].孔子研究,2014,(6).
[7]孔祥安.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J].学术探索,2013,(2).
[8]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4-10-13.
Confucius’ Thinking of“Virtue-oriented Governance”
and Its Ideological Basis
KONG Xiang’an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Confucius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Qufu City, 273100,Shandong,China)
Abstract:Confucius’ political proposition of “virtue-oriented governance” is the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Duke Zhou’s political opinion that “the monarchs should match their power bestowed by Heaven with virtue”. Confucius’ political views such as “government should be based on justice”, “guiding the public with moral conducts”, “loving and benefiting the common people”, and “winning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are the ref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uch governing philosophies as “the ruler should revere Heaven and protect the public” and “upholding morality while keeping cautious in committing penalty”. Confucius established the political “virtue” throughout all the aspects of his designed political life, and manifested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s, which possesses the inclination of moral determinism and idealism. Today, his thinking of “virtue-oriented governance”still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in such aspects as ruling the country by virtue, the reign capacity of the Party members and carders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Confucius; virtue-oriented governance; thinking; basis
〔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