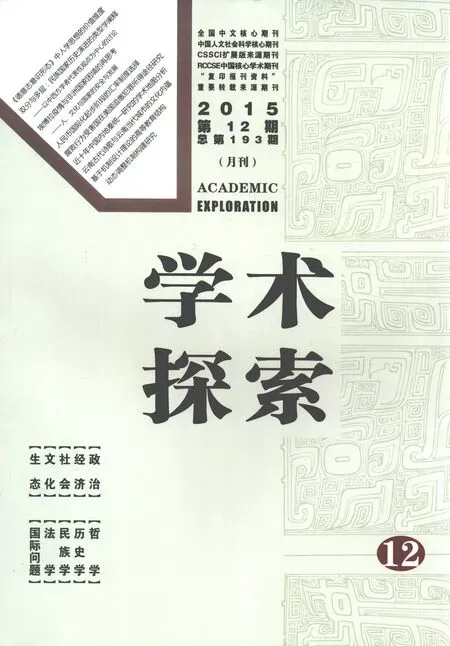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属性阐明
——以前置程序重构为中心
2015-02-25王亮
王 亮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属性阐明
——以前置程序重构为中心
王 亮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于中国发轫未久,在制度安排上多有相容性差、可诉性缺失等不适反应,究其根源,并非单纯的商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未得对接,而是源自法律移植的制度理论之内核尚存疑虑。在理论进路上,由股东代表诉讼之权源基础展开分析,阐明股东诉权非为“派生权利”而是由公司契约安排所得之原权利,是股东监督权的延展,并以此为据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价值基础进行探讨,厘清“穷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下的制度演绎路径,进而提出双轨制的股东代表诉讼程序设想。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内部救济
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与实务探索渊源已久,1843年Foss V. Harbottle一案被认为是最早的股东代表诉讼,其所确立的Foss规则否定了股东代为公司提起诉讼的资格,虽与现代股东代表诉讼理念一定程度相悖,但此一衡平规则乃出于对公司自治的尊重,以及排除司法权的任意干预,构成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审慎基础。随着世界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潮流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过渡,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趋势愈加明显,为防止管理层违背受信义务而滥权以致破坏权力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东代表诉讼与股东直接诉讼共同构成股东借助司法权力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双臂,愈受重视。中国大陆公司制度日渐发展完善,代表诉讼作为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之一被学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2005年《公司法》植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来,相关理论探索弥繁。然则近年来司法实务之反馈却并不如人意。
一、中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性缺失的思证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渊源
股东代表诉讼肇始于“运用衡平法矫正公司核心制度安排不合目的性”[1](P154)的理论构造,与“揭开公司面纱”源出一辙,乃公司制度内控缺陷的弥合机制。公司制度强调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与私法自治,而延续经年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以有限责任和股利分红作为投资人放弃直接管理权之对价,并仅赋予股东享有股东会议的表决权和一定范围的监督权,而由专业性强的集权机构——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之首脑。然则公司之人格毕竟出于法律拟制,其行为与表意皆借由公司机关而外现,当然地受制于公司董事会。基于外观主义的商事规则,公司董事会以公司为名所为行为皆天然地由公司作为权利义务承担者,除非证据充分地证明管理者所为乃出于私益而对公司造成损害。然而,过于强调自治与效益的公司治理模式往往因决策的即时性和不确定性而难以完全规避董事等管理者在公司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尤其在法律对董事受信义务未竟的衡量标准过于主观的情况下。随着规模经济的深入,市场规则日趋完善,公司管理权与所有权的隔离与制衡规则愈加完备,原有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亦面临变革,以CEO为代表的公司高管成为公司权力的实际掌有者,其在日常经营中的决策效率化和职业化于应对复杂市场环境、提高公司盈利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因其脱出传统权力制衡的固有窠臼,对其权力的制衡与监管益难。
股东代表诉讼实质是对传统公司治理机制的突破。公司人格独立为传统公司理论的核心,其衍生出股东有限责任、资本多数决,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当公司董事、高管等通过关联交易等行为窃取公司利益时,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乃救济程序中的不可替代主体。然而,当公司表意受管理者所制而失语之时,公司则不能因权益受损而主导自身意志形成寻求司法救济的意思表示,而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高管等实际控制者自不会主动代表公司为对己不利的诉讼行为,由此则陷入传统法人人格制度的困局。此时如使股东得以自己名义为公司利益求助于司法,借由诉讼维护公司利益并达致间接挽回股东自己所受损失的救济途径,可以有效克服公司表意的程序障碍。[2](P196)故而,基于一定怀疑主义基础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应是对公司管理层的有力监督机制,是两权分离公司治理模式的有益制度支撑。
中国市场环境下虽少有出现如美国般股权极度分散的公开公司,证券市场上的众多投资者也极少会主动探求其所持股公司的高层是否有恶意侵害公司利益之举,但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借由股东代表诉讼维护股东权益的现实需求并不鲜见,尤其在股东人数较少却更易发生损害外部股东利益事由的有限公司和股权配置较单一的非上市公司中。而于股东基数庞大的上市公司而言,随着机构投资者实力逐渐增强,单纯证券转让的利润率难以达致其经营预期,且大额证券交易往往造成市场大幅波动而被监管部门所严格限制,因而传统的漠视持股公司经营状况以及通过“用脚投票”形式维护投资利益的投资模式已难以满足其利益需求,故转而对长期持股收益加大关注,并对目标公司治理投入更多关心,对管理层恶意损害公司利益势不能忍。故而,作为股东制约管理层的重要制度,于中国公司法中确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乃势之所趋,其是对公司法中董事和高管受信义务归咎机制缺失现状的应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制度缺失。
(二)中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性缺失分析
中国大陆确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降,司法实务对学界广泛抱以厚望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适用反馈并不甚乐观。2005年公司法修改以来,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借以维护公司权益的案件数量仍未有明显提升,经检索司法案例中以“股东代表诉讼”为关键词的数目仅有两百余,另有以“股东派生诉讼”为名者一百余,而其中尤多以原告股东主体不适格或未竟前置程序为由而被驳回起诉,更鲜有因证据充沛而致告胜者。仅就此实证数据而言,中国公司法颇费周折方引入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致力于维护公司治理均衡、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立法目的并未得以良好实现。究其根源,当非是制度本身存有价值缺憾,其作为公司表意失灵的救济功能已得公认;亦不能仅归咎于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效用发挥尚需经磨合,此种论断有失消极与偏颇,与我国逐渐走向国际化的公司法发展态势有悖。其劣态之真正归属,一定程度上可咎于制度安排上的可诉性缺失。因制度移植未得妥善安排而至相关制度冲突与脱节,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身失于孤立与空泛,于整体设计上存有可诉性缺失,此方是该制度于实务中表现不佳的主因。《公司法》所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既无以市场观念为要的文化内核为依托,又仅以过分简单的条文设计作为其肢体,势必难以据此为私法与司法之沟通,使得法院裁判往往沦为简单的证据辨识过程,不只浪费司法资源,亦不可见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制度成效。
公司法中制度的可诉性,指的是其本身不仅具备判断纠纷是非的明确标准,并且具备可供当事人选择是否进入诉讼程序的安排以及最终通向诉讼的便捷途径。[3](P40)现行公司法所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集中规定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但仅原则上明确了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以自己名义代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并无具体构成要素、权利内容、法律责任等规定。法律规范原则性过强且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联性较差,故而难于原有实体和程序法律制度之中培育达致制度初衷的适法环境。一则,未对其权利属性予以明晰,其与公司诉权、监事诉权等是否有牵连或先后次序之关系皆未为阐明,与公司法其他制度间存有诸多不调和与有失关联之处;二则,涉及前置程序之规定似有路径选择僵化且合理性缺失之虞;三则,其更未能与民事程序法的发展相协调。甚而,相较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主体内容之法律条文表述而言,作为诉讼准备程序的“穷尽内部救济”规则之体现——例行请求——反而着墨更多。
针对此一可诉性上之劣态,国内众多民商法与诉讼法学者已做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呼声最高者为:构建独立的商事审判程序法律规范体系。商法规范作为技术性极强的市场经济法律,其程序法设置亦应当体现该种技术性,并在基本原则和裁判规则上与普通民事程序法做出一定区分,应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体现和践行与商事实体法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即效率至上而兼顾公平。于此前提之下,学界已有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与立法建议,大致而言,除始终宣示应警惕该制度本身易引致的滥诉风险外,主要集中于股东代表诉讼之当事人资格、管辖、证明责任、诉讼费用负担、诉讼利益归属等。其于程序之上的理论构建已趋完善,可资议论者唯余付诸立法之具体权衡。
然则,前已述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诉性缺失的核心问题乃集于其实体法条文表述粗疏,未明晰其权利属性,亦未合理安排与其他制度间关系。如仅由诉讼实现路径而为展开,相较于制度整体而言不啻细枝末节,恐有空中高阁之憾。本文窃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权源基础、前置程序之合理配置为研究重心阐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完善之理论进路。
二、股东代表诉讼源于“约得”的权利基础
纵观中国《公司法》制定始末,无疑处于摸索与实践交错进行之中,其三次修订和一系列司法解释的出台无不表征着立法与实践的不断调适。此一现象既是商事法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亦凸显了中国公司法制度不成熟之雏态。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条文表述较为粗疏,仅对提起前置程序以及未竟后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一定程度限制,即《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表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而未明确法人人格独立前提下的诉权基础及其获取路径,且权利行使方式以及滥用权利的法律责任等,皆未得述明。萨维尼认为,民事诉讼实际上是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在审判上行使的过程或方法,而诉权是实体法上权利的延伸和转化。[4](P403)股东代表诉讼本是商事实体法上的制度创设,并无专门的民事程序规则与其相适,欲于此构筑实体法通向程序法之路经,则其首要需于实体法上就股东诉权的形成、属性及其内容予以明确。唯有其实体法权利依托,民事程序法方有相应诉讼程序之形成,方能达致实体法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立法本意。但是股东代表诉讼这一制度创新于司法适用中所面临最大困境是其与诉讼法理论与立法实践的相斥:公司享有的诉权与股东享有的代表诉讼权利有何牵连或者差异?
(一)“派生”之义的误读
股东代表诉讼原生于英美衡平法的制度创设,其原有表述为“derivative suit”,译为汉语则为“派生诉讼”。据此国内有学者主张法律赋予股东代表公司为诉讼行为的权利乃“派生”于公司的诉讼原权利[5],[6](P4),既为“派生”权利,则相较于公司诉权乃为次生,其受重重制约应具有当然的合理性。诚然,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是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当然主体,当公司因利益受侵害而需请求司法救济时,应以公司的名义起诉,并直接承受诉讼后果,而具体代为诉讼行为者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代表诉讼以股东为名提起而诉讼后果归于公司,确是一定程度构成了对传统公司法理念的违背,亦与现行民事程序法的具体规则相差异,以内涵较宽泛的“派生”之意形容股东代表诉讼乃公司法人制度的衍生,而与其他商事诉讼制度区分开来,确为适当。但以“派生权利”对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权属性予以概括则恐有失其本意。
“派生”一词,于辞源之义上指由某一主要事物的演变中分化、产生而来,而民法理论中的“派生权利”,则指基于原生权利受侵害而生的法律所保护的救济请求权,两者须有发生顺序上的牵连关系。如确信诉权乃“派生”,其行权人的资格、权利获取、权利内容皆当然地受原权利——即受公司诉权的限制,但公司诉权受侵犯所引致的救济权利应为诉权保障的请求权,而非当然地引致另一差异主体行使不同质的另一诉权;且作为派生权利,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请股东应受有与公司同质之损失,此一要件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并无存在之依据,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内涵来看,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其内容涵盖利益获取权与有限监督权,而与公司相违背受信义务之董事、高管之求偿权利并无性质上的相通性。诚然,股东代表诉讼之权利乃公司法所明确赋予之权利,虽立法未明确其权源,但因其以股东名义提起之外观,可推断该诉权并非直接由公司诉权受侵犯而获取,以“派生权利”为由则其权利承继之间欠缺严密的逻辑推演路径。故此,以“派生权利”对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诉权加以界定,显有失其真意。
而仅作为国内尚无定论的法律概念而言,“股东代表诉讼”一词与“股东派生诉讼”一词于理论研究之适用上并无根本性差别,但作为严谨法律概念则尚待商榷。两者于概念外观上皆有未竟之处——前者“派生”概念未为程序法所援用,后者则与代表人诉讼并无关涉,且司法实践中因法官个人之理论偏好而往往选用迥异,造成了一定的裁判混乱,对笔者的案例资料收集亦造成了不小困扰。为了严谨司法适用中的概念应用,突破概念混淆所致裁判困局,应于立法中对其概念加以述明,赋予其确定的法律名称。具体之厘定则需进一步理论探讨,此处不做赘述。
(二)源于公司契约的救济性权利属性
既然股东代表诉讼之诉权并无“派生权利”之意,并否定了股东代表诉讼概念外观之直译,则为夯实股东代表诉讼的实体法基础,构筑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实现路径,解决本文所探寻其权源基础之疑问蔚为必要。股东作为投资人,与公司间关系仅集于股权之内容,亦即以收益、知情、参与重大决策、监督等为限,而于以公司为名提起诉讼中则天然地不适格,传统公司法制度中亦不存在股东代表公司起诉的规定。但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并主导自身意志乃法律预设之理想状态,公司实践早已证明法人独立需设例外规制以救济公司表意受控之时公司行为对自身利益之损害,其中最广为认可的例证即“刺破公司面纱”,此一制度上例外乃公司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方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而予以特别设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亦是同理,乃是公司制度对公司内控机制失灵的积极应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直接功能及其外观表现为挽回公司的损失,并在此基础上达致间接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但作为实体法上之制度,其本意并非直接便利诉讼(与程序法尽量促进诉讼便利的功能目标绝然相悖),更多乃是出于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之目的,具体而言即通过引而未发的诉讼构成对公司董事和高管的威慑,使其于公司经营中更加勤勉与忠实,仅将诉诸法院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但由公司法制度设计之自由价值本意衡量,势必不能因法律的强制规定而当然地构成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司法干预,否则有悖私法自治之意。
根据传统的公司契约理论,公司的本质是一组“契约的联结”,而公司法是对这种不违背公序良俗价值的契约内容予以授权的任意性规范集合。基于契约安排,股东因有限责任的设置而与公司隔离,仅享有包涵收益权、剩余财产分配权、投票权,以及监督权等权利内容的股东权,股东权作为综合性的权利类于社员权,乃基于契约或曰公司章程而享有的开放性权利集合,其内容可因约定而适度扩张与限缩。在“董事会中心主义”大张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股东尤其外部股东于公司中享有的股东权更多集中体现于根据公司盈利获取股利分配,其监督权受到愈多的限制,这种限制非是契约安排,乃是因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而大量信息难以为外部股东直接知悉的客观障碍。于是,当原有契约安排难以达致股东监督目的之时,势必需对原有公司契约做出小幅调整,即扩大监督权的内容延伸。公司契约赋予股东得于公司表意失灵时主动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追究背信董事或高管责任,此一安排乃是股东监督权适度扩张的外在体现之一,源于公司设立之时依公司法而约定之救济权利。在公司内部救济程序无效的情况下,股东监督权的实现求助于司法,应与公司监事(会)依监督职权而将董事或高管诉诸法院的权利内容同质。因此,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应为股东权之固有内涵的直接延伸,此乃其实体法权源。[6](P71)
据上述而可知,作为一种净化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公司契约安排,股东代表诉讼之实体诉权应为于公司章程中预设之约得权利,乃是公司治理的私法精神之具现。并由此可认定该诉权并非“派生”于公司诉权,而是独立的原权利。
(三)源于契约安排的权利内容
上已述及,诉权完整内涵包括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两个方面,程序含义是指在程序上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的权利,实体含义则是指保护民事权益或解决民事纠纷的请求。[7](P155~157)程序法上相对应之保障姑且不论,基于上述股东代表诉讼之权利属性为“约得”之原权利,则其实体法上的权利内容应有体现。
首先,股东代表诉讼乃股东监督权之衍伸,其独立行使主体为适格的公司股东,除受公司章程或法律强制规范约束外不受其他任意限制。其制度价值在于制衡违反受信义务之公司控制股东、董事、高管等,具体而言包括恶意浪费公司资产、不公平的自我交易或关联交易、利用公司机会造成重大损失、不对称高额管理报酬、投资上的重大失误等,以及第三人侵权表象下的管理层受信义务未尽 。[8](P438)
其次,作为契约上的权利,权利的实现应有相应的保障。作为股东监督权的扩张和衍伸,股东代表诉讼之权利的行使亦应得公司的相应配合,集中体现为股东为实现间接监督而需要的对其知情权的保障。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并可基于合理目的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最后,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利,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基于一定的前提,即对法律之敬畏。除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的强行性规范外,公司法于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上设有“前置程序”之限制,需符合一定资格的股东在向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或监事会(监事)请求起诉后遭拒绝或不得回应又或紧急之时方可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前置程序”概念的设计与内涵已得学界广泛认可,但对该程序的价值构造笔者尚存疑问,并将于下文予以展开。
三、“约得”权利属性下的前置程序构建
(一)前置程序防止滥诉之目的性局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基于利益相关人理论与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双重价值而构建完善,目的在于通过例外的制度安排衡平公司内部治理失灵之时的利益纠纷。但引入司法力量涉入以效益为终极目标的市场范畴中,势必要有不得已的缘由,以防股东任意提起诉讼,干涉公司正常经营。如前所述,商事立法以效益为先,通过司法干预解决公司内部治理困境乃不得已而为之,如此制度的引入与适用中必将面临两难的抉择:既不愿有损公司意思自治的私法传统,亦不愿对有损中小股东权益的非法之举三缄其口,以致立法对确定公司管理层违背受信义务的客观标准与惩戒规则犹豫不决。故此,基于国外立法中“穷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之表述,以及中国立法者囿于强制性规范传统的惯性,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设计中处处体现出对中小股东的提防与限制,防止中小股东提出无意义的诉讼,从而牟取个人私益或不必要地浪费公司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5](P315)
“穷尽内部救济”规则之价值于公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由其衍生的“防止滥诉”之制度目的亦有存在之合理性。股东代表诉讼毕竟是非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以自己名义单方提起的诉讼,其非公司内部人,虽公司经营状况与其切身相关,但由于天然与公司经营管理相隔离,以及在内部决策信息获取上的滞后性和被动性,不参与管理的公司股东绝难由公司行为外观判断其是否出于公司利益之选择,仅可通过直观的利润率等做出主观判断,往往会提起对公司并无价值的诉讼,甚而或有股东心怀恶意干扰公司经营或贪图和解利益而为诉讼。如此,如使股东可任意行使代表诉讼之权利,确实很难避免滥诉之风险。2005年《公司法》修改施行以来,如仅以“证据不足”“未经法定程序”而提起的诉讼为限作为“滥诉”之衡量,则借近年司法裁判而观之,可喻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设置无疑已达致防止滥诉之初衷。
毋庸置疑,防止滥诉乃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然则,确切地说,防止滥诉仅为程序法价值功能之一,而于民事实体法律制度中,更多关注权利的内容安排。在法律部门的功能划分上,民事实体法彰显人格的独立与唯一,乃以权利保障为法治精神内核,而民事程序法则借由对以司法效率为外观的形式正义价值的追寻殊途同归亦达致权利保护之义。由法律制度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而言,中国引入国外先进商事法律制度与理论的尝试势不可缺,但任何制度的移植绝非是为了完善诉讼程序制度构建,亦非是出于扩张法院权能的安排。就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言,确为实体法与程序法沟通之桥梁,但其制度价值非为便利诉讼、降低司法成本,而应是维护公司乃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权利保障之设定,乃“公司内部救济”未达目的的特别安排,仍归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市场经济繁荣与稳定之公司法价值本位。况且,如于制度设计之初即“未见功成而先虑败”,对股东代表诉讼可能存有的滥诉风险避之若浼,或有损制度进取之锐意。故此,出于达致制度设计初衷的考虑,在尚无针对性防范滥诉之商事程序法规则的前提下,实体立法仅需完善“穷尽内部救济”之实体规则,而不应于程序之上对股东代表诉讼苛之过严。
(二)前置程序之逻辑展开:制度相容性分析
依公司契约理论,公司内部治理安排中的纠纷解决机制应优于公权力的干预,在未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之时当非为法律强制调整之范畴,法院势必不可主动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而公司自为救济亦应首先依赖其设立之时所安排的内部控制机制,此即“穷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中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设计亦奉此为圭臬而特别规定了前置程序。然则,源于外生的法律制度条文失之简陋,原则性过强而并无具体条文立法意之解读,以致与现有公司法律制度相容性差。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符合条件的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前需先向监事(会)或执行董事(董事会)提起书面请求。此一谓为“前置”的程序路径之本意体现了对公司内部监管机制的尊重,深孚公司章程之约定。但是在于具体安排上失之孤立,与现有公司治理之内控机制并未良好对接,以致出现法律适用与理解上之困惑。
一方面,违反受信义务之董事或高管首先应负契约上之责任,即须先由公司契约所预设的内部监管与归责安排进行处理。依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内部常设监管机构乃公司监事(会),或者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及其组成之专门委员会。公司法虽并未授权监事(会)主动以董事、高管等违背受信义务致公司损害为由提起诉讼,使监事(会)之监管职能仅囿于公司内部,极易被限制或剥除,此不得不说乃监事会制度之疏漏,但至少于其职权中明确了监事(会)享有经股东申请可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权利内容。如此,则股东欲以董事、高管等侵害公司利益之由诉诸司法寻求救济,需先向监事(会)提出建议或申请之前置程序条文表述得与公司内部监管机制相协调,并可推知其“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之制度逻辑。但是,作为公司内设监督机构,公司法条文并未明确监事(会)在对公司管理人员提起诉讼时是以公司为名抑或仅依职权而以自己名义提起,授权不明则于司法实务中造成了一定困惑,亦使得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威慑价值某种程度上并未得以实现。另外,作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立董事制度,其同样为公司内部救济的组成部分,然则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未将其作为前置申请之要素,此于“穷尽内部救济”之规则而言似有未竟之意。
另一方面,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另有当监事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而由股东书面请求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向法院起诉之规定。然则,董事会作为公司机关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而执行董事亦仅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中确认为法定代表人者方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除此之外董事会职责中并无诉权之内容。且董事会或执行董事提起诉讼之前提乃监事于公司经营中违法或违约造成公司损害,不论实践中监事因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而对公司造成损害的例证是否多有,仅由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内容而言,监事作为公司内部监管机构之组成,其违约则应由股东(大)会决定对其处理和归责,而通过股东向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申请对其提起诉讼于制度上无据。故此,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之规定于此一意义上并无相关制度依托,可谓空置。
除此之外,如前置程序之设置并非如前所述乃出于“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之意,而仅作为防止滥诉之强制审查程序,则此程序亦应秉中配置,即以独立第三方衡量股东代表诉讼利益与公司管理层商业判断权力之取舍。而如将本为制衡管理者之股东代表诉讼发起程序之审核权反授之于公司董事、高管等,则不啻反授人以柄,有违衡平之本意。由此,对股东代表诉讼之提起正当与否的衡量权应赋予中立第三方。
(三)前置程序的价值重构:“穷尽内部救济”
于制度整体价值而言,股东代表诉讼规则的确立相较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外观而言,应更多体现为一种促进公司治理环境改善的威慑常态,其诉讼价值之实现反落为下乘。股东代表诉讼发起的制度前提是“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具体而言则为最大化发挥公司内部监管机制的功用,其主动履行监管职能以维护公司治理良性配置为最理想之状态,而如其监管中存有疏忽,则股东依监督权提起质询案、发起内部审议,以为监事(会)等内控机构之提示与补充,唯当上述皆不可得时,股东依法律或章程而获得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由此乃得构建对控制股东、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有约束力的监督常态,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控制股东、董事、高管等人员为商事行为时更加谨慎。
由上可知,理想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配置乃由股东行使监督权向公司内部监管机构发起质询与审议、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而股东代表诉讼乃防范公司内部治理失衡的最后防线,在“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之后,公司内部已无法制衡背约之管理者,当此之时,与其徒费功夫于搜集股东已经前置申请程序的烦琐证据,不如仅基于审慎而就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之股东资格上予以限缩,以“连续持股原则”和“高额股份比例”等规则排除临时起意的频繁诉讼,并可以学界已广为讨论的“诉讼担保规则”作为诉讼正当性的制度保障。因此,笔者建议在重新厘清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之制度逻辑的前提下,可考虑赋予适格股东双轨制的选择权,即可先向公司监管机构发起请求,亦可直接于证据充沛时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此种制度安排早有成例可循,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代表(派生)诉讼的规定仅设定了股东“宣称股份所有权”的资格要件,即证明股东于被起诉进行时即为股东,或其股份是在交易之后因法律运行而转移给自己的,并无前置程序的要求;[9]P192台湾公司法中,对继续一年以上持有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赋予其先经请监察人对公司董事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于30日内监察人未起诉时赋予该股东为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10](P263)虽规定了一定前置程序,但其更多着眼于股东对监察人行使监督权之提醒,并不要求特别证据予以证明;我国《公司法》亦有紧急情况下、不立即起诉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时股东得直接提起代表诉讼的例外规定。
此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在于:第一,股东发起质询与审议作为股东监督权的核心内容是“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东通过向董事会或监事会提出的质询案要求其提供关涉股东疑问的公司经营信息、会议记录及财务会计报告等,作为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授予之权利,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有相应义务对质询案做出迅速答复,不得以需要调查为由拖延,即使因涉商业机密、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而拒绝亦应做出具体说明并出具拒绝书,如此可尽量发挥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功用,既体现了对股东权的尊重,亦可有效抑制不良诉讼的发生;第二,在股份公司中,股权相对分散,持股比例微小的股东往往追求股份转让的差价收益,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关心仅止于其影响股价涨跌的幅度以及由此影响其转让与否的选择,而设置高额持股比例方能体现持股股东或股东群体对公司利益受损而请求救济的真实需求,且持较高比例股权的股东或其群体实力较强,常常可获取更多的公司经营信息,于此一层面而言亦可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可有效减少实务中起于举证的滥诉,而中国公司法以百分之一持股比例作为股份公司股东提起诉讼的资格要件失于宽松;第三,一定时期内连续持股,是英美法“同时持股原则”在各国立法安排中的体现,即从侵权行为发生时起到派生诉讼结束时止股东必须持有公司股份,以防止“购买诉讼”的出现,当然公司成立后不久即发生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应为立法上之例外,允许股东在公司成立后继续持有股票就可以提起诉讼;[11](P158)第四,双轨制的制度设置乃出于对民商事主体自由选择权的尊重,且于实务中更为灵活,在公司表意确已被公司高层控制的情况下免除了股东证明已经前置程序的证明责任,节约了社会资源,是公司法效率性的体现,同时也更加利于制度本身救济性价值的实现。
四、结语
诚然,上述双轨制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解决了现行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配置相容性差的问题,并体现了对公司自治以及股东权利的尊重,但与此同时亦加大了对诉讼正当性的审查强度。“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或“情况紧急”为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前提,且提起诉讼之股东亦受公司法上持股比例、持股时间的资格限制,对上述条件与资格的证明应由适格的原告股东向法院提交书面证明材料,而非向公司机关提交。上已述及,公司表意失灵多为公司董事或高管的背约所致,如将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审核权授予该董事或高管控制的公司机关则有违制度本意。因此,本文主张应由法院在审前程序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予以审核。并且,审前程序本为证据辨识的简易程序,乃基于节约司法资源、防止滥诉的诉讼制度安排,与抑制股东滥诉的出发点一致。
但是,由于商事审判的专业性,以及前置程序中信息辨识的困难性,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商事审判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止如此,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裁判多确定以“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董事或高管责任免除的重要依据。但因“商业判断规则”主观性过强,逻辑严谨的法律推演难以据此抽象出可行的裁判标准。故此,股东代表诉讼不仅需要大量具有一定公司法专业底蕴的法律人才,还需借助于处于中立地位的具有丰富公司管理经验与市场评估分析能力的职业人员以备咨询。另外,《公司法》未将独立董事的功能发挥作为上市公司中股东代表诉讼提起之前置程序,而作为外部董事,其独立性更强,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制衡价值更为突出,法院可于审前程序中向公司独立董事及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咨询,以之作为股东代表诉讼正当性的判断依据之一。
[1]蔡立东.论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的范围[J].当代法学,2007,(1).
[2]赵万一.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赵万一,张长健.后立法时代的中国公司法可诉性[J].北方法学,2014,(1).
[4]江伟.民事诉讼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6]陈南男.派生诉讼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7]赵万一.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8]辜恩臻.论诉权的性质及其适用[J].法学杂志,2008,(3).
[9]朱云阳.法律移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改革的经验和启示[J].清华法治论衡,2011,(1).
[10]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M].徐文彬,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1]保成法学院.攻略民商法[M].台北:新保成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
[12]刘凯湘.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以《公司法》第152条的解释为中心[J].中国法学,2008,(4).
〔责任编辑:黎 玫〕
The Property of the Right to Claim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Prepositional Procedure
WANG Liang
(School of Civil and Business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The system of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appeared in China before long. There are a number of unhealthy reactions to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such as bad system compatibility and deficiency of suability. These problems are not simply caused by the less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but by the fact that the basic theory is not convincing enough which came from transplantation of law.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ource of the right to claim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and illuminates that the right of action enjoyed by shareholders is the original right grown out of company contract and part of the right of supervision, instead of “derivative right”.Moreover, it discusses the value of prepositional procedure of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By clearing the deduction about the rule of “exhaustion of internal remedies” we propose the idea of dual track procedure of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prepositional procedure; internal remedies
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XZYJS2014014);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度科研青年项目(2014XZQN-21)
王 亮,男,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法、保险法研究。
DF43
A
1006-723X(2015)12-00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