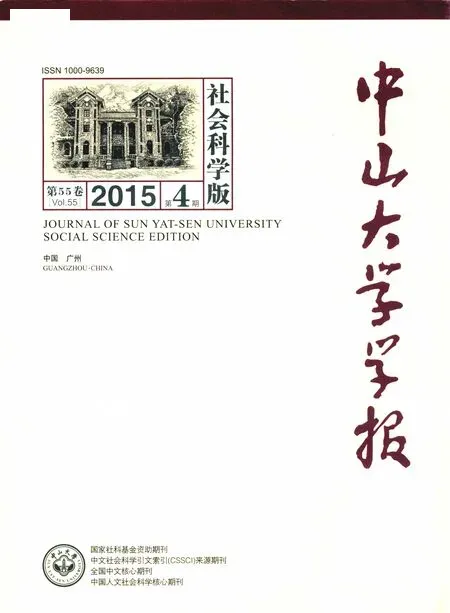“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文体生成*——关于叙事诸文体录入总集的讨论
2015-02-25胡大雷
胡 大 雷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文体生成*
——关于叙事诸文体录入总集的讨论
胡 大 雷
摘要:“左史记言”之“言”,或以语言行为动作而被命名为独立文体,进入总集。“右史记事”之“事”以史书的“传”为单位,或庞杂多种文体,或因“互见”而不周全,故只有随赋、诗、辞、移等文体一并,被从史书中“剪截”出来入《文选》,或“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与文体并列入类书。宋时,“叙事”自成文体入总集:一是“传”、“记”以“篇翰”方式生成文体;二是《左传》、《史记》的文字被命名为文体“叙事”入总集。其原因亦有二:一是对古文的崇尚使总集录入《左传》、《史记》的“叙事”文字成为社会需要,于是,总集的功能,既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读本,又是“作文之式”;二是解决了《左传》、《史记》中的文字转化为“叙事”文体的技术性问题,即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剪截”等问题。《左传》、《史记》入总集,为经、子及其他史体文字入总集做出榜样,为中国古代更多的文章进入文学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记言; 传; 记; 叙事; 总集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7页中。《尚书·序》称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38页。。以上两段话讲述了文字、文籍的产生及其功能。《文心雕龙·书记》:“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8页。“书”者为“史”,《礼记·玉藻》所谓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473—1474页上。;《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集合体为“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那么,“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二者各自生成文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总集者,“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页。,即分文体汇集各位作家的作品,从总集最可看出文体是否生成。因此,本文把文体生成与总集录入合在一起来讨论。
一、“左史记言”之“言”生成为文体
“言”,即指言语这一动作,这一动作的功能就是表达。《释名·释言语》:“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刘熙撰,任继昉汇校:《释名汇校》,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76页。“左史记言”之“言”就是言语这一动作所表达者,此处考察“言为《尚书》”的文体生成情况。前人谈《尚书》文体,有“六体”之说,伪孔安国《尚书·序》称:“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除“典”具有“记事”功能外,“谟、训、诰、誓、命”都是语言行为动作,有些成为了后世延续使用的文体,就是因为这些行为动作产生了文辞,即以此命名文体,而行为动作也由动词变成了命名文体的名词。下面来看具体情况。
其一,训。《高宗肜日》“乃训于王曰”,伪孔传:“祖己既言,遂以道训谏王。”*《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训”,训勉、教导,其词就是训体文字。
其二,诰。《大诰》“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伪孔传:“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诰天下众国,及于御治事者,尽及之。”*《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诰”,即告诉、告诫、劝勉,这个行为动作产生的文词,就是文体诰的文字。
其三,誓。《尚书·汤誓》为商汤动员部属征伐夏桀的誓师词。伪孔传解题:“戒誓汤士众。”孔颖达疏曰:“此经皆誓之辞也。”*《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从其中“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可知当时就称此文字为“誓”。“誓言”是“誓”这个行为动作发出的,于是这个行为动作就成为文体“誓”。
其四,命。《顾命》伪孔传:“实命群臣,叙以要言。”*《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命”这个行为动作产生的言语文辞为“命”体。《文心雕龙·诏策》称“诰、誓、命”曰:“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724—726页。
其五,谟。《皋陶谟》:“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伪孔传: “谟,谋也。皋陶为帝舜谋。”“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以辅谐其政。”*《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是开场白,以下是帝舜、禹、皋陶君臣之间的讨论、谋划。《皋陶谟》中不见“谟曰”云云,但文辞的确是“谟”这一行为动作所产生的,那么,这些讨论、谋划形成的文辞即应该是“谟”体。但“谟”体后世没有延续使用。
又有《尚书》“十体”的说法。孔颖达疏:“说者以《书》体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贡、歌、范四者,并之则十矣。若《益稷》、《盘庚》单言,附于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举其机约,亦自征、贡、歌、范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14,176,198,160,237,138,115页上。“征、贡、歌、范四者”,依《尚书》篇题而称,孔颖达疏称其“非君出言之名”,故可并于六体。但是,孔颖达以“君出言之名”为文体,实质上提出了文体命名的一个主要原则,即依语言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虽然有不尽恰当之处,但给我们以启示,可以依语言行为动作所产生文辞这一现象来探讨《尚书》中的文体,这应该是文体的最早形态。而这些作为表达的“言”之所以可以成为文体,就在于这种表达具有较强的自足性,自有界限,自成单位,其成为文体的最后一步就是以行为动作为其命名了,有学者称这是古代文体生成方式之一,即“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详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又见胡大雷:《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所说“以产生文体的行为动作即‘做什么’来命名文体”,载《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由此可见一斑。
当最早的“左史记言”者《尚书》可以析出诸多的文体时,表明“左史记言”生成的文体已经可以独立,作为独立文体的“言”,自然就可以入总集。而虽然有诸多的“左史记言”之“言”成为文体,但“言”仍有整体性存在者,如以《论语》、《国语》为代表之“语体”;或如《战国策》,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之所以称其“策”,所谓“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文心雕龙·史传》,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71,569,583,604页。,就以连编的竹简相称了。整体性存在的“言”,至《文选》时尚未进入总集,即《文选序》云: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首第2页。
这些“美辞”,这些“话”,如何生成为文体,这是后话。
二、“右史记事”之“事”与总集
与“左史记言”相比,“右史记事”的整体性存在的状况更突出一些,延续的时间也长一些。原因在于最早的“右史记事”者《春秋》,其“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03页中下。。《春秋》即以“年”为单位记事,而不以“事”为单位;《左传》的“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文心雕龙·史传》,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71,569,583,604页。,“传”者解说而已,《左传》的叙事单位仍是“年”。“年”长短的固定性与“事”长短的随机性,使二者并非总能恰切相合。因此对叙事而言,以“年”为单位的叙事,在“事”的自足性、自成单位上,对其生成文体是有妨碍的;以“年”为单位的“事”,不大适合于生成具有自足性的、自有界限的文体。
“右史记事”在司马迁时开始以“人”为单位,《史记》创“传”体,“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文心雕龙·史传》,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71,569,583,604页。。其突出的特点即以“人”为单位叙事,但如此的“传”仍不能从史书中析出而入总集,也就是仍不能成为集部的独立文体,原因有如《文选序》云: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但是,“传”不入总集而“传”中某些成分可以作为文体入总集,即萧统称“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中自成文体的“赞、论、序、述”是可以入总集的。“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中的“传”为什么“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呢?首先,“传”是一个集合体,比如说它是含有“赞、论、序、述”等文体的集合体;且在“记事”上也是一个集合体,“传”是对人一生事迹的记载,人的一生必定有许多事,这许多事凑在一起不见得就是一件完整的“事”。而“篇翰”,应该是一个自有界限的具有自足性的文体单位。其次,刘勰曾论“传”在记事的另一方面也有“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之处:
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文心雕龙·史传》,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571,569,583,604页。
刘知几也有类似的说法: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8页。
因此,诸人之“传”的“记事”在史书中以“互见”的方式存在,就史书整体而言,“事”是完整的;而单就一“事”来说,“传”的“记事”就是不完整的,所谓“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所以,“传”在史书中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篇章,但剥离出来就构不成一个独立的篇章,所以说“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事”在总集中也有出现,不过是以附属的形式。在《文选》中,“右史记事”是随同各种独立文体存在的,即《文选》在录入独立文体的作品时,一并“剪截”了史书所叙产生此作品之“事”,称之为“序”。请看下例:
《文选》赋“郊祀类”录扬雄《甘泉赋》,其起首云: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辞曰。*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11,135下—136,407页。
这是从《汉书·扬雄传》“剪截”而来,是叙说《甘泉赋》是如何产生的“事”,《文选》把它与《甘泉赋》一并录入,把这段文字作为“序”。
《文选》赋“畋猎类”扬雄《长杨赋》,其起首云: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纲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其辞曰。*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11,135下—136,407页。
这也是《汉书·扬雄传》的叙事,是叙说产生《长杨赋》之“事”,《文选》把它与《长杨赋》一并录入,把这段文字作为“序”。具有说服力的还有《文选》赋“畋猎类”所收扬雄《羽猎赋》,《文选》赋“鸟兽类”所收贾谊《鵩鸟赋》,都是如此,在载录的赋作前,分别有“剪截”《汉书·扬雄传》、《汉书·贾谊传》的“记事”。
我们再来看《文选》其他文类的情况。《文选》诗“劝励类”有韦孟《讽谏》,《汉书·韦贤传》载录此诗时有说明文字:“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曰。”*班固:《汉书》,第3101,1967,3565—3566页。《文选》依样录入,作为“序”,然后录诗。《文选》诗“杂歌类”的汉高祖《歌》,其“歌”前载:
高祖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11,135下—136,407页。
这是对汉高祖某一段生平事迹的介绍,是叙说高祖“自歌曰”的背景。《文选》把这段文字视作“序”。上述文字亦见于《汉书·高帝纪》,仅首句人称不同。《文选》“移”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书·楚元王传》载录此文时有曰: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班固:《汉书》,第3101,1967,3565—3566页。
《文选》所录也有与此相同的说明文字,《文选》视之为“序”。
《文选》“设论”有扬雄《解嘲》,《汉书·扬雄传》载录此文时有说明文字: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辞曰。*班固:《汉书》,第3101,1967,3565—3566页。
《文选》把此段文字作为“序”。班固《答宾戏》,《后汉书·班固传》在载录此文时还有说明文字,《文选》所录也是有说明文字的,与《后汉书·班固传》所载相同,《文选》把这段文字视作“序”。
《文选》“辞”有汉武帝《秋风辞》,其前有序,云: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36上,831下—832页。
《汉武帝故事》载录此文时有说明文字,文字与此基本相同。
《文选》“吊文”有贾谊《吊屈原文》,有序:
(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汩罗江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36上,831下—832页。
此即《汉书·贾谊传》载录此文时的叙述文字,《文选》“剪截”而来。
可见,《文选》在载录各种文体的作品,把史书对作品介绍的“事”一并“剪截”。考其原因,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所说“言、事”合一:
《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第9—10页。
《文选》载录的这些作品,都是由“言”生成的文体;但“言”离不开“事”,所以一并载录,但这是“右史记事”附属于“左史记言”了。《文选》载录各种文体作品的“言、事”合一,源于生活现实的“言、事”合一。《尚书·舜典》有“询事考言”,蔡沈集传:“尧言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蔡沈:《书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9页。即《韩非子·二柄》: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1页。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462页中、2472页上。先“言”后“事”,说了就要做到,“言”与“事”是一体而不可分的。
“言、事”合一,又有类书中“叙事”与诸文体的并立,《艺文类聚序》:
以为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艺文类聚》按门类采摭群书,辑录资料,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先是“叙事”,出自于经、史、子各类著述所载;后列诸文体之“文”,这是“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的文体之“文”。唐刘肃《大唐新语》卷9记载《初学记》的编纂情况: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刘肃:《大唐新语》,《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因此《初学记》载各门类资料,先列“事”,直接标明“叙事”与“事对”,后列诸文体中叙及该“事”者。
上述情况表明,史书的“传”不适合单列,而在总集、类书中,“事”却屡屡要展现自身,个中透露出要求独立的强烈意愿,这应该是促发“右史记事”生成文体的动力之一。
三、“传”、“记”以“篇翰”方式生成文体
史书的“传”不能作为独立文体,于是文人撰作以“篇翰”形式生成的“传”。当然,其基本条件是“事”在“传”中具有自足性。如刘知几说:
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刘知几:《史通·列传》,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第15页。
这段话虽然是批评某些史书的“传”不重“事”,但纪传体史书就在于重“人”,故人物“靡徵其事”即无“事”亦有“传”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以“篇翰”的方式撰作“传”就该注重“事”及其“事”的集中性。《文苑英华》有传体30篇,章学诚对其作了说明,其曰:
《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于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于史家正传例者,凡十余篇……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亦次于诸正传中。*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第77,9页。
这是对有人提出入“集”之“传”非“正传”所作驳辩。但我们应该看到,入“集”之“传”不仅重在“事”,更重在单一的“事”,所以章学诚突出提到“公卿”、“节钺”、“文学”、“节操”、“贞烈”的叙事统一性以及“立言有寄托”、“借名存讽刺”、“俳谐为游戏”等题材的单一性。
从另外一方面说,如刘知几称《史记》、《汉书》,“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云云*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第77,9页。,倒过来说,以“篇翰”的方式撰作的“传”重在“事”,一般是要避免“唯上录言,罕逢载事”、“文辞入记,繁富为多”的,是不像史书的“传”那样包含传主的诸种文章的。所以,史书的“传”与以“篇翰”的方式撰作的“传”,二者的篇法是不一样的。方苞《古文约选序》就称,诸如《左传》、《史记》之类,“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分剟”,“虽有篇法可求”,“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方苞:《古文约选》,雍正刻本卷首。。
又有姚铉《唐文粹》卷99、100为“传录纪事”(读传附),内有“题传后二”、“假物四”、“忠烈三”、“隐逸二”、“奇才一”、“杂伎二”、“妖惑一”、“录二”、“纪事十”,共27篇。从这些纲目,可见其“记事”的单一性。
再有吕祖谦《宋文鉴》卷149、150收录“传”17篇,分别为《补亡先生传》、《退士传》、《六一居士传》、《桑怿传》、《赵延嗣传》、《范景仁传》、《文中子补传》、《无名君传》、《洪渥传》、《曹氏女传》、《方山子传》、《公默先生传》、《上谷郡君家传》、《巢谷传》、《孙少述传》、《钱乙传》、《玉友传》。这些都不是录自史书的“传”,而是以“篇翰”的方式撰作的“传”。
又有“右史记事”之“记”生成为文体。“记”,即把印象保留在脑中,进而记录、载录。《国语·晋语四》:“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 。’”*《国语》,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78页。“记”指公牍札子,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吴王占梦》:“王孙骆移记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马王孙骆,受教告东掖门亭长公孙圣:吴王昼卧觉寤,而心中惆怅也如有悔。记到,车驰诣姑胥之台。’”*《越绝书》,《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页。“记”又指典籍、著作,《庄子·天地》:“《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4页。《记》即书名。“记”,或指记述或解释典章制度的文字的专书,如《周礼·考工记》、《礼记》、《大戴礼记》。“记”成为文体名,即以叙事为主,兼及议论抒情和山川景观的描写。明人吴讷《文章辩体序说·记》:“《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吴讷、徐师曾:《文章辩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1,145,7页。作为文体的“记”,晋陶潜有《桃花源记》,沈约有《南齐仆射王奂枳园寺刹下石记》*诸葛亮《黄陵庙记》,世以为伪托。。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记》称:“《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吴讷、徐师曾:《文章辩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1,145,7页。“记”的盛行以唐代时撰写嵌在墙上的碑记即“壁记”为契机,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壁记》:“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封演:《封氏闻见记》,《四部家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州县官署也有壁记,如唐柳宗元有《武功县丞壁记》、《馆驿使壁记》等。《文苑英华》有记体37卷,其中有《枕中记》,《唐国史补》卷下称其“庄子寓言之类”,称作者沈既济“真良史才也”*李肇、赵璘:《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5页。,认定“记”的叙事性质。从以上所述也可知“记”的一事一叙的篇翰性质。《唐文粹》有记体7卷,《宋文鉴》有记体8卷。
“传”、“记”由“右史记事”之“事”生成文体,但其生成方式却是“篇翰”式的。虽然其文体命名,有所袭自,但与传统多有不同,如此独立的文体进入总集是自然而然的。
四、“叙事”成为文体而入总集
宋代又出现了自创以“叙事”命名的文体,彭时《文章辨体序》:
至宋西山真先生集为《文章正宗》,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天下之文,诚无出此四者,可谓备且精矣*吴讷、徐师曾:《文章辩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1,145,7页。。
永瑢等《文章正宗》“提要”曰:
是集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9页中。 按: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
真德秀《文章正宗》的文体以“叙事”命名,其体例的创新性有二:一为其创制的“叙事”文体,从文体分类上说,可以笼括所有“叙事”文字及其各种文体,既可录《左传》、《史记》文字入集,又录以“篇翰”方式生成的“右史记事”的文字,如韩愈《圬者王承福传》、《何蕃传》,柳子厚《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以及碑、铭数篇; 二为解决了以往“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不成“篇翰”的问题。真德秀破《左传》以“年”为单位的记事而以“叙事”为单位,篇题为“叙某某本末”,如第一篇《叙隐桓嫡庶本末》,或“叙某某”,如《叙晋文始霸》。这些“叙事”,或为一年之中多种事的某一选录,或为一事跨两年度的合一,如“左氏”《叙晋人杀厉公》就是把成公十七年和成公十八年事合在一起为一篇。又其破《史记》以“人”为单位的“记事”,节录为以“事”为单位者,篇题为“叙某某”,如《叙项羽救钜鹿》、《叙刘项会鸿门》;虽然其亦有“某某传”,但却是拆《史记》合传整篇而单录一人之传者,如《屈原传》,且删略了原文所录屈原的《怀沙之赋》以及篇末的“太史公曰”,即“赞”体文字。总之,其“叙事”的构成是一事一篇,或一人一事一篇,其“叙事”作为文体可谓以“篇翰”方式生成。
现在讨论“叙事”何以能成为文体而入文章总集?
首先,社会需要把古文经典变为“作文之式”。宋初文坛,推尊韩、柳,提倡古文,陈师道云:“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后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5页。人们要学习古文以提高写作能力,写作能力就是“属辞比事”,《礼记·经解》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下。。“属辞比事”的典范就是《左传》的叙事。而文人对《左传》的崇尚由来已久,如杜预称《左传》“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春秋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06—1707页。。《史通·杂说上》论《左传》的叙事之美: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指《公羊》、《谷梁》)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第156—157,80页。
《史通·模拟》称:“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第156—157,80页。至《文章正宗》,以“叙事”为文体收录最多者即是《左传》的文字。宋时,学习《左传》古文以应课试成为时尚,姚铉《唐文粹序》:“五代衰微之弊,极于晋汉,而渐革于周氏,我宋勃兴……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躏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初编》,第3页。称编纂“古文”入总集是为了“求试者之急用”。而尤为突出的是,如吕祖谦生平研究《左传》,其自序《左氏博议》“为诸生课试之作”,“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吕祖谦:《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左氏博议》,又称《东莱博议》,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所谓“《博议》则随事立义”*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提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220页下。,“随事”就是“剪截”《左传》片段,“立义”就是评点。因此,宋代总集在注重“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阅读功能的同时,又“把古文经典变为‘制义之金针’”*吴承学语,见氏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五章《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本文所述多有受其文启发之处。。正是如此,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称“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有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真德秀:《文章正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6页。。
其次,历史的经验使“叙事”以“篇翰”方式成为文体。“剪截”具有整体性的优秀作品的片段以独立成体,在史书与总集发展历史的理论大厦与技术武库里,有成法可依。
一是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出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礼记·大学》,《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上。,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纲,将重要史实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437中,1763页上。。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出现,解决了“事”的独立问题,吕祖谦《左传博议》“随事立义”,为“剪截”《左传》“纪事本末”的片段提供了经验,如《文章正宗》“叙事”首列《叙隐桓嫡庶本末》,这当然是真德秀作为编纂者自定的篇名。
二是“剪截”《左传》“纪事本末”的片段,体例上必定要有所依。钱锺书云:“古人选本之精审者,亦每改削篇什。”*钱锺书:《管锥篇》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67页。《文选》就多有删节、合并,以下略举数例。《文选》卷40任昉《奏弹刘整》,李善注云:“昭明删此文大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61上,595页下。可见萧统出于《文选》整体的考虑,对原文有所删节。《文选》卷42曹植《与吴季重书》李善注曰:“植集此书别题云:‘夫为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谓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之下,盖昭明移之,与季重之书相映耳!”*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61上,595页下。顾农说:“由此可知《文选》本《与吴季重书》乃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实际上原来是两封信,这里给合为一信了。”*顾农:《文选论丛》,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46页。
五、经、史、子、集齐入总集与文学观念的新变
《左传》、《史记》可以“剪截”出“纪事本末”的片段独立成“篇翰”,以“叙事”文体入总集,那么,从观念与技术上讲,其他经、史、子应该也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入总集的。如曾为真德秀宾客的汤汉所编总集《妙绝古今》,卷1选摘《左氏》、《国语》、《孙子》、《列子》、《庄子》、《荀子》的文字,卷2选摘《国策》、《史记》、《淮南子》的文字。明陈仁锡编《古文汇编》,《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以经、史、子、集分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437中,1763页上。。清代《古文观止》,录《左传》、《国语》、《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礼记·檀弓》共70篇,还录有《史记》的《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滑稽列传》。其中《屈原列传》原为《屈原贾生列传》,删略了屈原《怀沙》及贾生的事迹。《滑稽列传》只录淳于髡事迹,其他删略。又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收录经、史、子三类的文章,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分量,这是超越传统集部的总集,涵括经、史、子、集四部,把中国古代具有魅力的文章乃至片段文字都笼括进来,所谓一个也不能少。而我们今日的诸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也是经、史、子、集的作品都录的。于是我们想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把经、史、子、集的文章都当作文体来论述的。而从文体学上讲,文体生成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路走来,发展成为各自界域明晰的文体,又能够走出其原有的诸如经、史、子、集之类的集合体而融入新的集合体。在这个过程中,文体或自我改变,或不断丰富并发展,文体学也在如此的过程中前进。
【责任编辑:张繤华; 责任校对:张繤华,李青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001-09
作者简介: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桂林541004)。
*收稿日期:2014—05—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