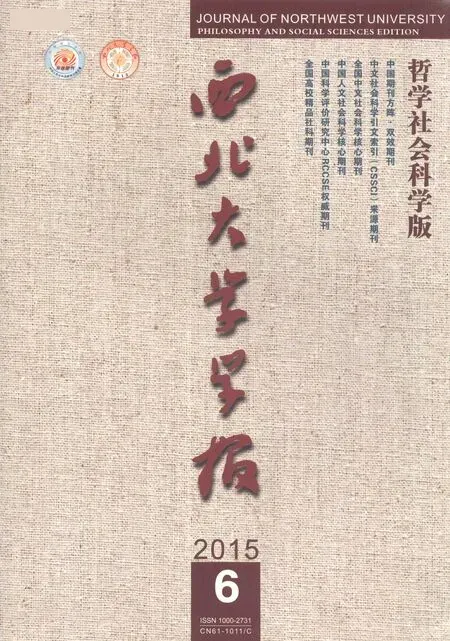别有忧愁写心曲——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创作心态成因考论
2015-02-22黄胜江
黄胜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3)
别有忧愁写心曲
——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创作心态成因考论
黄胜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230053)
摘要:通过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赵眠云《心汉阁杂记·双星会》及剧本的文本细读,可推考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与青楼女子周麟官曾有一段不被世俗认可的情缘,司马章的二种剧作正是围绕此段悲情而自伤怀抱、隐怨吟哦的写心自喻之作。司马章这一写心自喻的创作心态与乾嘉之际的文化环境和剧坛风习密切相关,有多向度的文化成因:清中叶激涌的人文思潮对人之个体价值肯定的影响,明末清初以来写心剧风潮所带来的强烈个人化倾向之影响,南京地区繁盛的青楼戏曲文化之影响,宗法等级社会对青楼戏曲文化的压制偏见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章;写心自喻;创作心态;文化成因
一、司马章及其剧作述略
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双星会》《花间乐》二种传奇,清人未见著录。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二著录,谓存钞本,见《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有乾隆壬子(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傅惜华旧藏[1](P1381-1382)。陆萼庭《曲目拾遗(初稿)》著录司马章《双星会》(传奇),依据《随园诗话补遗·卷三》所录司马章《浪淘沙·辛亥记游》词中“辛亥”为乾隆五十六年,推测其为乾嘉间人[2] (P314)。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将《双星图》列为司马章名下[3] (P 586),但此《双星图》为清初邹山所作,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五集》,非司马章作。《中国曲学大辞典》著录司马章二种曲目,与庄一拂著录同,且注明“未见”[4] (P 520)。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亦著录司马章二种曲,云归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剧作文本形式描述同庄一拂氏,且二书皆未获见,待查[5] (P1084-1085)。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乾隆五十七年条下著录本年司马章《花间乐》《双星会》有种石山房刻本,两剧皆未见,生卒及生平事迹未详[6] (P 465)。王永宽《中国戏曲通鉴》乾隆五十七年条著录情况同程著,两种剧作皆未见[7] (P 715)。《中国剧目辞典》介绍司马章云:“清人,生卒年月不详。字石坡,江苏南京人。所作传奇有《花间乐》《双星会》二种,均存。”[8] (P 1129)《金陵录鬼簿》载南京剧作家司马章生卒年不详,剧作有乾隆刊本,故知为乾隆或乾隆前人。剧作内容不详[9] (P 40-41)。
以上是迄今关于司马章及其二种剧作的基本著录情况,可知目前学界外关于司马章及其剧作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成果多属于目录性质的,且颇多讹误,理论探讨更处于空白状态。笔者有幸阅读《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15册所收的司马章二种剧作[10],对司马章及其两种剧作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和感受,并先后撰成几篇习作,对其生平事迹、剧作内容、交游著述、艺术特色等作了初步分析,今欲对其制曲心态及其成因略加考述。
南京人司马章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后裔,由附贡生捐纳县丞,嘉庆后期为蓟州知府,工于词章,颇有政绩,年少多才。其生活时代约为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之交。《种石山房二种曲》,今存,其中《双星会》传奇作于乾隆五十五年,《花间乐》传奇应在《双星会》前不久完成。《花间乐》传奇,不分卷,21出,剧演上界菊花仙史秋英、牡丹仙史香玉、奈冬仙史绛雪因一笑之缘,历经尘缘,重登仙班之事。《双星会》传奇,不分卷,13出,剧演德、慧二星离合了悟之事。其剧作内容集中在追求自由的男女至情真爱、批判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透露士人的悲情哀绪等方面[11]。
二、司马章写心自喻之制曲心态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中给《双星会》的写作缘起作了一个较详细的脚注,他说:“白下秀才司马章,字石圃,风神潇洒,年少多情,与周麟官校书有三生之约,而格于家范,乃撰《双星会》曲本,以舒结轖。”[12](P641)女校书是对有文才的妓女之雅称,亦省称“校书”。周麟官何许人,不可确考,但从其名字后面的“官”字看,多是一个善唱戏的青楼女子。因为清代不少戏曲演员多以某某官为艺名,如在张次溪编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优伶以“官”命名,袁枚的《歌者天然官索诗》也可为证。赵眠云在其《心汉阁杂记·双星会》中更详细地披露了司马章《双星会》传奇的创作背景:“《双星会传奇》,上元秀才司马章石圃所撰。石圃身长玉立,有潇洒出尘之致,与某校书有啮臂盟,事为父知,遂托人荐至京中处馆,并令试北闱,不许南还。石圃虽恋某妓,不敢违父命,乃撰此传奇,以写胸中抑郁。有《南柯子》词一阕云:‘渡口传桃叶,溪头说范云。笑他街巷说纷纷,都把才郎心事作新闻。 心结愁千缕,人归瘦几分。内人不解问殷勤,今日眉头真个为谁颦?’后某校书适人,石圃知之,以词遣意,有‘从今无计会双星’句。”[13](P96-97)
原来《双星会》传奇是司马章述怀写心、自伤怀抱的隐怨吟哦。其实,司马章连续创作的两种传奇都是围绕其这段悲剧恋情展开的写心自喻之作,除了上举二例材料为证外,还可从剧作中找到印证。如《种石山房二种曲》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世境况与司马章和周麟官自身情况吻合;《种石山房二种曲》的序跋题词及部分曲文,也提示我们这两种剧作是剧作家的写心自喻之作。顾椿年《花间乐后跋》云:“《花间乐院本》,剧为曲江倦游人吐气。”被父逼往京华的司马章,无意科举,心恋旧人,抑郁无奈,干脆以传奇补恨遣怀,一浇胸中块垒。任康《双星会传奇序》亦云:“借洛神而赋怨,托巫雨以言怀,总由怨莫能偿。……然而命不由人,千秋一辙,事难如意,大抵皆然。”“怨”“蕴”“填”“写”“借”“托”“命”七字,已经将司马章这段不被家长认可的恋情委婉道出,得之为幸,不得为命,不得则只能将满腹幽情寄托于戏文之中了。《双星会·提纲》直接说:“楼上吹箫,筵前驻拍,一春留念平康,少年孟浪。回首恨茫茫。此日重寻旧事,风流客亲上俳场。”[14]已将司马章少年孟浪的情事明白道出,他已是“亲上俳场”,自报家门。
三、司马章制曲心态之文化成因
司马章的这种“别有忧愁”、不便言明的写心自喻创作心态,并不是一种偶然与冲动,背后有着多向度的文化背景与时代思潮在影响。
首先,清中叶激涌的人文思潮对人之个体价值肯定的影响。明清易代,满族统治者以赫赫武功廓清天下,定鼎江山,又以煌煌文治牢笼天下,驯化人心,创造了延续百年的“康乾盛世”。此时清王朝全面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倡行理学、禁止结社、开博学宏词科以笼络文化领袖,修四库全书以考据消磨异端锐气,同时大兴文字狱以威劫文心。康乾文坛上充斥复古之暮气,大行风化之旧说,横溢清真雅正之格调。随着封建制度烂熟后的极盛而衰,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苏,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哲学与文艺领域反理学、反汉学、反复古、反诗教,重自然真情,追求个性解放,高扬主体意识,崇尚艺术个性的人文思潮再度兴起[15](P23)。戴震以经学明道,高扬理性批判的人道哲学大旗,斥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16](P174),揭穿了程朱理学残酷虚伪的本质,力主满足人的正常欲望:“体民之欲,遂民之情。”这股潜涌的人文思潮关注个体本真生存状态,尊重个体尊严与个体欲望,注重主体意识的表达,追求平等的人格,略具近代人本主义的气息,表现在文艺创作上,注重个体主观精神性灵的展示和自我意识的张扬。石涛的《画语录》关注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 郑板桥标举“自写性情,不拘一格,有何古人,何况今人”[17](P150)。蒋士铨主张“空诸依傍,独抒性情”。而袁枚的“性灵说”文学观更是清代文学解放的大纛,主张以灵巧的诗才抒发饱含个性机趣的真情实感。他在理论上强调“提笔先须问性情”“性情以外本无诗”,标榜“自把新诗写性情”[18](P62、567、275),强调带着“我”这一个体色彩,“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要求诗歌抒写个人的性情,这种性情必须真实,符合诗人的“自我”。他在创作上的确也做到了“诗写性情,惟吾所适”[19](P3)。以袁枚为核心的性灵派影响巨大,郭麐《灵芬馆诗话》云:“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20]同在南京生活的袁枚与司马章存在交游关系,必然受到袁枚关注个体本真价值,提倡独抒性灵文学观的影响,况且袁枚将男女之情作为其“性灵说”创作的重要题材:“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21](P527)按此观点,司马章那份难以明说的恋情是非常适合抒写的题材。
其次,明末清初以来写心剧风潮所带来的强烈个人化倾向之影响。“制曲者,文人自填词曲以陶写性情也。”[22](P52)明中叶以来梁辰鱼、陆采、郑若庸、康海、王九思、徐渭、汪道昆、杨慎、王衡等大批文人介入戏剧创作,产生了大量的文人剧。戏剧这种代言体形式与长短伸缩的体制容量,加之传统意义上将其视为不入主流的私语化文体观念,文人曲家将传奇杂剧作为写心抒情、立传自述的抒情诗与讽刺小品散文式的拟剧体来经营,在粗线条的叙述中寄寓内心情思,濡染浓重的个人色彩,主体意识表达凸显,呈现出浓重的审美趣味个人化倾向。他们或以遭际、身世、性情相似的剧中人代为立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或以自我入剧,现身说法。明末清初以来更是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写心剧风潮。尤侗的《西堂乐府》全然“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极致而后已”[23]。尤其是廖燕的《柴舟别集》直接以己身入剧,主人公即名廖燕,纯然自述之作,开一代写心剧新风习。乾隆时期更是出现了大批写心剧,如徐燨《写心杂剧》、曾衍东《述意》、黄振《石榴记》、唐英《虞兮梦》、顾森《回春梦》、蒋知节《秋竹山房二种曲》、丁秉仁《绣锦台》等均是其代表。乾隆四十三年徐燨的《镜光缘》传奇以乾隆二十八年徐爔与青楼女子李秋蓉相识、爱恋以及因人作梗而死别为线索,“兹之所谓《镜光缘》者,乃余达衷情、伸悲怨之曲也”。“十六出,比诸小传一篇,纪其始末。……乃余高歌当哭之旨也。”[24](P1836)剧作以其名字“余羲”入剧,女主人公李秋蓉和余羲之妻钱氏则径取现实人物之真实性名,乃缅事怀人的悲情之作,这与司马章《种石山房二种曲》用意、手法完全一致。而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十年间真实展示徐燨心态史的《写心杂剧》,在写心剧史上更是一部具有“范式”意义的作品。同样为袁枚好友的徐燨与司马章[25],同在江南,同样的创作方式,相仿的创作时间,他们之间或许存在相互的影响。乾隆四十四年顾森著《回春梦》亦以其真名入剧,其《自序》云:“《回春梦》何由而作也?伤余生平之命蹇也。……藉此消胸中块垒。”[24](P2046)当然嘉庆以降还有左潢《兰桂仙》传奇、舒位《瓶笙馆修箫谱》、张声玠《玉田春水轩杂出》、杨恩寿《桃花源》、汤贻汾《逍遥巾》、周实《清明梦》等写心剧。完全可以理解,习染于浩荡的写心剧创作风潮,乾隆后期司马章创作了《种石山房二种曲》两种写心之作。
再次,南京地区繁盛的青楼戏曲文化之影响。作为六朝古都,明清以来南京以其优越的政治地理区位和发达的城市经济,造就了城市娱乐业的繁盛。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余怀《板桥杂志》亦追忆晚明南京青楼盛况云:“妓家分门别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酒淫淫,兰汤艳艳,衣香一园。亭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扌刍筝,梨园扮演,声彻九霄。”[26](P4994)清中叶南京和附近的扬州下里河地区更是青楼戏曲繁盛之地。乾隆末年珠泉居士著《续板桥杂记》云:“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乾隆四十一二年间)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享上下,照耀如画。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酉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靡费。真风流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26](P5053)六朝金粉,山温水软,一河风流,两岸笙歌,秦淮宴游之乐,繁盛无比。可谓承平日久,风月撩人,大可征歌选色。乾嘉之际的捧花生在《花舫余谈》中说:“凡有特客,或他省之来吾郡者,必招游画舫以示敬。”[27](P264)南京元代就形成了“金陵曲派”,明代南都教坊演剧更是名闻天下,南京的书坊更是刻印了大量曲本,民间高淳高腔与目连戏十分活跃。清代康乾时期江宁织造府组织了大量演剧,成为南方戏曲北上的重要推介窗口。乾隆年间南京知名文人曲家就有张坚、王金英、程廷祚、汪恺等五人,数量在全国仅次于上海与苏州。狎妓听曲已成为当时的官场风气、士林风习。郑板桥对同性恋者表示理解,袁枚更是风流韵士,《秦淮闻见录》云乾隆末年双湖太守禁妓,简斋太守以诗解之,赵云菘观察翼戏题五绝句。在这样一个青楼与戏曲文化繁盛的都市,司马章年少多情,将自己的这段与青楼女子的情事以戏曲形式抒写便是非常自然之事。且当时的青楼娱乐文化在司马章剧作中亦有反映,《双星会》第四出《宦闲》叙述了淮扬安抚使秦正收到好友来文,并寄上两本书,一部江宁人编著的《花间乐》传奇,一部评点淮扬名妓的《群芳小谱》,后书中记载秦娟娟善唱《花间乐》新曲。值得注意的是花谱《群芳小谱》中载录了秦娟娟的芳名,而这正与清中后期出现的“花谱热”有关。幺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一书认为以乾隆五十年《燕兰小谱》的出版为标志形成了一股花谱热,这是以伶人为宣传对象、商人运作、文人参与商业操作的娱乐盛事[28](P327)。《群芳小谱》就是一部花谱性质的著作。《花间乐》第七出《俗赏》在反映了当日狎玩年轻男性伶人的风习,并留存了一副戏班的史料。该出演官宦公子哥卜知事应花神庙道士邀请至庙中赏花,其间因取乐,道士派人到城中找来一班戏子相公,道士吹嘘道他们“都是有名的相公,都是城里大财主赏识的。”后来让他们演出了《牡丹亭·堆花》一折,其后让其以歌侑酒。这副班子叫作“庆华班”,当日到场的演员有本班领袖陈桂林以及红相公施五官、项元宝、陈德元。历史上实有“庆华班”,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梨园总局,是昆班艺人聚会议事的公所。为了修砻老郎庙,苏州的戏曲行会如意会、水安会和众多的昆班及艺人纷纷捐助银两,在《历年捐款花名碑》上留下了记录。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起,到四十六年(1781)五月止,其中第二十三个戏班便是“庆华班”[29](P217)。
第四,宗法等级社会对青楼戏曲文化的压制偏见造成的影响。多数青楼女子是不得已而误入风尘,内心的贞操观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慕冲动,她们多忍辱求伸自救自信,心怀脱籍从良。从文人士子方面看,一则妓女尤其是艺妓的艳丽姿容、风流举止、妙曼伎艺、诗词酬唱,使他们寻找到新奇快感,二则妓女是礼教的弃儿,是毫无负担的交流,文人与妓女可能相互理解甚至成为知音,使文士暂时脱离枯燥冰冷的门第宗法与家庭伦理规范,获得片刻假性自由。《双星会·友聚》便云:“人间难觅会心人,向群芳来乞怜,果能够花神怜惜心相印,不羡闲题品,都忘俗讲论。”三则歌妓的演唱可以增强文士诗词作品的传播效果。从妓女方面看,一则妓女倾慕文人士子的风华才情与艺术趣味,二则欣赏文人士子风流自赏的浪漫人格和怜香惜玉的求爱方式,三则文士的题品可以增强妓女的知名度。从社会地位来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赉志没齿无异也”[30](P126)。娼妓与士子对外物本主之有待,根本上均缺乏自我确认的独立性,尤其是她们失意之时,“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促使二者相互理解和慰藉。出于人格尊严的理解与爱抚,主体意识的参与和真挚情感的投入,使得青楼女子与文人士子之间便产生割不断的情结,形成了彼此依倚、互相推毂的互补关系。然而明清以来随着理学名教之鞭挞、社会稳定之考量,公权力必然对青楼采取控抑的态度。明代的《菽园杂记》早就记载道:“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狎妓宿娼有禁,至罢职不叙。” 清初统治者反思晚明纵欲亡国的乱局,对娼妓现象大力抑控,康熙初年废除教坊司,裁掉宫妓女乐,雍正元年下令废除乐籍,从法律意义上废除了妓女制度。《扬州画舫录》云:“官妓既革,土娼潜出,……一逢禁令,辄生死逃亡不知所之。”《金台残泪记》重申:“本朝修明礼义,杜绝苟且。狎妓宿娼,皆垂例禁。”对于象征礼教道统的文士,更是严加整饬,《大清律例·刑律》规定监生、生员“狎妓、赌博”,问发为民,治应得之罪。 “监生生员……狎妓赌博……者,问发为民。褫革治以应得之罪。”[27](P259)社会舆论之歧视,自我贱视的奴化心理,娼妓被视为社会的异常存在。
优伶是古代奴隶制度的残余,其出身低贱,常遭到歧视、禁锢与摧残,没有独立人格与社会地位。上至国法律令,中有族规乡约,小到家规训示,众多的礼俗禁忌,使艺人沦为供既得利益阶层声色享乐的弄臣奴仆,戏曲艺术逃脱不掉被玩弄的地位。历代戏曲禁毁不绝如缕,王利器先生的《元明清三代禁毁戏曲史料》可谓一部戏曲艺人艰难生存的血泪景观史。“既称义门,进退皆务尽礼,不得引进倡优,讴词献技,娱宾狎客,上累祖考之嘉训,下教子孙以不善,甚非小失;违者,家长箠之。”[31](P170)婚姻方面对优伶更是禁忌重重,一般实行优伶行业内群婚配,禁止良家与优伶婚配。《元典章·卷十八》规定:“乐人只叫嫁乐人,咱每根底近行的人,并官人每,其他的人每,若娶乐人做媳妇呵,要了罪过,听离了者。”明清法律规定优伶与良家通婚,杖责一百,若官吏娶优伶为妻妾,杖责六十。如此,官宦良家可以与优伶逢场作戏,但忌惮法令的惩戒和舆论的压力扦格,他们基本不会与优伶通婚的。李渔曾说“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32](P252)原来司马章和一个善戏曲的妓女缘定三生,在“家范”看来,这怎么了得、成何体统!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三六九等,不能混乱。士为四民之首,而娼优卒隶同属下九流的底层贱民,父母大人、亲戚朋友绝不会允许这段孽情实现的。这是司马章与周麟官悲剧的直接原因。
四、结语
综上,司马章写心自喻创作心态的文化成因是多方面的,在南京地区繁盛的青楼戏曲文化环境中,波染于清中叶激涌的肯定人之个体价值的人文思潮,基于少年心性的叛逆和陶情风月的浪子情怀,司马章与一位擅长戏曲的青楼女子相恋,但却受到世俗礼教的压制与否定。乘着明末清初以来写心剧风潮,满腹才情的青年司马章将一腔难言之情,化作《花间乐》《双星会》两种写心自喻的传奇,进行了自我虚幻的补偿与结轖之纾解。
参考文献:
[1]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3] 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4] 齐森华,等.中国曲学大辞典[K].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5]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6] 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8.
[7] 王永宽.中国戏曲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8] 《中国剧目辞典》扩编委员会.中国剧目辞典[K].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9] 《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南京分卷》编辑室.南京戏曲资料汇编:第一辑[G].内部刊物,1987.
[10] 吴书荫.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第15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11] 黄胜江.清中叶曲家司马章及其剧作发微[J].名作欣赏,2012,(12).
[12] 袁枚.随园诗话校注[M].顾学颉,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3] 赵眠云.云片[M].郑逸梅,校.上海:中孚书局,1934.
[14] 吴书荫.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第15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15] 王英志.性灵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1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 郑燮.郑板桥文集[M].吴可,校点.成都:巴蜀书社,1997.
[18] 袁枚.袁枚全集:第一集[M].王英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9] 袁枚.袁枚全集:第三集[M].王英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0]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M].嘉庆二十一年刻二十三年增修本.
[21] 袁枚.袁枚全集:第二集[M].王英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2] 吴梅.顾曲麈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 尤侗.西堂杂俎二集:卷二[M].清康熙刻本.
[24]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G].济南:齐鲁书社,1989.
[25] 杜桂萍.论袁枚与乾嘉戏曲作家的交往[J].学习与探索,2009,(6).
[26] 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笔记小说大观:五编[M].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0.
[27]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8] 幺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9] 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K].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0] 李中馥.原李耳载[M].凌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31]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2] 李渔.李渔全集:第八卷[M].萧欣桥,点校.杭州:浙江古籍书版社,1991.
[责任编辑赵琴]
【文学研究】
There is Another Sad to Write the Song that from Heart:On the Writing
Mentality of the Mid-Qing Dynasty Playwright Sima Zhang
HUANG Sheng-jiang
(AnhuiAcademyofSocialSciences,Hefei230053,China)
Abstract:Through reading Yuan Mei′s Suiyuan Shihua Addendum Vol. 3 and Zhao Miamyun′s Xinhange Miscellanea,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id-Qing Dynasty playwright Sima Zhang had an unrecognized love with the brothel Zhou Liyuan. Sima Zhang′s two plays were works of his own story and image. Sima Zhang′s writing mentali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tradition of drama in the Jia - 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so it has multi-reas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personal values at that time; the trend of personalized writing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fluence of the brothel drama culture in the Nanjing area and the prejudice of social hierarchy towards brothel drama culture.
Key words:Sima Zhang; self-image writing; writing mentality; cultural formation
作者简介:涂年根,男,江西南昌人,博士,从事叙事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5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广义叙述背景下的叙事空白研究”(15WX07)
收稿日期:2015-04-11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