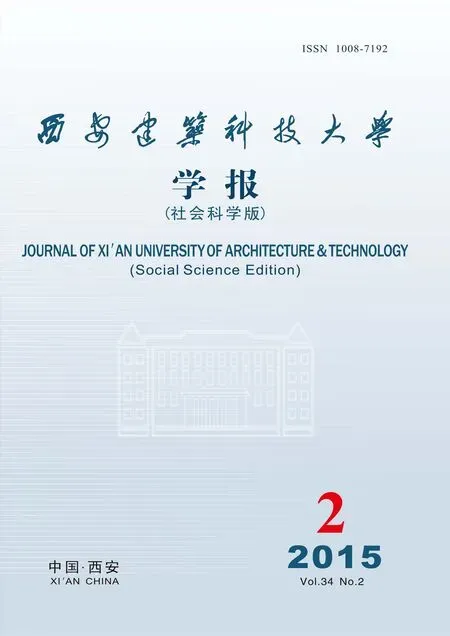论海明威作品的创作特征
——以存在主义为视角
2015-02-21覃承华
覃承华
一、存在主义与海明威的创作
哲学上的“存在”概念是指由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丹麦著名神学家、哲学家基尔克加尔(1813—1855)在19世纪率先提出了“存在主义”,并奠定了宗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后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该概念进行改造,创立了存在主义哲学[1]。这一哲学有时又被称为有神论存在主义。后来,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德国老师的影响下,剔除了这一思想体系中的宗教色彩,创立了无神论存在主义学派,紧密地联系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来考察人的生存问题。萨特是将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引入文学领域的第一人,其大量著作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的前景》、《辩证理性批判》等成为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奠基之作。由于萨特自身极力主张张扬个性以及信奉个人主义至上,其思想内容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反理性等倾向。独特的战争经历也对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残酷的战场体验迫使萨特逐渐放弃先前的个人主义,进而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冥想,并开始尝试以文学干预生活。因此,在创作后期他更加侧重联系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来考察人的生存问题。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常常将人物投放在对自身存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使其在近乎挑战极限的境遇中通过 “自由选择”领悟自己的存在。因此,存在主义文学注重描写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以及无限恐惧的阴暗心理[2]。
从存在主义视角考察海明威的作品,发现他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存在主义特征。和许多存在主义作家一样,海明威试图借助创作活动实现人生哲学与作品的融会贯通,并通过小说艺术形式深入详尽地描绘了人物的厌倦、恐惧、孤寂、烦恼、迷惘甚至绝望,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存在的不易后深刻领悟存在的本质。在他的创作活动中,海明威常常以战争、狩猎、滑雪、斗牛、饮酒、谈情说爱为题,但他的真实意图绝不是简单的描写上述主题;而是着力描写在这些空间或场所中活动的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注重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呈现他们的生存状况。海明威惯于设置“圈套”,将主人公设置其中,让他们“自由选择”以便仔细察看他们的勇气、胆识并考验其人格与尊严。由于这些“圈套”往往涉及危险,海明威的作品大多都有一个主题:死亡。为了突出这一主题,探索人的本质并描绘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则是他一切作品的主旋律。海明威一生留下了许多有关“迷惘”、“暴力”、“死亡”的作品,其中一致公认具有典型存在主义特征的首推他的长篇《太阳照样升起》和短篇《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这一特征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二、海明威作品存在主义创作特征
概而言之,存在主义对海明威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海明威的作品与存在主义一样注重对“环境”的突出强调和对“人”的主观感受的刻意描绘,尤其注重呈现人物的境遇和思维活动。其次,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苦难方式也深深影响了海明威的创作。荒谬、厌恶、绝望等体现人的存在状态的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总之,海明威在思想和创作上与存在主义有着自觉不自觉的深刻契合。具体来讲,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文学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人物刻画上的“存在先于本质”、以“荒谬”和“痛苦”为基本主题、人物行动上的“自由选择”以及“他人即地狱”的环境描写四个方面。
1.人物刻画:“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最基本的观点[3]。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所谓 “存在”,就是个体“自我存在”,“自我感觉到的存在”。如果“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自我”先于本质。换言之,人的本质由“自我”决定,其他一切均对“自我”存在构成威胁。综观海明威的作品,无论是成长小说系列中的尼克·亚当斯、《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丹,还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以及《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都是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典型。在海明威笔下,他们首先是一个个普通的人,都存在于种种于己极为不利的困境中。这是他们的自我存在。后来,通过逐一排除各种威胁,终于实现了自我价值,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英雄,,体现了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这种从“存在”再到“本质”的人物刻画顺序,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观点的生动诠释。
尤其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堪称“存在先于本质”的典型人物形象。首先,小说开篇“他是一个独自在湾流中钓鱼的老人”一句便点明了老人的生存状况:老无所依的渔夫。具体地说,“独自”暗示了老人的社会关系——无依无靠;“钓鱼”则表明了老人的职业——以捕鱼为生;“老人”突出了圣地亚哥的年龄特征。寥寥数语,鲜活地勾勒出了圣地亚哥老无所依、孤寂凄苦的生存状态。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海明威先后描绘了圣地亚哥的皱纹、眼睛、良性皮肤癌以及肩膀等,再次暗示了老人作为“人”而存在的艰辛。如果说饱经风霜的外表表明了圣地亚哥存在的艰辛,连续八十多天没捕到大鱼则表明了他作为一名渔夫的彻底失败,而且更直接威胁到他赖以存在的基础和作为渔民的尊严。其次,捕到大鱼后的几天几夜让老人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人”而存在的本质: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在短短的几天中一扫过去的失败者形象,使自己的生命大放异彩,体现出崇高的人生价值。尤其是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依然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与劲敌战斗到手无寸铁,是一副高尚、可敬的“胜者无所获”的英雄形象,极大地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之所以海明威把时间紧紧锁定在几天几夜,是因为在或长或短的人生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往往是一瞬间。对大多数人而言,一瞬间既能体现出人生的高贵与本质,也能使人丧尽尊严与人格。关键取决于关键时刻个人的选择。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自己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创造的,不是给定的。在紧急关头,圣地亚哥勇于面对挑战并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这既是自己果断选择的结果,也是力排险情(他人即地狱)的结果。因此,圣地亚哥是一个“存在先于本质”的典型人物形象。
2.基本主题:“荒谬”和“痛苦”
“荒谬”和“痛苦”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为了突出这两个主题,存在主义者常将其主人公置于极为险恶的环境中或尔虞我诈的现实中,人间遍布冲突、丑恶和罪行,使他们切身感到荒谬、痛苦的存在。由于存在毫无安全感和幸福感,人物总是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中,因此,存在主义文学十分注重对人物的虚无、迷惘、绝望甚至死亡情节的描写,使其命运体现出不可抗拒性和极强的悲剧性。
《太阳照样升起》体现了“荒谬”和“痛苦”的鲜明主题。小说以 1924—1925年这一历史时段和名城巴黎为背景,围绕一群在感情或爱情上遭受过严重创伤或者在战争中落下了严重心理或生理机能障碍的英美男女青年放浪形骸的生活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展开,反映了这代人意识觉醒后却又感到无路可走的痛苦、悲哀的心境。通过对主人公们之间的爱情进行剖析,发现各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十分荒谬,因而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痛苦:美国青年巴恩斯虽然和英国人阿施利夫人相爱,但巴恩斯由于因伤失去性能力,而夫人阿施利又一味追求享乐,他无能为力,只好借酒浇愁。为寻求刺激,两人和一帮男女朋友去西班牙参加斗牛节。无法满足欲望的阿施利内心斗争激烈。她虽成功拒绝了犹太青年科恩的苦苦追求,却迷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然而,在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施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尽管她明知无法获得性福,阿施利最终又回到了巴恩斯身边。在这几对人物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荒谬,因此痛苦的结局是必然的。《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用存在主义思想在文学上所做的一次“试验”。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表现出他的存在主义思想[4]。
《永别了,武器》详尽地描述了战争的荒诞性。主人公亨利以为参军光荣而走上战场,但当他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后转而厌恶战争,认为“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牲场”。于是,他开始逃避并企图以爱情来忘却战争,然而爱人凯瑟琳又因战争失去生命,彻底毁灭了他的爱情。这个怪圈正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无论尤瑟林怎样努力,都逃不出军官布置的圈套。
《老人与海》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存在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主题。圣地亚哥连续八十余天没捕到鱼,其他渔民不仅没有同情和关怀这个无依无靠的、倒了血霉的老渔夫,还对他冷嘲热讽。唯一有爱心、对圣地亚哥倾心关照的曼诺林却又因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离开他。这种冷漠和无情使圣地亚哥切身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和存在的荒谬。但是,曼诺林走后,他就时来运转,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但鱼实在太大,迫使他“被钓”了几天几夜,最后他奋力一搏才将其杀死。正欲将大鱼拖回渔港扬眉吐气,可又被鲨鱼吃的所剩无几,靠岸时只剩下一副大鱼骨架。在和大鱼以及鲨鱼周旋期间,圣地亚哥数次提到曼诺林,“I wish the boy were here”.这是绝望无助之际的深情呼唤,但呼唤之后依然是绝望无助。可以说,圣地亚哥捕到大鱼前是痛苦的,捕到大鱼的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捕到大鱼后更是苦不堪言。捕鱼前的冷嘲热讽、捕鱼中的绝望无助、捕鱼后的垂死挣扎使得圣地亚哥尝尽了活着的辛酸。这实际上是一个缩影,暗示了圣地亚哥一生的痛苦。
3.人物行动:“自由选择”
关于对“荒谬”和“痛苦”这个问题的解决,存在主义者认为,只有行动起来创造价值为自己争得生命的意义,体现出“压力下的优雅”,才能扭转“荒谬”消解“痛苦”,最终捍卫尊严。这就表明,作为存在的人必须做出“自由选择”。
“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认为,正确的“自由选择”是扭转“荒谬”消解“痛苦”的有力武器。由于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若果一个人连选择的“自由”都没有,他的存在不仅荒谬、痛苦,更谈不上尊严。萨特认为,人在抉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正是一个个自由的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才使得每一个具体的人有了自己特定的本质。由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有的人在“自由选择”中因坚持正确的选择成功扭转“荒谬”消解“痛苦”,最终捍卫尊严,体现出强烈的“存在”;有的人则在“自由选择”中因选择错误不仅没能扭转“荒谬”消解“痛苦”,而且丧失尊严,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
因此,萨特主张,存在主义文学不应按照传统文学那样去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不应让人物选择环境,而是应该让环境支配人物;应该为人物设定“圈套”并将其放置其中,让他们在“自由选择”中体现存在的意义。因此,存在主义文学往往以悲剧结束。海明威的作品与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太阳照样升起》中的“自由选择”十分明显。首先,小说标题本身就暗示了自然物体的“自由选择”:太阳升起与落山是它自己选择的;这一选择是理性的(选择落山才能照样升起。不选择落山就无所谓升起)。其次,主人公们也在进行一次次选择:巴恩斯首先选择了和阿施利相爱;阿施利选择拒绝科恩;阿施利先选择接受罗梅罗后又选择离开;阿施利最后又选择巴恩斯。从这一系列的选择可知,虽然大部分选择都是“非理性”的,但是他们最终都以理性的方式接受和承担其结果。如太阳的选择符合自然规律一样,这些人物的选择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和道德规范。
几乎海明威所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进行某种选择。他们有的选择挑战如圣地亚哥;有的选择等待死亡如安德烈森;有的选择逃避如《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的老顾客;有的则选择推卸责任如《白象似的群山》中的男主人公,等等。这些都是主人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 “自由选择”,具有极强的自主性。《赌棍、修女、收音机》描写的是赌棍、修女、收音机的主人等三种人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做出的不同选择。在《丧钟为谁而鸣》、《过河入林》中,海明威则让乔丹和坎特威尔主动选择了死亡。显然,在海明威的笔下,“死”一倍赋予崭新的含义:它不仅是人生结局,更预示新的开始。这正如太阳落山之后又必然会再次升起一样。
总之,海明威作品中主人公的 “自由选择”十分明显。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极限境遇中自由地做着各种选择。尽管同为悲剧,但一副副“压力下的幽雅”模样仿佛使他们更可谓英雄人物。
4.环境描写:“他人即地狱”
由于过度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否定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否定他人的价值。存在主义者认为,个人价值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他人永远分离对立;社会、他人是“自我”的天敌,时时威胁着“自我”的存在,“他人就是(我的)地狱。”因此,存在主义文学往往涉及不利的环境描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主人公因环境、他人而酿成死亡等悲剧。
成为作家后,海明威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书写死亡,“死亡”是他作品的永恒主题。海明威始终如一地书写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早期的经历,这些经历不仅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而且造成恐慌与压抑,并最终形成对死亡的恐惧、焦虑[5]。这些挥之不去的自身经历,经过艺术升华后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成为他消解对死亡的恐惧、焦虑的一种秘密武器。对此,董衡巽曾指出,对死亡的恐惧是海明威个人亲身经历的关键,也是他的整个形象和风格体系的关键[6]。明威作品中的硬汉人物实际上是置身于死亡环境中的人格面具,他们均遭受着“他人即地狱”的考验:斗牛场上的要么人死、要么牛亡;战场上的“古来征战几人回”(乔丹、亨利等);狩猎、拳击、钓鱼过程中的随时都会出现的“极限”挑战。显然,“他人”严重威胁到人的“存在”,人随时面临死亡。在《死在午后》中,海明威明确指出,“所有的故事,要深入到一定程度,都以死为结局,要是谁不把这一点向你说明,他便不是一个讲真实故事的人”[7]。
由于“死亡”是地狱的前提条件,海明威总是在作品中突出强调恶劣环境描写并将人物投放其中,以此映衬他们的不幸。在诸如《在我们的时代里》、《战斗者》、《印第安营地》、《密执安以北》、《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等短篇以及四大名著(《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四部作品被称为海明威的四大名著)中,都不同程度涉及到死亡书写。“仔细研究海明威的全部著作,几乎可以编撰一部‘死亡学’的详尽注解”[8]。海明威一面书写死亡,同时对人生的终极意义、归宿以及如何面对死亡做出了深邃的思考。如果说“他人即地狱”作为客观存在不可避免,海明威则深入探讨了人在“地狱”中如何存在、如何主观选择等基本问题,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死亡”哲学。
三、结 语
海明威是20世纪广受关注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与海明威相关的性别模糊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态问题以及流派归类问题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海明威的创作是否与存在主义存在某种关联也是一个不能妄加断言的问题。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流派,它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反映。存在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是现代派文学中声势最大、风靡全球的一种文学潮流。主要表现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达到高潮。就时间而论,海明威的创作生涯( 20年代—60年代初)明显早于存在主义。但是,纵观海明威的作品,几乎所有都和某种存在主义存在深刻契合,尤其是短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与萨特等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海明威作品中的各种“境遇”以及主体在其中所做的“自由选择”也与萨特小说《墙》、戏剧《死无葬身之地》等“境遇文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以海明威的作品为基础,主要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梳理、分析和探讨了海明威小说的创作特色,发现这些作品在创作手法上存在十分突出的存在主义特征,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
[1] 蒋澄生,廖定中. 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精粹[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30-131.
[2] 覃承华. 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M]. 绥化学院学报,2007(6): 81-83.
[3] 王堪林.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海明威小说《太阳照常升起》[D]. 西北大学,2005.
[4] 覃承华. 死亡主题与硬汉人物:海明威的焦虑呈现与消解[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134-136.
[5] 苏明海. 生活·创作·创伤:从文学与治疗的角度看海明威及其创作的复杂[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20.
[6] 海明威. 午后之死[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32.
[7] 滕永文. 试析海明威早期小说作品中的死亡意识[J]. 江苏社会科学,2009(3):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