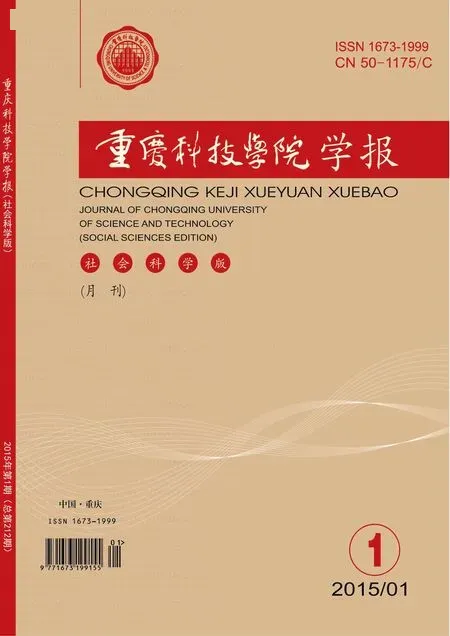试论对《论语·学而》第一章的解读
2015-02-21庞明启
庞明启
试论对《论语·学而》第一章的解读
庞明启
依据程树德《论语集释》中的有关引述,分析了古代学者对《论语·学而》第一章三句话的注解。根据各家的不同解读,认为这三句话之间有两种逻辑关系:一种关系显示三句话的重心逐渐由“学”转到了“教”;另一种关系则显示三句话的内容始终没有脱离“学”的重心。从整体来看,《学而》篇第一章是紧紧围绕“学”来展开的,指明了学习的途径、品格、目的和境界。
《论语》研究;《学而》篇;注解;考据;义理;逻辑
《论语》以“学”开篇。《学而》篇首章共三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于这一章的三句话,历来注家各有解释,程树德(1877-1944)在其编著的《论语集释》中有详细引述。三句话三层意思,相互间又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一、关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集释》引述《论语集解义疏》解释“时”:
皇侃《义疏》:曰者,发语之端也。许氏《说文》云:“开口吐舌谓之为曰。”(按:今《说文》无此文)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爲时,二就年中爲时,三就日中为时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扞格,幼迷昏。故《学记》云:“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是也。既必须时,故《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并是就身中为时也。二就年中为时者,夫学随时气,则受业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是也。春夏是阳,阳体轻清,诗乐是声,声亦轻清。轻清时学轻清之业则爲易入也。秋冬是阴,阴体重浊。书礼是事,事亦重浊。重浊时学重浊之业亦易入也。三就日中为时者,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故《学记》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时是日中之时也[1]2。
此段注释,主要就“时”而言。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简称《皇疏》)将“时”理解为选择合适的时间,犹“农时”之“时”也。亦犹《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之“时”。《皇疏》所言“身中”、“年中”、“日中”三时,分别对应合适的学习年龄,以及不同年龄合适的学习内容,不同季节合适的学习内容,并不同年龄、季节及其对应之学习内容日日不辍之功。可见,“日中之时”乃涵盖“身中”、“年中”并加意义的延伸。此“时”乃“日中之时”。“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并为学习之不同方式与内容,同时对应着不同的学习时间。年岁不同,身心与智力发育程度不同。一年寒暑温凉不同,身体与精神状态各异。无论何年何月,学习乃一以贯之的行为,不可一日而暂废。
《论语·为政》中,夫子自道不同年龄段之学习体会,大略云:“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学习乃终身之事,亦为不断进步、不断觉悟之事。是不是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岁,就到了学习的最高境界,而可以不再学习了呢?当然不是。若孔子活到八十、九十甚至更高的年岁,当更有超越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体悟。《庄子·则阳》云“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种顿悟更是岁月的玉成,也是对生命的更新,一切待学然后知。
《论语集释》引《说文解字》《白虎通义》解释“学”:
“学”者,《说文》云:“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朦也。臼声。学,篆文‘斅’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爲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与《说文》训同[1]2。
“学”可解释为“觉”,即“觉悟”之意。“觉悟”乃瞬间事,之后便应该“时习”,不断地、按时地巩固所悟,将瞬间内化为自身、稳定为永久。
《论语集释》引朱熹《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云:
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已矣[1]3。
朱熹解释“学”为“效”。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后觉效先觉,年幼者效年长者,学生效教师者,皆此类也。朱熹没有抛弃“学”的“觉”义,“学”最后所要达到的效果是“复其初”“善”。“习”为“鸟数飞”,有反复实习、实践之意,非徒今所谓反复温习、反复复习之停留在书本层面,而强调应用中的反复。学以致用,反反复复运用,终至于成为生命本能、化为生命自身,最后到达“善”的道德境界。既然学习有所得、运用能自如,自然高兴,故曰“不亦说乎”。有什么样的快乐,能比通过不断学习、反复练习终有所成更深刻、持久的呢?
《论语集释》所引诸家重要注解,尚不够详尽。现补充如下:
何晏《论语集解》引王肃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怿也。”[2]4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在此基础上更详细地说:“学者,觉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而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而’犹因仍也;‘时’,是日中之‘时’也;‘习’,是修故之称也。言人不学则已,既学必因仍而修习,日夜无替也。”[3]2
邢昺《论语注疏》曰:“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又曰“学而时习”为“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在“诵”“所学篇简之文”外,加以“习”“礼乐之容”[4]2457。
朱熹在《论语集注》上段引文之后,又说道:“程子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5]47
何晏、皇侃代表的是汉儒考据之学,邢昺、朱熹代表的是宋儒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不避繁琐,务必字字落实,必以前代注疏为依据,轻易不做更为深入全面的阐释。义理之学轻考据,或者在适当考据之后大讲发明义理,有较强的启发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然而,如上所列,宋儒的义理之学并不是完全基于个人化的解读和阐释,并未忽视前人在字词考索上的贡献,而是在前人考据的基础上再做考证,以发明义理为主要。
比较汉、宋两派之不同,可以发现,前者解释“学”重在“觉”,后者重在“效”;前者解释“时”为“按时”、“以时”,后者解释为“时时”;前者解释“习”为“诵习、修习”,后者则偏重“实习、实践”之意。可知宋儒更注重学以致用、知识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同时也更将学习看作是无时不能、无所不在、无施不可的事情,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主动、昂扬姿态,更加笃信人的力量,而非仅靠自然的安排。
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说文》云:学,觉悟也,……夫子十五志学,其后不仕,乃更删定诸经,……凡篇中所言为学之事,皆指夫子所删定言之矣。”[6]2又曰:“古人为学,有操缦博依杂服兴艺诸事,此注专以诵习言者,亦举一端以见之也。《说文》:‘习,鸟数飞也。’引申为凡重习、学习之义。《吕览·审己》注:‘习,学也’。下章传不习乎,训义亦同。”[6]6
刘宝楠对于“学”的解释,回归到了汉儒上面:行为上来说是“觉悟”,对象上来说是诸经。将“习”和“学”的意思等同,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变得非常狭隘,学习以及学习之乐就是非常明确的、特定的反复领悟孔子删修之书,有所得而悦之。
在《论语·学而》中,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子夏把“学”的范围看得很广泛,而最终指向“善”的境界。“学”既然是终身不息之事,是生命活动的本然状态之一,是融入生命、成就生命不得不为之事,那么“学”就不能仅仅视为读书,更不能仅仅视为读孔子删述之书,而是要博及万物、了然万事,并身体力行、求真求善,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论语·先进》中,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学”与“读书”不是一回事,并且可以通过人民社稷“为学”,当然最终也要施之于人民社稷。
《论语集释》又引朱熹之言曰:
《朱子文集》(《答张敬夫》):学而,说此篇名也。取其篇首两字为别,初无意义。但学之为义,则读此书者不可以不先讲也。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其精纯尽在此书,而此篇所明又学之本,故学者不可以不尽心焉[1]3。
朱熹对“学”的理解,不拘泥于字的本义,更看重它在实际运用之中所产生的引申义,即由“效”而“至”,由“效”先知先能而“至”各种无大小贵贱之分的技能与知识,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学”。在将“学”放大之后,朱熹又将它缩小为“儒者之学”,即“学为圣人”。“圣人”是什么样的呢?“圣人”就是尽了“为人之道”的人。在这里,他又扩大了“圣人”的含义。再回头来看被缩小为“儒者之学”的“学”,则此“学”又被放大了。然而,它不再是技能型的学习,更不是向负面事物的学习,而变为正心诚意的品德与心性的学习,变成了尽心唯善的学习。那些“辞章之学,训诂之学”当然不足挂齿,不是说这些学问可有可无,而是说它们所代表的“学”是基础性的,是不能仅仅停留甚至满足于那个层面的“小学”。
二、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集释》引曰:
(何晏《论语集解》)包咸曰:“同门曰朋。”
《皇疏》引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讲习,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远人且至,况其近者乎?道可齐味,欢然适愿,所以乐也。”
(朱熹《论语集注》)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1]6-7
朱熹与何晏、皇侃的差别主要在“朋”字的解释上,后者将“朋”解释为“同门”、一同讲习的“朋友”;前者则解释为“同类”,又引程颢的解释“朋”为“信从者”。朱熹的解释范围是最宽泛的,也是最模糊的。什么叫“同类”?不大能讲得清楚。大概可以理解为志同道合之人。何晏引包咸之说,将“朋”解为“同门”。“同门”或“讲习之朋友”,都在近前,又何为“自远方来”?皇侃转而曰:“远人且至,况其近者乎?”强并“远人”“近者”,终不相干。皇侃之落脚点只在身边朋友的“齐味”“适愿”之乐,而无关于“远方”。朱熹有承袭其说处,而其所谓“同类”之朋,未必一定是近前的日与切磋琢磨的同门之朋。这样就可以理解为:远方有志于学者都闻其名而来,近便之学者更可想而知。远近皆至,正所谓闻名遐迩、蜚声中外。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士族名流时常相聚在一起讲求玄理、品评人物,自然没有“自远方来”的奔波劳苦。所以,便把“自远方来”者虚化,作为“朋”之陪衬。在何、皇诸人看来,“远人”和“朋”并不是一回事。即使有慕名远来之人,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一定不会高贵,是不能看作“朋”的。在士族的小圈子里,呼朋引类、相与为乐,足矣!
宋代科举考试发达,已打破门阀限制。科考举子及中第为官者,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有了公平的取士制度,加速了社会流动,故自远方来的朋友很多,各种集会层出不穷,其中亦不乏名师硕儒主盟其中。另外,两宋时,私人讲学风气渐盛。有著名的“南宋四大书院”,就是这种风气的反映。所以,程颢说,“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这种乐是讲学的学者之乐,“朋”并非地位、名望、学问等同的朋友,而是“信从者”。
《论语集释》“余论”引清人说法:
(刘逢禄)《论语述何》:《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才乎?”《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友天下之善士故乐。”阮元《揅经室集》: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语,即生平学行始末也。故学必兼诵行,其义乃全。《注》以习为诵习,失之。朋自远来者,孔子道兼师儒。《周礼·司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各国学者皆来从学也。盖学而时习,未有不朋来。圣人之道不见用于世,所恃以传于天下后世者,朋也。潘氏《集笺》:《史记·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即“有朋自远方来”也。[1]7
刘逢禄将“有朋自远方来”解释成“自远方的朋来者”,强调来的人多。弟子既众,夫子之道即使不见用于世,其传也愈广、其流也愈久,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后世,天下之人,靡不信从。此时,“远方”已经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远”,也涵盖了时间距离上的“远”,不仅仅是形象具体的“远”,更有哲理抽象的“远”,即所谓“存在方式上的远方”[7]。这样,对于孔子而言,“朋”显然就不是简单的朋友了,在当世为弟子及其他信从,在后世则天下之人皆是,所以“朋”的意思自然只能向“多”倾斜了。
如果我们不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主语看成是孔子,或某位众望所归、天下闻名的耆宿大儒,只看作普遍意义上的同道中人,那么这句话又可以做更加开放式的理解。
《礼记·学记》曰:“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易·兑·象传》曰:“君子以朋友讲习。”《学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可见,“学”不是封闭式的行为,而必须有交流、沟通、切磋、讨论、互补,否则不仅不会增广见闻,更可能导致孤陋寡闻、固步自封。前面谈到过“学”的实践性品格、广泛性意义,“学”的手段、内容和目的都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如果只是读闭门书、做死学问,孤芳自赏,自我陶醉,那么“学”的包容性、开放性、实践性都会失去。这显然不是《论语》中“学”的本意。朋友,尤其是四面八方的朋友聚在一起,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不仅会有知识的去伪存真,更会有知识的新陈代谢,同时会有知识的萌发生长。交流、学习,可谓是人类知识迅速增长、人类文明迅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每一次民族的交融、文化的碰撞都会产生一次知识的爆发。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朋友在学习之中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清人汪中《讲学释义》曰:“讲,习也;习,肄也;肄,讲也。《国语》‘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传》‘大雩讲于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为教也,以四术:《书》则读之;《诗》《乐》同物,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让周旋,是以行礼。故其习之也,恒与人共之。‘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所谓‘君子以朋友讲习也’。”[8]108这是在广义之“学”上,从先秦时代“学”的具体情形探讨朋友的重要性。
古今之“学”,虽然内容、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学”本身对学习主体的群体性要求并未减弱。孔子说《诗》的功用是“兴、观、群、怨”,其中的“群”也不乏“志同道合的同类人集会、交流”之意。
三、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集释》引录此句注疏:
(何晏《论语集解》)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皇疏》此有二释。一云:“古之学者为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内映,他人不见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备于一人。故为教诲之道,若人有钝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又引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诲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学者,始于时习,中于讲肄,终于教授者也。
(朱熹《论语集注》)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1]8
何晏对此没有做任何阐发,只就字词句意作出解释。皇侃列出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与朱熹相类,重在指出“学”是“为己之学”;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学”为得“先王之道”,后者则没有明确指出“学”的最终目的,专在区别“己”与“人”。可以看出,后者的个人化意识更强烈。皇侃的第二种解释不在“学”而在“教”,与“诲人不倦”联系起来,突出老师的耐心与宽容,即君子的“忠恕之道”。
仔细揣摩“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觉得,其中有让步的语气,有“退一步说如何如何”,“即使如何也会怎样”的意思。别人不理解你,你却不生气,这不也是君子的作风吗?言下之意,如果别人能够理解那就更好了,还是希望别人能够理解的。既然“学”不仅仅是书本学习,更有实践学习;既然“学”在朋友的交流互补当中,能够更有进益或者说能够吸引远人来学习传播你的知识;既然“学”不是封闭式的行为,而是要有开放式的品格,那么,就需要别人的理解,否则怎么能有沟通、交融、传播呢?当然,所谓“人不知”,只是说终究会有那么少数人无法理解自己或自己所学,是他们的领悟能力、知识水平不够,或者是他们所学领域差异太大,还有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你的知识与见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仁者、君子的“忠恕”,不仅仅是“诲人不倦”所体现的耐心和宽容,更有不强使人同己的气魄与风度。
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评价王安石,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9]1427苏轼认为,这种强使人知、使人同的作风,对于丰富多样的世界来说是灾难性的,就好像是肥沃的土地能够生长出种类繁多的植物,而贫瘠的土地只能生长出清一色的“黄茅白苇”。
“有朋自远方来”,并不是为了使五湖四海的人趋同,而是为了知识的生长与传播。孔子教授弟子,不仅“有教无类”,无论各个地方、各类阶层、各种天资的弟子,都一视同仁地教,而且在教法上注重“因材施教”,尊重个体性差异,开发各自所长。苏轼说“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即便孔子要求全部的学生变得和他一模一样,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朋”既然“自远方来”,种种先天性的差异就摆在那里,交流沟通本来就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人不知”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强使人知,后果恐怕就是学生或朋友“强不知以为知”,反而达不到学习或教学的目的。
上面是从他人的角度谈论“人不知”。若单从“为己”而言,则还有一种理解。
《论语·颜渊》:“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对此,《皇疏》曰:“朋友主切磋,若见有不善,当尽己忠心告语之,又以善事更相诱导也。若彼苟不见从,则便止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则彼容反见骂辱,故云不自辱也。”[3]174这就纯属一种无奈之举了,也是孔子在长期的治学与处事当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提倡知识、能力、思想的传递与传播,同时他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品格和丰富的现实生活与政治经验。当自己的仁政思想不能为鲁君所用,他就周游列国;不为列国之君所用,他就退而教学、删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无奈的喟叹,也是孔子变通的思想,是孔子在不断追逐理想的过程中得到的宝贵经验。由此也可见,孔子所说的“君子”也不是什么万能的。有无奈的时候,有失意的时候,但能够不因无奈和失意而气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强求他人理解、认同和支持自己,这也是“君子”应有的品格。
《论语集释》引清人的解释云:
王衡《论语驳异》:罗近溪谓:“愈学而愈悦,如何有厌;愈教而愈乐,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以其不厌不倦处。”此却说得好。《论语补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则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则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愠之,忌也。君子不矜则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为君子也。《后汉·儒林传》注引《魏略》云:“乐详字文载。黄初中,征拜博士十余人,学多褊,又不熟悉,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质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毛奇龄《四书賸言》:《论语》“人不知而不愠”,《孔疏》原有十义:一是不知学,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后说,似于本章言学之意反未亲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学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犹言“君子易事不求备”也。盖独学共学,教人以学,皆学中事。夫子一生祇学不厌,教不倦,自言如此(见《默识》节),门弟子言如此(见《公西华》节),后人言如此(见《孟子》),故首章即以此发明之[1]8。
罗近溪只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上面来解释,将“学”与“教”纯粹看成单方面的一己之私,将“不厌”与“不倦”夸张为“悦”与“乐”。这种故意忽略“学”“教”的开放性、群体性、对话性品格,刻意夸大个人热情的作用,恐怕有悖《论语》原意,也与历代注疏家相去甚远。
《论语补疏》以“矜”与“忌”解释“愠”,侧重于“教”与“学”当中的双方平等与谦虚平和的心态,似乎有些道理。这种劝人不矜不忌不怒的说法,只怕是受了禅宗的影响。
毛奇龄认为这是孔子一生中“学”与“教”的心得体会,而“独学共学,教人以学,皆学中事”,“教”的落脚点也是“学”。“人不知”后面省略掉的宾语是“学”,而非“我”。这就与上面皇侃与朱熹所说的“学”为己、非为人,故不必求人知的说法异趣。人不知“我”,则易愠怒;而人不知“学”,则无论在己在人,都是无可避免的,更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可愠怒的呢?毛奇龄只知有“学”,而不知有“人”,将“学”与“人”割裂开来,这是有悖常理的。既然“不知学”的现象乃常见的客观现象,人们也不可能因此而发怒,那么后面所言“不亦君子乎”就显得莫名其妙。孔子所说的是在一般人会怒的情况下而不怒,这才符合君子的特点。显然是说对一般人、非君子来说,“人不知”是要引起愠怒的。所以,毛奇龄的解释不能成立。
四、《学而》篇首章的逻辑
按照上面介绍的各家之不同注释,《学而》篇首章的三句话可以有两种逻辑关系。
第一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说一己的“学”与“习”,在心领神会、驾轻就熟之后,滋生出内心的喜悦之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说自己“学”“习”有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名望,吸引远方的信从者前来受教,这是对自己学问的肯定,同时也使得自己的知识与思想传播开来,因此,自然快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弟子愚钝、领悟力差,一时不解甚至终不能理解所传授的知识与方法,自己也不生气,因为通过一直以来的学习修养,已经具备君子的“忠恕”之德。按照这样的解读,则三句话的重心逐渐由“学”转到了“教”。
第二种:第一句是说自己“学”“习”有所得,因而喜悦。第二句是说同门或朋友之间切磋琢磨、取长补短,或者远方的志同道合者聚集到一起交流、沟通、论辩等等,使得“学”有精进,从而感到快乐。第三句是说“学”本身是“为己之学”,是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收获、自己的提升,并不在于他人知与不知,所以别人不理解自己所学所得,又有什么关系?又何必动怒?如此一来,三句话就始终没有脱离“学”的重心。
综上所述,《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一章三句话,有着深刻的内涵,也有丰富的解读空间。历代注疏家根据《论语》语境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对此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从他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三句话在逻辑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紧紧围绕“学”而展开的,指明了学习的途径(时习、朋)、品格(习)、目的(朋)、境界(悦、乐、不愠、君子)。同时,这三句话也有着超越特定语境、时代的普遍性意义。无论是“学”之内容的广泛性、实用性,还是“朋”之作用的交流性、传播性,还是“不愠”所显示的“知”之个体差异、“君子”之人格,都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激励。
[1]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2]何晏.论语集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7]陈赟.“学而时习之”与《论语》的开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8]汪中.述学·别录[M].戴庆钰,涂小马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9]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编辑:米盛)
B222.1
A
1673-1999(2015)01-0017-05
庞明启(1985-),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国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201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