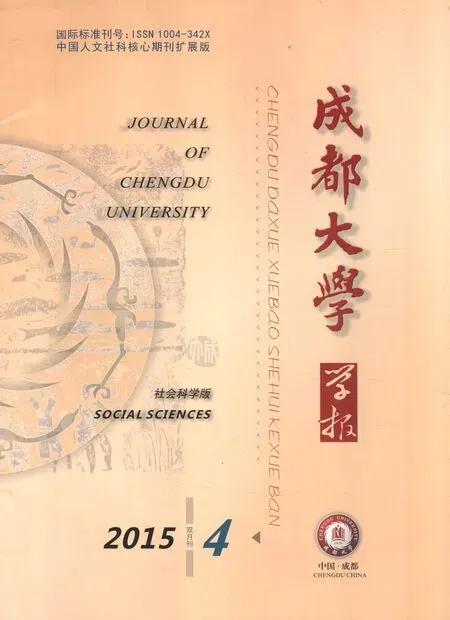论语派与现代小品文文体规范的确立*
2015-02-21俞王毛
俞王毛
(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西 南昌 330032)
论语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流派,它生成于1930年代的上海,以提倡和写作幽默、性灵小品文而知名,在小品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写作始于二十年代,在周作人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下,小品文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作为一种文体,小品文在此阶段并未成熟,除了周作人,真正热心建构小品文文体理论的人很少,即使是周作人,对于小品文文体的认识也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在论述中留下了不少破绽和矛盾。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相关文章虽时有所见,但尚未建立起自足的小品文文体理论。论语派出现后,小品文理论贫弱的问题得到极大改观。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十分重视小品文建设工作,在辨明概念、多方借鉴的基础上建构起一套自成体系的小品文文体规范,小品文也由此走向成熟。
一、对小品文概念的辨析
现代小品文萌生于文学革命时期,引起广泛关注则在周作人《美文》发表之后。在此文中,周作人将外国随笔和中国古代的序、记、说等称为“美文”,提倡学习其真实简明的写作方法,希望借此给中国散文开辟新的领地。[1]在周作人的倡导下,逐渐有批评家和作家加入到小品文文体建设中来。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小品文文体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在《美文》中,周作人将美文归于论文一类,又将其与散文、诗、散文诗等作了极为含糊的比较,最终也没有说明美文的文体归属。后来,“小品文”这一名称取代了“美文”,并被附加上不同于“美文”的内涵。周作人在1925年以后经常使用“小品文”这个概念,他将现代小品文看成晚明小品的复兴,这种文体也因此偏离了他昔日对“美文”的构想。在梁遇春那里,小品文主要指西方随笔,他以“小品文”对译西方的essay,中国传统小品文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周作人和梁遇春都是现代小品文的奠基者,他们的分歧实际上表明了小品文文体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妨碍了小品文的发展。事实上,在论语派出现之际,小品文正遭遇生存困境:周作人等人主持的小品文周刊《骆驼草》创刊不久即走向终结,晚明风小品文的试验困难重重;徐志摩、梁遇春去世后,那种高度西化的小品文也后继乏人。论语派作家大都热爱并擅长小品文,其中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丰子恺等人都是现代小品文名家,在论语派形成之初,林语堂即提出写作“模范小品文”的构想[2],事实上,这也是论语派作家的共同追求,是论语派得以形成的动力之一。对于论语派作家来说,廓清对小品文的模糊认识,重新激发这种文体的活力,就是写作“模范小品文”的第一步。
论语派在重新界定小品文概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林语堂所撰《论语》编辑后记、《人间世》发刊词、《论小品文笔调》、《小品文之遗绪》、《再谈小品文之遗绪》都涉及到文体概念问题。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对小品文的解释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并将小品文等同于“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的文章。[3]在《论小品文笔调》中,林语堂指出,现代小品文与古代小品文在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但现代小品文题材范围更广阔,表达方式更自由,“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4]。在对小品文的理解上,林语堂既不像19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那样偏重于传统小品,也不像梁遇春那样独钟西方随笔,他心目中的小品文是融合西方随笔与传统小品特征的亦中亦西的现代散文类型,它兼有西方随笔的幽默和中国传统小品的清丽,区别于小说、诗歌和戏剧,也区别于战斗性的杂文、高度西化的随笔及古典小品文,是一种既传承了古今中外散文资源、又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文体。
作为论语派成员的周作人、郁达夫在小品文辨体方面的成绩也值得提及。周作人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将小品文看成晚明小品的复兴,认为它很少受外国文学影响,论语派时期,他仍然热心介绍晚明小品,但也注意将中国小品文与外国随笔接轨,他指出:“日本的松尾芭蕉横井也好,法国的蒙田,英国的阑姆与亨德,密伦与林忒等,所作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假如这是同的,那么自然就是一类,名称不成问题,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5]他根据文体的性质和特征将外国随笔和中国小品文归为一类,对20年代的小品文观念作了修正,他的小品文观念也因此显得较为通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他将“散文”看作prose的译名,但实际上他是参照西方随笔来确定散文特征的,他在文中多次引用林语堂对小品文的相关论述来阐明散文特征,可知他所说的散文正是小品文,郁达夫将此种文体的特征归纳为四点:表现个人性、题材范围的扩大、幽默,以及人性、社会性与自然的调和。[6]5-11这种论析和归纳使小品文与杂文、报告文学等其他散文样式区别开来,获得了鲜明的个性。胡风指出,小品文“是在林氏的独特的解释之下被提倡被随和了的”[7],林语堂和他的朋友们对小品文性质和特征的阐释纠正了小品文定位上的偏颇,澄清了以往对小品文的模糊认识,使这种文体既可以与西方文学接轨,又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为小品文的独立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小品文资源的广泛择取
现代小品文作为一种年轻的文体,其成功离不开对古今中外散文资源的多方择取。二十年代,周作人和受其影响的俞平伯、废名、沈启无、钱玄同等人大力发掘晚明小品,梁遇春则热心翻译西方随笔,但是两股资源之间没有发生交集和沟通,小品文也因此无法均衡生长。真正做到将外援和内应结合起来、并使之融为一体的是论语派。论语派作家一方面提倡学习外国随笔,一方面从传统文学中摄取资源,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形成了一种杂取古今、融合中西的小品文文体。
论语派诸多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陈炼青、陈叔华、邵洵美、郁达夫等都参与了小品文资源的择取和转化过程,其中用力最勤者是周作人和林语堂。周作人在20年代将目光投向晚明小品,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小品文理论。在论语派时期,周作人延续了这种资源择取路向并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晚明小品之外,宋代文学、清初文学都成为他择取的对象,周作人以现代目光打量古典诗文尤其是晚明小品,期望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因子,并使其精神转化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读周作人此期发表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的大量读书笔记,可以看出他这种化古为新的努力。周作人对古典文学的评价重点在阐释其重个性、反道统的精神,并注意引古人文学精神入现代,借此解决现代文学中的道学思想遗留问题。作为论语派精神领袖,他的这种工作意义重大,在其引导下,论语派作家纷纷阅读明清小品,写作相关读书随笔,标点、出版明清小品文集,读者也对明清小品文产生了极大兴趣,争相购阅,以至于在1934年左右形成了席卷文坛的晚明小品热。在这样的读书潮流中,传统小品文中的不少因素如反抗精神、自我表现色彩、趣味性等等也就不知不觉地融入到现代小品文之中。
林语堂的小品文文体概念主要来自西方,西方随笔是他建构现代小品文文体的最重要的参照系,他对西方随笔资源自然十分留心。林语堂根据笔调的不同将英国散文分为小品文和学理文两大类,前者以乔叟、E.F.福斯特、伍尔夫的作品为代表,风格散逸自然,行文无拘无碍;后者以培根、麦考利、米尔顿的作品为代表,风格整洁细密,行文踌躇滞碍。林语堂推崇乔叟诸人,认为他们才是现代散文大家,因为他们的散文在写法上类似于好友闲谈,“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愤于幽闲。”[8]他向中国读者介绍的,就是这类笔调自由的西方散文,乔叟、伍尔夫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只要其文章表现出个人笔调,他也欣然推荐。《人间世》“译丛”栏和“西洋杂志文”栏所登多是这类散文,《西风》所译介的也多是闲谈体的西洋杂志文章。
林语堂对传统散文资源也同样重视,在他看来,西方随笔代表的毕竟是外国人的生活态度和情感体验方式,只有将其与中国传统文体相印证,才能实现随笔的中国化:“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8]因此,他在论述西方随笔的文体要素时,总不忘与传统资源相对照,力图寻出“中国祖宗”。他寻到的传统资源主要是晚明小品,在这一点上,他深受周作人的启发。不过,林语堂的目光没有局限于晚明,也没有局限于小品。小品方面,除了公安、竟陵,他对苏东坡、徐文长、李笠翁、袁子才、金圣叹、舒白香、沈复诸人同样看重,认为这些人的小品笔调都是闲散自在,“独往独来,有一片凌云驾雾天马行空之气”[9]。除了传统小品文,林语堂还找到小说、戏剧、史传文学等作为现代小品文的资源。林语堂认为,白话小说中有不少闲谈文字,不妨将其看成散文,“议论之佳者如凤姐之评人论事,姑之说道,逸云(《老残续集》)之谈爱,聊有西洋小品闲谈风味”;戏剧方面他推崇李笠翁,认为李笠翁戏剧中的宾白“别开生面,竟然是现代白话文”;史传文方面他推崇《左传》与《史记》,认为《左传》在叙事写景方面尚有魄力,司马迁下笔淋漓生动,都有值得借鉴之处。[8]郁达夫、俞平伯、施蛰存、黄嘉德等论语派作家也比较关注小品文资源择取问题,他们或介绍传统小品,或翻译西方随笔,为现代小品文的生长输送了大量的营养,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论语派作家在文学资源的择取上互相呼应、互为补充,其取于晚明小品者,在于信口信腕的手法和反抗权威的精神,取于西方随笔者,在于现代的思想感情、题材观念和写作技巧,这一切都是现代小品文不可或缺的品质。这两种资源在论语派期刊上同时得到展示,实现了互相对话、互相融合,不再像20年代那样呈二水分流的局面。资源上这种博取与融合使西方随笔资源中国化、传统小品资源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一种具有现代意味和民族风格的散文文体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建立新的小品文文体规范
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论语派作家对小品文的功能和形式特征作了集中的思考。在文体功能方面,论语派作家最重视的是小品文对个性的表现。周作人认为小品文是“个人文学的尖端”,林语堂认为小品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郁达夫将“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看成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6]5“个性的文学”是他们对小品文的共同想象。这与他们所择取的资源有密切关系,周作人舍弃载道文章而重视明清小品,是因为小品文有着真实的个性的表现;林语堂不取学理文而取西方小品文,是因为西方小品文行文自由随便,作者个性能够尽情展露;郁达夫排斥古代散文而重视西方随笔,也是因为后者的个人性来得特别强。论语派对于小品文功能的这种思考和认识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三十年代,不少作家遵奉政治化文学观,以宣传作为散文的主要功能,尽管他们宣传的可能是现代之道,但既然将散文作为工具来利用,其思维方式就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暗中相通,这对于散文现代性的生成来说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尽管那些优秀作家能够超越这种功能限制,将自己的个性融入散文之中,但是从总体上看,以散文为宣传工具的观念毕竟不利于作家的自由思考,也容易造成散文文体的僵化。论语派对散文功能的重新认定意在解除散文的“载道”重负,使之变成自由、活泼、契合现代人的思维特征、能够培养现代人生观的文体,从而促进散文文体的现代转化。
在小品文形式方面,论语派特别关注的有体式问题、笔调问题和语言问题,这几个问题也正是小品文确立自身形式特征的关键。论语派推崇闲谈体式,林语堂对这种体式作了如下富有诗意的阐释:“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福音,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8]这段话与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对于essay的相关论述异曲同工。闲谈体的特征是散漫自由、无拘无碍。论语派选择闲谈体,意在促成小品文体裁的解放。论语派还提倡个人笔调。所谓个人笔调,指的是小品文的表现手法,其特点是“在谈话之中夹入闲情及个人思感”[8]。个人笔调是论语派对那些能够表现作者个性、形成独特风格的写作手法的总称,个人笔调强调的是文笔的个人性和独创性。事实上,在林语堂等人看来,闲谈体与个人笔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闲谈体式的小品文必定拥有充满个性色彩、表现出闲情逸致的笔调,而个人笔调的运用必定能够增进小品文自由随意的闲谈风味。论语派对于小品文语言的建设也极为重视。林语堂在为黄嘉德译《流浪者自传》撰写的引言中,对该书语言十分称赏:“此书尤有一专长,就是他的文字,虽然掷地铿锵,甚得白话自然之节奏,却毫无文人粉饰恶习。”[10]节奏自然、不加粉饰,是论语派对小品文语言的共识。在具体的语言组织方法上,大部分论语派作家沿用了周作人的思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11]“杂糅调和”、“雅致”正是论语派为小品文语言确立的基本标准。也有部分作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林语堂取法晚明小品的语录体、老舍熔铸多重资源的俗语体,等等。论语派的语言观念强调的是自由精神和审美品格,杂糅语言与闲谈体式和个人笔调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小品文重个性、重艺术的形式特征。
总之,论语派在广泛择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小品文文体规范,表现个性、广泛取材、采取闲谈体式和个人笔调、追求语言的韵味,就是这些规范的具体内容。这套规范既使小品文文体得以凝定,又使其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实践了这套规范的论语派小品文既继承了传统小品文洒脱不羁的风度,也染上了传统小品文的清、涩、雅、拙等语言风致;既借鉴了西方随笔的自然随意的结构方式和从容不迫的语调,也学习了西方随笔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的写作方法,是中国化了的英法随笔、现代化了的晚明小品文,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实现了论语派写作“模范小品文”的初衷。“文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两者相得益彰”[12],对于自我表现的强调使小品文摆脱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束缚,题材上的任意择取使小品文贴近现实人生,不拘一格的表达方法消解了创作上的清规戒律,小品文也因此呈现出自由气象和勃勃生机。
四、结语
论语派出现在小品文低潮期,其时小品文因概念不明、功能不清而显得身份未定,又因过度西化或沾染了太多的晚明风气而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论语派通过辨析小品文概念、拓展小品文资源,最终建构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小品文文体规范,使小品文获得鲜明的现代品质和民族特色,也使小品文获得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的身份标志。在其指引下,小品文实现了有节制的自由和有法度的放纵,确立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独立的文体地位。此后,尽管小品文概念的内涵有所变化,小品文文体规范也有过修正和革新,由论语派所确立的文体规范总是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人们的小品文观念,引导着小品文的写作和欣赏,同时,体现在这套规范中的自由精神和审美意识也遏制了盛行于三十年代的政治化文学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派所确立的小品文文体规范不仅丰富了现代散文理论,而且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解放和更新。
[1] 周作人.美文[A]//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2] 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J].论语,1932(6).
[3] 发刊词[J].人间世,1934(1).
[4] 语堂.论小品文笔调[J].人间世,1934(6).
[5] 周作人.再谈俳文[A]//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 郁达夫.导言[A]//赵家璧主编,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7] 胡风.林语堂论[J].文学,1935,4(1).
[8] 语堂.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1935(22).
[9] 语堂.再谈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1935(24).
[10] 语堂.《流浪者自传》引言[J].宇宙风,1935(1).
[11] 周作人.《燕知草》跋[A]//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2] 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