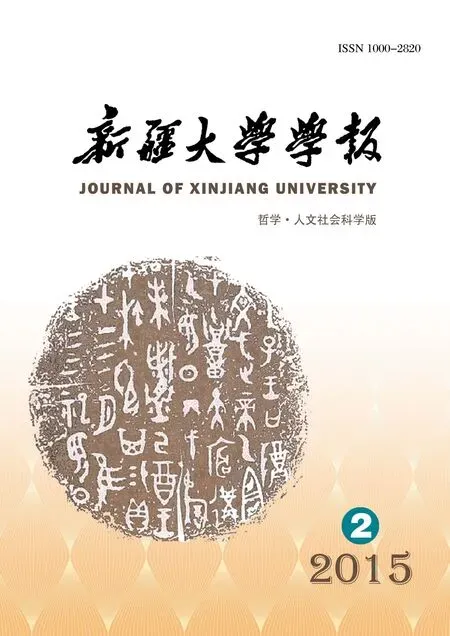论超文本叙事理念的源起∗
2015-02-20李森
李森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在网络媒介时代印刷书籍并不会消失,但是“数字媒体给了我们一个上千年中难得的机会:以新眼光看待印刷文学,并思考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有多大程度上是以印刷媒介为前提的。如同我们研究的电子文学批评实践理论,就可以更新对印刷文学特性的评价”[1]。时至今日,技术层面上,文字的电子化运用已经比较成熟,除个人电脑以外,电子书阅读器,手机等便携电子设备也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相对纸媒而言,电子屏幕所显示的内容是即时性的、可变的,而纸媒上的内容,尤其印刷文本,变动起来十分麻烦。由于电子屏幕的这种可变性,使得一种非线性、互动性和跨媒介的叙事方式变得容易而触手可及。而这种叙事方式并非仅由技术层面来决定,虽然超文本技术的实际运用出现得较晚,然而超文本的理念却很早就产生了。超文本叙事的诞生与三种理念密切相关:技术层面的超文本、哲学及文学理论层面的超文本,以及小说家在创作中体现出的超文本理念,超文本的文学叙事便是在这三种理念的影响下出现的。
一、超文本技术的诞生
《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超文本,也称作超链接,用于链接由电子连接的信息单元,目的是为了使用者更容易的运用它们。超文本允许电子媒介上电脑程序的使用者选择文本中的某个词,以获得和该词相关的额外信息······超文本链接常常使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的高亮词汇和语段来标示。超文本链接也可以把文本与声音、图片,动画链接起来。”[2]在笔者看来超文本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链接,其他特征都是附属性的。以不同方式链接文字就是纯文字超文本;链接非文字媒体(如图像)的超文本,即超媒体(hypermedia);而被热议的互动性更是超文本链接的特性之一,如果链接不是互动性的那么链接也就不存在了。其实传统的书籍也具有互动性,读者必须翻动书页否则内容便无法呈现,只不过这种互动只有一种线性模式。所以,如果链接是超文本的核心,那么其自由链接的非线性特质就为叙事提供了新式的界面和可能。
首先,技术层面的超文本观念最早来自德国数学家F·克莱恩(F Klein)于1704年提出的“超空间”(hyperspace)概念。克莱恩用这个词去定义一种非欧几何的多维几何学特殊类型。时隔200余年,1965年电脑科学家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首次提出了“文学机器”概念[3],他已经认识到计算机创造和运用文本网络的可能。他认为“文学可以是一种进行中的互联文本系统(system of interconnecting documents)”[4]。因为超文本就是“一种完全非线性书写的电子形式······这意味着一种多线性和多序列的词语网络,允许读者链接到更多的信息资源。通过其交互性,读者能够在文本链接间跳跃,甚至建立他自己的链接”[5]。实际上,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依赖于硬件,且都出现在现代意义上的电脑之前,但纳尔逊相信可通过机器生产出一种新的写作技术。甚至在纳尔逊之前,身为工程师和科学家的维纳沃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也设想了一种作为超文本读写系统的电子技术[6]。在实践性的超文本软件系统被发明以前,布什和纳尔逊就已经确定了超文本的关键性特征,“一个超文本包括主题和主题间的链接,这些主题可以是段落,句子,单词,或者数字化的图像和视频剪辑。超文本就如同被作者用剪刀裁剪为方便语段大小的印刷书籍。不同之处是电子超文本并不是简单的一堆无序的堆砌,因为作者用电子链接定义了文本碎片间的关系”[7]。纳尔逊将“超文本”定义为“非连续记录,即分支的、允许读者选择的、便于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是通过链接而关联起来的文本块,那些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径”[8]。
遗憾的是布什与纳尔逊都没有能编程出投入实际使用的计算机超文本系统,但他们的理念早已渗入到现代计算机运用之中。纳尔逊构想的“上都(Xanadu)”系统和布什的“麦麦克斯存储器”最初都是针对文件管理或者资料的存储查询,也就是说终究都是工具性的。“使用者可以用此装置······将所有资讯,例如:书籍、照片、笔记、信件等,这些资讯可以加注释、一页页或是一次跳多页浏览,重要的是,使用者可以以一种‘关联法’快速、便利地检索这些资讯,这种相互关联法就是依人的思维联想跳跃法结构的。”[9]传统的文本以线性方式表达信息或组织数据,其缺点在于无法对应现实世界的信息系统,与人的联想思维有很大差异。超文本是全新的文字处理形式,创立之初它的意义就在于有效的组织信息,使得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和自然地获取、修改、组织、传播和共享信息资源,使计算机更有效地迎合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工具性思维的主导下以万维网(World Wide Web)为代表的互联网运用已经将超文本现实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日常的计算机运用中,超文本链接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不论是查询还是娱乐都是以读者的主观目的为主导。超文本在技术层面上的链接运用迎合了人们对信息的个性化需求,但也使得个人在信息获取时的目的性更加彰显。某种意义上,这种观念与传统的线性叙事有重合之处,尽管读者有自由选择情节发展或跑题的可能,但最终仍然指向事件的终结,使读者感到阅读故事的愉悦和满足。即便“叙事数据库”中还有剩余的信息,但如果读者已经满足了自己对作品的“文体期待”就可以停止下来。如同在网络上进行资料搜索时,已经得到足够的信息,便可以停止了。实际上,阅读模式有很多种,追求情节发展结构的目的性阅读只是其中一种。有的作品会吸引读着更加关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并对人物产生情感反应。阅读小说与查询资料不同,因为叙事的快感并不完全来源于故事从开端到结尾的情节发展。
二、作为理念的超文本
对于早期哲学家与文学理论家们来讲,虽然不知道超文本技术的存在,但却明确提出了各自对叙述传统的异议。如维特根斯坦提出:
我们的目光扫过印刷行时的方式同扫过一系列随意的勾勾弯弯和装饰花样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人们会说,目光的移动特别轻松自如,既无停顿,也不打滑。而同时,在想象中进行着不由自主的言语。在我读德语和其他语言用各种字体印刷或书写的东西时情况便是这样——但在所有这一切中对于读本身来说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并没有一个在一切读的实例中都出现的特征[10]。
维特根斯坦强调各种阅读并没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各种阅读表现为异质性存在,不同语言、不同印刷、不同阅读方式等等都可以导致不同的阅读经验,因此阅读并不存在什么整齐划一的标准。对于叙事来讲,似乎也不存在什么统一的线性标准,时间、因果等不过是各种联系中的一种。在当代理论家中,这种观念继续发展,“像巴特和福柯关于作者之死的论述,德里达的文本性,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等等,这种融合了创新与非中心的模式很容易地发生在超文本上。”[11]此外,利奥塔的“小叙事”,德勒兹和瓜塔利的“块茎”与“平原”,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星丛(constellation)”概念等等对应在叙事中都讲述着相似的观念。“德里达在《语法学》中指出,裂痕已经正在小说的‘身体’上积累裂痕,因为它内在的线性正被怀疑。同样,另一位哲学家利奥塔,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书:‘一本好书······应该······读者可以从任意一页,以任意顺序阅读。”’[12]尽管这些理论家的学术背景千差万别,但他们概念的相通之处是对“中心”和“线性”的反叛,强调每个个体、片段独立存在的价值。叙事受这些后现代与解构观念的影响也产生了非线性的渴望。
上述理论家哲学著作写作形式的先锋性可以和纸媒上印刷的拟超文本小说相媲美,如德勒兹和瓜塔利的《千平原》,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文之悦》、《S/Z》,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美学理论》等等,在写作形式上都是当代理论著作中的“酷儿”。他们尝试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片段性写作,用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无定向性的言语方式进行理论言说,将其哲学理念与行文方法融为一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多诺的“文本重构法”。他在第一稿《否定辩证法》完成后又将本来章节明晰的文本打乱为“碎屑状”,文字不分章节且没有段落(德文原版),再装订起来。文本完全拒斥被从某种同一性思路解读,故意在文本形式上制造障碍。阿多诺说自己著作的“第一稿总是一种有组织的自我欺骗之作;在第二稿中,我自己潜入其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批判”[13]。他不再以逻辑条理组织材料,而把它们打碎混合,这种“各部分、各种理论观点‘具有相同的分量’的文本,也就是阿多诺制造出来的理想化理论星丛和文本蒙太奇”[14]。在对文本形式的解构与重构中,读者的主体性被调动起来,文本也从“固体”变成“流体”。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叙事似乎要放弃线性,使每个成分都显示出独立价值,“开端—高潮—结尾”这样的叙事“权力结构”被看作故事的尸体或假面,真正的叙事应该是动态的,直面读者的,每个部分都应具有平等的意义。叙事的超文本理念正是这种“星丛化”理论的背景中诞生的。
与哲学家相比,叙事学家脚步慢了半拍。如热奈特的“超文性(hypertextualit´e)”是指:“通过简单转换(后文简称转换)或间接转换(后文称为模仿)把一篇文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15]这明显是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派生而来,用以强调不同文本间的关系。而热奈特的例证也说明他的“超文本性”,与电脑专家们的“超文本”概念有明显差别:
《爱涅阿斯纪》和《尤利西斯》大概是同一蓝本《奥德赛》的两个程度不同、书名各异的超文本了······从《奥德赛》到尤利西斯的改造可以描述为一种“简单”改造或“直接”改造,即把《奥德赛》的情节搬到20世纪的都柏林。从《奥德赛》到《爱涅阿斯纪》的改造则更复杂、更间接,尽管表面上似乎更接近一些······维吉尔······完全叙述了另一个故事,但是借鉴了前者,以便创作一部与荷马在《奥德赛》中所确立的类型相同的作品······即摹仿了荷马[16]。
同时,巴赫金也常常被用来引证为超文本观念的先驱。但正如托多罗夫所说:“巴赫金研究的······超文性······不再具有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外壳,而是属于文化史的范畴。”[17]因为“对话”与“狂欢”不过是对某种效果的讨论,本身并不是文本的形式特征。巴赫金认为“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个接触点上······该文本进入对话中”[18]。而这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可谓异曲同工。尽管这些词汇(如:互文性、对话、狂欢······)在超文本文学的研究中常常出现,但其所指与它们本身的意义已有明显脱节。这些概念所针对的仍然是传统文学,它们大多数要求读者以新的视角看待文本,使文本获得一种精神价值。它们并不涉及电子媒介中的超文本,甚至也不涉及纸媒超文本,仅仅是对文学精神的阐述,而非文学形式的说明。这样,(哲学背景较少的)文学理论家还远未达到哲学家们的境界,他们并没有对某篇小说中的终极线性产生质疑,而是强调文本间的相互指涉,尽管有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但在超文本理念上实无先见,虽论者甚多但与文本媒介空间的联系较小。
三、文学虚构中的超文本
小说家从作品中反映出的超文本观念与前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别。如卡尔维诺所说:“文学生存的条件,就是提出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超出一切可能的不能实现的目标。只有当诗人与作家提出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时,文学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能否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络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19]文学家们则把这种构想在小说中直接以虚构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博尔赫斯的“迷宫”系列中所提到的各种书:
那本书叫“沙之书”,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20]465。
人们猜测某个六角形里的某个书架上肯定有一本书是所有书籍的总和:有一个图书馆员翻阅过,说它简直像神道[20]121。
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20]130。
我认为神只应讲一个词,而这个词应兼容并包······这个词等于一种语言和语言包含的一切,人们狂妄而又贫乏的词,诸如整体、世界、宇宙等等都是这个词的影子或表象[20]273。
以上四部小说中都出现了对神奇书籍或文本的描写,其中的非线性与前文提及电脑技术专家的超文本如出一辙,而其内容庞杂、求全责备则是独特之处。“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21]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恐怕就只能靠一本虚构的包罗万象且形式奇特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了,可不论是博尔赫斯还是其他文学家都无法做到。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的文学才能已经枯竭了,因为对于一个故事和结局总有一个确定性的结尾。去恢复文学的活力,应该进行多样性地写作,这包括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将它们封闭。博尔赫斯可以想象那样一种小说,但是他无法写出来······博尔赫斯自己从未接触过电子空间,那里文本可以包含分叉,汇聚和平行的的网络”[7]147。这种对书籍(纸媒叙事)有限性的超越也表现为对神秘事物的描写,如博尔赫斯对神秘的“阿莱夫”小球的描写:“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公分,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20]306。另外,其他一些作家,如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翁伯托·艾柯的《玫瑰之名》、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等作品中也都充满了迷宫结构①参见朱桃香《叙事理论视野中的迷宫文本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总之,这些文本都试图达到一种超文本效果,跨越文本中时间与空间的限定,将可能的叙事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包括所有可能的故事,它们代表着一种文学家叙事理念的未来指向。
当然也有些作者根据纸质媒介有限的可塑性,创作出一些纸媒超文本小说。这些作品极具实验性,如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塔1962年出版的《第一号创作》就被称为“扑克牌小说”或“读不完的小说”。因为印刷出的小说没有标注页码,且都为单面印刷与扑克牌很像,阅读之前读者可以将未装订的书页任意“洗牌”,这种排列组合可达10的263次方。根据“洗牌”后所得页码顺序的不同,导致我们的阅读有时将男主人公理解为“一个市井无赖······是一个盗窃犯和强奸犯;有时他又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外围成员······有时他简直就是一个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英雄······因为,事情发生的客观环境的先后秩序不一样,导致失误或悲或喜的结局就会有异”[22]。此外,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及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等虽没有《第一号创作》在形式上这般激进,但都具有情节上的多向选择性。他们似乎都实践着博尔赫斯的文学理想,产生一本读不完的书,让有限的文字无限的循环。文学在现代意义上有一种野心或霸权,想用语言包容所有的可能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语言是我世界的界限”和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著名论述,似乎与文学家的理想如出一辙,但事实上语言包含一种广泛性的同时又意味着一种范畴边界。文学家所想象的无限叙事,是某种语言权力的膨胀,是与线性叙事相似的文本霸权的体现。
四、差异中的超文本叙事
我们可以把三种超文本目的观与叙事直接联系起来:纳尔逊提出的根据某种目的进行的链接阅读,可以理解为对目的性情节的关注;哲学家们的后现代文本观可以看作叙事以形式手段反映的在思想层面上的追求;而小说家们对超文本“百科全书式”的野心则是对具体内容的要求。很明显它们之间存在目的性差异,想要把三种目的都统一起来是极其困难的。
现代计算机的超文本技术运用集中在如何让使用者在短时间获得最丰富、最相关的信息,以克服超文本的无限链接给使用者带来的信息冗余。目前的“云技术”“云运用”就是计算机超文本技术方面发展的最新阶段。而哲学家则对超文本提出了“星丛化”的要求,各个单位都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而不依赖于某种总体模式。对应到超文本叙事中,就要求超文本每个节点的内容都具有独立的意义阐释价值,形式上近似套盒式小说,如《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等等,而这些传统的套盒式叙事需要统摄在某个主题下完成(如大家围坐讲故事),这是后现代理论家难以接受的。小说家则与哲学家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理念诉求,他们希望用某种结构(如循环)把将叙事变成一种没有终点的线性延续。这种延续是环状,而非网状。因为一般来说,文学家所面对的纸质书写是无法像数字媒介那样提供超文本链接的。叙事线性的无限延续与内容的无限增殖,表现出某些现代小说家在面对文字叙事衰微时狂妄的留恋。
由此,三种超文本理念是存在差异的,如此繁复的理念关系如何与叙事结合起来就成了问题。可以说在具体运用中,哲学家和文学家的理念占了上风,似乎这些超文本作家在新媒体上就是要表现出与旧媒体的差异。一些小篇幅的超文本叙事近似于简单的文本游戏,而篇幅较大的超文本叙事又让人在链接的海洋中无所依凭。相反,超文本的非文学运用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在网络上看新闻、查资料等,无不感到超文本链接的便利。在超文本媒介的背景下,文学叙事与日常语言的背离所唤起的究竟是那种“使石头成为石头”的艺术审美,还是对文字进行的购物狂般的透支消费?原来在纸媒上无法完成的想象中的叙事形式,就是超文本叙事的现实,当理念可以成为现实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进步吗。如博尔赫斯作品中那些神奇的书一样,如果这些书就呈现在博尔赫斯眼前时,他还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去描述它们吗?或者如伊瑟尔所说:“可能的事情往往是令人不安的,但它同时表明任何渴望的确定性都是虚幻的替代品。由于隐含着无穷无尽的游戏变化基本是无凭无据的,所以,当构成游戏的差异性阻止了所有消除这种差异的努力时,‘文本的快乐’就允许阅读主体滑向其自身的无根据性······因为这种状态吞没其既不能使之远去也不能使之关联的自身,所以它是令人愉悦的,因此,它使阅读主体得以沉浸在‘文本主体’之中。”[23]
从文体上看,超文本是否适合用来叙事一直有争议。按卢卡奇的说法,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样式:口传时代的史诗,手写时代的罗曼司,以及印刷时代的小说。兰道(Landow)就认为信息时代的超文本似乎更加适合诗歌。
超文本更应该是诗性的形式而不是叙事性的形式······超文本生产——在叙事句法的层次上——以与诗歌生产的话语(phrastic)层次已十分相似。换句话说,重构叙事的方式导致一种与词序、日常使用等分离的诗性的陌生化······简单来说,超文本的链接把文本与类比、隐喻及其它思考的效果联系起来,即诗歌与诗性思维的联系[24]。
而另一位超文本大师博尔特则说:“文字文化仍然认为小说是属于印刷空间的······但(一些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创造了一批有重要意义的(数字叙事)作品。事实上,超文本小说已经成为超文本观念最有信服力的表现方式。”[7]121从创作实践来看,超文本文学中诗歌新作、佳作颇多,但叙事作品相对较少,自1990年第一部超文本小说迈克尔·乔伊斯的《胜利花园》出版以后,文字性叙事的超文本作品在创作量上始终低调,以至于以超文本写作软件鼻祖著称的东门(Eastgate)公司的网站目前也只有28部较正式和严肃的超文本小说提供出售。当然其它软件如Netscape Composer、Microsoft Frontpage也可以进行超文本创作,但总体上超文本叙事作品并非某些学者所估计的那样花团锦簇。原因在于超文本叙事理念与超文本技术理念的差异,对超文本工具的文学化使用本身就是对这种工具的“误用”,对于结构相对松散的诗歌来说与超文本的特性比较契合,而且诗作一般文字较少,保持了对其整体认知的可能。而叙事则不同,它自身的线性显得与超文本的链接方式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就是超文本叙事所要求的读写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使得故事的创作和阅读都成了一场“艰辛”的旅程。
或许“在得到了技术支持的叙事中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实验,美妙而大有前途,但却没有给经久不变的叙事结构带来一场革命,甚至微小的变化。叙事将继续是叙事,所以······叙事的未来就是叙事的过去”[25]。似乎叙事在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艺由人作······一台计算机的作用虽远远无法取代艺术家的创作行为,而后者当从排列组合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抓住这个集中反驳计算机辅助文学趋势的天赐良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文本艺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