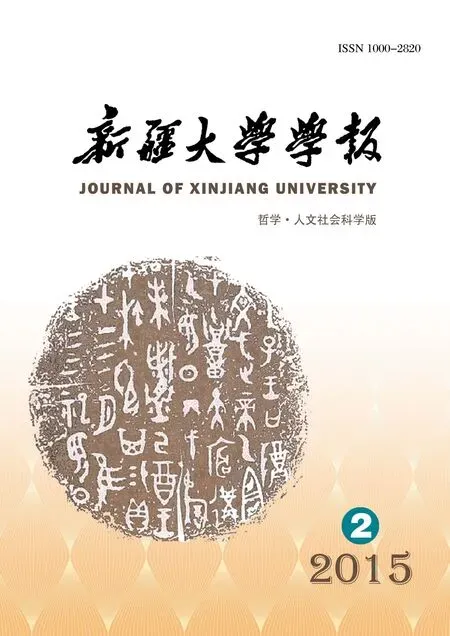“涉渡”与“越界”
——黄卓越的文艺批评思想述略∗
2015-02-20邹赞
邹赞
(新疆大学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黄卓越是一位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受到广泛关注的学者,其关注视域和学术实践具有鲜明的跨界意识。黄卓越的学术探索之旅呼应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与文化变迁,既是特定时期社会文化情境询唤的结果,也反映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下文将集中关注中国古代文论与思想史、文化研究以及海外汉学三个研究范域,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语境变迁及文艺批评界的学术论争,总结评述黄卓越的主要文艺批评思想及其学术贡献。
一
20世纪90年代初,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遭遇空前挫折,80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渐趋消褪,学者们开始反思“学术的价值”、“思想的意义”、“自我的位置”,由积极吸纳西学话语资源转向重新潜入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处,以期“沉淀自己的心态,检讨历史的经验”[1],学术旨趣也有意远离80年代喧嚣的方法论热潮,重视从学术史层面返归传统文化与古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卓越开启了自己庞大繁复的古代文论与思想史研究工程,这也成为他本人最富代表性的研究系脉,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完成了以明中后期文学思潮为考察对象的几部厚重专著,如《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二是参与主编、辑录、校注了卷帙浩繁的传统文化与思想读本,如《中华古文论释林》、《中国佛教大观》等。
总的看来,黄卓越的古代文论与思想史研究注重一种整体视野的全景式观照,综合运用史料考证、话语逻辑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文学思想作系谱化专题化的深入阐释。其创新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明中后期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强烈转型意味的特定时段,其思想文化携带着丰富的历史密码,成为学界认知中国现代性的近代起源、探析晚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所必须参照的对象,但既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小说和戏剧两类文体上,对诗文的关注远远不够,更谈不上理清这一时段的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心态及知识分子问题。因此,黄卓越别具慧眼将晚明文学思潮、明中后期思想史以及诗文观纳入研究视域,通过勘发大量过去未曾触及的史料,重新梳理了多种观念发展的线索。黄卓越的古学研究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新颖的阐释视角,还遵循一种自觉的方法论体系,他尤其强调要突破文学内部研究的形式诗学的局限,倡导一种沟通文本内外的整体性“社会——文化”视角,比如在考察晚明佛学中兴时,既关注当时的社会性因素,也突出佛学内部要素的组合转化。这种对整体视野的重视,实际上关联着黄卓越对于新文化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吸纳,比如他在考量“情感—性灵”这一对晚明文学思想进程中的内在矛盾时,直接引述了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思想,认为要深入考察某一思想话语的形塑过程,就应当重视社会场域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机制、文化场域中的结构性互动等等。
其次,在一般性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突显历史语境意识,既注重对关键概念的历史化梳理,也强调对隐藏在概念背后的话语逻辑的深层分析,形成了一套有意味的文化阐释框架。在黄卓越看来,任何概念都不是封闭的、绝对自足的,“概念的使用均有其自己的逻辑定位,又与一定语境相关,这是讨论一种思想命题的前提,否则便会重蹈一些学者在解释这类概念时的故辙,在思维网络的穿行中迷失方向,引起误读”[2]。基于此,黄卓越的绝大多数论著都注重对理论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语义学层面的细致梳理,借助于观念史的构筑,搭建起自我言说的话语框架。《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的“下编”就是对此时期文学思潮的几组关键概念如“心源说”、“童心说”、“性灵说”等的专题研究,旨在以概念分疏为线索,考辨源流、澄清误解。或可认为,黄卓越对文论核心概念的辨梳,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式的文化史、思想史考察,兼及历史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的逻辑架构,条分缕析思想话语自身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此处不妨举“性灵说”为例,黄卓越以“性灵说”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措用为线索,追溯其学术渊源,比较分析了“性灵”与“童心”、“真性”等相关概念的差别,从历史考证与概念自身的体系两个层面展开分析,令人信服地纠偏了一些早已化装成“常识”的误读。
再次,通过反思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现状,在比较分析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概念史、文学批评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观念史”的重要范畴。黄卓越认为:“观念史不仅研究作品与批评中的‘思想’······也研究未能明确被指称为‘思想’的‘观念’。”[3]3一般来说,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思想史研究常常采用“概念史”的模式,但单纯的“概念史”研究并不契合中国古代文论的构成逻辑,最主要原因在于它抛开了这些概念得以呈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在场,以致使这些概念因“不受当时具体关系要素的制约而成了自由游荡的要素,因此便可任意利用、组合,无视意义的原始确定性”[4]正文序言第6页。相比之下,“观念史”的范畴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它遵循一种整合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文化诗学”视野,融合了文论史研究中的“内与外、个体与群体、抽象与历史、理论与作品之间相互隔绝的情况,或相互间常发生的紧张关系”[4]序言第7-8页。不仅如此,“观念史”摈弃那种脱离历史文化维度对概念作单线逻辑的读解路数,它尤其重视要在各种关系要素的参照比对下考察概念的缘起及其意义变迁,呼吁要密切结合特定的“境域”来评估文论话语、文论家或文艺流派的文学思想史意义。而相比较于思想史的研究,观念史则可以将被摈弃在思想史之外的那些处于前意识状态,或隐伏在文本肌理与生活史实之中的多种“意识”一并纳入在观察的视域之中。“文学观念史”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文论研究中的“义理”与“考据”之争,成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方法,“观念史概念的引入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种知识形态的产生与更替并不是自足的,而是受到更大范围内席卷的观念的影响与支配的”[3]4。值得注意的是,黄卓越还在“文学观念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地域性文学观念史研究的思考,比如他在阐释明中期的吴中派文学时,结合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性经验,从“隐逸传统”、“博雅与审美主义传统”、“文人谱系”等综合视野考察吴中派文学与文化传统习俗之间的关联,透视吴中派文学如何启动重新编码机制,整合与再造一种契合于地方性经验的“文化传统”。
最后,黄卓越认为批评史研究应当加强对文献史料真实性、学理性的考辨,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史料一般分为史实性史料和评论性史料,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忽视基础性史料清理工作的价值,“基础性的史料确认与秩序梳理等本身即是最尖端的,不一定阐述性的工作就高于实证性的,关键还在于要看注入其中的技术含量程度,对事相的揭露程度,及对学科知识增长所提供的数量值”[4]序言第6页。另一方面,批评史研究对于评论性史料的择取务必慎重,因为对材料的精准把握不仅有助于察知所谓权威性、常识性提法的偏颇之处,比如各种中国文学史、文论史教材和著作均使用“诗必盛唐”来标识前后七子的诗歌理念,但如果对前后七子的言论作一番细致的知识考古,就会发现“无任何一人曾经如此措辞表示过,而且其中有几人的基本观点还与之有鲜明对立之处”[4]序言第4页。此外,材料的选择不当、标准不严也将直接导致研究整体水准的下降,甚至可能导致荒谬吊诡的结论。
二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在思想文化界激起了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汹涌而来的市场化、商业化潮流为大众文化提供了理想的土壤,以启蒙和审美主义为诉求的精英文学,逐渐让位于以感官娱乐和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学丧失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光环,在以商业赢利为首要目标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下节节败退,一边是文学遭遇不可逆转的边缘化,向影视等大众文化俯首称臣;一边则是审美边界急剧泛化,审美客体扩张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语境下,一批有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后果,尝试在思想史、文化史的脉络上测绘90年代的文化地形,解码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症候,进而评估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随着西方文化理论的大量译介,加之港台流行文化的催化剂作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迅速进入中国大陆学界,并且在以文艺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为中心的学科阵营攻城略地[5]。狭义上的“文化研究”指向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传统,它以政治性、实践性、当代性和批判性为鲜明底色,强调从跨学科视角研究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青年亚文化、流散文化、劳工政治等边缘文化样态,旨在发掘其间的支配性结构和权力关系,试图探索一种别样社会的可能路径。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应用,既是本土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受益于西方文化理论的大规模译介及本土学者对之的谱系梳理,形成了所谓“研究‘文化研究’”和“做‘文化研究’”两脉,虽然各自关注的重心不同,但都没有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完全割裂开来。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黄卓越率领自己的学术团队,细致分梳文化研究的学理谱系,创建“BLCU国际文化研究论坛”、“国际文化研究网”等学术平台,积极开展与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并且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境,重新阐释“意识形态”、“大众”、“书写”等概念,以区别于西方的同类概念,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话语和思想资源。
应当说,黄卓越对于文化研究的关注,一方面是缘于90年代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思想危机与知识转型,“社会”的层面显影于文学批评界;另一方面则要追溯到学界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论争。在他看来,如果要准确认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从学理上探讨文化研究的源流及其兴起的必然性,“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出现就不单是一种学术或学科选择的问题,在其学院化的表述中反映出的是对战后欧洲社会重大转型的一种敏锐感受,这种转型需要学术界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与探索的框架、新的知识表述体系,以对之作出积极的反响”[6]。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重建一种整体化的思想和立场,以便重启对既定知识秩序与思想谱系予以深刻检审与反思的工程。黄卓越指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绝不仅是一次学科越界或者理论话语、研究方法的借用,真正的价值在于重新激活文学批评的活力,使之由边缘性话语转化为公共性话语,重返社会生活的中心场域。再者,文化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文学研究敏锐回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生产—流通—消费”的文化运作模式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运行流程、权力机制与意识形态症候。此外,黄卓越充分利用其古学研究、经典研究的既有视野,认为文化研究的介入将大大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一方面使大量边缘的、底层的文学材料和文化经验获得重生,这将有便于学界回应“文学研究的边界移动”、“文论何为”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漫长历史与文化观念建构的整个过程中,考察历史上的书写权力、表征建构、编码活动及各种文本之后隐藏的观念习则等。从后一方面来看,文化研究也就与新文化史的实践密切地交集在了一起。
黄卓越结合本土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境,相当敏锐地认识到文化研究理论话语在旅行过程中遭遇了改写、移位和变异,有些理论话语则并非西学之独创,在中国也有其自身的传统,因此他主张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重新阐释这类核心概念。就前者而言,针对中国文艺理论界常常混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化理论”的情况,黄卓越专门撰文以厘清三者在学理上的差异,认为它们“处理知识与观念的基本模式不同”[7]。文化研究尽管也重视对各种理论工具的使用,但又更加倾向于民族志式经验参与,尤其重视发掘那些被传统学术研究和精英主义边缘化的文本或文化现象;文化批评则呈现出泛专业化、重视理论性思维的态势,更追求所谓思想性价值而非事实性价值,容易陷入凌空蹈虚的庸俗化境地;文化理论则高举“普遍性话语”的旗帜,与文化研究所指涉的对象不尽相同,比如杰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严格说来不属于“文化研究”,应当归到“文化理论”范畴。如果参照斯图亚特·霍尔对“文化研究”几种范式的划分,那么当文化研究发展到结构主义阶段,尤其是吸纳后现代理论之后,文化理论就基本上可以放置到文化研究的范域内加以讨论了,这也可看做文化研究所具的一种强大的归化性与整合性功能。就后者而论,黄卓越对“大众”、“意识形态”、“书写”等文化研究关键概念做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此处仅以“大众”为例略加阐述。“大众”一词在中西思想史、文化史上有着各自的脉络,围绕“mass/popular”(通俗—大众)的语义分析也成为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翻译问题之一。黄卓越从语词翻译入手,循英语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爬梳“大众文学”的意义变迁,尝试廓清其为“大众文化”所遮蔽的语义向度。与此同时,黄卓越立足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探析了“大众”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显影之途,“中国近代的所谓印刷资本主义与大众文学在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力量被接纳的,未像西方话语那样视若消极之物而处以苛严的批评”[8]41,他聚焦于启蒙话语的逻辑,分析中国知识界如何认知“大众”以及“大众文化生产”,“经由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与毛泽东的延安讲话,遂在建国以后摒却群言,大众文学树立为覆盖一切文学书写的正统型范”[8]42,此时“大众”开始作为“革命的主体”,与代表历史进步性的“群众”、“庶民”、“民众”、“人民”、“平民”等指称相类同。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原来的“革命大众”转化为了“消费大众”,另一方面,“大众”所承载的“能动性”、“抵制的潜能”等意义维度也被重新发掘出来,由此而导致了“中西方‘大众’话语始而有异、渐次趋同”[8]47。
中国文艺理论界自引入“文化研究”的思想话语以来,大部分学者都忙于“借他山之石”应答本土文化热点问题,较少有人从学术史角度勾勒文化研究的(准)学科渊源及播撒之旅,由此导致学界对文化研究的认知存在诸多不足。一般认为,广义的文化研究不仅指向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英国文化研究,还包括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等等。作为一名自觉的文化研究学者,黄卓越指出,尽管国际上的文化研究存在多重路径,“但后来也以Cultural Studies概说之,是以英国的范式为某种参照系来梳理的,并借之而构形为一种国际通约型的学术样式”[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黄卓越率领自己的学术团队,尝试对英国文化研究作系谱学的学术史梳理,并在细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提炼问题意识,围绕英国文化研究的事件或人物展开专题研究,有意突破“导论”、“概论”式简约介绍,深入探查文化研究的微观细部。一方面,黄卓越示范性地考察了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核心论题,比如通过全方位的文献细读、纵横交错的比较分析、历史化与反思性相结合的观照视角,对“文化”概念的塑形做了令人信服的勾描①详见黄卓越的系列论文:《定义“文化”: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表述》,载《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1期;《定义“文化”: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载《燕赵学术》2010年第1、2期;《“文化”的第三种定义》,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另一方面,黄卓越强调英国文化研究自身的多元性,自觉解构伯明翰学派的神话,重视结构主义范式之后的“《银幕》理论”、默多克的政治经济学传播理论、本内特的文化政策研究等其它分支,相关研究成果汇集为《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成为国内学界集中展现英国文化研究的一扇窗口。
虽然黄卓越主要侧重于研究“文化研究”,但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比如就撰有对博客私人写作与公共空间的讨论等文章,最具代表性的当推2012年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文化政治》上的长篇英语论文《两种话语之争:一种新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形成》。该文从“社会意识形态”的概念出发,对北京地区“小升初”教育现状展开文化分析[10],有效地“接合”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民族志经验,堪称当代中国文化个案研究的范本。
三
黄卓越的学术探索历程呈现出相当清晰的“由窄到宽,由宽到窄”的发展脉络,新世纪之交,他游走在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国际汉学开始成为黄卓越的关注重心,作为一项处于“进行时”状态的庞大研究工程,虽然许多极有分量的论著尚待发表,但国际汉学研究犹如一得天独厚的学术演武场,充分调用了黄卓越在诸多领域的研究积累,可谓一次比较集中的智识爆发。总的来说,黄卓越对于国际汉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其一,积极倡导“国际后儒学话语谱系”,引领一种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模式;其二,突破国内学界大多集中关注20世纪70至90年代海外著名汉学家的视野局限,尝试将19世纪初及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英美中国文论纳入研究视域,使得国内的汉学研究更具连贯性和整体视野;其三,敏锐察觉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汉学新变,尤其是英美汉学的“文化转向”,主张将英美中国文论研究放置到英美后期汉学演变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观照,试图从更深层次发掘英美中国文论研究与整个汉学发展体制之间的关联。
为了阐明儒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具体处境及其发展走向,2006年,黄卓越与多位国内外学者携手合作,成功主办了“儒学与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后来汇编成册。黄卓越在为论文集撰写的“代序”中详细回溯了国内外儒学的变演过程,对自现代以来就在国内外儒学圈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儒学”模式展开了深入检讨,认为“新儒学”所标榜的“整体论”太过本质主义化,“尽管在他们的论述中已更多地注意到社群的功能,但这种‘关系’或‘关联’却不是‘接合’(articulate)性的,而是依然要从决定性的心体或主体启程的;依然不是美学式关联的,而是因果逻辑式关联的”[11]2。“新儒学”存在的问题还包括精英主义色彩太浓,关注视域脱离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鼓吹本土文化的普适性,与多元主义文化观及多元文化现状格格不入。因此,黄卓越明确提出“后儒学”概念,试图以“后儒学”代替西方汉学的“新儒学”模式,“我们这里所用的‘后’,不唯有遗存的意思,更主要地还是后现代的意思,含义更为广泛。因此,我们所说的后儒学也就是一种后现代儒学,当然这也包含有新儒学之‘后’的意思”[11]18−19。“后儒学”对“新儒学”的取代堪称一次“范式革命”,“后儒学”提倡一种置身于本土—世界、地方性—全球化张力空间中的商谈对话,摈弃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模式。为了适应全球化与后现代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背景,“后儒学”所关注的问题对象及其实践运作的方法论模式都发生了改变,显现出与新时代汇通与对话的态势。在黄卓越看来,前一段出现的有关儒学研究范式的指称如“新儒学第三代”、“新新儒学”、“后新儒学”等,也都在不同层面具备一些“后儒学”的前瞻性视野,但与之同时又还仍然陷入在“新儒学”的思维模式中,保留了旧哲学的深刻痕迹。而“后儒学”的命名则有效地规避了“新儒学”的单边话语模式和决定论思维,既有利于应对后现代的差异政治与微观政治,也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多元文化格局。如今,“后儒学”的提法已经为学界广泛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一种“对话式”的汉学模式。
诚如学界所论,20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文论研究在英语世界蔚成热潮,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在大汉学的繁复语域里成功突围,显影为海外汉学的中心论题。基于此,国内学界对于英美汉学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这一高峰时段,客观上忽略了那些散落在其它时期的话语现象,导致了一种“断代”、“断裂”的假象。为了打破这种“断裂”的幻象,重新建构起英美中国文论研究的历史化叙事,廓清中国文论在英美学界被构形为“独立言说形态”的演进脉络,黄卓越开启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汉学原典研读计划,通过追溯19世纪初以来英美中国文论研究的变演过程,旨在厘清该领域“从大汉学研究至文学史研究,再至文论史研究”以及“从‘理论的研究’至‘理论的诠释’,再至‘理论的建构’的进阶”[12]201。黄卓越强调要对英美中国文论研究作整体性、动态性观照,他细致梳理了19世纪英国的中国文论研究概况,通过评述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汉学家的代表性成果,总结出19世纪英国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特点,比如欠缺独立的学科意识,对文本的择取相当宽泛随意,将文本对象锁定为“大文学”;此时的汉学家大多兼具外交官、传教士等身份,他们习得汉语主要是为了日常交际,因此他们在介绍中国文学时会集中关注文字与音韵。至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意象派文论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批评思潮,以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庞德(Ezra Pound)等为代表的对中国诗学的新阐释,通过逆袭的方式改造了英美汉学中国文论的观照视野,并直接影响到40年代后如修中诚(E.R.Hughes)、海陶纬(J.R.Hightower)等学理化与学院式的研究。而紧接其后,才有了学界较多关注到的70至90年代那种更以专业化面貌出现的英美国家的中国文论研究。客观上讲,前一阶段的英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尚处于“懵懂的潜伏期”或初步展现期,但对之进行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细致与完整地了解英美国家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动态性框架,也能更为有效地探查诸相关批评家与理论家在这一谱系中所居的言述位置,及文论研究有可能给整个英美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的某种意义反馈”[12]201。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伴随着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环球旅行,英美汉学羼入了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这些理论与方法的汇入推动了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汉学研究态势,但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黄卓越率先关注并专门探讨了英美汉学的“文化转向”,他旁征博引汉学研究个案,专题分梳性别理论、传播理论、书写理论等对于“文论”话题的影响。黄卓越指出,随着文学边界的扩容,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类同于“文本、想象、书写、表征”等理论关键词,与此同时,“文论”的既定边界也将被打破,其话语框架也将为相关学科所共享,回返“大汉学”的趋势十分明显。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英美汉学将更加注重“理论意识”和“场域意识”,“文论”不再被预设为权威话语,而是需要重新放置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及关联机制中加以考察,正如黄卓越在造访英美汉诗形态研究的理论轨迹时所得出的结论,“一方面,西方各阶段对汉诗诗学的研究均与其学术与批评模式的特点相应,并经历了由粗至精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每一期的研究或变更之下也均蕴含着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整体设定,认同的程度自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汉学家对自己阐释方向的选择”[13]。
结语
近三十年来,黄卓越潜心问学,上下求索,在这段谱牒不算太短的“学术苦旅”中,黄卓越统摄中西视野,由西学和文艺心理学入手,关注重心相继聚焦于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思想史、文化研究、海外汉学等领域。他在广阔的学术天地间撑起一叶涉渡之舟,有意识地接合文本内部的能指狂欢与大历史的文化政治,实现了个人学术生命中一次次的“华丽转身”。无论研究对象是批评史、思想史、文化研究学术史、当代文化现象抑或是海外汉学新动态,黄卓越都依循严谨规范的资料爬梳与历史论证,借助多维交叉的话语逻辑分析,对抽象枯燥的学术命题展开极富个性化的深度思考与情感对话,建构起一种兼具历史理性、人文关怀与生命温情的独特批评样态,在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思想图景中显得分外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