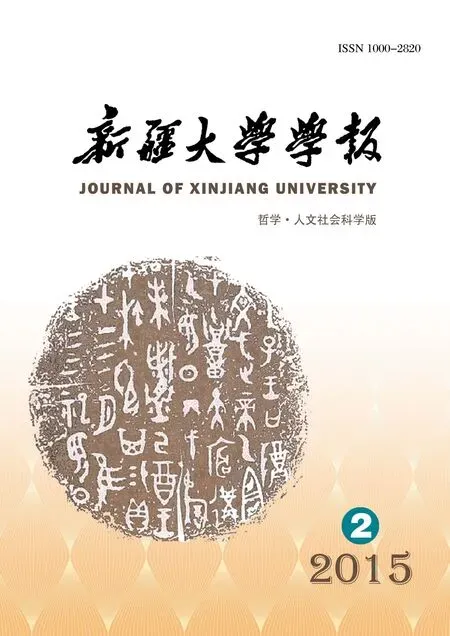叙述背后的故事
——赵毅衡文艺思想述略∗
2015-02-20李松睿
李松睿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北京100029)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赵毅衡教授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位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钻研形式主义文论的文艺理论家,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将形式主义文论介绍到中国,改写了中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由现实主义—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例如《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等,更是以其理论把握之精到、研究视野之开阔、叙述文笔之酣畅,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80、90年代,很多学者正是通过赵毅衡的著作才一窥形式主义文论、叙述学的门径。以至于到了今天,无论文学研究者是否认同形式主义文论将广阔的现实生活暂且放入括号存而不论的理论前提,形式主义文论处理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都已经成了文学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工具。有些研究者甚至还不无偏激地指出,能否在方法论上超越现实主义—反映论,掌握形式主义文论的基本方法,是判断文学研究者是否合格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赵毅衡的文艺思想已经在中国的文学研究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迹,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他的某些学术判断、学术观点,其思想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需要人们进行认真的整理。本文就试图以时间为叙述线索,勾勒赵毅衡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呈现其研究在中国学界所处的独特地位,并总结其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
一、以形式为中心
赵毅衡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回到上海,并在这座城市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正像他后来在回忆中提到的,“上海的建筑、城市格局、西方人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等,我印象深刻。实事求是地说,上海文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1]。的确,上海在解放前长期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它那畸形繁荣的经济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都市文化,并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于是,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想以及价值观在这座城市相互碰撞、交锋、融合、新变,熔铸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品格。而赵毅衡后来的学术风格——以用舶来理论解读中国作品,利用本土经验推进理论发展为特色,这无疑与其早年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1963年,赵毅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英文系,并很快成为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然而不幸的是,赵毅衡毕业于1968年,正好赶上“文革”高潮,他作为英文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却先是分配到农场劳动,后调到徐州市郊的煤矿当矿工,并且一干就是七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勤奋好学的赵毅衡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他借着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机会,在心里将其中的文章翻译为英文,为其日后从事外国文论研究并赴美学习做了充足的准备。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后,赵毅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诗人卞之琳攻读硕士学位,这才离开了煤矿进入文学研究界。应该说,在农场和煤矿劳动的经历,是赵毅衡生命历程中的一段“弯路”,但在这一过程中所接触的人和事,却锻炼了他的性格与心智,让他能够摆脱种种人云亦云的套话,对社会和人生有了独立的看法,为他日后成长为具有鲜明学术风格的学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像他在回忆那段煤矿生活时所说的:“1978年早春,我从黑咕隆咚的煤窑里爬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叫人打战。十年的体力劳动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几十年来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主义。我贴近生活,贴得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态的生活,一切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2]
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写于21世纪的回忆或许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赵毅衡在1978年的心理感受,但它无疑揭示出:赵毅衡和彼时大多数文学研究者一样,因为经历了“文革”,开始对长期流行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只不过赵毅衡没有像大多数同代人那样,在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心生厌恶之后,立刻就生吞活剥地运用诸如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系统论以及结构主义等一系列西方理论,在这些舶来理论所布下的重重迷宫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而赵毅衡虽然同样否定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但却没有匆匆忙忙地弃之如敝履,而是开始思考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得以流行的原因。他认为现实主义文论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是“中国现代以来的庸俗的经济—社会关系决定论,与中国本有的文以载道论相结合的后果”,因此文学批评总是“把文学当作‘现实的反映”’[3]。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们更关注所谓“内容”,而忽视了文学的形式。在赵毅衡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亟需补上形式主义文论这一课,摆脱只看内容忽视形式的惯常思维方式。因此他才选择形式主义文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显然,这一选择绝不是在仓促之际的随意之举,而是源自赵毅衡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界存在的问题的清晰判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这位才华横溢的研究者会花费数十年的精力来耕耘这一研究领域。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赵毅衡对形式主义文论所做的研究主要是《新批评》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这两本专著。今天重新翻开这些著作,人们或许会觉得它们显得有些简单,特别是《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似乎不像是一本学术专著,而更像是一部教材。赵毅衡在该书中用简明流畅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例证,对叙述学中的基本概念,如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等,进行了系统介绍。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认真阅读这部著作,人们就可以掌握对小说进行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我们当然无需指责该书偏于概念介绍,而较少学术创见,因为它本来就是作者于1985年写博士论文时的读书笔记。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文学研究者认识到80年代的文学批评流于印象式批评和对作品内容、主题思想的空洞阐发,缺乏对作品形式的细致分析,开始尝试运用叙述学理论分析作品。但由于中国学界在这一时期缺乏对叙述学理论的详尽了解,使得“大学生研究生经常犯叙述学错误,往往使整篇用功写的论文失据。甚至专家们堂皇发表的文章,甚至参考书,甚至教科书,也会出现‘想当然’式的粗疏”[4]。那么该书对叙述学基本概念、小说分析基本方法的简明介绍,正可谓恰逢其时,使中国学界系统地接触了叙述学理论,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这也就难怪该书问世后很快就行销一空,在青年学者中间广泛流传,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盛况。
与《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相比,《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该书在新世纪经过修订后,更名为《重访新批评》)更像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它以新批评派对文学性质的理解、从事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以及诗歌语言分析方法这三个切入点,对这一文学批评派别的发展过程、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介绍。由于国内学者大多是通过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了解新批评的,使得人们虽然对新批评派关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他们对传纪研究、心理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评,以及他们解读作品的基本方法有所了解,但对这些观点形成的背景、这一流派内部的种种分歧等却不大了然。而赵毅衡对新批评派的研究则没有局限于对观点的介绍上,而是深入到这一文学批评流派的内部,努力呈现各种观点如何在争论中形成的过程。例如在涉及到“感受谬见”这个新批评派提出的重要命题时,赵毅衡没有仅仅介绍该命题指的是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并非判断其水平高下的标准,而是从1941年兰色姆在《新批评》一书中指责瑞恰兹、艾略特、温特斯以及燕卜荪等新批评派中的代表人物进行“感受式批评”入手,呈现这一命题得以提出的复杂背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毅衡没有把西方理论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努力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其思想特色进行评说。他认为“反‘感受谬见’说,作为一种权宜性的批评方法,暂时把读者问题搁起,未尝不可一试。但在理论上,它却是站不住脚的”[5],并举出维姆萨特、比尔兹莱等人在评价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不得不借助读者感受立论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新批评派那颇为偏激的理论预设和精彩的批评实践之间的裂隙,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因此《新批评》一书并不仅仅是全面介绍了新批评派的文艺思想,更总结了该派理论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过程中的得失成败,为中国读者进一步寻找合适的批评方法提供了借鉴。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学者解读西方文学理论的经典范例。
二、“形式—文化论”诗学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形式主义文论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确实充满了洞见,但其理论预设却极为偏激。它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小宇宙,切断其与作者、读者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一切联系。因此,形式主义文论虽然对作品内部所蕴涵的张力、悖论以及反讽等因素异常敏感,但却对广阔的现实生活视而不见,这使得形式主义文论多少显得有些狭隘局促。关于这一点,对形式主义文论情有独钟的赵毅衡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他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历时提到:“大约在1985年左右,我从叙述学读到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6]247也就是说,赵毅衡非常清楚形式主义文论就形式谈形式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但他并不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是重新回到内容,相反,他觉得探究形式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是突破形式主义文论自身局限性的有效路径。正基于这一研究思路,赵毅衡在研究西方文论时以系统介绍形式主义文论知名,但在从事具体的文学研究时则没有单纯地使用形式主义文论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对作品的形式分析和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在笔者看来,最能体现这一研究思路的作品,当属初版于1994年的《苦恼的叙述者》。
这部学术著作以晚清时期出现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与传统中国小说、五四白话小说之间的区别,分析其叙述形态之特异性的来源。20世纪80、90年代,晚清时期以其中国与西方相互杂糅、传统与现代犬牙交错的特质,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赵毅衡、陈平原、王德威等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趣的是,《苦恼的叙述者》和陈平原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均使用叙述学理论处理晚清小说,将二者进行对比,或许是呈现赵毅衡研究思路之特色的最佳途径。表面上看,赵毅衡、陈平原在处理晚清小说时,都是从叙述角度、叙述时间以及叙述结构等叙述学理论出发,分析晚清小说在形式上的特殊之处。对叙述问题,或者说形式问题的高度关注,是这两本著作最有特色的地方。并且由于赵毅衡、陈平原处理晚清小说的方法基本相同,他们在总结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特色时也有不少暗合之处。只不过在陈平原那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被贯彻得更为彻底,而超越单纯的形式分析则是《苦恼的叙述者》一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他对1902至1927年间出现的千余种著、译小说进行抽样分析,以叙述角度、叙述时间以及叙述结构为参照系进行量化统计,认为“中国小说1902年起开始呈现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大幅度背离,辛亥革命后略有停滞倒退趋向,但也没有完全回到传统模式;‘五四’前后突飞猛进,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基础”[7]。而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在陈平原看来则是“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8]这二者的合力。
如果说陈平原主要以叙述学理论为依据对晚清小说进行量化统计,其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超出形式主义文论的窠臼,那么赵毅衡则是以叙述学分析为出发点,进而去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在晚清时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苦恼的叙述者》中,赵毅衡没有把目光局限在晚清小说的形式特征上,而是将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机制的表征。这也就是赵毅衡所说的,“小说叙述文本,可以作为文化的窥视孔,可以作为文化结构的譬喻”[6]249。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形式也就成了某种指示器,其种种变异不过反映着中国社会文化在晚清前后经历的变化。在具体的分析中,赵毅衡虽然同样分析叙述角度、叙述时间等叙述学问题,但他关注的重点是叙述者的形象问题。他认为在传统中国小说中,“叙述者享有干预的充分自由,成为叙述中几乎是垄断性的主体性来源,牢固地控制着叙述,由此阻止诠释分散化和意义播散”。到了晚清时代,“叙述者对其权威受到挑战相当不安,而用过分的干预来维系叙述的控制······有时叙述者干预之多到了唠叨的地步,不必要地自我辩护其控制方式,显得杌陧不安”。而在五四白话小说中,叙述者地位开始下降,叙述控制得以全面解体,“使整个叙述文本开始向释义歧解开放”[6]166−167。在赵毅衡看来,由于传统中国在文化上从未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也就牢牢地控制着作品的意义;而在晚清时代,中国文化的合法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时期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也就进退失据,显得极为不安、异常苦恼;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价值越来越趋于多元,使得小说叙述者再也无法控制文本的意义阐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苦恼的叙述者》一书对晚清小说的研究是从形式分析入手的,但其真正关心的对象却是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也就是说,赵毅衡实际上是将小说的形式特征看作是文化结构在小说文本中刻下的一系列印痕,并由此去窥探文化结构自身。这就使得赵毅衡的研究相较于陈平原那部专注于形式分析的著作,获得了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赵毅衡的研究实际上是联结小说形式与文化的中介,它一端勾连着小说的形式特征,另一端则与更为广阔的文化对接。这一独特的研究思路,被赵毅衡命名为“形式—文化论”。在赵毅衡后来的很多研究论文中,如《无邪的伪善:俗文学的道德悖论》、《重读〈红旗歌谣〉:试看“全民合一文化”》以及《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等,这种“形式—文化论”研究思路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无邪的伪善:俗文学的道德悖论》中,赵毅衡就对明清时期戏曲舞台上折子戏大行其道,而全本演出相对较少的现象进行了精妙的解释。他没有像很多古典文学研究者那样,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本演出耗时过长等纯技术性原因,而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解释作品的演出形式问题。赵毅衡认为以《白兔记》为代表的俗文学内部存在着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张力,诸如灵异、闹剧等亚文化内容必须包裹在符合主流文化的整体框架中才能得到呈现。在赵毅衡看来,折子戏的演出恰好可以化解这一文本内部的张力,因为“在折子戏中,伦理逻辑被悬置了,被推到一个方便的距离上。这样,在释读文本的意义时,全剧语境既可以被引出作为道德保护,又可以置之不顾以免干扰片段的戏剧兴趣”[9]。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赵毅衡的文学研究超越了单纯的作品形式分析,进而去讨论使文学作品成为可能的文化背景、文化结构。
三、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
从赵毅衡所使用的“形式—文化论”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他将人类的社会生活看作是某种双层结构,上面一层是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新闻以及影视等在内的各种叙述文本,而下面一层则是支配前者,并使其成为可能的元叙述(或者用更通俗的说法,那就是文化)。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元叙述提供意义的来源,而上一层的叙事文本则将意义以各种形式叙述出来。赵毅衡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通过对上一层叙事文本的分析与解读,去窥探下一层元叙事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形式—文化论”。只是因为赵毅衡在此时碰巧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因此他才会选择将文学文本作为通向元叙事的幽谧小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赵毅衡渐渐地不再满足于将自己处理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文学上,而是希望去探究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这就是使得他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形式主义文论、叙述学研究,开始进行符号学和广义叙述学研究。而由此引发出的问题是,这里的所谓形式主义文论、叙述学以及符号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赵毅衡的研究转向究竟有何意义?
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赵毅衡谈到了形式主义文论、叙述学以及符号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表示:
我把形式文论分为这么几个大的部分:符号学,属于这里最抽象的层次;叙述学是符号学运用于叙述,正如语言学是符号学运用于语言,但是语言学学科之独立庞大历史久远,远远超过叙述学和符号学,因此很难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运用。叙述学本身也太庞大,所以单独成为一个学科,符号学与叙述学现在就并列了。其它应当属于形式论范畴的,包括风格学、修辞学,它们都是由符号学总其成的形式论的一部分[10]。
也就是说,赵毅衡认为符号学本来属于最抽象的层次,叙述学不过是将抽象的符号学原理运用于叙述文本之上而已。但由于叙述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有着庞大体系和自身历史的学科,使得人们很难将叙述学看作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因此他虽然将符号学看作是涵盖面最大的学科,但迫于学界惯例却不得不将符号学和叙述学、风格学、修辞学等权宜性的并列在一起,放在形式主义文论之下。
以文学文本,特别是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叙述学,只能涉及人类表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而研究如何表达意义、解释意义的符号学,则将人类的全部表意活动纳入其研究范围。因此,当赵毅衡将研究重心转向符号学时,他实际上是要将人类社会的全部表意活动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无疑是一项规模庞大,让人望而生畏的工作。而赵毅衡最新的两部专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和《广义叙述学》——就是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
在2011年的专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赵毅衡尝试在综合国际符号学研究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和中国符号学传统,重新建立一套符号学体系。不过在笔者看来,赵毅衡花费巨大的心力按照符号的构成、符号的意义表达、符号的传播、符号的解释以及符号的修辞等项目,构建起一套表述符号学的完整体系,其意义当然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但读过该书之后,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那套完备的体系,而是赵毅衡在总结西方各派理论家对某一符号学问题的论述后,会运用中国本土的经验与例证,指出西方理论家论述的不足,并进一步推进对该问题的探讨。这才是赵毅衡的这部著作中最令人钦佩的地方。例如在《符号学》上编第九章第十节谈到符号学修辞的四种主要类别——隐喻、提喻、转喻以及反讽的演进时,赵毅衡先是引证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格雷马斯等人关于上述四种类型相互之间是否定关系的论述,接下来,他又依次引用了维柯、诺瑟罗普·弗莱以及卡尔·曼海姆关于四种类型在历史过程中依次演化的观点。再次,他还进一步介绍了皮亚杰、E·P·汤普森以及海登·怀特等人如何在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运用符号学修辞四体演进的理论。最后,赵毅衡又用中国传统小说以及宋代易学家邵雍的论述,证明四体演进理论对于中国本土文化来说同样适用。行文至此,赵毅衡已经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博学和宽阔的理论视野。但他对此还并不满足,而是进一步对四体演进理论提出质疑,即“四体演进说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反讽之后,下一步是什么?”[11]221在赵毅衡看来,中国文学史上发生的一系列文体变迁表明,当文学发展到反讽时,并不像保罗·德曼所言,意味着“文化表意无法进行下去”[11]221。恰恰相反,文化总是会在一种表意方式终结后,重新发现新的表意方式,“重新构成一个从隐喻到反讽的漫长演进”[11]221,就像古典小说让位给白话小说、现代小说让位给影视作品一样。正是在这里,赵毅衡没有像很多中国学者那样视西方理论家的论述为普遍真理,而是敢于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并进一步推进对问题的讨论。在笔者看来,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学术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些地方。
如果说赵毅衡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主要在抽象的层面上探讨了意义的传播、释读等问题,那么他于2013年出版的新作《广义叙述学》则主要探究意义如何通过人类具体的叙述活动表达出来。与传统的叙述学相比,所谓广义叙述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不再把研究对象限定为文学叙述,而是试图为包括文学、历史、传记、新闻以及影视作品在内的人类全部叙述行为寻找规律。需要指出的是,创建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广义叙述学绝不是什么异想天开或头脑发热的举动,而是近几十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医学都出现了所谓“叙述转向”,叙述成为这些学科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界迫切希望能有一门能够讨论所有叙述体裁的共同规律的学科,而赵毅衡试图创建的广义叙述学正顺应了这一要求。在笔者看来,或许《广义叙述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创造了一种覆盖所有叙述体裁的分类方法。赵毅衡在书中按照横纵两条轴线展开对所有叙述体裁的全域分类方案。一条轴线是按照叙述体裁的“本体地位”,分为纪实型体裁和虚构型体裁;另一条轴线则是按照所谓“时间—媒介”分类,分为过去时的记录类叙述、过去现在时的记录演示类叙述、现在时的演示类叙述等等[12]。于是,人类社会的所有叙述行为都可以在这一分类方案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为进一步探讨叙述行为的规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广义叙述学》一书在讨论具体的叙述问题——如叙述者、叙述时间、情节以及叙述分层等时,似乎与传统的小说叙述学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广义叙述学还没有找到真正超越传统叙述学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赵毅衡试图总结人类社会全部表意活动之规律的努力,还只是刚刚开始。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赵毅衡最关心的问题是意义究竟如何得到表达的,因此他始终在探究各种各样的叙述背后的故事。只不过在20世纪80、90年代,他主要研究文学叙述,而到了新世纪,他开始关注人类生活的全部表意活动。在长达三十余年的研究工作中,赵毅衡的文艺思想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他从不随意选择研究对象,每一项研究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形式主义文论,是为了扭转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弊病;在新世纪研究广义叙述学,则是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界急需一种涵盖各类叙述的学科。这就使得赵毅衡的学术研究总是能解决一些真正的问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次,赵毅衡以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知名,但他的研究却具有鲜明的中国主体性,他总是用中国本土的经验与例证,指出西方理论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推演出新的理论表述。因此阅读赵毅衡的著作,我们总能在里面觉察到作者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自信,这在长期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的中国学界中非常少见。最后,虽然赵毅衡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但他的研究却有着一条贯穿性的主线,那就是以对文学形式的关注为核心,并进而生发出对人类整体表意活动的探究与思考。他的研究在学界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无疑与他能够对某一学术问题进行长期思考有着密切联系。直到今天,赵毅衡仍然在思考着人类表意活动的基本规律,并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和《广义叙述学》中做出了初步探索,为国际符号学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