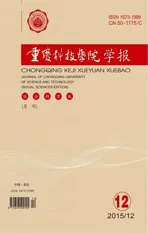论本·琼生《森林集》中的古典主义
2015-02-20吴美群
吴美群
论本·琼生《森林集》中的古典主义
吴美群
本·琼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典型的古典主义诗人。但他的《森林集》却既体现了本?琼生对古典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又表达了诗人对这一传统的超越甚至颠覆,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本·琼生并不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古典主义卫道士。他是一个古典主义思想家,但更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主张从古典主义和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双重视角来关注人性、考察人性。
本·琼生;《森林集》;古典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
一、本·琼生与古典主义
本·琼生是莎士比亚同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和评论家。王佐良与何其莘认为“在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比莎士比亚晚八年出生的本·琼生就比他更有名望”[1]155。本特利(G.E.Bentley)也认为,“在德莱顿之前,英国主要诗人和文学天才是本·琼生而非莎士比亚”[2]201。莎士比亚于1616年在家乡小镇默默去世,而本·琼生1637年去世后,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社会各界名流参加了他的葬礼,并纷纷致辞缅怀。其中包括了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达千余人的部落——本的儿子们 (Sons of Ben)。莎士比亚的名望超过本·琼生是在17世纪晚期,在此之后,本·琼生的成就和名望就更与莎士比亚紧紧捆绑在一起。
将本·琼生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研究是评论界的一种潮流,随着莎士比亚名望的日渐上升,本·琼生却逐渐屈居于他的光环之下。这是造成国内评论界对本·琼生知之甚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本·琼生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戏剧、诗歌、文学理论,还是戏剧的经典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戏剧合集出版的英国文学家,他的第一个对开本《1616年对开本》(1616 Folio)比莎士比亚首个对开本 《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1623)早七年发表,为英国戏剧从舞台走向页面的经典化过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本·琼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文学家,哈罗德·布鲁姆曾称其为“诗人中的诗人”[3]43。
本·琼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被公认为古典主义的典范。自17世纪德莱顿(John Dryden)至今,评论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对其古典主义思想的研究之作。德莱顿在《论戏剧诗》(Essays On Dramatic Poetry,1668)中认为:“琼生深通古典,不论希腊或者罗马,而且自由地借用他们……而且他是公然抢夺,不怕被人绳之以法。他侵略作家犹如帝王,在别的诗人该算剽窃的在他只是出征胜利。”
德莱顿开启了本·琼生研究领域的古典主义传统,本·琼生也因此被称为“英国新古典主义之父”[4]2。此后,众多评论者纷纷探讨过他的古典主义思想,如巴里斯(Jonas A.Barish)、赖茨(L.C.Knights)、邓肯(Douglas Duncan)等。最近一位对本·琼生古典主义思想进行详细解读的代表人物是维多利亚·莫尔(Victoria Moul),她的专著《琼生,贺拉斯和古典主义传统》(Jonson,Horac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2010)从新的视野重新详细研究了琼生的古典主义思想,特别是本·琼生对贺拉斯抒情诗歌的借鉴,莫尔认为“贺拉斯式的抒情诗广泛影响了本·琼生的书信、假面剧、戏剧以及翻译等”[5]13。尽管20世纪以来评论界涌现出大量对本·琼生作品 (特别是戏剧)的狂欢性、对话性的探讨,但这丝毫不能动摇本·琼生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先驱的地位。
相对于戏剧而言,本·琼生的诗歌更能凸显他的古典主义思想。如果说在戏剧上本·琼生和莎士比亚分别代表着城市讽刺戏剧和宫廷浪漫喜剧这两个传统,那么在诗歌上本·琼生则和约翰·邓恩(John Donne)分别代表着17世纪初两个主要的诗歌流派:古典主义和玄学派。而这两派又同时代表着17世纪英国诗歌与16世纪伊丽莎白时期诗歌的截然不同。被伊丽莎白诗人奉为圭臬的十四行诗逐渐消失不见了,16世纪诗人竞相模仿的意大利诗风(主要是彼特拉克)也逐渐减弱。以邓恩为代表的玄学派更加注重诗歌的哲理性和思辨性;而以本·琼生为代表的古典诗人则转而学习古希腊罗马诗歌。本·琼生在英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他的古典主义诗歌开启了英国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序幕,德莱顿、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等均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然而,本·琼生并不是被动模仿古典主义。“古典主义对于本·琼生和培根而言,都是一种发掘的习惯,是在不断的调查实验和积累古代知识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审视认识论”[6]144。本·琼生的座右铭“Tanquam explorator”和其散文集的标题 《发现》(Explorata:or,Discoveries,1640)便直接来自于塞纳加《致鲁基里乌斯的道德信函》(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中的诗句:“我要跨越敌人的营地——不是作为一个逃兵而是作为一个侦察兵。”[7]8-9“发现”或者说 “发掘”是本·琼生古典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本·琼生虽然深受古典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却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意识,将古典传统与17世纪初期英国现实题材相结合,同时他也深深扎根在英国本土诗歌传统之中,他的诗歌是古典传统、英国本土传统和17世纪社会现实的完美结合。因此,在分析本·琼生作品时,哪怕是最具古典意识的诗歌,也应该考虑英国本土诗歌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等非古典因素。
《森林集》收集了15首不同类别的诗歌,加德纳(Gardiner)将这15首诗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由颂诗组成,包括第一首 “我为何不写爱情”(“Why I not Write of Love”),第五首 “致西莉亚”(“Song to Celia”),第六首“再致西莉亚”(“To the Same”),第九首“致西莉亚”(“Song to Celia”),以及第七首“女人只是男人的影子”(“Song:That Women are but Men’s Shadows”)和第八首“致疾病”(“Song to Sickness”)。第二类是类似于讽刺诗的一些书信诗和两首宗教诗“致世界”(“To the World”)和 “致天堂”(“To Heaven”)。本论文重点探讨《森林集》中的第一类颂诗,偶尔也会涉及宗教诗“致世界”。这些诗歌被评论界认为是本·琼生为数不多的抒情诗的代表,它们往往被排斥在本·琼生古典主义诗歌的范畴之外。诚然,本·琼生颂诗由于其强烈的情感,比较自由的韵律而相对缺乏讽刺诗的严肃性和道德性,也因此有违背古典主义原则的嫌疑。事实上,这些颂诗既明显地表达了本·琼生对古典主义诗歌传统的传承,也表达了他对英国本土诗歌传统的内化,更体现了本·琼生诗歌将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对话性和多样性。
二、对古典诗歌韵律的吸收与创新
《森林集》第五首“致西莉亚”(“Song to Celia”)表达了本·琼生对古典诗人卡图卢斯 (Catullus,84-54BC)爱情诗歌的借鉴。该短诗最先出现在本·琼生盛期喜剧《福尔蓬涅》(Volpone,1604)中,剧中老态龙钟的行骗者福尔蓬涅以遗产为诱饵,让商人博纳瑞尔(Bonario)将妻子西莉亚送至自己的病房中(装病),随后福尔蓬涅厚颜无耻地向西莉亚献上了该诗。抛开剧情不说,这首短诗是本·琼生除了第九首同名诗之外最典型的爱情颂诗。诗歌的首八行如下:
来吧!我的西莉亚,让你我证明,
我们尚能拥抱爱情;
时光虽会离我们而去,
可它终归会留下些美好;
万不可浪费了这馈赠,
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升起;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便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 (Forrest 5,lines 1—8)
而卡图卢斯《诗集》第五首的开篇如下:
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
那些古板的指责一文不值,
对那些闲话我们一笑置之。
太阳一次次沉默又复升起,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Catullus5,lines1—7)
可见,本·琼生在创作该诗歌时深受卡图卢斯诗歌的影响,他甚至直接借用其中的诗句。与莎士比亚不同,本·琼生青年时期有幸在威斯敏斯特文法学校接受了一段时间正规的古典主义教育,师从著名的古典主义者和历史学家威廉·卡姆顿 (William Camden)。在此期间,本·琼生积累了大量的古典知识和良好的阅读习惯。古典诗人贺拉斯、维吉尔、卡图卢斯等人的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学校的必读书目。因此,本·琼生对这些古典诗人的作品非常熟悉,在创作时,自然也是信手拈来,而他对古典诗歌的借鉴最明显地体现在诗歌韵律上。但他不是被动模仿,而是将古典诗歌韵律加以改造创新。
本·琼生非常注重诗歌的韵律整齐,在大部分诗歌中使用古典双韵诗(couplet)的形式,他在与苏格兰诗人威廉·德莱姆顿(William Drummond)交谈时曾经表示 “憎恨除双韵诗以外的一切诗歌韵律”[8]235。他虽作诗歌颂邓恩的诗才,却也批评他对诗歌韵律的忽略,认为“多恩该绞死,因其诗不协韵(for not keeping of accent)”[1]232。众所周知,英国诗歌在莎士比亚时代主要采用无韵诗(blank verse)的形式,莎士比亚、马洛、斯宾塞等均是无韵诗的典型代表。马洛是第一个将无韵诗完全发挥的英国文人,莎士比亚的诗体戏剧也大都使用无韵诗创作,而之后的17世纪诗歌巨人弥尔顿在创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时也是采取无韵诗的形式。
然而,本·琼生却为17世纪英国诗风带来了新的因素,他主要向讲究韵律整齐的古典诗歌学习,结合英国本土诗人前辈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双韵形式,提倡诗歌完美整齐的韵律,这种韵律整齐的双韵诗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主要形式。琼生的讽刺诗大多采取五音步抑扬格的双韵形式 (decasyllabic couplet with iambic pentameter)写成。如他在讽刺诗“To King James”中写道:
But two things rare the Fates had in their store/ And gave thee both,to show they could no more.(Ben Jonson,Epigrams 4,“To King James”,Lines 3—4).
同样整齐的双韵形式也能在德莱顿和蒲柏的诗歌中找到,如德莱顿在1660年写到:“And welcome now,great monarch,to your own,/Behold th’approaching cliffs of Albion”。半个多世纪之后,蒲柏也使用同样的形式创作,如“To thee,the world its present homage pays,/The harvest early,but mature the praise”。可见,由本·琼生首先使用的闭合式双韵诗(closed couplet)被王朝复辟时期的德莱顿和18世纪的蒲柏大力发展,成为英国王朝复辟时期和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主要诗歌形式。
本·琼生的抒情诗相对于讽刺诗来说,韵律自由多变得多,但《森林集》第五首 “致西莉亚”依旧是按照双韵诗的形式创作。然而,不同于他早期讽刺诗的五音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该诗虽然采取双韵的形式,却使用了四音步抑扬格 (iambic tetrameter)。而且是严格按照闭合对偶句(closed couplet)的形式,每两行押韵,组成一个完整的句法单位,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诗节。比如第一二行:“Come,my Celia,let us prove,/While we may,the sports of love.”是一个按照四音步抑扬格创作的意义完整的句法单位。句末押韵词“证明”(prove)和“爱情”(love)重点突出该诗的爱情主题。诗歌总共十八行由九个类似的独立句法单位构成,两两押韵,典雅整齐,是古典爱情诗的典范。 然而,本·琼生也不是自始至终采取闭合双韵诗形式,很多时候他的双韵诗相对于蒲柏等人严格的闭合双韵诗来说显得开放自由很多。有时甚至也采取自己憎恨的无韵体创作,这显然离不开伊丽莎白时代无韵诗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森林集》第九首与第五首同名,均为 “Song to Celia”,如上所述,第五首是按照双韵诗的形式创作,并且直接借用古典诗人卡图卢斯的诗句。然而,第九首情况有变。首先,该诗由两个诗节组成,每节八行,而不像第五首用双韵来划分诗歌句法单位。第九首在韵律上相对自由,并不是严格按照四音步抑扬格(iambic tetrameter)创作,而是每四行一个大循环,每两行一个四音步与三音步交叉小循环,如第一节
Drinke to/me,one/ly,with/thine eyes,(a)
And I/will pledge/with thine;(b)
Or leave/a kiss/but in/the cup,(c)
And Ile/not looke/for wine.(b)
The thirst,/that from/the soul/doth rise,(a)
Doth aske/a drinke/divine:(b)
But might/I of/Jove’s Nec/tar sup,(c)
I would/not change/for thine,(b)(Forrest 9,lines 1—8)
如上所述,该诗节第一三五行是四音步抑扬格(iambic tetrameter),而第二四六行则是三音步抑扬格(iambic trimeter),韵脚为abcbabcb。也就是说这一节诗的韵律节奏为a4b3c4b3a4b3c4b3,与该诗的爱情意象“花环”(“wreath”)相对应,凸显了爱情的曲折缠绵,反映了诗人的独具匠心和用心良苦。而该诗第二节也是按照同样的节奏和韵律,整齐典雅,读来朗朗上口,成为英语抒情诗歌的典范,被后人谱写成曲,至今仍为人传唱。这首诗歌的韵律不同于古典诗歌的闭合双韵体,也不同于当时依然占据英国诗歌主流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甚至不同于本·琼生自己早期创作的讽刺诗体,这是本·琼生不断学习、试验、发现、创新的结果。可见,单从韵律上看,便能发现本·琼生在《森林集》里并不是自始至终严格遵循古典双韵体形式,两首同名颂诗“Song to Celia”(第五首和第九首)便体现了诗人在韵律上的灵活多变。值得提出的是,哪怕在双韵诗中,本·琼生也习惯使用有规律的长短句交叉的形式,如他在诗体戏剧《福尔蓬涅》的前言中便采用了五音步和四音步交叉排列的双韵形式,如:
Now,luck/yet send/us,and/a lit/tle wit,(a)
Will serve/to make/our play/hit;(a)
Accor/ding to/the pa/lates of/the season,(b)
Here is/rhyme,not/empty/of reason;(b)
This we/were bid/to cre/dit from/our poet,(c)
Whose true/scope,if/you would/know it;(c)
In all/his poems/still hath/been this/measure,(d)
To mix/profit/with your/pleasure.(d)
显然,该诗节的第一三五七行是按照五音步抑扬格创作,而第二四六八行则按照四音步抑扬格创作,长短交叉、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同时本·琼生在《森林集》的第十一首 “Epode”中也采取了整齐的长短句交替的形式,可见本·琼生对长短句交替形式的喜爱。也说明他并非是古典诗歌形式的被动模仿者,而是在其基础上发掘与创新,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形式,既不同于16世纪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不同于以马洛为先驱被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大力发展的无韵诗,也不同于18世纪新古典主义派对诗歌形式刻意追求的闭合双韵诗。
三、对古典诗歌简洁文体的借鉴与超越
从诗歌文体来看,《森林集》也表达了本·琼生对古典主义诗歌的改造和创新。众所周知,古典诗歌用词严谨、表意清晰、文体简洁(plain style)。本·琼生特别推崇西塞罗和昆体良的修辞艺术,主张采取简洁的文体,他曾在散文集《发现》(Discoveries)中表示“宁肯选择简洁直白的智慧,而不要愚蠢做作的雄辩”[9]244。而他的早期讽刺诗歌也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简洁文体,不同于莎士比亚诗歌的隐晦性、含混性、多义性,琼生的诗歌往往被认为是简洁、直接、平实的。加德纳(Gardiner)认为琼生的诗歌属于简洁传统 (the plain tradition),“他的诗歌有着很强的逻辑性,清晰、直接、有力、雅致”[10]8。而且琼生并不主张使用过多意象,哪怕采用意象,也多为直接的表达,鲜有多种解读可能。本·琼生的《森林集》基本采取简洁文体,意象较少,鲜用形容词,诗歌的重点往往依靠动词来表达。如上文所示第九首第一节八行诗中仅第六行中有一个形容词“神圣的”(“divine”),而意象“花环”(“wreath”)则明显直接地表达爱情。然而,再仔细查看不难发现,这首诗歌并不是那么言辞清晰,同样存在着含混与多义。
如上所述,该诗节是按照长短句交叉排列,短句表意往往清晰直接,而长句便相对复杂含混。如第一句“Drinke to me,onely,with thine eyes”,句中的副词“only”用得巧妙,它既可以修饰前半句,也可以修饰后半句;也就是说既可以表示“只和我对饮”,也可以表示“只用你的双眸”。因此,这句诗的涵义便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了,诗中男主人示爱的方式是犹豫踌躇的,因此提供了两种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都会令男主人欣然快乐,虽然第一种可能性可能更符合他的心意。而随后的短句则非常肯定清晰地表示了男主人的回应,“And I will pledge with thine”,也就是说不管对方是只和他对饮,还是仅用双眸与他对饮,他都会回报以自己的热情。
同样,第三四句诗也有这类似的效果。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构成排比,第三句同第一句类似,男主人公提出一种并不确定的期望,哪怕只是在杯边留下一个吻,这种看似与男主人公可能完全无关的举动,他也会视之为爱情的征兆,他“不会向杯里找酒”(第四句),而是从灵魂深处渴求爱情之美酒的降临。而第五六句则通过押头韵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效果,第五句“The thirst,that from the soul doth rise”连续使用三个“th”音开头,读来让人有种不太清晰确定的感觉;而接下来第六行的三音步短句却使用三个爆破音“d”,“Doth aske a drinke divine”,发音清晰可辨,表意明确,向对方索取爱情的美酒。该句的形容词“divine”则将爱情上升到了神圣的地位。由此可见,本·琼生的《森林集》并不是严格按照古典主义简洁文体,而是通过长短句交叉排列,先用长句表达相对含混隐约的意义,随后用铿锵有力的短句予以解释和说明,因此实现了对古典诗歌简洁文体的突破与创新。
其次,从诗歌叙述者来看,《森林集》也反映了本·琼生对古典简洁传统的超越。巴赫金在论述自己的对话性理论时,曾将诗歌排除在对话性之外。他认为诗歌是独一性的文体,发出的是诗人独一的声音。而小说则可能是对话的文体,可以有多种声音,以至构成复调小说。然而越来越多的评论者认为诗歌中也存在对话的可能性,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便认为本·琼生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对话性质,认为“本·琼生严肃修正主义诗学中的‘向心力’时刻受到一股潜在的不受控制的‘离心力’的超越”[11]7。对话性并不是本论文探讨的重点,仅用以说明本·琼生诗歌(特别是《森林集》)中古典主义的复杂性。评论界往往认为本·琼生在诗歌创作中自始至终保持一种静止不变的态度,是一个维护古典主义传统的卫道士、宫廷权威的拥护者,这用来形容其讽刺诗或许是合适的,早期讽刺诗往往是诗人自己作为叙述者说话,诗人是作为叙述者存在于诗歌之中,因此表意清晰明了、精简直接。但如此形容《森林集》便显得过分牵强和绝对。
《森林集》中的颂诗有一个共同点便是采用戏剧性人物作为叙述者(dramatic speaker),而不是直接道出诗人自己的声音。这些颂诗中只有第一首“Why I write not of love”中的 “I”是可能指代诗人自己,而在其他颂诗中均采用了戏剧性叙述者的形式。如第五首 “Song to Celia”中的叙述人是引诱者Volpone,第六首标题为“To the Same”,顾名思义这首诗与第五首一样是献给西莉亚,因此叙述人也与第五首相同。而第九首“Song to Celia”的叙述者则是一个满怀激情却略带踌躇的求爱者。至于第七首 “Song that the Women are but men’s shadows”中的叙述者却是一个嘻哈顽皮,追逐女人的男子。而第八首“Song to Sickness”的叙述者却从第七首的追逐者变成了一个责骂者。戏剧性叙述者的采用将诗人的声音(观点)隔离出来,诗歌也就不再纯粹是诗人观点的直接表达,而是或者委婉、或者曲折、或者反讽。因此,这些颂诗不再像早期的讽刺诗能够清晰地表达作者对待人生、道德和政治的态度;也规避了诗人毕生追求的道德观念对诗歌的制约,与古典诗歌中简洁直白(plain style)的文体相背离。
四、对古典斯多葛思想的传承与颠覆
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森林集》也体现了本·琼生对古典主义思想既推崇又违背的矛盾态度。琼生古典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西塞罗、塞纳加、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等斯多葛思想家对人类道德完美的坚持。斯多葛派推崇严谨的道德观,提倡按照自然准则生活,并甘愿接受美德的控制和指导。教育人们对任何外部事物都应保持漠不关心,并称这种漠不关心为“斯多葛的淡漠”(Stoic Apathea)。完美的斯多葛主义者被称为斯多葛圣人,是一个既能获取心灵和道德的完美知识又能完全控制自己情感的道德完善者。他既不受人生逆境的影响,如疾病、贫穷、批评、毁谤、死亡等;也不受人生顺境的左右,如健康、财富、名誉、长寿等。斯多葛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回归心灵以达到道德的完美,拒绝外部世界对灵魂的影响。
本·琼生一方面提倡斯多葛道德观念,强调回归心灵,另一方面又时时表现出对斯多葛道德局限性的讽刺和批评,他的戏剧中不乏有斯多葛代表人物,如 《沉默的女人》(Epicene,or The Silent Women,1609)中的主人公莫罗斯(Morose)和《巴斯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ir,1614)中的奥夫多(Overdo)均是斯多葛代表人物,然而本·琼生对两者都进行了讽刺和批评。他在其诗歌中也表达出同样的矛盾态度。首先,《森林集》第四首“致世界”(“To the World”)表达了诗人明显的斯多葛倾向,特别是对心灵回归的强调。诗歌最后两节如下:
不,我并不知道我生来,
要遭受衰老,不幸,疾病,痛苦;
但我将会蔑视着忍受这一切,
而不需要你虚伪的解脱。
我不会向远处寻求平静,
就像流浪者依旧在四处流荡;
而是在最初的地方创造力量,
在我的心里,我的家园。(Forrest 4,lines 61—68)
不难发现,这两节诗非常清晰明了地表达了诗人强调回归心灵的斯多葛思想。第一节(一二三四行)提出人生无常,人总会遭受生老病死与悲伤不幸。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因素,人们应该努力摆脱它们对心灵的影响,因此诗人对它们持有鄙夷的态度,同时希望能够忍受它们的困扰。而第二节(五六七八行)则表示不会向外界去寻求平静,而是转向人的心灵,只有人的心灵可以提供力量,心灵便是诗人的家园,也是一切力量的来源。毫无疑问《致世界》表达了本·琼生对斯多葛思想的肯定与推崇。然而矛盾的是他在《森林集》中的另一首诗中则表达了对斯多葛思想的背离,而提倡被斯多葛派批评的另一种哲学思想——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 (Epicurean Hedonism),那就是第五首“致西莉亚”。
第五首“致西莉亚”的第三四五六行诗中男主人公提出时光匆匆,终会离去,而我们万不可浪费了时光的馈赠。第七八行提出当“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因此他接着说“我们为何要延迟这快乐,名誉和流言只不过是玩偶”(九十行)。这里道出了该诗的中心主题——及时行乐(carpe diem)。人生苦短、时光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享受一切快乐,包括肉体上的享乐,而及时行乐正是斯多葛派极力反对批评的人生态度,却被伊壁鸠鲁派奉为圭臬,伊壁鸠鲁派是与斯多葛派相抗衡的古希腊著名哲学流派,该派思想家主张快乐原则,认为快乐是善良的基础,人们应该懂得及时行乐。诗歌的末四行如此说,“窃取爱的果实并非罪恶/甜蜜的窃贼想要表达/宁愿被抓,宁愿被发现/在这所谓的罪恶里”。
本·琼生所推崇的斯多葛完美道德观在这些遭到瓦解与颠覆,“窃取爱的果实并非罪恶”让人想起人类的原罪——亚当夏娃窃取爱之果实。然而诗歌此处表达的是这并非罪恶,这显然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公然挑衅。而且斯多葛派推崇一种隐忍规避的生活态度,认为追求道德完美最好的方式是回归自己的内心,离开世俗烦恼的困扰,然而诗歌此处则宣布甜蜜的窃贼想要表达、想要将自己的所谓罪恶公之于众。显然,斯多葛的隐忍在这里也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由此可见,本·琼生在推崇古典斯多葛思想的同时,也时刻坚持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时代精神与诗人的独立意识,讽刺批评了斯多葛派过激的避世态度和其对人类世俗快乐的完全抵制。这充分反映了本·琼生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既提倡人的道德完善,也肯定人对世俗快乐的追求。关于古典斯多葛思想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矛盾融合,在本·琼生的城市喜剧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琼生虽然极力推崇古典诗歌传统,韵律上主张用古典双韵体,而反对以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为主的意大利诗风;文体上主张西塞罗和昆体良的简洁传统;思想上主张塞纳加、利普修斯等斯多葛派对道德完美的坚持和对人类心灵的关注。但他在《森林集》中却时刻体现出对自己所主张的古典诗歌传统的超越甚至颠覆。特别是其中的颂诗,韵律相对自由,诗人即使采用双韵体,也相对开放而非严格按照闭合式双韵形式,善于用长短句交叉形式,以达到韵律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本·琼生在诗歌中虽然不常使用形容词,却往往通过头韵和谐音的手法,结合长短句交叉形式,既实现诗歌语言的张力,又达到精简直接的效果。诗人虽然一面强调回归心灵,拒绝外界因素的干扰,以实现道德的完善,另一面又时刻清楚斯多葛派的道德局限性,从基督教道德观的角度来肯定人的世俗权力,特别是关于爱情和快乐的权力。
由此可见,本·琼生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但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传统卫道士,他在广泛吸收古典传统的同时,也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为17世纪英国诗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诗歌成就深刻影响了王朝复辟时期以及18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英国诗歌,甚至在现代诗人如艾略特那里激起共鸣。
[1]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55.
[2]Hirsh,James.New Perspectives on Ben Jonson [M].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97:201.
[3]Pricthard,Willian H.“Ben Jonson:Poet”.The Hudson Review[J],2012.
[4]Coronato,Rocco,Jonson Versus Bakhtin:Carnival and the Grotesque[M].Amsterdam:Rodopi,2003:2.
[5]Moul,Victoria.Jonson Horac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3.
[6]Trimp,Wesley.Ben Jonson’s Poems:A Study of The Plain Style[M].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44.
[7]Seneca,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M].Richard M.Gummere,London and New York,1917:8-9.
[8]Schelling,Felix E.Ben Jonson and the Classical School[J]. PMLA,1989.
[9]Bevington,David.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Ben Jons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244.
[10]Gardiner,Judith Kegan.Craftmanship in Context:The Development of Ben Jonson’s Poetry[M].Mouton and Co.N.Y.,Publishers,1975:8.
[11]Womack,Peter.Ben Jonson[M].Oxford:Blackwell,1986:7.
(编辑:张齐)
I106.4
A
1673-1999(2015)12-0112-06
吴美群(1981-),女,博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
2015-09-25
2013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本·琼生喜剧中的反讽诗学研究”(13C509);2013年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课题“本·琼生与英国道德剧传统研究”(CX2013B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