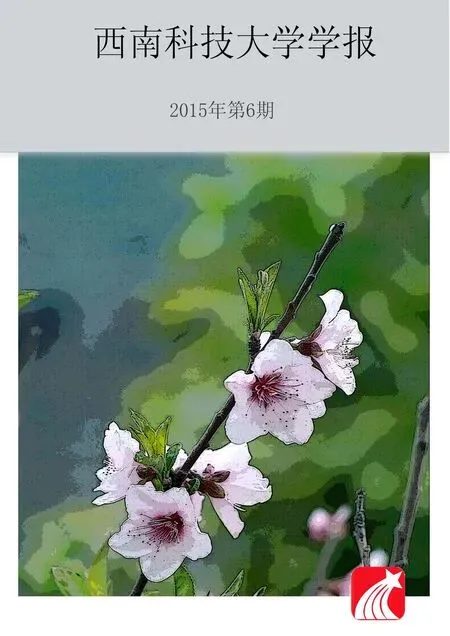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阈下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中的城市文明演进
2015-02-20付玉群
付玉群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生态批评视阈下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中的城市文明演进
付玉群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在自然生态的强烈比照之下,从浪漫主义的“自然”写作;勃朗特姐妹的“荒原”文学、简·奥斯丁的乡村桃源;狄更斯、萨克雷等小说家笔下的罪恶之都或名利场;哈代小说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生活,再到王尔德童话故事里的灵性自然与亟待革新的“城市”,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这些经典逐一呈现了工业革命助长下,城市文明在与充满自然生态的乡村生活的博弈中,经历了被抗拒、批判、质疑,再到被接受中求革新的全过程。这些作品呈现了城市文明与环境生态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体现了要求二者和谐共生的终极诉求。
【关键词】生态批评;城市文明;文学经典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早、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已初见端倪。与此同时,英国进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维多利亚统治的强盛时期。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演进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给英国本土社会更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及城市生活)发生巨变。“进入19世纪后不久,伦敦就成为西方世界第一座居民超过一百万的现代城市。”[1]36另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行为反应”,独特的社会背景对19世纪的英国文学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文学异彩纷呈,集多维度、多元化和统一性于一体,大气磅礴地涵盖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等,除大量男性作家和诗人涌现之外,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女性作家和诗人。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童话,都不乏经典佳作。
概括国内外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可得出如下特点:第一,国内外学者对于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分类的前提,即浪漫主义文学和维多利亚文学,从而忽视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整体性和同一性,禁锢于对两个分类文学泾渭分明的研究。第二,从各作家作品的专项研究的综合考查可以发现,19世纪英国文学存在许多共同的创作思想与主题。例如,“自然”、“女性”等关键词频频出现在19世纪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的经典作品中。第三,19世纪英国文学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交织中,体现出城乡生活变迁的不可逆转性与无所适从感。
本文旨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阐释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经典,探查其间存在的生态伦理以及城市文明的变迁与发展,揭示早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经典中便折射出来的生态伦理与城市文明进程的紧密关系,从而探求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在新世纪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批评转向文学中的城市文明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气候的变迁、科学乐观主义和科学悲观主义并存,以及末世情结影响之下,生态批评这一理论视角在国内外备受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产生以来,在短短20、30年间备受推崇,并不断得到发展、延伸,且在新世纪表现出新的转向。
1978年,鲁克尔(William Rueckert)在其《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首次将文学与生态学相结合。虽然,今天的生态批评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对其定义却各有异同。生态批评采取跨学科的视野,从文学领域延伸至生态领域,试图探索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文学与环境的关系。而这一概念的延伸始于上世纪末期,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指出:“生态批评简单地说就是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2]xviii。由此,生态批评从单纯的发掘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生态,发展为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解读对象更是从单纯的自然写作或自然文学文本延伸至整个文学领域,甚至包括诸如莎士比亚之类的经典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批评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得到发展。生态一词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延伸至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环境一词也囊括了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等。
进入21世纪后,生态批评本身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陈爱敏教授研究,生态批评已发生3大转向。首先,“生态批评变得更加宽泛、包容”,“人们更趋向于用‘环境批评’取代‘生态批评’”,而“环境批评”的研究远不局限于对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其次,“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多于对自然环境的关注”,这尤其表现于女性生态主义,对女性生存环境的关注尤为热烈;“生态批评将视域从荒野、农村转向了城市和大工业化”[3]65-72。基于前两次转向,第三次转向则更为广阔,关注焦点从被投注在人类自身,转向城市环境、工业发展,并同时反观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生态关系。由此可见,城市环境成为当代生态批评理应把握的重点。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去探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和城市文明有其必要性,同时在文学作品中反观人类对于生命的渴望;对自然世界的依恋;梳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变更,从而探索城市文明与环境生态的辩证关系,正是当下生态批评的核心内涵。
而“城市历史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学科”[4]7,但城市文明可追溯至罗马时代,“屋大维最先启动了城市化运动……在他的推动下,罗马城从一座砖坯造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大理石的城市,成为帝国尊严的象征。”[1]3由此可见,城市的发展最初就与宗教、政治息息相关。而后城市由最初的崇拜功能到之后的防守建筑,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逐步与乡村隔离,形成独有的存在形式。而这一新兴形态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剩余价值的产生,社会分工的加剧,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一系列城市文明设施与制度便得以建立。城市文明的内涵广泛,不仅包括其中的建筑、法制、社会,也包括其中的人。“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人群体现城市文明的类型”[4]10。因此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文明,不得不了解其间的人群。同时,文学作品要再现城市风貌,也必定会再现城市中的人群。故而,在文学中的城市文明研究中,人物角色、人群特征和作家诉求都不容忽视。
文学中的城市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圣经文学,也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创世纪》中,该隐和亚伯这对兄弟最初都是依靠大地为生,放牧羊群。后来,该隐杀弟,遭到上帝的诅咒:“即使你种地,地也不再为你生产。从此,你将流离失所,余生都将在居无定所中飘荡。”①之后,该隐离开耶和华到了伊甸之东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生子以诺,并建造了以其子之名命名的“以诺”城。由此,圣经文学中便有了该隐是城市缔造第一人之说。从这个故事也可以品出,人类从自然世界走向城市生活的不得已和必然选择,同时也可反观人类偏离自然世界之后彷徨无措、终身寻寻觅觅的生存常态。《理想国》中更是详述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城邦的构成,涵盖全面,包括其体制、人群(管理者、守卫者和劳动者)、正义美德等等。
随着工业革命对城市、乡村生活的重大改变和影响,19世纪的英国经典文学更再现了城市文明的系列演进。无论是被浪漫主义诗人疏离的“城市”,还是狄更斯、萨克雷笔下的伦敦、巴黎,以及哈代小说中威塞克斯之外的城市,甚至王尔德的童话故事里,都无不能管窥文学中城市文明的逐步演进、再现和接受。
二、城市与大自然的博弈
“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4]15从城市的起源,也可看出自然与城市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过程:最初,人类依靠土地为生,居住于丛林之间,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命和财富;为了感恩神灵的庇佑和大自然赐予的丰收,用于祭祀的寺庙产生;随着财富的增加剩余物品的产生,物物交换应运而生,于是寺庙周围出现换物的集市;随着市集的兴旺,统治者逐渐搬离丛林,住进寺庙和集市间的“皇宫”。自此,城市与自然开始了全新的彼此联系而又独立的模式。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经典中,自然意象与城市意象更是如影随形,相互比照,在对立统一中共生。从浪漫主义的“自然”写作到勃朗特姐妹的“荒原”文学;简·奥斯丁的乡村刻画到狄更斯、萨克雷等小说家笔下的罪恶之都或名利场;托马斯·胡德等诗人诗歌中烟囱林立、黑烟缭绕的工厂与对自然的无限向往,到哈代小说中乡村的闲适、城市的诱惑,再到王尔德童话故事里的灵性花草动物与缩影人世的“城市”,都无不折射出城市与自然意象的交织,处处充满着二元对立的博弈。
(一)牢狱——乐土
在浪漫主义诗人笔下,乡村、自然是灵魂的乐土,人性的归属,城市却如牢狱般禁锢人的心灵。艾米莉·勃朗特在其诗歌中便多处使用“牢狱”来暗指城市世界。艾米莉自身更是鲜少离开家乡,终身与荒野为伴,对城市文明极度排斥。1840年5月8日,其妹安·勃朗特离开豪渥斯这个弹丸乡村进城做家庭教师,而恰巧在5月4日安临行之际,诗人“为妹妹被迫离开家乡赋诗一首”[5]115:“我不会因你离去而哭泣,/这儿原没有什么可爱;/但黑暗的世界倍加令我哀戚,/当你的心在那儿悲哀/”[6]234。现实生活中3姐妹为生计奔波,以及艾米莉蜗居家中守护老父的生活状态,让诗人说出“这儿没有什么可爱”之言,但同时却把城市比作“黑暗的世界”,“你”会“在那儿悲哀”而“倍加令我哀戚”。这里,诗人对乡村自然生活的习以为常和对城市的恐怖与抗拒,足可管窥一二。
城市是黑暗的世界,是牢狱,而自然却成为向往的乐土。艾米莉在诗歌中曾高声吟诵:“在我可爱的高沼地,/风光荣自豪地醒来!/啊,请从高地和峡谷里,/唤我去山间小溪徘徊!/”[6]141。不谋而合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群诗人因不满都市生活的束缚和繁杂,一度定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与山水为伴,试图抛离工业对生活的改变而自给自足。这批诗人对工业革命冲突下的城市文明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极度反感,其诗歌多讴歌闲适的乡村生活、纯朴勤劳的乡民与迤逦的自然风光。自然写作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共性,其中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被誉为“自然的诗人”。自然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充满着人性,更是诗人重温回不去的“美好时光”的乐土。
(二)冒险之城——世外桃源
现实主义作家对乡村与城市的再现却大为不同,不再有“牢狱”与“乐土”的天壤之别,却也分明在城市与自然的意象中鲜明地对照出冒险之城与生活家园之别。简·奥斯丁无论是在《傲慢与偏见》还是在《理智与情感》里,对于乡村生活和习俗都进行了刻意的描画:闲适、富足、自由,而且一切均可掌控。即便是女性在这样的土地上都能获得尊严、爱情或者幸福,远离工业喧嚣的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跃然纸上。而其作品中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画也独具匠心,充分凸显了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那神秘莫测而未可知的城市。那里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冒险,甚至背叛。投身城市就如赌徒下注,是全新的契机还是走向深渊,都未可知,从而给人以冒险的体验。在《傲慢与偏见》中,当宾利一家还未出现时,小镇的人是闲适而安宁的,而这一切皆被城里贵族的到来所打乱。在彭勃斯庄园,伊丽莎白找寻到了富有和真爱,而莉迪亚却受骗于外来者威克汉姆,走向生活的深渊。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走出孤儿院的平凡女子,在似乎远离尘嚣的桑菲尔德庄园经过曲折离奇的冒险之后,才成功获得了尊严和爱情。
(三)罪恶之都——欢乐家园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较为全面地对城市文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再现与批判,包括其中的用工制度、法律制度,甚至救济院,尤其是城市中的人群。在狄更斯笔下,伦敦就是一个罪恶之都——人群的畸形、法律的不公、社会的冷漠、制度的不合理,所有这些造就了这个罪恶之都。然而与此相对的是,作品中的自然成为了“劫后余生”的欢乐家园,自然可“净化心灵,消除邪恶”。托马斯·胡德的诗歌,多批判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生产方式,反映下层民众的悲苦。在其诗歌《我记得,我记得》中,作者一开篇便对比儿时的美好时光与此刻现实的迥异。诗歌第二节清新自然地陈述着:“我记得,我记得/玫瑰红色和白色,/紫罗兰和百合花杯——/全都是光织成的花朵!/知更鸟筑巢的那颗紫丁香下,我哥哥在他的生日里/洒下了金莲花/那棵树还活着!/”②这里的大自然无限美好,承载了美好的过去时光与童年的所有乐趣。毋庸赘述,这与诗人在《衬衫之歌》里所呈现的贫病肮脏、血泪四溢的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率先从英国开始至19世纪早、中期,城市飞速发展着,“所有的这些变化只发生在短暂的几十年之中……而且也不产生新的稳定。反之,却推动着更快、更深刻的变化。”[7]782“这种不加控制的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物质后果,使下层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7]783而且,“19世纪前半叶,工业革命的缺陷显得如此严重和深刻”[7]783,让人难以忽视。在《雾都孤儿》中,救济院充满着压迫和虐待,城市充满着黑帮和诈骗;黑暗与肮脏充斥着伦敦的大街小巷。所谓的城市文明在这里是野蛮而粗鄙的,充斥着腐败和罪恶勾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变得唯利是图、阴险卑劣。奥利弗在这样的城市中遭遇了种种欺凌和不幸。有趣的是,小说结尾奥利弗和他的新家搬到了一个小村庄,从此快乐地生活着。作品中,似乎“幸福结局”永远不可能在城市中存在。而在乡村,奥利弗却就此摆脱了所有“邪恶”,得到了安定。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小说情节的安排似乎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诉求甚有关联。狄更斯是典型的依赖着城市人群与文明而发迹的作家,靠着写作从伦敦的小巷进入豪宅,在享尽都市的繁华之后,晚年却决然移居郊外重享乡村与自然的安逸。这一切皆恰恰反映了在那个年代中,如狄更斯这样的“文化人在精神上是由乡土塑形的”,虽然得益于城市,因城市而发迹,但始终感知“他被自己的创造物即城市所掌握和拥有,而且变成了城市的动物,成了它的执行器官,最终成为它的牺牲品”[8]99,从而失去了自我。于是,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罪恶的城市、欢乐的乡村,也在现实生活中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四)世俗新世界——精神家园
而如哈代一般的自然主义作家,对城市罪恶的批判却显得更为乐观。在他的笔下,虽然城市成为堕落的熔炉,但却充满着新兴资产阶级所希冀的机遇、繁华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城市从一无是处的罪恶之都,还原成世俗新世界;自然、乡村生活成为精神和灵魂的寄托与归属。哈代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从最初对都市诱惑的向往,到铅华尽去后对乡村与自然的回归。但此时的乡村世界并未被美化,它充满着世俗的林林总总;乡村世界也从世外桃源和欢乐家园,升华成了远离生活层面的精神家园——与外界隔离、与现实相争的精神寄托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应而又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3]45哈代的《还乡》发生的场景是爱敦荒原。爱敦荒原的居民固守着旧有的习俗,与世隔绝。男主人公克林·姚伯年轻有为,怀揣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梦想从巴黎还乡,试图在故乡的穷乡僻壤开创自己的事业,却遭遇重重阻碍。他生于荒原——走向城市——复归荒原。女主人公游苔莎却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荒原奔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城市,她生于城市——流落荒原——意欲逃离荒原,最终淹死在荒原。而克林的资产阶级梦想虽未曾实现,却求得了精神的回归。在自然主义文学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体现出某种世俗中的真实。不同的是,城市是汇聚多元生活、充满异质性的新世界;乡村让人重新拥有自始至终简单生活方式的精神愉悦。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与环境都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发展逻辑。
(五)丑恶俗世——灵性圣地
不同于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开始在花草的灵性中感知世界的真实,而同时又承认都市世界的存在真实,只是其间充满着不公和丑恶,充满着渴求改变。在《夜莺与玫瑰》中,夜莺用一夜的歌唱和生命染红了玫瑰,只试图让男孩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爱情。这样的灵性与牺牲是都市人无法企及的,更是工业社会的功利主义所鄙薄的。在王尔德作品中,大自然就是人类的发源圣地或者灵性所在,无法企及,却又无法隔离。在其作品中,城市文明包括城市规划与建筑艺术都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在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中,已然出现代表城市符号的雕塑。“在城市上空,高高的柱子上,矗立着快乐王子这尊雕塑。”③[9]11
此时,都市童话在城市文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城市意象在童话故事里得到再现。《快乐王子》中,生前住在王宫里欢乐无忧的王子,死后被塑成雕像,高高矗立在城市之中,“目睹了城市中所有的丑陋和痛苦,尽管我的心是铅做的,也不免哭泣”④[9]15。在这城市中,“富人们在漂亮的房子里寻欢作乐,乞丐们却坐在大门口忍饥受冻”,“饥饿的孩子们面色苍白,无望地望着昏暗的街道”;流浪的孩子饥寒交迫,即便在桥下“相互偎依着取暖”也被守卫驱赶到雨夜里徘徊⑤[9]22-23。这些描述,不仅反映了城市生活中贫富悬殊的严峻和下层人生活的苦难,也表达了对工业化城市寸土寸金,穷人区昏暗、狭窄、拥挤的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谴责。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描述曼彻斯特市中心时便这样写到:“街后面的情况更糟,并无足够的通道通向这些街后的小巷和院子,人们只能穿过非常密集的建筑间十分狭窄、往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通道而到达这些小巷和院子。”[7]801这样的街道怎能不“昏暗”?这也和王子生前在宽敞明亮的花园里与伙伴玩耍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上、下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和矛盾。
“快乐王子”这个革新家希望改变城市的丑恶与痛苦,他期待一位助手。作者没有创造别的角色来担当这一神圣的助手,却选择滞留一只南飞的小燕子作为这位城市领袖救苦救难的助手,这其中似乎别有深意。而故事的结尾也寓意深刻:王子爱上了燕子,高兴地以为燕子要南飞了,而燕子却亲吻过王子的嘴唇后死在了他脚下,于是王子那颗铅做的心也脆裂了。在政客和大学艺术系教授的怂恿下,王子被推倒了,那代表城市革新的铅心被丢弃在燕子的尸体旁。燕子和铅心被上帝视为世间最可贵的两样东西,便让天使把他们带到天堂,在天堂里鸟儿可以终日歌唱,王子谦卑的铅心可以置身于上帝的黄金之城。
这里不难看出,王子和燕子的隐喻——王子代表城市及城市的革新力量,燕子代表了自然界的万物,二者的合作犹如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的携手,但其奋斗却举步维艰,在城市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难以得到认同。与此同时,过度使用大自然,违背自然规律,最终的结局也是城市与自然的双重毁灭。作品的最后,作者借上帝之手,幻想了最可贵的这二者和谐共生,同时也寓意在城市发展中,城市革新与自然生态的重要性。从这个视觉看来,这个故事不仅传达着城市发展、社会变革的主题,更是对人类城市文明和生态伦理和谐发展的一则寓言,让人警醒。
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文学再现了文学世界中城市的发展历程:从最初遭受排斥的牢狱,到让人希冀的冒险之城,再到遭受严厉批判的罪恶之都,继而成为认知的世俗世界,于是再度凸显其丑恶,希翼城市的革新,渴望城市、自然的正态分布与可持续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也可见,城市文明愈发达,人的自然本性也就会愈凸显,对自然的渴望也就愈加强烈,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和谐共生是人类恒久以来的渴望。而19世纪文学经典中的生态伦理与城市文明预言式地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向往都有迹可循,且这一过程循环往复。然而,在一定时期里,征服自然的城市文明或能得到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随着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使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中,人类在承认城市文明的同时,也会更加向往自然、大地并渴求回归,从而达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诉求。总之,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再现了城市文明与生态伦理这一对矛盾统一体,并为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且日益凸现的母题,强力再现了人们的终极诉求——城市文明与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共生。
注释
①笔者译。Holy Bible中其英文原文为:If you try to farm the land, it won’t produce anything for you. From now on, you’ll be without a home, and you’ll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wandering from place to place.
②笔者译。原文为:I remember, I remember/ The roses, red and white,/ The violets, and the lily-cups-/ Those flowers made of light!/ The lilacs where the robin built,/ And where my brother set/ The laburnum on his birthday, -/ The tree is living yet!/
③笔者译。这是Oscar Wilde的The Happy Prince开篇第一句话:High above the city, on a tall column, stood the statue of the Happy Prince.
④笔者译。原文为:…I can see all the ugliness and all the misery of my city, and though my heart is made of lead yet I cannot chose but weep.
⑤笔者译。原文为:So the Swallow flew over the great city, and saw the rich making merry in their beautiful houses, while the beggars were sitting at the gates...and saw the white faces of starving children looking out listlessly at the black streets. Under the archway of a bridge two little boys were lying in one another’s arms to try and keep themselves warm…“You must not lie here,” shouted the Watchman, and they wandered out into the rain.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上帝之城[M].黄晓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Glotfelty, Cheryll,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3]陈爱敏.生态批评中的美国华裔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2010(1):65-72.
[4]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Chitham, Edward. A Brontё Family Chronology[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6]艾米莉·勃朗特.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8卷艾米莉·勃朗特诗全集[M].宋兆霖,主编.刘新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M].薛钟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M]. New York: Knopf, 1928.
[9]Wilde, Oscar.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 New York: Knopf, 1995.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in the 19th-century British
Classic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FU Yu-q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From the nature writings of romanticism, the “wilderness” works of the Brontё sisters, the country novels of Jane Austen, the city of sin or vanity fair in Dickens’s and Thackeray’s, the sharp contras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life in Hardy’s works, to the spiritual nature and the city demanding innovation in Oscar Wilde’s tales, the 19th-century British classic literature, conta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y, reveals that with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urban civilization, competing against the rural life full of ecological balance, experiences the whole process of being resisted, criticized, doubted, and then received partially with ideas of innovation. Henc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civilization and ecology are clearly displayed and the ultimate quest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coexistence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y is vividly expressed.
Key words:Ecocriticism; Urban civilization; Classic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6-0030-06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中生态伦理与城市文明究”(SCWY12-21);西南科技大学2015年度出国进修项目。
作者简介:付玉群(1977—),女,汉族,四川简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