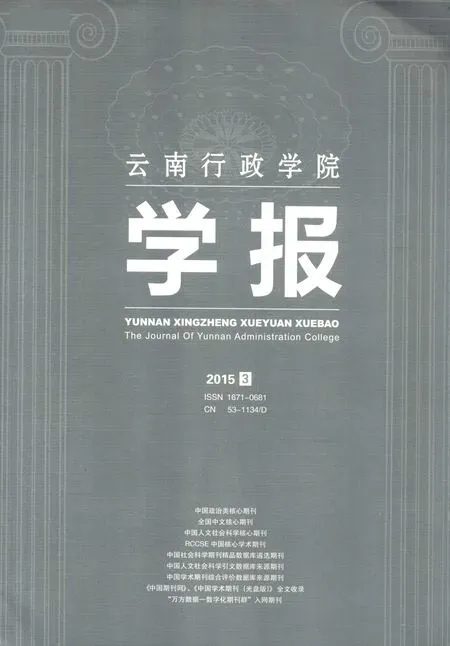“协同治理”的产生与范式竞争综述*
2015-02-14李妮
李妮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珠海,519000)
“协同治理”的产生与范式竞争综述*
李妮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珠海,519000)
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作为一个理论框架近年开始流行,但还没有达成在概念定义上的高度共识,同时一些竞争性理论框架及类似的术语混淆与模糊了研究者的视线。本文就协同治理及其竞争性范式进行比较,梳理了协同治理这一新兴范式的理论脉系,指出其内在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协同治理的中国研究现状提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方向,以促进对这一范式的理解与深入研究。
协同治理;范式;网络
本文首先呈现了协同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然后厘清类似术语以获得一个初步的概念边界,继而对一组竞争性范式进行了详细阐述。结合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梳理了研究现状,并提出协同治理研究的局限性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判断该领域的发展是否足够,而是致力于对这一理论框架在其学术脉络当中位置的更为清晰的界定,对其概念术语、内在要素及研究取向上的更为充分的剖析与呈现,以期促进这个领域内相关研究之间的理解、沟通与对话。
一、协同治理:产生背景
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反思新公共管理的各种前沿理论相继推出:网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协同治理等都是这个网络化、跨边界、伙伴关系风行时代的产物。
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从恐怖主义、国际贸易到气候变化、疾病传染,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损失惨重的复杂问题。“要解决这些深刻的涉及环境污染、失败的公共教育及增强弱势群体的社区等社会问题,需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社区领袖和其他许多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有效的合作与资源分配机制”。面对“邪恶(wicked)”问题(复杂的问题),更大范围跨机构、跨辖区的联合行动不可或缺。俞可平认为,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如何创造出适应全球化新现实的有效治理模式,决定着全球化的前途与命运。约瑟夫·S.奈等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需要一套提高协调性、创造疏导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安全阀的治理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包括政府、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共同参与。这也是有效应对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家,跨区域问题的必然选择。
而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机构裂化,公共服务碎片化的问题,加速了以协作为特点的协同治理的讨论。McGuire认为社会变革是新公共管理的决定因素之一。通过私有化来规制经济活动以促进公共服务及管理的效率和效益,私营机构及半自治机构带来了非层级与分权化的网络、团队等组织设计,更灵活更创新的管理和领导工具,结果导向的和自我领导的训练。这种变革以权力分散化为特点,要求更多的自主权与个性化。然而,Rhodes认为NPM实际上是脆弱的,它的缺陷在于核心过程中“竞争”与“掌舵”之间的分歧。NPM关注层级控制,强调权威与责任分配;NPM热衷于目标和结果导向的管理。这些特点与跨组织网络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对结果负责的实质相悖。“NPM可能适合官僚制的管理却不适合跨组织网络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跨组织网络将破坏NPM组织内目标与结果导向的管理”。随着NPM改革进程的深入,国家越来越依赖非直接行政的方式进行治理,更多的公私、第三部门组织的协调,由包括公民在内的多元主体而非单一的政府机构制定公共政策。
与此同时,国家行政系统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Kettle在讨论美国行政边界一文中谈到,为了更好地回应公民的需求,一些州政府,如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开展了“now rong door”运动。即,无论公民走进哪间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都不会被告知找错部门或程序申请错误,而是以实现政府服务功能的整合来满足公民需求。“now rong door”运动试图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实现无缝化的连接,这无疑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要求,同样需要依靠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回应公民需求。
以上挑战使得对公共行政体系责任与能力的要求日益复杂,公共行政学者纷纷从“跨机构、跨区域、跨部门、多层次”的“合作、参与”取向建构、重构政府治理理论与治理结构。就地方行政实践改革的经验而言,合并地方政府和扩大其规模(建立超级部门)、过多地寄希望于组织结构的变革,并不是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最佳办法。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一种基于协作的治理机制与理论框架,正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二、协同治理:范式比较
与协同治理类似的一组概念,存在多个术语,意涵重叠,难以区分。如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联合(coalition),协作(collaboration),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s),协作性公共管理(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同盟(alliances),伙伴关系(partnership)等等。这些概念界限模糊,缺乏明确一致且取得共识的操作性定义,以致成为公共行政学者随机使用的的“战略”选项或“结构”选项。“协同治理”类似术语之间的互换使用以及缺少跨学科的对话,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我们知道,“理论化可以包括这样几个层级:简单的分类、构建类型学、概念化、形成概念框架、模型化”。显然概念上的混乱无助于理论化进程,有必要进行梳理与界定。
关于“协作”,在西方语境中通常会提到“法团主义”的利益团体及其关系,法团主义(corporatism)表现为国家青睐涉及三方(工会、雇主团体、政府),并以三方作为“社会伙伴”进行谈判和管理的一种经济合作。施密特认为,这些“法团”即利益团体通常来说是垄断的,代表特别团体的利益。而协同治理,则往往意味着包含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并且这些利益相关者并不具备对特定部门的代表性垄断。如果说社团主义是较狭义的界定,那么协同治理就是更为广泛的术语。而协会(联合)治理(associational governance)与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区别在于前者通用于协会理事的模式,而协同治理,甚至可能不包括正式的协会。
协同治理通常依靠网络化组织来实现,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与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各自的重点在于:“政策网络”是用来描述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更多元化的形式,政策网络是一种在网络中进行的行动者之间的讨论或决策的合作模式。然而,协同治理是指将各种利益相关者纳入多边和达成共识的决策过程的一种明确和正式的战略。与此相反,政策网络中内在的合作,可能是非正式且隐密的。
时下流行的公私伙伴关系(PPP)与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有时二者指涉相同的现象。不过PPP通常要求具有协作的功能,但其目标往往是达成协调,而不是达成决策共识本身,达成决策共识则正是协同治理的关键。以上概念的辨析是我们理解“协同治理”理论范式的基础,下面对几组竞争性范式进行比较分析。
(一)网络化治理与协同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
公共行政学本身就是在范式的分裂与竞争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在“治理”成为流行词汇的九十年代,同样也活跃着一些竞争性理论范式。网络治理最先缘起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有关公司治理的跨组织网络研究。琼·皮埃尔和盖伊·彼得斯把它看作是与科层体制、市场及社群并存的一种治理结构或过程(政策网络),斯蒂芬·戈登史密斯和威廉·D·伊格斯则把网络治理看作是与一种特定的政府类型关联在一起的。许多有关网络治理的实证研究基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的分析框架。
戈德史密斯根据“公私合作程度”和“网络管理能力”两个维度,划分了四种政府管理状态。“层级制政府”属于传统的官僚制政府形态,“鸽笼化”管理色彩比较浓厚,靠层级制权威进行协调,因而效果不佳;“第三方政府”意味着公私合作程度高,但政府对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低下。“协同政府”的网络管理能力强,因而能实现有效的跨界合作,但这种合作仅限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网络化治理”既包含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又意味着政府对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强。戈氏认为,“网络化治理”是跨界合作的最高境界,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如何实施有效的政府管理:必须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线;根据新兴的各种网络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绘制出脱离传统政府及其运行理论的新模式,构筑起一个帮助政府增强绩效及其责任性的基础。
网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网络是社会协调的普遍形式,管理组织间联系的重要性与私营部门管理同样重要。网络途径认为,行动者之间相互依赖,如果没有其他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他们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网络是一个结构,合作的过程在这个作为非正式的社会系统的协调设置中进行。Fountain强调了新制度主义与网络视角对研究者的重要性,因为网络视角提供了丰富的描述性能力和精确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组织过程的研究方法。在组织间层级,网络分析展示了组织的战略性操作,寻找、形成以及脱离联盟。Fountain认为有效的公共管理者如果没有理解内外部网络结构的可持续性和灵活性,就不能进行有效地管理。
实际上,网络管理提供了找到协作性管理模式的机会。考虑和包含(网络)互动过程中的外部效应是非常重要的,如开放、细心、可靠性和合法性。而这些标准与协同治理过程要求的透明度和责任制的主要原则是一致的。可以说,网络化治理既是协同治理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又是协同治理的研究内容。协作可以成为网络的一个特征,也可以存在于网络之外。同样,也可以延伸到网络之间的协作关系。不过,由于这两个术语经常交替使用,容易产生不正确的印象,即认为所有的网络都存在协作且所有的协作都在网络中发生。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collabrative public management)与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协作性公共管理是由美国学者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在对城市地方政府的实证研究中提出来的,是公共管理者在组织网络时代应对跨界(不仅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政府与准政府之间的关系)相互依赖挑战的管理活动和新战略。各个城市实现战略目标的协作机制是丰富的,协作性管理的程度和目的因城市而异,协作活动的独特机制、层次和目的,体现出协作活动的多种类型和模式。在对多种协作活动模式的研究中,协作性公共管理正是试图“形成的一个关于公共管理的新的理性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意味着基于互惠的价值,协同工作,跨越多部门关系边界,达到共同目标。
协同治理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于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公共政策和分权化进程的加剧,改变了21世纪治理的面孔。Bingham指出,参与治理是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行动。治理意味着引导、控制影响决策的过程及在私人、公共和公民部门内的行动[17]。协同治理就是这么一种治理安排,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直接与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一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个过程是正式的,以共识为导向,审慎的,并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是管理公共项目或公共资产。从概念来看,协作性公共管理是问题导向的管理模型,而协同治理则是以形成共识为目的治理安排。二者区别详述如下:
首先,内涵不同。许多学者认为,协同治理是一个较协作性公共管理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术语。其一,协作性公共管理关注点在地方;其二,注重组织层次及组织间相互依赖的研究。相对于关注地方层级的协作性公共管理,协同治理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国家边界。就产生原因而言,二者也不尽相同。许多学者认为协同治理是全球化进程与技术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带来的责任问题引发了公司治理的讨论。而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于人类福利与个人特质的兴起。从发展进程看,可以区分先后。Halachmi指出,协作性公共管理到协同治理是从“动词的治理”(governing)到“名词的治理”(governance)的转换过程。所以,协同治理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下一步(nextstep)。而协作性公共管理用于解释政府组织间的协调,协作存在于跨越司法辖区和部门边界的组织之间,存在于私人组织与邻里协会之间。因此,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被认为是强调外部关系与组织环境的新公共管理的下一步。
总之,协作性公共管理和协同治理,从工具理性角度来讲,享有共同的过程价值,比如透明性、问责性和信任,协作性公共管理是协同治理在操作层面上的延伸。协作性公共管理更加关注地方层次上的议题,而协同治理更加关注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上的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更多关注组织层面上的组织相互依赖性,强调运作层面上的过程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协同治理更强调公民参与和多中心治理主体;协作性公共管理中公共组织是跨组织协作网络的中心,而协同治理中的政府组织已经越来越失去其优势地位,仅是网络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之一,与其他参与者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小。“治理”(governance)本质上是一个描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理论,具有社会治理的意涵。概念的宽泛使得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容可以容纳于协同治理之中,并可作为检验其治理过程的一部分。
伴随全球化、数字革命和国际经济市场的发展,协同治理——作为一个宽泛的术语,为我们带来了政府治理的全新视角。当然,由于路径依赖,每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不尽相同,而协同治理作为一个“类”的概念,比协作性公共管理更具普遍意义,更适于广泛使用。网络管理、政府间合作及跨组织间协作都是整个协同治理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选择“协同治理”进行探讨,更为倾向使用“治理”而非“管理”。
三、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协同治理的研究还处于低程度的共识阶段,研究与实践都比较分散。因此,下文关于“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将视“协同治理”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纳入相关议题的研究。其中“协作性公共管理”部分,大多数研究还处于西方理论的初步的引介阶段。秦长江,刘亚平等学者就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国外研究的大致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认为这些新的理论趋势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与批判,不过分析的脉络有所不同。或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或从组织发展的角度,还有的从理论来源角度进行阐述。此外,有少量国外协作经验的介绍,如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美国的区域协作性公共管理机制——州际协议等,主要以美国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
作为协同治理方式的“网络治理”研究颇多。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其一是公司治理,这些研究运用网络治理的框架探讨网络治理的优劣及其与组织效率和效益的关系。聚焦于企业组织网络的主体特征、网络关系的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而政府往往作为其中的一个治理主体在对策建议中被提到。二是较为宏观的社会学维度的讨论,侧重于以网络为组织结构对其要素和功能进行分析。文献多集中于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权力关系、网络行为者与网络治理;知识产权网络关系治理研究;网络治理的模式、结构、因素与有效性等传统的社会学结构、功能描述。不过,这些对网络要素的讨论为协同治理的组织基础提供了研究素材与认知途径。其三是新兴的传播学角度的讨论,关注即时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与网络治理,即如何管理互联网。这里的网络治理与我们的研究关系不大,也说明“网络治理”一词的用法极为模糊和宽泛。综上,“网络治理”其研究偏重于私人部门,缺少以公共部门为主体的探讨。社会学路径的探讨又尤为宏大,缺少具体的网络治理机制或操作模式的探讨。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少量研究通过具体的案例,从政府职能、公共服务主体、政府协同及公民参与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现状及其局限,勾勒出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并提出针对性对策。主要涉及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合作研究;城市治理中的基层治理、社区治理问题;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区域治理及公共危机治理等研究内容,不过,这些研究注重对策探讨,缺乏理论分析框架,仅是取协作与多主体参与的观点充实对策建议。可以说,相关文献对协作议题的讨论,缺少理论对话,即使同一学科领域的探讨,也没有形成较具共识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总体而言,中国语境下的协同治理研究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而西方国家协同治理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与具体,并发展到操作性层面,强调通过实证研究提出解释变量并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Ansell等学者对西方协作治理文献作了一个整体回顾,通过137个协同治理的案例分析,确定了一组影响协作治理模式是否产生成功协作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历史冲突与合作、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激励机制、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领导力、制度设计。同时,还确定了一系列合作过程本身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面对面的对话、建立信任、承诺的发展和共同理解。研究者发现,当协作论坛专注于“小赢”时,深度信任、承诺、共享理解将有助于发展一个良性的协作循环。同时发现,整体而言协同治理针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案例研究比例很高,反映出协作战略对有争议的地方资源的纠纷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西方国家对协同治理的研究同样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如这一领域的研究仅仅评估“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或管理的结果”;对具体的变量的提炼与验证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研究,如影响绩效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同治理的程度。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方法的片断化(piece—mealapproach),与其他路径相隔离,缺少整合与学科对话;其二,没有取得高度共识的变量及测量:如没有单一的或一组有效、可靠、可识别的措施去分析和比较不同的合作,评价如何培养和保持有效的合作等。许多文献聚焦于具体的领域,没有上升到类型化的高度。其三,研究滞后于全球化语境,没有很好地回答如何应对跨国界,跨区域网络出现后的公共管理问题。中国语境下协同治理研究,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土实践,思考该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发展出对中国情境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四、协同治理:挑战与未来
协同治理的讨论已然兴起,理论与实践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尤其需要关注协同治理实际存在的几组内在矛盾:行动者的自主性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之间的矛盾;任务网络中的成员个体与组织目标的冲突;共享责任下的问责问题;协调与效率的关系……不过,“尽管协同治理中,传统代议制民主的责任性在降低,但是强大的公民参与,使得治理过程更为有效,并提升了治理的有效性”。如何调和矛盾,处理好这些竞争性关系,是协同治理的优势得以实现的基础。
对公共管理者而言,面对协同治理的环境,需要构建新的管理能力。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管理者是天然的网络代理人,需要培养与层级、市场制度中不同的管理技能,如连接,协商,谈判,激发与促进等。关键行为者承担着作为个体与组织的边界联系人角色,因此,拥有特殊资源与有影响力的人或组织(关键行为者——公共组织/公共管理者)对组织的影响重大。如何运用资源,发挥有效的影响,公共管理者的能力构建是关键所在。
协同治理还需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在西方语境下,协同治理就缺乏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中国,由于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条件与治理目标,协同治理在经验世界的实现有其独特性,也存在更大的障碍。西方国家的网络治理建立在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我国政党制度完全不同;网络治理强调建立在利益协调上的自组织体系,我国社会自组织远远不够;西方的网络治理是以信任为基础、以获取共同利益为动力,而我国城市的网络治理动力机制则比较复杂,既有政府的推动,也有相关群体的自发行动;这些分殊,使得我们在认识协同治理的同时,更应注重协同治理产生的环境和条件。
要补充的是,对协同治理的强调与讨论,并没有否认官僚制的存在。官僚体制不但存在,而且仍然是管理的主要形态,协作仅仅只是单一组织管理的补充而不是超越。特别是在没有深厚自治传统的中国,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协同,在我们的领域引发了许多的共鸣,无论是协作性公共管理关注公共机构与管理者的实质内容还是协同治理关注的共享决策,包括过程和内容中的民主与公共角色,最终都需要到真实的公共行政世界中实践,以实现“善治”的目的。虽然过程并不简单,但从其他国家获得经验,有助于规避一些可能的冲突并发展出更符合中国实践的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中国六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数据显示,139个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中,与国家和社会的协同治理相关的项目高达92项,占全部入围项目的66%以上。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在地方政府创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实践的兴起需要理论的指引。如果协同治理的安排对于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是有价值的,那么理解与制度持久性相关的要素和理论框架对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就是必要的,对协同治理的讨论,目的在于推进这一领域持续的反思与创新,进一步的质疑和促进理论化的进程。当然,“西方学界的既有概念框架,不能简单替代学者对社会属性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定义。因此,将中国社会置于全球背景下,持续对社会事实作出甄别,同时与国际学术界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对既有概念理论不断反思,这些应该成为立足本土社会研究的学者的重要工作”。对于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协同治理”,同样如此。
[1]Ansell,C.&Gash,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oryand-Practi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J].2007,18(4),543-571.
[2]Henton,D.,J.Melville,T.Amsler and M.Kopell.2005.Collaborative Governance:A Guide for Grantmakers.Menlo Park,CA: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美]约瑟夫·S·奈,[美]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McGuire,M.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A ssessingWhat We KnowandHow We Know I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2006,Special issue,33-42.
[5]Eliassen,K.A.andN.I.Sitter.Understanding Public Management[M].London:Sage.2008.
[6]Rhodes,R.A.E.Thenewgovernance:Governingwithout Government.Political Studies[J].1996,XLIV,625-667.
[7]Kettl,D.F.Managing Boundariesin American Administration:The Collaboration Imperativ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2006,(12).
[8]Huxham,C.Theorizing collaboration practice.Public Management Review[J].2003,5(3),401-423.
[9]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10]张康之,程倩.网络治理理论及其实践[J].新视野,2010,(6):36-39.
[11](美)戈德史密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Klijn,E.H.andJ.F.M.Koppenjan.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Network:Foundations of a network approach to governance.Public Management[J].2000,2,2,135-158.
[13]Fountain,J.E.Comment:DiscipliningPublicManagement Research.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Management[J]. 1994,13,2,269-277
[14]Kapucu,N.,Yuldashev,F.,&Bakiev,E.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Conceptu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J].2009,2(1),39-60.
[15]Bingham,L.B..Legal frameworks for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In Bingham,L.B.and R.O’Leary(eds)Big Ideas in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M].NewYork:MESharpe,2008:247-269
[16]Agranoff Robert&Michael McGuire.Collaborative Public-Management:New S trateg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M]. 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3.
[17]Halachmi,A.Gover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challenges andpublicproductivity.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 Sector Management[J].2005,18,4,300-317.
[18]Bovaird,T.andE.Loffler(eds).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M].London:Routledge.2003.
[19]庞云黠.“哈佛学派”与互联网空间的未来.国际新闻界[J]. 2012,(02).
[20]Bowornwathana,B.Minnowbrook IV in 2028:From American Minnowbrook to global Minnowbrook.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2010,70(Suppl.1),64-68
[21]Klijn,E.H.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Networks in Europe:AnAssessmentofTenYearsofResearchonthe Theme.Public Management Review[J].2008,10,4,505—525
[22]Brass,D.J.,Galaskiewicz,J.,Greve,H.R.,&Tsai,W.Taking Stock of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2011,47(6),795-817.
[23]Berry,F.S.,Brower,R.S.,Choi,S.O.,Goa,W.X.,Jang,H.,Kwon,M.,&Word,J.Three Traditions of Network Research:What the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genda Can Learn from Other Research Communitie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2004,64(5),539-552.
[24]陈映芳.“转型”、“发展”与“现代化”:现实判断与理论反思南京社会科学[J].2012,(7).
(责任编辑马光选)
D63-3
A
1671-0681(2015)03-0018-06
李妮(1978-),女,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5-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