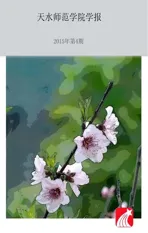银河永存天地间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审美表达探析
2015-02-13张学敏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马 超,张学敏(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银河永存天地间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审美表达探析
马超,张学敏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书写陷落生之困境的女主人公旅途中触摸民间生存真相,穿越夜晚的黑暗与疼痛,灵魂自我救赎之后完成了凤凰式的涅槃。在艺术上表现出独特的美质:套叠镶嵌的同故事叙述之美、对举呈现的人物设置之美、诗意缤纷的意象之美,这一切构成了小说特有的叙述机制和艺术格调,使文本呈现出沉静婉丽的审美特质。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审美表达;同故事叙述;人物设置;意象之美
进入21世纪以来,迟子建的妙笔生花不断给文坛以惊喜,其中篇代表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标志着她对生命与人生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新深度。女作家蒋子丹说:“翻开小说,一种与温馨的北极村童话里决然不同的,粗粝、黯淡、艰苦、残酷,完全可以称得上绝望的生活,扑面而来。”[1]36-37该文表达了迟子建对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关注和参与现实的人文主义情怀,突显出新世纪蜕变后的迟子建铅华洗尽,带着生活的伤痛与磨砺、无奈和感怀,以她特有的悲悯情怀去触摸生活的创痛,揭示出生存的本相;同时,小说中诸如“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2]的诗意抒写,又表征着她仍一以贯之地以抒情的笔调营造柔美凄清的意境。那由北向南,一泻千里的迢迢银河,使文本弥漫着一种感伤的温情,升腾起湿润的缕缕诗意,引起无尽的遐思和动人的故事,让读者确信“银河永存天地间”,在银河清辉的笼罩之下,人间的幸福终会停泊在彼岸,这一构想将小说的意义升华到了人文关怀的高度之上,与此同时,构成了这部小说特有的叙述机制和艺术格调,使文本呈现出沉静婉丽的审美特质。
一、套叠镶嵌的同故事叙述之美
套叠镶嵌的同故事叙述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显示出迟子建作为一个小说家对叙述方式的出色把握力。
从故事的层面来讲,《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主干讲述了一个具有丧夫之痛的“我”出外旅行的伤怀故事。“我”的“魔术师”丈夫车祸意外死亡之后,“我”为排遣丧夫之痛,独自去三山湖旅行,旅程中火车意外抛锚,“我”于是在一个名叫“乌塘”的小镇停留,去收集民歌和鬼故事。以煤矿起家的小镇乌塘很多男人都死在了频发的矿难中,所以这里盛产寡妇。在乌塘,“我”目睹了诸多小人物的生活情状和悲剧真相后,来到三山湖,在卖火山石的小孩云领的导引下,我们在夜晚的清流放河灯,送走了曾经的悲伤和哀痛。小说在这一主干故事之下延伸出了许多枝干故事,这其中主要有乌塘开旅店卖豆腐的周二夫妇的故事、寡妇蒋百嫂的故事,开画店唱丧歌的陈绍纯的故事,开婚介所给人唱喜歌的肖开媚的故事,三山湖卖火山石的云领父子的故事……如果按照故事的功能来区分,“我”的故事贯穿始终,发生在小说展示的所有情境中,显然属于一级故事。“我”的故事中“我”的丧夫哀痛就像一条珍珠项链的丝线,串联起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其他故事。当然,“我”的故事处在核心,其他的故事作为一粒粒大小不等的珍珠,组成了漂亮精巧的故事链,不但丰富了“我”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镶嵌在“我”的故事中,组成了套叠关系。显然,“我”的故事引导着故事情节不断延伸,让小说中的人物不断丰满起来,引发读者的思考。而枝干故事属于二级故事,而且每个二级故事结束后又回到一级故事营造的叙述情境中,但它们的存在,使整个叙述结构丰厚起来,使故事具有了深度。毫无疑问,这种叙述技巧的效果就是善于呈现纷繁复杂的人生世相,社会百态。
故事中“我”在乌塘小镇开始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与被大众日常经验操持的事物对话。“我”的故事理所当然地是通过“我”的“讲述”展现,其他故事随着“我”的眼睛“显示”出来,在经典叙事学中这其实是运用了“同故事叙述”。所谓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是“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层面的叙述。”“当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时,如在《永别了武器》中,同故事叙述可以进一步确定为自身故事的叙述。”[3]171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之一,和蒋百嫂、陈绍纯、云领等处在同一个故事中,因此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对“我”自身的故事进行叙述,这属于典型的同故事叙述。文本中叙述者作为主人公参与到故事的情节中来,与故事中的人物有对话和感情的沟通并形成交集,读者通过叙述者的讲述,不但明白了“我”的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且在讲述的过程中,又镶嵌进对别人故事的叙述。这就注定了作者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的叙述视角,读者在“我”的带领下,沿着线性叙述顺序,跟着“我”走完了“我”的爱情追忆之旅,也领略尽我所看到的各个小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命运人生。当然第一人称限制性的叙述视角不可能全景式地凸现故事的方方面面。
不过,叙述者“我”作为小说中的一号主人公的身份和地位,对于读者来说,本身就是一大看点。“我”参与了其他人物的故事,并且在这些故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比如,在“我”与蒋百嫂的故事中,我的行为和感受是蒋百嫂性格和命运得到呈现的条件,同时,蒋百嫂的命运也是“我”性格和态度得到呈现的条件。同理,在“我”与陈绍纯的故事中,“我”的关注和欣赏是陈绍纯个性和价值得到呈现的条件,同时,陈绍纯的命定和结局也是我情感和行动得到呈现的条件。当然,在“我”与云领父子的故事中,“我”的同情与参与是云领性格和命运得到呈现的条件,同时,云领的导引和执著也是“我”感情找到凭借超脱得到呈现的条件。由此可见,故事中的双方互相依存,交相辉映。而作为现实主义的写作,不像现代主义小说,在故事讲述的方式上,根据作家的意图达到的文体效果安排全景式、共时性的故事结构,而是基本遵循线性的、历时性故事结构,故事的连接完全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承接为基本依据。
二、对举呈现出人物设置之美
如果只从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等层面来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每个人物似乎迥然不同,甚至毫无共同点可言,但细读小说,令人惊叹的是小说中的人物,有很多共性的内涵,非常明显的是人物设置遵循对举的原则。“对举”语出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对举字》,和对偶相近是相对举出的意思。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4]8显然这里的对举是诗文辞章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现代汉语中,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似成分放在一起使用叫对举,是一种语法手段。我们认为在小说的描写艺术中,将相互对应或相反的物象罗列在一起,以求产生特殊的衬托效果就是“对举”。循此思路,我们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但主要人物对举安排,次要人物也是两两相对,而且相对的两者又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关系。“我”是贯穿小说的人物,与其中的另一位主人公蒋百嫂对举,与“我”丈夫魔术师相对举的是在三山湖帮父亲做小买卖的云岭,民间歌者陈绍纯的对举者是唱喜歌的肖开媚,与周二夫妇对举的是那个只在周二夫妇口中讲述出现的瘸腿人与他的薄情寡义的妻子。
1.“我”与蒋百嫂
一个是城市里搞研究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小镇乌塘的底层妇女。如果不是“我”的人生出现意外,如果不是火车滞留,我们的人生永远不会出现交集。恰恰是由于许多的如果变成惨痛的真实,我们便有了命定的相似与相知,有了共同的命运与身份:寡妇。寡妇身份的形成都可以归因于人祸。
小说里“我”那魔术师丈夫,深夜演出完毕归家的途中,被一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肇事所撞,死于人祸。蒋百一年前死于一次矿难,是天灾,但更是人祸!因为矿领导为了自保,私下用“巨额赔款”封住了蒋百嫂的嘴,让蒋百死了连土都入不了,变成了沉默的冰山。有悖常理的是原本勤劳、本分的蒋百嫂,丈夫失踪后,竟然酗酒耍泼,浪荡轻浮,可实质却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了内心最痛切的反抗。”[5]258-259在突然停电的夜晚她跺脚哭喊:“我要电!我要电!这世道还有没有公平啊,让我一个女人呆在黑暗中!我要电,我要电啊!这世上的夜晚怎么这么黑啊!!”[2]她如此愤激地呼喊,使“我也明白了乌塘那被提拔的领导为什么会惧怕蒋百嫂,一定是因为蒋百以这种特殊的失踪方式换取了他们升官晋爵的阶梯,蒋百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就可大事化小。”[2]蒋百的失踪换取了乌塘官员们的升迁,这是金钱的诱惑、权力的威逼、官场的腐化。金钱和权力的合谋把一个善良无辜的女人逼得走投无路,她的余生注定了要在永无终结的漫漫长夜中度过。对她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只有痛彻心扉的伤痛与愧疚,只有冷入骨髓的严寒与孤寂。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霸权社会里,死亡与性外加政治权力相纠结,形成扑朔迷离的生存困境,从她身上可以折射出对人性、人生乃至中国社会的思考,暴露出女性天生的弱势与困境。魔术师丈夫的死让“我”在瞬间由温暖跌入刺骨的寒冷,为走出伤痛,与流俗保持一定距离的“我”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在寻求中“我”与生活在社会底层,过着平凡琐碎生活,经历着世间的丑恶、不公和荒谬的小人物有了交会,对他们形形色色的生命和现世的磨难进行了目击。目睹他们的人生苦难,“我”完成了一次情感疗伤,精神得到升华,超越了人间世俗中一切生与死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清流获得了灵魂的安宁,得到了生命的涅槃。
2.魔术师与云领
小说中魔术师丈夫和会玩点小魔术的小男孩云领又形成了对举关系。变戏法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不同的是魔术师是在舞台上变,现实生活中变没了自己,而云领在现实生活中变戏法,他的存在变没了“我”的伤痛,让“我”走出了失去魔术师丈夫的悲哀。
文中魔术师的故事完全是在“我”的讲述之下呈现的,他在舞台上翻云覆雨、千变万化,仿佛万事万物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完全吸引了“我”。家中日常而逐渐清贫的日子,由于他的体贴和温爱,让“我”的人生变得多彩丰富而又浪漫幸福。但魔术师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的“魔术”归根究底也只能点缀我们的生活,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了剧团和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把他的清高当作破鞋一般扔掉,奔波于各个夜总会之间。当死神的魔爪无情地伸向他时,他的“魔力”尽失,任“我”如何抚摸他的眉骨,如何痛彻心扉地呼唤,也无法让他把自己从死神的“魔术匣”中变回来。其实小说中“魔术师”的命名耐人寻味,充满着无穷的寓意。因为魔术师最终被车撞死没能走出变幻的命运,暗示着爱情犹如梦幻变化不定,人生就像魔术般无法预言不可捉摸结局只有虚空!蒋百嫂说把自己嫁给魔术师,就好像把自己装在了神奇的魔术盒子里,那么“我”变化无常的命运就是人生的必然。显然迟子建在这里隐喻人生、爱情即像魔术般变幻以及命运多舛。而云领的所谓“魔术”充其量只能是变戏法,其目的是推销他的磨脚石。他加了机关的衣袖、帽子,被明眼人一眼就可识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养家糊口的手段,只是生存的凭借和依托而已。而正是这些花招,让他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们相识,而且正是在他的引领之下,在七月十五夜,我们一起来到清流放河灯,让缠绕“我”的伤痛和对丈夫的思念随着溪流清风明月飞奔银河。
3.陈绍纯与肖开媚
陈绍纯是作为小说中最光华的生命被书写的,和魔术师一样也是文中一种符号化的形象,他经历过死亡、文革中亲友的背叛,深味人生的诸多苦难后,在灵魂的幽深地带自然孕育出唱响心灵的生命之歌,他孤寂地唱着人世间至纯至美的悲凉之音,坚执地用他的传奇人生书写着乌塘的民间历史,竟被自己不愿涂改的艳俗而又轻飘的牡丹图框砸死。尼采说:“民歌首先是世界的一面镜子,是原始的旋律,这旋律现在自己找到了对应的梦境,将它表现为诗歌。”[6]21陈绍纯的悲歌像是梨花枝头晶莹的露珠一般,又像一面照尽世人真面目的魔镜,让人欣悦片刻后顿觉凄婉悲凉。钱钟书先生认为“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7]946陈绍纯所唱的丧歌,叙述者“我”听来感觉确实“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8]482而“我”和蒋百嫂之所以为之动容,一方面陈绍纯所唱悲调与“我”的丧夫悲痛契合,也与蒋百嫂无法安葬蒋百的伤痛吻合,另一方面与人类本性中喜欢哀挽和悲伤的曲调有关。卢文昭在《龙城札记》卷二中评说古人“音乐喜悲”,而早在《礼记.乐记》中就记载“丝声哀”,意指听起来哀怨的声音是最婉妙的,嵇康也在其《琴赋》中说“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认为“最谐美音乐必有忧郁与偕”。也许陈绍纯的经历、他的天籁之音都注定了他永远孤立于世、为世俗所不容,唱着只有真正的哀伤者才能懂得的又悲又没歌词的丧歌。陈绍纯可谓我们民族的非凡智慧和极高境界的代表,他凭借一双冷眼,一份静心,一份悟性,来领略和透视历史、现实和文化的锐变嬗替,“甘为旧有美质文化而殉道……走上与心中的完美事物(虽然是历史性的)共相厮守的终极之路”。[9]236因而陈绍纯寄寓着以自然平和的态度和淡泊宁静之心化解人生痛苦、超越荒诞现实,从而获得心灵的超脱以及领悟生死的智慧人生的诉求,是道家所言及的清净虚无、本性真纯境界的最后代言人。
陈绍纯的对照者肖开媚,她经营着一家婚介所,除此之外专门在婚宴上给别人唱喜歌。由于她品行低劣,她的喜歌里飘出的都是铜臭之气,让人的心灵不会因歌声而产生真正的喜悦之情。而她也因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给矿工刘井发介绍了心如蛇蝎的“嫁死女”而被刘砍伤,成了人物口中叙述出的又一出悲剧的主角和导演。可以说歌者是陈绍纯和肖开媚共同的身份,但一个唱丧歌,一个唱喜歌;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但一个开画店为的是唱歌方便,一个办婚介所却为牟利。所以陈绍纯的丧歌中流露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突显出一种自我陶醉的“古典情怀”,而肖开媚的喜歌中传达着一种喜庆吉祥的现实感,突显出一种迎合媚俗的“现世功利性”。这样喜与悲纠缠在一起,他们的存在和对立,恰好体现了传统文明、文化形态和现代文明、文化形态的对抗。
诸多人物间的对举、对应带来映照、衬托甚至反差的意义,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世态百相,品味人物各自的心理和生活轨迹,咀嚼到人生无常的况味。迟子建“让人物与人物互相勾连,让事件与事件互相映照,易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使独特和深刻成为最大的可能。”[10]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的说法:“如果人的行为或产物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的系统。”[11]25可以这么认为,小说特定的环境背景及其中发生的故事情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运行在其中的人物,在系统中可以看作是某种符号,产生意义,并得到认定。所以小说中对举的几组人物,虽然各自特点不同,存在状态有差异,但并不和整个的系统构成矛盾,而是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特有的意义。
三、诗意缤纷的意象之美
意象是感觉的遗留,“有一种观点强调自我表现,即诗人通过他的意象来展示自己的心理”[12]230在小说中一如迟子建其他的作品,仍然通过精心营造的意象显现出具有令人伤怀的艺术美感。其意象营造的特点是善用一种流动的、飞翔的、明朗的美感,铸造人、情、景相融一体的伤怀之美,把忧伤静静地沉淀在生活的纵深处,析出意象的暗示能力并把它发挥到极致,突显出一种一直和感性相通的理性的气息。
1.“夜晚”意象
是对存在状态的隐喻,在小说中具有定性的作用,传达出作者对生活及人生的理解。蒋百嫂反复地吟咏:“这世上的夜晚啊——”这是对现实宿命般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所具有的无奈与鄙视。她的丈夫已经进入万劫不复的夜晚,永远没有了白天,更别奢望葬礼,别奢望墓地,而她今后的所有日子,甚至漫漫一生,也将在暗无边际的夜晚中延宕。在此,处于黑夜的蒋百嫂和夜晚这两个意象互相隐喻,发生关联,成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夜晚”对于叙述者“我”来说,更是目击人生真相和生命限度的必备场景:魔术师丈夫死于夜晚的一场车祸,蒋百蹲坐于永是夜晚的冰柜变成沉默的冰山,陈绍纯在夜晚被一幅艳俗的牡丹图砸死……痛苦的记忆如同世界上所有的黑夜一样笼罩在人们心头,无法释怀,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夜晚”之痛。黑暗,阻断了人们渴望的幸福和安宁!
2.“蝴蝶”意象
小说末尾“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煽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2]这一“蓝色蝴蝶”的意象成为一个在读者阅读时引起审美注意的关节点,它唯美、悲弱、淡雅、婉约、温柔、诗意的特质,让人产生淡淡的失落感的瞬间又会让温暖油然而装满胸间。这弥漫在文本中婉丽凄迷的造境可谓感伤的温情抒写,说它是“气氛”也好“情调”也罢,可以确定的是升腾起缕缕诗意氤氲在文本间,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借用霍桑的话就是“一种诗意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必要……什么真实性……”[12]242不但满足了人们祈求主人公爱情追忆之旅的超越与圆满的心理,而且蕴涵了更深刻的思考,造就了更为宽阔的审美空间。在传统文化积淀中,“蝴蝶”与人的关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意指:一是梁祝化蝶的故事所蕴聚的爱情内涵已经化成集体无意识驻扎在人类心灵的深层。在我国文学传统中以梁祝化蝶传说为原型衍生了多种文艺样式,自明清至现在,光是小说就有近30部(篇)。有论者指出:“这个传说的动人之处在于梁祝二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几乎每一部小说作品都是以化蝶作为结局,这种带有幻想色彩的唯美句号早已成为梁祝传说的经典桥段”。[13]可见蝴蝶意象早已成为了生死爱情的镜像。二是作为对人生态度的隐喻,浸透着忧伤的美丽、浪漫。小说中“蓝色蝴蝶”经过“我”情感的过滤,带有浓郁的主观感觉色彩,是一种超然、解脱,又是刻骨的思念。迟子建认为“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以‘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展览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5]304这样“蓝色蝴蝶”与“我”的爱情追忆之旅的终结也就自然形成关联,它轻盈温暖地化解了我缠绕心间的丧夫哀痛。其艺术指向在于营造了一个典雅优美的意境,传达出厚重悠久的文化格调,飘散出繁复悠远的人生体悟和韵味,使得整个作品的意蕴丰厚而含蓄蕴藉起来。
3.“银河”意象
这一意象传达出“我”对磨难的超越和高境界体认。因为银河上接天际之苍茫,下引地上之泉流,永存天地之间,它苍凉却不失温暖,凝重而不失明朗。小说结束之际,“我”凤凰式的涅槃是借助于在云领的引领之下完成的。在幽静恬谧的清流之夜,“我”身处小溪、河灯、明月之间,心灵之伤痛刹那间获得了稀释和修复。“魔术师”丈夫的死尽管让“我”的人生变成了一轮残月,让“我”的世界和生命满溢出无法修补的残缺,但是相比陈绍纯无人倾听的孤独,以及抱憾而终的宿命,相比蒋百嫂陪伴冻在冰柜无法安葬的丈夫,仍然为了生存要挨过的漫漫长夜,我毕竟拥有过与魔术师丈夫心有灵犀的过去,我毕竟用葬礼为他画上了人生的休止符。因而知道了云领一家的遭际,想起蒋百嫂的过往,“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2]所以在清流,“我”把忧伤、悲痛、虚空与河灯一起放走,于是“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2]这一浪漫唯美的场景可谓赋予了夜晚应有的美好希冀,重新赋予人生应有的温暖亮丽。显然我们看到一个身陷生之困境的女主人公内心自我救赎之后完成了她的涅槃,耀现出普度众生的大悲悯情怀,至此“我”史诗性的成长伴随着蓝色蝴蝶的停落终于圆满落幕。
那么,小说中“夜晚”、“银河”、“蝴蝶”这些意象生成了怎样的结构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写形显意,形意相偕的原则;在西方美学中“意象可以作为‘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12]203这里,“夜晚”、“蓝色蝴蝶”和“银河”的意象已经超越了描述的性质,也不在于其传输什么引申意义,而是在隐喻层面上来使用,而隐喻势必生成意义。所以这些意象蕴涵着明显的语义指向,概括而言,其意义在于象征性地表达了主题、揭示出“我”的一种心理状态、丰富了故事的情景和人物的感觉。
四、结语
总之,套叠镶嵌的同故事叙述之美、对举呈现的人物设置之美、诗意缤纷的意象之美等别致的景观共同构造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独特的审美机制,其中不仅承载着迟子建不堪回首的个人哀恸和厚重的人生体验,更熔铸着她洞察人性的深度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陷落生之困境的女主人公旅途中直面生活,触摸民间生存真相,从伤痛和磨砺中出发,穿越了夜晚的黑暗与疼痛,对人类生存本相进行叩问和审视。其实在迟子建所有的创作中,都试图给生命温暖与爱意。她说:“我的很多作品意象是苍凉的,情调是忧伤的。在这种苍凉和忧伤之中,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应该让人欣喜的。”[14]文学应该像暗夜中的灯塔,给信仰它的人以温暖光明和启迪导引,呈现一个阔大、辽远、丰富和复杂的世界。正因如此,在小说的结尾,关于银河和蓝色蝴蝶的诗意抒写,向人们传达出幸福和希望,给人以无尽的美好遐想。
[1]蒋子丹.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及其它[J].读书,2005,(10).
[2]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J].钟山,2005,(3).
[3]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鲁迅.鲁迅大全集:第30卷[M].李新宇,周海婴,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5]迟子建.迟子建散文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
[6]尼采.尼采经典文存[M].李瑜青,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7]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徐渭.徐渭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10]王立宪.生死的伤痛与生的意义——读迟子建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J].名作欣赏,2010,(10).
[11]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13]匡秋爽,王确.梁祝小说的产生与传播[J].当代文坛,2014,(4).
[14]迟子建,方守金.以自然与朴素孕育文学的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钟山,2001,(3).
〔责任编辑艾小刚〕
I227
A
1671-1351(2015)04-0070-05
2015-04-29
马超(1960-),男,甘肃天水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思潮互动关系研究”(12BZW101)、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女性文学视域——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路径与困境”、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多元格局中的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