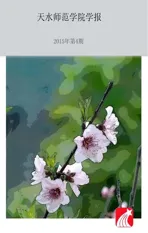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何时到来——解读习近平文艺讲话的五个关键词
2015-02-13王贵禄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王贵禄(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何时到来——解读习近平文艺讲话的五个
王贵禄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习近平文艺讲话是围绕“如何实现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这个主线展开的。《讲话》却没有简单地从政治的角度谈如何实现文艺复兴,而是在深度把握百年中国文艺发展演变的规律的前提下,紧扣“人民性”、“大众化”、“审美性”、“民族化”和“风格化”这五个
,结合中国文艺的现实境遇与历史诉求,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讲话》所运作的这五个
,的确是中国文艺生存发展的命脉所在,也是中国文艺走向复兴的唯一通道。如果文艺工作者能洞悉这五个
,全面体认和真切实践《讲话》从这五个
所生发的文艺新命题,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实现,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不会是遥远的。
人民性;大众化;审美性;民族化;风格化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①《讲话》发表以来,受到文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各地的文化部门都举办了不同层次和形式的讨论会,②而多家学术机构也召开专题研讨会,并组织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学术性论文。应该看到,这些研讨对于扩大《讲话》的影响,以及正确认识《讲话》精神都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我们同时看到,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讲话》的认识,多停留于表象,缺乏深入的理论观照,而学术性刊物所刊发的论文,也多是就《讲话》精神的某一个层面做讨论,还没有从理论高度进行整体性的观察。笔者以为,就目前来看,《讲话》所提出的新命题及其学术张力,尚未得到系统的揭示,因此其指导性就可能被弱化。鉴于此,本文力图整体把握《讲话》,并就《讲话》提出的新命题展开分析,以求深度探视其精神旨归。
纵览《讲话》,我们发现,其阐述的问题固然很多,但从文艺理论的视野来观察,主要是围绕几个展开的。只要我们抓住了这几个文本,我们不难归纳出“人民性”、“大众化”、“审美性”、“民族化”和“风格化”是《讲话》展开论述的几个
,这几个
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框架结构,从而支撑起了《讲话》的所有论点。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
既秉承着文艺理论的固有内涵,又被赋予了新的能指,因此产生了新的文艺命题。而这些新的文艺命题,无疑是值得我们反复讨论和研究的。
,对于《讲话》精神的解读就能做到提纲挈领,做到心中有数。那么,这几个
都是什么呢?细读
一、人民性:新世纪中国文艺的基本属性
“人民性”是一个中国文学有着久远历史传承的本质属性,如最早出现的诗集《诗经》中大量的诗篇就表现出这个属性。但从理论上明确阐述文艺的“人民性”属性,并率先使用“人民性”概念以判断文艺作品的,则是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其后,马克思、葛兰西、卢卡奇、毛泽东等理论家对文艺的“人民性”都有深刻的论述。“人民性”属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属性,20世纪中国作家对于这个属性的认识及其把握,形成了最具中国特征的文艺传统,深度规范了新文学的走向。那么,到底什么是文艺的“人民性”呢?有研究者在整合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民性”的内涵,即“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文学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文学的‘人民性’就是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同情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1]这个阐述揭示了“人民性”三个方面的内涵:(1)体现“人民性”属性的文艺作品,必然关注和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而不是限于私人化的生活;(2)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活动中,应该以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为基本立场和价值尺度,而不是从作家、批评家的个人好恶出发进行创作或批评;(3)对民众的认可与同情。可以认定,这个阐述对于文艺的“人民性”内涵的揭示是全面的,也是可取的。
习近平在文艺讲话中,也是从以上三个方面阐发新世纪中国文艺的,以明确“人民性”这个根本属性。如其所论,新世纪中国文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这三个论断,对新世纪中国文艺如何体现“人民性”提出了深切的期待,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始终是在把握“人民性”内涵的前提下进行论述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这是要求作家艺术家关注和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而不要把作家艺术家本人及其小群体的生活作为“表现的主体”;“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要求作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中,以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为基本立场和价值尺度;“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这是要求作家艺术家理解和同情人民大众,以真诚的心来书写人民大众的愿望心声,使自己的创作能够真正传达出人民大众的情感诉求。
《讲话》关于“人民性”的论述,其意义当然不限于对“人民性”既有内涵的表述,对“人民性”内涵新的能指的阐发更值得我们重视。我们注意到,在对“人民性”既有内涵的表述中,《讲话》都赋予它们以新的能指。先来分析“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论断,我们知道,那些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艺作品,必然是真切映像了广大民众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是能够被“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人民所认可的作品,这就是说,文艺家应该以“真切而深刻地映像广大民众生活”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而广之,一部文艺作品是否体现“人民性”,以及体现的程度如何,应该作为判断其价值优劣的首要标准。这实际上对新世纪的文艺家和研究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把“人民性”作为文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评判文艺作品的价值意义,取决于该作品对“人民性”的体现程度。概而言之,《讲话》是说,“人民性”应该而且必须作为新世纪中国文艺的基本属性。只有深度体现出“人民性”,这样的文艺作品才能被广大民众真正接受。《讲话》指出,深度体现“人民性”的根本路径(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就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对待民众的态度,仅仅有理解和同情是不够的,《讲话》认为,艺术家更应高度肯定广大民众推动历史的壮举,通过“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的方式,以“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讲话》将“人民性”视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必须具备的基本属性,这既是对百年中国文艺最重要的经验的准确概括,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个最具中国特征的文艺经验的大力倡导,对扭转中国文艺不正确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人民性”对当下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术语,但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真正自觉表现“人民性”属性的文艺作品早已是凤毛麟角。这是因为,从1990年代以来,相当一批文艺批评家在躲避“崇高”、解构“集体主义”、颠覆“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将表现“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当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在表现“人民性”的文艺作品被大肆攻击之时,虽有文艺理论家预感到丧失“人民性”对中国文艺造成的深重危害,并呼吁重振中国文艺的“人民性”,但其微弱的声音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当中国文艺经历了各种逆流,如“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日常生活叙事”,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才痛切地认识到,远离了“人民性”,也就远离了中国文艺的精气神,就远离了中国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讲话》不仅对各种逆“人民性”的思潮给予了坚决的否定,而且旗帜鲜明地重倡“人民性”,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人民性”提出了众多新命题,这对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大众化:新世纪中国文艺的重要向度
文艺的“大众化”与文艺的“人民性”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大命题,可以说这两个命题,是现代以来中国作家艺术家都无法回避且不能不正视的。“大众化”命题的缘起,与新文学初期的“西化”与“拟古”有关,即与新文学的形式要素(尤其是语言表达)相联系,在1930年代“左联”期间,理论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形式要素的讨论中,但随着讨论的深入,理论家逐渐认识到,“大众化”其实不仅包含形式要素,还包含更复杂、更重要的内容要素。“左联”理论家尚未澄清“大众化”的内容要素,这个问题只有到了1940年代的延安,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得到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谱系,即“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文艺的意识形态问题,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批评的问题,文艺的源流问题”。[2]毛泽东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点,通常被研究者看作是最权威也最深刻的,因为其既阐述了“大众化”的逻辑起点,又指明了“化大众”的可能途径。那么,“大众化”命题与“人民性”命题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我们说,“大众化”在内容要素上体现着“人民性”的基本属性,但它是在现代语境中产生的,是文学意义上的民主精神的体现,大众化文学的极致就是人民文学;而体现“人民性”的文学却不一定是大众化的文学,因为“大众化”还包含“化大众”的问题,即以广大民众可以接受的文学形式,层级性地引导与教育大众。理清了“大众化”的问题谱系,就能更好地解读习近平文艺讲话的意义所指。
在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上,习近平《讲话》无疑继承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观点,但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了新的阐发。我们来看作家艺术家改造的问题,《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作家艺术家如何做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唯一的可能就是成为大众中的一员,除此别无他法,但如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呢?这就非来一次改造不可,这种“改造”,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乃至于世界观,长期而深入地在大众的实际生活中观察和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才能真正代表大众的声音,从而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成就。关于新世纪中国文艺的意识形态问题,《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实际涉及到我们下文所说的“民族化”,这是另一个大的话题,本文将详细讨论。但我们可以把握的一个总体方向则是被大众“喜闻乐见”,只有大众能读得懂且喜欢读,文艺作品才可能发挥较大的社会效能,毋庸置疑,所有被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必然是民族化的。关于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讲话》谈的较多,针对性也很强。《讲话》指出,作家艺术家首先应把握住时代主潮,引领社会风气,这是“化大众”的前提,如其所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其次,大众的欣赏和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作家艺术家应根据大众的审美需求做相应的调整,而不能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在文艺批评的问题上,《讲话》提出要把握四个标准,即“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而前提是“说真话、讲道理”,从而形成“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关于文艺的源流问题,《讲话》提出了两点,一是人民大众及其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二是作家艺术家只有扎根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才能发现素材,找到灵感,“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应该看到,“大众化”是习近平《讲话》展开论述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围绕这个命题而阐述的问题谱系与毛泽东《讲话》是一脉相承的,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但两者又有所不同,毛泽东《讲话》因为诞生于战火弥漫的战争语境,故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论点显示出极强的阶级对抗性与现实功利性;而习近平《讲话》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后,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产生的,因此更多地是基于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提出的建议与箴言,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与导向性。无论如何,习近平《讲话》关于大众化问题谱系的阐发,对于破解当代文艺诸多难解的谜团(如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现象),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大众化”及其实践理应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
三、审美性:新世纪中国文艺的生存之本
文艺之所以是文艺,必然有它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质的规定性。韦勒克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是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济慈等人的作品为文学,而不是以西塞罗、蒙田、波苏埃或爱默生等人的作品为文学。”[3]14韦勒克这里强调的“虚构性”、“创造性”和“想象性”,指的就是文学的审美性,文学属于审美领域,而“与审美领域相对的其他主要领域则有科学——工具领域(如数学、生物学、工程学、电子学及各种技术组织等),道德——实践领域(如历史、政治、宗教、伦理、社会学等)”,“文学应当摆脱其他文化形态(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历史等)的直接纠缠,而成为以审美为中心的自主性活动。”[4]56这就是说,文学艺术必须以审美性为其存在的根基,丧失了审美性,文学艺术将不再是文学艺术;同时,作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活动中,应摆脱现实利益关系的困扰,而使其创作活动成为以审美为中心的自主性活动。任何艺术创作活动都离不开自主性与审美性,自主性是前提,审美性是结果,失去了自主性就谈不上审美性。只有把握住了文艺的自主性和审美性的特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讲话》的意义所在,因为《讲话》的诸多论点都是在“审美”这个范畴提出来的。
关于文艺创作的自主性问题,《讲话》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讲话》的这个论断的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是对19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当代文艺表现出的一种不良倾向的坚决否定。我们知道,消费主义在1990年代席卷全球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当代文艺也在所难免。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扩张及影响下,文艺从“自由的精神生产”开始倒向市场,在单向度的适应与迎合中,文艺创作离大众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观照也越来越趋于浅表化,而商业逻辑、拜金主义、享乐原则却大肆盛行。这是一种以牺牲文艺创作的自主性为代价的做法,其后果是作家艺术家在不知不觉之间消解了文艺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艺创作被商业逻辑所左右的另一个恶劣后果,是“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批量生产”原本是指一般的商品生产,却被追逐利润的作家艺术家也照搬过来,例如,某类作品在市场上受欢迎,大家便趋之若鹜,竞相模仿,于是这类所谓“作品”便表现出“机械化生产”的窘相,其生命力如何也就毋庸赘言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醒过作家艺术家,文艺作品虽然属于一种商品消费,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消费,具有一般商品不具备的属性,即具有“精神享受”与“意识形态再生产”这样的属性,并主张必须维护文艺作品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讲话》还对1990年代以来“伪大众化”文艺倾向做出了批评,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伪大众化”文艺似乎在张扬文艺的审美功能,而其实质则是对文艺审美的解构与颠覆,诚如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如果说低俗化的文艺降低了作品本应有的道德教化功能的话,那么,过度娱乐化的文艺则会削弱其本应有的激发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审美涵养力量。”[5]
除对违背文艺创作规律的不良倾向进行批驳外,《讲话》从文艺审美的规律出发,直言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时,应如何把握审美性,并进而创造审美价值。对于审美性的把握,其实是从审美关系上把握生活。作家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对象世界,文艺创作必须深入而且超越这个对象世界,把这个对象世界视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从而揭示隐含其中的人的内容,以展现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审美过程,概括起来,就是《讲话》所指出的,“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勃兰兑斯曾深有感触地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6]2可见,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都注重展示人的生活,表现人的情感,剖析人的灵魂,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度体现出审美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话》的论断对当今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具有不容置疑的指导性,“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为扭转那种漠视审美价值创造的低俗化、庸俗化、娱乐化的文艺潮流,《讲话》提出要创造文艺精品的问题,认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审美性作为文艺作品存在的根本,在《讲话》中得到了深入的阐发。《讲话》一方面论述了违背审美规律的种种表现,如盲目迎合市场,追逐利润,不注重精神内涵挖掘的粗制滥造,打着“大众化”之名而行“低俗化、庸俗化和娱乐化”之实的伪大众化潮流等;另一方面指明了如何把握文艺的审美性和创造审美价值,关于如何把握文艺的审美性,《讲话》倡导作家艺术家“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关于如何创造审美价值,《讲话》认为应该深入生活、深入人的灵魂,抒写作家艺术家的生命体验,描绘巨变时代人的灵魂及其变迁,从而创造文艺精品。《讲话》关于文艺审美性的阐发,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的创作实践,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对于反面教训的总结尤为深刻,值得所有作家艺术家深思和研究。《讲话》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转折关头出现,具有拨云见日的意义。《讲话》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审美性是新世纪中国文艺的生存之本,必须坚守。
四、民族化:新世纪中国文艺的文化指向
“民族化”与“西化”是百年新文学两个相反相成的重要命题。众所周知,新文学的催生是借助于外力的作用,这“外力”就是西方文化资源。缘于此,新文学便埋下了“西化”的种子,“五四”文学中“西化”的迹象尤为明显。随着大众化问题的浮出,“西化”受到了来自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全面而峻切的质疑,“左翼”文学已表现出民族化的趋势,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创作要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此,“民族化”便作为新文学一个重要的命题而存在。(这里需要明白的是,当我们讨论“民族化”的时刻,即是以“西化”为话语背景的,倘若没有这个话语背景,单纯来谈“民族化”意义并不大。)1980年代初,在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民族化文艺受到冲击之时,“西化”之风复燃,这次由全国性的“现代性冲动”所引发的“西化”风潮,使西方文化资源海量涌入,这次的“西化”势头比“五四”时期更其迅猛,大有非西方文化资源莫谈文艺的气概。1980年代初那种蔑视和淡化文艺民族性的风潮,引起了作家艺术家的必要警觉,他们怀着失去民族文化身份的深沉焦虑,踏上了寻找民族文化资源的漫漫长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寻根文学”。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在“民族化”与“西化”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中,“民族化”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甚至持续处于“西化”的下风。现在看来,“寻根文学”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在不断提醒我们,民族文化资源和文艺的民族化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中国文艺每一次“西化”的盛行和“民族化”的衰退,都是在中国社会开放状态下发生的。这就是说,有社会开放,就有“西化”的可能,我们却不会因为有“西化”的可能就不开放,因为世界已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从理论上讲,那种纯粹地方的、民族的、封闭的发展已不大可能。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文艺现象,这就是中国文艺每一次“西化”的盛行,都必然引发强力的反弹,从而使“民族化”问题反复浮现。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西化”(极端论者甚至提出“全面西化”的主张),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包括中国文艺传统)的被同化与被覆盖,其严重后果是,使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失去文化标识,弱化我们的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最后使中国人一个个变成文化意义上的漂泊者。这样,当代文艺不能不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便摆在了我们面前:“西化”既然对民族文化有着如此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的文化资源?在西方文化四面楚歌的包围中,我们的文艺还要不要“民族化”,如果要的话,又该如何突围并走向“民族化”?我们应该以何种心态对待民族文化资源,如何汲取其最精华、最典范的东西,以确立文艺创作的民族形象?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我们的文艺就会失去航向,失去重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到底何去何从将始终是致命性的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话》从文化高度围绕文艺的民族化以及如何民族化等做出的论断,对于我们理性而有序地发展中国文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所谓“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就只能是民族化的文艺作品,而决不可能是“西化”的文艺作品,这实际上指明了新世纪中国文艺朝“民族化”努力这个基本方向。既然“民族化”的基本方向已经明确,那么作家艺术家又该如何把握“民族化”,换句话说,“民族化”的核体是什么?《讲话》有这样的论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个论断可从三个层面来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化”的基础和依据;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所在;民族精神还必须注入时代内涵。概而言之,文艺的民族化要紧紧把握“民族精神”这个核体来展开。《讲话》的这个观点在果戈里那里得到了印证,果戈里在评价普希金时指出,“他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因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7]1-3既然彰显民族精神是新世纪中国文艺“民族化”的轴心和发力点,那么,这民族精神的内涵又是什么?《讲话》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这就可以认定,所谓民族精神应该包括“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人审美追求”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精神”即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而体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等指向的文化精神;“中国人审美追求”尽管可以有很多种说法,而《讲话》所提出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以及能够“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说法,应该是最完满的一种解读,因为放眼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哪一部优秀作品不是体现这种审美特质的呢?这种审美特质的达成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解决了“民族化”这个努力方向以及“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对待“西化”以及西方文化资源的问题。很显然,“西化”不应该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流,这在上文已做了分析,但我们却没必要对西方文化资源持否定态度,因为西方文化资源中的优秀文艺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该怎样学习和借鉴?果戈里说得好,要“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这就要求对西方文化资源必须进行“民族化改造”。《讲话》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其所叙,“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
中国文艺的“民族化”以及“如何民族化”诸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格外凸显,因为西方文化正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文艺的各个角落,倘若我们缺少“民族的眼睛”,不进行有效的“民族化改造”,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艺必将堕落为西方文艺的衍生品和附属品,从而使我们的文艺丧失独立的存在价值。《讲话》关于“民族化”方向的确立、民族化过程中应把握的核体,以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资源等问题的阐发,其意义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
五、风格化:新世纪中国文艺的内在诉求
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不难发现,在“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者对文学风格的构成、类型及表现的研究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而曹丕、钟嵘、刘勰等研究者在评价某个时代、某个流派、某个作家的文学时,也是将“文学风格”作为关键词而展开论述的,此后,对于文学风格的分析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一个不可逾越的惯例。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文学风格之所以被研究者所看重,原因有四:首先,文学风格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修辞表达,任何作家的创作都要受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的特点,对文学风格的研究也意味着对特定时代的研究;其次,文学风格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境遇的修辞表达,是一个民族的历代作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这种体现民族特质的文学风格,是不同民族的文学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再次,文学风格的形成既是一个作家的创作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一部作品达到较高艺术境界的标志;最后,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呈现,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达到繁荣程度的显性标尺。据此而论,只有在一个平庸的文艺时代,文艺才会表现出风格的缺失和风格的雷同,才会“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相反,在一个繁荣的文艺时代,文艺必然会表现出风格化的气象和风格的多样化趋势。毋庸置疑,新世纪中国文艺要走向繁荣,就必须风格化,而事实上,风格化也是文艺发展的内在诉求。
《讲话》关于新世纪中国文艺的风格化以及如何风格化等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艺走向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见关涉如何形成时代风格的问题,如何体现民族风格的问题,如何形成个人风格的问题,如何使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作家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相结合的问题等。我们先来看时代风格的问题,《讲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这段论述的焦点有两个:把握时代精神是形成时代风格的前提,时代风格具有审美的持久性。时代精神并不是指一个时代所有的精神表现的综合,而是指一个时代最能给人以启发、激励和想象的精神元素,只有把握住了这样的精神元素,才有可能形成时代风格。以当下而论,我们所面对的精神状况是异常复杂的,如果我们具备一双慧眼,就能把握住那些“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精神元素,并将其体现在作品之中。时代风格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一种审美标志,能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精神上的沟通和审美上的共鸣,从而使读者形成一种对时代的特殊记忆,并获得持久的审美享受。在文艺的时代风格问题上,茅盾的观点可与《讲话》的论断形成参照,茅盾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风,然而同一时代的作家在共同的文风之中又有各自不同的风格。有健康的文风,具备着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又有不健康的文风,那就是浮华、堆砌、装腔作势、故弄玄虚。”[8]28关于如何形成民族风格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前文做了详细的分析,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形成民族风格就必须使文艺创作民族化。关于如何形成个人风格的问题,《讲话》阐述的观点有:首先是作家艺术家要有明确的风格意识,风格的形成就意味着创新,就意味着审美理想的达成,如其所论,“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其次是“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作家艺术家如果要在文艺创作领域达到一种高度,没有审美理想是不可想象的,审美理想作为标杆,可引领作家艺术家走向成熟,走向风格化。除了坚守审美理想,作家艺术家还要不断提升自我境界,并且在文艺创作中持续探索,这就从主观层面奠定了风格形成的基础。最后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很显然,仅有风格意识、思想积累、文化修养、艺术训练等主观方面的储备还不足以形成风格,风格的形成更多的是要向生活学习,在民众生活的现场发现活生生的美,捕捉转瞬即逝的美,体验前人未曾体验到的美,这些审美发现和审美体验的获得,为风格的形成夯实了客观性基础。在以往的个人风格的研究中,多注重主观性层面的东西,而相对忽视了客观性因素,《讲话》的观点校正了这个倾向。我们再看如何使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作家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相结合的问题。在前文所论述的人民性、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中,《讲话》实际都涉及如何将这些关键词相融合的问题。我们对文艺风格不能单纯从形式层面来理解,它更多地是指内容要素与形式表达之间的契合程度,即相融合的程度。《讲话》也是从相融合的角度谈文艺风格的,如其所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个段落讨论了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个人风格相融合以及怎样融合的问题,这就是以人民性、审美性为中介,将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一切都要表现得自然、妥帖,如风行水上。茅盾关于文艺风格相融合的问题也有论断,可作为《讲话》的注脚。在茅盾看来,“民族化、群众化和个人风格不是对立的。个人风格必须站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上。但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不一定都有个人风格。离开了民族化、群众化的大路而追求所谓个人风格,猎奇矜异,自我陶醉,那就必然要走进形式主义的死胡同。”[8]14《讲话》对文艺风格的多样化呈现表示了强烈的期待,并阐述了如何使文艺风格多样化,“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本雅明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论证了机械复制技术给文艺带来的重大变革,而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变革,文艺作品频频表现出相似的面影,这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风格的价值。19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大幅提高且日益普及,其对文艺创作造成的深刻影响是,作家艺术家更难摆脱“复制”这个魔咒了。在全球化时代,“复制”的魔力似乎渗透到了文艺作品的神经末梢,我们在此类文艺作品中实难感受到风格的存在。“风格”已成为掣肘中国文艺发展繁荣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如果解不开,“中国文艺发展繁荣”的设想终将是一句空话。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讲话》关于风格所阐述的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六、余论:如何实现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
新文学的发生已逼近百年。这百年来新文学经历了太多的潮起潮落,它曾经以迷人的光环令世人仰视,但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它早已黯然失色。此情此景,迫使文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中国文艺到底还能不能有所作为?换句话说,中国文艺还能不能参与并且推进历史的进程?这似乎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被人们遗忘许久的“老问题”,因为后工业时代是一个解构与颠覆的时代,在长年累月的解构与颠覆中,人们已经很难相信文艺可以“参与并且推进历史的进程”。这个老问题,在今天已渐渐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新问题。这不仅是新文学的悲哀,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悲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阐释和解决,终将是问题。文艺工作者期待有人能从至高的视点(这“至高的视点”就是历史的高度、文化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重新对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做出定位。《讲话》正是从至高的视点上,重新定位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如其所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讲话》的这个定位,不仅高度肯定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对文艺“参与并且推进历史的进程”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可能的贡献。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高度来定位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领域的全面复兴,文艺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极其重要且异常活跃的构成部分,当然也需要复兴,这就是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艺复兴的浪潮兴起过多次,其中以汉唐两代的文艺复兴最为壮观。近现代以来,“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都曾蓄势待发,而终未形成文艺复兴的宏大气象。百年新文学的“文艺复兴梦”何时能梦想成真,这应该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密切关注的大问题。纵观中外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文艺复兴的实现,有赖于主客观条件的双向成熟。以客观条件而言,那就是国力的强盛;以主观条件而言,那就是对文艺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与总结。汉唐两代的文艺复兴莫不如此。就目前而论,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主客观条件是否都成熟了呢?我们不妨做一个简析。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具备了的。从主观条件来看,新文学百年来所经历的潮起潮落,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积存了太多的教训,尽管如此,如果对这些经验教训不能有效归纳和总结,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意见,就不能说主观条件成熟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讲话》对百年新文学成功经验的精准概括和对失败教训的深度总结,以及对新世纪文学如何发展等问题的阐发,是完全基于延展、深化和完善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主观条件。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如何实现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高度来观察和解读《讲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其精神指向,并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讲话》并没有简单地从政治的角度谈如何实现文艺复兴,而是在深度探询百年中国文艺发展演变的规律的前提下,紧扣“人民性”、“大众化”、“审美性”、“民族化”和“风格化”这五个关键词,结合中国文艺的现实语境和历史诉求,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关于“人民性”的论述,其意义当然不限于对“人民性”既有内涵的表述,对“人民性”内涵新的能指的挖掘更值得我们重视。《讲话》对新世纪中国文艺提出了确切的要求:把“人民性”作为文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性”应该而且必须作为新世纪中国文艺的基本属性。“大众化”是《讲话》展开论述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其关于大众化问题谱系的论述,对于破解当代文艺诸多难解的谜团,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大众化”及其实践理应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审美性作为文艺作品存在的根本,在《讲话》中进行了深度的阐述。《讲话》一方面论述了违背审美规律的种种表现,另一方面指明了如何把握文艺的审美性和创造审美价值。《讲话》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审美性是新世纪中国文艺的生存之本,必须坚守。中国文艺的“民族化”以及“如何民族化”诸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格外凸显,因为西方文化正在雄心勃勃地同化和覆盖我们的民族文化。《讲话》关于“民族化”方向的确立、民族化过程中应把握的核体,以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资源等问题的阐发,都具有廓清迷雾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艺的风格缺失和风格雷同等现象,已成为制约中国文艺发展繁荣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如果解不开,“中国文艺发展繁荣”的预设终将是一句空话。正因为如此,《讲话》关于风格所阐述的所有问题,都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讲话》所运作的这五个,的确是中国文艺生存发展的命脉所在,也是中国文艺走向复兴的唯一通道。《讲话》对百年新文学成功经验的精准概括和对失败教训的深度总结,以及对新世纪文学如何发展等问题的阐发,都是从这五个
出发的。只要我们重温中国文学史,就可发现,百年新文学的兴衰都与这五个
息息相关,而这五个
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缺少了任何一个
都会使这个有机整体受到破坏,从而使一个时代形不成文艺繁荣的峥嵘气象。这五个
指涉文艺创作最重要的五个环节。一个作家艺术家对“人民性”的认识,决定着其文学观的健康与否;对“大众化”的实践,决定着其素材资源的丰富与否;对“审美性”的把握,决定着其文艺作品美学价值的高低;对“民族化”的理解,决定着其文艺作品文化底蕴的深浅;对“风格化”的努力,决定着其文艺作品独立价值的有无。五个
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清晰的:一个作家艺术家只有形成了“人民性”的文学观,才可能进行“大众化”的实践;而“大众化”的实践,将真正加深对“民族化”的理解;作家艺术家形成了“人民性”的文学观,进行了“大众化”的实践,把握住了“民族化”的真谛,就可能大幅提升“审美性”价值,最终走向“风格化”。《讲话》对每个
的阐发,都能结合中国文艺的现实语境和历史诉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新命题。如果文艺工作者能在其今后的文艺活动中把握住这五个
,领会和探索《讲话》从这五个
所生发的新命题,新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实现,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不会是遥远的。
[1]方维保.人民性:危机中的重建之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6).
[2]王贵禄.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1).
[3]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党圣元.消费主义思潮对文艺创作的冲击及其应对[J].求是,2014,(18).
[6]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1分册[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果戈里.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M]∥果戈里,等.文学的战斗传统.满涛,译.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3.
[8]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M]∥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责任编辑艾小刚〕
When the Renaissance in New Age China will Arriv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Key Terms in Xi Jinping’s Talk on Literature and Art
Wang Guil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Xi Jinping’s talk centers on the main line of how to realize the renaissance in new age China,which focuses on the five key terms as“people’s character”,“popularity”,“aesthetic character”,“nationalization”,and “stylization”,elucidating the past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 in a systematic and in-depth way.The five key terms are indeed the lifeline of Chinese arts,and the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have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ese terms,carrying them into practice.
people’s character;popularity;aesthetic character;nationalization;stylization
I200
A
1671-1351(2015)04-0001-09
2015-04-29
王贵禄(1967-),男,甘肃秦安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1&ZD113)阶段性成果
①参阅“人民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凡在文中出现将一律简称《讲话》),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5/c22219-25842812.html。因《讲话》还未正式出版,本文所引《讲话》中的文字,均来源于此,下文将不再逐个注解。
②参阅“中国文化传媒网”所载报道《各地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http://www.ccdy.cn/wenhuabao/eb/ 201410/t20141017_10098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