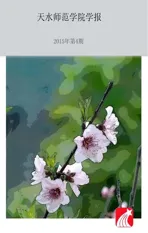那时的风景
——霍松林先生《文艺学概论》述论
2015-02-13王元忠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王元忠(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那时的风景
——霍松林先生《文艺学概论》述论
王元忠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文艺理论研究是霍松林学术研究之重要构成,《文艺学概论》是其文艺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该书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语境,也经历了极富意味的编写过程。立足于“历史的同情之立场”,可见该书编写在内容构成上的明显不足,但亦呈现出了开国人同类编著之先风、坚守文学本位、彰显时代特性和突出史论结合之正面特征,在中国当代文论史及其文艺理论教科书编写的历史中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霍松林;《文艺学概论》;时代语境;历史贡献
提及霍松林先生的学术业绩,一般人模糊的印象,总是更多集聚于他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但实际的情形似乎出乎了人们的所知,霍先生一生勤学广修,博观杂取,多区域多面向涉略,创获建树自然也便难以局限于一二方面。此中情况,其弟子汪聚应有过较为周全的描述:“霍松林先生是20~21世纪杰出的人文学者之一,也是享誉学界的著名学者、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其学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尤以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具特色和成就,其文艺创作诗、词、曲、赋、文兼擅,并与书法艺术兼通。”[1]
谈及其师学术之成就,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汪聚应特别强调了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他的强调极为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霍松林先生是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第一代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人,1951初受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的邀请,他从老家甘肃天水来到西安,在该校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任讲师,接受了原本并不擅长的文艺理论的教学任务,其时即着手进行《文艺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他专门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三年之后,即已复归自己更为熟悉的古典文学领域,改教“元明清文学”,但从实际的情况看,他对文艺理论的思考却并未中断,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其影响较深之论文和著作即有:《试论形象思维》(《新建设》1956年5月号)、《文艺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诗的形象及其他》(部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滹南诗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瓯北诗话〉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原诗〉、〈说诗啐语〉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文艺散论》(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文艺学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唐音阁论文集》(部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等。
相对而言,于霍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和诗词创作方面的成就,人们关注较多,言说也比较深入和多样,而对其文艺理论一域的建树,相关的研究和表述却不仅数量有限,认知也有待进一步深化。有感于业界用力用心的这种不平衡,立足于“历史的同情”之立场,本文以霍先生的《文艺学概论》为具体的分析对象,力求通过写作语境的还原、文本形成过程和内容的描述及其我们现在应有的批评三方面的工作,对霍先生文艺理论思考的基本情况做一具体的介绍。
一、《文艺学概论》的编写动机和语境
在霍松林诸多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之中,毫无疑问,《文艺学概论》说得上是霍松林先生专门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作为一本理论教科书,这本著作不仅写作时间早,集中了先生在建国初期对于文艺理论的系统思考,而且影响深远,其意义诚如一研究者所言:“《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在其前已有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不少人就曾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2]
为了能够对本书进行有效的解读,我们有必要首先追问,霍先生当时何以要编著《文艺学概论》一书?而这一追问,不用说自然关涉到了该书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语境。
从个体层面讲,《文艺学概论》一书的写作动机和语境了解似乎是较为清晰也容易的。1951年初,先生到西北大学来教书,最初承担的工作,就是教“文艺学”课。讲课不能没有教材,出于教学的需要,于是从接受工作伊始,他就开始了教材的编著,《文艺学概论》这本书就是其教材不断充实和完善的结果。但是,这种个体层面的清晰和容易,实质上只是一种浅表的了解,它并不能揭示著者写作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若于此不满足,将问题进一步推进,推想霍先生编著这本书之前,前人有没有编著过相关的文艺学教材?如果有,他为什么不用,又为什么要重新编写?超越个体一己的描述,我们则会发现一些更为有意义的时代背景因素。
诚然,无论中外,对于文艺的理论思考,自然都是“古已有之”的事,但文艺的理论思考发展而成“学”,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使在国外似乎也只是近现代才有的事情。这一情况在我国更为滞后,最早也就在民国初期,因为对于国外的学习,所以作为学科的“文艺学”才随着现代大学的诞生在高校教育中慢慢落下脚跟。自觉虽然不易,过程虽然缓慢,但是概念一旦引进,学科意识一经产生,配合学科建设的需求,文艺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自然也就成为了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应有且必然的内容。
从目前我们所能搜集的文献材料看,署名伦达加、1921年由广东师范学校贸易部出版的《文学理论》应该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文学理论教材。其后,因为大学教育的需要,参照相关的一些外国理论译书——如托尔斯泰《艺术论》、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特别是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和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两本译自日本的理论教材——的影响,及其外来理论本土内化过程中中国学人教材编著意识的不断增强,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在我国便渐渐有了一些成绩。从1920年代中期到建国之前,其中较有影响者即有: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11月初版的潘梓年的《文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11月初版的田汉的《文学概论》、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9月初版的夏丐尊的《文艺论ABC》、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1月初版的姜亮夫的《文学概论讲述》、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10月初版的马仲殊的《文学概论》、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3月初版的赵景深的《文学概论讲话》、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10月初版的顾仲彝的《文学概论》及上海生活书店1946 年8月初版的蔡仪的《文学论初步》,等等。
如此这般的编著,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共和国建立之后,新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不断加强,而以新的政治眼光看,此前主要参照西方价值理念和体现知识分子独立自我的价值追求的学院文艺学教材的编著,无疑是和新的政治形势、和党对文艺学建设的政治诉求相乖违或者冲突着的,所以,寻找新的理论表述,编著新的文艺理论教材,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也便成了当时高校文艺学学科建设包括文艺学教材编著必走的路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一段《文艺报》在1951年第五卷第二期所开设的“关于高等学校文艺学教学中的偏向问题”讨论中编辑部所提供的背景材料:
下面几封读者来信,谈到目前高等学校文艺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从这些来信里可以看出,现在有些高等学校,在文艺教育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有些人,口头上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和语录,而实际上对新的人民文艺采取轻视的态度,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不足。
情况非常清楚,立足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文艺报》的编辑们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存在的实质:形势变了,不少高校的文艺学教学却还重蹈旧辙,它们不仅脱离了新生活、新文艺发展的实际,而且也没有真正领会党的领导人对于文艺发展意见的实质,所以其为进步青年和政府相关的话语权力机构所不满,也便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旧的不行,但是新的改变又应该如何进行?具体到文艺学教科书的编写,没有新的文艺学教材,当时能够参照的一些著述,如巴人的《文学初步》等,又由于“著作时间太早,用处不大”,所以霍先生讲,自己只能通过“反复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拟出提纲”,然后再结合平生所学,“一节一节地编写讲义。教一遍,修改一遍。”1956年暑假后又参考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并且参照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制定的《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在1957年7月,交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3]
霍先生的解说基本讲清楚了他的《文艺学概论》一书编写的时代语境和理论资源:新的权力机构有着新的话语诉求,此前所进行的是有问题的,依据权威的说法,“都与新社会的飞跃发展和青年的需要极不相称。我们觉得,对于这一类错误观点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展开批评,是完全必要的。”[4]能够为新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样本又还没有产生,新旧无依,所以自己只能结合对领导人讲话的理解和自己学习所长,并且以新引进的苏联同仁的著述为参照,在不断的修改中成就自己的表述了。
二、《文艺学概论》的编写过程及内容构成
搞清楚了编著的动机和语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本书是怎样编成的?它由那些内容结构而成?
对于这本书的编写经过,在不同的地方,如《文艺学概论》的《后记》、《文艺学简论》的《后记》和《霍松林选集》(一)的《前言》之中,霍先生先后有过不少的交代,其中《文艺学简论》的《后记》中的交代最为周全和清楚。在这篇文章里,霍先生介绍说:
一九五三年,我在西安师范学院讲授“文学概论”的时候,编了一部讲义,第二年又改写了一遍。先被选为高等院校的交流讲义,接着又被选为函授教材,打印和铅印过好多次。因函索者甚众,供不应求,院领导便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前,我早已改教古典文学,“文学概论”课也已改为“文艺学概论”课,由胡主佑同志担任。胡同志参加了一九五六年暑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是《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修订者之一。于是我便在她的帮助下,按照《大纲》的要求,对原讲稿作了修改和补充,改名《文艺学概论》。
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文艺学概论》一书从编写到出版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先生自己编写和修改的阶段;一是胡主佑介入,先生在她的帮助下按照《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修改和补充的阶段。对于第一个阶段的编写和修改情况,因为原来的手稿无从得到,所以真实的情况很难具体确知,但是,依据上引的《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先生自己的介绍,读者大体还是可以了解到,讲稿的编写,其内容的构成,应该有如下的一些成份:一是“反复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拟出提纲。”解放之前,先生虽追求进步,但客观来讲,对于党的文艺政策其实了解并不是很多。解放后有这样的自觉,一方面自然是大势所趋,大环境变了,而且在党所领导下的大学教书,所教的课程又是最能体现党的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理论课,所以,与时俱进,先生对于党的领袖和文艺方面领导人讲话、意见的“反复学习”,也便清晰反映出了他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造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整体追求的一种体现。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建设初期执政党清明向上的精神面向,不仅使从旧时代走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适应外在的政治变化,自觉向政治权力靠近,通过自己的工作体现执政党的价值诉求;而且也使这些知识分子从内心里感觉到了一种精神人格的吸引,感觉到了一种自我改造的必要,所以虽然并不熟悉,但他们还是如霍先生一般通过勤奋的自我修习努力靠近着。二是“结合平生所学”。来西安师范学院讲授“文艺学”之前,霍先生平生所学亦是所长,更多为古典文学和文论。党的文艺理论也是文艺理论的一种,文艺发生、发展规律的探讨自然也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新的文艺学理论的建构,自然无法脱离中国文学具体的实践经验,它的诸多的理论阐释,是需要理论工作者给予具体经验的支撑的。此外,在谈到新文艺的建设之时,敏感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高度西方化和现实生存语境中西方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共和国的不友好态度,同时也是受自己文艺经验的内在规约,党的领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显现了某种民主倾向和民间取向的古典文艺作为新文艺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的意义。内在的相通和认知上的被接受,缘此,将领导人的意见和自己平生所学相结合,阐释新的意识形态的诉求,同时也充分发挥自己学术所长,这“戴着镣铐的跳舞”也便成了霍先生当时可以做也能够做的唯一选择。
而关于第二阶段的情况,亦即胡主佑先生介入之后的事情,根据霍先生的说明,与教材编写相关的意义事件似乎有这样两件:其一,就是1956年前后对于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参考。中国左翼文论一直有“向苏联学习”的传统,加之建国初期,我们尊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一切建设都以它的做法为参照,所以成熟的苏联理论一经引介,便往往成为中国学者争相仿照的摹本。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对于建国初期国内文艺学教材编写的影响便是极为典型的一个范例。该书1948年初版,是前苏联高等教育部批准使用的大学语言文学系及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教材。由于在此书初版之前,国内已有季莫菲耶夫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先后翻译出版,所以《文学原理》一书一俟翻译出版,[5]便在当时的中国文论界产生了极为重大和广泛的影响。受其影响,1950年代中期国内出版界形成了一股苏联文学理论教材翻译出版的热潮,其中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是其代表。关于这些教材的使用及相关的情况,有学者在仔细梳理之后总结说:“这些文艺理论教科书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地位,它们具有体系化、系统化的完整理论形式,是法定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为我国各高校普遍采用。当时条件较好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直接聘请前苏联专家来华授课,国内各高校尽可能把自己的文艺理论骨干教师送到北京面聆前苏联专家授课。作为一种先在的文艺理论范式,培养了整整一代新中国的理论人才,在中国各高校青年中广为传播,其影响巨大而深入。”“后来我国有了自己的文艺理论教科书,1957年先后初版了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冉欲达等4人的《文艺学概论》、刘衍文的《文学概论》以及李树谦和李景隆合著的《文学概论》共4种。除了在材料方面力图增加一些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的例证,它们和前苏联的几种文艺理论教科书在理论构架、概念范畴、价值标准到语言问题诸方面,都有极为明显的理论渊源关系。”[6]
其二则是胡主佑先生1956年暑假在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并具体参与《文艺学概论》一书修订的事宜。于此一点,霍先生曾说:“于是我便在她的帮助下,按照《大纲》的要求,对原讲稿作了修改和补充,改名《文艺学概论》。”霍先生原讲稿是怎样的,笔者当下无从具体知道,所以他的“对原讲稿作了修改和补充”之话,也很难具体予以坐实。但胡先生是霍先生夫人,此事对于《文艺学概论》一书的最后成稿,无疑关系至为密切。基于此,在1957年版的《文艺学概论》之《后记》一文中,霍先生曾更为详细地介绍说:“从一九五四年起,我专教古典文学,‘文学概论’课改由胡主佑同志担任。胡同志在几年来的教学过程中,对这部讲稿做了许多补充和修改,大大地提高了它的质量,丰富了它的内容。初版之前,又在胡同志的帮助下参考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一九六五年暑假在北京召开)修订的《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进行了适当的修改。胡同志参加了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是《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修订者之一。她在这一次的修改工作中尽了很大的力量。给予这些理由,我主张用我们俩人的名义初版;而胡同志坚决不肯,只好作罢。但应该声明,在这部稿子中,是包含着她的许多劳力的。”[7]不能直接举证进行具体说明,但借助于其他一些当事者如黄药眠、林焕平等的回忆,我们现在还是能够大体了解,在当时前苏联文艺学教科书纷纷出笼之际,大纲讨论会和后来制定的具体的《大纲》,其主要的话题内容和编写思路,更多还是来自于苏联学者编写经验和党的文艺政策及其相关领导人讲话精神的学习和借鉴。
比较分析《文艺学概论》一书的内容构成,受大环境的影响,可以发现它对于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前苏联学者文艺学教科书的参考和借鉴。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由三大部分构成:其一是文学概论,主要讲述文学的本质、特性和功能;其二是怎样分析文学作品,主要讲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主题、结构和情节,及文学语言的特征;其三是文学发展的过程,着重阐述作家的风格、流派、方法及文学的类型分析。虽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但是这些话题大都也出现在了霍先生的《文艺学概论》一书中,而且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前者在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具体话题的设置上对于后者给予了非常明晰的思路支持。不过,因为当时中国文坛所面临的具体的文学问题,加之著者自己对于文学自身问题的特别关注,所以,虽然在理论的体系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上霍先生的著书不如季氏等人的教科书,但是他的著书在内容的构成上无疑显现出了著者自己的一些理论追求。《文艺学概论》共分四编:第一编讲文艺的特质,包含六个具体的话题:文艺与生活、文艺的形象、典型、文艺的民族风格、文艺的人民性和文艺的社会作用;第二编讲文艺作品的构成,包含七个具体的话题:内容和形式、题材和主题、人物、环境(背景)、情节(故事)、结构和文学语言;第三编讲文学的种类,包含六个具体的话题:诗歌、戏剧、小说、电影、散文和人民口头创作;第四编讲创作方法,包含六个具体话题:对于创作方法的一般理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四编的构成,显现出了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紧扣文学,立足于文学本体;第二,着力寻求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三,联系文学的生存现状,凸显了文学思考中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内容。为此,有学者评论说:“《概论》之所以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根本原因,是能够立足文学本体,着力于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和揭示,理论和创作事件紧密结合,论述精当。”[8]
三、《文艺学概论》一书的历史贡献
于自己《文艺学概论》一书,1957年4月在书行将出版之际,霍先生即总结说:“这部稿子因为原来是讲课用的讲稿,所以基本上是吸取大家的研究成果‘编’成的,独抒己见的地方不多。同时,有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大家正在研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而我自己的理论水平又很低;所以不论在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的取舍上,或者在对某些问题提出的个人看法上,都免不了发生错误。”[7]时过境迁,2010年10月10卷本的《霍松林选集》编著已就,对于该书进行推介之时,霍先生再次反省,以为“因为是距今半个世纪以前出版的,当然有着不言而喻的历史局限性。”[9]前言以今日眼光看,实事求是地讲,这本文艺理论教科书也确乎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譬如政治性太强、话题设置的内在逻辑还不尽严密、一些内容阐释的理论纯度不够和对别人的观点的阐释多而独立自我的见解较为不足等,但是,对于历史的对象进行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还归著者当时写作的具体历史语境,许多学者还是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历史评价。资深文艺理论家张炯先生1989年在其《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到此书,即认为它“对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各方面的特征和规律,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浅出的论述,这对于指导广大作家和文艺爱好者进行创作,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10]浙江大学陈志明教授1988年更是连续在《人文杂志》上发表长文,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形象思维的强调、文学遗产的继承和诗歌理论的独特阐发五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文艺学概论》一书的理论价值,以为其“在‘左’的政治环境与文艺环境中,不只是一般地传播了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较为系统的文艺理论知识,而且由于它相当注意对文艺的某些特殊规律的探讨”,所以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历史作用。[2]
概括分析他人所述,并与同时代其他文艺学教科书进行比较,我个人以为,霍先生《文艺学概论》一书在当代中国文论教材史上的贡献或曰启示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开当代中国人文艺理论教科书著书之风气。霍先生该书的编写,早自1951年接受文学概论授课之始。建国初期,国内系统的文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教科书的编写还处在初步的探索时期,当时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只有巴人根据旧著《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改写的《文学论稿》,学者们讨论类似的问题所能参考的理论文本,也只是有限的几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和国内的一些学习材料,如周扬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以及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小译丛》。以群所翻译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虽然在1952年重新出版发行,但是由于论述较为粗疏,而且印刷数量有限,所以流播面并不广泛。相比较而言,前苏联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影响无疑要更为深远和广泛。这本书理论性强,话题建构系统,1953年12月其由平民出版社出版之时印刷量又非常之大,多达3万册,其后在1954年春至1955年夏之间,又因为季氏的学生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而得以进一步推广。在当时普遍的苏式理论和教科书遍布高校文艺理论讲坛之时,霍先生在参考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之下,编著并出版了建国之后最早的一部国人自己系统阐述文艺理论基本知识的文艺学教科书(1957年同年出版的文艺学教科书还有三本——刘衍文的《文学概论》、李树谦和李景隆的《文学概论》及冉欲达等四人的《文艺学概论》,但其写作时间都晚于霍先生的著作),其筚路蓝缕、开一时代中国学者编写自己的文艺理论著作风气的创始之功,是应该永志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历史的。
其二,坚持文学本体立场。前以述过,和当时前后相关的著书相比较,霍先生《文艺学概论》一书的编写更多地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自身及其规律关注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文艺学概论》一书的话题设置一域给予说明。《文艺学概论》共四编,以第一编文学和生活为例,在这一编中,围绕文学和生活关系的论述,霍先生首先说明了文学对象的特殊性,得出了“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的结论”,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作为文学形象高级形态的典型的审美特性。全编虽然也涉及到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党性”、“文学的人民性”和“文学的民族性”等意识形态极为分明的理论话题,但无论从论述的篇幅上,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上,我们都可以发现文学自身特性的论述始终是先生理论关注和思考的中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具体话题的论述得以生动去感知。举例如关于“文学对象的特殊性”话题的论述。在这一话题的论述中,为了说明文学对象的特殊性,霍先生先将“文学的对象”和“科学的对象”加以比较,通过具体的对比,得出文学的对象是“作为‘社会关系之总和’的活的具体的人,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具体的外貌特征和内心特征及其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联系和关系”,而后,为了更为清晰地说明这种特性,他又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论文进行分析比较,清晰且形象地让读者具体感知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充分理解了文学对象独自的存在特征。
其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唐诗人白居易曾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中的文章之概念,不单指文学作品,其实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写作,理论著述自然也在其中。翻阅霍先生的《文艺学概论》,无论话题的设置还是具体的论述,我们都能发现其与具体时代的紧密关系。话题方面,我们可以举第一编第二节关于“文学的形象”的论述为例。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方式,形象思维亦是文艺创作中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成为一个文学理论话题,原本是俄国一些理论家的功劳,1840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命题。1953年,前苏联理论家布罗夫在《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一文中对于此一命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形象思维不能解释艺术家在创作形象时的思维本质。但另一理论家尼古拉耶娃反驳了布罗夫的论断,她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一文中讲:“‘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定义的中心。”[11]其后,1956年,布罗夫出版了《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由此更趋激烈。“形象思维”这一概念1930年代即被引介到我国文坛,但当时人们并未将其上升到艺术特殊的思维方式层面去思考。1950年代中期,《文艺报》刊发了前苏联学者的数篇文章,如狄莫维埃夫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伯林斯基的《论所谓纯粹艺术问题》、索包列夫的《美学问题与苏联文学》等,从而将当时前苏联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引介过来,始才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此一话题的热烈讨论。霍先生《文艺学概论》第二节“文学的形象”三个话题的设置,“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和“与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斗争”,可以说都是对于当时国内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论争的直接呼应和成果总结。其第三个小话题“与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斗争”的论述,如“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还没有完全克服,有些作家,不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从固定的公式和概念出发进行创作。他们先设定一个主题思想的‘框框’,再往里面填塞人物;人物呢,也不是从生活中来的,而是‘正确’、‘进步’或‘落后’、‘反动’等等概念的图解。这样的作品,当然是没有生命的”[9]12-13等,更是直接指向当时一些作家的创作现实,显现出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特性。
其四,凸显了史论结合特征。理论本身是经验的提升,所以好的理论的表达,总是和具体的文学实践紧密结合的。在具体接手文学理论课的教授之前,霍先生所擅长的,原本就是古典文学历史和古典文论的讲授,《文艺学概论》在后期修改补充之时,先生又重归于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之中了。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关系的深刻理解,加之自身深厚的文学史修养有意无意的影响,所以在《文艺学概论》一书的编写和完善过程中,理论的思维和文学史经验相结合,也便使该书自然地显现出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特点。对于这种结合的说明,我们可以以该书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种类”中“神话”类型的介绍为例。在这一部分内容的编写中,先生先引述鲁迅、马克思和高尔基的说法,对神话做了一种基本的理论说明,而后又例举舜、禺、后羿、羲和和常仪等中国古代神话的材料,最后得出“这些‘神’的确是‘人们的教师和同事’。对‘神’的礼赞,实际上是表现了人对劳动的歌颂,对智慧的崇拜,对自己的生产成就的赞美。”[9]231文学史材料的引用,一方面印证了理论的界定,一方面也深化了理论的表述,史论结合,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
因为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化,不断地总结反省中意识到了《文艺学概论》一书存在的问题,从1978年秋季开始,结合理论界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考,霍松林先生对于该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删削和补充,并于198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文艺学简论》的修订本。修订本虽然对原书进行了不少的改动,删掉了一些距离文学较远的话题,增加了更多的古典文论和文学史知识内容,使书本的论述更为集中于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介绍,但是,精益求精,霍先生对于修订本却并不完全满意。书编订之后,他又在该书的《后记》一文做了两点声明:“第一,作为一本概论性质的书,是应该广泛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涉猎未广,做得很差,因而远远未能反映我国文艺理论界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这是十分抱愧的。第二,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要通过自己的头脑。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都很有限,所以不仅对某些问题提出的个人看法难免有错误,而且在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的取舍和运用上也难免有错误。”[12]后记霍先生的声明是对的,站在今天的学术水平特别是文艺理论教科书编订的水平上看,《文艺学概论》也罢,《文艺学简论》也罢,的确都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历史的对象历史地看,特别是细细咀嚼霍先生这种永不满足、永在路上的可贵的探索精神和自我反省意识,我觉得先生通过一本教科书所要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也便远远超过了教科书本身。
[1]汪聚应.霍松林先生的文化人格[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4).
[2]陈志明.霍松林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下[J].人文杂志,1988,(3).
[3]庆祝霍松林教授八秩华辰及从教六十周年筹备委员会.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62-63.
[4]《文艺报》编辑部.编辑部的话[N].文艺报,1951,(2).
[5]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M].查良铮,译.上海:平民书店,1953.
[6]代迅.前苏联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5).
[7]霍松林.文艺学概论·后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
[8]韩梅村.论霍松林文艺理论体系:上[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1).
[9]霍松林.霍松林选集:第1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10]张炯.毛泽东和新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9,(5).
[11]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8.
[12]霍松林.文艺学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艾小刚〕
The View at That Time——A Review on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by Huo Songlin
Wang Yuanz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Stud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covers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Huo Songlin’s academic researc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i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the coming of which has special times context,undergoing meaningful process.The work is based on“historical sympathy”,which displays its insufficiency in content construction,but also demonstrates its positive features as“creates a new style in its kind”,“sticks to literature standard”,“manifests era characteristics”,“highlights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y”,possessing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tudy and the related textbook compilation.
Huo Songlin;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times context;historical contribution
I06
A
1671-1351(2015)04-0027-07
2015-04-23
王元忠(1964-),男,甘肃甘谷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天水师范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