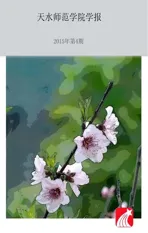萧统、萧绎“文学独立观”的历史定位
2015-02-13郭外岑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郭外岑(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萧统、萧绎“文学独立观”的历史定位
郭外岑
(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在我国文学史上,魏晋六朝虽不是个很显耀的时代,但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却因成就辉煌而屹立于世纪的巅峰。其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社会观念的大转变,给人们打开一个全新的思维和创造空间,他们破天荒地对文学自身存在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论阐释。于是许多前人从未接触过的文学创作问题,都被他们一一揭示出来,如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关系、艺术创作思维、艺术创作语言,以及感兴论、风骨论、通变论、声律论等。而文学独立论,也正是构成这一文论新思潮的重要一环,只是它的最后完成却落在萧氏兄弟身上。他们抛弃传统“言志”观,而以“缘情”和“绮靡”为文学创作两大新基点,把儒家经典、诸子散文、历史记传乃至应用杂文从文学中排除出去,终于确立文学独立存在的自身价值和地位。
萧统;萧绎;人的觉醒;文学的自觉;文学独立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魏晋六朝虽不是个很显耀的时代,甚至愈到后期则负面批评愈多,然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却是个成就斐然而雄踞世纪巅峰的时代。鲁迅曾将刘勰《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视为东西文论中的两座高峰,他曾这样评价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朱光潜更将我国中古之刘勰的《文心雕龙》与西方上古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近古之黑格尔的《美学》三书相提并论,称为“要学好美学需读懂三本书”。无论其在理论建树上的开创性、新颖性乃至体系的完整性,都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如若称之为“空前绝后”恐亦不为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其成就主要是哲学的而非文学的,然至秦汉则经学兴盛而哲学悉归沉寂矣。宋元明清则诗话词话一类著作盛行,但表面繁华却难掩理论的割裂及碎片化,感兴式的片言要语虽不乏精彩,若言其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者则不多。这个奇特的历史现象,虽经数百上千年的时间洗涤,却始终未能揭开真正谜底,乃至扑朔迷离而延宕至今。
其实它的谜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然而,文学的自觉则根源于“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又导源于魏晋玄学的兴盛,尤其是玄学家提出“自然”以抗衡“名数”的哲学理念。因此,我们的论述就先从魏晋玄学谈起。
一、背景:魏晋玄学的兴盛和“文学的自觉”
作为影响过整整一个时代的魏晋玄学,其兴起绝非仅是简单的哲学问题,更是一次社会思想的大解放运动。而且其出现也不是突然的孤立现象,源头可追溯到汉末名士的“清议”运动。班固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当时“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弗,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以至造成“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强大舆论压力。[2]而这种放言不讳,无所避忌,乃至公卿豪强亦闻之胆寒的“士人清议”,正是人们冲决封建专制统治和神学迷信思想所闪现的人性觉醒的理性光芒,无疑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人运动,在永康至熹平的十年(167~176)“党锢之祸”中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其所开启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觉醒之光,却深深影响着此后的建安和魏晋名士,终于建构起以“自然”抗衡作为封建统治根基“名教”的玄学哲学。早在朱穆《崇厚论》即说:“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即已把人性和名教对立起来,可谓首开魏晋玄学之先声。至建安时期,于是人们才捧出“自然”概念,以称扬一切逸出纲常名教的特行个性。如据《三国志》记载:郭嘉称颂曹操“公体性自然”(《郭嘉传》),杨修称扬曹植“体通性达,受之自然”(《陈思王传》),孟康称扬崔杜“禀自然之正性”(《崔杜传》)。[3]此后玄学家如何晏、夏侯玄、王弼等,即承此而建构起人性自然的“正始玄学”,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亦由此展开。
贯穿玄学始终的“自然”一词,实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万物的自然本性,尤其是人的自然本性;二是指客观大自然,尤其是山水自然。这是玄学前后两个阶段转化的关键,也是我国文学走向自觉及生成新质的根本动因。关于后者,因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故下面只就前段来谈。
正始玄学所说主要是前一重含义,如何晏《无名论》中说:“自然者,道也。”认为“自然”是天地运行的根本大法,而圣人法天,故治理国家亦应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这就叫“无为而治”。尤其是王弼在其《老子道德经注》一书中提出“因物自然”说,更使人性解放的时代思潮才真正得到哲学抽象和理论升华,从而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号召力。
首先,他认“自然”为物之“常性”,即天赋的自然本性。其次,本性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故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不能妄加改变的。若人为地去施加什么或改变什么,都只能使其“败之”“失之”,而最终丧失其本性。故因势利导,顺其天然,使之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或发挥,即会得到“自然之性”而成其“天全”。他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因为圣人体道,应法自然而为化,故只能保全万物之“性”而不是损其“性”,此之谓“因物自然”。故他又说:“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因物自然,不设不施,故不用关、楗、绳、约而不可开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由此可知,所谓“因物自然”者,其目的即在“不造不施”,亦即人为地(如礼法名数)去施加什么,改造什么,其实所宣扬的正是君主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然在其背后所高扬的则是个性解放的独立人格精神。
如果说正始玄家所说还只是抽象的理性思辨,并尽量调和“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那么,到了“高平陵政变”之后的竹林名士们,由于他们反对司马氏的假名教,与现实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于是更把“自然”和“名教”根本对立起来,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遂把人性解放的思潮推向高潮,甚至表现为畸形或变态。
嵇康《释私论》说:“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大人先生传》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欺愚诳拙”,“汝君子之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既然礼法名教是违背自然人性的,而世间一切贼害酷虐皆由此造成,那么作为名教偶像的儒家圣人,自然皆在扫荡之列:不只汤武周孔要“非”要“薄”,乃至上推亦要“轻贱唐尧而笑大禹”,而这一思潮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人性解放的张扬和自由精神的鼓吹。嵇康又在《难自然好学论》一文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吹。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总之,倡言从(纵)欲而为,任性而行,脱弃儒家名教的一切束缚,即“任自然而为化”,遂成为他们追求的人生终极目的。而竹林名士们所称赏的那些离经叛道之举,狂悖怪异之行,概可由此得到解释。故而我们称这个时代乃“人的觉醒”的时代。
然而,对人的个性的张扬,对人的情感生活的肯定,乃至对人“欲”的无限拔高,固然是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伴随而来的更是“文学的自觉”,因为他们才真正把文学当作“人学”来创作。我国文学发展至魏晋的一个鲜明特征,即由客体转向主体,由外在转向内在,由物质转向精神,故重个性、重才情、重风貌、重特行,而一改两汉人的重道德、重德行、重事功、重学问,于是使功利实用的文学一变而为真正抒情的文学,进而“缘情”的文学观才代替传统“言志”的文学观,被社会广泛接受。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从此“诗赋不必寓教训”“寓训勉”而取悦于人,因为文学本身自有其不朽的价值在,而我国文学也才有真正纯抒情诗的产生,世所称“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即是代表。
文学既已发生质的改变,自然会在敏感的理论批评中反映出来。对其进行新的定义、阐释、梳理乃至理论建构,便不只是他们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更是激发他们强烈兴趣和探索激情的强大动力,何况这还给他们提供了超越前人的理论创造空间,因而文学评论呈现一时的高度繁荣,遂成为历史必然。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曾慨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即已初露文学自觉之端倪,至陆机更首发其绪,一篇《文赋》不仅揭开“诗缘情而绮靡”的诗歌要旨,且对创作特征无论巨细均一一谈及,如感兴、想象、思维通塞、虚寂心态,乃至构思谋篇的技巧、语言、修辞等,都结合其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做了非常生动的具象描述,可谓开前人所未言。当然,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所批评:“陆赋巧而碎乱。”即偏于感性的经验描述,尚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而刘勰正是承其统绪才完成“体大而思精”的巨著《文心雕龙》的,终于把我国古代文论推上世纪的历史巅峰。他对《文赋》所提出和未提出的文学理论问题,都设专篇而详加论述,择其要者如: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关系(《原道》)、艺术思维(《神思》)、艺术语言(《情采》)、感兴论(《物色》)、风格论(《体性》)、风骨论(《风骨》)、声律论(《声律》)以及继承和创新(《通变》)、文学批评(《知音》)等,都以其博大精深之内涵,思虑周密之逻辑而超迈前古,成为后世文论之轨范。陆机首先推翻“诗言志”的陈说,钟嵘《诗品》则将汉代经学家郑玄、孔安国树立的“比兴”权威一并推翻,认为其实质都是为说解《诗经》之王功政教“大义”而设立的。钟嵘《诗品序》即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当是魏晋以后诗歌情感内容渐趋潜隐化含蓄化的精彩概括,而此后如唐代的“兴象”说,及成为论诗歌意境常言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似皆导源于此。并且,他还以当时兴起的新型文学审美观,评论自《古诗》至齐梁的历代重要诗人,写成我国第一部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诗人评论专集,同样开时代之先导。至于沈约、谢脁等提出的“永明声律”说,亦是文学“新变”的产物。尽管他们提出的“四声八病”,由于尚不够成熟而广受非议,但其意义远非止是单纯的声律问题,正如宗白华先生曾引艾里略所说:“创造一种形式并不是仅仅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韵律或节奏,而且也是这种韵律节奏的整个合适的内容的发觉。”[4]可知它同样是“文学的自觉”引发的文学质变的必然产物。总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理论氛围中,给文学以新定义并设定范围,使之从其他文体中分离独立出来,遂成为水到渠成之必然趋势,只是这个任务却最终落在萧氏兄弟身上。
二、正题:由“文”“笔”之辨到文学独立论
“文笔”之称当滥觞于汉代,而用“文”“笔”二字辨析文学和非文学,则是晋宋时期才出现的。不过由于尚缺少文学自觉理论的指导,却一度陷入难以自圆的尴尬,最终遂被“缘情绮靡”的新理念所取代,可知这也是文学观念发生巨变结出的时代硕果。
汉人喜将自己所作结集成册,故学界或认为“文”“笔”概念的提出,实与他们编辑文集时分类的需要密切相关。不过当时最常见的记载,却往往是按文体一一细列,如《后汉书·冯衍传》曰:“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崔骃传》曰:“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等。当然,“文”“笔”的称谓在汉时亦已出现,如《汉书·楼护传》有“谷子云笔札”之说,《论衡·趋奇》有“文笔不足类也”之言,而一般则只称文或文章、文词、文彩等,用法都相当杂乱,似乎内涵上是差别不大的概念。如《汉书·贾生传》曰:“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曰:“以博辩能属文,闻于郡中。”则此所谓“文”,当包括诗、书、博辩诸体均在内。而《司马相如叙传》曰:“文艳用寡,子虚乌有。”《扬雄叙传》曰:“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则此“文”便专指赋而言了。因此,这一时期之所谓“文”者,并非专指某一类文体,而是统一切文章言的,无论文笔、文章、文词等,似均是随文使用,并没有严格的“文”“笔”之区分。三国魏晋时的情况,亦复如是,如《魏志》王卫二刘傅传曰:“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蜀志·却正传》曰:“文词灿烂,有张蔡之风。”并载其《释讥》一篇而评曰:“依则先儒,假文见意,号曰《释讥》,其文继崔骃《达旨》。”然建安七子并非皆长于诗赋,而却正《释讥》正后来所谓“笔”者,故知“文采”“文词”之说,亦只是泛用,斯时亦尚未有文笔之分也。
然《晋书·蔡谟传》曰:“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又说:“文笔肇端,自此以降,厥名用彰矣。”这条材料却比较重要,因是说自此以后,“文笔”之说才广泛流传并使用起来。若验诸史实,则《晋书·习凿齿传》曰:“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袁宏伟》曰:“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其所传达的重要信息,是此时人们对“文”和“笔”的区分,似已萌生模糊意识。这也不奇怪,因为两晋究竟是文学观念开始转变并进入自觉的时期,借已有的“文”“笔”概念,把文学同其他文体区分开来,应是时代之必然。此外,如《晋书·成公绥传》曰:“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既然把诗赋和杂笔对举,则知诗赋已不同于“笔”,应该另有称谓,按传统认知当是“文”。又《抱朴子·外篇自序》曰:“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箴记三十卷。”则认为碑、颂、诗、赋为一类,而军书、檄移、章表、箴记为另一类,前者当是“文”,后者则属“笔”,区分亦很明显。而《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曰:“文章诗笔乃是佳事。”此承前人,“文章”当是总称,诗和笔则是分称。尤其是《晋书·乐广传》这段记载:
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意,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称名笔。[5]
潘岳代乐广所写者乃“让尹表”,故特称之为“名笔”,故知“笔”已成为指称某类文体的特有概念,说明认识上已渐清晰。而颜延之的这段话,似更成为当时人们在“文”“笔”认识上的一道分水岭。据《南史·颜延之传》载:“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可知时人对“文”“笔”的认识已非常清楚,不再存在模糊区。
不过,当时人们最常用的还是“诗”“笔”对举,偶尔也有“辞”“笔”对举者,也大概是因为诗歌是当时最主要文学形式的原因吧。如《南史·任昉传》曰:“任(昉)笔沈(约)诗。”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曰:“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梁书·庾肩吾传》载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曰:“诗既如此,笔亦如之。”《刘潜传》曰:“潜字孝仪,秘书监孝绰弟也。幼孤,兄弟相励勤学,并工属文。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然梁究竟已不同于前代,在几代皇室成员的倡导下,已完全进入文学独立自觉的探讨期,在沿用传统概念的同时,普遍还是以“文”“笔”对举。如《梁书·鲍泉传》即称其“兼有文笔”。《周书·刘璠传》亦称其“兼善文笔”。刘勰《文心雕龙》似已成定例,如《序志》曰“论文叙笔”;《章句》曰“裁文匠笔”;《时序》曰“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才略》曰“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等。而杜之伟《求解著作启》则曰:“或清文赡笔,或疆识嵇古。”总之,此时人们对“文笔”的辨识已基本固定,不过还没有严密的界定,故往往会造成不少麻烦。对“文”“笔”作定性分析者当首推刘勰,其《文心雕龙·总术》曰: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6]
应该说这是时人的普遍认识,然细究其说,似亦其来有自。如前引《抱朴子·外篇自序》所说“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箴记三十卷”;潘岳《西征赋》所说“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等,就都是以有韵或无韵分类的。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亦说:“手笔差异,文不拘韵故也。”凡此诸说,都可看作有韵无韵说之先导,只是尚未明确提出而已。戏剧性的一幕,是自文藻绮丽、对偶工整的骈体文兴起以后,却使这种区分陷入尴尬。因为不但原来所说“文”,且原来所说“笔”如章表奏议之类,如今皆可用骈体来写,于是有韵无韵的界限遂变得模糊,在创作实践指导上也失去意义,而造成混乱亦不可避免。然而,文学和非文学究竟是客观存在的,企望用新的理论对其重作定义和阐释,遂成为时代提出的迫切任务。
文学观念的改变,总是同传统及时俗观念纠结在一起进行的,并非断崖式的突变。因此对文学和非文学的辨识,也就很难脱离“文笔”说的影响。萧氏兄弟的情况正是这样,但实质却已发生微妙变化。萧统《文选序》言其编选取舍曰: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裁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术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7]
他把经、子、史、辩说之类,一概排除在文学范畴之外,却不是简单地以有韵或无韵等形式特征为根据,而是提出具体理由作具体分析,这是前人未曾言及的,故起点亦已不同。具体来说,周公孔子之径,乃是人伦行为的准则,不敢妄加议论,以切割剪裁选择某一篇,所以不取。而老、庄、管、孟之书,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自然也不录取。至如贤人、忠臣、谋夫、辩士之言,虽事美一时,流传千载,但那究竟不是结构完整的文学创作,也不录取。而用于记事的史传书记之类,重在“褒贬是非,纪别异同”,只是实录历史而非虚构的文学创作,同样不予录取。但有一种情况,若史传中的赞论述序,或综辑辞采,或错比文华,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故应属于文学。于是“沈思”“翰藻”二语,遂被后世认为乃萧氏衡量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从全篇来看,所谓“沈思”,当指精心的创作虚构;所谓“翰藻”,当指语言的美丽文采。他提出的这些理由,是否完全正确充足,今天看自然未必,但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却不可小觑,因为判断文学和非文学自此提上理论思考的层面。
当然,他的不足是明显的,即尚未接触到新型文学的本质。至梁元帝萧绎遂再进一步,以“缘情而绮靡”的新观念来论文,又打开一片新天地。其《金楼子·立言》曰: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徙,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徙,止于辞赋,则谓之徒。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篡,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斯之流,汎谓之笔。[7]
汉以前所谓“文”,已有“文学”和“文章”之分,故曰有二。今再细辨其作者,实可别为四:孔圣门徙如七十二贤人者,可称为“儒”。延至今日,则只成为老于章句的经师们,他们虽博穷子史,却不能通其理,故只能称“学”。至于阎篡、伯松之流,乃长于章表奏议而不善为诗,即今所说“笔”。而真正的“文”,便只有以屈宋和枚马为代表的骚赋一类作家了。显然,此乃是就作者的不同分类,当为区分文学和非文学预作铺垫,下面才转入具体分析: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用心。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辨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儒者,同样是“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故不论。重点所申谈者乃三种人:学者大都“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虽对经学研究有贡献,却不能与予作家之林。笔者,所长在章表奏议,故云“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即不是创造表达主体思想情感的完整篇章,只是一些“神其巧惠”的应用杂文而已,故亦不能与予作家之林。至于真正的“文”,他曾作前后两次说明:一曰“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顿看似难理解,不过在萧梁时期,从开国皇帝萧衍始,君臣上下都酷爱乐府民歌,群起拟作者甚夥,若武帝今存诗九十首,而拟乐府之作则多达五十四首,故“风谣”之说,当是在特定时代形成的文学观念,然其主旨则是强调“文”的抒情特征。二曰“绮縠纷披,宫征靡曼,情灵摇荡”。因为文学本质上是抒写人的思想感情的,故最大特征就是要有激荡心灵的感人力量。而要达到此目的,则必须讲求语言的声韵美和词彩美。前文已谈到,文学独立自觉的根本动因,是玄学兴起对人的主体情感的热情肯定和极力张扬,从而促使文学发生质的转变,由前期的“言志”转向后期的“缘情”,新的文学观亦由此确立,陆机的“缘情而绮靡”说首发其端,至萧氏兄弟又发辉得如此淋漓尽致,对后世自会产生深远影响。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质;文彩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情(原作理,据周振甫校改)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这是如今人所说讲“内容决定形式”吗?也可以这么看。但往更深一层想,则“辩丽本于情性”,当是说诗歌语言的趋于华美,是由其抒写情感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了的。故抒情的语言,便不同于一般叙述或说理的语言。对此,《诠赋》亦有明确说明:“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因为对诗人来说,他所观照之物,已非纯粹的自然生造之物,而是被情感化心灵化的物,自然“人化”了,人也“对象”化了,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其表达的语言也就不同于一般语言,求新求变求其“巧丽”,遂成为创作之必然,故今人特称作“艺术的语言”。当然,一切事物皆过犹而不及,如果雕饰过甚,陷入“淫丽而烦滥”,刘勰他们也是坚决反对的,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
三、余论:关于“广义文学”说之我见
可以想见,如果进入唐代后,文论家们能继六朝人对文学认识的新成就,而进行更深入广泛的探讨,我国古文论将取得何等辉煌的成绩!可是,唐代的“古文运动”家们,却连这点艰难的进步,也全盘否定了,岂非历史的倒退!他们针对“缘情绮靡”“义归藻翰”之说,以“雕饰”“淫丽”等为罪人武器,不仅否定萧氏等的文学独立论,进而还否定屈宋以来之整个中国文学传统,转以圣人经典和秦汉古文为号召,重新回到文、史、哲不分的浑沌文学观去。早期如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柳冕则更激进,凡文学皆斥为亡国之音,其《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一文指出:
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
将历代文学皆说成“名教”的反动,其范围之广,可谓无一遗漏,岂非是对魏晋以来文学自觉运动的全面否定。下引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中的这段则尤值得注意:
自成康殁,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为分二。不足者强而为文,则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文而知道,二者难兼!……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
所谓“文与教分为二”,大概是说此时之文学,已经从经、子、史中分离出来,有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故对儒家的王功政教传统造成严重冲击,在他们看来这即是“文”的衰微,因而“文学自觉”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此说可谓一语破的,把古文运动家们所以否定整个文学传统的思想动因,展示无遗。总之,他们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的眼光看“文”的,恰恰不是用文学家的眼光看待“文”,文学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然而,随着古文运动的真正领袖韩愈,柳宗元出,时代观念亦随之一变。韩柳都是对文学有深厚修养的人,故不再像他们的前辈如柳冕等,采取一概排斥乃至敌视的态度,而是又回到文、史、哲不分的浑沌文学观。这固然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如他们提出“文以明道”说,即认为道之行,必借文方可致远,道和文本非绝对对立关系。故韩愈《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又有《答尉迟生书》云:“体不备不可以为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文虽只是“明道”的工具,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而给文学腾挪出存在的空间。不过,这又恰恰抹煞了文学存在的个性特征,重又退回到汉代以前的浑沌文学观。他们谈“文”,总是上溯圣人经典、诸子散文、诗骚汉赋,下至魏晋古体、六代五言,眉毛胡子一把抓,根本没有文学和非文学的观念。韩愈《进学解》谈为文“博取”曰:
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柳宗元也一样。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古代典籍分为学文时可“本之”和可“参之”的两类,前者当讲个人品德修养,故必“本之”五经。但更值得注意者则是列入可“参之”的一类,因为这更关涉到“文”的创作:“参之縠梁氏以历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其《与杨京兆书》谈前人文章之可法者则曰:“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凡文、史、哲、论皆涵括其内,涉及范围更广。韩愈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今人多引以说文学创作,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论文概念),首言《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至“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接着说道:
其末也,庄周以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来尝绝也。
总之,在他们看来,似乎凡是用文字符号写作的东西,便都可涵括在“文”中,它们虽有高低之分,却无本质差异。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文学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植。由于韩柳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浑沌文学观遂成为毋庸置疑的社会共识,从此人们眼中只有文、史、哲浑然不分的“文”而没有独立自觉的文学,萧氏兄弟倡导的“文学独立”论遂被历史尘埃淹没,人们理解的中国文学史也不再是真正的文学史。
然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文学本来已有更加明确清晰的界定,可是在我国古典文学尤其文学史研究领域,却无视时代进步而要重拾唐宋古文运动家的浑沌文学观,并创造出一个“广义文学”的概念来为之曲护呢?是的,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也会有重叠,但不能因此打破界限而无限延展,把诸如哲学、历史乃至应用杂文之类的“文”都包括进来。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有规律可寻的,这正是文学史写作之要义所在,如果把根本不同性质的东西(文学和非文学)人为地杂凑于一篮,那还有什么规律可言。而所谓“文学史”恐怕只能是某朝某代有哪些作家作品的现象罗列。何况,如果我们也依样画瓢,创造一个什么“广义历史”或“广义哲学”,因文学反映时代变迁,便说成历史;或反映社会思潮,便说成哲学,那又该置文学于何地呢?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萧统.文选序[C]∥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安建军〕
Historical Localization of Xiao Tong and Xiao Yi’s“Liberation of Literature”
Guo Waicen
(College of Arts,Lanzhou Liberal Arts College,Lanzhou Gansu730030,China)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stand high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critic,during which social ideas took great changes and a totally new space for thought and creation was opened.The literature’s own existence was given new interpretations.“Liberation of literature”is an important one among these new ideas,which fell on Xiao Tong and Xiao Yi.They held“poetry out of affection”and“beautiful and intricate”for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excluding Confucian classics,Zhuzi proses,history and biography and essays,thus establishing the value and position of liberation of literature.
Xiao Tong;Xiao Yi;awakening of man;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liberation of literature
I206.09
A
1671-1351(2015)04-0054-07
2015-03-28
郭外岑(1935-),男,甘肃武山人,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