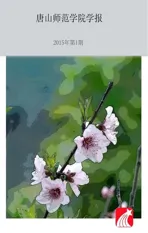困境中的人性张力
—— 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空间意识
2015-02-13林业锦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7
林业锦(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困境中的人性张力
—— 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空间意识
林业锦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7)
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隐含强烈的空间意识,不仅呈现了张大民家外表逼仄混乱而逻辑严密“圆形系统”外在居住空间对内在的个体心理空间的规训、压抑,还暗含了个体自由生命本能在苦难的生存现实面前的强韧和坚守,折射出个体在面对极限环境时人性及小说艺术的巨大张力,进而透射刘恒对逼仄的城市生存空间的反思以及在苦难包裹下顽强、坚韧人性的认同。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圆形空间;隐形权力空间;个体心理空间
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写实”小说中坚力量的刘恒,其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1997年发表时,并未引起当代文坛的极大关注。直至 1998年,冯巩将小说的电影版权买断,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并凭此获得“第七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小说才“浮出历史地表”,正式带给当代文坛不小的震惊,而小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随之也荣获“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与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相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一样,描写都市居住空间的狭窄与逼仄,描摹底层小市民的灰色苦难人生,从而揭示外在的生存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的扭曲与压抑,以及个体在面对极限环境时坚忍和乐观,向内进入到内心深处去寻找精神空间和向外去寻找具体的生存空间。小说讲述了生活在北京逼仄小胡同里的张大民一家对苦难生活坚忍和乐观,它以一种调侃诙谐的语言将张大民一家的苦难生活娓娓道来,凸显了在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中个体顽强的生命本能的巨大张力。
一、逼仄的居住空间:生存之艰
纵观“新写实”小说,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底层市民生存空间的关注。池莉的《烦恼人生》描摹的是轧钢厂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遭际:逼仄、局促的家庭住房且面临搬迁的困境;刘震云《一地鸡毛》小林在家庭和单位间的双重生活遭际,狭小的居住空间以及长期分不到房子使他的家庭面临解体的命运。如果说池莉《烦恼人生》和刘震云《一地鸡毛》呈现的是城市市民在狭小逼仄的居住空间下的危机和焦虑,那么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将这种焦虑和危机感推向了绝望的边缘。
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描写了张大民一家六口生活在一个仅有20来平米的“汉堡包”形状的住房空间。这个“汉堡包”空间外表看似杂乱无章,却有逻辑严密的结构分层。这个20来平米的居住空间总共分为四层,第一层是院墙、院门和院子,院门极其简陋,是某大礼堂椅背夹板随意钉制而成,甚至连椅子序号都清晰可辨。院子是由一个只有四平米的坑底构成,杂乱地堆放着蜂窝煤、旧自行车、大蒜、油漆桶……;“汉堡包”空间结构的第二层是“酱肘子”似的厨房,这是张大民一家赖以生存的饮食供应地,正如刘恒所说的“这是汉堡包出油的地方”。第三、第四层分别是菜窖般的只有10.5平米的客厅加主卧室和6平米的里屋,这不足 20平米的客厅加卧室就是张大民一家六口赖以存活的休息场所。这个内容杂乱却结构分明的四层式“汉堡包”居住空间背后有其重要的文化隐喻,它不仅刻画了特定时代城市底层市民居住环境逼仄、窘迫的普遍性,而且揭示了这种特定地理空间下人物的或顽强、坚忍或扭曲、变形的主体心理。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这个多层的汉堡包掉在地上,掉在城市的灰尘里……”[1]刘恒将张大民一家比喻为一个“汉堡包”形状有其深刻的现实指向意义,实际上他本人就是这种居住空间的一个载体。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父母住着两间房,不到20平方米,……里里外外塞了十几个人。……我们盖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后来我就在里面幸福的结婚了。”[2]这是作家刘恒的真实经历,也是特定时代城市市民的普遍生存状况,正是有了亲身亲历的生活材料,才催生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如此生活原生态的文本。正如刘恒自述,“生活经历最重要的是童年、少年这一段,印象非常深;包括许多成年时的经历有时也是以童年、少年经历为背景才显示出某种意义来,……童年、少年时候的经历对创作的升华有很大作用。”[3]从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写的大多是与自身有关的逼仄的生存状况,但刘恒又不单单在写自己,他在描摹和审视自身的同时,将视野上从个体空间上升到社会现实空间的高度,通过描摹个人对狭窄、逼仄的生存空间焦虑与挣扎的现状,从而表达、呼吁人们对城市底层民众居住空间的关注与改善,显示一个有担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时代与现实的关注。
二、坚韧的个体心理空间:绝望之反抗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将张大民一家六口置于一个“汉堡包”式的空间熔炉里,这个结构分层错落有致的地理空间,凭借着一系列特定的地域与文化观念,生产出与之相对的个体与文化空间。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言,“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人们的文化观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4]可以看出,张大民家“汉堡包”居住空间里生产出性格坚韧的个体心理空间。如果说这个“汉堡包”式的圆形空间的逼仄、狭窄让人难以承受,那么居住空间里个人隐私性的缺失则将大民一家推到了绝望的边缘。由于住房空间的局促和狭窄,等到大民结婚时,大民母亲被迫睡在两个箱子拼成的简陋单人床,大民夫妇和三民夫妇也荒诞地住到了只有数平方米的房间。由此一来,张大民家的隐私性几乎被逼仄的空间吞噬殆尽。由于大民夫妇和三民夫妇同住一个无墙隔开的透明空间,不但日常行为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夫妻隐私也暴露无遗,这充分体现在大民、三民夫妇行房事时,大民夫妇羞于空间感的无阻隔以及对隐私的尊重,被迫压抑默不作声;然而三民夫妇恰好相反,他们毫无保留的嘶吼彻底惹恼了大民,最终导致兄弟关系的破裂。从大民三民夫妇关系的破裂中我们不难发现居住空间的狭窄逼仄,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看清的一个事实是,这种个人隐私性的被腐蚀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隐喻:逼仄的地理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的侵吞。大民夫妇对隐私性的羞愧和对于快感的抑制与承受,其实是个体对本能欲望压抑的表征;而三民夫妇对快感的放纵则是个体心理空间反抗社会空间压抑人性的呈现。
如果说大民、三民夫妇隐私性的丧失是社会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侵蚀的表征,是现代文明对人的自由生命本能规训的结果,那么大民围绕石榴树砌墙造屋的举动则将这种社会空间压抑、规训个体心理空间的隐喻推向了顶峰。逼仄的居住空间已然扭曲了大民个体的心理、生理和交往等正常行为,他不得不向外进一步寻找空间谋求基本的立足生存,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一颗石榴树周围。为了围绕石榴树砌墙造屋,他不惜玩命和邻居抢夺那点可怜的地理空间,以致被邻居打破了头,终于用鲜血换来了些许空间,围绕石榴树砌起了几平米的房子。这种用鲜血和尊严换来的私人空间看来荒诞,却有其深层的合理性。从大民这个抢占空间的举动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但被迫和自己同处底层的群体抢夺空间,更荒诞的是和自然界抢夺生存空间。石榴树是自然个体存在的表征,而大民却与其抢夺地盘,甚至将树封闭在屋里。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整个文本包涵了四重隐形的空间结构。首先是社会这个外在的空间结构;其次是大民家逼仄的居住空间结构;接着是大民砌起的石榴树空间;最后是内在的大民个体心理空间结构。细察这四重隐形的空间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这是隐形的外在社会空间对内在的个体心理空间的规训、监视和挤压。
张大民家“汉堡包”式的逻辑严密的隐形空间结构,隐含的是外在的社会权力空间(现代文明)对内在的个体心理空间的监视规整。透过这个结构分层严密的圆形空间结构,我们可以窥见福柯笔下的“现代微型权力结构”,福柯从监狱的演变和结构中发现了一套隐形的权力话语的生产机制是一个“全景敞式建筑”的圆形结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为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5,p224]。这个圆形空间系统“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的安排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既是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本身的载体”[5,p226]。这就使得“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5,p227]。福柯从现代监狱的圆形结构中发现,现代文明的进程既促进了解放,但也加剧了规训、监视和压抑。反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们对外在逼仄居住空间的争夺和内在心理空间挣扎,何尝不是在四层圆形空间的包裹下被规训、监视和压抑的结果,只不过这个“圆形结构空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展开,具体表现在张大民个人身上罢了。正如福柯指出的,“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5,p216]。张大民家“汉堡包”式圆形空间结构是如此的狭窄和逼仄,以致于个体自我隐私性丧失殆尽,每个个体在被对方“监视”的同时,也扮演着“监视”者角色,共同成为现代文明这种隐形权力的载体,同时打上了强烈的“张大民”式个人化烙印。
这种隐形权力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的规训和压抑在张家其他成员身上表现得更见力度。二民为了逃离这个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空间,而屈身远嫁山西农民;五民放弃北京农大而考西北农大,也是为了逃离这个空间,在临走前哭着诉说:“我受够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业了我上内蒙,上新疆,……我找个宽敞的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你们杀了我我也不会去了。”[1,p224]和大民的用鲜血和暴力以及跟石榴树争夺生存空间相比,五民身上呈现出来的个体自由生命本能被隐形社会空间的压抑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轻聪慧的四民的死亡和老母亲的痴呆、神秘失踪,社会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的规训和压抑达到了极致。张家这个圆形空间及其成员是外在的社会权力空间规训、压抑的产物,在这种隐形的权力压制下,四民和张母沦为了牺牲品,而张大民却显出了承受苦难的顽强和坚忍,正是这种顽强的韧性精神,将中国传统国民性的可贵之处鲜活地呈现出来,同时也起着反抗社会隐形权力结构的作用。正如刘恒所言:“我觉得中国国民性的最大优点确实是韧性,为了生存他们能够承受旁人不能承受的痛苦。……他(张大民)超越了常人承受痛苦的能力。一个人再渺小,有了这种能力就什么都不怕了。”[6]而这正是作者刘恒在小说里反思的一个事实,在社会权力空间的挤压下,个体自我要么扭曲变形,要么顽强、坚忍地去承受和反抗,刘恒选择了后者,与其说是悲观色彩,不如说积极的韧性战斗精神。这是小说文本和作者刘恒的独特和深刻之处。
三、小结
总之,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隐含强烈的空间意识,不仅呈现了逼仄狭窄的外在居住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人的规训、压抑,还暗含了个体自由生命本能在苦难的生存现实面前的强韧和坚守,折射出个体在面对极限环境时人性的巨大张力。小说文本在呈现外在隐形的社会权力空间对内在个体心理空间规训、监视和压抑的同时,也通过个体对苦难生存的追求、坚守来反抗隐形权力空间,从而显示出巨大的人性及艺术张力。
[1] 刘恒.刘恒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15-224.
[2] 刘恒.乱弹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23.
[3] 林舟.人生的逼视与抚摸——刘恒访谈录[J].花城,1997(4): 114-120.
[4] 包亚明.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
[5] 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 张英.人性的守望者——刘恒访谈录[J].北京文学,2000(2): 84-93.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The Tension of Human Nature in Plight: on the “Gossip Happy Life” Spatial Awareness
LIN Ye-j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7, China)
The novel Gossip Happy Life implies a strong spatial awareness, which not only presents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iscipline and depression from the external living space of the chaos outlook of Zhang Damin’s to the internal space of “circular system”, also implies individual freedom life instinct to survive in the face of suffering and stick to tough reality. A refl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eat art of the novel strai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face of extreme environments, and thus the transmission Liu Heng cramped urban living space for reflection as well as in suffering parcel tenacious, tough human identity.
Gossip Happy Life; circular space; invisible power spac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pace
I206.7
A
1009-9115(2015)01-0054-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1.014
2014-07-31
林业锦(1985-),男,瑶族,广西平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