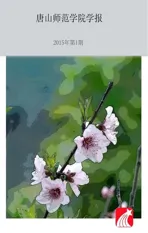论语言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2015-02-13赵泽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北京100081
赵泽琳(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北京 100081)
论语言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赵泽琳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北京100081)
语言人类学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自人类学发端开始,在人类学视野下的语言研究就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而语言学的研究亦从未离开过人类学关乎文化命题的讨论。语言人类学就是在两个学科的交错互动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定位,即研究语言、文化及人类社会的关系。
语言人类学;学科发展;学科定位;文化命题
一、学科界定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交叉学科,有些学者在进行学科定位时,将其定义为边缘交叉学科。在北美学界又常常被叫做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而欧洲大陆则更倾向于称其为语言民族学(linguistic enthnology)或民族语言学(enthnological linguistics),“这跟欧洲学者爱用‘民族学’,不爱用‘人类学’是一脉相承的”[1,p3-4]。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的术语争论点在于其归属是人类学还是语言学,学界多同意将语言人类学归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并不再争论命题术语的问题,海姆斯(Heymes D.)在进行学术定义时同时使用“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两种说法[2,p2],“杜然提(Duranti)认为,想要区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就要承担重写历史的风险。”[2,p1-2]
在中国学界,由于南北人类学、民族学界不同的学术渊源也滋生了语言人类学和语言民族学两种定义,并时常与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进行难解难分的学科界定。何俊芳在其《语言人类学教程》中讨论了语言人类学同“文化语言学”“语言民族学”“社会语言学”三者的关系和其各自的研究侧重,得出的结论是“几个学科之间有许多重合,它们之间很难划清界限”[3,p18]。而这种局面也并非中国学界独有,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帕克斯(Douglas R. Parks)在总结美国语言人类学学科发展时也提到:
目前许多用以代指跨人类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工作的非标准术语,比如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甚至社会语言学,其存在使我们目前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更加复杂。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术语意义相近,可以替换使用,但另外一些人却试图把他们区分开,让不同术语指代从不同角度入手的某一种文化语言研究。但是即使我们努力去区分不同术语,学者们也很难就其用法达成一致。[4]
其实,学科的定义取决于各国的学术渊源和学者个人的学术倚重,正如纳日碧力戈所言“其定位取决于学者或学者群,并无绝对界限”[2,p1]。不论是命名为语言人类学、社会语言学还是文化语言学,都是观照语言、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二、学科溯源
18世纪,已经有学者进行语言与人类文化的思考,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横向比较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人类的自主性,提出人类的思维与语言具有密切联系。纵向考察了人类的发展,强调人类的历史性,提出了语言是人类历史纽带的观点[5]。19世纪,美国学术界开始对印第安语展开比较研究,与此同时,随着对印第安部落田野调查的开展,应运而生的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正式登上学术舞台。人类学家始终注重语言同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是人类学的诞生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推动了人类学的进程。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在其作品《古代社会》一书中就已经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与语言的关系[3,p12],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其著作《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中探讨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制度也是从当地语言入手的。随后的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弟子为美国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著作《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手册》更被后人称为“近乎一部现代美国语言人类学的奠基作品”[6,p16-17],他还在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目前北美人类学的学科构架依旧沿袭了由博厄斯确定的人类学研究的四大分支——生物或体质人类学(biological/phys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以及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他的学生萨皮尔(E. Sapir)走上了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萨皮尔和他的弟子沃尔夫(B. L. Whorf)在调查印第安人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pair-Whorf hypothesis),又被称为语言相对论(lnguistic relativity),这一假说认为语言决定着持有这一语言者的思维,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讨论成为语言人类学经久不衰的论题。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被认为是对前辈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 von Humboldt)“思想和语言互相依存”语言观的进一步发挥[2,p11],在洪堡特看来,“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民的个性的表现,都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语言的外部形式是由每种具体语言的内部形式规定的,人内部形式作为声音和概念的中介,是因民族而异的。它反映着一个民族对于周围世界的理解”[7]。在洪堡特的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中,社会、文化、语言往往被放在一起讨论,不容易区分出什么是社会语言学的,什么是人类语言学的,什么又是纯语言学的。总的来看,他的研究大概可以叫做“社会文化—人类语言学”[8]。欧洲民族学的舞台上,伦敦大学的弗斯(J.R. Firth)带动形成了“伦敦学派”,他们把语言看成是“社会过程”,试图把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语言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的社会性质[9]。弗斯深受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 Malinowski)的影响。索绪尔区分了言语和语言,并由于语言与言语的对立,进一步认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对立。他创造语言价值理论,将语言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强调田野调查和语言形式的意义表达。法国学术界深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梅耶(A. Meillet)为代表的法国语言学界认为语言是社会事实,“唯一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变化的变量就是社会事实,语言变异只不过是社会变异的结果。”[3,p14]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形成了结构主义人类学派。而结构主义直接影响了认知人类学的产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乔姆斯基(Noma Chomsky)的转换语法掀起了语言学界的革命,转化语法代替结构主义成为语言学中的主要范式。70年代以来,为濒临语言考证和调查成为当代学界的新热潮。
三、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语言的研究要从先秦的训诂和魏晋的音韵算起。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兴起,则是受到20世纪西方科学理论传入的影响。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端于1950年罗常培先生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该书从词语含义的变化论证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建起一个桥梁”[10],“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专著”[1,p5],“堪称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开山之作”[3,p19]。然而直到 35年后,“语言人类学”才被李如龙定义。虽然中国学界正式提出语言人类学仅不到30年,但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要从20世纪初期算起。有学者将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分为草创期(20世纪上半叶)和发展期(20世纪下半叶)两个阶段[1,p4-9],但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一个滞缓期,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受政治环境影响,诸多学科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上半叶,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之争的学术背景下,有人提出要结合人类社会文化环境来研究语言。梁启超在《国文语原解前记》中谈到,通过语言文字可以考察古代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演变[11]。这一时期张世禄、王国维、芮逸夫等学者从文字研究的角度研究古代社会文化,林耀华等学者通过语言研究民族文化。罗常培率先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论证了语言分类对民族分类的意义,并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一主题。林惠祥首次阐明“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语言”的目的和范围[12],提出四个主要论题[1,p4-9;3,p18]:
(1)从文化整体来讨论语言的功用;(2)特别注重语言文字中的拟势语;(3)利用语言来讨论民族关系;(4)借助语言文字证据来推论民族历史状况。
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其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是重要内容,其调查成果最终集合成“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这次普查的结果主要用于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的谱系问题,以便进行民族识别。这一时期虽然语言人类学由于重视不够没有得到长足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语言人类学和语言民族学积累了宝贵资料,也锻炼了一批兼擅田野调查和理论整理的学者。随着“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民族学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也一度停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和学术发展的小高潮,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作为其重要分支的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语言人类学”于1985年被厦门大学的李如龙正式提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并提出了学科的六个研究论题,比林惠祥在30年代提出的四大论题范围更广、更深刻[3,p21]:
(1)语言起源;(2)语言与思维;(3)人类群体和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4)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5)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6)语言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1988年厦门大学首开“语言人类学”课程。1993年出版了邓晓华的《人类文化语言学》,并推为第一本学科教材。1999年朱文俊出版译著《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使外文的理论前沿资料进入学科视野。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界都有学者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研究主题涉及语言的使用、语言与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接触及方言研究、语言与文化理论、宗教语言等。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改变人类生活方式,语言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新兴词、沟通方式及网络交际空间等问题。
四、余论
纵观语言人类学的发展,交叉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其学科定位具有模糊的边界。不论是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语言民族学、文化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其研究命题和可追溯的学术源流都有重叠,研究队伍也分布在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学术机构中,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试图寻找语言、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关系或者揭开这种关系之谜的密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人类学也正在拓宽研究的视野,与人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共同发展、相互依存。
[1] 周庆生.中国语言人类学百年文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2] 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3] 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4] 道格拉斯·帕克斯.路静,译.人类语言学的历史,传统,定位和新进展[J].满语研究,2005(1):72-82.
[5] 庞文薇.人与语言——赫尔德语言哲学思想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36-39
[6]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6-17.
[7]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44.
[8] 姚小平.洪堡特与人类语言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 116-118.
[9]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文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285.
[10]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2.
[11]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1990:62.
[12]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刷出版社,1991:349-350.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On the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ZHAO Ze-lin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chool,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f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study of languag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s ever since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has always been under the discussion of anthropology.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which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human society was establishing its own disciplinary positio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ubjects gradually.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subject orientation; cultural propostion
C95-05
A
1009-9115(2015)01-0026-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1.007
2014-10-18
赵泽琳(1988-),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