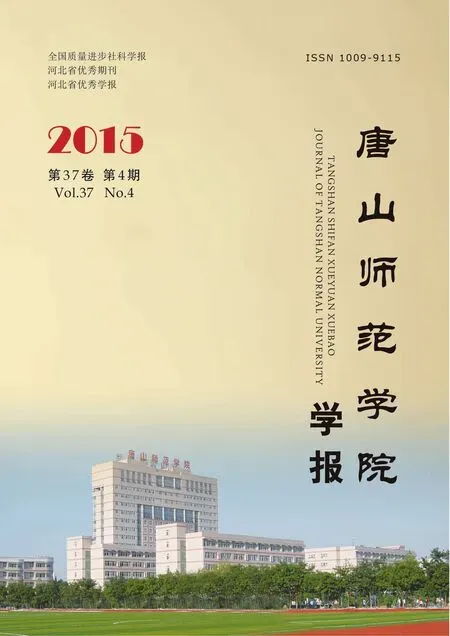对“招夫养夫”文学现象的解读—— 以《春桃》《天狗》和《远村》为例
2015-02-13金转
金 转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对“招夫养夫”文学现象的解读
—— 以《春桃》《天狗》和《远村》为例
金 转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招夫养夫是一个充满人生困境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人看重其中的文学价值,像许地山、贾平凹和郑义他们各取所需,许地山以宗教式的仁慈给予困境中的春桃们安宁的家园;贾平凹以深刻的眼光、写实的手法,挖掘天狗们的人性和灵魂的深处;郑义却用温情的叙事谱写了一首“远村”的山歌,道出了万牛们的哀歌。这种招夫养夫的文学现象,都是在传递一种生存困境和情感苦楚,也彰显了书写的意义。
关键词:招夫养夫;人生困境;人文关怀
自古以来,在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童养媳”,这一形象最先出现在元杂剧《窦娥冤》中,窦娥悲惨的童养媳地位为这一形象开了先河,随后关于“童养媳”的文学形象逐渐出现在许多作品中,如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沈从文的《萧萧》中的萧萧和王安忆小说《小鲍庄》中的讨饭女孩小翠等等。除了“童养媳”这一文学形象外,还有一类就是“典妻”,这一文学形象既是一种地方风俗的表现,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类形象最具典型代表的是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无论是“童养媳”还是“典妻”,这些都是关于女性在特定时代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还有一类关于男性家庭身份的文学现象就是“招夫养夫”①。
所谓的“招夫养夫”,是指当一名男子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他的妻子可以招一名壮年男子进家,同宿同作,承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这是我国某些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在现实生活中,“招夫养夫”这一现象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至今依然存在。在文学作品中,像许地山的《春桃》、贾平凹的《天狗》和郑义的《远村》都出现了“招夫养夫”这一文学现象。在表面上看,这既是一种习俗,又是作者的一种现实主义情怀。但无论是许地山的《春桃》、贾平凹的《天狗》,还是郑义的《远村》,都反映了一种生存困境,这一特殊的婚姻形式牵连着他们的情感天地,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挣扎与苦闷。
一、乱世中“不得已”的选择
许地山的《春桃》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春桃与丈夫李茂在举行婚礼的当晚便被战乱冲散,并四五年杳无音讯,春桃为了生存,辗转流落到北京,做起了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与难友刘向高同居,正当两人过着“非法”的同居生活时,李茂闯了进来。李茂因为战争而失去了双腿,在乞讨的街上遇到了春桃,春桃热情地将其带回了租屋。这时,三人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也面临着新的选择。同时,他们各自的内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茂虽然还是春桃名义上的丈夫,但他深知自己早已没有这个资格,无奈只好委曲求全。刘向高面对这样的局面,内心十分痛苦,通过几番挣扎,还是割舍不下那份对春桃的牵挂,回到了春桃的身边。
春桃在这场伦理冲突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因为她之所以把叫化子李茂接回家中,是出于同情,也是出于她对乱世的一种同情。春桃对于她和李茂之间的过去已经放下,但在同情的驱使下,当李茂将他俩的龙凤帖还给她的时候,她依然说:“我还是你媳妇。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人吗?”[1]春桃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乡下人,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在她的字典里她把仁义与道德看得很重。她完全可以不管李茂的死活,毕竟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何况她心里早已装上了刘向高,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感情。而在刘向高心里,他很不乐意和别人一起拥有春桃,而且他所拥有的全部也只有春桃,没有了春桃,他找不到目标,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婚姻契约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但春桃爱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也使他的地位更加牢固。虽然他不能容忍哪怕是名义上的一妻二夫,但他也忍受不了爱的饥渴,最终依靠理智战胜心理的不平。春桃之所以能够承受两个“丈夫”带给她的压力,是因为“在艰难困苦中,劳动者只能相濡以沫,为了维持最低底层的生存,不得不打破文明层次的伦理传统”[2]。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两男一女”畸形家庭形式存在的社会原因。春桃顶住了李茂的自杀、刘向高的出走,为了尽妻子的义务和责任,她最终不得不默认她是李茂和刘向高口中的“你是咱们的媳妇”这样的事实,只有这样,三个人通过经营捡破烂的活计维持生活,获得了乱世中的平静。在这时,这种“一妻二夫”的家庭模式已不再是精神层次的追求,只不过是在战乱年代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罢了。
许地山通过对春桃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所陷入的生存困境,同时也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春桃这一女性形象。“作品中‘两男一女’的伦理模式,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都还可以看到某些春桃形象的复制品。”[2]许地山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笔触,为他笔下的弱小人物塑造一个虚幻的家园,尽力不去触痛在这个家园里避难的可怜人,用人道主义的情怀为他们寻求动乱中的安宁。相对于乱世,三角模式下的和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因而,他们宁愿用仅有的余温相互取暖,也不愿苟活在世俗的非议中。
二、面对现实,小人物的人情冷暖
贾平凹的《天狗》是以堡子村的李正、李正的女人和李正的徒弟天狗之间的关系与平凡的生活琐事来展开故事的。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来体现民间生活的琐碎,表面没有什么特别喝彩的地方,但作者运用他敏锐的目光将笔锋转入新的亮点处:招夫养夫。
李正有一手过硬的打井的技术,在堡子村日子过得滋润。但是,李正存有私心,他拒绝收徒把祖传的秘法传人,害怕懂得这一技术的人变多而断了自己的活路,他只想传给儿子五兴。李正的女人为人善良,处处替他人着想,尽力说服了丈夫收了天狗为徒。但他处处刁难天狗,把苦事、累事都让天狗去做,最终因为不愿看到得到的钱要分给天狗,将天狗逐出了师门。作为孤儿、单身汉的天狗,表面木讷内心却很丰富,虽然师父对他十分苛刻,但师娘的温柔善良深深地打动着天狗。所以,当李把式在一次打井过程中被一块巨石压中下身成为废人时,天狗不愿看到师娘红润的面容渐渐地憔悴下去,就明里暗里地帮助女人。李正看在眼里,心里感激天狗的帮忙,但毕竟过意不去,所以劝女人招夫养夫。天狗热慕师娘,把她视为活菩萨,但招进李家的天狗白天出去干活,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晚上悄悄地回破屋睡觉,李把式对于天狗名义上的丈夫,心里又感激又内疚。通过无数次的挣扎,李把式决定以自杀来成全天狗和女人,最终,李把式用自己侠义的自杀换取了天狗与女人的幸福。作者用真切的语言,一步一步地逼近人物的内心深处,将这种民间习俗逐渐地放大,最后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作品中,李正和女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但李正深知不能动弹的自己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再也无法给这个家带来什么,只会使这个家更加的破败,所以感情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了,生存逐渐被放大。但想“苟活”下去并不那么容易,内心的愧疚最终给死亡让了步。这种小人物的悲剧,正是困顿处境里的人们选择的最终归宿,生不能生,只有死。在李正的眼里,劳动能力即是他活着的资本,当他失去了这一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女人和家庭的资格,这种男权主义的权威已经在他心里拥有根深蒂固,导致了他的宿命。
贾平凹的《天狗》和许地山的《春桃》都是在传述:一个断了双腿的李茂和只能卧床近乎废人的李正,他们都是失去了劳动能力,只能依靠一个女人才能存活。他们都提到了“招夫养夫”,但最终的结局却不尽相同,一个选择了“生”,一个选择了“死”。如果说许地山是出于宗教式的仁慈,让李茂与向高、春桃和谐地生活下去,那么贾平凹出于遵从写实的动机,写出了人物的自然本性,深入到男女之间的复杂的潜意识世界,让井把式痛苦地吊死来成全天狗。他们之间的不同,并不能说明谁写得就更好,因为他们所处的外部条件不同,许地山所写的是30年代的战乱时期,而贾平凹作为当代作家,他笔下的堡子村是新时代的乡下,他们的观念和出发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他们所反映的文学现象都是“招夫养夫”,但彰显的却是别样的生存困境。《春桃》和《天狗》中的女主人公都彰显了人性的善,困境中的不离不弃,倔强而顽强地与现实的残酷抗争,面对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厄运,她们都表现得相当冷静,春桃果断,李把式的女人顺从,她们以不同的方式驻守着生活这片天地。
三、为爱而存,无怨无悔的爱情悲剧
郑义的《远村》将我们带进了太行山深处沟壑之中的一个偏远小村,讲述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段凄凉的故事。羊户杨万牛——一个曾经走南闯北的复员军人,自己成不了家,却为曾经深爱过自己并且已经嫁为人妻的女人叶叶拉了18年的“边套”。这里的拉边套就是相当于“招夫养夫”,以这样不为别人所看好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爱情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土地上蔓延,这种畸形的婚姻现象向我们传递着苦难在人们内心深处所留下的伤疤。
小说不仅仅是从畸形婚姻现象出发,而且是大大地扩大了题材和人物的内涵,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自我生存所具有的高度耐久力和坚韧的延展力。于是,在作者的笔下万牛、叶叶和四奎他们这样的一女二男,在面对现实的残酷时,不得不向“拉边套”的婚姻模式低头,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仅仅是个人愚昧的结果,也是客观条件促成这个结局。因为叶叶既是四奎“豆腐换亲”的妻子,又是万牛两厢钟情的情人。她不能和四奎离婚,因为这牵扯着两个家庭的幸福,但她又放不下对杨万牛的爱情,她对爱充满了激情,她渴望拥有它,所以她要维持这个畸形的家庭就必须尽自己的全部去担当起一个女人应尽的责任。叶叶是个面容清秀、温柔贤良的女子,她忠于自己的爱情,在婚姻面前她挣扎过、努力过,但她失败了,她不是败给了自己,而是败给了父母的“恳求”,败给了这个贫瘠而古老的山村。在古老落后的阴影覆盖下,爱情没有容下的地位,爱的美感也不堪一击,它只有向命运低头,只能向生存让步。在残酷的选择面前,万牛、叶叶和四奎这三个善良的人,都无法挣脱经济、风俗和情感的绳索,一齐低下了头,默认了这样的结局。在苦难面前,他们只能选择这条路,“这条路象征着人的变形,这条路是贫困和愚昧铺就的坎坷之路,这条路也是无数丧失了爱的权利和共同迎受生活重担压迫的人们,为了生存于无可奈何中踩出的崎岖小径”[3]。然而,故事中的人物,在这条崎岖小径上走得无怨无悔,无论是叶叶还是杨万牛,都是用生命和青春来祭奠他们之间的爱情。看似卑微的“拉边套”方式,传达的却是真真切切的情感细语,温情的背后,消解了人物的悲怆和对绝望的挣扎。
从整个故事的内容上看,郑义的《远村》所反映的“拉边套”与许地山的《春桃》、贾平凹的《天狗》有着很大的不同,万牛、四奎和叶叶这种畸形婚姻形式的出现,不是因为俩个男人当中的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组成的家庭,而是因为纯粹的爱情,杨万牛为了爱情宁愿过这种不被别人待见的“拉边套”生活,而且一干就是20年。但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共同点,招夫养夫的春桃、五兴她娘和叶叶她们都是受害者,她们或多或少都承受着生活的压迫,饱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不管是因为爱还是因为生,这种畸形的婚姻对她们而言都是一种摧残。在用泪水汇成的长河之中,真情的浪花却异常动人心魄。作者用纯粹而又美好的口吻叙述着真切的情感故事:有流离失所下的惺惺相惜,也有出于道义的相互扶持,更有源于内心的倾情付出。
四、“患难见真情”式的爱情悲歌
从许地山的《春桃》可以看出,许地山的现实主义并不彻底,他的作品中更多的保留的是浪漫主义的情愫,他没有让畸形婚姻下的春桃和她的男人们给予悲剧的结局,而是从温情的角度,让他们像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和王子和谐幸福地生活下去。然而,“人物在作品的世界里和我们活在的现实世界上一样,它也有它存活的基本条件,当这个基本的条件一经被破坏了,那么它的生命也应该随之结束,真正的作家应该有能力窥见这个秘密。”[3]贾平凹就是用现实主义的写实姿态向《天狗》中的人物内心一步一步地逼近,用诗意的叙事手法写出了苦难的哀歌,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更接近现实与真实。“艺术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在于运动。”[4]《远村》的张力在于,表面是寂静的,内蕴却是强劲的。杨万牛经常回忆往事和不断的幻想都表明他对过去的不舍,对爱情的怀念,而叶叶为爱牺牲,却给万牛留下了一双儿女,这是善良苦命的妇女对“拉边套”情人的忠贞奉献,也是生命流动的气息在不断的绵延。悲剧的背后却留有诗意的温情,给小说增添了人性的光环。
“招夫养夫”这一畸形的婚姻模式,虽然给春桃、五兴她娘和叶叶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是作者都从温情的角度,弱化了这些女性命运的悲剧性,而是把笔深入到人性中善良的本性当中,文字中充满了感人的基调,舒缓了读者对主人公的道德责备,增加了读者对其命运的同情和理解。“招夫养夫”的女性,在作品中都表现了其坚强的一面,面对生活的困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顽强地抵抗狂风暴雨的降临,成为家庭中的砥柱。这些女性虽然坚韧,却不霸道,更不强悍,她们依然保留了女性的柔情,她们的内心充满了爱,同时善良的天性驱使着她们对道德底线的遵守。春桃对名存实亡的丈夫不离不弃,五兴她娘对丈夫男权主义的遵从,叶叶对杨万牛真情的回报,都显示了她们内心的那份道德标准,即患难见真情。无论自己在患难中遭受多大的困顿,但是拥有的那份真情却是不能丢失,这便是普通大众固有的美好品德。许地山、贾平凹和郑义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怀,不忍打破小人物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选择突出赞美小人物的自然美,肆意地赞扬了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身上所散发的朴素之美。因为纯真的内心正是朴素的劳动人们应该具有的品质,这在作品中被很好地体现出来了。小人物虽然生活在最底层,但是他们也有爱,也渴望爱情的圆满。也许他们的爱不能给人以震撼,但是这份流动于人世间的真情却深深地回荡在读者的心间。许地山的《春桃》、贾平凹的《天狗》和郑义的《远村》都向我们展现了一曲爱情的悲歌,困顿年代里小人物对爱的理解以及追寻,在这里,叶叶是我们不愿忘记的一个勇敢的女性,她身上所体现的多样色彩,虽然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她的形象却融化在读者的心中。善良的叶叶将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母性般的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温暖着两个男人以及两个家庭。女性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更加弱小,在生存面前,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这必然造就了她们比一般人更能忍受生活之苦和生命之痛。
困顿的人生处境,泯灭的不是人性的美好,而是宣扬了人们强烈的生存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招夫养夫”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荒诞,女性的悲剧,更反映了落后时代人们的思想状态,呼唤物质生活的提高,改变人们贫瘠的思想境界,对人性中美的赞扬和保留。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像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随着物质文化的飞速发展已是很少见了,这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进步,也体现了现如今的人文关怀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注释]
① 本文所讨论的“招夫养夫”现象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以许地山的《春桃》、贾平凹的《天狗》和郑义的《远村》为研究对象,阐释和分析“一女二夫”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 许地山.春桃:许地山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 梁德智.伦理冲突中的一女二男——读许地山短篇小说《春桃》[J].天中学刊,1999(S1):26-27.
[3] 雷达.《远村》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J].当代,1985(3):247-251.
[4] 闫海田.招夫养夫:《春桃》的“宽”与《天狗》的“窄”[J].钦州学院学报,2010(1):47-50.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The Literature Phenomenon of Recruiting a Husband and Keeping the Husband by Taking Spring Peach, The Dog and Far Village as Examples
JIN Zhu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Recruiting a husband and keeping the husband is a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is full of plight. And its literary value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writers like Xu Di-shan, Jia Ping-wa and Zheng Yi. Xu Dis-han gives peaceful home for the plight of the gears like Chun Tao from religious mercy; Jia Ping-wa, with a deep insight and realistic approach, deepens human nature and the soul of these people like Tian Gou; Zheng Yi, with the warmth of narrative, writes a folk song in far village like Yang Wan-niu. The literature phenomenon of recruiting a husband and keeping the husband reveals a survival difficulties and emotional pai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Key Words:recruiting a husband and keeping the husband; difficulties in life; humanistic care
作者简介:金转(1989-),女,安徽庐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4-20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5.04.019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4-00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