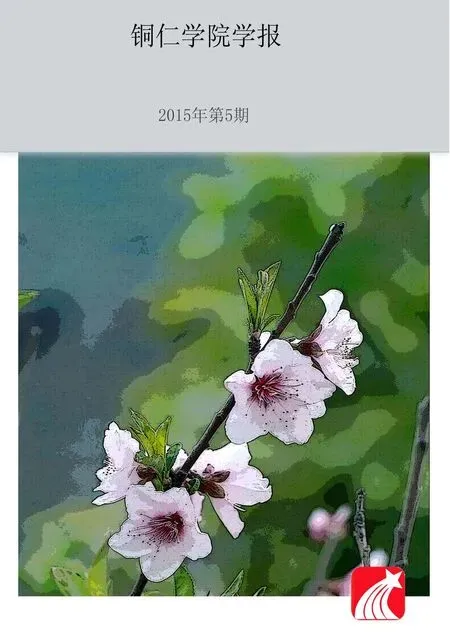《卜居》、《渔父》作者探析
——以宋玉骚赋考察为主
2015-02-13马军峰
【文学研究】
《卜居》、《渔父》作者探析
——以宋玉骚赋考察为主
《卜居》、《渔父》是作者存疑的楚辞作品之一,而宋玉是与屈原同时代或稍于其后能追步屈原辞赋者,世称“屈宋”。从辞赋发展史看,将屈宋作品对比观照,对于判定和证成《卜居》、《渔父》的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而通过屈宋作品的对比观照以及《卜居》、《渔父》思想情感探析,其作者定为屈原较为允当。
《卜居》; 《渔父》; 署名权; 宋玉骚赋
对于《卜居》、《渔父》的作者,自汉至宋多遵从王逸之说,以为屈原作品。明清以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学者对这两篇作品作者产生质疑,以致“现代一些研究《楚辞》的学者往往不提到《卜居》、《渔父》,甚至干脆把这两篇屏诸屈赋之外(如刘永济《屈赋通笺》)。即或有人提到了它们,也必认为它们不是屈原所作,却又说不出什么可靠的根据,可信的理由。”[1]661尽管以陈子展等为代表的治楚辞者撰文予以驳斥,但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目前楚辞研究界大多仍取存疑或否定态度,而“确认其作者及其产生时代,对于认定屈原的成就、影响及先秦文学的演变、战国后期至汉初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意义重大。”[2]有鉴于此,笔者拟以与屈原同时代或稍于其后的宋玉骚赋为考察对象,同时,结合两篇作品思想情感的探讨,以期进一步证成、坐实《卜居》、《渔父》的作者,得出符合作品本身和辞赋发展实际的正确结论。
一、宋玉生平及作品考略
在辞赋史上,屈宋并称,对于宋玉的代表作品《九辩》,鲁迅赞曰:“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3]25高度评价了宋玉作品的独创性,肯定了其在辞赋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楚辞作家,同他的前辈屈原一样,能为后人称引的可靠资料无多。这里,为后文研究的方便,我们试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宋玉作品,对其生平经历做一大致勾勒。
宋玉,生卒年不详,刘向《新序·杂事第一》“楚威王问于宋玉”、《杂事第五》“宋玉因其友以见楚襄王”和“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有载,然威王至于襄王有近百年时间,其故事颇可疑。楚辞学界现一般仍以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为宋玉生平重要参考和立论基点。王逸《楚辞章句》说宋玉曾以屈原为师,如果我们将这种关系理解为楚辞艺术上广义的师承,或说是仰慕屈原的后进似较符合实际。据此,我们大致可以认定,宋玉是继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据《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可知,其大致生活年代当与襄王相始终,是襄王时代一个才貌双全的文学侍从;又据《九辩》宋玉称己为“贫士”,王逸《楚辞章句·〈九辩〉解题》:“数遭患祸,身困极也”,似政治地位不高,且在仕途上屡受困厄,王逸说他曾为“楚大夫”,但不久“失职”,晚年“无衣裘以御冬”,由此大致可判定,宋玉是一个政治失意且生活窘困的下层文人。
关于宋玉的辞赋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16篇,惜未详载具体篇目。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署名宋玉的作品大致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等,惜多被认定为伪作。如《招魂》,王逸明言其为宋玉悯师之作,但一般治楚辞者多认同司马迁的观点,以为其为屈原作品。一些学者甚至连《九辩》都不承认是宋玉之作,可见以往对于宋玉否定的程度。但新文献的出土往往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甚至带来一些戏剧性的变化。诚如研究学者所言:“以‘地下之新材料’来补论‘纸上之材料’是现代研究文学的一条新路子,对于材料相对缺乏的先秦文学,尤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4]在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 1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20余枚赋的残篇,因首简背面上端署有“唐革(即勒)”,篇中又有唐勒话语,故最初命名为《唐勒赋》,作者定为唐勒。后经李学勤等楚辞专家精心考证,终定名为《御赋》,并将之与署名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相对照,最终认定其作者为宋玉。“《唐勒赋》残篇的出土,为宋玉生平与作品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学术界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除《史记》外宋玉生平资料全不可信,除《九辩》外宋玉作品全可怀疑的偏颇态度。”[5]可以说,《御赋》残篇的出土,拨正了以往将署名宋玉的作品多定为伪作的偏激态度,治楚辞者或结合新资料,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纷纷撰文对署名宋玉的作品进行重新审视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宋玉对于某些作品的署名权。应该说,这对于宋玉研究,还是放置在辞赋发展史看都意义重大。对宋玉作品的体认,将使我们对于辞赋发展的历程认知更为清晰,同时,对于与其生活时代相仿佛或稍前的某些楚辞作品作者的澄清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卜居》、《渔父》是作者争论较为激烈的作品。通过对“屈原既死之后”的重要楚辞作家宋玉及其作品的考察,无疑为我们研究认定屈原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考察视角。
二、屈宋作品之比较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载:“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这里,刘勰对宋玉作品的文体特征做了重要总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这成为赋体文学,尤其是汉赋文体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不妨将宋玉“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作品同《卜居》、《渔父》,甚至汉赋作品做一比较。
首先,“述客主”指文体的的结构形式,即主客问答,这是宋玉作品乃至汉赋的重要特征,宋玉《风赋》、《对楚王问》,汉贾谊《鵩鸟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诸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均采用这一结构形式布局谋篇。我们发现,其结构与《卜居》、《渔父》惊人一致。对此,宋洪迈《容斋随笔》总结道:“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二京赋》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6]888可见,《卜居》、《渔父》在文体结构上的创获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成为后世文学尤其是辞赋创作效法的对象。但我们仔细对照宋玉及汉赋作品,就会发现其呈现出明显的演变发展轨迹。对于《卜居》、《渔父》,我们多以为“日者”、“渔父”实有其人其事。屈原作品出于写实,有着一定的事实和经历,但宋玉《风赋》、《高唐赋》等虽在形式上保留“宋玉对曰”、“楚王曰”的形式,从其所论之事看,应是有所经历的感发之作,但其所论显然已与《卜居》、《渔父》不同,已是有意识的虚构,而非“实录”。这点,阅读《神女赋》“巫山神女”、《登徒子好色赋》“邻家之子”等即可感知。如果说宋玉作品尚有一定事实的话,汉赋则几乎全出假托。因此,就“述客主以首引”这一特征而言,从辞赋渊源看,《卜居》、《渔父》实肇其源,其开创的问答形式具有“实录”性质,后继之宋玉则申而述之,作品中出现了出于创作需要的虚构,而汉赋则完全出于假托。对此,鲁迅评价:“(《卜居》、《渔父》)其设为问答,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所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皆是也”[3]22。从辞赋发展观之,鲁迅指出宋玉是楚辞向汉赋过渡的中间人物,这点从考察“述客主以首引”这一文体特征亦可得到印证。
其次,“极声貌以穷文”指赋体文学的语言和艺术手法等。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刘勰“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汉赋摹态写物时辞藻华丽、铺张扬厉。对于宋玉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以《风赋》为例,宋玉以风为喻,分为“雄风”、“雌风”进行对比,其间描写细腻,措辞巧妙,想象奇特。再如《神女赋》对于神女外貌情态的描绘,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开掘。《大言赋》、《小言赋》莫不如此。从文体承继发展性来看,宋玉辞赋对于汉赋“铺采摛文”、渲染夸饰的文风是有极大影响的。相较而言,《卜居》、《渔父》则是近乎客观性的描述,甚至可视为“质木无文”。而宋玉作品则描写手法多样灵活,甚至大肆渲染巧比夸饰。从两者艺术手法对比言之,《卜居》、《渔父》可谓“但开风气不为师”,这种开创为宋玉等承继并发展之,进而影响到汉赋。
再看其创作动机,虽均出于“讽谏”,但其采用的方式、方法显露了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之不同。如,宋玉《九辩》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奸佞误国的黑暗现实,显示了作者对于黑暗现实的批判锋芒,但从总体上看,《九辩》整体上所显示的还是贫士失职鞅鞅、老大无成的一己之思,与屈原基于爱国情怀下的《离骚》显然有不少距离。再看《卜居》、《渔父》对于现实的认知:“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显示出作者对于黑暗现实决不妥协的态度。而宋玉《风赋》虽也有批判和揭示,但更多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统治者的批判和对于劳动者的同情。再如《对楚王问》,对于楚王加于自己的无理责难,宋玉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鸟之凤与藩篱之鷃,鱼之鲲与尺泽之鲵相对比,隐喻自己就是“阳春”、“白雪”、凤、鲲,间接表达了对于楚王不能用贤的批判,侧面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志向高洁。其他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作品对于“巫山神女”、“东家之子”的描写已近情色的肉欲描写,更大大降低了其批判的力度。可以说,屈宋二人虽主观命意均出于“讽谏”,但屈原是“直谏”,宋玉是“曲谏”,这种命意转化在宋玉作品中悄然显露。而通过阅读一定量的汉赋作品不难体会,其创作虽有“劝百讽一”的主观动机,但毕竟淹没在“润色鸿业”的“诵”、“赞”中,大大弱化了屈原所开创的“直谏”传统,其承载的“讽谏”效果更微乎其微。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7]2491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似将“辞”、“赋”作为两种不同文体而目之,宋玉爱好楚辞,但学习的结果是创作了大量赋体作品;二是在屈原作品中,能为宋玉创作“赋”体提供直接营养,又可称“从容辞令”者,观照目前署名屈原的作品,似惟有《卜居》、《渔父》这一系统可以担当;三是“莫敢直谏”,也就是“曲谏”,宋玉作品多缺少《卜居》、《渔父》中放胆直言的气势,多借助于比喻、对比等隐晦曲折手段来加以讽谏。从以上分析看,司马迁对于宋玉作品特点的把握准确,大致指出了辞赋发展的历程:宋玉是一个爱好楚辞,创作大量赋体作品的作家,屈原作品对于宋玉创作可谓是“导夫先路”,而宋玉则是辞赋到汉赋的中介。
通过上述探讨,对于确立屈原是《卜居》、《渔父》的作者具有重大参考价值。放诸在辞赋发展史角度看,能承担这一开创性角色的似惟有屈原。屈原正是这样优秀作品的开创者,犹如楚辞在这位天才作家手中大放异彩一样,他的这种开创深刻影响了楚地的作家如宋玉等,进而影响汉赋。
三、《卜居》、《渔父》文本所蕴蓄的思想情感探析
朱熹《楚辞集注·〈卜居〉解题》载:“屈原哀悯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故佯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蓍龟以决之,遂为此词,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说者乃谓原实未能无疑于此,而始将问诸卜人,则亦误矣。”[8]113但若考虑篇章中被流放三年的困境,说屈原因“竭忠尽智,而蔽障于谗”从而产生“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似乎更与诗人心境相合。因为当一个人执著于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不为世俗所容,屡受挫折打击时,考诸实际,诗人必然对自己所坚持的理想信念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卜居》正是这一精神困境下的产物。开篇,诗人以八组话语一气呵出: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可以说,这八句犹如长江大河般将诗人愤懑不平之气决堤而出,“宁”字句表现了诗人所认可的事物,而“将”字句则表现了世俗的丑恶现状。如洪兴祖所言:“上句皆原所从也,下句皆原所去也。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而以问詹尹何哉?时之人,去其所当从,从其所当去,其所谓吉,乃吾所谓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9]179应当说,它们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对于自己进退黜陟的理性思考。紧接着诗人将这种思考的抉择推向了矛盾的最高潮,对于这样一个黑白颠倒、价值错置的社会,儒家强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勉力之行,但在更多情形下,儒家采取的是一种明哲保身或者是“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价值取向,而道家则主张采取纯任自然的无为对策。但诗人毕竟无法像儒、道两家所能提供给他的样式来解脱自己,因而形成了诗人无法超越的精神困境。而这种困境,对于太卜郑詹尹而言何尝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只得以“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作答,将问题再一次推给诗人。
值得注意的是,若将这种回答与《渔父》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相较,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一种开放式的、富有巨大张力的回答,其去留均由诗人或读者自己去抉择。在《渔父》中,诗人“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矛盾的困境相较《卜居》似乎更深一层。“渔父”遽然发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亦是脱口而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可见诗人对于自己遭受困厄的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此,“渔父”以“与世推移”相劝导,然而诗人的回答是决绝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改易节行。如果说《卜居》是“竭忠尽智,而蔽障于谗”从而产生“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展现的是诗人思想上的困惑甚至动摇,那么《渔父》中诗人思想上的困惑乃至动摇则是一扫而光,仅剩决绝,“从两篇所折射的诗人心理状态而言,从心灵困惑到看透浑浊人世而产生的坚定,《渔父》可视为《卜居》的续篇”。[10]529
若从思想情感的继承和发展性而言,两篇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情感状态由愤懑彷徨至于决绝坚定是如此相衔接,似告诉我们两篇作品当是出自一人之手。“《卜居》、《渔父》均借寓言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感情,其感情的深挚远非汉世拟屈之作所能比,其作者必有与屈原相同或相类的遭遇。特别是《渔父》的作者,可以肯定是生活在‘末世’的清醒者;而这一‘末世’,又非战国后期莫属。”[11]39说它们“感情的深挚远非汉世拟屈之作所能比”,其说甚是,其作品断限也大致不错。但如果说这样独特的经历与深切的感受是“战国后期”、“‘末世’的清醒者”所复制,当过于武断。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我们以为《离骚》必出于屈原之手,就在于我们体认《离骚》所包含的诗人的深切体验和思想是绝难复制的这一客观事实。那么,对于《卜居》、《渔父》,则如潘啸龙先生所评价的,“在这心灵的痛苦撞击声中,展示着一位伟大诗人的心灵世界,展示着他经历的探索和追求、焦灼和忧虑、绝望和依恋的整个心路历程。”[12]206试问,在这“战国后期”、“‘末世’的清醒者”有如此惨痛的经历和深切体验,我们是否能说:不有屈原,岂见《卜居》、《渔父》呢?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从我们对于文本思想情感深沉、发展承继性和诗人异于儒道的情感抉择看,恐怕在这“战国后期”、“‘末世’的清醒者”当是屈原。换言之,从两篇作品思想情感探讨看,它们当是屈原思想和情感经历的产物。
四、结论
通过我们对于屈宋作品的分析,参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论断,从屈宋楚辞艺术继承与发展角度看,宋玉祖述屈原所开创的《卜居》、《渔父》传统,并大大发展了《卜居》、《渔父》所开创的艺术手法和技巧,从而为汉赋体制奠定大致的基础。元人祝尧有言:“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即《子虚赋》、《上林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13]这样辞赋发展历程就大致可以想见并勾勒。在这一历程考察中,宋玉正是这一历程中的转关和中介,证实了屈宋楚辞承继的演变历程。而通过我们对于两篇作品特殊的思想情感的探讨,结合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其作者定为屈原较为允当。
[1]陈子展.楚辞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蔡靖泉.《卜居》、《渔父》的产生与屈原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朱啟迪,温庆新.对20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相关研究的反思[J].铜仁学院学报,2012,(3).
[5]罗漫.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6](宋)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杨义.楚辞诗学[M]//杨义文存(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潘啸龙,蒋立甫.诗骚诗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元)祝尧.古赋辨体[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马军峰
( 铜仁学院 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The Analysis of the Author of "Buju" and "Fisherman"——Mainly on Sao and Fuinvestigated by Song Yu
MA Junfeng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
Who is the author of "Buju" and "Fisherman" is of doubtful in the Chu’s works. Song Yu who was the cotemporary of Qu Yuan or slightly behind could catch step of Qu Yuan’s Ci Fu, known as the "QuSong".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 Fu, contrasting Qu’ sand Song’s work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judging and proving the author of "Buju" and "Fisherma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Buju" and "Fisherman", Qu Yuan might be the author of both works.
"Buju", "Fisherman", author ship, Song Yu’s Sao Fu
I207.223
A
1673-9639 (2015) 05-0064-05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田兴斌)
2015-03-12
马军峰(1983-),男,河南睢县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