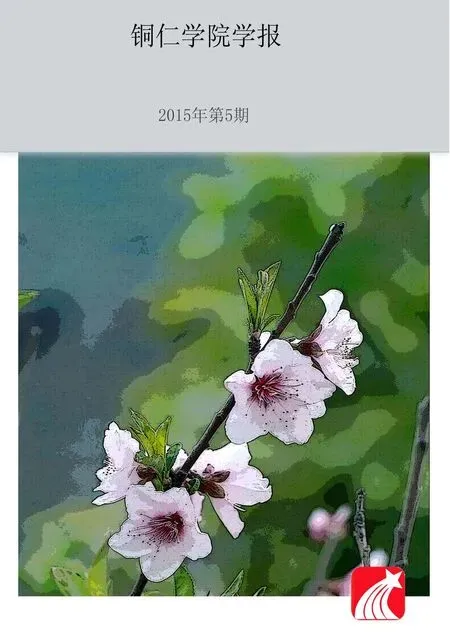熟读《文选》理
——主持人语
2015-02-13范子烨
【梵净国学研究】
熟读《文选》理
——主持人语
范子烨(1964-),黑龙江省嫩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选》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与文化。主要著作有《〈世说新语〉研究》、《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中古文学的文化阐释》、《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和《竹林轩学术随笔》,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篇。
某一年的正月初一,儿子宗武十五岁的生日,杜甫先生高兴地写了一首《宗武生日》诗:
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飞片片,涓滴就徐倾。
或许是受到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的自我表述的影响,老杜对儿子在文学艺业上期望甚殷,至于世俗所推许的老莱子式的孝道,他并不挂怀,正所谓望之深而责之切,一位慈父的襟怀跃然纸上。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五之三评此诗:“前四提笔。中四,勖子正文。后四,以己之老惫,儆惕后生。”“‘何时见’,期以学成名立也。中四句,字字家常语。质而有味。由祖而来,诗学绍述。此事直是家业。人言传说有子,特是世上俗情耳。须得学问渊源,本于汉魏,熟精《选》理,乃称克家。岂必戏彩娱亲,方为孝子。面命之语,如闻其声。”杜甫出身于北方世族京兆杜氏,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而晋代大将军杜预则是其远祖。如此显赫的家世自然使杜甫感到自豪,因而在诗中劝励儿子要秉承家学,发扬光大,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以“熟读《文选》理”为第一要务。唐人素来重视《文选》自不必言,但何为“《文选》理”?广义而言,《文选》中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文选》理”;狭义而言,“《文选》理”则是专指《文选》所包含的文章妙道。我想,老杜的本意当指后者。然而,以今人的文化眼光和学术视域来观照这部中古时代的文学圣典,则我们不妨以前者为“《文选》理”。
本期梵净国学研究的五篇论文正是“熟读《文选》理”的结晶。
钟仕伦教授的《〈永乐大典〉所录〈文选〉考释》以《永乐大典》残卷所录 47则《文选》为核心,对其所依据的《文选》原始版本进行考证,谨慎地推断赣州学刊本为其版本渊源,属于六臣注本中的“李善—五臣注”系统。文章指出,《大典》所录《文选》不仅为《文选》版本学提供了一个可资研究的对象,而且有用于唐钞《文选》集注本、敦煌写本、胡刻本、明州本和景宋本的校勘,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研究中古时代的文学典籍,今存《永乐大典》残卷确实值得重视。实际上,在传统的选学研究史上,版本研究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饱和状态,很难有所突破,故仕伦教授的这篇宏文是一个绝大的贡献。文章详细比勘萧《选》诸本,其功力之深,读者一望即知。做这样的学问是非常辛苦的。让我们向他致敬。
胡旭教授的《〈文选·奏弹曹景宗〉发覆》重点阐发任昉《奏弹曹景宗》一文产生以及进入萧《选》的历史背景。基于对其不同的文学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深刻认知,文章深入开掘了这篇作品背后的隐情。作者指出,此文之所以能入选《文选》,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曹景宗家族在梁大通年间的彻底败落,二是因为南朝上层社会流行尚文黜武的社会风气,三是此文在文章分类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同时,作者发现,《梁典》、《梁书》中关于“曹景宗被弹”一事的记载和感情倾向,受到了《奏弹曹景宗》一文的影响,而北朝的《魏书》由于受此文影响较小,因而相关的记载比较客观。通过对这三部历史典籍关于曹景宗以及司州之战、钟离之战有关记载的比较,作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相以及曹景宗其人的原貌。但文章的建树尚不止此。胡旭教授指出,梁武帝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君主,他成功地利用任昉的正直,以徇情的方式,使曹景宗对其感恩戴德,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换言之,萧衍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取得了制约满朝文武的双赢双效。学者固然不是政治家,但是,不懂政治的人,或者没有政治眼光的人,也绝不会成为优秀的学者,因为政治素养的欠缺必然使其看不到时时影响文学创作的非文学因素。这是胡旭教授这篇文章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这位《选》学届的“旭哥”一向给我潇洒美少年的印象,文章写得如此老道,实在值得赞许。受他的启发,我想在这里对一些相关问题略作申说。我对《文选》卷四十的奏弹之文一向很好奇,如果说沈约的《奏弹王源》属于契合萧《选》选录标准的典范之作的话,那么,任彦昇的两篇奏弹文字就都有问题,《奏弹曹景宗》是典雅不足,《奏弹刘整》则纯粹是大白话,至今还被语言学家们奉为研究中古口语的秘库。由于《奏弹刘整》的风格完全不符合萧《选》的择录标准,我甚至认为,这篇文章是在萧统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孝绰等人胡乱塞进来的,或者如曹道衡先生所说,《文选》本来就是一部未定稿未完成的书。《奏弹刘整》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期待着“旭哥”为我们再作发覆。历史上的曹景宗,其纵欲豪奢固然属于恶习,但其为人风格也值得欣赏。《梁书》卷九《曹景宗传》载:
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
这一代名将的豪气确实令人感动。传世所谓岳飞《满江红》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正源自曹景宗的豪言,辛稼轩《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的“弓如霹雳弦惊”也源自曹景宗的壮语。《奏弹曹景宗》说:“窃寻獯猃侵轶,暂扰疆陲,王师薄伐,所向风靡。……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厉义勇,奋不顾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犹有转战无穷,亟摧丑虏。方之居延,则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则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声援,则单于之首,久悬北阙,岂直受降可筑,涉安启土而已哉!”这是以汉代的匈奴比拟北魏之鲜卑。其实作为儒将,岳武穆与曹景宗的为人风格完全不同,他与当朝皇帝的关系也不同于曹景宗与梁武帝的关系,所以《满江红》用曹景宗的典故实在不伦不类,正可证明其为伪作,但无论《满江红》的作者是谁,他都肯定是一个“熟读《文选》理”的人。
宋人对《文选》的尊崇热度远不及唐人。张明华教授的《陆游“国初尚〈文选〉”的历史考察》和李昇博士的《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及其文化成因》这两篇论文就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明华教授以大胆的质疑精神和科学的求证态度对陆放翁“国初尚《文选》”之说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确认了宋初出现的文选学著作并不多,士人学习《文选》的情况也不多见的事实,同时,他从宋初诗文出发,对所谓“当时文人专意此书”的情况进行了印证,发现这种情况仅在宋庠、宋祁兄弟的文集中有较多体现。这些观点一经明华道出,即可确证无疑,因为他是根据现存的文献来立论的。但是,他并不以为放翁纠偏为满足,通过考察,他证明在庆历时期以后,《文选》的影响仍然较大,主要表现在集选诗的出现。由此,宋代《文选》流布和影响情况就基本清楚了。李昇的研究正可与明华互补。他首先根据《文选》的体例说明萧《选》不选经书的事实(当然,《文选》所收子夏《毛诗序》和杜预《春秋左传序》属于经部著作),随后表明这一事实乃是北宋以前人所共尊的惯例,这一惯例在南宋时代被打破,《左传》作为经部著作被编入了诗文选本之中,且主要是南宋理学家所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随后,他深入揭示了这种文学景观赖以生成的文化动因,如北宋的“疑经弃传”思潮,南宋理学家对《左传》文理文风的推崇,南宋进士科的现实需求以及宋代“《文选》学”的衰落等等,都对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此透过文学的表象,深挖其思想史以及现实需求的本质,确实表现了不俗的学术功力。
张一南博士的《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一文虽然研究的主体对象是晚唐诗人群及其诗风,但是,由于其论题关涉齐梁,故可视为对《选》学的拓展性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南朝文学的特质是有帮助的。她指出,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可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具体给出每一位诗人在诗体结构系统图中的位置。这些诗人可分为旧式诗人与新式诗人两大类。前者以关陇集团后裔为主,创作结构完整而忠实于齐梁旧体;后者以士族和寒素为主,创作结构残破而倾向于新体。在论文中,一南采取了数理统计的方法,得出了可靠的结论。这篇文章是其关于齐梁、晚唐诗歌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读者如果和她即将在《文艺理论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一同观赏,则对其所言所论能够获得更为具体的感受。这篇文章没有涉及具体的文献材料,甚至所研究的诗人名字也并未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但由于作者成竹在胸,且与即将发表或已经发表的成果互相配合,必然能够取得很好的研究效果。
《文选》的魅力是无穷的,《选》学的话题也总是说不尽的。
2015年7月5日夜记于京城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