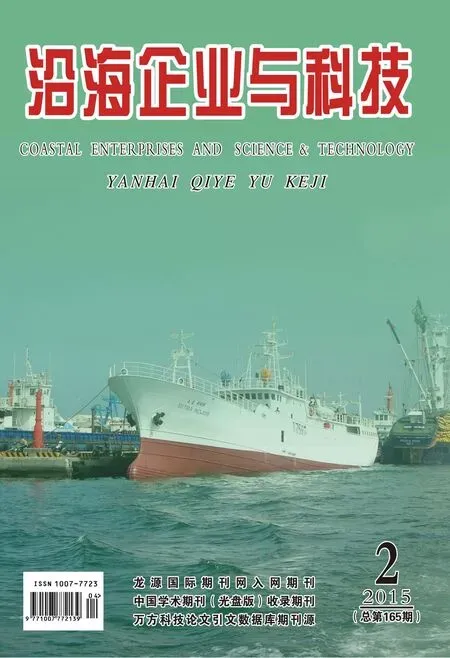花山岩画反映壮族先民宇宙观与灵魂信仰*
2015-02-13黄桂秋
黄桂秋
花山岩画以及左江崖壁画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国内外专家进行的实地考察已有好几次,各级报刊出版机构发表出版的考察与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也有上百种。笔者认为古今中外人类的原始文化遗产大都与原始崇拜宗教观念有关,要解开左江崖壁画的各种迷团,必须从壮族先民古越人的原始崇拜和宗教观念入手。具体来说,壮族及其先民最初的原始信仰是以对巫信仰和麽教信仰为中心的。关于巫信仰,有人认为它还不是宗教的范畴,但它确实曾经是壮族先民长期信奉的原始信仰观念;麽教信仰由巫信仰发展而来,是一种带有原生型巫教性质的民族民间宗教。也就是说,壮族及其先民的巫麽信仰是完全植根于中国南方珠江流域特有的地理环境,经济生产和历史文化土壤,渗透了壮族及其先民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尤其是与信仰有关的灵魂观。而且,与后世神学宗教的空灵虚无不同,壮族的巫麽信仰还明显地带有群体自发性、巫师操作性、功能实用性、民族民间性等原始信仰共有的属性特点。为此,笔者把左江崖壁画定位于壮族先民巫麽信仰前提下所反映的壮族三界宇宙观与壮族灵魂信仰。
一、崖壁画位置选择与壮族宇宙三界观
根据1985年《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报告》显示,综观对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各地点崖壁画考察,它们在分布上有如下特点:
1.大部分集中于江河两岸。据统计,在79个崖壁画地点中,有70个地点位于江河两岸的临江石壁上,约占地点总数的88.6%。
2.在方向上,画面大部分朝南或基本朝南,一部分基本朝东、西,基本朝北的很少,朝向正北的目前还没有发现。
3.作画的崖壁,绝大多数是选择临江一面的崖壁作画,有的崖壁底部直接与江水相接,有的崖壁下则有因山体石块崩落堆积而成的倒石锥坡或错落体,画面一般高出常年江水面20~40米,最高的可达120米左右,画点的两侧或对岸多有一块平坦的河流阶地[1]。
以上左江崖壁画分布及作画位置的选择,根据壮族先民原始崇拜巫麽信仰观念来看,应该与壮族先民宇宙观中的天、地、水三界说观念有关。
壮族宇宙“三界”观是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产生和演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了解中逐渐形成的原始哲学思想观念。壮族远古神话《天地分家》说: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三黄蛋,后来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方成为天空,一片沉到地下成为河海,中间一片成为中界大地,形成了“三界”自然界物体。类似的说法在壮族麽教经书里多有叙述。如东兰县坡峨乡永安村板勾屯布麽覃教兴收藏的麽经手抄本就说到:从前天低矮,舂杵顶破天,天裂开掉下一巨大石块,三十只蜾蜂从里面咬,四十只拱屎虫从外面啃,大石块破成数片,一片弹到上方方变成宽阔天空,一片弹到下面变成中界人的住地,一片滚到下方凹坑变成水界深潭。另外,壮族麽经每一章的开头几乎都有“三盖(界)三王置,四盖四王造”的经文。按照壮族麽公的解释,宇宙“三界”是由“三王”创造的,天上是上界,住着神灵,由雷公管理;大地是中界,住着人类,由布洛陀管理;水下为水界,住着小矮人,由水神图额管理。宇宙三界观是壮族先民在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观察认识后给予的哲学解释。
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来,左江崖壁面绝大多数的作画地点为什么要选择在朝南临水的高山崖壁上,它跟壮族先民的宇宙三界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按照壮族先民原始崇拜中的巫信仰和麽教崇拜观念,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而且只要借助某种媒介,通过举行一定的礼仪,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灵魂,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的灵魂是可以沟通交流的,甚至于那些对本氏族的生存发展繁荣立下功勋的先祖的灵魂可以是永恒的,就像圣灵布洛陀一样,不仅永恒而且还能光耀后人。由此推知,古代壮族先民认为,左江边上那高耸的崖壁上可通天、下可接水,中间连着中界人类,是沟通宇宙天地水三界的最好媒介,而崖壁上的人像代表着先祖的灵魂,通过巫师特定的巫术礼仪将这些已经死去的先祖的英灵导入永生的境界(待后详论)。至于左江崖壁画的空间方位为什么又大多是朝南的,没有一面是朝北的,这或许跟壮族先民古越人始祖的起源地与生活的地域均在南方有关。
二、崖壁画剪影式人像与壮族灵魂信仰
据考察,左江崖壁画的各种图形,大致可归纳为人物、器物、动物等三大类。当中人物图像占全部图像的88.5%,每个崖壁画地点,均以人物图像为主,其形态有正身和侧身两种。
正身人像:基本形态是两手向两侧平伸,曲肘上举;双脚平蹲,屈膝向下。侧伸的双大臂大部分与肩平,也有的略高于肩。曲伸向上的小臂多向外撇,也有一部分与大臂垂直,故使肘关节或呈直角状,或呈钝角状。
侧身人像:面向左或向右,手脚向同一侧伸展。双手多曲肘上举,也有的平直斜伸向上;有的头、颈、身连成一直线,有的头略后仰。双大腿与身躯的夹角、膝关节的夹角多呈钝角,少数为直角[2]。
左江崖壁画的的人物图像主要是采用平涂的剪影式画法,即在上下和左右的二度空间内表现立体物像的艺术形式。其特点是仅限于形像的外轮廓平面描绘,但却能够充分表现出物象的基本形体。有学者认为:“在没有掌握绘画立体表现方法的古代,平涂画法的确为原始艺术家们所常用的绘画方法之一。左江崖壁画之所以也采用这种基本的画法,说明作画者还没有掌握立体透视的绘画技巧,只能用简单而明瞭的平涂形式来表现。”[1]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对的,第二句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同一时期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生活地区发掘的铜鼓,其鼓面鼓身上的立体雕饰和绘画,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发掘中铜器上精美的漆绘作品“招魂升天图”、“猎头图”等,就包括了立体透视线描勾勒等多种复杂的绘画技巧。崖壁画上的平涂式画法应属有意为之。
笔者认为,左江崖壁画既然是壮族先民原始宗教的产物,其灵魂信仰观念还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壮族先民甘冒生命危险爬上江边悬崖绘制的一幅又一幅千篇一律的剪影式人像图案,并不是没有立体透视的绘画技巧,也不是不懂得勾勒出人的眼睛、鼻子、嘴巴等轮廓形象,而完全是由于灵魂观念所支配。因为,在壮族先民看来,崖壁上的剪影式人像就是人的影子,而这些影子则相当于人的灵魂。关于左江崖壁上人的影子和人的灵魂的关系,蓝鸿恩先生曾经从壮族民间习俗的角度,作过精僻的论述:
“花山崖壁画画的人物都呈现影子的形态。影子在民间习俗里被认为是人的魂魄,人若无影,便为鬼怪。……可见影子是代表魂灵的,灵魂这个字壮语意指缥缈的影子。因而无疑,崖壁画的人影,即灵魂的图像”[3]。
其实,不单是中国,也不单是壮族,世界上许多的民族都有把人的影子等同于人的灵魂的信仰观念:
精灵,或者被昏睡的或有幻觉的人看见的幽灵,是一种虚幻的形态,如同一个阴影,因此同样的词“s h a d e”(阴影)就用来表现灵魂。……祖鲁人不只把“吞吉”这个词用作“阴影”、“精灵”和“灵魂”,而且认为,在死的时候,人的阴影就会以某种途径离开人的肉体,从而成为祖先的精灵。巴苏陀人不只称死后留下的灵魂为“谢利其”或“阴影”,而且认为,当一个人沿着河岸行走的时候,鳄鱼能够在水中捉住他的阴影,把他拖入水中[4]。
原始人为自己的影子担心,……如果他失去了自己的影子,他就会认为自己这个人岌岌可危,难逃劫数。对他的影子的任何侵害都意味着对他本人的侵害。……影子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严格等于我们叫做灵魂的那种东西;但它具有灵魂的性质。在灵魂是复数的地方,影子有时就是灵魂之一[5]。
当我们仰望着左江沿岸延绵200多公里每一处崖壁上一个个人物形象,宛如一个又一个人的影子,自然会触发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联想,其焦点无疑都集中在这神秘莫测的“影子”上。其实,上面我们论述了那么多关于“影子”和“灵魂”的关系,再将它与前述壮族先民宇宙三界观联系起来,其神秘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了,还是前面那句话,左江崖壁上的剪影式人像代表着先祖们的灵魂,通过崖壁这特定的媒介,进入天地水三界永恒永生的境界。
当然,这些灵魂要实现永恒的愿望还得需要通过一定的巫术礼仪。
三、崖壁画巫舞与壮族超度亡灵仪式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原始人并不是以各种纯粹抽象的符号而是以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情绪的。人类出现最初的时候,就开始用推论性符号与呈现性符号两种手段去把握世界。前者由语言而科学,后者由祭祀、神话、宗教而艺术;前者是科学性的符号,而后者则是生命性的符号。这呈现性的生命性符号之一,便是舞蹈。卡西尔还断言,“人是语言的动物”。谁把握了语言,谁就是同类中的强者。巫的地位的确立,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他(她)同时把握了两种语言,即文学语言──咒语和人体语言──舞蹈。巫师优先的语言能力,曾使部落成员(包括今天未开化的原始部落)对“神灵附体”者五体投地,并由惊讶不解而产生神秘感,从而产生对语言本身的崇拜。这就是咒语产生的根由。在某些语言被当作具有特殊魔力的东西被供奉起来时,掌握了它们的人就意味着获得了超凡的能力,尤其当与鬼神信仰结合起来时,它们便成了巫师法力的一种特权。巫舞作为一种语言同样如此,只不过它的外壳不是语音与字符,而是一套特殊的人体动作。……这些舞姿动作的超现实的形态,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掌握的,加之秘而不传的程式,高难的技巧,以及使用法术与魔术等装饰行为,必然使其成为一种超凡的语言[6]。
在壮族及其先民原生态宗教信仰中,巫婆巫公的咒语唱词和麽教法事仪式上麽公喃诵的经书,就体现人们对宗教语言具有的特殊魔力的信仰。而左江崖壁画上的人像舞蹈,则借助了人体语言来表达同样蕴藏着巫文化具有的巨大神奇的力量。在以往众多对左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中,已不约而同地集中聚焦到崖画人像的舞蹈动作造型与宗教关系上。
在左江崖壁画数万个人物图像中,仅有正身与与侧身两种形式,人物动态也表现得简单而程式化。……这种程式化的举手蹲足的动态又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在具有一定组幅关系的画面上,图像的组合也几乎都表现成规则的形式,即画面普遍以高大醒目的正身人像为中心,在其左右或上下方整齐地排列着几个、十几个甚至百余个举手投足、动态一致并面对着中心的小侧身人。这种固定形式的画面反复出现,无疑是表现了当时人们某种强烈的精神寄托[1]。
左江岩画反映的是人物活动的场面,在这些画面上,往往有一个高大魁伟的首领人物处于画面的中心或重要位置,其特殊的身份不言自明。这些画面,就整体来说,所表现的无疑就是古代骆越人进行巫术礼仪的场面,而画面上的中心人物,就是巫术活动的主角──巫觋形象[2]。
毫无疑问,左江流域各地崖壁画上的人像造型场面都是属于具有巫信仰性质的舞蹈,这种群体性舞蹈就叫巫舞。所谓巫舞,是指有关巫教性舞蹈的总称。也泛指以人体动态为中介来沟通神明、施展法术的活动。在远古时代,女巫男觋以舞蹈为媒介,通过失掉自我去连接天地,沟通人神;通过强烈的意念去扬善抑恶,驱鬼除邪。人类学、民族学资料证明,中外民族都有各种宗教性舞蹈贯穿于人类早期生活中的各种重大行为及其特定阶段的仪式:从婴儿诞生到成年割礼,从恋爱婚配到生男育女,从医治疾病到死亡葬礼,从神仙崇拜到宗教祭礼,从祖先崇拜到鬼神作祟,从出征御敌到胜利凯旋,从外出狩猎到满载而归……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不约而同地在不同部落的巫师率领下,为了相同的目的手舞足蹈。
宋兆麟先生把巫舞分为巫师舞、神舞、祭祀舞、巫术舞、送葬舞等类型。不管什么分类,其所要体现的宗教功能都是一样的,归纳起来就是祈神安鬼、逐祟除疫。具体来说,这类舞蹈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一是鬼神世界,向鬼神叙述人间祈愿,降神驱鬼以遂人愿。二是人间世界,即面对参加仪式,祈望鬼神福佑的世俗人群。他们要把人们聚集在周围,为这些人注射精神兴奋剂,坚强对鬼神的信仰,同时坚定其生存的信念;他们要使这些人,甚至包括跳舞行仪的巫师自己,相信这仪式的确是沟通了无形鬼神,借来了它们的力量为人们消灾降福[7]。
广西左江崖壁画上所绘制的巫舞应与鬼魂信仰有关。鬼魂信仰是原始部落最早也是最基本的信仰之一。它与祖灵信仰密切联系。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执著于宗族生命永恒绵延的信仰,老人亡魂往往被送往祖灵聚居地,使它们安居在那里荫蔽子孙,向子孙注入宗族生命的原生力。出于鬼魂信仰观念,壮族及其先民在处理死者尸体,安抚亡魂的过程中,形成巫麽信仰色彩浓厚的葬礼习俗,如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中,有一件铜筒上面用黑漆绘有为墓主招魂升天的葬礼。图中人像以墓主形像为主轴,皆戴有羽冠。图像内容有巫师邀神附身时毕恭毕敬的神态;有天神乘云豹升落天空的情景,有代表天空仙境的日(太阳树花)、月(玉兔)、雷(怪鸟)神像;代表地上的游鱼、狗、山脉图像,画面的主题是巫师已将墓主的灵魂送上天空[8]。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左江崖壁画上的巫术舞蹈,是一种专为殇死者举行超度亡魂的具有巫术法术功能的葬礼舞蹈,其目的是为本民族尊严荣誉而战死捐躯的英烈们招魂,让英灵进入永生的境界。
四、相关佐证材料
壮族及其先民的原生性宗教巫信仰和麽教信仰是一个体系,因此,广西左江崖壁画上所体现的巫麽信仰形态,就不会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信仰现象。为了使笔者研究左江崖壁画的新说更具说服力,下面举出与此相关的佐证材料:
佐证之一:中国南方悬棺葬
悬棺葬是崖葬中将殓尸棺木高置于临江面海,依山傍水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种葬俗。置放棺木的形式可以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打桩,亦可利用天然崖洞或岩石裂隙,或者在绝壁上用人工开凿洞穴。悬棺葬位置的选择与左江崖壁画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选择于江河两岸的悬崖绝壁上。
据陈明芳考察与研究,中国悬棺葬主要分布于中国南部及西南部的福建、江西,淅江、台湾、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年代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不等。行悬棺葬的民族大多与古代的越人僚人及其后裔有关。
广西悬棺葬主要分布在桂北湘江流域和桂西南的左右江流域。具体包括全州、田东、隆安、平果、大新、崇左、龙州、扶绥等县均有遗迹。而左江流域的悬棺葬又是广西分布最密集的地区。目前在大新县的全茗,榄圩、福隆、那岭、恩城、五山,崇左县(今江州区)的山峙山,白龟红山、扶绥县的驮拉山、龙州县的沉香角、棉江花山、天等县的那砚山等地均有发现。还有就是左江流域悬棺葬大多分布在左江沿岸极为险峻的石灰岩绝壁上,棺木全置于天然岩洞之中,距江面高30~150米不等。不少地方的悬棺葬与左江崖壁画共存。
关于悬棺葬的目的,陈明芳认为:从葬地选择、置棺方式、葬制和葬式等各方面来看,这种葬俗属原始宗教中在鬼魂崇拜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具体来说:“为使祖先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息,将殓装尸体或尸骨的棺木高置于陡崖绝壁,就可秘藏祖先遗骸,尽量避免人兽或其他因素对尸骸的伤害,这样才能得到祖先鬼魂在冥冥之中的赐福与保佑。”“棺木放置得越高越悬,越是人迹罕至,便越加符合人们长久保存祖先遗骸的愿望。……因为人们深信尸骸在空中保存的时间越长久,……子孙后代的福佑、安康也就更加有了保障。”[9]
以上佐证说明,左江崖壁画与中国南方古越人及其后裔的悬棺葬,在原始宗教灵魂信仰观念上有密切的联系。
佐证之二:有关左江崖壁画的民间传说
有关左江崖壁画的民间传说广泛流传于左江流域各县市壮族民间,广西宁明县的《勐卡造反的兵马》传说梗概是[10]:
从前,宁明那利有一个叫做勐卡的青年,力气非常大,一餐六十斤米只够吃粥,一百二十斤米才够吃饭。后来,勐卡造反打皇帝,没有兵马就在纸上画,他画的兵马,经过一百多天就可以变成真人真马,可是不能给任何人知道。秋收时,勐卡已经画了九十多天,但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母亲见他白天不做工,有一天趁他不在家,打开箱子察看,那些兵马都飞出去了。
勐卡的兵马飞到哪里去了呢?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宁明岜耀屯有一个穷人到岜来打柴,不小心,柴刀掉落到崖边,顺着悬崖滑落下去。砍柴人顺着陡崖爬到山脚,不知不觉到了明江边。这时,突然听到敲锣、打鼓、弹琴、唱戏的声音从一个岩洞里传出来,原来洞里的兵马正是勐卡的画变成的。不久皇帝知道那岩洞的兵马是勐卡的兵马,派了许多人来打。山洞里的兵马寡不敌众,全部被杀光。血、人、头和尸首到处都是,映到明江边的峭壁上,形成现在的花山崖壁画。
以后,凡是遇到阴雨天,走到河边山边,能隐约听到号哭的声音,民众惋惜武士们的不幸遭遇,请僧道打斋醮,祈祷他们英灵升天。老人讲那花山壁画的人兽图形,就是当年那些英烈们的形象。每逢大风、打雷、下大雨,壁画的图形有一些剥落,老人这样讲:他们去别处投生了,去做他们还没有做完的事。
上引传说中提到的“纸画的兵马,”“祈祷英灵升天,”“英烈们……去别处投生了”等也与笔者的新论不谋而合。
佐证之三:壮族麽教超度亡灵经书
壮族民间丧葬习俗中,有一种专门为殇死者举行的超度亡灵仪式,主持仪式的必须是巫师或麽公,壮族麽教经书中有专门用于超度殇死者灵魂的经文篇章。如广西壮族和贵州布依族广泛流传着一部关于以罕王祖王两兄弟相争王位反目成仇故事的麽教经书。广西壮族的麽经叫《汉王一科》、贵州布依族叫《罕王经》或《赎头经》,内容大同小异。广西壮族的经文叙说:汉王的母亲死后,父亲续娶一寡妇为妻,生下祖王,汉王和祖王本相处很好,但祖王之母欲让祖王独占家业和王位,唆使祖王害死汉王。汉王被迫离家出走。父亲因此病倒。汉王闻讯后回来探望。祖王以取药为名,欲将汉王害死于深井之中,在水神图额和雷神图岜的帮助下,汉王得以脱险。汉王对祖王发出多种诅咒,表示要以各种灾害迫使祖王屈服。祖王均不服输。最后汉王上天,做起了痧子、天花、旱灾等。天上出现了十二个太阳,晒得石头熔化,人死了不少,祖王这才请鹞鹰作使者,去向汉王请罪认输,愿交回王位权力。最后,以汉王管上方,祖王管下方,下方对上方每年交租进贡的协议,解决了同父异母两位王子的纷争。
《汉王一科》专门用于为死于战争,凶灾者举行招魂仪式时喃诵。根据贵州布依族学者韦兴儒、周国茂的考察,这类招魂仪式由布麽主持,地点选在野外看不见村寨的山坳,用芦苇在一平地上插成迷官似的魂归径。挖一坑,坑内将红泥与水搅拌成血色,谓血河;又挖一口灶,上置油锅下燃火,谓火海;另将三十二把杀猪刀刃朝上做成刀梯,谓刀山。魂归径旁东向用八仙桌搭成神台。仪式开始,远近民众云集山坳,布麽与十来名徒弟穿着法衣,在神台祭布洛陀,后开始诵《罕王经》;从清早一直诵到下午。接着,布麽手执“麽剑”带领孝子贤孙去魂归径把亡魂引出。引魂时所有观众也参加,因为过刀山、火海、血河被人们认为可以免掉人生几多灾难。“血河”上搭一块木板,布麽先带亡灵子孙从上“渡”过,以示亡灵已离开苦海;“火海”旁备有一堆荞麦糠壳,由一布麽徒弟在旁念经,向油锅中撒一把糠壳时,便有一人从火焰中跃过,以示亡灵走向光明;“过刀山”时,布麽在旁念咒,孝子们纷纷赤脚从利刃上走过,众人皆从旁绕道,招魂活动整整一天才结束,最后将做魂归径的芦苇拔出烧掉,将写有亡灵名字的牌位护送至丧家,安放于神龛上,等待来日做超度仪式,送回祖先住地[11]。
壮族布依族麽教丧葬招魂法事中为什么要喃诵汉王祖王故事的经书,因为据说当年汉王祖王两兄弟仇杀时,冤死了太多的人,喃诵此经书警世后人;更重要的原因是,民间认为此经书具有召唤慰藉殇死者灵魂的作用。
以上佐证都属于壮族原生态民间宗教巫麽信仰的范畴。
本文从壮族原生态民间宗教巫麽信仰理论角度,对广西左江崖壁画的地理位置、剪影式人像、巫舞祭仪、绘制年代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探讨和理论重构,辅之佐证的还有中国南方古越人及其后裔的悬棺葬,左江流域关于崖壁画的民间传说,壮族麽教超度亡灵经书等三个方面,结论是:广西左江崖壁画是壮族先民瓯骆族群用巫舞祭仪来超度那些在战乱中为民族捐躯的亡灵,祷祝牺牲的英魂在天地水三界宇宙中得到永恒与再生。
[1]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2]王克荣,等.广西左江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3]蓝鸿恩.花山探迷[J].民间文学论坛,1987,(2).
[4]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列维 -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刘建,孙龙奎.宗教与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王克荣,等.广西左江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7]宋兆麟.巫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8]潘其旭,覃乃昌.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9]陈明芳.中国崖棺葬[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10]过伟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出版中心,2001.
[11]周国茂.摩教与摩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