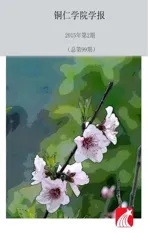彝族“撮泰吉”与希腊狄奥尼索斯崇拜比较研究
2015-02-13刘艳
刘 艳
( 铜仁学院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贵州 铜仁 554300 )
【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彝族“撮泰吉”与希腊狄奥尼索斯崇拜比较研究
刘 艳
( 铜仁学院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贵州 铜仁 554300 )
在资料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宗教学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以彝族“撮泰吉”与希腊狄奥尼索斯崇拜为主题,探析了两者在祭程、供品、象征符号、祭祀目的及与戏剧的渊源方面的异同,旨在透过两者的社会表层实践,探寻人类共同的认知方式,揭示其蕴含的宗教文化象征及相似的祭祀本质。
撮泰吉; 狄奥尼索斯崇拜; 比较研究
一
狄奥尼索斯崇拜即酒神崇拜,源于古希腊,流行于底层民众,是一种以“生命—复活”为主题,祈求葡萄丰产的祭典,是西方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与狂欢之神,不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向虔众布施欢乐与慈爱。公元前7世纪,随商贾关系渗入的古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更使狄奥尼索斯崇拜增添神秘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在文化堕落和经济衰微的资本主义后期让希腊人内心得到纯净和释放。在酒神祭典中,人们打破禁忌,复归自然,享受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1]。
“撮泰吉”,即“变人戏”,现仅存于贵州威宁,刻录了彝族先民的历史记忆,是彝族图腾崇拜在现实中的积淀。“撮泰吉”祭仪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是彝族灵魂的重要表征。目前“撮泰吉”仅存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且已处于濒危状态。保护“撮泰吉”对展示彝族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增强彝族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觉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撮泰吉”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被世人关注,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众多专家、学者从民俗学、宗教学、戏剧学等学科角度阐释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认知方式。纵观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定向于静态的现象与细节的描述,而忽视了对仪式内涵与本质的深化。鉴于此,在吸鉴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析这一宗教现象的内核,通过对“撮泰吉”与狄奥尼索斯崇拜的解构分析和比较剖释,探寻两种祭仪给人们带来的宗教体验和文化意蕴。
二
狄奥尼索斯崇拜和“撮泰吉”最初作为宗教演变的社会实践和行为,都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场域、祭舞等内容。在现代,这种宗教化的祭仪更多的是传承与再造。东西文化的迥异纵然使两者在场域、规矩及附加情境之中的符号存在差别,但同为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两者更多的表现出相似性。因为神灵的产生是相似的,早期的万物有灵观念和灵魂不灭意识,使祖灵崇拜滥觞于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并随宗教的深入发展而不断成熟完善。狄奥尼索斯崇拜和“撮泰吉”的产生都是基于人类早期普遍的原始思维习惯:通过与众神灵的“祈求性交流”,渴望获得某种神祗、精神、权力或其它圣灵的通融,希冀获得神灵庇佑,求其禳灾降福[2]。
(一) 从祭祀程序看
从仪式的构成部分看,狄奥尼索斯崇拜和“撮泰吉”都是古老宗教仪式的综合体。古希腊纪念狄奥尼索斯的绽花节在每年春季举行。绽花节共三天,始于黄昏,终于黄昏。在开坛日,人们打开酒坛,酒香吸引着狄奥尼索斯的灵魂从冥府归来;在酒罐日,人们开怀畅饮,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在瓦钵日,秘仪唤醒了大地上不朽的生命,人们唱着婚礼赞歌为狄奥尼索斯守夜。在狄奥尼索斯节日庆典上,还有庞大的“法勒斯”游行和狂欢活动。“撮泰吉”在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举行,含祭祀、正戏、喜庆和“扫火星”四个祭程。其中正戏又囊括迁徙、驯养、耕耘、丰收、繁衍等程序。祭祀场域选在寨子西方被山水包围的平地,传统的表演一般在夜间进行。祭祀伊始,人们在场地四隅挂上黑、白、红、绿四色“朵鲁”(即灯笼),伴随祷词与祭舞,引领祖先魂灵从寄居的岩洞归来。正戏也即耕作环节,带鸡蛋眼镜和修长白须的惹嘎布教授众“撮泰”劳动生存技能,模仿先民迁徙、创业。喜庆部分,人们敲锣舞狮,共庆丰收的喜悦。“撮泰吉”的扫寨环节,是村民的集体狂欢,人们在喜庆的场域里祈祷合境平安、儿孙满堂。
可见,两种仪式虽在个别指称上有所差别,如狄奥尼索斯祭拜中人们宰杀公牛,畅享美酒,葡萄和常春藤等植物性象征符号贯穿整个祭仪,而“撮泰吉”中主要是米酒和五谷食粮;狄奥尼索斯崇拜主要通过其随从来体现祭仪实质,而“撮泰吉”则通过直接扮演先民来体现祖灵崇拜。但其目的都是以祭颂、舞蹈等象征光明与欢乐的方式赞颂神灵,希望神灵赐予人类光明与欢乐。
(二) 从祭祀供品看
首先是酒。宗教祭仪中,酒是辅助信徒接近神境的媒介。祭酒能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参与者借助酒,得到与神交融的浑然感受。同时,人们借助肢体动作并附加如祷词、祭舞、面具等能驱魔逐恶的力量来战胜对鬼魂类邪恶力量的恐惧。酒让狄奥尼索斯的醉境迷狂染指成一种民众情绪,他的周围永远萦绕着鳞次栉比、浪醉狂荡的信徒,她们癫狂不羁、藐视常伦,酒使她们处于介乎神性与人性的模棱两可情境。如此便可达到一种交织着神性与信众界限的冰释,产生超越传统规矩和界限的变形[3]。“撮泰吉”里,佩戴面具的众“撮泰”在惹嘎布的引领下,供香献酒,祭颂祖先神灵。正月十五,惹嘎布领众“撮泰”从寨中居住位置最高的住户开始,自上而下扫火星,所到之家,主人斟酒献祭,惹嘎布酒敬祖宗和火神后,众人挨次饮酒,双手扶杖,摇头扭胯,齐念颂词,扫疾驱疫。
其次是血牲祭。自古血牲祭祀在神灵祭仪中就极为普遍。原始思维中羊是哺育者和启蒙者的象征,酒神祭中公羊是普遍的牺牲。参加完“法勒斯”游行的公羊在祭师的祈祷下宰杀,混同牛奶烹煮后放火上烤至灰烬。整个牲祭摹仿的是植物的生长过程和狄奥尼索斯的经历,通过牲祭再次感谢他赐予人类欢乐。“撮泰吉”里,人们供奉鸡、肉、鱼三牲,鸡为主要供奉之物,因鸡乃杀鬼之神的佐物。人们在神灵注视下,杀鸡祭血。如鸡在宰杀后仍扑腾,则暗示神灵已接受献祭。煮熟的三牲先供于神灵,祀毕,众人分享。
再次是各类食物。绽花节的瓦钵日,人们用新酒迎神,供奉头茬果实,用蔬菜与谷物调和的蜂蜜粥抚慰亡灵,用泉水调制的葡萄酒奠祭鬼魂。燔祭也存在于酒神祭仪,人们给神灵祭奉熟食和新酒,并在狂欢中进行集体的饕餮盛宴。“撮泰吉”里,“撮泰”们在祭拜神灵时,各家祭献各色干果。扫火星时,家家蒸馍煮肉,并备酒水果品在门前燃炮迎侯。“撮泰”们每扫一间房主人就祭献一个鸡蛋和一束麻。
(三)从祭祀的象征符号看
仪式是“符号的聚合体”,“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个世界”[4]。人们依据既定习俗,将仪式中的象征符号看作“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5]。植物是宗教祭仪中不可或缺的符号象征。酒神祭中,酒和常春藤是酒神生命表述中主要的叙事符号;“撮泰吉”里,五谷粮食的生命意象与四季的更替类同。
植物的符号表达隐喻了丰产和生殖的意向。首先,植物符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演绎。人们从植物生长中感受生命存在、体验生命变动、企盼生命永久,这是植物符号最直接的象征性内涵。其次,物质化的符号器具通过专属的仪式程序诠释了生命的永恒。酒神祭仪里的常春藤,原本就是永生的象征;“撮泰吉”里对先民生产、繁衍等的模仿,将生命的感知提升到极致。狄奥尼索斯崇拜里代表男性生殖器的控制符号与“撮泰吉”里的生殖崇拜不谋而合。再次,符号的能指向所指的转变,是祭仪从形式到内涵的升华。无论是狄奥尼索斯还是“撮泰吉”,其符号簇系统并非按常规思维的“类象”与“本象”归类,“而是直接观照自然现象的生命理解和附丽”。生命如四季,一岁一枯荣。狄奥尼索斯的“生-死—再生”,“撮泰吉”里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孩童的嬉戏与哺育,都完整的演绎了生命的基本循环,生命的自然形态与四季枯荣变迁浑然一体。
(四) 从祭祀目的看
驱魔辟邪是所有宗教祭仪的基本功能和共同目标。不论是狄奥尼索斯崇拜,还是“撮泰吉”,虽然仪程呈现差别,但驱鬼仍是其核心功能。古希腊纪念狄奥尼索斯的绽花节里,祭鬼是主轴。瓦罐日的晚上是不洁的,黑暗世界的魂灵在街上游荡,人们咀嚼乌荆子叶避邪,在门栏涂上沥青,防止鬼魂飘进来。瓦钵日,人们用蔬菜、谷物调和的蜂蜜粥抚慰鬼魂,夜幕降临时在沼泽地呼喊“绽花节结束了,走吧,鬼魂!”,呼喊声中,所有不洁与邪恶的精灵离开城市。“撮泰吉”里的驱鬼主要体现在扫火星。惹嘎布引领众“撮泰”高念祭词,众人齐呼“火星走喽,火星走喽,把不吉利的东西扫走喽”。绽花节的祭鬼驱逐了人们对冥界的恐惧,“撮泰吉”的祭鬼谴散了人们对鬼魂的畏怯,中西方先人对生与死的思索同时折射了灵魂转世的早期观念。
祛病逐疫也是“撮泰吉”的重要功能。扫寨仪式结束后,“撮泰”们在众人簇拥下奔跑至村外焚烧茅草,熊熊火焰象征全寨来年与病疫、火灾根断。最后支起三角架,用麻丝绑吊鸡蛋祭烧奠神,并埋下鸡蛋占卜来年吉凶。一年后,如蛋未烂,则预示今年风调雨顺、人畜平安;如蛋已腐,则暗示不祥之兆。扫寨至久婚不育之家,“撮泰”们在火坑上祭酒后将拐杖插于灰烬中,阿布摩与阿达姆做交媾示意动作并附上风趣逗乐之语,驱晦迎新,祈祷神灵送子。
“驱鬼”与“迎神”是同一仪式功能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绽花节更多体现为驱鬼,酒神节则更多为迎神。在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宗教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模糊:神既是秩序的力量也是无序的根源,神龛既是神圣同时也是危险的所在,鬼与神本就是对立的统一。“撮泰吉”亦如此。人们插香奠酒吟颂祭词祭拜各路神灵,临摹先人迁徙、繁衍,表演“铃铛舞”和“狮子舞”,主旨就是娱神。通过祭仪让神灵愉悦,得到眷怜。而全寨性的“扫火星”则是彝族人们在恶劣自然环境下趋灾避祸的集体活动,更多的作用于驱鬼。究其本质,两种祭仪都是以安抚的形式驱鬼逐魔,从而达到净化生存环境、保护丰产,带来幸福平安的目的。
(五)从祭祀与戏剧的渊源看
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曾指出,戏剧来源于对祭仪的摹仿。众多学者也对亚氏理论进行过考述和推证。伴随历史变迁和种族交融,戏剧与仪式的渊源已形成独特的话语系统。祭仪成为横亘于神祗与原始戏剧间一个不言自明的中介,戏剧的仪式起源说也长期被视为戏剧发生学解释的经典之说。酒神祭仪催生了希腊悲剧,而彝族“撮泰吉”也与傩戏的产生息息相关。
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酒神祭成为希腊悲剧的缘生形貌,基于以下三点。其一,酒神颂歌衍生了戏剧的雏态。古风时代,酒神颂歌是整个祭仪的主轴。伴随商业演进酒神颂渐成有组织的神圣化活动,也成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无论是从历史的逻辑性考虑,还是从“原作”与“临摹”的二元关系探究,抑或是在二元关系上的派生与演绎,都不可否认,仪式是戏剧的本源。希腊悲剧的酒神起源说在历史的累积和检验中已成“公理”。其三,悲剧意为“山羊之歌”,系模仿狄奥尼索斯随从萨提尔之称。悲剧与萨提尔剧(羊人剧)在“前戏剧形态”的渊源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撮泰吉”作为傩戏雏形,相较于傩戏,处处彰显其原始风貌。首先,“撮泰吉”剧目单一,情节拙朴,带有早期傩戏祭祀神灵和驱逐瘟疫的共同特征。其次,“撮泰吉”面具造型粗犷,色调单一,延续了古代祀神驱鬼活动中鬼神面具的基本风格。再次,祭祀中请走火神和瘟疫的山神老人(即惹嘎布),是傩戏巫师“毕摩”的原型。流动的演出场地、类似猿猴的怪腔、矮蹲状的行走方式、生产间隙的两性交媾,无不彰显“撮泰吉”是一种古朴的傩戏雏形[6]。
可见,两种祭仪都是戏剧的雏态。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动作、语言、器具等的结合完成一个形式上的仪礼性过渡,实现潜意识里的宣泄功能,引起“恐惧和怜悯”的戏剧效果,起到“净化情感”的作用。另一方面,两种祭仪中所有亲历者并非“真正的本人”,而是根据特定语境转化为“符合规范的人”。这种转化和代理关系,契合了亚氏关于“戏剧起源于仪式的摹仿”的论断。
(六)对祭祀本质的思考
西方的酒神崇拜实质上是对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生命”主题的弘扬。狄奥尼索斯是人之本真形象的最强冲动的表达,是自然界性的万能力量的象征。对欢乐与生命力的追求和肯定,也是“撮泰吉”的本质诉求。这个活动的主旨就是禳灾纳福,毓子孕孙。
首先是生命本质。种族繁衍是人类重要的本能需求。酒神崇拜是解除束缚、复归自然的体验,它催发人内心的癫狂,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7]5。图腾崇拜的原始时代,生殖器是与自然万物具有同在生命力的象征,正如纯粹奔腾的葡萄酒象征着丰收与喜悦,阳具展示的是狄奥尼索斯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是淫荡的色情欲望。塞斯谟福利节仪式中扛着生殖器造型游行的妇女以狂女的形象成为狄奥尼索斯的随从;酒神祭中,生殖器造型在萨提儿身上以夸张的形式体现出来。游行队伍中狄奥尼索斯阳具的出现激活了世间万物的活力,人们欢歌狂舞,淋漓尽致的表达对生命的崇拜和对丰收的渴望。
“撮泰吉”中的交媾行为和情歌演唱也镜射了人类现实的生命之根。生产间歇,嘿布突袭阿达摩从背后与之交媾,阿布摩追赶嘿布后又与阿达摩交媾。“扫火星”里,惹嘎布将拐杖插入火坑摇晃(暗示交媾),教不育夫妇模仿原始交媾方式并以情歌逗乐。这不仅是彝族顺势巫术观念的反映,也影射了彝族人民祈求繁衍传承的人生观。同时,穿插在丰收仪式中的繁衍意象,镜射了农耕文化,祈望生产丰收。
其次,是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既有参与者的绝对平等,也包含精神的彻底放松和本性的真实袒露。在酒神祭中,狄奥尼索斯崇拜演化成一种迷醉,人们抛弃界限,载歌载舞,沉醉于集体的狂欢。这种对原始生命和人类冲动的本真诠释,在疏导情绪的同时释放了精神的原动力。“法勒斯”游行里的狂女,借助精神的力量进入迷醉状态,外表张狂,内心纯洁。这种力量本质是宣泄对疾病与自然的惧怕,解脱内心,并在经历不幸和哀痛后仍觉得世界充满了欢愉和美。作为宗教祭仪,“撮泰吉”也升华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祭仪里长途跋涉的雄浑气魄、开荒耕作的拙朴情节、生产与繁衍的粗犷原始都让人身临其境,先民不畏险阻的精神和图求生存的意志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人们对五谷神灵的顶礼膜拜、众“撮泰”的纳吉祈福,无不彰显人们积极的人生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激励着整个民族继往开来。
两种祭仪都充满了原始情调和乡土本色的自然主题,人们回归生物本能,释放自由。对生命的张扬和对精神自由的讴歌,贯穿祭仪始终,是酒神精神与“撮泰”精神的完美演绎。“生命-复活”是酒神祭的主题。从生命角度看艺术,酒神是万物根基,若缺乏精神支撑,生命早不堪一击。生命的本质,就是酒神祭的根本。“撮泰吉”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祭仪,无论是迁徙的艰辛、丰收的喜庆,还是“扫火星”时的驱病除魔,抑或是男女交合示意动作,均是古代彝族为恢复土地孕育力而举行的“孕育仪式”的遗留,都是以人的生命意识作底蕴,处处洋溢着对生命意志的肯定、对精神自由的礼赞和种族繁衍的永恒追求。
三
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野蛮/文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神圣/世俗”到格鲁克曼(Mikael Krogerus)的“冲突/整合”,随着内涵的深化,仪式逐渐成了人类与神祗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话语表达。人们从仪式中管窥到社会历史变迁的主题、人类复杂感情的杂糅和自然关系的经纬纵横。虽然在狄奥尼索斯崇拜与“撮泰吉”里,洁净和危险都还没达到人为宗教在系统教义下的缜密分类,但仪式对传统的凝聚与颠覆、对现实与超现实的整合在两种祭仪中仍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仪式的阈限理论昭告人类生命如斯的流程以及不可复返的阶段过渡形式。酒神祭里,常春藤等植物的一岁一枯荣、狄奥尼索斯从宙斯大腿的出生到被赫拉迫害致死;“撮泰吉”里,先人迁徙开荒、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植物与人类的生命流程融为一体,无可复返。另一方面,仪式行动着宗教的可操控精神,人们在仪式实践过程中介入对待生命期许的有效指喻,生命的价值并非无可奈何,而是形同自然节律循环复返而已。酒神的“生-死-再生”,“撮泰吉”里的耕种与的繁衍,都在讴歌生命与自由的同时淡化了生命的阈限和过渡边界。
纵然古希腊民族与我国彝族在文明起源、历史背景及宗教理念上各相迥异,但酒神祭与“撮泰吉”却有着相近的祭程、目的和宗教内核,处处洋溢着对生命的礼赞与对精神自由的探寻。透过“撮泰吉”表层,它所镜射的喜庆、欢乐、企盼与酒神精神完全契合。无论绽花节,还是“扫火星”,人们在严冬的祭仪里渴望春天的到来,送走鬼魅,迎来希望。这不仅是一种心理期盼,更是一种生命在时节中的阈限性通过,是东西方先民对生命认知的摹仿和企盼做出的同一诠释。此外,两种祭仪里的神灵都有明显的“致病/治病”的双重隐喻。古风时代,因疾病而留下的悲怆使人类将疾病认知成超自然力量,内心的害怕恐惧,寄托于祭祷来排解和宣泄。狄奥尼索斯作为理性的“逆子”、文明的“病患”,祭仪所包含的“病一药一酒一醉”的祭程恰恰就是自我治疗,而人们通过酒神祭唤起内心的怜悯与恐惧,达到净化治病的目的。自古东方祭仪就重视它的治疗作用,“撮泰吉”里耕作环节的欢畅、丰收环节的喜庆、扫火星时的庄重、不孕夫妇对生殖的企盼,通过“撮泰”在祭仪中对各种符码的解读,平复了人类心理上“本我”的本能性盲目与“自我”的理智性洞见间的矛盾与冲突。
总之,不论是狄奥尼索斯崇拜还是彝族的“撮泰吉”,都是人类文明长期积淀而成的宗教文化象征。祭仪里神祗与病魔两个完全迥异的结构性隐喻与人类生命存在形式的欲望与平和相通缀,萨提尔与“撮泰”们通过祭仪展演传递着共同体的袭成价值和知识表述。在祭仪中,虔诚的信徒摆脱束缚,讴歌生命,通过仪式换取对附丽其中的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可。狄奥尼索斯崇拜里对人类自然之性的展露,对民族传统、族群发展等社会记忆的贮存与扬弃,与“撮泰吉”中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对社会变迁的展示如出一辙。对生命力的肯定,对精神自由的讴歌,正是“撮泰吉”中“酒神精神”的根本。
[1] 魏凤莲,刘立辉.狄奥尼索斯来源考证[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4).
[2] 彭兆荣.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3] 彭兆荣.西方戏剧与酒神仪式的缘生形态[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2,(3).
[4] Turner, V. W. 1986. The Drums of Affl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endon press):2 .
[5] Geertz ,C. 1973.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12.
[6] 长白雁.贵州彝族的原始傩戏雏形——撮泰吉[J].中华艺术论丛,2009,(9).
[7]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A Comparison of “Cuotaiji” Rite of Yi People and Dionysus Worship in Greece
LIU Yan
( Department of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Guizhou 554300, China )
Based on the materials arrangement and field work, using a comparativ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n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uotaiji” rite of Yi People and the Greek Dionysus worship as its theme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ir ritual procedures, offerings, symbols,ritual purpos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to the origin of drama. It explores the common cognitive model of human beings, reveals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similar nature of sacrifice through the superficial social practices of “Cuotaiji” rite and Dionysus worship.
“Cuotaiji” rite, Dionysus worship, comparative study
G127
A
1673-9639 (2015) 02-0099-05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5-01-11
刘 艳(1986-),女,汉族,湖南长沙人,铜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