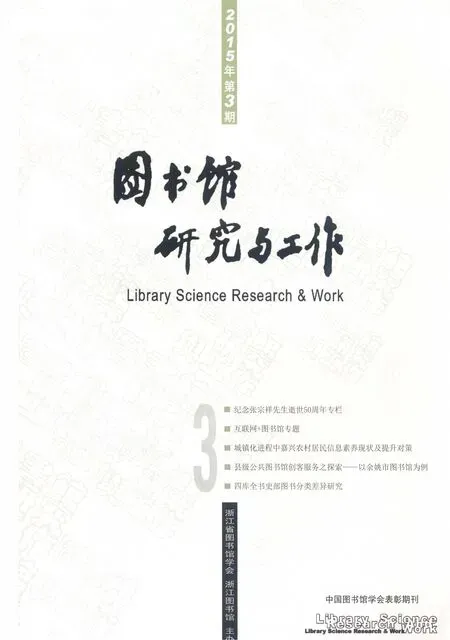四库全书史部图书分类差异研究*
2015-02-13江庆柏
江庆柏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7)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它的分类法也格外被人重视。但现有的研究多只是就《四库全书总目》来作分析,没有注意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放置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来研究。实际上,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其图书分类一直是在不断调整的。本文即以史部为例,分析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以下分别简称《初目》、《荟要总目》、《总目》)分类的差异。《初目》为乾隆年间抄本,现藏台北国图,这是最早给四库图书进行完整系统分类的一部目录。《荟要总目》是编纂《四库全书荟要》时所形成的一部目录,其形成时间在《初目》之后、《总目》之前。《总目》是最后完成的一部《四库全书》目录。
为说明问题,先将三部目录的分类情况列举如下:
《初目》分为17类: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类、传记类、史抄类、时令类、法令类、地理类、职官类、目录类、金石类、史评类、故事类、谱牒类、起居注类。
《荟要总目》分为12类:正史类、编年类、时令类、地理类、诏令类、法制类、别史类、故事类、史评类、目录类、器用类、谱录类。
《总目》分为15类: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以下我们从类目设置、类目名称、类目顺序三个方面,来考察《荟要总目》与《初目》及《总目》史部图书分类的异同。
关于史部类目的设置
从类目数量上看,《初目》分为17类,数量最多,《总目》其次,《荟要总目》最少。《荟要总目》类目数量少,与其收录图书数量较少有一定关系。
《荟要总目》与《初目》、《总目》共有的类目有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时令类、地理类、史评类、目录类7类(暂不考虑类目名称相同而内容或存有差异这种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部著作的基本类型,也都是我国古代史部目录的基本类目,所以《荟要总目》等都有此设置。
部分相同的有一种,即《初目》、《荟要总目》的诏令类,《总目》作诏令奏议类。《初目》和《荟要总目》在史部设置了诏令类,在集部另有奏议类。《总目》则将两类合并为一类。《总目》卷首“凡例”说:“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入集部。今以其事关国政,诏令从《唐志》例入史部,奏议从《汉志》例亦入史部。”不过《总目》虽然将诏令、奏议合并为一个类目,而实际上其下面还是分立为诏令、奏议两个三级类目的。《总目》的这个合并有一定道理。
如果将这8类去掉,《荟要总目》还有法制类、故事类、器用类、谱录类4类。这4个类目,故事类与《初目》名称相同,谱录类与《总目》子部类目名称相同,法制类、器用类这两个类目的名称则是《荟要总目》独有的。但不管是与《初目》或《总目》相同,还是《荟要总目》独有,其类目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再看传记类的设置。传记类是史部的一个大类,如《总目》传记类叙所言:“魏、晋以来,作者弥夥。”在历代史志书目中,都设有这一类目。这一类目的名称,最初称之为杂传。杂传是相对于正史列传而言的。梁代阮孝绪在《七录》中设有“纪传录”一门,其“杂传部”著录正史以外的传类作品241种(《广弘明集》卷三)。之后的《隋书经籍志》对此有具体说明:“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也就是记载各类人物的事迹。其后“杂传”成为史志目录的必有类目。《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改名“传记”,自此以后“传记”也就成为这一类目的基本名称。在《四库全书》中,收录圣贤、名人、总录、杂录类传记合计60部。《初目》也设有这一类目。《四库全书荟要》未设此类,原因不得而知。可能因为《荟要》收录图书量少,类目设置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就将内容与正史、编年、别史类多少会有一些重复的传记类文献删去了。
再看纪事本末类,这是《总目》的创设。纪事本末类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基本体裁之一。《初目》收录有《宋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诸书,但未能设立“纪事本末”这一类目。《荟要》同样收录《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书。《荟要提要》已经注意到了这类著作的特点,经部春秋类所收《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提要云:“史家记事之例,初别六家,后归二体,编年、纪传,相辅而行。至宋孝宗时,袁枢创纪事本末,使一事自具首尾,循览易明,遂于二体之外,别为门径。”可见《荟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纪事本末这一体裁“自具首尾”这个特点,并认为这一体裁的出现是在传统的编年、纪传体史书外另立了一个“门径”。但《荟要》同样未能设立“纪事本末”这一类目。这是很遗憾的。《四库全书》注意到了这类著作的特点,并根据图书性质与书名标注,设立了“纪事本末类”这个类目,使我国图书分类更为精密,也使得我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式得到更完善的概括。
由于《荟要》收录图书数量较少,在类目设置上就受到了很多限制。其类目的设置情况与《初目》、《全书》不可简单类比,但比较其间的差异,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的。这不是指责《荟要》的疏漏,而是为了更好地看到古籍图书分类的发展演化情况。
关于史部类目的名称
如上所说,《荟要总目》史部类目中,法制、故事、器用、谱录这4类名称,与《初目》、《总目》或同或不同,但类目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以下依次讨论。
《荟要》法制类收录《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国朝宫史》四部书,都与典礼等有关。《荟要总目》《法制类叙》云:“臣谨案:旧史簿录多以‘刑法’为一目,‘仪注’为一目,而礼节制度则附于‘礼经’。臣窃以为因革损益,定一代之章程者,莫大于会典。其中礼制纲要,虽已略备,而仪节度数,或未详晰,则别为通礼。故二者常相辅也。兹特立‘法制’一目,恭载钦颁二书,而图式类次之。至于《宫史》一编,首载训谕及诸典礼官制,因亦同编于此,未敢用旧史《汉宫阁簿》、《洛阳宫殿簿》之例,入地理类也。”
作为图书分类类目名称,法制类最早见于《七录》记传录,名为“法制部”。但自此以后,目录书似未再用这一名称,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至《明史艺文志》等都是如此。所以《荟要总目》在提及历史上有关这类图书的著录时,也只是提及“仪注”这一名称,而没有提及“法制”这一名称。
“仪注”这一名称,最早也见于《七录》,作“仪典部”,《隋书经籍志》改称“仪注”,其后自《旧唐书经籍志》以下史志书目亦都用这一名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汉旧仪》四卷、《晋新定仪注》四十卷等,是所说仪注即指制度、仪节,《隋书经籍志》《仪注篇叙》所说进止威仪之数、朝仪、节文等都指此。
《荟要总目》认为所谓的“礼”既包括仪节度数,即具体的程序形式,也包括礼制纲要,即制度问题。不过奇怪的是《荟要总目》在设立这个类目时并没有使用在我们看来更为明确合理且也是历代书目都采用的“仪注”这个名称,而是用了一个相比起来并不十分恰当,而且后来的书目也都不再使用的“法制”这个名称。也许在《荟要总目》看来,“仪注”这个名称过于偏重于仪式、程序这些方面,与自己所收录的主要是有关礼的制度方面的图书距离过远。但“法制”这个名称同样是模糊的。而且就《荟要》收录的四部图书看,《钦定大清会典》固然多论及清朝制度,而《钦定大清通礼》等,实际也多是记述相关仪式。《荟要》卷首所载《联句》诗写道:“令典迈陶妫姒子。”自注:“皇朝制度,备于《大清会典》。其中节文仪数,则《大清通礼》、《礼器图式》所载尤详。而《宫史》一书,实昭宫庭典式。今并列为。”说得非常清楚。
或许仪注、法制这些名称都不够恰当,所以在《总目》里都没有保留。《总目》将这类图书都收录在了“政书”这一类中,并在政书类下再次细分为通制、典礼、法令等目。《钦定大清会典》被收入通制之属,《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国朝宫史》被收入典礼之属。
《荟要总目》使用的这个法制类名称,在《初目》中比较接近的类目是法令类,收录《疑狱集》《补疑狱集》、《科场条贯》。法令类,在《七录》中称之为“法制部”,其后通常称为刑法类,只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之为法令类。《总目》中,“法令”这个类目被列为政书类下面的一个类目。
《初目》与《荟要总目》类目名称相同且所收录图书内容也相同的有故事类。
“故事”作为图书分类的类目名称,最初称之为“旧事”,也见于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其后《隋书经籍志》沿用了这一名称,并对这一类目的性质作了说明。其文所说“旧事”,简单地说,就是指记载以前的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等状况的著作。《隋书》以后,《旧唐书经籍志》设有同一名称的类目,《新唐书》、《宋史》、《明史》艺文志及《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称为“故事类”,《直斋书录解题》则称之为“典故类”。名称不同,实质无异。
《初目》史部故事类收录图书31种,大多见于上述各史志书目的故事类(或典故类)。《荟要》故事类收录有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两种。其《通典》即见于《文献通考经籍考》故事类、《直斋书录解题》典故类。《明史艺文志》只收录明人著作,收录有明人王圻所撰与《文献通考》性质类似的《续文献通考》,也在故事类。由此可以说《初目》、《荟要总目》的故事类,当是沿用了历史上这一类目的名称。
《总目》取消了“故事”这一名目,而将收录有关典章制度的图书归之于政书类。《总目》卷八十一政书类叙批评了以往书目将这类图书称之为“故事”的不当,认为“循名误列,义例殊乖”。然后指出命名为政书类的理由:“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惟我皇上制作日新,垂模册府,业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袭旧名。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义焉。”“政书”一词作为一类文献的类名,源于明钱溥《秘阁书目》。虽说“政书”一名并非《总目》新创,但这一名称确实能够更好地反映这一类文献的性质,名实相符。而且政书类作为后来使用极为普遍的一个部类名称,也应归功于《总目》的使用。政书类这一名称的确立,是四库馆臣认真思考的结果。这一名称比《初目》、《荟要总目》都要贴切。
不过《荟要总目》所列名称虽不贴切,但其对这类图书的认识还是很明确的,其谓“考鉴制度,宪章旧闻”、“览其因革之故,亦可以参验得失”,也都说出了这类图书的性质及其功用。《荟要》卷首所载《联句》诗写道:“旧章备礼乐刑兵。”原注:“志故事者,代有成编,不啻充栋。《通典》、《通考》二书,其职志也。”此谓《通典》、《通考》两书,为史部故事类图书的代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在我国古代的目录书中,“器用”这个类目名称使用的不多。就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时常用的目录书来看,也未有专门列出“器用”一类目的。《荟要》所收录器用类著作共两部,即《西清古鉴》与《钱录》。由此可见,所谓器用类,收录的图书实际就是金石类著作。
在编纂四库书之前,目录书没有专门设立金石一类的,有关金石类的著作都收录在目录类中。目录类这一名称,在《隋书经籍志》中称为簿录,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中称为目录类(或目录)。其时著录的都是书目类著作。从《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开始,目录类著录的图书,除了传统的书目类著作,如《七录》、《崇文总目》之类外,还开始著录金石类著作,如《遂初堂书目》著录有《赵氏金石录》、《川郡金石录》等,《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田概《京兆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等。《京兆尹金石录》、《金石录》在《宋史》中,也是著录在目录类中的。《千顷堂书目》卷十簿录类,既著录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也著录顾起元《金陵古金石考目》等,都是书目著作、金石目录著作一起著录。
在《荟要》编纂之前,只有《初目》将书目与金石分作两类。《初目》既设有目录类,也设有金石类。《荟要总目》承袭了这一点,也将书目与金石著作分别设立为目录类、器用类两个类目。就这一点来说,《荟要总目》及《初目》确实有独到之处。但遗憾的是,《荟要总目》使用了器用类这个名称,而未能使用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金石类这个名称。就类目的设置这方面看,金石类这个名称无疑比器用类这个名称具有更大的容量,也具有更多的通适性。器用可以是金石的一个部分,它不能等同、不能涵盖金石学的全部内容。就这一点来说,是在《初目》的基础上倒退了。
需要说明的是,《总目》同样只设立了目录类,而将金石学著作系于该类之下。金石学自宋代开始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王国维说:“自宋人始为金石学,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 金石研究发展到清代,已蔚为显学。据《四库全书》统计,其收入的目录著作为11部,而金石著作则多达36部。金石著作数量远远高于目录著作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总目》非但没有将目录、金石分开设置,反而将金石合并于目录中,就很不合理。如果说没有《初目》、《荟要总目》的分类在前,《总目》将金石合于目录成一编,尚可说是继承了历代编目的传统,有历史的根据,如《总目》卷八十五目录类叙所说:“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学,《宋志》乃附目录。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那么在《初目》、《荟要总目》已将金石独立成类的情况下,《总目》仍将金石并入书目,就显得在图书分类的观念上落后了。
因此尽管《初目》的分类总体上说不如《总目》精细、合理,但如金石类的设置,比《总目》要合理。同时尽管《荟要总目》设立的“器用类”这个名称不尽妥当,但从分类的角度看,仍要优于《总目》。
《荟要总目》的谱录类与《初目》的谱牒类,看上去名称接近,但实际上内容有差异。从《初目》谱牒类所收录的四部图书《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吴越顺存集》、《顾氏谱系考》、《希姓补》来看,这一类收录都是与记载宗族成员世系或人物事迹有关的图书。而《荟要总目》的谱录类所收录的则是用图谱这一形式编著的图书。这两类图书实际上会有某种交叉,但就《荟要总目》的说明及实际收录的图书看,与谱牒类毫无关系。
与《荟要总目》谱录类名称相同的是《总目》子部的谱录类。不过这两个类目也是名称略为相同而已,实际上对这个类目的理解《荟要总目》与《总目》并不相同。
“谱录类”作为部类名称,最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在此之前,目录书并无这一名称。《遂初堂书目》在子部创立了“谱录”一门,将附记于其他部类的图书单独归为一类,所著录的图书有《宣和博古图》、《钱谱》、《锦谱》、《茶谱》、《竹谱》等。《总目》对这一类目的设置评价极高,称“为例最善”。但这一类目并没有被其后的目录书采用,宋元史艺文志都没有这一类目。《宋史艺文志》中《笋谱》等类著作依然被收录在农家类,甚至《钱谱》也收录在农家类中。《宣和博古图》则被收在经部小学类。
在图书分类中,重新设立谱录类的,是四库馆臣。现在一般论著,都将在《遂初堂书目》之后谱录类的重新设置归之于《总目》。而实际上,《遂初堂书目》之后最早重新设立谱录类的,是《荟要》。《荟要》在史部设立了谱录类,收录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一书。《帝王经世图谱》书前提要校于乾隆四十二年八月,而《四库全书》谱录类中收录的图书都在这一时间之后。所以准确地说,《遂初堂书目》之后最早重新设立谱录类的并不是《总目》。
《荟要》在其“总目”及书前提要中,对谱录类的相关情况作了具体说明。《荟要总目》云:“谱录之书,体裁不一,或以程器用,或以志艺术,或以纪动植。盖小说者流,非史家所重也。若夫禀经酌雅,纲举条晰,成一家之言,为有用之学,则唐仲友之作,洵为创格,而后亦罕继之者。兹于尘埋蠧蚀中,得大圣人表章而出之,抑亦幸矣。昔人著录,多入子部,今以其有关于经世之事,而并记往古之说者,故特为标曰‘谱录’,用殿史部云。”在《帝王经世图谱》书前提要中又写道:“其书缀图列谱,分类纂言。”
《荟要总目》首先指出了谱录类图书的内容,即程器用、志艺术、纪动植。然后指出由于这类图书的性质同于小说者流,因而不被史家看重。《荟要总目》认为《帝王经世图谱》这部图书,形式上采用了谱录的方法,“缀图列谱,分类纂言”,内容上则是“禀经酌雅”,依据经书阐说帝王治国的道理,为有用之学。这属于谱录类的“创格”,所以《荟要》史部收录了这部图书。《荟要总目》最后特别说明了将谱录类图书由子部提升入史部的理由。
不过《荟要总目》的做法没有得到《总目》的认可。《总目》将谱录类列入子部,分为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类。《四库全书》则按照所分三类收录有关图书55部。
《总目》卷一百十五谱录类叙云:“《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颇病于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按照《总目》的这一看法,所谓谱录类,收录的是较为系统记载事物类别的图书。《总目》批评的是以往的书目随意放置这类图书的情况,但对谱录类的性质,与传统的看法并无二致。所以在《四库全书》中,《帝王经世图谱》被收入子部类书类,而不是谱录类。
《荟要总目》的观点之所以未被《总目》采纳,我想可能在于《荟要总目》的观点既不符合这类图书历史上的归属情况,也不符合这类图书的实际内容。《荟要总目》与《总目》对历代书目的著录都有批评,但《总目》不满的是关于这类图书归类的混乱状况,对谱录类图书的性质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荟要总目》则还根本否定了这类图书的原本属性,且任意从子部提升至史部。
谱录类收录的图书其所反映的应该是具体的事物,即《总目》所说的“专明一事一物”(《总目》卷一百二十三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按语),而不是抽象的观念、思想等等。所以但就这一点看,将《帝王经世图谱》收入谱录类也显得不合情理。
《荟要提要》云:“兹于尘埋蠧蚀中,得大圣人表章而出之,抑亦幸矣。昔人著录,多入子部。今以其有关于经世之事,而并记往古之说者,故特为标曰‘谱录’,用殿史部云。”所谓“大圣人”,即乾隆帝,所谓“于尘埋蠧蚀中”、“表章而出之”,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荟要》卷首所载《联句》诗写道:“图居史左赏经营。”原注:“《永乐大典》内所采辑《帝王经世图谱》一书,仰蒙御题褒赏,谨载入谱录类,固非花谱、茶录所可拟也。”其书前提要也说:“伏蒙皇上亲洒奎章,特加褒许,并付剞劂,以广流传。以数百载湮没之陈编,获邀大圣人之品题,遂得与日星同炳。臣等编次之余,既仰钦宸训,且以庆是书之遭云。”可见此书获得《荟要》重视,很大程度上与乾隆帝对此书的表彰有关。虽说我们今天来研究《四库全书》及《荟要》的编纂,必须充分考虑到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如《荟要》对《帝王经世图谱》一书的处理那样,完全根据乾隆帝的态度来决定此书的归属及评价,就与图书的学术性相距过远了。
因此我们认为,《荟要总目》关于谱录类性质的阐述及在四部分类法中的归隶,都是非常不恰当的,是违背我国古籍分类的基本规律的。《四库全书》与《总目》未采纳《荟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史部类目的顺序
由于史部文献类目名称及各类目之间的顺序差异较大,这里无法一一比较,兹就其大者略加分析。
就《荟要总目》与《初目》、《总目》史部顺序看,其最大的差别在地理类的位置。《荟要总目》共12类,地理类在第4位,仅在正史类、编年类、时令类之后,这个位置是非常靠前的。尽管在《初目》、《总目》史部类目中,地理类的位置也不一致,但都较靠后。《初目》17类,地理类在第10位;《总目》15类,地理类在第11位。
在我国传统目录著作中,地理类的位置在史部中通常都是靠后的。如《七录》记传录12部,土地部在第10部。地理类在史部中的这个位置是符合类目性质特点的。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历史和地理是两门平行发展的学科。但在我国古代的观念中,“治史”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作“治世”之鉴,所以通常把地理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空间舞台。这样,在图书四部分类法中,地理类即从属于史部。
地理类虽列入史部,但与那些以人物、事件、时间为中心的历史著作相比,毕竟也还有一些差别,所以历代书目将其在史部中的位置安排在后面,通常仅仅在目录等这些没有多少明显的人物、事件、时间或地理因素的类目之前,是可以理解的。在《总目》中,地理类之前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类等10类。这些类目所记内容大都与人物、事件、时间相关,所以《总目》对地理类的安排是合理的。而在《荟要总目》中,地理类前面的3类固然与人物、事件、时间有一定关系,而在其之后,如诏令类、别史类、故事类,也都与上述内容有关,所以从这个史部分类这个层面看,地理类排在第4类并不恰当,也不符合已经形成的关于地理类性质的基本看法。
再如《荟要总目》史部将时令类排在第三,也非常不恰当。时令类著作中人的因素极为淡薄,与主要记载过去的人类活动的著作如传记类、载记类著作相比,仍然应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初目》将其置于第10类,是恰当的。《初目》置于第8类,虽然不如《总目》恰当,也要优于《荟要总目》。这些也都是《荟要总目》史部类目的不足之处。
所以虽然由于《荟要》收录图书较少,其分类情况不能和《总目》作完全比较,但就现有情况看,《荟要》分类虽有优于《总目》之处,但总体上不如《总目》合理。《总目》吸取了在其之前的《初目》、《荟要总目》的分类成果,代表了当时图书分类方面的最高成就。
〔1〕纪昀.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
〔2〕纪昀.四库全书荟要总目﹝M﹞.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85-1988
〔3〕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台湾世界书局编辑部编.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Z﹞.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85-1988
〔5〕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990
〔6〕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