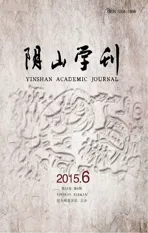合作化小说的农民主体性建构
2015-02-12张连义
张 连 义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中文系,江苏 常州 213001)
合作化小说的农民主体性建构
张 连 义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中文系,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自“五四”新文学始,农民就成为文学中的重要形象,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讲话》虽然赋予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但文学中的农民还是摆脱不了被启蒙的尴尬地位。合作化运动中,诸多作家深入农村,对农村现状的熟悉和农民命运的了解使他们的创作有了农民的立场,也为合作化小说的农民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基础。但由于环境的制约,农民主体性带有了更多政治的因素,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主体性。
关键词:合作化小说;农民;主体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发现”了农民并赋予其重要地位,但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一直作为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存在于文学之中,即使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甚至5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农民也并未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没有体现出主体性。农民真正以主人公的身份进行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并实践之,集中体现在合作化小说中,合作化小说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剧烈变革,也在想象中建构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不过,由于当时的特殊的社会形势,农民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所规约,其主体性也带有了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使其主体性体现出双重性和复杂性。本文即对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主体性建构进行简要探讨。
一、解放区小说中的农民:被启蒙的客体
清末以降,基于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与追求,在具有先进思想的诸多“五四”学人的现代化国家想象中,传统不断遭遇否定,负载着传统思想的农民自然地成为启蒙的对象,其麻木、愚昧、自私、落后的形象定格在了现代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将其置于未来国家结构中的重要位置;马克思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及其中国化的阐释,更从理论上肯定了农民的重要地位,农民成为共产党政权政治想象中的未来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毛泽东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更是一改历史上农民的从属地位,旗帜鲜明地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地位进行了置换,农民被赋予了政治主体性地位,也成为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成为“学生”和被改造的对象。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文艺创作的指导性原则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被边缘化了,‘工农兵’成为‘人民大众’的同名词或代名词,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是农民,当时的工人、士兵大都是来自农民,这样农民自然就成了人民大众的核心。”[1]《讲话》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处于当时的特定环境,也就变为主要为农民服务,而毛泽东的特殊定位更使《讲话》成为解放区作家创作的指导性文件。在《讲话》的思想指导下,解放区作家自觉地深入群众,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解放区农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对于大部分作家尤其是由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作家来说,他们的思想转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痛苦的过程,当时一些知名作家进入解放区后的创作焦虑就反映出这一事实;而对于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且出身于农村的解放区作家,反映乡村风景和农民生活则是其创作的常态,但出于解放农民、发动农民的政治需要,尤其是潜意识中的知识分子思维,使其创作呈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
《小二黑结婚》被誉为实践《讲话》的代表性作品,赵树理也藉此树立了自己在解放区文学中的权威地位。作品中的故事原型是民间青年男女的恩怨情仇,小二黑的原型岳冬至与同村青年石献英等三名村干部因为追求一个叫智英祥的女青年产生矛盾,并被他们打死。赵树理在下乡的时候听说了这个故事,将之做了艺术化处理,改编成《小二黑结婚》。在原故事中,岳冬至有童养媳又和智英祥恋爱,在当时的农民看来显然是作风问题,石献英等对其斗争、捆打,在民间伦理看来也合乎情理。这也难怪即使石献英等接受惩罚的时候也不服气,甚至村人也对岳冬至持否定态度。“岳冬至和智英祥的恋爱本来是合法的,但是社会上连他俩的家庭在内没有一个人同情。”“斗争会叫岳冬至承认错误,正是叫他把对的承认成错的,事后村里人虽然也说不该打死他,确赞成教训他”。[2](P188)可见,在乡村传统观念中,岳冬至是违反乡村伦理的。但在解放区的政治宣传中,童养媳、包办婚姻等属于封建社会的遗留物,是应该也必须否定的,由此看,岳冬至与智英祥的恋爱又是合理的,并且由于符合新政策又是合法的。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由此发生了抵牾。赵树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以启蒙者的立场强化民间传统的愚昧成分,突出了民间传统的愚昧伦理对青年人爱情的干涉和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以此肯定政治伦理的合理性并籍此达到政治宣传的效果。作品中,二诸葛和三仙姑一个是阴阳先生、一个是神婆,都具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二诸葛因为“不宜栽种”的迷信耽误了生产,成为村民的笑柄。三仙姑好吃懒做、性情风骚,“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为了钱财,三仙姑将女儿小芹许配给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刚丧偶的退职军官吴先生,吴先生的身份,无论是在政治上——阎锡山部下的退职军官,还是在伦理上——年龄大且刚丧偶,都应该是否定的对象,三仙姑将小芹许配给吴先生又拿取钱财,无疑有着道德上的缺陷。由此不难看出作家对三仙姑道德上的否定姿态。作家对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塑造尤其是对他们弱点的强化显然是为了否定封建性的糟粕,但显然,熟悉农村农民的作家否定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影响着他们行为和思想的封建伦理。所以,作品并没有对二诸葛、三仙姑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他们揭示迷信的危害从而达到否定封建伦理的目的,并由此确立作为新政权支撑的政治伦理的合理性。“原故事的结局,赵树理觉得太悲惨了,他认为既然写反封建的东西,就应该给正面人物找下出路,照原来那个结局,正面人物是被封建习惯吃了的,写出来不能指导青年和封建习惯作斗争的方向。可是当时是革命的初期,群众性的胜利,例子还不多,光明的萌芽,还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支持着的(当时的村长大部分是上面委派的,所派的人还不一定是本村的人),除了到上级去解决,赵树理没有想到其它的办法。所以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弄了个大团圆。”[2](P188~189)在对村干部的处理上,赵树理也是将石献英等具有争议性的村干部置换为金旺、兴旺等有着更多“匪行”的流氓,其目的也不过是证明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的合理性以及政府对其恋爱支持的正确性,也由此巧妙地避开了政治伦理与传统伦理的抵牾。不难看出,拿作品与故事原型对比,无论是故事的改编还是人物的变化,都有着明显的功利因素,显示出作家基于政治目的的启蒙意识。
《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民,无论是老一辈的三仙姑、二诸葛还是新一辈的小二黑、小芹,都缺乏对生活的理想追求,他们走着祖辈父辈曾经走过的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延续着历史的惯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涉,祖辈父辈的今日就是他们的明天。他们既缺乏挣脱家庭追求个人幸福的决心,也缺少追求革命融入集体的自觉,他们的命运既不能摆脱父母的控制,也摆脱不了乡村势力的干扰。就此看,新政府对他们的解救和帮助一方面显示出新政府在反封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其对农民命运的决定作用。按照福柯的权力理论,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关系,农民所生活的乡村环境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一个生活于其间的人们都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也受到这种权力的支配。这也决定了岳冬至的命运悲剧。在《小二黑结婚》的创作中,作家不仅对岳冬至的命运进行了改写,而且也通过坏人——金旺、兴旺的破坏,突出了小二黑追求婚姻自由的合理性,从而在乡村伦理的范畴内达到了反封建的目的。也就是说,作品表面上宣扬反封建反迷信,实际上却是通过反封建反迷信的形式将政治伦理渗透到民间,在利用乡村伦理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改造从而达到乡村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巧妙结合。“小二黑结婚”也成为当时的农民可以接受的争取婚姻自由的符号,即小二黑被符号化,反而是二诸葛和三仙姑由于负载着太多的传统重负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典型。在艺术上,小二黑、小芹远远不如二诸葛、三仙姑更具魅力,这也显示出作家对他们的类型化处理和概念化呈现,表现出其基于政治宣传的功利意识。从实际效果看,赵树理的创作也达到了宣传教育的目的。“由赵树理的‘小二黑’,到各村庄农民自己的‘小二黑’,实际上‘小二黑’已经成了太行山农民反对封建思想,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化身了。”[3](P197)强烈的政治意识使作家操纵着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也正是在功利思想的制约下,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启蒙意识和人为雕琢的痕迹。就此看,赵树理等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写给农民看的,对于农民思想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则略显匮乏。“土改”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迎合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心理得到他们的拥护,但由于有着强制性的特征而带有更多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可能表现出主体性,这也决定了“土改”叙事农民主体性的缺乏。
二、合作化小说的农民:主体性的呈现
合作化有着农民自发的基础,是他们由于生产生活的困难而采取的一种民间互助形式,国家的合作化政策尽管有着浓厚的政治目的,但总体上却迎合了农民的要求,适应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给予了农民更大的自主性,使其有条件和可能体现出主体性。合作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对农村农民的处境有着真实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也就有可能表现出农村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真实想法,为合作化小说的农民主体性建构奠定了基础。
在合作化过程中,舍小家顾大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农民成为时代的先锋,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学所着力塑造的新人形象。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三里湾》中的王玉生、王金生还是《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乃至《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都以对集体的无私付出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典型。梁生宝们因为呼应了当时的政策而显示出强烈的工具性,但由于作家忠实于现实的创作理念以及当时浓郁的政治氛围,他们的追求和奋斗具有了更多的合理性。“每个时代属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力图使本阶级的英雄人物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并以此作为传播统治阶级政治社会理想、伦理道德理想以及审美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作为从精神上巩固其统治的有力媒介。因而在新中国文学中提倡表现工农兵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是与革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历史要求相适应的。”[4](P147)事实上,郭振山、范登高等老共产党员无疑更容易受到党的政策的影响,也更应该成为代表社会主流思想的典型人物,可由于浓厚的小农意识,他们很快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梁生宝、王金生等之所以迅速成长并超越他们的“前辈”,无疑是因为他们为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奋斗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农民的新的特质,理想主义是其主要特征,对理想的不倦追求与紧跟时代的坚定步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理想追求与当时主流政治有着内在的一致,他们也由此无可争议的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由于各种势力的阻挠,梁生宝、王金生等的合作化道路遭遇了种种挫折,但他们始终没有动摇互助合作的决心——在他们看来,互助合作无疑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途径,他们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确认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未来社会主人公身份的。“一旦某一个体获得位置感(比如三辈儿),并且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如何恰当地做人行事时,无疑主体感就产生了,所谓主体感也即一种统一感和身份感,也就是说他的自我认同‘在形成新的认同并与以前的认同相结合的能力方面获得自我证实,这便将他自己和他的相互作用塑造成一部独一无二的生活史。’在唱颂着神圣的成长仪式中成长为主体的叙事主人公一定会‘感慨万千’的,因为他汇入了一个庞大的新兴的‘整体’。”[5](P73~74)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是梁生宝们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们奋斗的动力。正是在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中,梁生宝们牢固地确立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也从中确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地位。
梁生宝等社会主义新人在探索互助合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与秉持个人发家致富的传统农民的冲突。如果说梁生宝等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性体现为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那么传统农民的主体性则体现为对未来道路的自主选择。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柳青、赵树理等忠实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其作品呈现出合作化的原貌。以《创业史》为例,尽管梁生宝和姚士杰、郭振山分别代表了创业发家的不同选择,但作品表现的更多地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冲突。从乡村伦理来看,郭振山、姚士杰自主发家的道路和梁生宝选择的合作化道路具有相同的意义。富农姚士杰对合作化的破坏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财产,过分一点就是拉拢梁生宝互助组的成员,真正够得上阶级敌人破坏的事例实属罕见。郭振山之所以被树为负面人物,也仅仅是因为他在“革命”之后只顾着自己发家致富而抛弃了一起同甘共苦的贫困户。事实上,郭振山和姚士杰都走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尽管他们所谓的互助合作仅仅是一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梁大老汉等传统农民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并没有受到权力的强制,互助合作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更主要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姚士杰、郭振山看到梁生宝的互助组、合作社抢了风头之后,也想着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梁生宝们上山砍竹子、买高产稻种,不仅帮贫困户度过难关,而且也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入社是他们利益衡量之后的选择。“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传统农民未来道路选择的自主性,也决定了他们的主体性,即传统农民之所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因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个人利益的审慎思考。《三里湾》中,马多寿加入合作社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决定,其对合作化的态度完全出于利益的衡量——当单干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他坚决地抵制入社;当儿子、儿媳等都与其分家,入社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马多寿选择了入社。作品中对马多寿在入社问题上的计算显示出传统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在真实表现农民思想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党的干部范登高,身上有着浓厚的小农意识,雇人做生意、顽固地坚持单干,但在政治前途与个人发家之间,范登高最终选择了政治前途,女儿范灵芝对他的“反叛”以及他在党员会议上遭受的公开批判,迫使其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范登高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是基于利益权衡下的选择,并不是上级的强迫,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可见,范登高、马多寿等传统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主要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强迫,尽管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合作化的选择上体现出来自愿,也因此显示出主体性。
三、环境规约下农民主体性的反思
阿德勒认为,性格特征“是个体试图使自身和他所生活的世界相适应的一些特殊表现方式的显现。性格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和他环境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性格特征。”[6](P121)也就是说,在性格的形成中,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主义思想和合作化道路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也有着政治上的合法性,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更是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无限想象的美好空间,获得了广大青年人的拥护。尤其是,长期的革命战争形成了人们的战争心理,也使合作化运动成为和平时期的“战争”,成为他们的理想。“生宝现在就是拿着这个精神,在小农经济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中,开始搞互助组哩。杨副书记说得对: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7](P87)带领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他们的理想,党和政府发动的合作化运动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之所以将合作化作为自己的理想,正是缘于当时的环境,或者说,从表面上看,他们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性格是个人意愿的真实表达,但真正影响其性格的却是当时政治化的环境。在合作化的大背景下,集体主义精神和公有制观念以及舍小家顾大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的主流,也是社会主义新人成长的环境。他们的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梁生宝十几岁就从地主吕二财主家牵回小牛,使梁三老汉家里有了牲畜,表现出一个精明庄稼人应具备的品质。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土改之后,梁三老汉完全可以完成创业的梦想。但是,在社会主义环境的熏染下,梁生宝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满足于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幻想着带领蛤蟆滩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业,环境的改变使梁生宝的人生目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其从一个精明的庄稼人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福柯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并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由于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其对人的影响无处不在,福柯将其称之为微观权力。从表面上看,合作化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由于当时政治化的环境所建构的关系,政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影响、左右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对革命的自觉追求既是其理想的体现,也是环境影响的结果。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并使其政治化。社会主义新人的舍己为人、大公无私,为了集体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其思想政治化的典型体现。梁生宝为了集体事业拒绝了改霞的求爱,刘雨生为了合作化事业与妻子张淑贞离婚,任为群为了治理九河不惜和妻子分居……对他们来说,政治就是一切,在个人生活和政治之间,政治更为重要,典型地反映出其意识深处的政治思维,也显示出他们主体性背后的政治主导作用。
合作化小说中的传统农民大多是“中间人物”,他们对合作化抱有一种骑墙的态度,其合作化道路的最终选择或出于利益的衡量如马多寿,或出于思想教育之后的醒悟如“菊咬金”,无论哪种情况都体现出了自主性或者说主体性。但在其主体性的背后,却是政治的规训。在合作化的选择上,虽然有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方针,但在具体的行动中,单干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当时的舆论宣传中,合作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也天然的具有合法性,是海上行驶的安全大船,而单干则是小农主义,是大海上漂泊的孤舟,经不起大风大浪。尤其是,国家还会借助政权的力量通过宣传、发动甚至上门做工作等方式,形成对单干户的“围剿”,使其处于国家引导和“熟人”劝解的包围之中,由于坚持单干,他们也被定义为“落后分子”,政治落后的定位使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为了鼓励合作化,政府还会通过支持或鼓动单干户的家庭成员通过脱离家庭使落后家庭发生分化,从而达到进一步孤立单干户的目的。土改中,由于家庭成员都有权利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因此,家庭成员的叛逆也预示着单干户土地和劳力的减少,其生产也往往因此而陷入困境。在合作化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况下,在一个村庄的社会结构中,单干户愈发显示出脆弱和孤单,在人际关系中也往往陷入孤立。生活和精神上双重孤独的事实,使传统农民不得不接受合作的命运。但这显然与他们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冲突,传统农民成为时代大潮中的犹疑者,也成为复杂的“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这样看,在他们入社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是自愿,实际上“权力”的规训和惩罚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 “关系”的规约由于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更显示出微观权力的影响,从而也说明了环境对他们的支配作用。
正是环境对农民的影响尤其是对其性格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使合作化的农民显示出两重性,他们选择合作化一方面出于个人的自主选择,体现出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的制约,体现出环境的制约作用,从而在体现着主体性的同时也解构着主体性。合作化时期的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内在的分裂——先进人物、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的划分,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内在矛盾——包括先进人物的概念化和中间人物的真实性,显示出合作化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作家即叙事者的复杂情感和矛盾态度。
四、合作化叙事的民间立场解析
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以及与农村的血肉联系使作家身上具有了农民的基因,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渗透又使其具有了知识分子意识,二者矛盾统一于他们身上,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解放区文学和合作化叙事的大部分作家深受“五四”思想的影响,对“五四”的尊崇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继承了“五四”启蒙思想的衣钵,并将之加以改造、换装以适用于抗战时期的语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当时急于解决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发动农民进行抗战和斗争的迫切需要,所谓的为工农兵服务带有了更多的功利性因素。尤其是,解放区政府的各种政策要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就必须适应他们的欣赏习惯和接受水平,从而达到宣传发动的目的,这就更强化了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对政策合理性的阐释义不容辞地落在了知识分子身上,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启蒙意识。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宣传婚姻自主、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宣传阶级意识、发动抗战等。在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土改”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说教意味是很浓的,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干预也是很明显的——尽管这种干预是以“解放”的形式。在这种干预中,预设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乡村处于愚昧之中,只有对农民进行启蒙才能逐渐使其符合建设新社会乡村的要求。而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恰恰为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提供了政治的合法性,也为其付诸实现提供了条件。在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前,乡村依然上演着由于历史的惯性遗留的悲剧,比如青年人的不幸爱情、地痞流氓横行乡里等,而破除历史惯性建立新的乡村秩序只能靠新政权。启蒙意识借助于新政权树立了合法性,而新政权也借助于启蒙宣传巩固了合理性,启蒙意识与新政权形成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
解放区的作家大都有着乡村生活和工作经历,与农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赵树理等作家更是将农村作为自己的“据点”。深入民间之后,他们更了解农民的疾苦,如果说未到农村之前他们对农村的了解仅限于宣传,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分析,那么深入民间之后,对农村的了解则是切身的体会,是一种实践的认知。但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他们将农村痛苦的根源归结为封建和奴役,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封建反压迫。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延续着深入民间的传统,特别是思维中的政治无意识更使他们自觉地走向民间。其后要求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的政治号召及相关政策更使他们走向民间获得了舆论的支持。走进乡村之后,他们对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其启蒙立场在遭遇了民间疾苦之后逐渐向民间倾斜,并由此形成民间立场。从当下视角看,解放后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农村和劳动第一线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夹杂着诸多对知识分子伤害的因素,但谁也不会否认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怀抱的真诚的自我改造的态度,以及内心深处那种真诚的忏悔意识和自责心理。正如黄秋耘所说,“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8](P102)也正因为这种忏悔意识和自责心理,激活了知识分子意识深处“为民请命”的传统意识,从而在浓郁的政治化氛围中表现出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关切,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呈现出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的痛苦、犹疑、欢乐或失望。新政权提倡、要求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原本是基于民粹主义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实践性的教育,可当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之后却自觉地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对当时不适宜的政策和做法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表现出异议,这时,他们的叙事方式无疑具有了民间立场。
合作化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呈现出对合作化的不同倾向,在合作化的颂歌声中,也夹杂着对合作化的反思和疑虑,形成合作化叙事的杂音。这种杂音不仅没有解构和削弱反而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性,也显示出作家摇摆于政治与民间的特定时期的知识分子立场。合作化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农村重大变革运动,合作化小说的本意在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宣传合作化、推动合作化,也就是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里湾》的政治功利性就是很明显的。但由于赵树理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及其对农村农民的熟稔,小说也就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传统农民在这一历史遽变中的矛盾心态和复杂表现。随着合作化的推进和发展,合作化的弊端日渐显露,与农村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对这一切熟视无睹,于是就有了对合作化问题的揭露。对农民思想和感情的融入以及对农村的了解和农民的熟悉使作家无形中与权力的行政性指令拉开了距离,作品也由此与政治产生了裂隙,比如《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合作化小说中的落后人物,尽管作品对他们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由于对他们所处语境的如实描摹以及作家的同情态度,反而借助于这些落后人物对合作化提出了质疑,进行了反思。在合作化弊端日益暴露的时候,有的作家由于政治惯性其写作成为空洞的理论说教,有的作家干脆停止了创作,还有一些作家秉持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坚持着写作,曲折地呈现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柳青、赵树理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柳青《创业史》写作的犹疑和停笔,赵树理《锻炼锻炼》等作品对合作化的反思,无疑代表了另一种乡村的现实,显示出对事实的尊重和农民命运的忧虑。其实,知识分子合作化前后的创作尤其是拿合作化小说与解放区文学相比,更具有鲜明的理想与现实相对比的意味:合作化之前的社会主义想象无疑是在理想中建构一个新的乡村世界,而合作化则是直面农村农民的现实。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异无疑以现实的“现在”回应了理想的“历史”,在美化理想的同时也强烈地质疑着现实的残酷与丑陋。“后来,公有化发展到高级社,再完全公社化,农民的利益渐渐得不到保障,赵树理就犹豫了起来。一位熟知赵树理的干部说:赵树理在初级社时十分积极热情,甚至有点卖命;高级社时就好提意见了;进人人民公社后,就沉默寡言了。”[9]尽管作家对政治有着高度的认同,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农民身上,而是如实写出了他们的消极和疲惫甚至其小农意识中自私狭隘的一面,并通过落后农民的自私性呈现对合作化提出质疑。合作化政策的宣传和推动无疑代表了对农民的启蒙,而其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冲击及其中的各种问题又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也因此,知识分子在对农民进行启蒙的同时也在质疑着启蒙。这无疑是以农民的立场代表农民的呼吁,从而在对既有政策提出质疑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农民的尊重,并由此建构了农民的主体性。
合作化是社会主义想象的尝试,合作化小说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想象的一次文化实践。在合作化小说中,作家不再是农村生活的旁观者,而是通过积极的参与切身感受合作化带给农村的巨变。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合作化事业的投入使他们自觉地向农民靠拢,体验着农民的酸甜苦辣,感受、见证着这一乡村巨变的历史时刻。合作化过程中,农民不仅遭遇着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也由于传统心理的惯势表现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无限留恋,感同身受,作家自然给予农民以高度的情感认同。当对农民的感情贯注与新政权所要求的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农民的政治号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知识分子自然具有了农民的思维和立场。当秉持着农民立场的知识分子进行创作的时候,必然呈现出农民的价值观念,从而也就有可能建构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但处于当时的环境,农民的主体性又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农民的主体性,也使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具有了争议性。
参考文献〔〕
[1]吕周聚.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民粹主义思想[J].东岳论丛,2013,(3).
[2]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苗培时.《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山(节录)[A].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张炯.在巨人的光环下——毛泽东和新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6](奥)阿尔弗德雷·阿德勒.理解人性[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7]柳青.创业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8]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9]刘旭.赵树理的农民观:“现代”的限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责任编辑张伟〕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the Cooperative Novels
ZHANG Lian-yi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Abstract:Since the new literature of May 4th Movement, farmer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images in literature, but in a long time, they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object of the enlightenment. Although the “Speech” gave them a high political status, they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many writers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and had the he position of the farm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of rural familiar. This is the basis of familiar in the cooperation novels. However,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 the main body of the farmers had more political factors, which deconstructed the subjectivity in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cooperative novel; farmer;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27-07
作者简介:张连义(1973-),男,山东聊城人,博士,苏州大学博士后,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