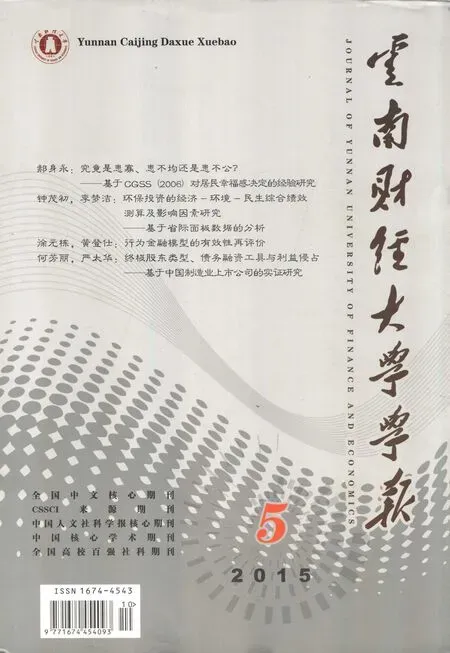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2015-02-12林浩,刘玉,舒求
林 浩,刘 玉,舒 求
(1.云南财经大学 哲学与伦理研究所,昆明650221;2.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201)
秦汉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但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统治过程、郡县设置、官吏治迹、民族起义等政治治理,经济方面虽涉及了移民屯田、道路交通、农牧工商等问题,但多被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对中央政府在云南地区的经济政策未作系统考察[1~3],甚至认为元以前历代均不见在云南的经济政策方面有所建树。[4]本文从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内地移民和经济部门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秦汉对云南地区的经济治理,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和总结秦汉对边疆地区的治策和经验。
一、引论
战国中期以后,云南地区逐渐卷入中原争霸。惠王更元九年,秦以“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而灭蜀[5]《秦策》,又“贪巴、苴之富,因取巴”[6]《巴志》,随后深入原为蜀王“园苑”的云南地区[6]《蜀志》。惠王更元十四年,“属滇国”[7]的“丹、犁臣”[8]《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6]《蜀志》;至始皇帝统一时,秦“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9]《地理志》,已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
秦“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8]《秦始皇本纪》,归附的少数民族或纳入郡县管理,或设“属邦”及县一级的“道”。一些首领仍封为君长,如“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皆废为君长”[8]《东越列传》;保留有一定的权力,如“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法津上也有优待,如“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 ”[10]《法律答问》。 在 云 南 地 区 也 有 “郡县”[8]《司马相如列传》和“宜 属”[9]《地理志》两 种 治 理模式。
秦汉之际,以云南地区为主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8]《西南夷列传》。但汉初“接秦之弊,……齐民无盖藏”[8]《平准书》,无力顾及西南夷地区,“皆弃此国”。而作为汉朝藩属的南越则“以兵威边,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势力深入至云南西部,“然亦不能臣使”[8]《西南夷列传》。
自汉高祖实行“与民休息”政策[9]《景帝纪》,至武帝初已是“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8]《平准书》,国力大为提升。建元中,武帝为应付南越,以唐蒙通南夷,试图役使“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此制越一奇”。但武帝仍采取了与南越类似的手段,“蒙厚赐,喻以威德”,与夜郎侯“约为置吏”,而“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 且 听 蒙 约”,“乃 以 为 犍 为郡”[8]《西南夷列传》。“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为内臣妾”,武帝又以司马相如“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8]《司马相如列传》,“为置一都尉”,初步控制了云南东北和西北部。汉朝繁荣的经济虽然对西南夷上层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治理,“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控制成本也极高。元朔三年,为“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元狩元年,武帝为联合“大夏”,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8]《西南夷列传》。
元鼎五年,“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汉平南越后,“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夜郎遂入朝”;又诛“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元封二年,“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请置吏入朝”[8]《西南夷列传》;“后数年,复并昆明 地 ”[9]《西南夷传》,又 “渡 兰 沧 水 以 取 哀 牢地”[6]《南中志》,云南大部重新纳入中央的控制,设置的郡县主要是益州郡以及犍为、牂柯、越巂郡的部分县[9]《地理志》。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贤栗等“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置永昌郡[11]《南蛮西南夷传》,全面控制了云南地区,并对部分郡县进行了调整,犍为南部也改设属国[11]《郡国志》。
汉制,地方既设郡县又封王侯,归附的少数民族一些“因其故俗为属国”[9]《卫青霍去病传》,一些则设“部”[11]《南蛮西南夷传》。“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11]《百官志》。武帝控制西南之初虽未设属国,但“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故俗治”[8]《平准书》。同时,分封一些少数民族酋豪为王侯君长,“长其民”[8]《西南夷列传》,不同于武帝以后内地“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9]《诸侯王表序》。但对诸侯的限制仍具一般性,如规定朝廷为诸侯“置吏二百石 以 上 ”[8]《淮南衡山王列传》, 诸 侯 不 朝 “ 当诛”[9]《荆燕吴传》,控制西南后,滇王“请置吏入朝”[8]《西南夷列传》;规定“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8]《南越列传》,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朝廷派员“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夜郎王即被诛[9]《西南夷传》。
在控制云南地区的同时,秦汉在维持全国政策的一般性及总结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云南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展开了针对当地少数民族、内地移民和各经济部门并与政治、军事治理相适应的经济治理。
二、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治理
纳入秦汉控制后,适用于全国范围的一般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逐渐影响云南地区,但对少数民族更直接的经济治理是贡纳和赋役。
贡纳具有早期赋税性质,但更强调政治上的臣服,因此往往伴随着赏赐,所谓“羁縻之义,无礼不答”[11]《南匈奴列传》。春秋以后,巴蜀曾多次向秦纳贡,如穆公时“巴人致贡”[8]《商君列传》,“蜀人来赂”;惠文君时“蜀人来朝”[8]《秦本纪》。但秦控制云南地区前后均无当地民族纳贡的直接记录。而秦二世时仍称“四海之内皆献贡职”[8]《秦始皇本纪》,因此从丹、犁的臣服到牂柯、越巂、益州的宜属,纳入秦控制的云南地区各族也可能有纳贡的义务。
汉初,“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充输”[12]《本议》。武帝重新进入西南之初,称各少数民族君长“常效贡职”,实际是先以“厚赐”收买西南夷上层,才得到他们纳贡的承诺,但“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8]《司马相如列传》。重新纳入汉朝版图后,滇王“请置吏入朝”[8]《西南夷列传》,云南当地民族才正式纳贡。东汉,云南地区原属徼外的民族要求内属则均是先朝贡才得到封赠。如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王贤栗等遂率种人“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明帝永平中,益州白狼等百馀国“举种奉贡,种为臣仆”,朝廷“多赐缯布,甘美酒食”[11]《西南夷列传》。
秦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虽无直接记载,但秦对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可能有一定的参照性。在秦集中设置属邦、道的惠文王至昭襄王时期[13],对西南东部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也同时出现,多数也延续至汉。对巴郡南郡蛮,“秦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11]《南蛮列传》。秦汉时期,内地民户“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秦时,田税为“什一之税”,粮“石三十”[9]《食货志》;“布长八尺,幅二尺五寸为一布,当十一钱”[10]《金布律》;“羽二翭五钱”[14]。巴郡南郡蛮其君长年出赋为百亩田税的4.7倍,民户出幏布、鸡羽分别为百亩田税的1/4和1/6。西汉,田税“三十而税一”[9]《食货志》,粮石百钱[15];布“长四丈为匹”[11]《食货志》,“价直一百二十五”[16]《衰分》;“钱六百二十,买羽二千一百翭”[16]《粟米》;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9]《高帝纪》颜师古注。其君长年出赋为百亩田税的5.2倍,民户出幏布为百亩田税的1/2;鸡羽是内地赋算的4/5。要注意的是,从鸡羽的价值看,不能简单地说“对于渔猎为主的巴地蛮夷而言,并非难为之事”;而从民户所出的结构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贡赋”[17]。
在黔中郡,秦“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18]《李特载记》,仅为巴郡南郡蛮民户所出鸡羽的1/2。西汉则“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11]《南蛮列传》,大人输布与内地赋算相当;内地“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9]《高帝纪》颜师古注,小口输布则为内地口赋3倍。对其中的板楯蛮,秦昭王时因射虎有功,“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11]《南蛮列传》,免整族田赋、口赋。“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18]《李特载记》,实际可能只“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11]《南蛮列传》,延续秦的口钱,为内地算赋1/3。在南郡夷道,汉高祖十一年,“蛮夷大男子”毋忧,按《蛮夷律》“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不当为屯”的原则,“岁出五十六钱”[19]211,多于板楯蛮余户口钱,但不到武陵蛮大人输布或内地算赋的1/2。
总的来看,秦汉对西南东部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模式大致具有一致性,即赋税已与人口挂钩,有阶层和年龄之分,并有货币和“随地所出”的形式,一些还呈现出结构化的特征,且普通民户的赋税大致均轻于内地民户;在役的方面,各族均是整族无徭役,并非只是“君长不服役”[20],但仍有强征,如“南郡尉发屯有令,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即遣之”[19]211;赋役依据是秦的《属邦律》和汉的《蛮夷律》,赋役差异的原因应是秦汉郡守可在规定范围自设条教[21]831~832。由于这一赋役模式的一般性和延续性,秦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模式也应类似。
汉武帝重新控制西南后,在“初郡”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8]《平准书》。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在经济上一般不干预各族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但对诸侯的经济限制仍适用于各族君长,如规定诸侯不得“煮海为盐”[9]《晁错传》,朝廷在连然设盐官[9]《地理志》,即剥夺滇王对盐的控制。所谓“毋赋税”,即“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均由“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军事行动“费皆仰给大农……,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8]《平准书》。
但“毋赋税”实际只是“初郡”阶段性的政策。在汶山设郡仅40年后的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11]《西南夷列传》,说明此前汶山夷人已不再享受“毋赋税”政策,而是按一般郡县承担较按部都尉管辖更重的赋税。但在桂阳郡的含洭等三县,东汉初仍“习其风土,不出田租”,不同的是“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11]《循吏传》。而且,军事行动的临时征调有时也会形成大规模赋役。新莽时,句町反,“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9]《西南夷传》;之后几次征讨,又在犍为、益州等地“赋敛民财什取五”,“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9]《王莽传》。
东汉,“初郡”各族转为按属部甚至属郡管辖承担赋役更为普遍。建武初,桂阳郡守卫飒在含洭等三县“凿山通道五百馀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11]《循吏传》。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引发了反抗。建武十八年,“马援平交阯,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22]《马援》,“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馀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 ”[11]《马援列传》。 实 际 是 苏 定 “ 以 法 绳之”[11]《南蛮列传》,执行了赋重的“汉律”;而马援恢复了赋轻的“越律”,即适用于交趾越人的《蛮夷律》。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在朝廷上得到普遍支持,“议者皆以为可”,但随即因“贡布非旧约”引发了反叛[11]《南蛮列传》。大致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及赋役模式不得不一再调整,如汶山郡改部都尉管辖后,至“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已仍为蜀郡北部都尉。灵帝时再为郡。寻复为都尉”[6]《蜀志》。
东汉以后,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已开始服兵役。建武十八年,益州“诸种反叛”,朝廷“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一些少数民族也按“汉律”承担赋税。元初三年,益州徼外夷大羊等八种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大致也是执行了“汉律”,因此杨竦平叛后虽“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但“皆减死”[11]《西南夷列传》。
对少数民族赋役“汉化”的扩大,一方面是经过长期的治理,一些民族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使赋役“汉化”成为可能。在云南地区还引发了以哀牢人为典型的四次檄外民族大规模内属,建武二十三年,“绝域荒外”哀牢王贤栗几次败于“人弱”但已内属的“附塞夷鹿茤”,随后“贤栗等遂率种人……求内属”[11]《南蛮西南夷传》,另一方面,东汉初“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11]《光武纪》,以降低豪强插手地方军队的可能。而豪强对土地、人口的占有却难以抑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件”[23]《理乱篇》。随着军队规模特别是赋役人口的下降,对少数民族赋役“汉化”的需求也趋于扩大。
但东汉对云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有部都尉模式的赋役。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11]《西南夷列传》。在部都尉模式下,“自为都尉、太守”的郑纯即“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11]《西南夷列传》。由此,所谓属部都尉赋役模式实际就是秦汉对西南东部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赋役模式。
从哀牢邑豪“常赋”征收对象的量看,布贯头衣为棉布(白叠、布叠)所制,大致是“缝布二尺,幅合二头”24卷790引《异物志》,“幅广五尺”[6]《南中志》。棉布价格到唐代才有记载,天宝时期敦煌地区中等棉布(细緤)一尺“四十四文”,麻布一端“四百九十文”,生绢一匹“四百六十文”[25]13,19,24,“绢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26 卷 3《尚书户部》。东汉麻布一匹“价直一百二十五”16《衰分》;“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直钱六百一十八”[27]296。按汉唐棉、麻、绢比价,贯头衣二领在1087钱至5374钱之间。再按东汉盐一斛800钱28,粟一石500钱29,哀牢邑豪常赋大致是内地百亩田税的3/4至2.5倍,即使高限也低于秦和汉初巴郡南郡蛮君长的赋税水平。
三、对移民的经济治理
秦汉时期,大批内地移民进入云南地区。其中有家属随驻并落籍当地的官吏和军人以及招募或强制迁徙的罪人和平民等能享受一定经济扶持政策的官方组织的移民,也有自发的移民。移民的进入改变了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汉郡设守,下有丞、长史、都尉等佐官及功曹、五官、督邮、主簿等属吏;县设令(长),下有丞、尉、令史等佐官,武帝以后也分曹置掾。东汉洛阳县即有“员吏七百九十六人”[11]《百官志》注引《汉官》,云南地区郡县官吏不会有这样的规模但仍有一定数量。郡守及丞、尉和县令(长)由朝廷任命,不用本籍人,赴任可带家眷;属吏则由主官自辟,用本籍人,一般不能带家眷[30]。但云南地区设置郡县之初,地方小吏均为外籍人,携带家眷也可能放宽。一些进入云南地区的官吏携带有家眷并最终成为移民,“居官者皆富及累世”[11]《西南夷列传》。随着移民的发展,至东汉云南地区郡县属吏已多为本籍人,永寿元年益州太守碑“左有功曹椽故吏题名四十八人,皆属邑建伶、牧靡、弄栋、滇池、谷昌、俞元之人”[31]。
秦汉官吏均能免除一定赋役,秦时爵至“不更”则“不豫更卒之事”[9]《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但官吏并不满足,有“包卒为弟子”[10]《秦律杂抄》,有“匿户及敖童,……弗徭使,弗令出户赋”[10]《法律答问》。汉时有“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9]《高帝纪》,但官吏之家不仅“租常不入”9《何武传》,还“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9]《循吏·黄霸传》颜师古注,东汉“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11]《西羌传》。云南地区的官吏、领军则逐步把移民、戍卒和当地夷民占为家部曲[32],不再为国家提供赋役。
秦汉郡县驻有军队,“边郡太守各将万骑,……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33],在边境和要冲设置的关徼塞障也“分卒守徼乘塞”[8]《黥布列传》。 武 帝“通 西 南 夷 道,戍 转 相饷”[8]《西南夷列传》,汉军开始进入云南。由于西南夷各族“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11]《西南夷列传》,云南驻军规模始终不大。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9]《西南夷传》,所谓“奔命”即“郡国皆有材官、骑士,若有急难,权取骁勇者闻命奔赴”[11]《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书音义》,每郡发“奔命”大致五千人。东汉初,罢郡国兵,“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11]《百官志》,驻军规模缩小。建武十八年,益州诸种反叛,“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反,“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9]《西南夷传》,每郡募发夷汉士卒仅三千人。
秦汉成年男子服兵役,“为正一岁,屯戍一岁”[9]《食货志》。正卒在本地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11]《光武帝纪》,但云南纳入秦汉版图初期正卒也来自外地。戍卒一般是“一岁一更”[9]《昭帝纪》注引如淳,但也有“军无功者,戍三岁”[34]《兵令》,甚至”偿四岁徭戍“[10]《除吏律》,屯戍期满“不候代者,法比亡军”[34]《兵令》。汉朝还有每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的更役,由于个人成本极高,“诸不行者”可“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以“一岁一更”方式代役[9]《昭帝纪》注引如淳。秦汉允许戍卒家属随军,秦时南海尉赵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8]《淮南衡山列传》;汉时随戍家属还有廪粮,如居延“右城北部卒家属名籍凡用谷九十七石八斗”[35]203·15。由于路途遥远特别是家属随军,在云南地区应有一定规模的军事移民。
进入云南地区的军队也有屯田,汉成帝时,夜郎王与钩町王、漏卧侯“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杜钦担心久拖不决,“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9]《西南夷传》;新莽时,击句町不克,冯英建议“罢兵屯田”[9]《王莽传》。军队屯田是集体劳动,产品交公;耕种土地大致是“赋人二十亩”[9]《赵充国传》,以小亩计约为内地民户“一夫百亩”的1/2。
战国时期,秦已开始向边郡徙民。移民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36]《兵守》。取蜀后,“移秦民万家实之”[6]《蜀志》,以后又迁大量罪人和六国豪族入蜀。如吕不韦自杀后,其“家属徙处蜀”[8]《秦始皇本纪》;灭赵,迁“用铁冶富”的卓氏于临邛[8]《货殖列传》;灭楚,“徙严王之族于严道”24 卷66引《蜀记》,以至称“秦之迁人皆居蜀”[8]《项羽本纪》。而其中一些“迁蜀边县”者实际已进入云南地区,且“令终身毋得去迁所”[10]《封诊式·迁子》。如张若所取蜀边县的“江南地”[6]《蜀志》,即蜀王蚕丛“子孙居姚、嶲等处”7引《谱记》,汉以后又与其他一些巴蜀边县一起划入云南地区诸郡[6]《蜀志》。
汉文帝时,因“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开始移民实边。移民顺序是“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徙边者也“勿令迁徙”[9]《晁错传》。武帝建元六年,唐蒙“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8]《平准书》,开始向云南地区移民。以后移民的主体转向罪人,元封时开益州,“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置巂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6]《南中志》,又“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以充之”。三国时南中大姓雍闿的先祖为什防侯雍齿[37]《蜀志·吕凯》及裴注引《蜀世谱》,元鼎五年,雍齿孙因“坐酎金免”[9]《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其家族可能即徙益州郡[2]98。东汉迁徙罪人得到继续,桓帝时“李膺以党锢,流妻子门人于”云南地区[38]。但从明章时期开始,罪人徙边直接为屯兵,“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11]《明帝纪》;“父母同产欲相从者,恣 听之”[11]《章帝纪》,罪人徙边与军队屯戍趋于混同。
此外,秦汉“民无得擅徙”[36]《垦令》,但汉文帝时规定“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9]《景帝纪》。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近150年里,在全国人口徘徊不前的情况下,云南地区人口仍增长近1倍,扣除永昌郡及哀牢等内属人口,主要原因是当地少数民族纳入郡县管理、人口自然增长和内地移民[3](94~96),其中应有相当数量的自发移民。
秦汉对官方组织的移民有一定的扶持。秦时,普通移民“拜爵一级”[8]《秦始皇本纪》,“赦罪人迁之”[8]《秦本纪》,而“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36]《境内》,也有“复不事十年”、“复十二岁”等[8]《秦始皇本纪》。汉文帝时,一般移民均“予冬夏衣,廪食”,“先为室屋,具田器”,“为置医巫,以救疾病”,“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等。但扶持政策不仅有期限也有对象性差异,所谓“募民之欲往者,赐高爵,复其家”9《晁错传》,实际“虽有长爵不轻得复”[9]《贾谊传》,“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9]《食货志》;所谓“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9]《晁错传》,也“各有差”,只有“复终身”,才“不告缗”[8]《平准书》;所谓“予冬夏衣,廪食”,实际“能自给而止”[9]《晁错传》,“数岁,假予产业”,转为政府借贷,如“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8]《平准书》,虽不征告缗钱,但要还本付息。东汉以后,仍有一定的经济扶持,“凡徙者,赐弓弩衣粮”[11]《明帝纪》,“女子勿输”[11]《安帝纪》。
移民除屯田外还有训练、自救任务,但无“月为更卒”的劳役[9]《食货志》。耕种土地有“率人田卅四亩”[39]87~88,有“班田七顷,给弛刑十七人”[40]56,略少或等同于内地一夫百亩的标准[41]。但屯地为官地,大致是以类似“假民公田”方式分配给屯民;税赋也类似“收其假税”[9]《元帝纪》李 斐 注,高 于 “三 十 而 税一”[9]《食货志》,低 于 “耕 豪 民 之 田,见 税 什伍”[9]《食货志》,如“右第二长官二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39]303·7,“右家五田六十五亩租大石廿一石八斗”[35]303·25。扶持阶段结束,屯民转为普通农民,屯地可能以类似授田型“假民公田”形式转为农民的私田[42],赋役恢复正常。当然,私田也可能来自开荒,如西汉末文齐在益州“垦田二千馀顷”[11]《西南夷列传》。至东汉延光四年,滇池地区出现私有土地交易的记录[43]。
秦汉在云南地区的郡县治地多为各族君长原来的都邑,如滇池县“郡治,故滇国也”[6]《南中志》,“同并县,故同并侯邑”[9]《地理志》应劭注,移民开始也主要“居住在郡县治地及其附近地区”[2]98。在滇池地区,集中的汉人移民墓葬与石寨山文化墓地的共存,说明移民与当地族群并未立即与融合,因移民的进入,当地族群从昆明、呈贡等原住地南移至晋宁、江川、澄江等地,二者并未立即融合;当地既有社会结构虽未立即消失,但华夏式葬器开始为较多社会阶层所使用,显示高阶族群的权力逐渐消退,不再拥有独占华夏式葬器的能力[44]。实际上,还说明了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对当地族群基层民众影响的扩大。
秦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9]《酷吏传》,但也屡遭打击。如秦“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8]《秦始皇本纪》,汉初“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9]《地理志》。武帝“鉏豪强并兼之家”[9]《酷吏传》,也徙“奸豪”到云南地区。但与内地豪强的发展相似,至西汉后期进入云南地区的豪民也与官吏、领军一起成长为有别于当地夷王、夷帅的“大姓”。
西汉末战乱中,内地“豪右往往屯聚,……起坞壁,缮甲兵”[11]《酷吏列传·李章》,牂柯也出现“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11]《西南夷列传》。东汉,云南大姓与内地豪强一样又进一步发展。内地豪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31]《复古》,云南大姓还把当地民族占为私人部曲,开始“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大姓则以“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6]《南中志》;内地“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45],在云南地理条件下大姓不一定拥有大规模田庄,但仍存在以大姓为中心的经济共同体[46];内地“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9]《赵广汉传》,云南大姓及夷帅之间也通过相互通婚,“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6]《南中志》。大姓的成长及与夷帅的联合不仅分割了国家对人口和赋役的控制,也成为三国以后大姓割据南中地区的经济基础。
四、对农牧业、手工矿冶业和商业货币的治理
秦汉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的经济治理除在一定时期内对当地少数民族和移民有特殊的治理外,也有对包括转为正常郡县管理的少数民族和移民在内的农牧业、手工业、矿冶业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部门一般的治理。
在农牧业方面,秦在地方设“田啬夫、部佐”等农官[10]《田律》,规定“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8]《商君列传》。灭蜀后,在蜀地推广铁器牛耕、兴修水利,但对云南影响不大。秦汉之际,滇中地区多“耕田”,滇西多“随畜迁徙”[8]《西南夷列传》,滇池附近也发现了大量青铜农具,但铁制农具极少[47],也未发现牛耕迹象[3](109)。
汉代,“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11]《百官志》。文帝时,为使移民“作有所用”,由政府“具田器”[9]《晁错传》;武帝时,“徙民屯田,皆与犁牛”[9]《昭帝纪》注引应劭。纳入汉朝版图后,铁器牛耕和农田水利等技术逐步传入云南地区。武帝以后,云南地区出土的铁器数量迅速增加[48]。西汉末,文齐又在朱提“穿龙池,溉稻田”[6]《南中志》,在益州“造起陂池,开通溉灌”[11]《西南夷列传》。东汉,云南地区已出现牛耕遗迹及大量水田、陂池模型[49~53];滇西的越巂已“有稻田”,哀牢地区也“宜五谷、蚕桑”。农业发展在粮价上也有反映,灵帝时,益州平乱,太守景毅“初到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间,米至数十”[11]《西南夷列传》。牧业也有所发展,安帝时“诏越巂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11]《安帝纪》,在云南地区设立了官营牧场。
随着云南地区移民和一些少数民族转为郡县正常管理,农业税除“已奉谷租,又出稿税”外[9]《贡禹传》,也应“租及六畜”[9]《西域传》。成帝时,“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9]《翟方进传》注引张晏。益州还有“田渔之饶”[6]《南中志》,而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11]《百官志》。但云南地区农业发展极不平衡,牂柯郡至东汉末仍“寡畜生,又无蚕桑,……句町县有桄桹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11]《西南夷列传》。
在矿冶和手工业方面,秦从孝公时期开始“一山泽”[36]《垦令》,实行了盐铁官营。但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6]《蜀志》,仍有盐铁私营。汉初“弛山泽之禁”[12]《错币》,但征“山海池泽之税”[9]《百官公卿表》。武帝“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8]《平准书》,至王莽时盐铁等仍“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9]《食货志》。秦汉之际,云南地区已有矿冶、制盐、纺织、制陶等手工业部门,其中青铜冶铸最发达[3]119~138。纳入汉朝版图后,云南地区8县有矿产,虽只记连然“有盐官”[9]《地理志》,但“郡不出铁者”,也“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8]《平准书》,大致是“县官铸农具”[12]《水旱》。西汉晚期,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出土140多件铁器,形制类似滇文化中的铜器,应由当地制造[2]75;曲靖珠街出土不少器形和大小相同、结构较复杂、规格统一的铁斧[47],则应出自当地官工。
东汉,“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11]《百官志》本注,云南地区 13 县有矿产[11]《郡国志》,均应是民营官税。其中传世和出土有大量东汉朱提、堂狼铜器,“仅为器形相近的几种,规格统一,便于批量生产”,但铜器上的“工”、“牢”等字样多被认为是“精工造作,经久耐用”[3]135。实际上,武帝时已有“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按“牢,廪食也”[8]《平准书》及如淳注,官营盐铁时“牢”为“雇佣劳作人员的费用”[54];按“官与以煮盐器作,而定其价直”[9]《食货志》王先谦补注,民营官税时“牢”为“租借生产工具的费用”[54];按“《说文》:‘牢,闲养牛,马圈,取其四周是也’。则‘牢’为煮盐所”[55],是官府供给集中经营手工业的“场地”[56]。此外,按“采银租之,县官给槖,银十三斗为一石,□石县官税□银三斤。其□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16]192,则又以“牢盆”计算税收。据此,朱提、堂狼铜器上的“工”、“牢”字样实际是官府提供场地、民营官税的手工工场的产品标记。
另外,云南地区也应有大量从事“末作”、“诸作”的家庭手工业[8]《平准书》,东汉遍布云南的“梁堆”墓出土的大量汉式陶制冥器,说明“当时可能已有专门生产陶制明器的作坊”[3]140。少数民族的家庭纺织业也继续发展,东汉永昌地区“有蚕桑、绵绢、采帛、文绣”,又有“桐华布”、“兰干细布”、“罽旄、帛叠”等[6]《南中志》。
在商业贸易方面,秦汉对与徼外民族甚至属邦的贸易均有一定的限制,关徼也负责检查商旅、货物和征收关税。如秦禁“出珠玉邦关及卖于客”[10]《法律问答》;汉“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 ”[16]83,高后时“禁南越关市 铁器”[8]《南越列传》。但关徼随版图而变化,汉初未控制云南地区,只能“开蜀故徼”[8]《西南夷列传》,而不是开秦故徼,也不是“关蜀故徼”[9]《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略定西夷”时,“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沐、若水,南至牂柯为徼”[8]《司马相如列传》;东汉哀牢人内属后,又“关守永昌”[11]《西南夷列传》。但汉初西南地区关徼的控制并不十分严密,仍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8]《西南夷列传》。云南地区出土的战国末至汉武帝间的汉式器物,如呈贡天子庙的铜洗、嵩明凤凰窝的铁削和曲靖平坡的漆耳杯、环首铁刀等[57~69],一些可能来自与内地的贸易。
云南地区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琉璃珠等来自印度或西亚[60],大量环纹贝主要来自印度和缅甸[61];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但武帝令“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又“皆闭昆明”[8]《西南夷列传》,可能是这些民族担心汉朝对贸易通道控制会剥夺他们在对外贸易中的特权地位[62]。东汉哀牢人内属后,海外贸易通道进一步通畅,永昌出光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等[11]《西南夷列传》,实际多为徼外特产,所谓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37]《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秦汉市场设“市官”[6]《蜀志》,军 队有“军市”[9]《冯唐传》,设“军市令”[11]《祭遵传》。秦有“官府市”[10]《关市律》,即官营商业。汉高祖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8]《平准书》,民营商业迅速发展,“行贾遍郡国”[9]《货殖列传》颜师古注,坐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9]《食货志》。武帝“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大规模经营官营商业,“尽笼天下之货物”[8]《平准书》。随着秦汉在云南地区设治、派驻军队和官吏,官营商业、军市及市场管理官员等应随之进入,市税、关税等也应开征。秦代关税失载,汉代大致是“十分而取一”[16]《均输》。市税仅载个别商品,秦孝公时,“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36]《垦令》;汉昭帝时,“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9]《昭帝纪》。武帝以后官营商业逐渐衰退,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云南地区的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西汉作为行政中心、军事据点和移民聚落的诸“县”[9]《地理志》,到东汉已发展为兼有贸易中心的诸“城”[11]《郡国志》。章和时期,窦宪“移书益州,取六百万,……遣奴驺帐下吏李文迎钱,……文以钱市”[24]《王阜传》,显示了云南地区贸易的规模。
另外,秦汉奴隶政策及对奴隶的需求也一定程度刺激了云南地区的掠奴及与内地的奴隶贸易。秦代,奴隶为主人资产,如“百姓有赀赎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10]《司空律》,并“置奴婢之市”[9]《王莽传》。汉代,虽有过赦奴、限奴的诏令,如刘邦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9]《高帝纪》,王莽令“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9]《王莽传》,但奴婢既为人口,征口算,且“贾人与奴婢倍算”[9]《惠帝纪》注引应劭;又为主人资产,如“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63],征算訾,“訾万钱,算百二十七”[9]《景帝纪》颜注引服虔。官私均使用奴隶,秦“隶臣有工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10]《均工律》,吕不韦“家僮万人”[8]《吕不韦传》;汉初,卓氏“富至僮千人”[8]《货殖列传》;武帝“告缗”时,得“奴婢以千万数,……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8]《平准书》;东汉,马援子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11]《马援传附子防传》。
在秦汉奴隶政策及奴隶需求的影响下,秦时蜀地即因与云南地区的奴隶贸易而有“僰童之富”[9]《蜀志》;秦汉之际“巴蜀民或窃出商贾”也有“僰 僮 ”[8]《西南夷列传》,东 汉 牂 柯 仍 出 “僮仆”[6]《南中志》。云南地区各族也相互掠奴,如武帝攻南越时,“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8]《西南夷列传》。各族还掳掠移民和进入云南地区的其他人口,汉军讨伐云南少数民族反叛时也有掳掠人口的情况。如昭帝时益州诸夷反,“遣大鸿胪田广明等大破之,斩首捕虏五万人,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6]《南中志》。东汉安帝时“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剽略百姓”,从事杨竦“大破之”,“获生口千五百人,……悉以赏军士”[11]《西南夷列传》。成都人禽坚“父信为县吏,使越巂,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6]《先贤士女总赞》。
在货币方面,云南地区长期使用海贝,晋宁石寨山墓葬群中出土海贝11万余枚、文帝时期的四株半两钱3枚、武帝以后的五株钱180枚64,已大致显现了纳入汉朝版图前后云南货币的变化。以后中央钱币影响不断扩大,呈贡石碑村出土西汉五殊钱200多枚[65],昭通鸡窝院子出土东汉五株钱达2200枚[66]。云南地区还进一步发展为重要的铸币地,昭通曾发现新莽“大泉五千”钱范[67],个旧卡房则出土了东汉范母钱和未流通的新铸钱[68]。章和时期,窦宪“尝移书益州,取六百万”[24]《王阜传》,不仅反映“滇池地区已经通用铜钱,官府贮有大量全国通用货币”[3]153,还一定程度显示云南地区铸币的规模。此外,“牛也可能起着货币的作用”,除石寨山青铜器显示古滇人以牛为财富外[3]151,至东汉延光四年滇池地区的私有土地交易仍以牛计价[44]。
五、经验和启示
秦汉是对云南地区实质性治理的开始,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治理范例。首先,秦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很大程度是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汉初放弃西南夷地区的核心问题则是经济实力的不足,汉武帝对云南地区的重新控制实际上得益于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经济恢复发展,因此,经济实力与政治、军事实力一起构成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是边疆巩固的根本。其次,秦对西南东部和中南少数民族的经济治理实际已经注意到了经济政策与政治、军事政策的协调,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对云南地区经济治理的遗存不多。汉朝重新控制云南地区后,大致延续了秦对少数民族的治理模式,使经济政策与政治、军事政策一样成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再次,秦汉在对云南地区实施的经济治理,既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及移民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发展实际考虑了政策的特殊性、阶段性,也考虑了边疆政策与内地政策的协调,并努力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与内地的经济政策趋于一致,使中央对云南地区的经济政策成为国家统一政策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合理延伸。更为重要的是,秦汉还通过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引入云南地区,尤其是使少数民族基层民众从中获得收益,以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瓦解落后制度的经济社会根基,带动云南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保证了云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当然,秦汉对云南地区的经济治理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武帝初对待西南夷实际和南越一样主要是经济收买,经济吸引力也仅传递到西南夷上层,没有对少数民族民众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也的对云南地区控制成功的原因之一。二是,一些时期对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政策“比汉人”推进过快,没有顾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不平衡问题,造成一些少数民族的反抗。三是,一些政策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奴隶政策及奴隶需求对云南地区掠奴及与内地奴隶贸易的刺激。四是,向云南地区移民不仅规模不大,连续性不够,扶持政策也有限,对开发云南地区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1]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2]方铁.西南通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3]何跃华.云南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方慧.略论元朝在云南的经济法制措施[J].云南社会科学,1996,(5).
[5]战国策[Z].
[6]华阳国志[Z].
[7]史记正义[Z].
[8]史记[Z].
[9]汉书[Z].
[10]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1]后汉书[Z].
[12]盐铁论[Z].
[13]王宗维.汉代属国制度探源[A].马长寿纪念文集[C].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14]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算数书》释文[J].文物,2000,(9).
[15]刘金华.汉代物价考——以汉简为中心[J].文博,2008,(2).
[16]九章算术[Z].
[17]曾代伟,王平原.《蛮夷律》考略——从一桩疑案说起[J].民族研究,2004,(3).
[18]晋书[Z].
[19]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0]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J].文物,1993,(8).
[2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2]东观汉记[Z].
[23]昌言[Z].
[24]太平御览[Z].
[25]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Z].第3080,3083,3097 号,法藏馆,1990.
[26]唐六典[Z].
[27]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册)第1970A 号[Z].北京:中华书局,1991.
[28]丁邦友,魏晓明.关于汉代盐价的历史考察[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2).
[29]徐扬杰.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G]//中华文史论丛(第 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0]翟麦玲.汉代官吏家庭生活考[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4).
[31]洪适.隶释(卷十七)[Z].
[32]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3).
[33]汉旧仪[Z].
[34]尉缭子[Z].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6]商君书[Z].
[37]三国志[Z].
[38]万历《云南通志》《曲靖府古迹·汉李元礼碑》.
[3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第72.E.J.C:1 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40]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M].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31:56.
[41]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
[42]高敏.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J].求索,1985,(1).
[43]孙太初.关于新发现的汉延光四年刻石[N].云南日报,1956-10-30.
[44]江柏毅.汉王朝影响下的石寨山文化社会转变[G]//南方民族考古(第8辑).2012.
[45]汉纪[Z].
[46]尹建东,陈斌.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J].学术探索,2013,(7).
[47]王大道.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J].考古,1977,(2).
[48]张增祺.云南开始用铁器的时代及其来源问题[J].云南社会科学,1982,(6).
[49]李昆声.云南牛耕的起源[J].考古,1980,(3).
[50]呈文.东汉水田模塑[J].云南文物,1977,(7).
[5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嵩明梨花村东汉墓[J].云南文物,1989,(26).
[52]大理州文管所.云南大理大展屯二号汉墓[J].考古,1988,(5).
[53]王国辉,等.通海镇海东双水田池塘摸型[J].云南文物,1992,(31).
[54]曾磊.“牢盆”新证[J].盐业史研究,2009,(3).
[55]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Z].“官与牢盆”条.
[56]张明祖.“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辩析[J].连云港师专学报,2001,(3).
[57]梁银.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J].云南文物,1994,(3).
[58]王涵,梁银.嵩明凤凰窝古墓葬发掘报告[J].云南文物,2003,(5).
[59]康利宏,刘成武.曲靖市麒麟区潇湘平坡墓地发掘报告[G]//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北京: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60]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J].思想战线,1982,(2).
[61]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形[J].历史研究,1956,(9).
[62]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合校,第37.35 号[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65]王大道,邱宣充.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占墓群发掘简报[G]//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6]游有山,谢崇崐.昭通县鸡窝院子汉墓清理简报[J].云南文物,1983,(13).
[67]汪宁生.云南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68]朱运生.个旧黑蚂井古墓群[J].云南文物,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