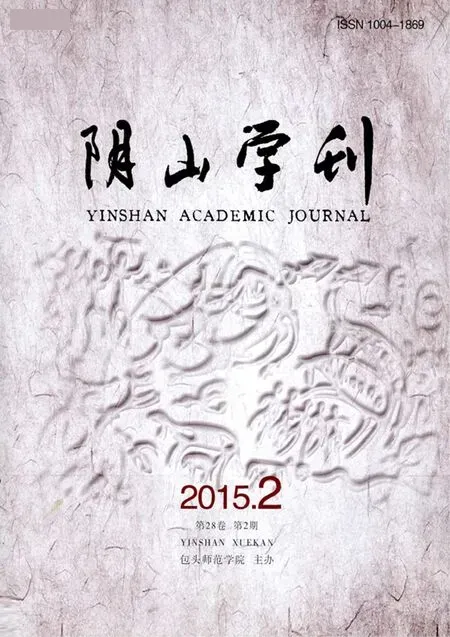论冯梦龙的情感本体论*
2015-02-12杨虎
杨 虎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论冯梦龙的情感本体论*
杨 虎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冯梦龙首次明确地对性情论模式进行了解构,从情感进路讲本体论,通过极成形上的“情体”而建构了后宋明理学的首个“情”本体论体系:“情”是万物的本体,无情则万物不生;人因情而生,故人世间的苦难与超越也必然因情而可能。冯梦龙对传统性情论持解构立场,并且明确地从情感进路讲本体论,这在其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冯梦龙;情教;情感本体论
一、孔孟儒学的情感领悟
儒学的根本观念在于仁爱。冯梦龙《情史序》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1](P1)按照冯梦龙的理解,这样的“情教”是超越佛教之慈悲和儒学之仁义的,具体说是能够超越儒佛之差异的更加一般性的情感教化。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教’是宗教的意思,冯梦龙‘立情教’,就是要创立一种与佛教、道教一样的宗教。”[2]实际上,冯梦龙的所谓“情教”并不必然具有一般所谓“宗教”意味,因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情感教化未必是宗教形态的,譬如所谓“六经皆以情教也”[1](P2):六经皆是情感之教化。“情教”就意味着它既是情感性的事情,也是教化的事情。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情教”与孔孟儒学并无隔阂,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的仁爱观念既是情感性的事情,也是教化的事情。
仁爱作为一种情感教化,并不是譬如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情感的领悟及其“唤醒”[3](P94~95)。这样的例子在《论语》当中比比皆是,言“仁”多达百余条,其义类多以爱的情感为根底。譬如樊迟问何为“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的理解中,仁首先是一种爱的情感,没有爱的情感何谈作为德目抑或其它义项的仁?从爱的情感谈仁,则一切教化譬如礼教和乐教从本源处说必然是情感性的教化:“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和乐作为教化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源出于仁爱情感。通过礼和乐而体现情感的领悟,通过礼和乐唤醒这种本源的情感领悟。孔子与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感性的教化,即情感的领悟及其唤醒: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表面看来,“今汝安,则为之”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教训”而无关乎情感性的“教化”。其实不然,孔子之意可以如此理解:作为“天下之通丧”的“三年之丧”,它乃是源出于“三年之爱”。亦即,惟有从仁爱出发,才会有“三年之丧”这样的节目。这样的节目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体现仁爱情感的一种“礼”的表现形态,这是为了唤醒“三年之爱”。这里的观念层序应是:先有对仁爱情感的领悟,才有体现这种情感领悟的节目之设立,通过这个节目的真知真行而唤醒原初的情感领悟。所以,孔子说宰我“不仁”的理由首先并不是因为三年之丧乃是“天下之通丧”,而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即“三年之爱”这样的情感领悟。要而言之,孔子与宰我之间的这个经典对话可以理解为体现了一种情感性的教化——情感的领悟及其唤醒。
仁爱作为情感领悟,它并不是个现成的东西譬如今人所谓的“精神实体”,故孔子常随处指点。虽于时于境,孔子的指点不同,但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作为爱的情感之事情。平心而论,我们确乎很难把孔子所说的“仁”僵固化、现成化地理解。这种原初的情感领悟在孔子是为“仁”、“爱”,在孟子是为“不忍”、“恻隐”。
孔子随处指点仁爱情感,孟子则直接的以心立论,并进一步“描述”了当下性的仁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一“乍见”的当下,恻隐之心呈现,这是前主体性、前反思性的,不待理性计较的。因为这不是为了“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不是为了“要誉于乡党朋友”,更不是因为“恶其声”。孟子这里显示的乃是原初的恻隐领悟。
孟子所显示的原初的恻隐领悟,是一切建构性的“源泉”,所谓四端,其实一源也。后儒关于孟子讲的四端之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即这四端之心到底是情还是性?当我们以性情相对的格局来审视原初的恻隐领悟,就已经进入了建构性当中。当然,浑伦总要建构化,犹如“混沌死”[4](P309)是必然的。从浑伦到建构,从原初的情感领悟到宋明理学的性情论建构,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性情论模式下,作为爱的情感与作为形上本体的性理是不同其层级的。以宋明理学观之,这种意义上的情是有待被超越的。所以小程子说:“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5](P182)当性情对置,性被视为形而上者而情被视为形而下者时,宋明理学家便极力否认仁的情感性。这里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仁爱如果是情感性的,它便不能是奠基性观念;仁爱如果是奠基性观念,它便不是情感。
宋明理学的性情论模式由于极成“性体”的需要而排斥仁的情感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遮蔽了原初的情感领悟。不过,当宋明理学发展到王阳明,从性情、性气、性心的对置不断走向性情、性气、性心的合一,就使得此心、此理的情感性维度重新浮现,呈现了情感重新本源化的可能性。阳明突出了此心的情感性维度,从原初的恻隐领悟讲起,故恻隐之心即恻隐之理:
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6](P49)
阳明这里直接以恻隐言理,是即表达此心当下发见即理。于此,则性情不二,心性不二,心理不二,性理不二。见孺子而恻隐之理呈现,即“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6](P1015),即“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6](P1015)。恻隐之心即恻隐之理,不忍之心亦恻隐之理,怜悯之心亦恻隐之理。故见孺子而恻隐,见鸟兽而不忍,见草木而怜悯,虽其见不一,而其理不二。在心即理的问题上,阳明突出了此心、此理的情感维度。由此不难理解,良知的情感性维度的突出亦是顺理成章: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6](P92)
当天理被收摄进良知,而良知又只是“一个真诚恻怛”,则知情理圆融,情性不二。故于此,“致良知”实可谓“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于事事物物”,这从根本上说的乃是情感性的事情。总之,阳明理解的“良知”二义不可或缺:一者真实(真诚),二者恻隐(恻怛)。合而言之,良知必是真情——真实的情感。
阳明为后来的情感的本体化、本源化走向开了一个口子。随着晚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一种情感的本体、本源化走向愈加明朗。譬如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7](P1093)“情”不是被“起”者,而是自起者,故至极之情可以“起”生死,这里的情是在本体的层级上运用的。晚明的情感论走向,至冯梦龙而大成。
二、冯梦龙:“情体”的极成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1](P1)这条“情教”的总纲领的提出,表达了冯梦龙对性情论的解构立场。所谓“天地”不过是“万物之总名”[4](P20),真正起生生造化的乃是“情”。这就犹如大程子之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细缘,万物化醇。生之为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7](P120)只不过,在大程子这里,仁之为“性”,是起生生造化者,而冯梦龙则不言“性”而言“情”。那么,冯梦龙的情论都包涵哪些观念层级呢?
其一,情作为形而下的情感。冯梦龙《情史序》说:“余少负情痴,……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1](P1)这里的所谓“有情”、“无情”显然都是在形而下的层级上使用的,这就犹如我们今天的所谓“有情有义”、“绝情寡义”。又如:“不情不仇,不仇不情。”[1](P388)情仇相对,这也是指形下层级上的情。再譬如:“夫人一宵之遇,亦必有缘焉凑之,况夫妇乎!……缘定于天,情亦阴受其转而不知矣。吁,虽至无情,不能强缘之断;虽至多情,不能强缘之合,诚知缘不可强也。多情者,固不必取盈;而无情者,亦胡为甘自菲薄耶!”[1](P56~57)“多情”与“无情”相对,都是处在同一层级上的,此情乃是有所“阴受”,即它是被给出的。总之,此种层级上的情是指作为相对主体性的——人——的情感乃至种种情绪等。它显然是不能“生一切物”的,而只能是被“生”者,亦即宋明理学所言之形而下的“情”。情感当然包涵了这个层级,但是,在冯梦龙的情论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性情论模式:“人性寂而情萌。”[1](P84)这和传统儒学的性静情动说、性体情用说并无二致。作为形而下的被给出者,“情”是从何而来?按照宋明理学的思考方式,它给出的答案是:形而下的“情”是被形上的“性”给出的。如果说冯梦龙仍然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么所谓的“情教”说相较于宋明理学的传统思想进路并无突破。不过,冯梦龙给出的答案则是,一切形而下的“情”都是被唯一的“生一切物”的“情”给出的,后者可以说是形上的“情体”(Ontological Emotion)。
其二,情作为形而上的“情体”。如果说情是给出一切形而下存在者的本体,那么天地鬼神、善恶美丑都是被“情”所给出的。故情之生生,一切物得生,一切人得生,人物有生有灭而情则一如:“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即令形不复生,而情终不死……”[1](P260)虽天地鬼神亦然:“古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盖思生于情,而鬼神亦情所结也。使鬼神而无情,则亦魂升而魄降已矣,安所恋恋而犹留鬼神之名耶!鬼有人情,神有鬼情。幽明相入,如水融水。城之颓也,字之留也,亦鬼神所以效情之灵也。噫!鬼神可以情感,而况于人乎。”[1](P189)鬼之情,神之情,人之情,以至鸟兽草木之情,其情之不同,皆一于“情”。故天地鬼神之情即鸟兽草木之情,鸟兽草木之情即人之情,皆为“情”之一如。举凡天地万物,都无所逃于“情”:
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于万物中处一焉,特以能言,能衣冠揖让,遂为之长,其实觉性与物无异。是以羊跪乳为孝,鹿断肠为慈,蜂立君臣,雁喻朋友,犬马报主,鸡知时,鹊知风,蚁知水,啄木能符篆,其精灵有胜于人者,情之不相让可知也。微独禽鱼,即草木无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泄露其象。何则?生在而情在焉。[1](P677)
虽犬马鹿羊、山石草木亦皆有情,与人无异。有生必有情,无情则不生。天地万物皆“分天地之情以生”,在这个观念层级上,天地万物其情一如,而绝无“无情”者,无情则不生。有生而“无情”者,世间万物中绝无,如鸟虫之鸣,不得已而然:“鸟之鸣春,虫之鸣秋,情也。迫于时而不自已,时往而情亦遁矣。”[1](P695)时事之往来,皆情之无为而为之。
按照一元论的思想格局,虽世间极善之人事,世间极恶之人事,皆是情之所使然。故而情能使男女相悦,亦能使人生离死别:“死者生之,而生者死之,情之能颠倒人一至于此。往以戕人,来以贼己,小则捐命,大而倾国。”[1](P165)世间之喜乐由情而生,世间之苦恼亦由情而起:“人生烦恼,思虑种种,因有情而起。”[1](P165)故善恶美丑、生死情仇皆一于“情”,“情”本身则可以说是“无善无恶”的:“盖善恶之气,积而不散,……惟情不然,墓不能封,榇不能固,门户不能隔,世代不能老。”[1](P569)“善恶”相对,相对必有生灭,而情则生生不灭,因其无善恶之相对,绝对无待之故也。
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本体之“情”是无善无恶的,但世间可能的系累亦因有情而起:
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文王、孔子之圣也而情,……。情何尝误人哉?人自为情误耳!红愁绿惨,生趣固为斩然。即蝶嚷莺喧,春意亦觉破碎。然必曰草木可不必芽,是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吾未见其可也
虽情不误人,而人之自误却因有情,人之有情却又是必然的。这里的观念层序是这样的:人因情(情体)而生,生而又可能因情(形下层级)而累。如此一来,我们就必然面临着这个问题,即:该如何超越种种系累?当其时,冯梦龙可以有如下两种选择:
其一,摒弃人的情感,这就犹如“去人欲,复天理”[8](P26)。但这就意味着,原来“情”对于我们人来说并不是必然的,还有比“情”更原初的。这对于情论的思路来说明显自相矛盾。
其二,走向普遍之情,从而超越相对之情,这便是《情史序》所说:“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1](P1),超越了“无情”与“私情”的“情”,这说的乃是普遍性的情感。总之,冯梦龙最终选择极成形上的“情体”,建构起“情”本体论。
不过,情的本体化却并不意味着情的本源化之完成。众多学者均有这样的印象,晚明思潮例如冯梦龙的情论是从理性走向了非理性,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哲学的所谓“非理性主义”思潮相较于传统形上学而言确乎突出人的情感、意志而拒斥理性的本体化。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什么叫做非理性的观念?这只能根据一种理性的观念来界定。”[9](P51)换句话说,非理性主义不过是理性主义的另一种形态而已。同样,冯梦龙虽然对性情论持解构的态度,但其“情”本体论并未彻底超越性情论模式,其实质是把“性→情”置换为“情→情”,这仍然是另一种形态的“性→情”。
儒学的情论从浑伦走向建构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反向观之,则情的本源化之完成就意味着彻底超越传统形上学的性情论模式,其实质是超越传统形上学的两层架构:形上→形下。整体来看,冯梦龙的“情”本体论仍然属于宋明理学的范式。尽管如此,冯梦龙对性情论持解构立场,并且明确地从情感进路讲本体论,这在其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1]冯梦龙.情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傅永洲.“情教”新解[J].明清小说研究,2003,(1).
[3]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7]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 伟〕
On the Emotional Ontology of Feng Menglong
YANG Hu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Feng Menglong deconstructed the Xing-Qing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Feng Menglong’s philosophy is in the route of feelings, and in the view of emotion, and constructed the first “Emotional Ontology” of post-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by the “Ontological Emotion”.“Emotion” is the reality of beings, human is given by “Emotion”. Therefore, only by Emotion can we win through the sufferings of the world. Feng Menglong’s philosophy attempts to deconstruct Xing-Qing theory, and which is the first signs of the emotional turn of Chinese philosophy.
Feng Menglong;Emotional education; Emotional ontology
2014-12-13
杨虎(1989-),男,河南周口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研究。
B222.9
A
1004-1869(2015)02-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