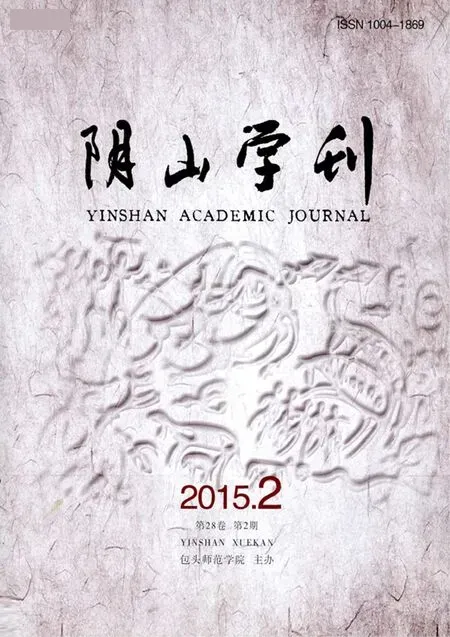明清之际佛教传戒制度之再创制*
2015-02-12刘晓玉
刘 晓 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哲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00)
明清之际佛教传戒制度之再创制*
刘 晓 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哲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00)
纵观中土佛教传戒制度的流变,乃至戒坛的沿革,实与印度佛教之中国化的历程相呼应,而律宗一脉的接续与开衍,传戒制度的再创制,直至明朝末年方见勃兴。
明清之际;传戒制度;再创制
佛教在教团初创期,尚未形成固定的出家授戒法,十种具足戒反映了佛陀时代僧人获取出家身份的不同方式。随着戒坛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授戒制度也发生了改变,其表现就是“方等戒坛”的出现。万历朝恢复传戒,弊端复显,这其中虽有国家宗教政策更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佛教自身内部的问题也是症结之所在。一方面由于国家解除禁令,并打破了过去只有律寺方可传戒的传统,进而演变成禅、教、律寺竞相传戒,滥传戒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因弘戒传承的长期中断,重禅教、轻戒律的修学氛围导致了仪典荒废,戒学不兴,修学毗尼者鲜有其闻的境况。也正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僧团队伍中出现了一批沿革古规,扭转时弊的有志僧人,他们研毗尼,立仪范,专精弘戒,促成了中国佛教传戒特质的“三坛大戒”制度的确立。
一、佛教传戒制度流变概述
最初中土没有出家授戒法,直到唐代,诸部律典传译完备,中土戒律受随不一的问题终得以解决。至元代,汉传佛教凋敝,唐宋时期诸家撰述的律学典籍因无人问津而渐散失殆尽,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流行传播,律典的传译,戒坛在江东一带也迅速普及。
(一)印度佛教的授戒法
比丘身份的获得,以出家得受具足戒为标志。有关原始佛教时期,教团授戒的情况,《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衹律》四部律典均有记述,其中《十诵律》综合了比丘与比丘尼的情况,共指出佛陀时代十种具足戒:
佛世尊自然无师得具足戒;五比丘得道即得具足戒;长老摩诃迦叶自誓即得具足戒;苏陀随顺答佛论故得具足戒;边地持律第五得受具足戒;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受八重法即得具足戒;半迦尸尼遣使得受具足戒;佛命善来比丘得具足戒;归命三宝已三唱我随佛出家即得具足戒;白四羯磨得具足戒,是名十种具足戒。[1](P10)
佛教在教团初创期,尚未形成固定的出家授戒法,上述十种具足戒,反映了佛陀时代僧人获取出家身份的不同方式。
至部派佛教时期,律分五部*部派分裂时期,有昙无德等五大弟子从《八十诵律》中采集律法,各有宗依,其中昙无德部为《四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弥沙塞部为《五分律》;萨婆多部为《十诵律》;摩诃僧衹部为《摩诃僧衹律》。自唐道宣采掇诸部,宗依四分以来,汉地佛教传戒仪轨均宗依昙无德部《四分律》,故本文亦以《昙无德律部羯磨》为例。,按此分法,昙无德部宗依《四分律》,按《昙无德律部杂羯磨》所记仪轨:“白四羯磨”前增加了“问遮难”(教授师向欲受戒者问十三重难、十六轻遮,受者须依实情答“有”或“无”);“白四羯磨”后增加了“示四根本戒”(淫、杀、盗、妄语)和“授四依法”(依粪扫衣、依乞食、依树下坐、依腐烂药)共三项内容[2](P1042)。
(二)中土佛教传戒制度沿革
佛法东传,最初中土没有出家授戒法,只受三皈依者落发以示有别于俗,如此大僧与沙弥则无区别。直至魏嘉平二年(250年),善诵诸部毗尼的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共安息国沙门昙谛,于洛阳译出《四分羯磨》与《僧祇戒心》,立大僧羯磨法,准用十人僧,中土戒律方由此始[3](P325)。
自佛教东传,至刘宋一朝,僧尼二众的受戒法终得以建立,但因最初戒律传译的偶然性,诸部广律并未全部译出,奉行者因无所准鹄,故而出现了受戒依《四分羯磨》,行持依《僧祇戒本》的状况,直到唐代,诸部律典传译完备,中土戒律受随不一的问题终得以解决。其中对此有决定性贡献的,当属弘扬《四分律》的南山宗祖师道宣律师,他以“化、制”二法判教,并以大乘思想会通属小乘戒法的《四分律》,最终确立了南山律学在中国律宗的主导地位。
(三)中土佛教传戒戒坛沿革
坛,梵云曼陀罗,梵文:mandala,有“聚集之意”,佛教中授戒的场所称为戒坛。依律建设坛场是教团传戒的前提,依法登坛受具则是比丘身份获得的唯一条件。按《释氏要览》的记载,佛教戒坛之滥觞,乃佛陀时代楼至菩萨请求筑戒坛为比丘受戒,佛许之,并于祇园精舍外院之东南建坛[4](P273)。依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的介绍,中土建坛之始,乃天竺僧求那跋摩于扬州南林寺所立[5](P812)。《佛祖统纪》记载“(元嘉)十一年(434年),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
随着戒坛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授戒制度也发生了改变,其表现就是“方等戒坛”的出现。“方等戒坛”专传大乘菩萨戒法,实与中土盛行大乘文化的背景相契,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到了宋代,律师们仍遵照《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的规制,设立戒坛传戒,比较特别的是别立大乘戒坛。据载,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开封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与此同时,全国的戒坛有七十二所,而开封的另一寺院——慈孝寺,则别立大乘菩萨戒坛,先于各方受声闻具足戒的比丘,后至慈孝寺增受菩萨戒[6](P404)。
二、明朝戒坛之兴废
(一)明朝前叶佛教的传戒情况
明朝初年,洪武、永乐二帝本着佛教对国家社稷有“阴翊王度”、“暗助王纲”功用的认识,对佛教多实行扶植和保护的政策。洪武十年、永乐五年两位皇帝先后下旨对依法出家受戒者给予支持和保护:洪武十年皇帝下旨令“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僧俗善人许令斋持戒牒随身执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他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7](P929)此时,拥有戒牒的僧俗自由度很高,往入城乡,结坛游化都受到国家政令的允可。至永乐五年,崇信佛教的朱棣皇帝,延续其父扶植佛教的宗教政策,乃至更为推崇、宽限。
尽管明朝前期的宗教政策较为宽松,对待佛教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这种宽松与友好是建立在佛教有益于社会稳定的政治功用之上,就佛教自身的发展而言,国家还是严令控制的。明朝早期规模较大的佛教丛林,多在皇权授意下,以上报皇恩,福佑社稷为由开坛传戒。
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多于全国钦选戒行高超,或是在僧团中有影响力的僧人传授皇戒,而帝王对佛教的这种扶植实则也包涵着或利用或笼络或信奉或控制的复杂心理,并且随着皇权的更迭,帝王个人的宗教偏好,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都影响到了历朝宗教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此影响下,佛教以及佛教僧团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地位与境况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明朝中叶政府诏禁戒坛传戒的宗教政策及影响
明中叶的嘉靖皇帝与明初的几位帝王不同,极为宠佞道教,排斥佛教。嘉靖皇帝在其当政期间颁布了一系列诸如焚佛骨,毁佛像,沙汰僧尼,不许僧人游方说法等针对和控制佛教的政令。据《明世宗实录》所载,他先后于嘉靖五年五月(1526年),二十五年七月(1546年),四十五年九月(1566年)下令,严禁僧尼开坛传戒,态度坚决且惩处严重。[8]皇帝崇道斥佛,虽有宗教权贵逞强争宠之原因,但落实到具体朝廷政令的下达,实应有现实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因素的考虑。
政府下达命令诏禁戒坛传戒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政府出于维护政权稳定,防止聚众而起祸事的考虑。在官府看来,佛教开坛传戒是一场大型的僧团活动,四方缁衣聚集一处,男女僧尼混淆,既有伤风化,又有作奸犯科之徒混入其中危害社会的危险。而此一时,白莲教兴起,为了防犯白莲教之徒混入其中,挟惑媚众,危及政权,政府以禁止佛教开坛传戒的方式,严格防控人口聚集。
其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虑,儒臣认为佛教法式活动靡废资财,无论是富民豪族,还是贫民寒士,施财于佛门,均不利社会生产。这种经济实用主义的思想,本无可厚非,确有利民利生的现实意义。然此靡废资财的崇教之风实有上行下效之嫌,翻阅史料,大量关于宫庭贵胄不计资财,豪施教门的记载不胜枚举,若上不端严,下实难改。
其三,有关文化正统的地位之争。一部分儒臣站在反对佛教的立场上,倡导通过儒家的礼乐教化,伦理规范,达到扬善止恶的道德追求。儒臣以释道二教为异端,认为皇帝之福得自于天,若以异教为用,则是违背遵祖制和儒家礼法。朝堂之上,既有崇佛信教的,也有反佛尊儒的,以正统自居的儒臣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也会站在崇儒反教的立场上,进而影响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与施行。
政府以控制僧团数量,维护社会乃至政权稳定为出发点,采取了禁止开坛传戒的政策,然按佛门僧人的记述,此项宗教政策的执行对整个佛教的长久发展,乃至僧团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不传戒,出家人则不学戒,不知戒,既无律仪之持守,公然违犯戒律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佛教甚至沦为了藏污纳垢之所,整个僧团队伍良莠不齐,流弊丛生。如此混乱颓败的景象,不仅对佛教不利,更是与政府整肃僧团,维护社会稳定的初衷不相符契。
(三)明朝后期开坛传戒的恢复
自古宗教政策的制定都以维护国家政权为第一要义,所以不论是明初的普开皇戒还是明中叶的政府诏禁戒坛,都是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政治考虑。嘉靖朝出于控制僧团数量,整肃社会的目的禁止佛教开坛传戒,但在现实效果上,却造成了僧人自不受戒,律仪无处可学,戒律仪轨渐被废驰的局面,更对整个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不利。因此,在戒坛被封闭的五十余年间,佛教日渐颓败的境况促使僧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对佛教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激进者更对给佛教造成不利影响的国家政令进行批判。另有一批僧团领袖则直接采取或温和或积极的传戒行谊,在实践层面展开了弘扬戒律,重振丛林的佛教复兴运动。
有僧人站在维护佛教的立场批评国家政策的不当,湛然圆澄就认为政府将超过百人的丛林一律视为红莲、白莲教,尽而诏禁戒坛的宗教政策导致了佛教的衰微,并指出纵然佛门有不肖之徒,那也只是少数人,佛门出现不端之事“非佛法之不善,而制法之不尽善耳”[9](P368)。
而被誉为晚明四大高僧之首的云栖袾宏,“以精严律制为第一行”,他在面对国家诏禁戒坛的情形时,表现出了僧团首领处理政教矛盾的灵活机变。在不违抗国家政令的前提下,祩宏以其影响力集合僧众,通过诵读菩萨戒经和比丘戒品的方式严持戒行,弘扬戒律,与一味慨叹相比,这种方式显然更具有积极意义。
相较于云栖袾宏较为温和的传持戒律的方式,与其同时代的古心如馨则表现得更为积极、大胆。他不惧朝廷的禁令,先后在江苏南京一代的灵谷、栖霞、甘露、灵隐、天宁诸寺开坛授戒,产生了“廷臣野叟,罔不知有戒”[10](P17)的重大影响。尽管有违抗政令的危险,但古心如馨弘扬戒律的行谊实则体现了出世僧人所应具有的独立品格和风范。
在政权大于教权的现实国情下,佛教丛林要想广泛地开坛传戒,弘扬戒律仪轨就必须得到国家政令的允可,这一转折的契机发生在明神宗万历朝,最终明政府解除佛教寺院开坛传戒的禁令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近幸神宗圣明英拔,于晚年深知佛戒有禆世道,乘五台僧远清之奏,慨赐衣钵、锡杖、斋钱若干缗,勅中贵张然传旨,许山中说戒。”[11](P612)自此,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国家颁布执行的严禁僧尼戒坛传戒的禁令就废止了。
三、明末清初“三坛大戒”制度的确立
古心所撰的《经律戒相布萨轨仪》意在强调在末法时期,为使正法久住,当以持戒为第一修持要义的宗旨,对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发展、完善实有首倡之功,当属三坛大戒的开山之作。法藏所撰之《弘戒法仪》明确提出了“三坛戒法”、“三坛传戒”之称谓,使得三坛大戒齐受的戒律实践有了可依之文本,为后世三坛传戒法式的成熟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心再传弟子见月的《传戒正范》是明清之际中国佛教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成熟之作,历代诸本传戒仪轨的集大成者,是明末清初以降,佛教丛林最为流行的传戒范本。
(一)“三坛大戒”制度的仪轨沿革与戒本解析
古心是晚明佛教恢复开坛传戒后,第一位奉命传皇戒的律师,并最早践行了沙弥、比丘、菩萨三大戒在一段时期内次第授受的传戒形式。其所撰的《经律戒相布萨轨仪》意在强调在末法时期,为使正法久住,当以持戒为第一修持要义的宗旨。尽管古心之《经律戒相布萨轨仪》在教义、仪轨上略显简单、粗糙,其对佛教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设计也仅具雏形,但是他对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发展、完善实有首倡之功,因此《经律戒相布萨轨仪》当属三坛大戒的开山之作。
法藏所撰之《弘戒法仪》承继古心之《经律戒相布萨轨仪》,是晚明第一部完整陈述三坛传戒仪轨的著作。据《弘戒法仪》序言所述,法藏于云栖袾宏处受沙弥戒,在古心处受具足戒,又在云栖塔前得受菩萨戒,愤于当时因戒坛封闭,“仪法尽亡”,禅律两宗“相互讥诃,难于会和”的局面,乃“求拾古规”,参演于古心处所受的具足戒仪,仿照袾宏《梵网经菩萨戒疏发隐》中的菩萨戒仪,力图达到“禅教律三宗,会归实相无相,涅槃妙心之一旨”[11](P576)的境界。作为传戒仪法的专业著述,法藏的《弘戒法仪》在中国佛教传戒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作为中国佛教独有的传戒形式,该法仪第一次完整组织了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三坛同受之仪式,并明确提出了“三坛戒法”、“三坛传戒”之称谓;其次,该法仪的出现使得三坛大戒齐受的戒律实践有了可依之文本,为后世三坛传戒法式的成熟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始自古心的《经律戒相布萨轨仪》,再到古心得戒弟子汉月法藏的《弘戒法仪》,明清之际中国佛教三坛大戒传戒仪轨的成熟之作,历代诸本传戒仪轨的集大成者,当属古心再传弟子见月的《传戒正范》。该书是明末清初以降,佛教丛林最为流行的传戒范本。《传戒正范》将沙弥、比丘、菩萨三个层次的戒法,在为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之内,次第完成,合称为三坛大戒的戒期法会。该文以四六对仗的骈体行文,读来流畅优美,加以开导、唱诵、问答的方式演进,使得科仪、轨则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该法仪被盛赞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12](P626)
(二)“三坛大戒”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
自佛教东传,中土设立戒坛传戒以来,沙弥、比丘、菩萨三坛戒法都是要在三个不同时期分别授受的,从未有一时俱受三坛之举,至明末,经历了戒坛兴废的佛教,于此时产生了三坛顿受的传戒方式,无疑是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的一种再创制,然任何制度的变革都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明末佛教传戒制度的再创制同样也是在当时佛学理论发展基础上实现的。
晚明以前,律寺传戒,三坛戒法分期授受,其特点是戒期难遇,求戒难得;晚明以后,为方便学子受戒,三坛戒法则在一个戒期内次第而授,传戒成为了规模盛大的法会。可见为得方便之利是当时传戒方式变革的一个直接原因,而三坛大戒传戒方式的起源,也正印证了这种方便说。
见月宗承南山,遵弘《四分律》,曾言:“今宗昙无德《四分律》者,盖是南山圣师之所宗故,自唐以降皆弘通故,……余今宗之”[13](P322)。中土所宗之《四分律》虽为小乘律典,但自唐道宣会通大小,以“删繁补阙”为宗旨阐扬以来,小乘的声闻律典即被赋予了大乘的精神解读,按道宣在《行事钞》中所论,戒法理无大小二乘之分,所现不同只因悟解有差,见月律师对三坛戒法同受的论证,也正是以“大小二乘,理无分隔”为精神宗趣的。
纵观中国佛教的戒律发展史,虽然自唐代道宣律师始,小乘的声闻戒已经在精神宗趣上被融摄成具有大乘意义的声闻戒,但从授戒的形式来看,声闻与菩萨,小乘与大乘戒律依然两分,表现为不同的授受体系。直至明清之际,以古心、法藏、见月为代表的晚明律学家,一方面继承前辈宗匠的律学思想,继承大小乘戒律相与会通的意旨,另一方面则通过一期三坛,顿受三戒的授受仪式,将大小乘的会通之义从理论付诸实践,此改革之举无疑是佛教戒律制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而于明清之际有此仪式创制,反映出此时中国佛教在思想理论上,已经视一期受持的小乘声闻戒与尽形寿受持的大乘菩萨戒为一体,菩萨戒是大乘的,声闻戒也是大乘的,如此可以一期同受,顿入佛乘。应该说这种仪制改革适应了中土佛教喜好大乘的机运,反映了中国佛教戒学思想于明清之际的成熟与完善。
(三)对“三坛大戒”制度的质疑与评议
三坛传戒,自明清以来渐为中土佛教传戒之定式,见月所作之《传戒正范》也被天下丛林奉为传戒司南。然在受到推崇与肯定的同时,历代对它们的评议以及质疑依然不断。
智旭与见月同一时代,虽非律师却潜心律学,曾三次遍阅律藏,著述颇丰,是晚明为数不多的通达律典的佛门高僧。然智旭对当时渐已流行的三坛传戒这样的大型传戒法会,颇有微词。智旭反对这种仪节繁复,人数众多的传戒方式,认为依照律典*按《五分律》‘有诸人欲受具足戒,不能得集十如法比丘’,作是念:‘若佛听我于布萨时、自恣时、僧自集时受具足戒者,无如是苦’以是白佛,佛言:“‘听因布萨时、自姿时、僧自集时,受具足戒。’”,只要具足十人僧,便可以在每半月诵戒之时(布萨日)、每年的夏安居圆满大众僧集会之日(自恣日),或者大众僧自行集合时,给请求出家者授戒。
如果说智旭只是对三坛传戒隆重而繁复的仪式表示不满,作为见月嗣法弟子的书玉律师则直接否定了三坛传戒这种传戒形式。依书玉律师所见,一期三坛的传戒方式只是度众的方便,传统的受戒方式,依受戒者的发心情况次第而授,方是正统。可见在三坛同受日渐流行的时代,此法虽然在现实层面被操作践行,但在理论层面,把小乘的声闻戒与大乘菩萨戒放在同一层级下等而视之,并未被完全接受认同。
清嘉庆年间,有曹洞宗性海觉源禅师与其本师焦山借庵作《觉源禅师与本师借庵老和尚论传戒书》一文,评议《传戒正范》三坛传戒,并从文义的角度指出其中的四点不贯串处,分别为:发菩提心不贯串,忏摩不贯串,问遮难不贯串,白四羯磨不贯串。
觉源所指《传戒正范》的发菩提心不贯串,忏摩不贯串,问遮难不贯串,以及白四羯磨不贯串的四种不贯串处,确有经典依据,觉源此举大有追本溯源之旨,正本清源之意,《传戒正范》之谬误虽非其所言重者,但实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发菩提心不贯串一项,需要特别注意。
综上可见,三坛顿受的传戒方式以及见月的《传戒正范》,自问世之时就饱受评议,这种争议与质疑的背后实则反映了印度佛教传统与中国佛教创制,遵从原始律典与现实环境调适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尽管与古规不甚相同,但三坛顿受这种制度改革无疑是时代变迁和佛教发展的反映,能立为定式和成为范本本身也是适应时代的明证。
[1](姚秦)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56)[A].大正藏·册23[C].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2](曹魏)康僧铠译.昙无德律部杂羯磨[A].大正藏·册22[C].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3](梁)慧皎.高僧传(卷1)[A].大正藏·册50[C].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4](宋)道诚.释氏要览[A].大正藏·册54[C].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5](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A].大正藏·册45[C].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6](宋)志磐.佛祖统记(卷44)[A].大正藏·册49[C].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7](明)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A].大正藏·册49[C].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8](明)徐阶.明世宗实录·明实录[C].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3.
[9](明)圆澄.慨古录(卷1)[A].卍续藏经·册65[C].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0](清)福聚.南山宗统(卷2)[A].台南:和裕出版社,2001.
[11](明)法藏.弘戒法仪(卷2)[A].卍续藏经·册60[C].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2](清)戒显.传戒正范·序[A].卍续藏经·册60[C].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3](明)见月.毗屁止持会集[A].卍续藏经·册39[C].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责任编辑 常芳芳〕
Buddhist Ordination System Recre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U Xiao-y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Zhengzhou 450000)
The theology of Buddhism initi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the altar of history, is corresponding in the Sincization of Indian Buddhism. While the splicing and open of the Vinaya School, the recreation of the pass-vinaya system rose until the Late Ming Dynasty.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pass-vinaya system; Recreation
2014-07-13
刘晓玉(1983-),女,河南南阳人,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讲师,主要从事宗教哲学研究。
B948
A
1004-1869(2015)02-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