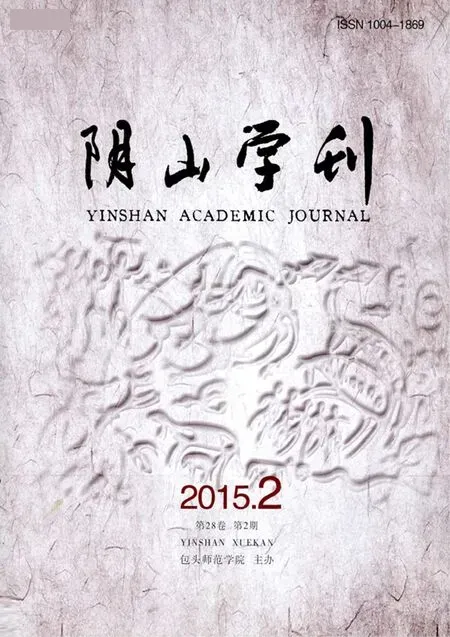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安徒生童话中的“天使”*
2015-02-12王敏
王 敏
(包头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 包头014030)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安徒生童话中的“天使”*
王 敏
(包头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 包头014030)
安徒生童话中写到了很多“失语”的女性及女性“天使”,一些评论以此认为这些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男权思想。其实安徒生童话更是一种通过为女性“代言”、写出女性主体的奋争之姿以及“双性同体”式的创作思想而唱响的“人类之歌”。
女性主义;安徒生童话;天使
一、从“失语症”说起
安徒生的两个著名童话《海的女儿》和《野天鹅》都写到了女性的“失语”,前者在追索“人的灵魂”的路途中不得不以付出甜美的嗓音和动人的歌喉作为代价;后者为了拯救十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哥哥而必须遵守“缄默”的规则。于是我们看到,小人鱼没有办法告诉王子是自己救了他的真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爱上了别人,因而失去了从爱情中获得不朽灵魂的机会;艾丽莎呢,必须承受大主教的恶意揣测,在流言蜚语中以一个罪恶的女巫形象活在世人的眼里,而她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辩诬,继续着寻找和编织荨麻的任务。
女性的失语曾是人类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男权文化对女性暴力统治的结果。保罗写道:“妇女必须学会沉默,必须完全屈从,我不允许她行如导师,不允许她在任何方面对男人施展权力,她必须缄默无声。”[1](P13)这样的社会现象导致在文学的书写中,男性成为绝对的主宰,他们可以任意地言说女性,将她们塑造成“天使”或者“妖妇”。男性的这套言说系统已不知不觉地成为禁锢女性的思想意志,内化到她们自身的血液和骨骼之中,使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无语的“他者”——这可以说是女性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发现,它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建立自己理论大厦的根基。因此,女性的无语或失语成为女性主义批评者极为敏感的意象和话题。
黄浩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安徒生童话——试析〈海的女儿〉和〈野天鹅〉》一文即是从两位女主人公的失语这一角度来展开论证的。文章认为,从海底世界的“主动保持沉默”到人类世界中“被迫保持沉默”,再到天空世界的“不得不保持沉默”,是人鱼公主在这三个世界的生存状态和“共同处境”,它们“充分说明”人鱼公主“是一个在男权文化社会中无法自由表达自我的‘他者’”。而艾丽莎也是一样,她“自始至终被迫保持缄默无声的失语状态,而沉默正是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文章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篇童话“宣扬了男性中心、女性依附的男权思想”,作者安徒生的“骨子里渗透着男权文化和父权思想”[2]。
对女性失语的文化现象给以关注可能正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但以此作为文学欣赏和解读的立论依据则要加倍小心。因为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什么,不一定意味着他对这一描写对象持赞赏的态度,作家的思想倾向的表达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安徒生在童话中描写了女性的失语,就据此认为是作家男权意识的膨胀,这样的推论过程和结果就显得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了。《野天鹅》是安徒生对格林兄弟搜集的民间童话《六只天鹅》的文学性改编,这深深植根于民间语境中的童话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遭受父权文化的侵染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女性的被迫缄默是父权文化压制下的一种历史产物,不是哪一位男性作家的发明。《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的原创,作者让女主人公失语,既可以理解为作家对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客观描摹,也可以理解为作家自己进入上流社会后,没有真正能与之沟通的语言,无法融入其中,在感情上还存在着极大的隔膜[3](P73)。
不能从作品的表面妄加揣度前人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只有深入到文本的内部、深处去细加揣摩,以一种审美的、文学的态度和方式去观照作品,才有可能得出中肯和客观的评说。
翻开《野天鹅》,最感动人的莫过于作者对艾丽莎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折磨、误解和伤害执着地采摘荨麻和编织衬衫的描写,这是仙女指点下拯救十一个哥哥的唯一办法,但与之相伴随的即是艾丽莎的“失语”。与其认为这是作者的男权意识的产物,不如将这种倾情的描写看作是作者替失语的女性的“代言”:“她用她柔嫩的手拿着这些可怕的荨麻。这植物是像火一样地刺人。她的手上和臂上烧出了许多泡来。不过只要能救出亲爱的哥哥,她乐意忍受这些苦痛。”[4](P167)“啊,她多么希望能够信任他,能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告诉他啊!然而她必须沉默,在沉默中完成她的工作。因此夜里她就偷偷地从他的身边走开,走到那间装饰得像洞子的小屋子里去,一件一件地织着披甲。”[4](P171)当十一件披甲掷向天鹅,十一个哥哥恢复了人形,作者将历史上被迫失语遭人误解的女性的清白还给了她们,他写出了历史和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当最大的哥哥说出真相时,“有一阵香气在徐徐地散发开来,好像有几百朵玫瑰花正在开放,因为柴火堆上的每根木头已经生出了根,冒出了枝子。”[4](P173)这是安徒生以童话的方式对真相的命名——女性之美的真相不会因为男性的刻意压制而被淹埋。
“安徒生也是一个洞悉社会与人,洞悉人性的崇高和变异,洞悉日常琐事和浩瀚宇宙的万象之谜的作家”[5](P60)。这种洞悉一切的睿智不也正体现在替女性的代言中吗?不仅如此,从格林童话中的六只天鹅到安徒生童话中的十一只天鹅,这应该不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简单递增,它也有可能是一种对男性群体的隐喻。被魔法禁锢的哥哥们不但失语,而且失去了人形,能使他们摆脱厄运的只有妹妹艾丽莎的拯救。艾丽莎对哥哥们的爱更近似于一种母爱,这无疑是女性所独有的、超越于男性的、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和谐和温暖的东西。我们猜想安徒生为什么只改写了这篇《野天鹅》,而没有触及格林童话中更为人所熟知的《白雪公主》或《睡美人》,可能是艾丽莎的隐忍、无语、牺牲的背后埋藏着更多的人性的高贵情愫打动了他,这应该是超越性别界限的全人类更为美好的东西。
构成《海的女儿》故事情节的基本动机就是人鱼公主与众不同的追求和渴望:从海底世界去到人类世界。一些持女性主义批评观的论者认为这是女性渴望进入到男性世界乃至永恒世界的象征,并以人鱼公主必须要将鱼尾变成双腿,同时失去自己的声音作为观点的支撑[6]。也就是说,《海的女儿》是安徒生对女性艰辛的追寻之路的书写。从童话象征的角度看,这样的解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的确,小人鱼的失语再次印证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艰难,但是作者不但再度道出失语背后的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遵从情感的逻辑让小人鱼抛掉了那把刺向王子的尖刀,纵身跳向大海,她“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小人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4](P56)小人鱼放弃杀掉王子而选择了自我牺牲,成为让全世界的读者最为动容的情节,其实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惊诧与震撼,更是熨贴心灵的欣赏和认同——这正是人世间的真爱必然要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男性为女性设计的规定动作。
真爱就是在“不是他死,就是你死”的两难困境中毅然选择牺牲自己的勇气和作为,在这方面,女性无疑比男性拥有更大的能量。不论从艾丽莎的亲情还是从小人鱼的爱情中,我们都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至于小人鱼并没有化为泡沫而升上天国并且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不朽灵魂的结局,既是童话追求圆满结构的需要,更是作者对女性乃至人性的至高赞誉,我们也不妨把它理解为女性已经超越了男性,为这个世界奏响了和谐之音。从这个角度上说,小人鱼并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洞察一切的造物主眼中的女性。
二、“他者”与“主体”再辨析
安徒生童话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童话的开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超越了传统民间童话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以白雪公主为代表的传统民间童话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模铸在厄运、魔法、获救、圆满的情节链条中,性格特征也多凝定于柔弱、善良、无助、被动等层面。这些被形塑为“天使”的形象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是“男性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是承载着男性欲望和目光的无语的“他者”。乍看起来,艾丽莎、小人鱼,包括拇指姑娘等等都是安徒生笔下的“天使”,她们与传统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们一样美丽、善良、纯真、可爱,但仔细辨别,她们在作家笔下,却显露出努力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体性光彩。
主体性的获得一直伴随着人类前行的脚步和历程。文艺复兴后,人的主体性的思考成为西方文学艺术乃至哲学的主要命题。而女性主体性更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的理论重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是否塑造了女性主体作为阐释文本意义的一种价值尺度和价值支点。刘思谦认为,女性主体性体现在女性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现在由他者、次性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表现在女性由依附性到独立性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7]《海的女儿》中,成为一个人、品尝人类的爱情、获得不朽的灵魂,成为小人鱼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自觉放弃了海底世界三百年的寿命,主动承担了“每一步都像行走在尖刀上”以及不能说话和唱歌的痛苦,虽然在争取爱情这一点上她失败了,但在得到不朽灵魂的征程中她胜利了。这不是作家给予人物的褒奖,也不是对读者的安慰,而是作者对人包括女性实现自身主体性的思考和解答。《野天鹅》中,同样是被厄运的阴影笼罩,同样被恶毒的继母诅咒和驱逐的艾丽莎为了寻找和拯救哥哥,毅然踏上了孤独艰险的旅程。这里,爱是主体行动的动机,更是主体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它具体化为“女性生产力的象征”——编织,它不以强力出现却有着强力不可比拟的力量,最终使艾丽莎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自我的拯救。《拇指姑娘》中,拇指姑娘那么小,那么柔弱,癞蛤蟆可以背走她,金龟子可以叼走她,田鼠可以将她许配给鼹鼠,但即便再弱小,她也努力成为一个命运的主体:怀着一腔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怀着一股与命运搏击的勇气,拇指姑娘最终摆脱了阴暗、庸俗、没有快乐的生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和爱情。
如果说,《野天鹅》和《海的女儿》是通过“无语”写出了女性的历史境遇,那么《拇指姑娘》则是通过弱小的体格与庞大的时空环境压迫的对比来表现女性的处境的。作为一个有着深刻的现实情结的童话诗人,安徒生不可能不对女性的生存以及命运给以关注。在这些童话篇章中,安徒生不仅以象征的手法写出了女性生存的客观情境,而且从女性的视角充满激情地写出了她们作为主体的奋争之姿;他不仅不吝笔墨地盛赞了女性之美,同时还向她们传递了最美好的人生祝福。
或许有人要说,美貌、善良、甘于牺牲,依然是男性为女性粘贴的性别标签,公主最后找到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男性为女性安排的最终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徒生并没有摆脱这种刻画女性形象的藩篱。然而,美轮美奂、心存善意、为他人着想、与自然更为贴近等不正是造物主赋予女性的特质吗?后现代女性主义已将发挥女性特质看作是两性和谐相处的最佳路径。另一方面,对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心灵相通的爱情和婚姻的向往和追求,难道不是每一个生而为人的最自然的渴求吗?女性主义理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其实也不断地进行着理论的自省和调适,我们不该将自己囿于这样一个理论怪圈之中,即在推翻男性霸权的过程中又将男性视为“他者”,这不该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最终的理想。安徒生作为一个创作主体,他在自己的童话创作中也大量地融入了个人的人生际遇、人生感悟、个性特征,在小人鱼、艾丽莎以及拇指姑娘身上,倾注着安徒生个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投射着作者个人追寻主体性的鲜明印记。
安徒生创作的时代,正值欧洲浪漫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重视挖掘想象瑰丽的民间文学、在创作中表达独特的自我体验成为时代文学的最强音。在丹麦本土,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对安徒生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位被称为“19世纪的苏格拉底”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认为,“宗教仅仅是一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理念,人们可以不必顾及上帝的存在与否,而只消面对他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另一个人可以是‘助产士’,但是‘分娩’最终还是个人自己的事。”[8](P205)他强调人可以利用自己命定的存在去创造自我的本质,“人之所贵”,就“在于人有选择改造自己的本质的自由,他如何选择做自己想要做的人,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人的本质。”无论是安徒生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是他的创作,可以说都是这种主体性超拔而出的形象证言。
安徒生从一个穷苦鞋匠的儿子,历尽艰辛与挣扎,最终凭借写作确证了自身主体存在的人生之旅,不也是一个“有选择改造自己的本质”,确立主体地位和价值的故事吗?这样充满坎坷的人生历程以及从中领略到的深入骨髓的人生感悟,是不可能不渗透进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中的。《丑小鸭》、《坚定的锡兵》是这样,《野天鹅》、《海的女儿》、《拇指姑娘》也是这样,命定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出身,但忠于自我感觉、重新进行自我选择,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的自由却不是命定的。巴赫金在谈到作家主体意识的时候曾说:“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构成自我意识的一些最重要的行动,都同他人的意识(同你)相关联。”[9](P377)主体人格投射其中的形象塑造,是一定具备主体性探寻和确立的内涵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些形象在追寻主体性的过程中,其中所彰显出来的至真、至善和至美,最终使她们成为一种超越性别存在的“天使”。
三、关于“双性同体”
这样看来,小人鱼、艾丽莎、拇指姑娘的故事不仅仅是在书写柔弱女性作为主体对命运的抗争,更是安徒生对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的高度赞誉。叶君健先生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的序言中说:“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和《拇指姑娘》中的拇指姑娘,包括‘海的女儿’,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都是他理想中‘人’的缩影。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一定能走向光明,创造出美好的生活。”[10](P2)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安徒生把对“人”这一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讴歌与赞颂,毫不悭吝地施与了女性。
其实不必过分敏感愤激地看待男性文本对女性的刻画,男性文本中不一定蕴含着歧视女性的父权意识。激烈的女权思想、愤激的性别立场很可能会导致对文学作品的误读。英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一个纯的男性头脑不能进行创造,正如一个纯女性的头脑不能进行创造一样”。自然界要求阴阳相互调和,合而为一。这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的结合,它孕育出世界上最神秘的奇迹——生命;一部分是头脑的结合,它创造出最完整的生命——艺术家。如同人的身体上存在两种性别一样,人的大脑和心灵也存在着两种气质,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两种气质只有相互作用才能达到创作的顶峰。她断言,双性同体是进行艺术创作的最佳心灵状态,伟大的头脑都是双性同体的。这一观点化解了极端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文本的抨击,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提供了启发。
从《小伊达的花》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的童话创作的美学风格经历了较大的嬗变,他自己将后者称为“新童话”,意即在这类童话中有了更多的现实生活的色彩,幻想的成分有所减弱。然而,无论是“小伊达”还是“小女孩”,这些可爱的“天使”的身上都倾注着安徒生无与伦比的温情与爱。面对鲜花的衰败与凋残,一个大学生对小伊达解释说:“这些花儿昨夜都去参加舞会了。因此它们今天就把头垂下来了。”而且作者让这种解释真的成为现实,小伊达真的看到了花儿跳舞的奇异情景。虽然最终,小伊达为花儿们举行了美丽的葬礼,但她的心境已非开始时的灰暗迷茫。那个蜷缩在墙角的卖火柴小女孩的命运之所以叩击着这个世界上每一颗善感的心灵,是因为安徒生以最深切真挚的同情为她勾画了一个火柴光中转瞬即逝的美好世界,她的愿望是那么简单质朴,又是那么美丽动人。这是一个有着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感的作家对儿童、对生存于底层人民所给予的最大的慰藉。是的,即使是这样美好的“天使”最终也只能在圣诞前夜冻饿至死,我们可以想象安徒生痛心到何种程度!
刘绪源先生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曾将安徒生的这类童话归入现代“母爱”型的母题(《卖火柴的小女孩》已具备了“父爱型”直面现实的特征),这一别致的理论划分并不涉及性别,但母爱和父爱毕竟是成人给予儿童的两种不同的情感。母爱更加细腻、温柔,父爱更加冷峻、严厉。处于古典的牧歌时代的安徒生给予儿童的更多的是这种母爱式的关怀,它们有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童读者的心灵。有人曾将安徒生童话的创作风格概括为柔美、阴柔等更具女性气质的特征,甚至有人认为安徒生的性格中就包含有女性的特质。这些当然不足以证明安徒生拥有“双性同体”的大脑,但这位仿佛是上帝专门为童话而创造的作家的确表现了不同于常人的才情和心性。
丹麦的詹斯·安徒生的《安徒生传》第四章“我唯一的错误就是爱情”有一节“一个雌雄同体的人”,介绍了安徒生创作于1833年的戏剧作品《阿格尼特和人鱼》,在这部改编自丹麦民间传说的戏剧作品中,倾注了安徒生强烈的创作热情,当时很多论者都认为阿格尼特就是安徒生自己的化身。这位“雌雄同体”的人,“她的情感中同时包含着两种性别的因素”,她“所追求的并不是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发现的东西。不满足于现状,对未知事物的追求”。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安徒生“为我们指明了另一种了解男人和女人双性本质的途径”[11](P96),也向世人描绘了他自己痛苦的灵魂和锲而不舍的追求。早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就存在着所谓的“神圣原始人”,而在浪漫主义时代“雌雄同体”更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隐喻,它表达了那个时代万事万物融会贯通、走向和谐的精神信仰。正如很多作家在自己的笔下描绘了这种“所有不同或相反的特性最终都融合在同一个象征着纯洁的人物”,现实生活中的安徒生本人就是这样的人。安徒生既属于那个时代,也超越了那个时代。这样一位用生命写作、将自我的真实更多地投射于创作中的作家,是完全能够突破性别的界限而写出“人类之歌”的。
我们无意于更多地去论证作家的“双性同体”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但“安徒生”与“童话”这两个名称的深刻契合又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思考与遐想。其实,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两块人类精神漫游的历史图表中,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必然都会渗透其间,这二者应该是平等的,代表着人类文化的不同侧面,给文学以不同程度的滋养。吴其南教授认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应从这两方面汲取有益的内容。“爱”、“美”与“柔”并不必然导向软、弱的审美态度——真正的爱是奉献,是一种能力、一种艺术,是真正有力量的表现[12](P16)。这可能是我们理解安徒生笔下的天使形象的真正态度。
[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浩.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安徒生童话——试析《海的女儿》和《野天鹅》[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11).
[3]吴其南,吴翔之.新编儿童文学教学参考资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4](丹麦)安徒生著.安徒生童话[M].石琴娥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5]韦苇.外国童话史[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
[6]陈丹.《海的女儿》的女性主义批评[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9).
[7]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J].文艺研究,1998,(1).
[8]石琴娥.北欧文学史[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9](苏)巴赫金著.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0]叶君健.《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序言[A].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2)[C].太原:希望出版社,2009.
[11](丹麦)詹斯·安徒生著.安徒生传[M].陈雪松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12]吴其南.论儿童文学对女性文化的认同与疏离[A].陈莉.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M].郑州:海燕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张 伟〕
Viewing the “Angels” in Andersen’s Fairy Tales through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WANG M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There are a lot of “Aphasia” women and female “angels” in Andersen’s fairy tales, and thus some commentators think these works reflecting the distinct male chauvinism. In fact, Andersen’s fairy tales is the song of “humans” endorsing for the women, writing the fight of female, which has the “androgyny” creative thought.
Feminism; Andersen’s fairy tales; Angel
2014-07-02
王敏(1971-),女,内蒙古包头人,硕士,包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儿童文学研究。
I106.4
A
1004-1869(2015)0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