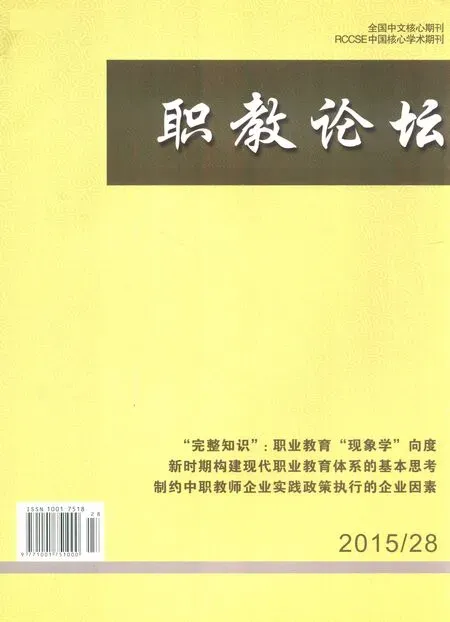高职院校章程下的学术权力与学术事务研究
2015-01-31傅新民谈应国罗政华
□傅新民 谈应国 罗政华
高职院校章程下的学术权力与学术事务研究
□傅新民谈应国罗政华
我们将学术权力界定为高校学术组织对学术事务和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作出决策、审定、审议和咨询的权力。高职院校存在三种学术事务,即纯学术事务、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和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对三种学术事务行使学术权力时,宜采取与之对应的方式:纯学术事务须由学术组织决策或审定,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须经学术组织审议,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须向学术组织咨询。
学术权力;学术事务;学术组织;章程制订;高职院校
一、高职院校亟待彰显学术权力
在本科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意识。学术权利意识即教师个体认识到,高校教师享有自由研究的权利、表达思想的权利、发展学科维护专业声誉的权利、选择教学方式方法的权利以及评价学生的权利等;学术权力意识即高校教师个体和群体认识到,高校学术组织及其成员享有的关于学术的权力。虽说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行使与落实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若连这种意识都不具备或这种意识过弱,纵使有好的学校内外部条件也无法有效地行使与落实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
高校的每位教师都享有学术权利,但学术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学术组织及其成员实现的。高校学术组织包括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依据相关的规则,经过一定的程序在教师中遴选出来的。这意味着学术权力并不像学术权利一样是每个教师都行使的,学术权力的行使者是教师群体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教师学术权利的享有程度有赖于学术组织行使学术权力的状况。出于此种考虑,本文侧重讨论学术权力。
我们注意到,相较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学术权力意识较淡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学术水平较低,不配行使学术权力
据教育部网站的教育统计数据,2009~2013年全国高职院校数分别为1215、1246、1280、1297和1321所,年增长率分别为2.88%、2.73%、1.33%和1.85%。由此可见,近几年高职院校的年增长率小。这意味着高职院校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期,本世纪初期的一窝蜂式的中职升高职“盛况”已经成为历史。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高职院校高校身份的自我认同得以完成(自我认同较外界的认可或许更为艰难),高校三大职能已深入人心,三大职能之一的科学研究已经受到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仍然处于较低层次。高校学术权力的行使与学术权力主体的意识和教师的学术水平密切相关。当教师学术水平较低时,首先可能导致教师行使学术权力的信心不足;其次教师会认识到,学术水平低可能致使对学术事务的分析欠深刻、判断欠准确,从而不热心或不主动行使本该享有的学术权力。这无疑会降低学术权力的权威性,而缺乏权威性的学术权力,其效用也会大打折扣。
(二)教授比例偏小,难以用好学术权力
一般而言,在高校教师群体中,教授的学术水平高于其他教师,教授能够更好地行使学术权力。也许正基于此,高校学术组织成员一般从教授中遴选。而这样遴选的前提是教授占教师的比例较大,且各个学科、专业的教授分布较合理。但现实情况是高职院校中教授比例偏小,不少高职院校就是几个至多十几个教授,并且有些专业一个教授也没有。以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现有在职教授30人,占教师总数的5.1%,其中大部分在医学系、护理系、药学系,而土建系、汽车工程系、机电系、经管系等一个都没有。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不少高职院校的学术组织哪怕全部教授作为成员,也可能充实不了各个学术组织。更何况在教授分布不尽人意的情况下,不可能只是教授作为学术组织的成员。对大多数高职院校来说,现实的选择是在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教师中遴选。但是,当学术组织中教授人数偏少时可能会导致以下不足:一是降低学术组织行使学术权力的整体水平;二是副教授或其他职称教师由于晋升职称等切身利益的考虑,在进行学术决断时相较于教授更易受到个人功利因素的干扰。
(三)行政权力强势,无心行使学术权力
高校的权力结构是二元权力结构,主要包括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1]。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只有相对独立和相互支撑,才能更好地承担高校的学术管理责任。而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二者的关系失衡,高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2]。几乎所有高校里行政权力都处于强势地位,学术权力往往被行政权力控制或渗透。这种情况,在高职院校表现得更为突出。
高水平大学里,学术组织不乏学科尖人和学术权威,他们有底气抵御非学术因素的干预,强力发出作为学术人员的声音。但在高职院校,这类顶尖人物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所以,虽说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都面对行政权力的强势,但高职院校学术组织的话语权更为薄弱,所起的作用更为有限。甚至有些高职院校的学术组织形同虚设——要么有名无实,基本上不行使学术权力;要么按照党政领导的意图进行所谓的学术决策。当学术权力经常性地被轻视、被漠视和被忽悠时,学术组织的纯学术成员只有两种选择:退出学术组织,或者习惯于被忽悠的权力,视权力为儿戏。这两种选择引起的结果是一样的,即学术人员无意无心行使学术权力。
二、学术权力的内涵
中国高校的现代大学意识“先天不足”。最早一批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等,是晚清政府在西学东渐和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为了救亡图存和维护统治而采取的经世致用的救国之举[3]。可以说中国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政府的控制之中,并且这种治理方式一直沿袭下来。这导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基本上只存在于理念层面,学术难以独善其身。
论及学术权力,一般会提到约翰·范德格拉夫等人所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一书。该书所讨论的学术权力,是指从高等教育管理系统的最上层——国家到最基层——教师等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所享有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力[4]。此种宽泛意义下的学术权力包含“为了学术的权力”和“学术本身的权力”。范氏这种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的学术权力观,或许为“先天不足”的中国高校强化行政权力轻视学术提供了借口。这是我们认为范氏的观点不适合我国高校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中国一直以来浓厚的“皇权”意识,导致民主、法治、公民权利等现代观念的缺乏。这种社会文化自然会影响到高校,有碍现代大学理念的彰显。对于范氏《学术权力》一书的受众来说,读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身的兴趣、知识结构、阅历经验、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等选择性接受书中的内容和观点。对于高等教育及高校的管理者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有助于行政管理的内容和观点。若如此,则不利于高校去行政化。
张楚廷教授认为:学术权力是指关于学术的真伪判断、水平判断、意义判断的学术性决断权[5]。这是我们赞成的观点。但结合2011年11月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来看,张教授学术权力的观点没有完全涵盖“学术咨询”。若章程制定或者实际处理学术事务时囿于张教授的观点,高校学术事务的处理就可能会存在遗漏。
关于学术权力的一种狭义理解则是指学术人员基于专业特长和学术能力所拥有的权威力和影响力[6]。在通常语境下,“权威力、影响力”指非权力性权威力和影响力。这种权力是由个人的学识、人品、成就等因素联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不是组织赋予或大众推举和选举的。因而这种权力不具备强制性。从社会组织的运行来说,非权力性权威力和影响力的作用有限。哪怕是权威人士的个人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其影响,往往是相关者、志趣相近者容易受到影响,对其他人也许没有影响或影响极小。而社会组织机构中特定职位的权力,其行使则牵涉到所涉范围内的所有人。所以,这种对学术权力的狭义理解对建设符合现代大学理念的高校缺乏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法》和《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从实施和操作的角度对学术组织与学术权力作出了规定和说明。《高等教育法》第42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11条要求高校明确“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以及其他学术组织的组成原则、负责人产生机制、运行规则与监督机制,保障学术组织在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学科研计划方案制定、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咨询、审议、决策作用,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前者将学术组织的权力落脚到“审议”和“评定”,后者落脚到“咨询”、“审议”和“决策”。基于此,我们将学术权力界定为高校学术组织对学术事务和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作出决策、审定、审议和咨询的权力。
三、高职院校学术事务的划分
不少高校行政权力不仅行使了本该行使的权力,而且越俎代庖地行使了本该由学术权力行使的权力。两种权力应该各行其是不越位、不错位,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让两种权力处于各司其职、协调运行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学校事务可分为三种:纯学术事务、纯行政事务和交叉性事务。交叉性事务又可分为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和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根据本文学术权力的界定和此处学校事务的划分,学术事务包括纯学术事务、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和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
对于这三种学术事务,其中的纯学术事务和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差异明显,在行使学术权力的方式上,一般不会混淆。但是,对纯学术事务和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以及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和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两两之间可能不易泾渭分明。这既与事务的性质有关,也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行使主体(组织、组织代表)的观念和态度等有关。对三种学术事务行使学术权力时,宜采取与之对应的方式。行使学术权力时,首先要弄清楚三种学术事务具体包括哪些事项。以下是结合我校章程制订,对高职院校三种学术事务进行分类归纳。
(一)纯学术事务——须由学术组织决策或审定
从权力行使的主体来说,只有具有学术底蕴、学术素养或者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教师群体,才有可能对事务所含学术内容做出真伪、水平、意义的恰如其分的判断。学术组织对纯学术事务作出决策、审定具有终极性,包括学校党委、行政在内的任何组织对其没有否决权。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院系按决定执行。
1.各种学术组织的规程、章程。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规程、章程等,由相应学术组织日常办事机构或秘书处拟订,相应学术组织或者学校最高学术组织——学术委员会审定。
2.各类学术、科研基金以及科研项目和教学、科研奖项的设立。既可以由学术组织自主设立,也可以就学校行政提议设立的奖项交由学术组织作出同意或不同意设立的决断。
3.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对外推荐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奖。学校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和对外推荐教学、科研成果奖分别由教学管理机构和科研管理机构组织,但需将评奖材料送交学术组织。学校教学、科研成果奖由学术组织评定成果等级;对外推荐教学、科研成果奖由学术组织审定。
4.专业设置及调整。新设专业及专业方向的调整由院系提交论证材料,由学术组织作出决定。已开办专业的退出,或由院系提交相关材料,或由学校教学管理机构按照专业退出机制提交相关材料,由学术组织决策。
5.校级课题和纵向课题的推荐。二者均属科研管理工作,即由科研管理机构将评审材料送交学术组织,由其作出等级或水平的评定。
6.教师职称评定或教师职称申报推荐。教师职称评定或申报推荐由人事管理机构组织,经过初审的职称评定或推荐申报材料送交学术组织,由其作出评定或申报推荐的结论。
7.学校优秀科研工作者评选,国家、省、市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师的推荐。学校优秀科研工作者评选和国家、省、市教学名师及优秀教师推荐,分别由科研管理机构和教学管理机构组织,评审材料送交学术组织,由其作出评审结论。
8.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学术纠纷的裁决。学校学术组织根据校内外有关部门、个人的要求或请求,对涉及到学校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纠纷进行调查,并作出裁决。
9.教学事故仲裁。对教学事故处理认为失当的教师,可以向学校学术组织提请申诉,由其作出仲裁。
10.其他需要学术组织决策或审定的学术事务。
(二)涉及行政的学术事务——须经学术组织审议
属于学术事务,但最终的决策权在学校学术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如党委、校长办公会议。这种学术事务虽然最终的决策权不在学术组织,但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一环是通过学术组织的审议。只有通过了学术组织审议的,才能进入到最后的决策程序。并且最终的决策应该以民主表决方式进行。
1.专业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由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如发展规划处、人事处)单独或会同院系制订这些规划,交由学术组织审议。
2.课程建设。教学管理机构会同院系从事课程建设工作,其重要文本交由学术组织审议。
3.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各院系制订、教学管理机构汇总。由教学管理机构将各个方案交由学术组织审议。
4.科研规划和教学及科研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由教学管理机构制订,科研规划和科研管理制度由科研管理机构制订,交由学术组织审议。
5.教师职称评定及职务聘任的标准与办法,教师职务的聘任。教师职称评定、教师职务聘任的标准与办法由人事管理机构拟订,交由学术组织审议。教师职务由人事管理机构会同院系聘任,交由学术组织审议。
6.优秀教师评选。学校优秀教师评选由教学管理机构组织,评选材料送交学术组织,由其作出审议结论。
7.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判断。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含新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录用、调入和杰出人才的引进等。这类事项由人事管理机构会同院系或有关机构完成,但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由学术组织作出判断。
8.学校认为需要提交学术组织审议的其他事项。
(三)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须向学术组织咨询
行政权力的运用要围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和充分运用[7]。这意味着正常状况下,学校的行政事务都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地与学术关联。但对学校的行政事务仍可做相对的划分:与学术无直接关联的纯行政事务,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依本文的界定,直接涉及学术的行政事务属于学术事务。此事务在决策之前,有关行政组织听取学术人员意见或学术组织为其提供咨询,能够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乃至于避免决策失误。为了确实发挥咨询的作用,对于学术组织提供的咨询意见,决策者应将采信情况及时反馈给学术组织。
1.涉及学术事务的学校重大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由学校有关管理机构(如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制订,送交学术组织咨询。
2.学校预算中教学、科研经费的安排和使用。由学校财务管理机构编制的预算方案中教学、科研经费的安排和预算执行情况,须得征询学术组织的意见。
3.重点建设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由学校有关管理机构(如发展规划处)单独或会同院系撰写申报材料,送交学术组织咨询;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告知学术组织,并收集反馈意见。
4.合作办学和重大项目合作。学校的合作办学和重大项目合作事宜(如合作对象、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征询学术组织意见。
5.校企合作机构管理办法、章程等。校企合作委员会等校企合作机构制订的管理办法、章程等送交学术组织咨询。
6.学校认为需要听取学术组织意见的其他事项。
[1]刘献君.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2(2):31-34.
[2]罗仲尤.大学学术权力的式微与张扬[J].大学教育科学,2014(3):37-42.
[3]张雪蓉,马渭源.中国教育十二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75.
[4]别敦荣.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44-47.
[5]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165.
[6]寇东亮.学术权力:中国语义、价值根据与实现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06(12):16-21.
[7]刘献君.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2(3):1-10.
责任编辑宋庆梅
傅新民(1962-),男,湖南津市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教授、所长,湖南省教育科学校企合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谈应国(1965-),男,湖南常德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罗政华(1964-),男,湖南安乡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专项课题“湖南省其他地区与长株潭地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比较研究”(编号:XJK014BJD034),主持人:傅新民。
G710
A
1001-7518(2015)28-00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