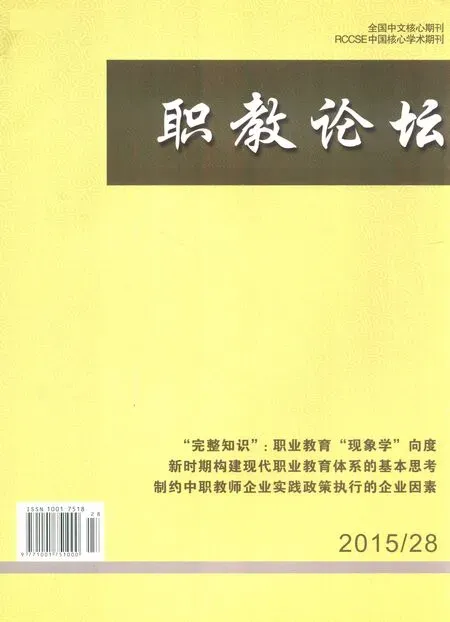“完整知识”:职业教育“现象学”向度
2015-01-31路宝利
□路宝利
“完整知识”:职业教育“现象学”向度
□路宝利
近代以降,“表征主义认识论”使原本完整一体的知识于“知性”与“物性”、“命题之知”与“能力之知”、“明言知识”与“默会知识”等多个维度上发生分离。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教育世界所传播的仅是知识的“一半”或言“半体知识”而已。20世纪中期以后,认识论革命尤其是职业教育对于“完整知识”的诉求,终使“表征主义认识论”走向瓦解,并逐步转向知识“现象学”。该背景之下,“现象学”知识即由范例、行动、叙事、情境所承载的“完整知识”在教育教学中逐一得以凸显,并将主导职业教育领域具有“现象学”旨趣的课程与教学变革。
完整课程;完整知识;职业教育;现象学
基于知识“不完整”、组织“不完整”与取向“不完整”等课程之弊,笔者在《完整课程:职业教育课程方向》一文中,提出“完整课程”概念。“完整课程”需“完整知识”,但是,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学校教育几乎一直在传播知识的“一半”或言“半体知识”,另“一半”更多在课程之外,或嵌入行动之中,或含于器物之内以“隐性”方式持存。究其原因,在认识论层面,近代以来“表征主义”霸权是为根本。基于“完整课程”之“完整知识”诉求,职业教育知识论须完成“现象学”转向。
一、“半体知识”问题
“半体知识”是一种比较形象的界说,实质上,即“整体知识”在不同维度上所遭致的“碎片化”。其中,主要包括“知性与物性、命题之知与能力之知、明言知识与缄默知识、垂直话语与水平话语”四种分离。
(一)“知性”与“物性”分离
人类童年时期,教育寓于生产生活的母体之中,以“符号”呈现的“知识”尚未从世界整体之中被剥离开来。伴随人的“抽象”能力不断提升,“知性”与“物性”遂发生分离。“知性”,德文原文Verstand。柏拉图视之为与“科学”相对应的一种心理状态;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被动理性”,与感性材料关联,居于“主动理性”之下;康德则将其看做“对感性材料进行思维”。[1]由此看来,尽管与“理性”有别,或言其“高级”程度逊于“理性”,但是,诚如黑格尔所概括的,“知性”已然显示出抽象性、普遍性、分离性等特征。
直白地讲,“知性”与事物之“物性”或器物本身基本分离。并且,“知性”部分逐一被置于学校教育的“象牙塔”内,命题以及承载它的教科书成为“知性”的象征符号与象征物。与之比较,“物性”部分失去了进入学校教育体制的“合法性”,只得在“工作坊”中保持“物性”之传递。与器物浑然一体的“完整知识”被“肢解”。试想,无论是学生或是学徒,习得“半体知识”自然难以整体把握认识对象,学生习得“知性”,多擅“玄谈清议”,但迁移并还原至具体事物之中时却手足无措;学徒整天与器物相伴,虽可胜任一般既定任务,却难以抽象其中之“义理”。就“完整知识”而言,“知性”与“物性”缺一不可,彼此“关照”是为方向。
针对技术教育中惯常的“物性”缺失,拜尔德在诠释“物性论”时指出:“加工实物是工具发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纸上设计并不是整个历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物体不是思想。如果我们不在头脑中公正的保持物体的物性,那么我们将误解技术……事实上,我们未能完整的描绘技术;有时,把手放在物体上,是非常激动人心的。”[2]现实情况是,以头脑关注“知性”之时,以身体感知“物性”依然被疏略。
(二)“命题之知”与“能力之知”分离
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在感受理性力量之时,科学的世纪随之而至,培根“知识即力量”的宣言是对于这个时代最好的诠释,可问题在于,培根之语被教育界“转译”之后便成了“知识即能力”,或言“知识可以转化为能力”的命题。“知识—能力”这对范畴之间的“线性”关系似乎已经明了,但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的“差异”却被疏略,教育史上由此进入“知识主宰”的时代。赫尔巴特“主知主义”与斯宾塞“科学主义”教育流派堪称代表,又加之“官能心理学”的潜在影响,至今,“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霸权”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扭转。事实上,知识以“命题形式”出现已有久远的历史,但以“命题之知”(KnowingThat)相称谓,并与“能力之知”(KnowingHow)并置则是20世纪哲学界热辩的结果。
20世纪中期,教育界关于“知识—能力”关系问题进入哲学家的视域。1946年,针对“理智主义”者沿袭培根以来的路线,即将KnowingHow最终归结为KnowingThat,或言将“能力”归结为“命题”的论断,赖尔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上发表题为“KnowingHowandKnowingThat”论文,提出“反理智主义”观点,指出二者有“种差”之别,并明确KnowingHow的优先地位,“一个科学家首先是一个KnowingHow,其次才是一个 KnowingThat。除非他知道如何,他不会发现任何特定的真理。”[3]可惜之处在于,赖尔“反理智主义”观点并未被职业教育界所捕捉,因此,尽管倡导能力本位课程理念已久,在哲学高度上,却尚无KnowingHow与KnowingThat之间关系的自觉意识,表层性理解自然无法解决二者分离之状。
(三)“明言知识”与“缄默知识”分离
理智主义者过度崇尚的知识局限于 “可以言说”的部分,事实上,直到胡塞尔“现象学”诞生之前,不可言说的部分一直搁置于学界以外。包括中国,孟子虽有“可授之以规矩,不能授之于巧”的论述,且孟子之后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流传,但在学理上于中国本土一直未被深度阐释。20世纪中期,继承胡塞尔得意门生海德格尔的认识论路线,波兰尼成为默会知识最有影响的诠释者。1958年,波兰尼在《人的研究》一书中,将知识划分为两类,其中,以口头、书面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达的为明言知识,而不能以如此方式系统表述的为缄默知识,或称默会知识。[4]针对非“命题”所能尽的默会知识,波兰尼尤其探究了其“前语言”机理,并构建出“From-To”默会认知图式。其中,“所有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的论断则明确了默会知识的位置。[5]
就职业教育而言,缄默知识尤为重要。与学术教育不同,职业教育强调完成工作的胜任力,是一门“做”的学问。无论是判断力、理解力还是经验、技能、诀窍等皆蕴含着极丰富的默会元素。事实上,工匠解决问题往往不是依靠命题、公式,在敲打机器的叮当声中,在对于火焰的观察中“答案”已经了然于胸了。由于缄默知识一般内化于“行动”之中,所以学校本位职业教育更多关注了知识的明言部分。20世纪中期以来,在职业教育界,伴随“学科型”课程招致批判,俄罗斯制、MES、CBE等诸多西方课程模式逐一登陆中国,并且皆强调“做”中学,并试图构建“理实一体化”课程,但却只关注“实践—技能”这对范畴之间的“线性”关系,换句话说,只是强调通过“实践”掌握“技能”而已,并未体认到胡塞尔以来哲学认识论层面“明言知识—缄默知识”之间的关系机理,尤其是,通过“做”最终掌握明言知识的“价值取向”并未改变,本来居于优先位置、占有更多比例、且对职业教育意义更大的缄默知识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
(四)“垂直话语”与“水平话语”分离
如果说,知性与物性、命题之知与能力之知、明言知识与缄默知识这三对范畴更多是依据表达形式而划分的,在组织或体系层面,还有“垂直话语”和“水平话语”之分。这一对概念由英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首先提出。做为一名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发现人类所使用的话语并非完全一致,遂将其划分为两类,即“垂直话语”(Vertical discourse)与“水平话语”(Horizontaldiscourse),“垂直话语”主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具有专门性与象征性特征,彼此联系并构建为学科体系或跨学科体系。与之不同,“水平话语”即日常生活知识,局部、零碎且有赖于语境变化是其特点,并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话语的参与者及其习性。[6]显然,学校教育更多是在传授“垂直话语”体系,而缝纫知识、烹饪知识等被伯恩斯坦视为“水平话语”的体系似乎是学校以外的事情。
“垂直话语”与“水平话语”分离对职业教育影响颇大。与哲学研究不同,如第欧根尼、泰勒斯等哲人圣贤离群索居甚至隐于“洞穴”之中即可独自漫天玄想,但职业能力培养需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即在“烹饪中学习烹饪”,在“建筑中学会建筑”,如此等等。与学术教育也不相同,依据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学说”,人类甚至依照逻辑推理即可产生新知识。以数学为例,自魏尔施特拉斯以来,尤其是希尔伯特开始使用“公理系统”、罗素建立“纯粹数学”公式之后,数学逐步走向“抽象”王国的极限水平,似乎真正到了“只问知识,不问世界”的状态。与之比较,如果没有与之对接的产业,没有“校企合作”制度,没有“工学结合”机制,没有“理实一体”课程等支撑“水平话语”的元素,仅在课堂之上进行学科知识即“垂直话语”体系传授,职业教育是断然不能完成的。现实是,“垂直话语”一直被高度重视,对于“水平话语”则缺乏自觉的研究意识,也自然未有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影响职业教育课程的变革。
二、从“表征主义”到知识“现象学”
追根溯源,在认识论层面,“表征主义”成为导致“完整知识”分离的核心因素。尽管“半体知识”或言“碎片知识”对于职业教育影响甚大,但职业教育本身并未参与到批判“表征主义”之列,不过其对于“完整知识”的诉求使学界无法漠视来自哲学界的批判,这自然迎来了职业教育“现象学”转向之机会。
(一)“表征主义”批判
自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之后,发端于笛卡尔、中间经洛克和康德并延续至20世纪的传统认识论招致前所未有的批判,批判的焦点之一即近代认识论的“表征主义”特征(representationalism)。随着“认识论危机”、“认识论破产”甚至“认识论之死”的论说出现,一时间,认识论成了第一哲学。[7]顾名思义,表征主义,即知识的本质是内在心灵对外部对象的表征。事实上,这一命题涵盖着两层涵义:其一,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其二,知识可以在人心灵中成为主观映像,或言通过理性被表征。关键在于,“表征主义”最终成为科学实证主义甚至是科学归纳法的哲学基石。通过现象追逐事物背后的本质是为根本任务,迁移至教育领域,抽象的知识“符号”及由其所构建的体系甚至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罗蒂之前,尽管对于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认识论不时有批判之声,但哲学界之外,各界对于“表征主义”的批判相对表层,如对学科知识、记忆价值等不同维度的质疑,至多是在游走于知性与物性、命题与能力等范畴之间时有所感悟而已。最终使“表征主义”走向瓦解的批判还是来自哲学界。表征主义的致命弱点有两处:其一,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消解。诚如泰勒所批判的,表征主义致使主体与客体相分离、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罗蒂则认为,表征主义混淆了因果说明和辩护。[8]尤其是,做为一种客观主义,“表征主义”扭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使人“淡出、退隐”,从而使之成了如波普所言的“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9]其二,知识的“整体性”被消解。在“表征主义”看来,命题才有知识意义,而抽象出命题的“原初事物”是粗糙的,从而走向“单薄的认识论”。艾伦拒斥了这种片面知识观,提出知识基本单位不是命题,而是一个复杂的“人化物”,在艾伦看来,“一座桥梁和一个科学命题一样,都是知识的实例。”[10]
(二)“完整知识”诉求
针对“知识分离”现象的批判并非是一件新鲜事,事实上,文艺复兴之后、杜威之前教育界已经开始觉醒,不过,该历史时期只是完成了课程层面即“古典课程”与“实科课程”的融合而已。英国教育家洛克与弥尔顿堪称先行者。在《论教育》一书中,针对于拉丁语、经院主义哲学等学科的空疏无用,弥尔顿甚至提出将“猎人、园丁、药剂师、工程师、水手”等实用人才与实用课程引进学园以改造现有教育的观点。[11]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洛克则提出既有学问又具备实际才干的“新绅士”的教育目标,以及与之相宜的实科课程。[12]可惜的是,欧洲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教育设想被英国清教徒在北美殖民地抢先实现,弥尔顿《论教育》出版20年后,基于“文法中学”脱离现实世界的批判,视弥尔顿为导师的富兰克林最终在美国创立了 “文实中学”,“古典课程”与“实科课程”趋向融合。
事实上,在“文实中学”,实科课程只是赢得了与古典课程并置的权力而已,“知识分离”问题并未被时人所意识到。在教育史上,批评知识“碎片化”并蕴涵“完整知识”取向者,当属杜威。针对“单门”课程对于“完整”生活的割裂,杜威敏锐地发现:“世界是整体的,而每门课程只是把积聚的知识片段教给学生。”[13]遂提出“主动作业”概念和“做中学”思想,从而为知识整合提供了框架。并且,早在赖尔之前,杜威即已触及KnowingThat与KnowingHow的关系问题,并对KnowingHow以充分地肯定,即“人们最初的知识,即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如怎样走路、怎样说话……怎样操作机械……。如果承认教材自然的发展进程,就总是从包含着‘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14]由此,动摇了笛卡尔以来的教育“二元论”思想,并且,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杜威教育“一元论”思想,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普职一体化”的进程。
可惜的是,普通教育在吸收职业教育元素之时,职业教育并未完全“朝向杜威的理想”。[15]如构建职业教育体系之时依然以普通教育为参照,沿袭教育“二元论”轨道的迹象明显,值得庆幸的是,在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变革中,透视出趋向“完整知识”的过程。例如,与学科课程比较,CBE即能力本位课程,使“能力之知”得以弥补,但在职业能力进行分解之时,无法“明言”的“缄默成分”多被遗漏,这也是该课程模式一直被学界诟病之所在。与之比较,MES课程也有类似之弊,德国学习领域课程则没有对职业能力按照“知识、技能、态度”逻辑进行分解,而是依据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围绕“典型工作任务”,构建了包括对象、工具、方法等核心工作要素的“行动领域”,并以此为基点向教学领域转化。自然,在此“工作系统化课程”框架中,“知识分离”问题得以有效的规避。
不过,“规避”不等于“解决”,德国学习领域课程并不是课程模式的终止,“知性与物性”一体、“命题之知与能力之知”一体、“明言知识与缄默知识”一体、“垂直话语与水平话语”一体的“完整知识”在当下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中并未完满地实现,“完整知识”诉求终使知识“表征主义”转向知识“现象学”,“现象学”知识则由此诞生。
(三)知识“现象学”与“现象学”知识
在传统认识论范畴中,“主体—客体”即认识者与对象之间关系明确,通过科学归纳法等工具手段,认识主体最终揭示客体或言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为目标。但“表征主义”最终导致传统认识论走向“没有主体的认识论”和“单薄的认识论”。与之比较,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无疑是一场革命。顾名思义,与追求现象背后本质的“表征主义”比较,胡塞尔提出“现象即本质”的论断,并由此提出“现象学还原”、“回到生活本身”等命题组成的方法论体系。做为胡塞尔的得意门生,海德格尔则提出 “在世(beingin-the-world)”的概念,首先瓦解了“表征主义”。波兰尼继承了海德格尔“在世”概念,提出“通过寓居而认知”的著名论断,“所有理解都以我们寓居于自己所把握的对象的细节之中为基础。这种寓居就是我们介入到我们所把握的对象的存在之中,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16]事实上,从海德格尔到波兰尼,通过“心灵寓居于身体之中”最终确立了身体的优先位置。“没有主体的认识论”已经在“现象学”中不复存在。可贵之处在于,波兰尼没有就此停止探索的脚步,与“明言知识”比较具有优先位置的“缄默知识”在波兰尼时代得到全面地诠释。可以说,海德格尔、波兰尼知识“现象学”诞生之后,“现象学”知识即“完整知识”带给学界一种新的知识观,这恰恰对于职业教育尤其重要。
“现象学”知识之所以对职业教育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具备“亲知”与“完整知识”两大属性。首先,“现象学”知识属于“亲知”范畴。亲知即第一手的知识,它要求与所知对象有亲密的接触(rapportwith theknown),直接性是亲知的基本特征。在此,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完全被消解,彼此之间转化为“沉浸、平等、关照、对话”的共同体。作为波兰尼的诠释者,凯农捕捉到“寓居”与“亲知”的关系,即“亲知是第一手的熟悉,具身性的寓居,它不能通过第二手的方式获得……以第二手的方式获得的东西,是表征性知识。”[17]在与摹状知识比较中,罗素阐述了亲知基本特征,即主体直接性参与。“现象学”知识作为“亲知”的意义在于,本身已有“能力之知”的成分在其中了,其与职业教育关系不言自明。再有,“现象学”知识即“完整知识”。在知识维度,“现象学”核心命题“现象即本质”至少有三层涵义:其一,与抽象的“符号”不同,现象即当下一个鲜活的、富含信息的“具象”,而“从现象直观本质”的方法可以翻译为“本质”通过独特的“具象”表达,并且,水平话语与垂直话语俱在;其二,现象包含器物本身,自然“物性”居于其中,通过“物性”反映“知性”是对“现象即本质”又一理解;其三,与明言知识不同,“现象学”知识包括缄默知识在内的更丰富的元素,正如具有阐释意义的文本一样,个中深意不是几个抽象的“命题”可以囊括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于“现象学”知识的“亲知”与“完整知识”属性,须有与命题性知识有别的存有与组织方式。其中,与之适切的课程与教学形式是关键所在。
三、“完整知识”存在与组织形式——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视角
提出“现象学”知识或言“完整知识”概念,旨在诠释知识固有之状,而并非是一种新型知识,“半体知识”则是其“碎片化”的结果。描述绝对的“完整知识”是有难度的,但与之接近的知识形式早已为人所熟知,只是由于职业教育界“现象学”意识一度缺失,诸如范例、行动、叙事和情境等等,只得一直处于课程体系的边缘而已。事实上,它们既为“完整知识”提供了框架,同时也是“完整知识”本身。
(一)范例
与规则、原理比较,在以往的教育教学中,范例一般是做为辅助工具而出现的,只是在命题繁难晦涩之时假以说明而已。如此,便消解了范例做为“完整知识”的现象学意味。事实上,范例业已嵌入“明言知识”元素,否则通过范例不会明了原理,可贵之处在于其同时涵盖无法言明的“模糊规则”,这即是言理“意犹未尽”之时,往往“举例说明”之故。与抽象、干瘪的“符号”、“命题”比较,尤其反映“现象学”特征的是,范例是“有血有肉”的知识体。试举一例,如“细胞结构”这一知识点,如果只是熟知到其由“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与细胞核”四部分组成的水平,则意义不大,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也往往无法辨认具体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不同门属的真实细胞。换句话说,不同门属的细胞各异,彼此蕴涵着各自不同且丰富的信息,即使同一细胞因视角或主体不同则观察结果必不相同,绝不是“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与细胞核”这些单薄语词所能囊括的,而这恰恰是“现象学”知识所具备的,即可揭示出“知性”,又可触摸到“物性”,即可体悟“抽象”,又可感知“具象”,如此等等。
在一定意义上,知识观决定课程与教学观。事实上,哲学界早已探清范例之学理。例如,为了避免明言知识、垂直话语的局限,尤其是面对“规则”无法穷尽对于“技能”理解的困境,波兰尼提出“通过范例学习”(learnbyexample),“一种难以说明细节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prescription)来传递,因为对它来说不存在规定,它只能通过范例由师傅传给徒弟。”[18]并且,为了避免“默会”成分丢失,波兰尼进一步强调:“通过对师傅的观察,直面他的范例,模仿他的各种努力,徒弟无意识地获得了该技艺的规则,包括那些师傅自己都不太明确了解的规则。”[19]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进一步揭示了范例之于规则的优先性,即“规则导源于范式,但即使没有规则,范式仍能指导研究。”[20]由于“规则—技能”是职业教育的核心范畴,因此,哲学界对于范例的诠释,恰恰成为该领域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
由于具备“完整知识”属性,在未来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中,范例势必将从边缘走向核心位置,视“范例”为教学辅助手段的理念将得以矫正,范例之“饱满”、“立体”、“全息”、“优先”等特征将于新的课程范式中得以彰显。
(二)行动
作为一种文化,古语“仁者在上、智者在侧、工者在下”揭示出“匠器”在史上之生存地位,同时凸显出“匠器”所学之地位。匠器是依靠“行动”或“做”安身立命的,但在技术哲学发现之前,在教育史上,“做”或“行动”从未被视做“知识”来看待。先是“学在官府”的政治原因,再是“学科霸权”对于理性的推崇,迫使“匠器”之“行动”的技艺只得成为民间“隐学”。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表征主义”遭致批判以后,哲学界遂而在两个维度上破解了“行动”中的知识意味。其一,缄默知识维度。缄默知识不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在,通常以“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action),或者以“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knowledge)而称谓。诚如挪威哲学家格里门所言:“对知识的表达而言,行动是和语言同样根本的表达方式。”其二,能力之知维度。作为一种“非”命题性知识,能力是依靠“行动”来表达的。对此,约翰内森曾有一句生动的诠释:“我拥有某乐曲的某种特定演奏的知识……想完全传达我知所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径直去演奏该乐曲的片段。”[21]值得一提的是,“行动”中不仅蕴涵了“完整知识”元素,尤其是“行动”中的主体已与工作对象、工作环境浑然一体,这些“现象学”特征是在“象牙塔”内无法体味的。
在职业教育领域,除传统学徒制外,将“行动”纳入课程之中,首推19世纪俄罗斯帝国大学校长奥斯发明的“俄罗斯制”,将“工艺”融于课堂之中是其贡献。继而是杜威对于“主动作业”与“做中学”学理的系统阐述,并由此带来整个教育界的深远革命。德国职教大家凯兴斯坦纳受此启发,撰著《劳作学校要义》一书,并对德国职业教育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推进。基于杜威“问题教学法”,杜威的追随者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进一步以“设计”提升了“行动”的高度。到20世纪初期,视杜威为师,且有“美国职业教育之父”美誉的普洛瑟,在著名的“职业教育16条原则”中推出了比较完整的工作课程理念,“行动”则尽显其中。如第10条即“培训越是以真实的工作而非练习或假工作进行,学习者就越能有效的建立起流程习惯。”等等。[22]之后,北美CBE课程、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等皆推崇课程中 “行动”元素,并且学习领域课程视“行动导向教学”为核心方法。可以说,做为课程的核心元素,“行动”对于职业教育领域已不再陌生。
但是,这些“行动”元素还不尽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行动”。在讨论普通法时,波兰尼有一段与之相关的论述可以帮助深化理解,即“普通法建立在先例之上。如果今天要判一个案子,法庭会参照其他法庭过去判定类似案例的范例,因为,在那些行动中体现了法律的规则。这个程序确认了一切传统主义的原则,即实践智慧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中,而不是表达在关于行动的规则中。”[23]所以,无论是对作为“完整知识”的“行动”的挖掘,还是主体与对象层面“平等”对话、浸濡一体等“现象学”的关照,皆需以自觉意识去重构“行动”课程。
(三)叙事
简言之,叙事即“讲故事”,寓言、史诗、小说是最常见的叙事作品。在教育史上,除文学、史学之外,叙事很少以课程形式出现。即便如此,文学课中的小说、史学课中的故事,也旨在挖掘其内在“客观”的“知识点”,或是寻求故事背后“整齐划一”的“道理”而已。本来是人类教育与生存的基本形式,却在“理性”面前被完全边缘化了,“饱满鲜活”的叙事仅仅属于家教或幼教范畴,学府文化则完全充斥着“符号化”的象征物。如此,理论成为抽掉“血肉”的理论,更多有用的信息随之被“过滤”掉了,完整故事最终被“肢解”。胡塞尔现象学之后,面向“现象”本身成为认识的逻辑起点,现象学“描述”即“叙事”成为现象学最核心的方法。事实上,寓言、史诗、小说等叙事作品本身即最好的“现象学描述”,诚如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赞美的:“小说家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在不认识任何现象学家的普鲁斯特那里,有着多么美妙的‘现象学描写’!”[24]叙事的价值已经从寻求背后隐藏的“东西”转向叙事“本身”,这即是叙事作品在课程中的价值所在。
基于现象学的“叙事”观,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需做两个方面的变革。其一,设置“叙事化”课程并编撰“叙事化”教材。除语文课、历史课之外,职业道德、职业指导等课程也适合“叙事化”课程,尤其在教材开发中,需变革惯常以罗列概念、命题、知识点的编撰体例,选择经典的“故事”案例并做系统化处理,并以其为框架将知识“镶嵌”其中。另外,即便是专业课程也可增加“叙事”元素,例如将技术事件、服务事件等编撰其中。原则是,适合“叙事化”的课程要按照“叙事化”方式编撰,不完全适合“叙事化”风格的,也勿将“叙事”元素排斥在外。其二,设计与“叙事”课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与“表征主义”不同,教师勿要一味传授既定的、抽象的“命题”、“原理”,而需成为一个很好的“叙事者”或者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学生则要成为一个会“读故事”的主体。再有,“现象学”教学注重“个别”事实,并在引领学生“直观”个别事实的当下领悟事实的本质,不是在“个别”中抽象“一般”,而是把“一般”还原为“个别”。如此,教师与学生需就故事进行“平等对话”,并彼此成为故事的独一无二的诠释者。
(四)情境
20世纪以来,脱离情境的“惰性知识”或“博物馆式知识”愈发为人所诟病。“知识—情境”之间的关系成为认知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莱夫在研究中发现:成人在做简单的数学题时,表现十分糟糕,可在杂货店中询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却能显示出能力和解决熟悉问题的策略。[25]在“学习环境的设计问题”一文中,布朗和柯林斯也指出:“概念知识不是抽象的独立于情境的实体,他们只有通过实践应用活动才能真正被理解。”[26]情境认知理论出现之后,情境在教育学上重新被理解。威尔逊(Wilson,G.B.)概括出“情境”设计的四个基本假设:(1)学习是根植于日常情境的行动中的;(2)知识只有在类似的情境中才可有效迁移;(3)学习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知识、技能和思维融合其中;(4)学习无法与由学习者、行动和环境组成的统一体分离。[27]由此看来,知识不再是独立于情境的“客观”存在,教学也不再是独立于情境的“符号”传递。
情境与知识相关,但很少视之为知识“本身”,这势必影响课程设计中的情境定位。反映在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中,俄罗斯制、MES课程、CBE课程等皆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从“学科世界”到“工作世界”的跨越,但在课程构建过程中还是将 “完整”工作任务进行了知识、技能等维度的“拆分”,从而使其从原有学科的“抽象”走向工作的“抽象”。比较而言,在课程创制过程中具备“情境”自觉意识的,当属德国学习领域课程。该课程模式着实考虑了典型工作任务的“整体性”,并以“对象、工具、方法、组织、要求”等要素还原出真实的生产情境,并且,基于生产情境构建出与之相对应的“学习情境”,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的“情境”意识是使之盛行至今的关键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即使在德国学习领域课程中,情境多是以知识的“载体”或“背景”身份而出现的,事实上,情境本身即知识,设若完成一项岗位任务如未考虑情境因素,“结果如何”自然明了;情境本身即课程,以“现象学”视角分析,作为“统一体”,情境俨然是一种“物化”的“叙事”。甚至,在情境中即自然有学习发生。诚如英国教育家纽曼在其名著《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所描述的:即使没有老师,如果将一群年轻人召集至一所大学三、四年,本身即是一种“活生生的教育”。[28]纽曼之语在职业院校同样适用,不过是学术“情境”与职业“情境”的区别而已。
需要注意,由认识论革命引发的职业教育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完整知识”诉求与职业教育“现象学”转向背景之下,在“抽象的、垂直的、明言的、命题性的”知识体系重新接受“审议”之时,尤其当“范例、行动、叙事、情境”等“隐学”逐步从课程边缘进入核心的过程中,不是从“抽象”走向“具象”的单项过程,换句话说,不是“回归”至传统学徒制中“范例、行动、叙事、情境”的原点,而是“个性中体现共性”、“物性中体现知性”、“具象中体现抽象”如此等等,从而在职业教育范畴,最终走向知行合一、主客一体的厚实的、有主体的“现象学”课程与教学。
[1]陈康保.康德知性范畴理论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10.
[2]Baird,D.TheThing-y-nessofThings:Materiality andSpectrochemicalInstrumentation,1937-1955. InKroes,P.,Meijers,A.Micham,C.(eds.).TheEmpiricalTurnin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ElsevierScienceLtd.,NewYork,2000:114.
[3]GilbertRlye,KnowingHowandKnowingThat,ProceedingsoftheAristotelianSociety,Vol.1946:16.
[4]邓线平.波兰尼与胡塞尔认识论思想比较研究[M].广州: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9.
[5]MichaelPolanyi,KnowingandBe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9:144.
[6]Bernstein.B.Verticalandhorizontaldiscourse:An essay[J].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ofEducation,1999,20(2):158.
[7][9][10]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83,358.
[8]RichardRorty,PhilosophyandMirrorofNatur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
[11][12]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223-225.
[13]Dewey,J.DemocracyandEducation [M].New York:Macmillan,1916:195-196.
[14]吕达,刘立德.杜威教育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81.
[15][英]琳达·克拉克,克里斯托弗·温奇.职业教育:国际策略、发展与制度[M].翟海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96.
[16]MichaelPolanyi.PrefacetoTheTorchbookEditionofPersonalKnowledge,NewYork:Harper andRow,1969,P.X
[17]DaleCannon.ConstruingPolanyisTacitKnowing asKnowingbyAcquaintanceRatherthanKnowingbyRepresentation:SomeImplications.2009:32.36.
[18][19][23]Polanyi,Michael.PersonalKnowledge,London:Routledge,1958:53.
[20][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21]KjellS.Johannessen,“KnowledgeandItsModes ofArticulation”,2000:168-169.
[22]Prosser,CharlesA.&Thos.H.Quigley.Vocational EducationinaDemocracy(reviseded.)[M]. Chicago:AmericanTechnicalSociety,1957:233
[24][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懂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1
[25][26]Wilson,R.A.,andKell,F.C.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767,770.
[27]BrownJ.S.,CollinsA.andDuguid,P.Situatedcognitionandthecultureoflearning,Educational Researcher,198918(1):32-42.
[28]JohnHenryNewman.TheIdeaofUniversity[M]. YaleUniversityPress,Newedition,1996:66—70.
责任编辑韩云鹏
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思想史、应用型大学建设。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界视阈下应用型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编号:HB15JY056),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编号:2015030425),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基地项目、校资助秦皇岛市社科联委托课题“应用型大学课程开发研究”(编号:201506186),主持人:路宝利。
G710
A
1001-7518(2015)28-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