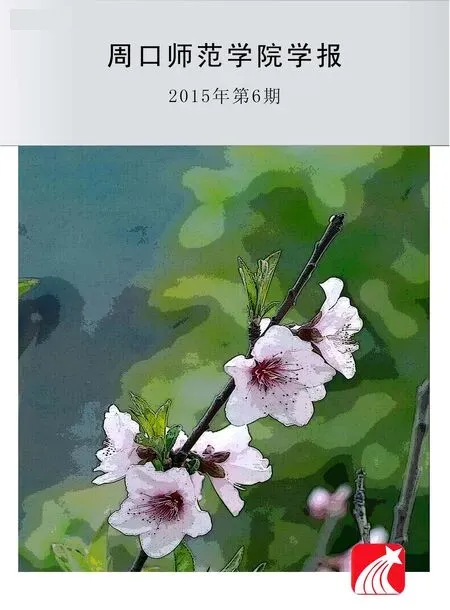论青少年完整性教育的三重场域构建
2015-01-31胡艳玲
胡艳玲
(周口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论青少年完整性教育的三重场域构建
胡艳玲
(周口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人的整全发展是教育的理想,人的无限潜能为其整全发展提供着物质基础,人的潜能挖掘上的实现不是单一教育场域所能完成的,生活教育的选项成为必须,从学校、家庭、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对此做出探讨。
场域构建;生活教育;青少年教育
人发展的整全是教育的理想,如何实现青少年发展上的完整性是教育面临的惯常性问题,实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链接是实现此论题的关键。
一、人发展的整全与三种生活领域
何谓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同的角度答案各不相同,相比而言,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的观点更全面,他说:“人是自然和精神的结合体,但本质上是一个精神体。”[1]如果我们把这一判断作为思考的指南,那么,如何促进人由自然体到精神体的转换涉及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由此,张楚廷先生把教育的目标定为:“教育使人更富有、更聪明、更高尚。”[2]教育的终极目标在此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即人的发展应是完整的,而不是单向度的。目标如何达成?路径怎样?何种方法?这些是实现教育目标必然要思考的问题,教育的目标是促进人从自然体向精神体的转换,但并不意味着“自然体”在教育价值中的意义消亡,“自然体”和“精神体”都是教育所应关注的关键领域。在青少年时期,人“自然体”的比重大于“精神体”的比重,精神体的发育虽然是人发展过程中关注的核心,但精神体发展的根基不是别的,而是来自精神的承载物——“自然体”。
“自然体”里隐含着人发展的各种潜能,如语言、游戏、制作、情感、文学、艺术等,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自己潜能的认知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人到底有多少种潜能?这是一个无法定论性回答的问题,它与人发展的实践性相联系,需要在一定的时空内被激发出来,为此,皮亚杰说:“知识是人与环境的互动中被激发出来的。”[3]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那么,作为促进人发展的教育也是没有尽头的。所谓实现人发展的整全,存在着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人发展的整全,即是把其潜能尽可能多地挖掘出来;二是潜能挖掘的方式与尽可能多的潜能实现相匹配。
杜威之所以成为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正因为他的教育哲学在人实现潜能与潜能实现上对传统的僭越,“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经验的改造”[4]。生活教育之所以成为杜威教育哲学的核心,正是他看到了生活教育与青少年完整性发展上的最佳匹配性。生活教育的价值何在?海德格尔说:“生活就是人的活法。”[5]人是生活中的人,即人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人不可能离开生活而存在,为此马林诺夫斯基说:“人是社会性动物。”[6]从表面看,生活被赋形为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神话等,生活的赋形是人对生活秩序化的结果,生活的形态从本真上说是隐性的,生活与人本质上是形塑和塑形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性。生活的原貌是整体性而非程序化、类属化的,生活之所以以类属化的形态出现是人为秩序化的结果,这便于人的认知和区分,具体表现为家庭生活、职场生活、社会生活三种类型。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一个概念束,即由场域、惯习和资本构成。“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7]134布迪厄对资本的论述涉及教育资源的问题,他说:“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这就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还可叫着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它本身存在三种形式: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则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7]151根据场域理论的概念束内涵,从教育的视野审视,三种生活形态形成三种教育场域,具体表现为学校、家庭、社会,三种场域体现着生活的整体性形态,它为青少年发展的整全提供了可能。
二、学校的灵魂是什么?
按照布迪厄的理论,学校是一个网络,一种构型,一类社会化的场域。它的应然存在是富有教育资本的场域,是个体充满期待、渴求进入其中争夺的行动者。问题的关键是学校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强烈吸引行动者去期待、去争夺,换句话说,学校的灵魂是什么?这决定着学校的品质,也决定着青少年的未来品质,作为一个优化了的社会场域,它应该是青少年完整性教育的理想构型。
研究者把田野中调查所得的学校面相呈现如下。
案例一:愿意赌命的学校
解放前,在乌蒙山区深处,有一个苗族寨子,寨子里从来没有人出去过,外面的人也从来没有进来过,读书对于寨子里的人来说是一种传说。一天,一位长者把他的第三个刚满7岁的儿子叫来,在他儿子身上拴了几只吹满气的羊膀胱,让儿子坐在一只竹框中,放到寨子边上的小溪里,儿子十分惊恐地说:爸爸,让我到哪里去呀?爸爸说:到一个寨子里的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儿子说:为什么让我去而不让他们几个去呢?爸爸说:选你去,今后你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但也可能是不幸的一个。爸爸说完就一把推走了竹筐,眼中充满了期待和悲伤的复杂神情,他之所以如此让7岁的儿子去冒险,是因为他听说了小溪下游很远的地方有个读书的地方。后来,这个7岁的儿童成了贵州石门坎走出的第一个医学博士。
案例二:骂出来的学校光明
乌蒙山深处的团结村是贵州石门坎乡最偏远的一个村子,由于大山耸立,跋涉艰难,一直没有通电。2011年,乡里告知说准备给团结村小学通上电,但电线杆需要他们自己抬回去,因为没有路,车子无法到达。团结村的村主任就带领村民到乡政府去抬,电线杆两头各8人,总共需要抬回8根。起初,抬电线杆的村民们因为马上要通电很是兴奋,大家有说有笑。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大伙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只是默默地走路;因为山路太难走的缘故,又走了几个小时,大伙中开始出现抱怨的声音,说知道这样遭罪就不来了,但也没有撒手离开;路远无轻重,等到下午的时候,大伙一歇下来就开始互相对骂。这里的对骂并不是因为有冤有仇,而是作为排解极度劳累的一种方式,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奇特的骂声了。在一天的对骂声中,电线杆被全部抬到了团结村,团结村小学也随即通了电,它使有史以来存在于黑暗中的学校终于在黑夜里见到了光明。但许多村民的肩膀也由此被压坏了,时常受到疼痛的折磨,但为学校做事他们很高兴,因为学校是他们心中的希望。
案例三:树枝换来的学校
解放前,石门坎光华小学决定在安顺紫云县开办一所分校,石门坎光华小学就派一位姓王的老师去紫云,石门坎离安顺200多公里,山高壑深,十分难走。王老师走到贵州花溪病倒了,也没了干粮,就住到一位苗族大嫂家。大嫂听说他要去办学校,二话不说,不但每天精心服侍他,而且还每天去山上砍柴为其筹集路费。连续砍了半个月,终于筹齐了路费,让王老师带着走了,这才有了今天的安顺紫云小学,紫云小学至今被当地人称为树枝换来的学校。
从三个田野案例本身来看,我们不禁要问:学校的什么东西使大家如此敬仰它、呵护它?是什么使学校在大家心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答案是明确的,那就是学校的灵魂使然,即学校能够给大家带来希望,带来美好的未来,又能够使村民或村民的子子孙孙顶天立地。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学校是结构与反结构的赋形,它引领、规范着社会的发展;第二,学校是爱的生态循环系统,它体现着对青少年强烈的人文关怀;第三,学校是唤醒生命活力的空间,是个体朝着特定逻辑方向自我发展的场域。一句话,学校的灵魂是在为青少年素质塑形的,它必须既能使青少年远走高飞,又能使他们坐地开花,单一、片面的学校教学是不可能在人们心中拥有如此大的生命力的。
三、公共领域的教育点在哪里?
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水平越高就意味着社会体系越发达。社会组织是为着个体的存在为目的,并且成为与个体相对应的范畴来谈论,个体之间存在着身体、能力、态度、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如何把存在着个体差异性的个体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体系是社会组织的关键。法律体系和公共道德是社会组织的两翼,法律是必须遵守的刚性律例,公共道德是共同维护的善性共识,任何一个优良社会都是二者的良性结合。社会又存在着地位差序的问题,每个个体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占有的社会资本也不同。社会的差序地位为个体提供着向上流动的动力,社会个体又是以劳动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社会地位诉求的,人的价值正是在实践中获得实现或实现的可能,“社会即学校”——社会的丰富性在陶行知先生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在青少年的发展中,作为公共领域里的教育更多地表现为公民性教育,社会是公民存在的真实场域,是公民素养养成的地方,公共领域的教育对青少年教育的基点在哪里呢?具体呈现为三个维度的教育:
第一,德性的教育。相对于学校、家庭来说,社会是一个公共场域,并非是一个优选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里是非、善恶的各种形态一应俱全,它的实践性特征,对青少年的行为规范有着直接、真实、实践性的影响。社会是个体群体性本质的必然表现,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但又不为单个个体所左右。换句话说,社会的面相是单个个体无法控制的,这样一个有所有人组成的场域,正是每个个体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它教育的价值和特殊性在哪里呢?家庭、学校是优选的、能够人为控制的场域,是从理想教育的角度来设置的,但理想化教育的人最终要投放到社会之中。这不但存在着场域的变化而且存在着应然与实然的差别,如何自觉地抵制恶的东西,主动践行善的行为,只有在实然的场域里才存在着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德育不是说教所能完成的,家庭、学校的德育认知还需要社会的实践来检验,青少年积极地参加义工、社会团体等组织,不断培育自己的德性,努力使自己的德性认知和德性实践统一起来。
第二,群性的教育。群性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群性作为教育目标一直延续到近代,“民国”课程标准中还把德、智、体、美、群定为教育方针,可见群性教育在青少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知识的分类来看,群性属于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与描述性、策略性知识不同,传授的方式也不同。描述性、策略性知识可以通过讲解、讨论来获得,而程序性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获得,社会的本质是一种群性的结构,人的本质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青少年的群性教育是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公共场域里存在着大量的对话关系、交往机会,为此,在公共场域里可以设置一些“假性部落”,即成员没有血缘关系而有共同爱好的社会群体,义工组织、读书会、公共运动队、旅游团等都属于这样的群体,可以在这样的群体里培育青少年的群性。
第三,生活的教育。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人的活法。生活之理的体认只有生活所能给予,万物同理,这就需要对物的观。观察力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基础性能力,如果没有对物以及物与物关系的观察,就不可能获得万物之理,生活的规律就会远离他们。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对青少年而言,进入真实的生活场域是至关重要的。从丰富性上来说,真实社会场域的丰富性是学校场域、家庭场域所无法比拟。为此,在青少年生活力的培育上,应该设置一些“到春天里去”“到田野里去”“到劳动中去”的相应场域,使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在阳光中赢获积极、向上的心态,在劳动中获得劳动的感悟,在田野中获得万物的体认,从而促使青少年在身体、人格、心理上获得整体性发展。
四、家庭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完整性教育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完整性是青少年身处场域的整合,家庭场域对青少年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价值。青少年生命中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人的未来素养又往往取决于童年经验,家庭教育的影响直接决定着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的走向。那么,作为一个青少年教育的第一场域,家的内涵应是什么样的呢?
(一)家——丰富性
家的内涵不是一座房子,而是存在着最大限度丰富性的场域。这种丰富性是对应着儿童生长复杂性的,它是一个特定的生活场域,儿童生长的复杂性需要由生活教育来完成,丰富多彩的生活是生活教育的源泉,儿童能在生活中获得多元的生命经验,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极力倡导经验哲学的原因正在于此。据此,天地之间存在的东西家中都可尽力存在,让青少年置身家的丰富性之中,在活动中积累进一步发展的经验素质。
家应是一个书场,读书是人成长的软要素,书是儿童精神世界的“第二个太阳”。自然万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需要太阳的照耀,人精神世界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需要太阳的照耀,书就是儿童精神世界生发的“太阳”,这是他们精神素养提高的主要途径。据此,提倡家庭书场的“四个一”工程,即有一个书架,积累一百册书,增订一份报纸或杂志,每天阅读一小时。
家的最大内涵是夫妻的匹配程度,良好的夫妻匹配程度是指夫妻有着良好的道德水平、积极的进取心、卓越的成就、稳定的收入等,这决定着孩子成长的速度、力度和厚度。反过来,极弱的夫妻匹配程度或单亲家庭,对孩子成长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二)家长——无为而治者,不言之教者
家长在青少年素养生发的初级阶段至关重要,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是“连体人”的关系,正因为这种特殊关系,孩子可以自然地从家长身上得到关爱,这种爱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获得。这样,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就极可能演变成孩子无尽地攫取父母之爱,而家长无穷地给予孩子之爱,此时,青少年就有可能被溺爱所包围,一切需要在家庭中养成的素质被溺爱所隔绝殆尽。
家长需要以特殊的方式对青少年施加影响,模仿是儿童的天性,他们的成长是在模仿中完成的,家长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因此,家长最好的教法就是——无为而治者,不言之教者。用自己的行动引领孩子去行动,用自己的品德去引领孩子的品德,用无为的方法无声地指挥孩子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家长不要当大包大揽的大人,而要做孩子的先行者。
(三)创造教育——一切皆是教育元素
家长要把一切人、物、事作为教育元素来使用,这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更能满足儿童生长的需要。为此,要精选旅游地,诸如历史文化圣地、科技馆、伟人故地、庄严的盛典、自然的山水等,使天、地、人的元素内化在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
家长要引领孩子共同创造,在读书、行路的二维中内化知识、能力。
孩子艺术素养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艺术是人类的教化之源,它对人精神世界的价值是巨大的。在当前孩子普遍学习艺术的同时,注意不要为学艺术而学艺术,要为他们所学提供一个投放的地方,比如为爱心而舞,为集体而舞,为审美者而舞,等等,这样就能在艺术素养中发展出道德素养。
青少年的生长是复杂的,他们需要完整性教育的教化,三种场域的关联是生活教育的赋形。它不但是青少年完整性教育的最佳匹配物,而且能促进青少年对实践生活的体验和认知,更能完成教育向生活回归的理想。
[1]莫里斯.裸猿[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13.
[2]张楚廷.教学论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5.
[3]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胡世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9.
[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陶志琼,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98.
[5]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
[6]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6.
[7]皮埃儿·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The three field of construction:How to realize the integrity of youth eduction
HU Yanl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466001,China)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is the ideal of education, the unlimited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to provide the material base, realize the potential mining is not a single field of education can be completed, the life education options become a mus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chool and family,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face of this study.
field construction;life education;the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2015-03-24;
2015-05-13
河南省教育厅2014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周派名师工程’四大基础性课程构建研究”(2014-JSJYZD-057)。
胡艳玲(1974-),女,河南商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德育。
G410
A
1671-9476(2015)06-0140-04
10.13450/j.cnki.jzknu.2015.06.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