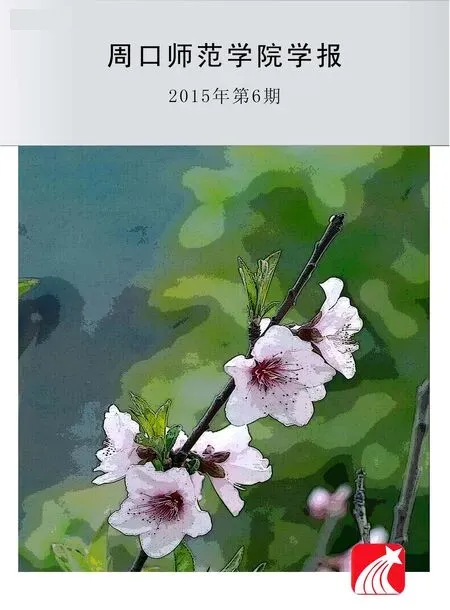新视角 新收获——评孙红震专著《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
2015-01-31沈文慧
沈文慧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解放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性、丰富性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都使之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20世纪40-70年代,解放区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建构模式,因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以颂扬为主的单一研究格局,看似辉煌实则沉闷。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控制的松动,开始进入学理化研究时期。90年代以来呈现出蓬勃生机,研究者以宽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学理态度走进解放区文学生成的历史场域,探究其本体属性和丰富内涵。进入21世纪十多年来,研究的着力点是从发生学的视角探究解放区文学的生成体制和运行机制,着重关注了战争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规训、多种文化资源的碰撞与融合等复杂因素对解放区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深层制约。另外,关于解放区文学的社团期刊研究、文学与媒体的互动关系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孙红震的专著《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为日渐深入的解放区文学研究增添了一枚特色鲜明、值得珍视的成果。该书入选201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文库,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同年12月出版。其特色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鲜明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认为,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前者“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研究尚未启动之前已经存在的“自在之物”,而是在“问题意识”引导下的一种探索、发现和建构,是否有基于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而生成的研究对象和审视对象的独特视角,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研究能否有所发现的前提。正是基于鲜明的“问题意识”,孙红震选择从“革命伦理”这一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进入解放区文学。在解放区文学中,目不识丁的老大娘可以将击毙自己汉奸儿子的八路军战士隐藏在自己家里帮其脱险;年轻女孩子被鬼子蹂躏后可以忍受着身心的巨大伤痛接受革命指派,借助其特殊身份深入虎穴获取情报;在面临血缘亲情和革命事业的两难抉择时,革命者上演了一幕幕毁亲舒难的壮举;连最私人化的爱情也与革命密切相关,“好革命”“好政治”“好劳动”成为美好爱情的标准和黏合剂,凡此种种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叙事景观,不少研究者对此不以为然。孙红震却认为,这种令人诧异的叙事景观“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对通常伦理形态的改换或背弃”。中华民族是一个伦理型文化的民族,但“在解放区文学叙事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与世俗的伦理规范却被改换面孔或被打得七零八落,何以如此?是什么样的巨大力量导致了一直不曾被撼动的伦理形态的崩溃与裂变?这显然不是‘革命’二字就能解释清楚的”。对此“困惑”与“问题”的思考与追问成为他解放区文学研究的兴趣起点和基本动机。
二是新颖的研究视角。在鲜明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经过深入思考、探求,著者找到了“革命伦理”这一新颖有效的研究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许祖华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就指出,以“革命理论”作为解放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抓住了解放区文学生成与建构的逻辑基点,解放区文学的价值诉求、人物塑造、表达方式都与“革命伦理”纠结缠绕、密不可分,是形成解放区文学“特殊性”的一个重要元素,“革命伦理,不仅是解放区文学思想主题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其艺术风貌形成的基础”,而此前的解放区文学研究对此问题或语焉不详或浅尝辄止,像这样系统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尚属初见。这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切入当时解放区群众的生存状态,切入解放区文学(创作与论争)原初的存在,触摸到当时作家的精神深处”[1],避免了人云亦云和跟风重复,拓展了解放区文学的研究空间和研究路径,开辟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三是严谨的理论思维。一般认为,1996年英国威尔士大学召开的“文学与伦理”国际研讨会正式拉开了西方文学研究“伦理转向”的序幕,倡导者如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批评家努斯鲍姆认为,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可以通过道德哲学实现突破,帮助精神迷茫和思想困惑的现代人建立一种“诗性正义”的生活态度。中国的文学伦理学研究兴起于21世纪初,在对西方文学伦理学研究借鉴创新的基础上成长发展起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2]。它将文学看作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不是从伦理立场出发对文学做出是非优劣的简单价值判断,而是要从本质上阐释文学的伦理特性,既为文学阐释提供新的可能性,又为思考和解决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和价值危机提供参照视角。这是文学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也是《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的基本学术诉求。著者以文学、伦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依托,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在广泛的学术视域里,对“革命”“伦理”“道德”等相关概念进行梳理辨析,在此基础上对“革命伦理”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质特征进行界定:“革命伦理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普通伦理的一般特征。”“区别于一般伦理形态,革命伦理以革命的旨归为其标向,将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终极目标的道德、措施、规范、准则视为善。”“革命伦理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与目的性”,“革命伦理是一种信念伦理……也可以说是以人民为本位的献身伦理”。相对周严的概念辨析和理论范畴界定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严谨的理性思维还体现在该书的整体架构及有新意的观点上。全书由四大部分构成,即“革命伦理的个体叙事”“革命伦理的身体叙事”“革命伦理的情爱叙事”“革命伦理的家庭血缘叙事”,分别从“个体”“身体”“情爱”“家庭”四个方面对解放区文学进行革命伦理阐释,系统探究解放区文学革命伦理叙事景观的社会历史原因:既注重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又观照到历史文化的传统脉流,视野开阔,内容广泛,研究深入细致,不仅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且不时闪现具有创意的思想火花。难能可贵的是,在对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叙事进行总体评价时,著者没有对之进行是非优劣的简单价值判断,而是秉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持论客观理性,因此才有这样的认识:“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叙事彰显了革命战争年代崇高的革命意识,显现出文学对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建构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介入。但是,在彰显崇高的革命意识与高扬革命之‘道’的同时,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叙事却削弱了对生命价值本身以及人性的关注,消减了对人与革命之间复杂多样关系的审美感受与反思。”这种客观性、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及在此立场上形成的学术观点,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解放区文学的伦理思想、伦理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四是充分的文本细读。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任何形式的文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细致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上。直面文本,咀嚼语言,悉心体味,发掘内蕴,才能避免文学研究因热衷“宏大阐释”和“整体把握”而疏离文本、缺少鲜活的审美感受和细腻的心灵体悟,导致立论空疏、空洞无文、阔略不当等流弊。《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一书真正将文本细读落到实处,所有思想观点均以充分、细致、深入的文本细读为基础,既有对《在医院中》(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等经典作品的细致解读,更有对《钟》(孙犁)、《乡长夫妇》(洪流)、《我的三个朋友》(韦君宜)、《秋收时节》(方记)、《围村》(周而复)、《儿子》(鹿特丹)、《洋铁桶的故事》(柯蓝)、《在旅部里》(刘白羽)等大量一般性作品的解读。这些细读从文本的语言表达、情节走向、场景细节、叙事方式等构成文本的各种元素入手,细心体悟作家的伦理思想,深入解读作品的伦理内涵,揭示作品中伦理现象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丰富充实的文本细读赋予了该书浓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使之成为一部带着著者个人体温和生命热度的学术专著。
当然,本书尚有一些不足,如对革命伦理的生成问题阐释得过于简略,对革命伦理的复杂性把握不足,文本细读涉及的文体类型还不够丰富,对解放区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纪实文学、戏剧、戏曲等较少涉及,而关于革命伦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形式变革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应该在本研究关注的范围之内,但本书没有涉及。行文至此,想起了十年前笔者与红震一起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我们都以解放区文学为研究对象,经常为博士论文的某个问题而焦头烂额,也因此常常在一起争论、交流、切磋。他才思敏捷、视野开阔,写起文章来不像我挤牙膏般艰涩。毕业后,行政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本书就是他利用烦琐行政事务的间隙,将博士论文修改、充实、完善而成,实属不易。笔者期待并坚信,未来的日子里他一定会取得更丰硕、更厚实的研究成果。
[1]刘增杰.回到原初: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4):74.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