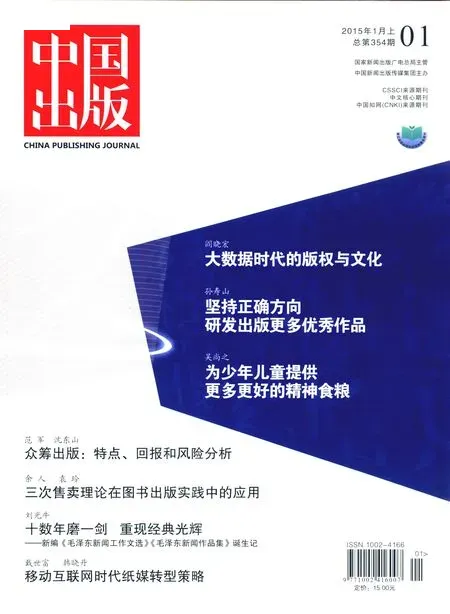近代报人社会形象与地位的重塑
——以近代报刊史料的发掘为据
2015-01-30□文│李礼
□文│李 礼
近代报人社会形象与地位的重塑
——以近代报刊史料的发掘为据
□文│李 礼
近代报刊出版被引入中国后,早期西方在华报刊对报刊、报人进行了新的形象再造。通过对西方报人的阐述,报人角色被塑造为独立而拥有重要社会地位。此外,通过《申报》公共舆论的示范,拥有批评监督“权力”的报刊面貌也开始在中国呈现。传统低下的“报人”形象经此重塑而发生历史性改变。
报人 形象 精英
近代报刊在晚清引入中国后,西人对这一新式出版与中国传统邸报加以区分,这种带有技术威力的新式出版被描述为文明而先进,并具有话语权力,以配合自己的宗教、文化传播。就国人而言,西方报刊也与“洋务”“新知”联系起来,成为洋务或自强运动在文化出版领域的落实,引发了最早的国人办报。
与此同时,早期西方在华报刊也对报刊、报人进行了新的形象再造。报人角色则被塑造为独立而有社会地位。通过《申报》公共舆论的示范,拥有批评监督“权力”的报刊面貌也开始在中国呈现。传统低下的“报人”形象经此重塑也大为改观,这也为甲午之后高级士人投身报界和精英报刊的出现,做了有力的先导。
一、传统“报人”形象及近代报刊的舶来
中国古代所谓报刊,或为官方邸报或为民间“小报”, 邸报可视为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或政治功能的延伸,而充当茶余饭后谈资的“小报”可视为对前者的政治偷窥,如宋代的小报,以及明清的小本、小钞、报条等,多被政府视为浮言惑众的非法之物。从媒体属性上看,邸报和各种“小报”并非真正媒体。中国传统“报人”的形象来源于“小报”,实质上将之等同于作为商贩的“送报人”, 此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报人”的社会刻板印象。
对晚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们来说,宗教目的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不过宗教的内涵以及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却必须灵活,在经过短暂的接触后他们发现需要引入有效的传播手段,并辅助以科学技术的光环和实利,才能有效吸引和说服中国人。
中国的方言是传教士选择报刊出版的主要原因。因为外来者发现,他们的“宗教之旅”难以突破中国各地方言的瓶颈。只有书面汉语才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沟通工具。此外,中国能够阅读的人群多为士绅,因此希望通过书籍和报刊传播影响这个阶层进而影响大众。事实上报刊与典籍的出版早期是并行的,如广学会的书刊结合,互相促进,大受欢迎。不过和书籍相比,对中国读者而言,报刊是更加新颖的出版形态,定期而快速的出版频率以及在携带的轻便程度方面,报刊显然更加有利于携带、分发和传播。就技术而言,出版报刊较之典籍也更加经济,因为“当时的印刷机非常昂贵,只能用来印刷报纸,而印刷书籍或者小册子只是额外的工作”。[1]
如果说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尚是一份宗教刊物,那么其后不久中国本土上的第一份中文外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则很快突破了宗教的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比例超过了宗教,并设有新闻和言论专栏。和中国传统邸报比较,西方报刊因社会公开交流新闻信息的需要而产生,早期报刊研究者戈公振已经认识到,其核心特征是“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戈公振把报纸定义为“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更将首要特点归结为“公告性”。[2]在华主办的西方报纸也基本具备了近代报刊的面貌,应该说中国近代报纸正是沿着西方导入的报纸形态而非邸报发展而来。早期在华中文报刊对报刊及其从业者的角色界定也大异于中国传统,这固然有利于西人宗教、文化传播的需要,也将中国报刊出版助推至新的历史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人,之所以不同于16~17世纪带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西人只是带来了一个陌生的技器,此时的西方已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一个“先进”的西方。和那些虽然先进却令人痛恨的坚船利炮相比,印刷机等虽是陌生技器却相对平和,而中国的印刷传统和对文字的偏爱也使得它更容易被接受、推广。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的血腥“胜利”以及他们的各种先进器物,已让其对中国人具备了心理优势。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等一样,从一开始即伴随其政治上的成功以强势姿态出现,而机器的技术威力也令其披覆着先进文明的外衣。因此早期的西方报刊,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先进的“洋务”出现在国人面前的,早期模仿西人办报的中国人也明显受到西方技术、文化影响,柯文认为“实际上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积极参与了创办中国近代报刊”。[3]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都在中国早期开放的城市中接触过西人和西方文化,不少还直接在外国人办的报社工作。他们主要包括接近体制的洋务派背景文人,以及体制外的接近西人的旧式文人。此外,直接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人员也成为早期报刊参与者,比如伍廷芳和容闳等。由于与西方技术、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甲午之前的早期报人也经常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洋务派知识分子等,此时的报刊阶段也被称为洋务派报刊。[4]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予中国更多的是打击,那么“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5]洋务派本身是各种西式技术和“洋务”“新知”的热衷者。《万国公报》出版者李提摩太去北京高兴地发现士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出版物,把它叫作“新学问”,直到维新派所热衷的“时务”“知新”“国闻”“湘学报”等,从报名看也没有溢出“新知”的边界。[6]采用西方技术的工矿企业和运输业以及翻译、出版机构甚至电报等出现自19世纪70年代,正是在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的背景之下。可以说,国人创办近代报纸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新闻领域的落实。[7]
以先进的印刷技术为基础,西方在华报纸得以“洋务”和“新知”面貌示人,而这种新的形象给了中国士人办报以很大的“合法性”。洋务运动和国人自己主办的报刊同时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60~1870年,并非偶然。这种模仿和学习,隐含着一个大的历史变化,即西方作为整体开始被以“先进”的形象描述,虽然在此阶段,这种“先进”还更多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根本动摇文化信心。
二、“报纸”“报人”新形象的塑造
从1833年开始,传教士们已经开始在报刊上撰写西方报纸究竟是何物,将这种出版的形式介绍给中国读者。当年刚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阴历十二月发出《新闻纸略论》,介绍了西方的出版自由以及报纸发展状况,描述着一个为中国人所陌生的新报刊形象。
据《中国新闻学术史》统计,从1834年至1899年,各报刊发表的论述新闻学方面的文章共计31篇,另外,最多的为西方人开办的《申报》12篇,[8]以及《万国公报》8篇。最为详细的《申报》刊发时间集中在1870年左右,这些文章谈不上多么学术,而主要是将西方近代报刊与中国旧有的邸报加以区别,通过西方的报馆价值和功能的解释,塑造报纸、报馆的地位。
在此方面,《万国公报》的政治诉求似乎更加明显。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首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然后单独发行。《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第六卷介绍英国变法,内有报馆免税介绍,第九卷在所列英国成为第一强国的各种政策、技术发明中,也包括报馆、电报。并称“英人既有举官之权,若不知国事何能措理,若不观新闻纸何能知国事,则新闻纸者,诚民间所不可少者也”。[9]从发行效果看,这些思想应该扩散于很多中国士人之中。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获得成功后,《泰西新史揽要》1895年正式出版即告洛阳纸贵,出版达3万部。《万国公报》以及广学会所传播的现代报刊理念深刻影响了一批中国精英。该刊的读者群处于中国社会上层,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洋务派大员,作者则包括王韬、孙中山等人。张朋园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下的维新派,其变法意识形态,多得自于传教士”,[10]主要指的就是《万国公报》。作为模仿,康梁不仅在甲午后首次主办报刊,还将其主办的第一份报刊取名为《万国公报》(随后更名为《中外记闻》)。
报纸强调自己为“新报”,并刻意在名称上加以突出,如《中外新报》《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等。“新”字在晚清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在中国的不断挫败和进化观念影响下,经常意味着先进与现代。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有学者称之为“新的崇拜”,比如英文的modernism今天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那时却译作“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11]
随着中国直至甲午的连续失败,西方这种“先进”形象已经不仅作为印刷技术,而且包括了报刊所刊载的内容,而“报人”显然也镀上了这层光芒。从《教会报刊》开始,西方人即开始塑造一个独立而有社会地位的“报人”形象,如称“所延主笔更可得到绝伦超群之名士”[12],《申报》这样描述英国报刊的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人皆与之交。”[13]这显然影响到了早期对报刊有兴趣的士人如王韬、郑观应等,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不无夸张地称“英国《泰晤士报》馆主笔者,皆归田之宰相名臣”。[14]中国新闻业之父王韬则称“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备其列”,王韬描述英国《泰晤士报》的地位是“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15]这样的报人形象不仅有着权威色彩,还与传统精英发生勾连,为甲午后梁启超等高级士人投身报界,再次重塑这个行业形象,做了一种铺垫。
三、“权力”的报刊——《申报》公共舆论的示范
从《六合丛谈》开始,西方在华报刊关于时局和变法的讨论就出现。不过就讨论的公共性和日常性而言,这种报刊舆论监督角色的呈现主要来自《申报》,正是这个报纸让中国人初步认识了报刊舆论拥有一种官方之外的“权力”。
《申报》的公共舆论建构奠定在其读者大众化和内容的广泛性上,这让其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读者群和介入日常公众生活的能力。在内容方面,《申报》报道上至国家政治中外交涉,下到风俗变迁、商贾贸易。在回顾自己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中国昔年只有邸抄(邸报),并无报纸”“只涉朝政,不涉细事(民间的事情)”。[16]而正是民间的细事,让《申报》迅速拥有大众读者群和影响力,从1872年创刊时销量600份,迅速到3年后日销6000份,此后的1877年已近万份。[17]1876年《申报》还创办了白话文《民报》副刊,以半个铜板的低廉价格使读者人群抵达底层工匠和手工业者。此外,1879年中国官场上“清流”的崛起,给《申报》提供了诸多“议政”的话题,形成体制内言路和体制外言路的交汇,使大批“学士、大夫”关注《申报》并成为其读者群。[18]到了甲午之前的1890年前后,上海士绅们很多养成了按日买阅《申报》的习惯。
《申报》的成功核心在于大规模的新闻报道和围绕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因此就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方针是从一创刊即开始而非随意的,如在发刊首月的言论中,就有《拟易大桥为公桥议》《拟建水池议》《团练议》《治河议》《拟请禁女堂倌议》等。[19]不仅涉及社会公众话题,且很多讨论无法回避地指向当局。这种讨论事实上试图将幕后的政治决策引向公开,而在此过程中,报馆和报人构建了体制外的影响力。特别是“杨乃武和小白菜”等一批报道挑战旧有政治制度(司法),官员已经无法不关注这个报纸的观点。包括租界工部局在内,在公家花园对华人开放等多次事件中迫于《申报》舆论而做出让步。
《申报》形成的“体制外言路”,这种所谓的“议”与传统的“清议”明显有着重大的区别。对读者和民主来说,这种议论有一种权利的暗示,即包括官方政治在内,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甚至参与的,而渠道就是报刊。这种议论由于其相对独立,一开始就带有批评和压力,而官方的回应和民众的反馈,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对传统权威的去魅,在此过程中报刊则日益多了“权力”的面貌。
在近代报刊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申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示范作用。西方学者特别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一批研究引人关注,他们认为《申报》已开始构建了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舆论”,当然对此学界尚有争议。不过不能否认,《申报》对晚清报刊舆论的形成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与《循环日报》等不同,《申报》的讨论或议论、批评最大的力量在于其巨大的读者人群及讨论的日常性,这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种自身权力建构的成功。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新闻报道无不带有选择和评价,而讨论的题材和结论,也为社会设置了议题。《申报》开启的舆论势力,是一种典型的近代报刊产物。
四、余论:甲午后媒体精英的出现
早期效法西方的报人如王韬、伍廷芳、陈蔼亭、蔡尔康等,很多具有秀才的身份,较之传统印象中低贱的报人,“身份”已大为改善,得以初步去污名化。不过总的来说,此时报人地位仍处政治权力边缘,直到甲午之后随着梁启超等高级士人的加入,报人作为新精英形象才开始在历史舞台呈现,后者塑造了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政治家报人形象。
甲午后登场的办报者如康梁等与政治权力中心也更加接近,更具有影响力。在《时务报》等精英报刊出现后,报人地位大为提升,舆论的重要性也逐步为社会认识,报人地位和生存空间大大扩展。姚公鹤回忆称,“康南海、梁新会以《时务报》提倡社会,社会之风尚既转”“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前文人学子所不屑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信员”。[20]在此转变下,报刊和报人均出现了一段此后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精英气质。读书人办报由此转为所谓“政治家办报”,《时务报》即被认为是“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始”,[21]也有学者称为之精英报刊(elite press)[22]。人们注意到,这是一群新型的政治公众人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注释:
[1]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8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9,103
[3][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3
[4]许正林.中国新闻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79
[5][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32
[6]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J].学术月刊,2011(12)
[7]吴延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93
[8]另有研究称《申报》应为18篇.见马光仁.《申报》与新闻学研究[J].新闻大学,2009(2)
[9][12][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89
[10]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198
[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63
[13]英国新报之盛行[N].申报,1873-02-18
[14]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42
[15]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A]//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叟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99
[16]本报第一万号议[N].申报,1901-02-24
[17]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3
[18]王维江.“清流”与《申报》[J].近代史研究,2007(6)
[19]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89
[20]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132
[2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28
[2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