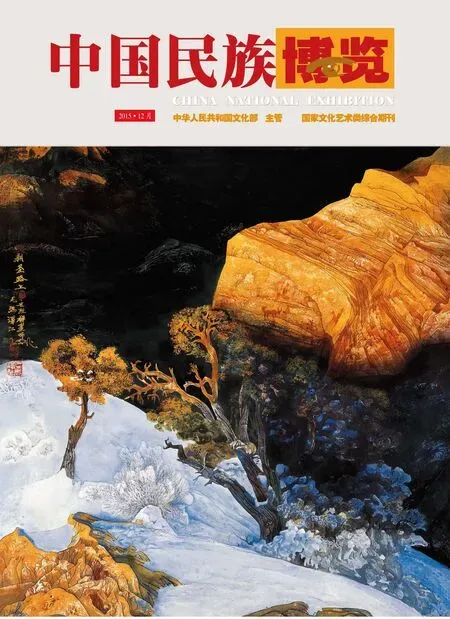明代瑞应现象刍议
2015-01-30孙良同
孙良同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明代瑞应现象刍议
孙良同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瑞应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代出现的各种瑞应以及人们对瑞应的看法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烙印,通过研究这些现象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些深层结构,追踪明代士人心态的变化轨迹并有助于对明代社会心理进行微观剖析。
明代;瑞应;瑞应观
瑞应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古人认为帝王修德,时代清平,就会有吉祥的征兆出现。这种吉祥的征兆称之为瑞应。《列子》《史记》等均有论述。虽然东汉王充对瑞应说进行过揭露和抨击,但是后世历朝帝王臣工依然对此津津乐道,甚至编纂出《瑞应图》等图籍,查考瑞应作为礼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被确定下来。
瑞应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综观历史上的各种瑞应现象,我们发现瑞应所关注的焦点在人世,尤其对帝王的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臣子也常常借助瑞应来对君王施加影响。具体到明代,瑞应以及人们对瑞应的看法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通过研究这些现象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些深层结构,追踪明代士人心态的变化轨迹,对社会心理进行微观剖析。
一
瑞应在明代各个时期出现的频度是有差异的,种类也稍有不同。这其中所展现出的更多是人们观念中的东西,而非自然现象。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与天下群雄相角逐,这一时期他需要大量瑞应以证明他才是唯一的真命天子,所以这一时期有关瑞应的记载很多。《明史》卷一写到朱元璋降生就不同凡响。“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之后各种神奇的现象屡屡发生在朱元璋身上,这些事情大多是无法验证的,上述红光盈室之事或可强拉邻里为证,母亲做梦之事恐怕只是朱元璋的杜撰。同时,朱元璋的属下同样需要证明自己所辅佐的是真正的明主,于是极力挖掘各种投射在朱元璋身上的瑞应现象,刘基堪称这方面的专家。甚至像常遇春也不例外。“(常遇春)独率十余人来归,未至,困卧田间,梦神人被金甲拥盾呼之曰:‘起,起,主君来!’忽寤,见上骑从至,即与其徒迎拜乞归附。”[1]按理此事只能出自常遇春自己的陈述。可以说双方共同的需要为瑞应创造了广阔的市场。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待瑞应的态度有所转变。各种瑞应虽也时有禀告,但他似乎并不像当初那样热心。洪武二年(1369)十月甘露降于钟山,群臣请告庙,朱元璋不许。(《明史》卷二)在朱元璋时代的瑞应记录中,有两次是值得关注的,即至正十七年(1357)五月,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明史》卷一)和洪武六年(1373)六月,盱眙献瑞麦,(《明史》卷二)朱元璋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甚至“荐宗庙”。这反映出一个布衣皇帝难以割断的农民情结。
朱棣即位之初,也面临着收拾人心的严重局面,要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作为正统的资格必须凭借上天的瑞应,所以永乐初年的瑞应记录异常频繁。永乐二年(1404)九月周王献驺虞,十二月黄河清。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接连出现了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青鸾群集、白鹤重临、神人效祝、宝盖随车、庆云捧日、瑞雪迎腊等一系列瑞应。《明史》卷九十七所载《瑞应图说》也是在永乐中编次完成的。总体来看,朱棣对待瑞应还是比较冷静的,十七年(1419)九月,“庆云见,礼臣请表贺,不许。”(《明史》卷七)另外,永乐四年(1406)六月,南阳献瑞麦,谕礼部曰:“比郡县屡奏祥瑞,独此为丰年之兆。”命荐之宗庙。(《明史》卷六)此外还有嘉禾、野蚕作茧等记录。可以看出朱棣对农业生产的关心。
第三个瑞应出现频繁的时期是嘉靖朝。嘉靖皇帝是以藩王之后得继大统,其正统地位自然易受到人们质疑。瑞应的效用再一次得到发挥。加之皇帝崇信道教,喜闻祥异,大小臣工更是极力挖掘瑞应之物来进献,以致芝草成山,白鹿、白龟之类更是累见叠出。
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这三个阶段成为明代历史上瑞应现象相对集中的特殊阶段。
二
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多取积极的态度,但作为臣子必须借助皇帝才能获得机会。文人常拿瑞应来做敲门砖,因此瑞应现象往往可以显示文人精神状态。
明初宋濂是金华学派的正宗传人、明初各项制度的重要参与者,对瑞应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读到。洪武二年(1369)冬十月十有三日,膏露降于乾清宫后苑苍松之上,朱元璋特命中官折示禁林诸臣。第二天,左丞相李善长率群臣称贺。有的称是“陛下恭敬天地,辑和民人,故天不爱道而嘉祥徽显”,有的认为“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也有的说“陛下养老之所致”。等到众人退去,宋濂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肯定这是“天人感应之恒理”,并对朱元璋匹马渡江十五年成就帝业加以颂扬。他说:“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书,……皇上以天纵之圣,留神至治,以得仁贤为瑞,以五风十雨为祥,视彼前代植金茎以承液,夸嘉瑞以纪年者未尝不指以为戒,则其英明之识超绝之智卓冠百王,为法万世。”[2]虽然宋濂很注意讲话的策略,但他的讽谏之意还是很明显的。洪武六年(1373)正月,朱元璋召御史中丞陈宁和太子赞善大夫宋濂谈嘉祥之应,并敕中贵人取所储膏露,赏赐二人。二人自然是极口称颂。关于瑞应之事,宋濂进一步强调了“王者有德”才是前提。
作为开国功勋,宋濂等人要为新王朝制造一张巨大的意识形态之网,而他们构设的统治之网也许罩住的是自己,最终这些开国谋臣或被杀头或被流放。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下,这些解读瑞应之谜的人,并不能借助皇帝赏赐的甘露“去沉疴而衍遐龄”,文人的理想和他们的命运一起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需要新生力量的加盟。
洪武十六年(1383),方孝孺被征召入京,他献给皇帝的作品是《灵芝甘露论》,在文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瑞应观。“圣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征。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臣闻天地于祯祥之类,非唯见于物,亦间见于人,故物有非常之质,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仅可为太平之征,非常之才实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圣人尤贵之重之。[3]
可见,方孝孺是在借助瑞应之说向皇帝进言,希望皇帝尊重人才。当时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动基本完成,专制集权达到极致。方孝孺的《灵芝甘露论》隐含着他对文人命运的忧虑,他以豪杰自居也许正是要充当文人及其理想的代言人。朱元璋或许领会到方孝孺的用意,但他恐怕也知道自己不能用方孝孺,所以赐宴后就把他打发回家了。数年后方孝孺被酷肖朱元璋的朱棣灭了十族。
朱棣登基,瑞应叠现。洪武建文间留下的旧部和永乐朝得官的新人,似乎组成一个合唱团,这一团体的保留曲目就是“瑞应颂”。永乐十八年(1385)定宴飨乐舞。《集祯应之曲》云:“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兆太平;驺虞出现甘露零,野蚕成茧嘉禾生,醴泉涌地河水清。乾坤万万年,四海永宁。”(《明史》卷六十三《乐志》)在众多明人别集内我们也能读到类似的作品。比如黄淮有《神龟诗》,高得旸有《河清颂》,陈敬宗有《瑞象赋》《麒麟赋》等,当然也少不了《圣孝瑞应诗》或《圣孝瑞应颂》。借助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台阁文学的底色,即专制政治下文人自我的萎缩。在这些文人身上我们不能苛求方孝孺那样的豪情,但从他们这种近似抽成蚕蛹的状态,我们偶尔也能感觉到生命活力的存在,他们是文人,是特殊时代的文人,命运注定他们必须为瑞应唱赞歌,文人未来的命运也许正期待着破茧化蝶的一天。
到王阳明时,文人终于找到了突破的机会。王阳明是一个重视事功的人,也确实为明王朝立下了特殊功勋。他长期不在皇帝身边活动,恰能获取一定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空间,当然也就不必努力去唱“瑞应颂”了。心学注定不是皇家思想苑囿里的灵芝或麒麟,它是一只蝴蝶,它的翅膀要承载文人的理想。它会飞到皇家的花园,也可以飞到市集与田间。
徐渭是季本的学生,季本是王阳明嫡传。他几经磨难最终只能到胡宗宪幕下为宾,在他生活的年代,瑞应仍旧发挥着独特作用。今见于《徐渭集》的《代进白鹿表》《代再进白鹿表》等在当时不仅为胡宗宪换得厚赐,也让徐渭的作品能上达天听,使他匡国致君的理想得到一些寄托。历史已经注定文人最终不能脱离皇帝的苑囿,文人的真正觉醒还需要一段艰难而痛苦的历程。甚至在皇帝的花园已经荒废,蝗虫横飞时,文人依然眷恋着这块土地。可以说,文人是否关注瑞应以及怎样去看瑞应,反映出文人的特定精神状态。
三
古代对瑞应的记录大多和人事结合起来,事件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因果的关系。如《明史》卷六记载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乐观,荐之太庙,赐百官。十二月辛卯,赦天下殊死以下。张辅大破安南兵于嘉林江。丙申,拔多邦城。丁酉,克其东都。癸卯,克西都,贼遁入海。”这一机制的形成也许是瑞应现象长期存在和被利用的思想根源。
明代对瑞应的操控权往往体现了当时政治权利的重心所在。朱元璋对瑞应是一种绝对掌控,他可以主动发现或者制造瑞应而让群臣响应,还可以把所谓上天降下的甘露分赐臣下,真正一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的姿态。后来者虽然也常效法他,但往往不能左右臣下对瑞应的控制,有时群臣称贺,连皇帝也不耐烦了,有时是臣子制造瑞应,欺骗皇帝。嘉靖晚期,瑞应基本成为佞臣用来拍皇帝马屁的一张王牌,《明史》卷三百七记载:“(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降一桃。”稍加思考就能知道肯定是身边的中官搞鬼,但迷信的嘉靖其心思已被左右牢牢掌握住,用瑞应蒙骗皇帝不仅不会获罪还能得到许多赏赐。至于像严嵩那样的权臣甚至可以借助瑞应操纵国柄谋取更大的利益。
当瑞应大量涌现时,其神秘性和特权品格逐渐丧失。一些瑞应也悄悄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出现。比如晚明时期的陈洪绶,在他降生之前,有个氅衣鹤发的道人,手持一莲子送给他的父亲,故陈洪绶幼名莲子,及老称为老莲。[4]陈洪绶的降生与命名或许更多寄托了他父亲的期望,但也会对陈洪绶产生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以降生的不俗来创造不俗的人生。连中三元的商辂的降生也被赋予神秘色彩。明周清原《西湖二集》第十八卷《商文毅决胜擒满四》写到商辂的父亲商提控搭救蒙冤的吉二,并且拒绝吉二夫妻的报恩,于是得到上天眷顾。商辂降生时也是“满室火光烛天”[5]这和明太祖朱元璋的降生几乎一样。从故事的逻辑来看商辂父亲的积德行善是诱发这一事件的起因。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大概人们对三元及第的艳羡才是产生这一故事的真正诱因。
总之,明代瑞应现象所蕴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观察明代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1]明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8.
[2]宋濂.宋学士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3]方孝孺.逊志斋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4]陈洪绶.陈洪绶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586.
[5]周清原.西湖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99.
G09
A
孙良同(1970-),男,河北阜城人,文学博士,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得到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13&ZD116)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