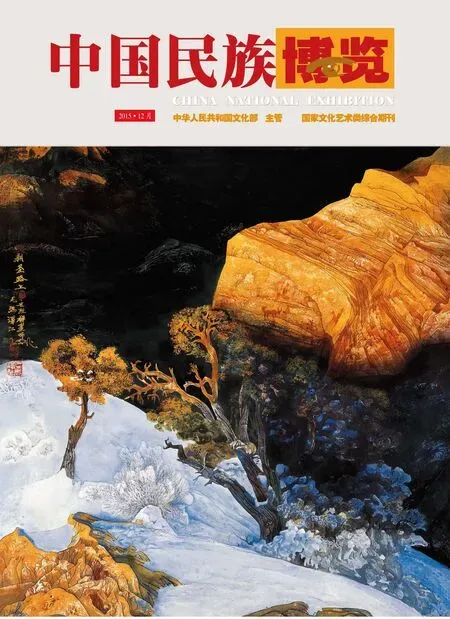民间信仰与社区整合
——以鲁中H村为个案
2015-01-30曹龙骋
曹龙骋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民间信仰与社区整合
——以鲁中H村为个案
曹龙骋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力量在农村地区的消隐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于民众生活实践的民间信仰活动重新获得了生存的空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构建村落生活秩序,民众纷纷将民间信仰活动作为一种熟知的知识加以改造利用,一时间,民间信仰的复兴成为农村社会的潮流。本文通过对鲁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庙宇重建的考察,分析了当代社会语境下民间信仰活动的复兴对于村落的整合意义。
村落个性;庙宇重建;社会整合
一、村落:传统的载体
H村位于鲁中山区,具体建村年代不详,据村民介绍,H村古为仙河、仁河、河东三个自然聚落,后统一划并为行政村H村。该村以丘陵和平原地貌为主,地势东高西低,村东为大片丘陵,村西则相对开阔,与镇中心罗村村相邻,居民大多聚居于此。该村煤炭、石料等自然资源丰富,90年代,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H村凭借其富饶的矿产资源,率先办起了水泥厂、机械厂、煤矿等集体企业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H村也因此成为镇上第一批发展起来“富裕村”之一。虽然村落经济较为繁荣,但H村民并没有因此而飞扬跋扈,相反,受邻近“文化村”洼子村的影响,H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保持着老祖宗的规矩,“凡事讲个理,凡事按个礼”一直是H村民的行动规范和准则,“礼”已经内化的村民的意识观念之中,并成为村落绝对的权威。
二、村庙:村落个性的神圣象征
石大夫庙位于村西北,是一座专属于本村的信仰场所,并且具有自己村落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村内流传的传说上。村里老人记忆说,“村里的石大夫庙源自于洪山镇,当时是明初,朱洪武坐殿,大杀山东,有一队官兵来到村落时突发兵瘟,村里人为其到嬷嬷幢请药,当他们祭拜石大夫时,忽然天降大雨,村民们以为是石大夫显灵,于是就接了雨水回到村里,官兵喝下雨水之后果然痊愈,他们感激H村民的救命之恩,没有屠村,并且在村里建下石大夫庙,以示感激。”还有一种说法是,“石大夫云游四方时途经村落,当时村里正爆发人瘟,石大夫便救治村民,村民感激石大夫的救命之恩,于是在村落的西北边为其建庙,供奉香火”。无论哪种传说似乎都表明,石大夫对全村具有救命之恩,村民将其视为村落的守护神而加以供奉,凝聚了村落的集体情感。
其次表现在石大夫庙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七张八王十二刘”这是流传于H村的一句俗语,而在这句俗语中,“七、八、十二”并不是指这三个家族人口多,而是指其房支众多,他们虽然是一个姓氏,但并非一个宗族,自明代迁移到H村之后,他们便定居于村落的不同聚落,并建立宗庙,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据村民说,H村先后有“关帝庙”“菩萨庙”等十多座寺庙,自此之后,石大夫的信仰中心地位逐渐衰弱,只有原住的家族依然祭拜石大夫。随后在村落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家族之间的融合以及对村落共同秩序的需要,各家族又重新确立了石大夫庙的信仰中心地位,清代光绪年间,张、王、杨等几个大家族联合对石大夫庙进行修葺,各家族轮流主持祭祀活动,围绕着石大夫庙而建立起来的村落公共秩序逐渐得到确立。
刘铁梁教授指出村落不能失去自我,因而特别依赖庙会。庙会的特征代表着村落历史上形成的个性,因此它才能作为村民自我认同的标志,整合村民的集体情感。石大夫信仰在历时性的变迁过程中几经兴衰,但始终没有中断,在村民们的解释中,石大夫庙具有H村守护神和维持村落秩序的双重含义,它早已融入到村民的记忆与村落的实践之中,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村落内部,石大夫庙是村民对村落一体感的认同标志,对于村落外部,它则凝聚了村落个性的象征文化。
三、庙会:村落的非常形态
2015年农历四月初八,H村迎来了一场属于自己村落的盛会,历经6个月工期的石大夫庙重修竣工,举行盛大的开光仪式。重修过后的石大夫庙坐北朝南,方正端庄,这个建筑用料讲究,朱漆红墙,画栋雕梁,庙门石匾上的“石大夫庙”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简雅素朴而又不失宏辉气势,而庙内布局错落有致,进入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郁郁青松,象征庙宇清雅脱俗,其后为主殿“石大夫殿”,殿中有三座神像,其中“石大夫”神像(高2.6米,宽1.3米)坐于中间,“石娘娘”“石哥哥”神像分立其左右,而在主殿的两侧分别为“观音殿”和“关帝殿”。庄严神圣的寺庙气氛不仅预示着村落不寻常的一天,而且村落自豪感和认同感也逐渐在民众中显现出来。
开光仪式在早上五点钟举行,仪式主要是在庙院内进行,在此期间庙门禁闭,村民不准入内观看,往日里习惯了看热闹的村民们不但没有丝毫怨言,还都停止了喧闹,安静地驻足于庙外等待。在这种神圣的情境中,仪式成为村落的主题,仪式专家成为村落的英雄,而村民对于石大夫庙的集体认同则是仪式专家的权威基础。八点钟,随着庙门一开,开光仪式宣告完成。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刚刚还异常安静的人群瞬间变得欣喜若狂,一扫之前的担心、焦虑,迸发出一股巨大的激情,早已等待多时的秧歌队也随着锣鼓声欢快地扭动起来,庙外空地上的小商贩也活跃了起来,纷纷叫卖他们的商品,一时间,锣鼓声、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种狂欢的气氛之中,村民们打破平日里的身份地位差异、抛开往日的间隙矛盾,共同载歌载舞,沉浸在村落的这一场盛会之中。此时,村落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集体力量的存在。
开光仪式当天,邻近十多个村落的信众也以村落为单元组成香会前来赶会,为石大夫老爷表演“献轿”仪式。各村的献轿仪式大同小异,一般是由会众两两一排组成方队,会头在前举香请神,而后是队伍两侧各有三人打幡旗、举花轿、其后的会众则统一用包裹着红绸的扁担挑着元宝树或祭祀品,整个队伍统一身着绣有荷花图样的粉红色布衣,腰缠绿绸。方队在离石大夫庙100米的路口处集结完毕之后,锣鼓队开始奏乐,而会众则随着锣鼓的节奏,迈起舞步,扭动身姿,向石大夫庙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会头走几小步就要磕头作揖,而会众则要配合着锣鼓的节奏上下晃动扁担,使元宝树翩然若飞。富有节奏的锣鼓声、轻盈欢快的舞步和上下翻飞的金银树相得益彰,整个方队融为一体,极富艺术美感。“献轿”仪式的这些表演多由普遍存在于村落之中的民艺活动组合而成,但在庙会这一情景之中,它又不是单纯的文艺表演活动,而被赋予了一层村落的含义。参会的各村香会之间普遍存在于一种竞争关系,他们力争用更好的表演去展示村落形象,提升村落荣誉,可以说,庙会活动已经不只是信仰活动,更是各村落展示其文化形象的平台。由于各村的献轿仪式大致相同,因而他们通常在锣鼓的声响、队伍人数以及步伐的整齐度上相互竞争。
詹森认为,“民俗不仅在同一集团的认同中,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而起作用,而且在形成或确定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态度上,作为一种分裂力量而起作用”。对于前来参会的邻村会众来说,竞争不仅只存在于表演献轿仪式的村落中,而且对于石大夫庙以及这次庙会的“主家”H村,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认同感。她们在羡慕石大夫庙修建的如此气派的同时,也遗憾自己村子里没有能力修庙,而且对于石大夫信仰她们则不甚了解,认为自己村落的庙才是最灵验的,一般她们在表演完献轿仪式之后就会迅速离开,这与H村民对于石大夫庙会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石大夫庙会始终是H村自己的活动,只有H村民才能感受到其对于村落的象征意义,并对它产生认同感,从而实现村落的整合。
四、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重建庙宇成为农村社区的一股潮流。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民间信仰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信仰活动,而且被赋予一种村落象征的含义,村落通过重建象征符号来表达村落的共同利益,实现村落的整合。但对于村际关系的整塑与认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B933
A
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Yxm201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