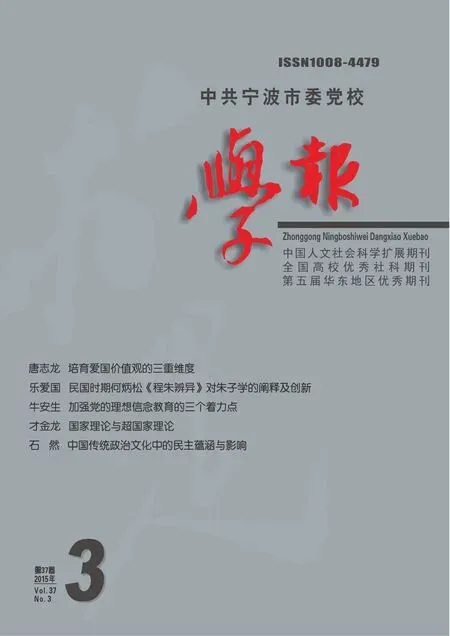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对朱子学的阐释及创新
2015-01-30乐爱国
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对朱子学的阐释及创新
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从中国学术思想有儒道佛三家而将宋明理学划分为程颐、朱熹和陆王三大派入手,深入分析朱熹与程颐在师承、哲学与经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的二元哲学以及“理必有对”的思想,分析了朱熹的心学以及与“穷理”的关系,并对朱熹与道家关系作了论证。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或是重要的补充和推进,或是一种纠偏,无疑是重要的学术创新;而且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何炳松;《程朱辨异》;朱子学
民国学人何炳松(1890~1946)以研究史学而著名。1928年,他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并且认为,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于是,他首先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学说,同时也研究程颐、朱熹、陆九渊三家的学说,而且专门就朱熹与程颐的异同作了深入的研究。1930年,何炳松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四期发表了近10万字的长篇论文《程朱辨异》;在此基础上,又于1932年出版了《浙东学派溯源》。[1](p8~9)对于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而言,何炳松的《程朱辨异》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重要的是,他的一些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对程朱异同的辨析
关于朱熹之学与二程的关系,一直有学者认为,程颢与程颐之间存在着学术思想上的差异,朱熹较多地继承程颐。陆九渊早就指出:“元晦(朱熹)似伊川(程颐),钦夫(张栻)似明道(程颢)。”[2](p413)后来的黄宗羲也说:“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3](p542)显然,这里既讲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认为朱熹的学术与程颢有所不同。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更名为《论性》)在论述宋代心性论的发展时,明确讲“朱子继伊川之说,而主张理气之二元论”[4](p34~35)。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指出:“伊川与明道,虽为兄弟,而明道温厚,伊川严正,其性质较然不同,故其所持之主义,遂不能一致。虽其间互通之学说甚多,而揭其特具之见较之,则显为二派。……其后由明道而递演之,则为象山、阳明;由伊川而递演之,则为晦庵。”[5](p164~165)这里明确认为,程颢与程颐分为两派,后来分别发展为陆王之学和朱子学。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也指出:“陆王学派,近于明道;朱子学派,近于伊川。”[6](p32)1926年,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儒家哲学》,其中指出:“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7]1929年出版的周予同《朱熹》认为,朱熹的学说“发挥小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直有舍大程(颢)而追小程(颐)之概”[8](p114)。显然,在何炳松《程朱辨异》发表之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熹的学说源于程颐,朱熹与程颐同属一派。
与此不同,何炳松《程朱辨异》专门就朱熹与程颐之间的学术差异展开深入讨论,其观点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何炳松认为,程朱的师承不同。他指出:“程氏的学说大都出于胡瑗和他的哥哥程颢。至于邵雍的数学、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性气二元论,程氏都绝口不谈。至于朱氏生平所最倾倒的而且亦最主张的就偏是上面这几位的学说;而他对于胡瑗反独不佩服。……这可见程朱两人的师承不但不同,而且相反。”[9]
第二,何炳松从“哲学上的各种基本观念”、“哲学上几个重要的问题”、“方法论”三方面,具体分析程朱哲学的不同,并且得出结论:“程氏主张万物一理,没有什么大小、内外、本末、先后、远近等等相对的关系,……是一个一元的、客观的、唯物的哲学家。朱氏一方面亦主张万物一理,但是他一方面又主张理必有对,对于体用、动静、本末、先后等等相对的关系,一概认为可以成立,……是一个‘太极图’式的二元的、主观的、唯心的哲学家。”[10]
何炳松还说:“程氏既然是一个一元的哲学家,所以他对于我国哲学上许多名词——理、性、命、心、天、神、鬼、道、情、气等——都认为同一个东西。……朱氏既然是一个‘太极图’式的二元的哲学家,所以他对于我国哲学上许多名词,要把他们一一分别开来”;“程氏既然是一个客观的哲学家,所以他主张凡是事物的理就是我们的性,我们只要格物就可以至于圣人,因此格物的工夫比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还要重要。朱氏既然是一个主观的哲学家,所以他以为求理于物,无绪可寻,求理于心,则有定体,因此我们必须先求放心再去格物”;“程氏既然是一个唯物的哲学家,所以他的方法论主张持敬,所谓持敬就是集义,集义就是格物,格物就是穷理,穷理就是穷尽事物的所以然;因此我们只要把事物一件一件格去,积累多了自然豁然贯通。朱氏既然是一个唯心的哲学家,所以他主张持敬和集义完全是两段工夫,我们应该先做持敬的工夫,再去集义;所谓集义就是用我们的心去辨别事物的是非。总括地说:程氏的方法就是现代所谓客观的归纳法,朱氏的方法就是现代所谓主观的演绎法。”[10]
第三,何炳松还分析了程朱在经学上的差异,尤其在《易经》以及《春秋》、《诗》、《礼》上的不同态度。他指出:“程氏说《易》主理,朱氏说《易》主数;程氏以《春秋》为圣人断案的书,朱氏以《春秋》为直载当时之事;程氏说《诗》宗《序》,朱氏说《诗》反《序》;程氏对于三《礼》半信半疑,朱氏对于三《礼》大体相信。”[10]
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朱熹与程颐的关系,既要关注二者的相同之处,也要探究二者的差异。朱熹曾论及自己的学说与程颐的差异。他说:“某说大处自与伊川合,小处却持有意见不同。”[11](p2359)朱熹还在评论程颐之学时指出:“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莹彻,于小小节目上犹有疏处。”[11](p2542)此外,何炳松还特别指出,明末的刘宗周、清初的黄宗羲、纪昀和清末的皮锡瑞等都就朱熹与程颐的不同提出过问题,而且,“明代的汪俊对于程朱不同这个问题尤其有相当的研究”[9]①。
事实上,民国时期也有学者对朱熹与程颐的学术差异做过探讨。周予同的《朱熹》说:“就哲学言,朱熹为程颐之继承者,故治思想史者每以程、朱并称;顾就经学之《易》学言,则程、朱不无敌派之嫌。”[8](p54)1936年,白寿彝发表的《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就周予同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朱熹虽很尊敬程颐,却并不一定无条件地接受后者的一切学说和见解。朱熹对于程颐《易传》的看法,并不是以它‘偏于义理’,而是以它的办法根本上有点不对。”[12]认为程、朱易学的差异不只是在于程颐“偏于义理”,朱熹“济以象数”,而是在朱熹看来,程颐《易传》在根本上不合《周易》之本义。
后来,陈荣捷发表《新儒家范型:论程朱之异》[13],徐复观发表《程朱异同——平铺地人文世界与贯通地人文世界》[14],杨向奎发表《程朱哲学思想之异同》[15],先后讨论过朱熹与程颐的关系,涉及二者的学术差异。但总体而言,学术界称朱熹与程颐同属一派者多,探究二者差异者少;而且探究朱熹与程颐的差异者,主要集中于朱熹与程颐在易学上的差异。应当说,何炳松《程朱辨异》对于朱熹与程颐之间的学术差异的研究,不仅限于易学,而且扩展至经学乃至全部学术,因而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于今天探讨朱熹与程颐的学术关系只是关注二者的一脉相承,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对朱熹二元哲学及“理必有对”的阐释
在何炳松《程朱辨异》看来,朱熹与程颐在哲学上的最大差异是:程颐是一个一元的哲学家;朱熹是一个二元的哲学家。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把朱熹哲学界定为二元论,并非何炳松为先。如前所述,王国维《论性》已经讲朱熹主张理气二元论。后来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也明确指出:“朱子既以理搭于气而行,又谓理气不可分先后,盖认理气为决然二物,此所以名字为理气二元论也。”[6](p57)此后,不少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周予同《朱熹》则认为,朱熹既主于太极一元论,即理一元论,又主于理气二元论,“实为一元的二元论者”[8](p21)。重要的是,何炳松《程朱辨异》对于朱熹二元思想的分析,不仅仅限于理气二元的关系,而是做了更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入阐释。
何炳松认为,朱熹的二元论主要表现为“因阴阳之说而有理必有对的见解”[9]。据《朱子语类》载,问:“‘天下之理,无独必有对。’有动必有静,有阴必有阳,以至屈伸消长盛衰之类,莫不皆然。还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来如此,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且如碁盘路两两相对,末梢中间只空一路,若似无对;然此一路对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谓一对万,道对器也。”[11]2435对此,何炳松认为,朱熹所谓的“一中又自有对”、“独中又自有对”、“二又各自为对”,把程颐主张“万物一理”的一元论“完全推翻”[9]。何炳松还认为,朱熹讲“理必有对”,因而“把道和器分成明明白白的两橛”,而且在朱熹那里,“一切事物都有体用、阴阳、动静、先后、本末等等的关系,最后归结到先本后末,先始后终”[9]。
何炳松认为,朱熹的二元论还表现在“把心和性情都分别开来”[9],“把道和性分得很清楚”,“把性和命亦分成两件东西”,“把道和理分别开来”,“把意和志分别开来”。[9]何炳松还认为,朱熹不仅主张理气二元论而讲性气二元,“把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相对举起来”[16],而且还将《中庸》的“已发”和“未发”“双双对举”,“把知和行完全分成两橛”[16],“以为主敬是主敬,集义是集义,完全是两段工夫”[17]。
由此可见,何炳松把朱熹哲学界定为二元论,主要是就朱熹所谓“理必有对”而言,是指朱熹哲学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而不仅仅限于朱熹的理气二元论。
对于朱熹所谓“理必有对”,学者一直少有关注。1937年,张岱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其中特别注意到朱熹的“两一”思想。他认为,在朱熹看来,“一切莫不成对,更无孤立之物。对乃理之必然,理是对之所以。事物固有其对,而绝对之本根,亦与相对者为相对”,并特别引述以上《朱子语类》所谓“一中又自有对”、“独中又自有对”,指出:“不只有外的对待,更有内的对待。此物与彼物为对,而一物之中亦有对。一之中有其二,独之中有其对,即今所谓内在的矛盾。凡一体之中,莫不有其对待。”张岱年还进一步认为,在朱熹那里,“两是变之所以,宇宙中一切充满了两,故万变万化无有止息了”,“凡一固皆有其两,凡两亦皆有其一,一切对立其实是一体的”,所以,“凡对待都是合一中之对待,而非只单纯的对待而已。对待莫不合一,合一莫无对待。没有绝然无两的一,亦没有绝然不一的两。一而两,两而一,乃万物之实在的情状”。[18](p139~141)
应当说,张岱年所述朱熹的“两一”思想,实际上包含了所谓朱熹的“理必有对”。不过,在何炳松看来,朱熹的“理必有对”是“极有趣味而又毫无根据的朱氏‘相对论’”[9],与程颐的一元论完全相反;而在张岱年看来,朱熹的“两一”思想,“与西洋哲学之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统一原则,极相类似”,因而大加推崇。但无论如何,从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过程看,在张岱年概括出朱熹“两一”思想之前,何炳松已经在论述朱熹二元论中揭示出与之相关的朱熹“理必有对”思想,因而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
三、对朱熹心学以及“穷理”的分析
民国时期,学者探讨朱熹哲学本体论,既讨论朱熹的理气论,又研究朱熹的“理”与“心”的关系。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的《朱子学派》认为,陆九渊以及后来王阳明的“心即理”说,与朱熹讲“心、性、理之一贯”以及“理在心中”,“无以异矣”。[19](p118~119)1925年,黎群铎发表的《晦庵学说平议》在讨论朱熹心性论时认为,在朱熹那里,“理与心并不是两件事”[20],“无论站在唯理主义的旗帜下,或是客观唯心派的旗帜下,都可以成立”[20]。1927年,黄子通发表的《朱熹的哲学》则认为,朱熹的“心”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理”,还说:“朱熹所讲的‘心’,程明道所讲的‘仁’、‘性’,周敦颐所说的‘诚’,皆是异名而同实。……朱子的意思,就是宇宙的本体即在我心之中。我心以外,并没有超心的本体。”[21]显然,这些学者都把朱熹作为宇宙本体的“理”与“心”看作同一的。黄子通还引朱熹所言“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指出:“这几句话,就是说凡是情、意、志所做的工作,就是‘心’做的。”[21]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读为心的活动。
在何炳松《程朱辨异》看来,程朱在哲学上的差异,不仅有一元与二元之别,而且还是客观唯物与主观唯心的对立。何炳松认为,朱熹接受张载“心统性情”的主张,“把心看得特别重要,认为是一切的主宰”[9]。他还引朱熹所说“人之一心万理具备”,指出:“人心之中万理具备,所以我们应该把心当作主宰。”[17]为此,何炳松特别讨论了朱熹对于养心的重视,并认为朱熹对于养心有两个见解:“第一就是‘理是心中所有’,第二就是‘常存此心以观众理’”[17]。他还认为,在朱熹那里,“理是我们元本就有的,不是外面的物事,所以他以为所谓穷理并不是穷物的理,实在是穷人的心”[17],“朱氏既然主张理是我们自身本有的,所以不必向外物去求得来。”[17]
正是通过这些分析,何炳松认为,朱熹主张人之一心万理具备,如同明镜一样能够照见事物的是非,因此是主观的哲学家;“他又主张凡百事物都应该先本后末,先始后终,我们为学做人都要以培养本原为主,因此我们又要称他为唯心的哲学家。”[10]何炳松还认为,作为主观的哲学家,朱熹以为“求理于物,无绪可寻,求理于心,则有定体”,因此必须先求放心再去格物;作为唯心的哲学家,朱熹主张持敬和集义完全是两段工夫,应该先做持敬的工夫,再去集义,而所谓集义,就是用我们的心去辨别事物的是非。
事实上,朱熹讲“理”,既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又讲“人之一心万理具备”;朱熹讲“穷理”,既要穷物之理,又要穷心之理。所以朱熹说:“要知学者用功,六分内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难,若六分外面,则尤不可。”“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11](p406)何炳松只是强调朱熹所谓“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认为朱熹的“穷理”是“穷人的心”,这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
在何炳松《程朱辨异》之前,胡适于1919年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更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对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作了阐释,认为朱熹所言“即物而穷其理”,是指“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胡适说:“这便是归纳的精神。”还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22](p366)此时,何炳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与胡适多有交往。1924年,何炳松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并于1928年因研究中国史学史而涉及程朱理学,有所心得,而与胡适书信交流。②应当说,何炳松认为朱熹的“穷理”是“穷人的心”,很可能正是针对胡适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
何炳松《程朱辨异》对于朱熹“穷理”的阐释,只是强调其“穷人的心”,虽然有所偏颇,但对于当时学术界在胡适影响下过多强调朱熹“穷理”只是在穷物之理而言,不失为一种矫枉过正。
四、对朱熹与道家关系的论证
陆九渊说:“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2](p16)对此,何炳松指出:“陆氏此地一口认定中国的学术不出儒道佛三家,这是很合事实的一句话。我们就历史上看来,儒道佛三家鼎峙的局面不但在北宋以前是如此,就在南宋以后亦是如此;不但在中国的思想上是如此,就在文化上亦是如此。总而言之:儒道佛三家既是中国学术思想上三个最大的潮流,亦是中国文化上三个主要的元素。”[9]重要的是,早在1928年,何炳松就依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儒道佛三家而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三大派,即:“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王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1](p6)何炳松《程朱辨异》则明确称程颐是一个正宗的儒家,朱熹是一个“儒化”的道家,并且特别对于后者做了论证:
何炳松认为,朱熹崇拜邵雍,“极端的赞美邵氏的数学”,“倾心邵氏的先天卦位图”,而据黄百家所说,“先天卦图传自方壶”,为道家术士所推崇。因此,“朱氏的以数说《易》,无非接受邵氏的道家言。这是朱氏属于道家的第一个证据”。[10]
何炳松又认为,朱熹全盘接受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氏本身的哲学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太极图’的发挥”,而周敦颐所得“太极图”传自道士陈抟,据黄宗炎所说,“周子‘大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实与老庄之长生久视又属旁门”,所以,周氏的《太极图说》是道家的学说,“朱氏竟全部的接受,多方的辩护。这是朱氏属于道家的第二个证据”。[10]
何炳松还认为,朱熹接受张载的“性气二元论”,并大加发挥,而据杨开沅所说“成性之说始于董子《天人策》”③,由于“现代我国的学者差不多都承认董仲舒为道家者流,甚至有人叫他为董道士”,据此,“张氏所唱的和朱氏所受的性气二元论岂不亦是一种道家者言么?这一点或者亦可以拿来当做朱氏属于道家的第三个证据”。[10]
此外,何炳松还说:“朱氏生平并亦深信神仙和阴阳五行等等道家的玄谈,我们亦可以把他们拿来做—个小小的旁证。最后朱氏还有一件有趣的轶事,……据纪昀说,朱氏曾经以‘空同道土邹’的寓名撰了一卷《周易参同契考异》。”[10]
尽管在今天看来,何炳松把朱熹称为一个“儒化”的道家,可能很难被学术界所接受,而且他所做的论证也并非足够严密,但是,把道家思想看作是朱熹学术思想的来源之一,强调朱熹与道家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既是对过度强调朱熹学术思想只是来源于程颐的一种纠正,也是对朱熹学术内涵特点的一种理解。朱熹曾出入佛老,他学术思想融儒、释、道于一体,其中包含了诸多的道家思想,而且这仍然是当今朱子学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
结论
何炳松《程朱辨异》从中国学术思想有儒道佛三家而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三大派入手,深入分析朱熹与程颐在师承、哲学与经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大创新。何炳松自己也认为,他的这一“大胆的主张”,是针对当时学术界认为宋明理学只有两大派,即程朱一派的道学和陆王一派的心学,而提出来的,为此,“他竟大胆的把南宋以来我国学术思想只有程朱和陆王两派的说法完全推翻,主张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旧,演成程、朱、王的三大派。并且因此竟大胆的把程朱两人同属一派的说法根本打倒,把两人的思想加以分析,表明他们的思想根本不同”[1](p7)。
正是在分析程朱思想之不同的过程中,何炳松对朱子学作了深入的阐释,讨论了朱熹的二元哲学以及“理必有对”的思想,分析了朱熹的心学以及与“穷理”的关系,并对朱熹与道家关系作了论证。应当说,何炳松《程朱辨异》对于朱子学诸多方面的讨论,都是针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而展开的,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其中强调朱熹与程颐的差别不仅在于易学,而且在于整个经学乃至全部学术,认为朱熹哲学中具有“理必有对”的思想,强调朱熹所谓“人之一心万理具备”以及“穷理”必须穷人的心,强调道家思想是朱熹学术思想的来源,这些讨论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或是重要的补充和推进,或是一种纠偏,无疑是重要的学术创新。当然,其中难免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善和欠缺,尤其是在今天看来,何炳松《程朱辨异》认为程颐与朱熹的差异在于一元与二元、唯物与唯心的对立,认为朱熹的“穷理”并不是穷物的理而是穷人的心,并且认为朱熹是一个“儒化”的道家,这些观点多有可商榷之处,为学术研究留下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何炳松《程朱辨异》对于朱子学的阐释,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而且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何炳松强调朱熹所谓“人之一心万理具备”以及“穷理”必须穷人的心一样,当今有些学者重视朱熹的心说;与何炳松强调道家思想是朱熹学术思想的来源一样,当今也有学者热衷于研究朱熹与道教的关系。因此,何炳松《程朱辨异》可以为当今的朱子学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而且,何炳松对于朱熹二元哲学的分析,并从中概括朱熹“理必有对”的思想,也可以为当今的朱子学研究提供不同的参照。但遗憾的是,何炳松《程朱辨异》对于朱熹与程颐之差别的讨论,这一对于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至今尚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当今学者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和研究朱熹与程颐的一脉相承,而对于二者的差异,则少有问津。正因为如此,则更显示出何炳松《程朱辨异》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汪俊《濯旧》指出:“‘有理有气,气形而理性。’朱子之说也。程、张之论,盖不如此。‘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性即理也。’此程子之说也。朱子论性,自谓宗程、张立说,似非程、张本旨。”“朱子分理气两言之,曰‘得气以成形,得理以为性’,恐非程、张本旨。”“朱子谓‘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继之‘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恐非程、张之旨。”“朱子宗程子立说,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为性,得气以成形,其推于人事,以事为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则是有器而无道。’盖歧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说矣。”“或曰:‘子亦求异于朱子乎?’曰:‘非敢为异也,将求同于程子耳。中和之说,程门论说甚详,似皆未领其旨。……若以动静之时分体用,而以静存为致中,动察为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转引自(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下册)卷四十八《诸儒学案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43~1149页。]
②何炳松曾在1928年致胡朴安的信函中说:“后学日来颇喜读南宋诸儒遗集,自觉略有心得,小程子似可视为吾国近七百年来寔学大师,流为浙东及湖南之史学,与朱子之唯理哲学,颇觉根本不同。此节曾请示于适之先生,尚未能得其心许,唯后学则未免自信过强耳。现正在潜心研究中,不日稍有所得,当趋前请教。”[《胡朴安友朋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
③据《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载,杨开沅谨案:“成性之说,始于董子《天人策》。张子未能摆脱其说,亦气质之性误之也。气质自气质,如何云性?况气质本无不善哉!”[(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七《横渠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8页]
[1]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王国维.论性[C]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6]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M].上海:中华书局,1916.
[7]梁启超.儒家哲学(第五章)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下)[J].清华周刊,1926,26(12).
[8]周予同.朱熹[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9]何炳松.程朱辨异(一)[J].东方杂志,1930,27(9).
[10]何炳松.程朱辨异(四)[J].东方杂志,1930,27(12).
[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白寿彝.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C]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3]陈荣捷.新儒家范型:论程朱之异[C]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徐复观.程朱异同——平铺地人文世界与贯通地人文世界[C]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15]杨向奎.程朱哲学思想之异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3).
[16]何炳松.程朱辨异(二)[J].东方杂志,1930,27(10).
[17]何炳松.程朱辨异(三)[J].东方杂志,1930,27(11).
[1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9]谢无量.朱子学派[M].上海:中华书局,1916.
[20]黎群铎.晦庵学说平议[J].国学丛刊,1925,2(4).
[21]黄子通.朱熹的哲学[J].燕京学报.1927(2).
[22]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C]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郭美星
B244.7
A
1008-4479(2015)03-0026-06
2014-12-29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项目编号:12JZD007)阶段性成果。
乐爱国(1955-),男,浙江宁波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