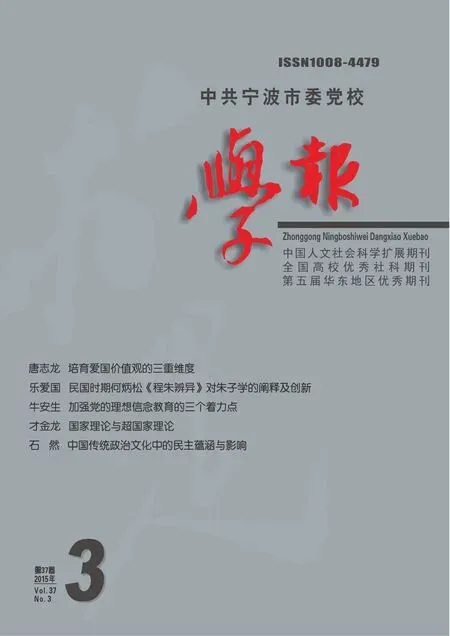阳明“良知”、“良能”概念之关系探究
——兼论“良知”之本质
2015-12-15贾庆军
贾庆军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阳明“良知”、“良能”概念之关系探究
——兼论“良知”之本质
贾庆军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关于阳明“良知”和“良能”概念的探讨,学术界较少谈及,因为良知已然包括了良能之义。对阳明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良知,它是气、精、神之合一体。具体来区分的话,在宇宙则为天理良知,在人心则为人心之良知。天理良知是全知全能之整体,人心之良知则必然亦是知能之整体。
王阳明;良知;良能
一、前言
众所周知,刘蕺山所说之“意”就是阳明之“良知”,之所以有此替换,是因为刘蕺山对阳明“良知”与“意”的误解①。但最近学者有不同之见,认为刘蕺山之“意”是对阳明“良知”的补充。“意”甚至是先于良知而存在的。还认为这是对孟子良知良能说的完善。“意”不仅是良能的表现,而且可作为“良知”的动力。所以,在意向和动力的意义上,良能比良知更具本原性②。这可能局限于认知心并从而对良知进行阐释,如此之心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一种自感和自觉,或如牟宗三先生所谓的逆觉,或者将良知或意变成了一种“彻底的内在性”之“绝对主体性”(刘蕺山之“纯意”),其自感是一种“绝对的自感”[1](p12~13)。将良知之学变成一种生命现象学③,本身就可能是对它的降低和狭窄化。阳明之学显然是放眼整个宇宙和人类整体的,它并非是西方私欲泛滥后诞生的现代生命哲学。阳明之良知其实就是宇宙的本原,并不只是具体心之具体认知。这一本原化生万物并与万物为一④。它已经包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所有之能,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皆已经包括在本然良知中,不必再析出一个“意”来补充之。所以,面对阳明良知学之珍贵宝藏,我们还是有必要不断努力去挖掘的,虽然有时我们的努力可能会造成一种新的遮蔽。
我们首先从其良知良能概念着手,然后试着探讨良知概念的本质。
二、阳明“良知”与“良能”概念的关系
翻看阳明语录,其在讨论良知时已含蕴了良知良能所有方面。阳明曾多次提到良知良能这一组概念,主要引用如下:
(1)在《传习录(上)》回答德章之问时,阳明就提到了良知良能,他说: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此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2](p31)。
(2)在《答顾东桥书》中,他又写道: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2](p49~50)。
(3)在《答陆原静书》中他又说: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末免于行不着,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2](p69)。
(4)在《答聂文蔚》中,他还说道: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2](p79)。
(5)在《传习录(下)》中,阳明明确点出“能”就是“良知”,他说:
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旧看何等玄妙,今看原来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我们试着来理解阳明所提到的这几组良知良能概念。
在第一段中阳明将良知良能分开来说,其实是为了一般人更好的理解。因为一般人都习惯“从躯壳上起念”,未免知行两分、心物两分、体用两分。而天理是整全的,为了让一般人都能理解这一整全天理,阳明就要强调其知和能的统一。这里所说的“天理”就是广义上的“良知”,它包含了从心上而言的狭义的“良知良能”。阳明说看重圣人分两而不是其天理之纯,就是从“躯壳上起念”,而非随心之纯乎天理。也就是说,从躯壳起念是分心和理为二的,其认知也是从心物分离开始的,如此之空无之心不免为物所役,沦于物欲。由此看到的只是物之分两、力量气魄,而不见其之真纯与否。从纯乎天理出发,则见万物一体、心理同一,知能或知行合一,其所见亦是精一,按现在的话来说,则是质和量之统一。所以,从天理来看,是从完整的角度来看,而从躯壳来看,则是偏于一隅。当尧、舜、孔子所做的事情依循天理时,无论多寡皆是一样,皆可称圣贤。若人人识得天理,依循天理,不管其事功多寡,皆可成圣人(所以,阳明“人人成圣”要表达的是人要遵循天理的意愿,而不是人人有相同之能力、可建立相同之事功的平等之言)。顺着这一逻辑,天理自然也是知、能合一的,无离知之能,也无离能之知。既然只是一,为何还要用两个概念来界说它呢?这也是后来为何阳明不再提“良知良能”,而只提“良知”的原因。而其提到“良知”时,又总是要免不了辩驳其知行合一、体用合一之内涵。“良知”于是就必然逐渐脱离狭隘心之良知良能的范畴,转而成为全能的本原天理。阳明在《答陆原静书》中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即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2](p62)在《传习录(下)》中他更说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p104)良知的宇宙本体、本原之特征显露无遗。它集精、气、神于一身,成就了万物一体。
而天人合一之义,阳明得自道家的启示良多。其在《读易》一诗中对道之思想推崇备至,其中写道:“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具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非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2](p675)在《忆昔答乔白严因寄储柴墟三首》中,阳明写道:“忆昔与君约,玩《易》探玄微。……盈亏消息间,至哉天地机。圣狂天渊隔,失得分毫厘。毫厘何所辩?惟在公与私。公私何所辩?天动与人为。遗体岂不贵?践行乃无亏。……无为气所役,毋为物所疑。恬淡自无欲,精专绝交驰。”[2](p680)在答赠友人湛元明和崔子钟的诗中,阳明提到了天道本原之状态,他写道:“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中有亦何有?无之即成空。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机,非子孰与穷?”[2](p679)同样写给两位友人的还有如下诗句:“起坐忆所梦,默溯犹历历;初谈自有形,继论入无极。无极生往来,往来万化出;万化无停机,往来何时息。来者胡为信?往者胡为屈?微哉屈信间,子午当其屈。非子尽精微,此理谁与测?何当衡庐间,相携玩羲《易》”[2](p682)这些诗都对《易》之“道”做出极高评价,称其为“至教”,揭示出了“天地机”、“玄化机”。可以看出,阳明深得“道”之宇宙论的精髓。道之存在样态初为“无极”,“无极”的运作方式是“往来”,即阴阳、动静。由此,化生天地万物。而万物的自然本来状态就是往来不息(“往来何时息”),此也可称为“天动”。万物(包括人依循天动),即是“公”而妄动或人为(依循一己之意)则是“私”。所以,要复天道,就要无欲、勿忘勿助(“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道”或“无极”,就是后来阳明所说的“良知”。所以,有学者认为,阳明龙场所悟之道就是《易》之道。[3]“良知”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旨就不仅仅是感官的、心理的和境界上的,而是生成论和宇宙论层面的。这里的“道”或“无极”后来也被阳明称为“气运”。[3](p871~872)刘宗周、黄宗羲则将其发展为“气”一元论。
在第二段中,阳明开始使用“致良知”一语。就笔者看来,阳明的“知行合一”、“良知”和“致良知”,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良知”。之所以会有“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表达形式,只是为了让常人更好地理解“良知”的本意。因为“良知”本来就是知行合一的,不必再去强调“行”,也不必刻意去“致”。但常人总有知行分离、先知后行之弊病,所以才有此强调。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去强调阳明“良知”学说的转型了,阳明学说的宗旨是一以贯之的。话说回来,这一段中的“良知良能”依然是“良知”本体。这里,阳明又强调了良知本体和事变(“节目时变”)之关系,也即体用之关系。对阳明来说,体用一源,皆属一气,[2](p124)体不离用,用不离体。规矩和方圆、尺度和长短是一体的。但常人往往不能领会万物一体之义,习惯分体用来视事物,结果是只见纷繁支离之节目时变,不见其精一之本体和头脑,结果是从分离之事用上产生诸多礼节规范,以此来指导时变。这种不见本体规矩而得到的各种节目,不过是一些僵化的陈规陋习,人们越拘泥于此,就越难以领会圣王宗旨,以致连圣王的行为都难以理解了。是以阳明批评常人的知行合一之浅陋。按照顾东桥的逻辑,凡知道温情定省之礼节者,皆可谓致知者。然而这样的致知不是真正的致知。致知必须是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也不仅仅是对日常简单礼节之知行合一,应为大道本原之知行合一,即良知。此良知是大道本原,不为节目时变所拘,也不为寻常礼节所束缚。不懂整体大道,只是遵循琐碎的礼仪,结果会离大道愈来愈远。以常人的逻辑看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兴师,是大大的不孝不忠之举。但从整体天理或良知本体来看,舜、武之行为是符合良知天理的。舜是遵循“为无后”、武王是遵循“为救民”之良知天理而行的,其举皆为大孝、大忠。而常人以支离僵化之礼节来看,就无法理解了。因此,只知道些节目时变,认知一些时俗礼仪并践行之,并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也不是真正的致良知。以分离的眼光想从节目时变上看到真正的良知本体或天理,是不可能的;以节目时变来决定本体良知,更是不可能的。是以,真正的“良知”不是先知后行,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知,而是本体意义上的“知”。此本体良知天然是知行合一、体用合一,也是良知良能之总体。所以,“良知”就是“良知良能”,这是圣人和愚夫愚妇皆有的,但惟有圣人能“致”良知,而愚夫愚妇却不能,圣凡之别就清楚了。这也可看成阳明并不赞同人人平等的主张。虽然他强调人人成圣,但只是从本体上看;而从现实看来,人之能力是不平等的。所以,阳明改变的只是成圣的途径,他强调不同的格物穷理之工夫,但并没有因此抹煞人们能力和素质上的差别。
在第三段,阳明更明显地承认知、行本体就是良知、良能。他先区分两种不同的行和知,即不同的着和察。圣人所说的真正的着和察就是本体之行和知,即良能、良知。而常人所理解的着和察局限于闻见之知行,也即在分离体用之后,单从发用事物上去知和行。这样的知行注定是分成两截的和非本体的。真正的知行或察着是体用一体的,是合一的和本然的。懂得这种本体知行之后,即使是无所事事之人,也是得生知安行之本意的。既然知行本是合一,那么良知良能也就是一体的。而这一体就可以统称为“良知”,无需再分开来强调。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对阳明知行合一之旨的解释依然牵强。当代大儒钱穆先生也是在体用分离、知行分离的前提下来理解“行”的,他所谓的“行”只是有形的行动实践之行,此行与阳明本体之行是不同的。⑤阳明所说的“行”是本体的,良知自然呈现本身就是“行”,而此发用所含的样态既有动的,也有静的,既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只要依循天理,莫不是行⑥。所以,不仅仅是行动的、实践的才是本体之“行”。
在第四段,阳明明确说出良知良能即是“良知”。他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他虽没有明确说出良知、良能的概念,但一看便知,“不虑而知”说的是良知,“不学而能”说的是良能。“是非之心”天然涵纳了良知和良能,而“是非之心”就是心之本体良知。所以,良知良能是一体的,其总体就是广义的、本体的、知行合一之“良知”。
在第五段阳明更是将“能”之内涵囊括进了“良知”。“良知”天然就具有“能”之意义。“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耳、目、心自气化流行中自然显现,其呈现的同时就具有聪、明、睿智之能。而这一呈现也是“良知”之呈现,此呈现中天然含有所有之“能”。所以“良知”也是“能处”。
至此,我们就明白,阳明的“良知”中已然蕴含了“良知良能”之全部,无需另外再强调一个“良能”,也无需强调另外之“行”。
三、阳明“良知”之本质
通过上面对其良知、良能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阳明的良知是分不同层次的:有宇宙本体之天理良知,即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的良知,此良知化生并主宰万物,也是一个知、能一体之存在。正如阳明所谓:“天即良知也”[2](p111);有人心之良知。天理良知落实在人心上,就是人心之本体,即心之良知。而人心之良知也是知、能一体的。而且,在天地万物中,人是最能体悟和承载天理良知的,因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2](p79)人是天地中最为灵秀之存在,最能感知和领受良知之精髓。为了更清晰了解其关系,我们通过图表来表述:

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皆因其在一整体良知内。徐梵澄先生对这一整体性认识得很清楚,他说,“所谓人与万物一体者,非在形而在性,即宇宙知觉性之为一。倘这前提被接受了,则亦易明白阳明之‘知行合一’之说。知觉性非实物,必以其所表现而见。表现亦即是行为。此在人即为‘良能’。良能今亦称本能。与智性皆属先天。即智即能,便是即知即行,外见有作为之善巧,必内在有作用之潜能。……体显用,用表体,此所谓知行合一。分言之,即良知、良能。何等简单。”[4](p98)
徐先生对知觉性之结构的描述还是基本与阳明之良知相吻合的,他所说的“知觉性”就是整体良知,而其在整体上看就是天理良知(道心),落实于人心则为人心之良知(人心)。[4](p90)在徐先生看来,这一弥漫宇宙的知觉性天然包含了良知良能之两面,此即一体两面。
但徐先生对此知觉性之性质的描述是笔者不能认同的。他将陆王心学作为一种精神哲学体系来谈论,并向流行的唯物实践观念靠近。虽然这一精神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心理学和唯灵论,此精神是属理性的,虽摄理性,但又大于且超于理性。[4](p13)而且这一精神讲求内外交修、实践实用。[4](p21)但这仍然将阳明之良知狭窄化了。且其对实用的刻意强调也会降低良知的自然性和整体性。“天理良知”自然包含了万物之气和万物之理,无论是“形”还是“性”,在最本源处皆为一体。阳明也曾说过:“夫大人与天,一而已矣。……谓大人之与天,形虽不同,道则无异。”[2](p844)这里的形乃气之固化,而对于其本然流行之气(即道)来说,仍为一。在前引诗句中,阳明也说过:“无为气所役,毋为物所疑”[2](p680。这里的气和物皆指后天形气,容易留滞人心,从而阻挡人心良知的恢复。人要抛开后天形质,体悟本然之气之流行,自然会接通天理良知。在《传习录》中,阳明明确点出天地万物乃一气所成,“太极生生之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阴阳一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一理也,一理隐显而为动、静。”[2](p64)可以看出,不仅阴阳为一,理气也是为一。理不过是气之屈伸而已。万物皆为理气化生,如何不为一呢?阳明所谓“气亦性也,性亦气也”[2](p101)说也是此理。所以,万物一体不仅是形气上的,也是性上的。将“良知”仅仅看成“理”或“知觉性”显然就狭窄了。
杨祖汉先生也对阳明良知良能之关系有所探究,他亦认为本体的知和行就是孟子的良知和良能。而且在本体的意义上,良知就是良能,“而言知行之本体本来是一,或良知即是良能,二者是分析地相函之意,不是就一般意义的知行关系说。”[5](p236)知行本体之一与良知良能之一,指的就是本原创生之天理良知。其为一就可以理解了。
阳明也曾说过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使人很容易将其与存在主义思想或生命哲学联系起来,并将天理良知与人心之良知的层次混淆,以人心之良知取代甚至抹杀天理良知。如他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p108)他还说,人乃天地之心,而人的心就是一个灵明,即良知,“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2](p124)这些话同阳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思想是一致的。如前所述,良知自其流行来说就是气,自其凝聚而言则为精,即灵明。而人则是天地之气精华所在,为万物之首。人之精华则是人心之灵明。此灵明亦是天地之灵明。就如宇宙乃是一个大身体,而具有灵明心之人则是这个身体的心脏枢纽,若心脏死去,身体也将死去。所以阳明才说,此灵明心在则万物、神鬼皆生,此心没则万物皆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心之灵明并不是肉体之心的功能,而是本然天理良知,只有当人心之良知与天理良知合二为一时,才能说人心与宇宙同生共灭。然而,如此对人之灵明的强调并不与天理之优先性相矛盾。对于天道人性之层次,阳明还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他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2](p15)“性一而已”之“性”,指的是整体良知;主宰之“帝”则是天理良知;“赋于人也谓之性”之“性”则是人心之良知。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之层次也就清楚了。人心始终是以整体良知和天理良知为其基础的。因此,如此之心与存在主义绝对的主体性或彻底的内在性就大相径庭了。
四、余论
综上所述,作为本然自然呈现之天理,良知已是全能之整体。在其中善恶自辨,为善去恶一随自然。这是一个完美的自然整体。宇宙就是一个放大的良知,它自然绽放和展开,无需另外的意识和感应。而人乃这个良知的核心,凝聚在心体上的良知,亦是天理大良知的体现,两者是一体的。所以,心体上的良知不需要去意识、去感应,它只需顺应宇宙良知的运行,自然去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至于不悟良知者,就是滞留于物之人欲在作怪,这时才需要一些致良知之工夫,使其复归良知。这就是阳明良知之学的大意。所以,阳明之良知也并不是孟子意义上的良知,他只不过借孟子之语,他的良知是宇宙万能之本体,不是体现认知能力的见闻之知。所以阳明会说,其良知说亦不过是借用词汇而已,如果悟透了天地万物一体之圣门宗旨,良知一语也只是个称谓罢了,不用固执于这一概念。同样,也不用执着于知和能之概念。
话转回来,阳明之良知或见在良知⑦是如此广大和完整,就不是简单的现实化和客观化,它是神秘莫测之宇宙总体,说它压制了人的想象力和超越性是不恰当的。说阳明良知是“显”,并不是说它就是简单显白。看似简易的东西反而更是深不可测,而故作复杂神秘的东西反而显得枯竭无力⑧。而且,具有西方思想色彩的“逆觉体证”、“纯情自感”能否真切理解阳明思想也是值得怀疑的。[1](p7、10)将神秘的东西说得越细致精微,便越是为具相所拘,越会遗失大道本原,就越会加速神秘之体的死亡[2](p115),西方的上帝就是如此。而恰恰是良知天理的广大和神秘才导致阳明在所有领域纵横捭阖、收放自如。也正是此天理的广大,才造就了古代中国人想象力的超拔和不羁。
陈荣灼先生虽然注意到了主客观二分思维方式的局限,并力求客服这种二元倾向。但他选择的存在主义途径是否真正客服了这种二元倾向令人怀疑。他不仅将阳明之良知误解为理智性之知,对刘蕺山的慎独之意的理解也有牵强附会之嫌。他将刘蕺山诠释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这是否是刘蕺山的本来面目亦值得商榷。陈先生如此作为,完全是受西方反本质主义思潮之影响。存在主义是其最典型之代表。在存在主义看来,本质主义是二元思维的结果。所以存在主义力求客服二元思维,抵制本质主义的专制。存在主义设想了一个不分主客体或主客体合一之整体存在。但对此存在的领悟和主导权却全归于此存在中之人,即此在。此在之优先地位决定了存在主义的后果,即它变成了人之恣情纵欲的工具。法西斯主义便是其极端之表现。这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后来从“此在”转而强调“存在”之优先性的原因。强调此在优先性的早期存在主义不仅没有克服二元之倾向,反而将人的主体性拔得更高,主体以绝对自由的方式扫荡了所有的客体,制造了更极端的专制。而陈先生及其所尊崇的生命哲学家亨利(Henry)所持的逻辑就是这种早期存在主义的逻辑[6](p90)。尽管他所引用的牟宗三和唐君毅对刘蕺山的解释是强调天对人的优先性的,但他却认为他们是错误的,并执意要将蕺山思想看成是以人之”意”为优先性的,强调其”彻底的内在性”[6](p85~93)。所以,牟宗三和唐君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即他们看出了不管是阳明的显白还是蕺山的归显于密,在天人关系上依然是以天为优先的。
强调天之优先性并不一定就造成专制和想象力之枯竭。造成这种后果,不过是人们对天的歪曲和误解。在阳明和蕺山那里,天是一个活泼泼的自然存在,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本质。正是因为天之流转不已和神秘莫测,才会不断提升人的想象力和生命力。而没有这样一个天之存在,仅靠人自身的意志,其未来才有可能变得枯竭和庸俗不堪。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了解阳明之高明了,刘蕺山之思想依然是在阳明的逻辑内展开的。阳明良知之高妙莫测,使他远高明于蕺山之上。所以,同朱熹一样,蕺山念念不忘的是在节目时变中寻找善恶之蛛丝马迹,不同的是他醉心于从心体上的节目时变中寻找有相之善恶的踪迹,而朱子却是在心外找寻善恶之理。由此,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失却本真善恶之辨识。相对于阳明的豁达豪迈、心胸开阔,蕺山和朱子却显得拘谨严肃。无怪乎阳明最后把乐归之于良知本体,得真体大道当然是至上之乐了。得此本体之乐,虽身经常人所见千痛万苦,亦只是乐。
如前所说,正是因为对良知天理的深切体悟,才使阳明深刻理解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兴师与常人遵循之忠孝礼仪的差别。在阳明看来,舜和武王才是大道之践行者,常人则是陷溺于节目时变的僵化教条者。正是如此,我们才会了解到阳明良知天理之广大。同时我们也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迄今为止我们所建立的社会可能都基于节目时变。在节目时变基础上,西方建立的是法制社会,在中国则建立的是礼制社会。然而这皆不是阳明所欲的终极宇宙。按照阳明的逻辑,节目时变最终不免走向僵化教条,造成专制,不承认甚至损坏更高价值的存在。讲民主法制的雅典人判了柏拉图的死刑,这就提醒世人,失去最高天道滋润的民主有可能变成暴民的专制。而礼制的专制我们是体会更深的,当这些细枝末节、节目时变之礼仪成了僵化的仪式教条时,它们就失去了天道活泼泼的本来面貌,成为了人走向更高、更自然生命的束缚。所以阳明会说,孔子之言也并不一定正确,它也有可能是节目时变之产物,不要固守于经书教条,更重要的是在僵死教条背后流动的活泼泼自然之天道。虽然阳明会否定孔孟的具体言辞,但从来不会否定孔孟对天道的追求。由此,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真正的孔孟之道恐怕从来没有实现过,被制度化的不过是被肢解的天道。即使是礼,也恐怕不是真正之礼,因为按照孔子对礼的要求,它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如孔子在《泰伯篇》中所说的礼:“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试问如此中庸极致之礼有几人能达到,历朝历代之典章制度有几条达到了如此的高度?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礼。所以,如上所述,阳明会站在更高更自然的本原天道的基础上,对寻常人的忠孝观念提出挑战。这也说明,真正的天道或良知天理是活泼泼变动不居的,“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2](p125)它不能被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现实社会能做的,是不断更新和完善制度化的东西,以求更接近天道,但不要奢求完全实现道。
在现实中,能悟透天道之人微乎其微,懂得天道存在之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在物欲和节目时变中沉浮,如果强行拔高他们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此之现实,反而凸显出低层次法制或礼制的部分合理性。正因为如此,民主社会才成了最适合大多数人的最佳体制,正如齐泽克对丘吉尔话语的阐释:“民主政治在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是最坏的;惟一存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比它更好的政治制度。”[7](p7)这就是说,考虑到大多数人的禀赋,在现实中最好的制度将是民主制度。而真正最美好、最高明的东西恰是不能制度化的,这就是天道的困境所在。在大多数人眼中,社会被降低为一种物质化、固化的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制度来约束,法制社会就是适应这种物质化眼光出现的。这种适应多数人的制度注定要在历史中取得胜利。这就是柏拉图要成全法制社会的原因所在。但是,法制或礼制社会能够长存的基础是它必须承认还有比之更高的天道的存在,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如果它夜郎自大、刚愎自负,将自己抬至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它的终结也就不远了。
所以,对天道或良知天理的追寻不仅不会过时,在现今私欲泛滥之世界反而显得更加迫切。只有带着对天道的敬畏行走在法制或礼制社会中,人才能走得更安稳。当然,对那些追求天道的人来说,他的整体生命更会因此超越制度的禁锢,得到无限提升。无论在哪一方面,阳明对天道所做的发掘都是意义巨大的,其思想也是我们寻求天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和导引。
[注释]
①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下,台北: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586~588页;杨祖汉:《黄宗羲对刘蕺山思想的承继与发展》,收入杨祖汉、杨自平编《黄宗羲与明末清初学术》,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41页;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08页;黄敏浩:《刘宗周及其慎独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235~237页。
②陈荣灼:《黄宗羲之孟学解释:从刘蕺山到王船山》,杨祖汉、杨自平编:《黄宗羲与明末清初学术》,第127~163页。
③就连蔡仁厚先生也跟着强调儒家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新儒家的现代转向之诱惑可见一斑。见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自序》,第1页。
④陈来先生最近也提出中国哲学“万物一体”之说并不是简单的境界论,而是本体论、宇宙论。见陈来:《仁学本体论》,《文史哲》2014年第4期。
⑤钱穆:《阳明学述要》,台北:兰台出版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2001年版,第62、63页,类似言论也见该书第93、94页。
⑥阳明说得好:“圣人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个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功业气节名矣。”载《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第96页。遵循整体天理,功业气节一应而全,不必再强调去争个功业气节。越是强调,越偏于一隅。对于“行”亦是如此。
⑦对阳明来说,良知只是当下的良知,无所谓过去与未来。说良知是见在的,并不是说它等于是现实的、客观化的,它依然是整个广大而神秘的宇宙整体。(《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第109页)。
⑧由此,牟宗三先生对阳明和蕺山思想路向所作的判断也就值得商榷了。阳明的论述方式表面上是“显”而实质上是更深刻之“隐”;而蕺山表面上是“隐”,而实质上是“显”。论到思想的高深和高妙,非阳明莫属。
[1]陈荣灼.回归“彻底内在性”——东西方“生命现象学”之比较研究[J].清华学报.2010(1).
[2](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朱晓鹏.阳明龙场《易论》的思想主旨[J].哲学研究.2008(6).
[4]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5]杨祖汉.儒家的心学传统[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6]陈荣灼.论唐君毅与牟宗三对刘蕺山之解释[J].鹅湖学志.第四十三期.
[7][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篇首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梁一群
B248.2
A
1008-4479(2015)03-0047-08
2
贾庆军(1975-),男,河北望都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浙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