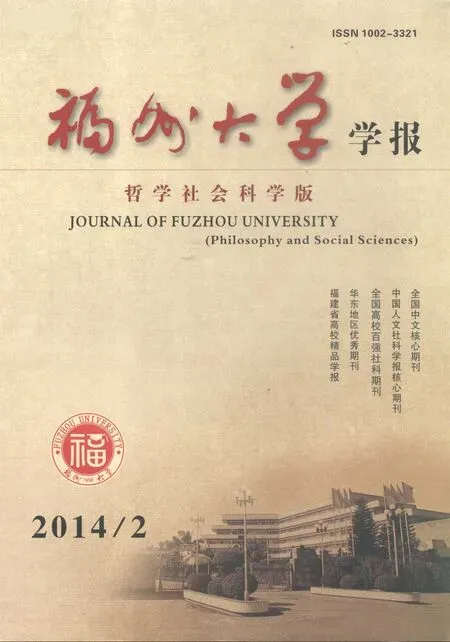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
2014-04-18朱人求
朱人求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近年来,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1]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朱子学是中国乃至东亚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作为一代宗师,朱子又以其真知睿见和“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恢宏格局而成为“蓄水池”式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700余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共有的统治哲学。换句话说,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世界化的朱子。概而言之,朱子思想本来就不只是“中国的朱子学”,对相关议题的讨论若以“东亚的朱子学”甚至“世界的朱子学”立场,可能才更符合文化实际,更有利于激发学术发展的潜能。
一、东亚朱子学的界定
朱子学,顾名思义,就是指朱子的学说,这是狭义的朱子学概念。最早的朱子学指闽学,就是朱子之学。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它指朱子及其后学的学说。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当然包括朱子及其在东亚的后学的学说。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
在《朱子学与近代日本的形成》一文中,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认为,朱子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朱子本人的学问,广义则是指所有师承朱子学的后继者所发展出来的学问。日本朱子学属于后者。若按狭义来理解“东亚朱子学”,则意指探讨与原始“朱子学”之间的距离。此类议论可以区分为“真实与虚伪”、“主流与旁支”以及“正解与误解”等两层构造。辨别真伪的议论是以“真正的朱子学”是否存在为前提,然而所谓“真正的朱子学”是隐含在研究者解释后所重构出来的意义中,也就是必须取决于研究者的正统意识、本源意识后,才得以显现。[2]有意思的是,子安宣邦称呼朱子后学所继承的朱子学为“朱子主义”,如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朱子本人的学问与后学所发展出的朱子主义之间,有必要做出区分。这样的区分,能够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日本的朱子学,也就是朱子主义式的学问和思想。
韩国西江大学郑仁在教授将朱子学传入韩国后的发展情况,区分为“本源朱子学”(比较符合朱子的学问)和“修正朱子学”(与朱子学说有一定差异的学问)。罗整庵是“修正朱子学”的鼻祖,李栗谷深受罗整庵的影响,属于修正派。李退溪反对罗整庵,属于本源派。郑仁在理解的朱子学,是指朱熹之前的北宋五子之学、朱熹本身思想,及其在中国、韩国、日本、欧、美的发展与修正。[3]这是一种广义的朱子学概念。
东亚朱子学是东亚儒学相关论述与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指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从东亚儒学的发展来看,朱子(字晦庵,1130-1200)之学涵盖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等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相关的儒学拓展、传承与研究呈现出两个层次的特质:第一个层次是儒学由中国经由韩国向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有着共同关切的典籍(例如《论》、《孟》)与议题(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四端七情”、“民贵君轻”等),而对议题的发挥程度与内容则彼此不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学价值理念在“同心圆”式的逐层展开时,呈现相当的类似性;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国朱子学思想内容在类似性中展现其殊异性,也是“理一分殊”之具体而微的表现。但是经典与议题的同源性和类似性,不能强制规范各区域的分殊表现,因而这里便涉及到第二层次的“去中心化”现象。就各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以及民族或政治之自觉而言,日韩儒者极不愿将中国儒学视为其唯一中心,而中国儒者也不能一厢情愿地将日韩儒学看作其附庸或边陲。“中心—边陲”的论述很难解释这类文化与思想的发展轨迹,即以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为例,西欧与美洲大陆日后的发展,已取代这两种文明起源地的重要位置而成为新中心;而佛教在东亚与南亚的特殊发展,亦早与印度佛教分道扬镳,并在后者衰亡之后成为新的思想与信仰的重镇。[4]实质上,这种“去中心化”的背后是就是“去中国化”,这一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正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5],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我们认为,东亚朱子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朱子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本源的朱子学,也必然包含本源的朱子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正确立场是“中国本位,东亚视点”,或者“中国本源,东亚视点”,注重东亚朱子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区分东亚朱子学的不同表现形态。东亚朱子学是“一体多元”的朱子学,“一体”指朱子学说本身,“多元”指朱子学在东亚的不同的发展形态。
二、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东亚朱子学研究课题的提出,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近年来,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东亚朱子学研究者逐渐正视中、日、韩和欧美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将自身定位在“国际朱子学”的脉络之中,密切关注同领域的研究动态,而日本、韩国学者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与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意义深远。
首先,组织策划东亚朱子学研究是朱子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系统而全面地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整体研究,比较中日韩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的异与同,总结出其中的方法论和规律,提炼出新的理论模型,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是朱子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对于进一步推动朱子学的合作与交流、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百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也有过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30年来,朱子学研究异彩纷呈,取得了大量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东亚朱子学学术成果、方法论及其理论模型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清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其发展趋势,为未来的朱子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其次,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发展。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6]宋代文化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其原因之一在于宋代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理学。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而有朱子学,所以朱子学与儒学以及宋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宋末之后,儒学实际上是朱子所诠释的儒学,文化是朱子学影响下的文化。然而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朱子学受到了太多的误解和批评。这对于儒学的研究,乃至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极为不利的。在全球化时代,系统而全面地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促进中日韩朱子学的对话与交融,不仅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再次,进行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以及东亚各国的学术文化交流,对那些企图“去中国化”、“去中心化”的东亚儒学研究起到纠偏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东亚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重大。海峡两岸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同属一个中国,朱子学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朱子文化在明清之际传入台湾,成为台湾地区统治意识形态,对台湾影响至深。至今,台湾许多书院仍主要供奉朱子而非孔子,朱子影响可见一斑。近年来,海峡两岸以及国际有关朱子学的学术交流尤为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了东亚朱子学和儒学研究的发展。
在肯定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台湾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是其中应有之义)的“去中国化”、去“中心化”的倾向让我们倍感忧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指出近年来台湾兴起的东亚研究,乃是一部分学者为了应对“去中国化”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7]这个分析虽是外缘性的,但作为第三者的一种审视观点,值得引起重视。日本子安宣邦的忧虑也有此意,台湾关于“东亚儒学”的提出是否想取代中国大陆成为新的“文化帝国”的中心呢?回答是肯定的。台湾大学“东亚儒学”研究计划的执行人黄俊杰旗帜鲜明地指出,“东亚儒学”这个新领域本身就已经蕴涵着多元论的观点。“东亚儒学”新领域之开拓,一方面超越旧“汉学”之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挣脱“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研究格局,实现去“中国中心论”的目的。简言之,“东亚儒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走向“台湾本土化”,以“边缘”取代“中心”,以达到“去中国化”、“去中心化”的目的,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我们认为,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坚持“中国本位,世界眼光”,对这一错误的文化倾向起到积极的纠偏作用,回归本源,以正视听。我们坚信,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之研究的东亚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反过来对于深入了解东亚的历史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东亚和近代以来东亚的社会、政治、文化、东亚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复次,大力推进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东亚文化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东亚朱子学核心话语、具体实践及其内在规律,就是要立足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朱子学,通过对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来推动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创新,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东亚朱子学是一门国际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中日韩国家最高统治哲学,影响东亚数百年之久。朱子学是能够在地区造成广泛文化认同的普世的东亚价值源泉,对东亚朱子学进行系统研究,可以提升东亚地区文化软实力,可能建构一种能得到中日韩普遍认同的东亚思想系统,有利于提高东亚各国的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促进东亚文化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最后,深入探讨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促进“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促进全球文明对话和人类未来精神的建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亚朱子学是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东亚历史上曾得到东亚国家的集体认同,东亚朱子学研究对于在多元文化论的前提下重建“东亚文化共同体”无疑是一项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思想文化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积极参与人类精神的重构,朱子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活水源头。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每一个民族文化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对话、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获得全球文化的主导权。正是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朱子学研究置于“文明对话”的视野,对中日韩朱子学的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展开深入具体的研究,进而为朱子学走向世界奠定基础,同时也能使朱子学为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总之,全球化背景下的朱子学研究理应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而自觉的朱子学研究源于我们对朱子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尤其是对时代问题、对当下现实的深切思考。展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畅想未来的朱子学研究,我们满怀信心、同心协力、奋发图强。
三、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
在汉语学界,我们对东亚朱子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仍缺乏系统性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第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东亚朱子学的东亚应该是整体的东亚和文化的东亚。以往东亚朱子学研究多以点为主,有较多的单篇论文和少量论文集,对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还不够。中日韩朱子学承传与创新及各自的特色,东亚朱子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东亚朱子学的共同价值,东亚朱子学的问题意识,东亚朱子学的人文精神,东亚朱子学的接受模式和类型,东亚朱子学的一体与多元,走向“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东亚文化的相互交涉,文明对话中的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未来,朱子学与全球化,朱子学的当代实践,朱子学如何走向世界等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真空,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只有在全球化的境遇中,这一研究才得以充分展开并成为现实。
第二,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朱子的思想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并在此后元明清各时期成为中国思想的正统,成为近世儒学发展的主流。朱子学自13世纪起开始向世界广泛传播,在日本、韩国的历史上曾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东亚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态。在上一个千年期,朱子无疑是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杰出人物。陈来先生指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相同而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之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的多元发展是可能性。从而,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8]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的风景。
第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的经典文本及其在东亚的传播,中日韩对朱子学文本的接纳、理解与创新,不同的朱子学文本在东亚各国的不同命运等等。例如朱子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和韩国作为科举教材备受重视,在日本却被《四书辑释》和《四书大全》所取代,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深掘;又如为什么《朱子家礼》在韩国和日本的接受和实践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中、韩与日本对朱子学经典推崇各有侧重?真德秀《心经》在韩国备受推崇,为什么在日本却屡遭批评?把朱子学经典文本放进东亚特定的时空进行分析,许多被历史遮蔽的问题脱颖而出,进一步拓宽了朱子学的研究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朱子学的理论内涵。
第四,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中国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体认天理、理气先后、无极而太极、理即事,事即理、理气动静、心即理、理一分殊),工夫话语(格物致知、主敬穷理、诚意正心、定性、慎独、拔本塞源、心统性情、尊德性与道问学、操存省察、已发未发、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社会政治话语(正君心、出处、国是、教化),境界话语(见天地之心、识仁、自得、致良知、民胞物与、全体大用)等。日本朱子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理气一体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工夫话语(格物穷理、主敬涵养、静坐、全孝心法、事上磨练、智藏说等)、境界话语(如全体大用等)、社会政治话语(如神体儒用、名分大义论、夷夏之辩、国体、王霸等)。韩国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如理气之发、理乘气发、理气一途、人性物性异同论等)、工夫话语(如四端七情、心体善恶、心统性情、定心与定性等)、社会政治话语(如事先理后、起用厚生等)。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与理论类型,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的同与异及其根本原因,极具挑战性。
第五,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东亚朱子学”是一门国际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是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东亚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中日韩国家最高统治哲学。东亚朱子学何如通过书院教育、科举、社仓、乡约、家族、朱子家礼的实践等方式推进朱子学的社会化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日韩三国朱子学社会化及其实践有有何不同?目前,学术界对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关注度还远远不够,相关成果十分薄弱。我们认为,朱子学是能够在东亚地区造成广泛文化认同并得到具体实践的普世的东亚价值,对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提高东亚各国的生命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促进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除了上述五个领域,东亚朱子学与中日韩各国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以及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方法论问题是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概括而言,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考证的方法,义理分析方法,体认式的研究方法,“脉络性的转换”的方法,多重文本分析法,身体哲学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话语分析方法、话语的内在解释方法等,为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东亚朱子学在历史上呈现出“一体多元”的理论格局,“一体”指以中华文化为体,以朱子学为体,“多元”指中、日、韩朱子学的多元化发展与具体呈现。东亚朱子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朱子学传统,但是它并不是上述各地域朱子学传统的简单累加。东亚朱子学的发展既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又展现出文本、话语以及结构的相似性。未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应以东亚为视域,以经典、话语与实践为核心,并以中日韩不同文化为脉络,分析中日韩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既求其同,又求其异。通过对东亚朱子学的经典、话语与具体历史实践的考察,揭示出中、日、韩朱子学的共性与个性、具体与抽象、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未来东亚朱子学研究新领域之开拓,一方面超越传统哲学研究的单一路径,坚持以话语与实践的阐释为中心,回归朱子学的“原生态”,走向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碰撞,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论研究格局;另一方面,东亚朱子学研究必须突破单一国家的边界,注重东亚各国朱子学之间的相互交涉,注重东亚各国学者之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走向国际化的新视野。展望21世纪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立足东亚,以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及其未来发展,东亚朱子学研究必能在21世纪开拓创新,绽放异彩!
注释:
[1]本文反对将“东亚”概念实体化和政治化,认为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东亚文化共同体之“东亚”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皆指文化的东亚。
[2][3][4]黄俊杰、林维杰:《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第 155-168,298-305,1-4页。
[5][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6]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澳]梅约翰:《东亚儒学与中华文化民族主义:一种来自边缘的观点》,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8]陈 来:《东亚儒学九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