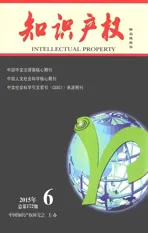我国专利无效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之反思
2015-01-30熊文聪
熊文聪
我国专利无效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之反思
熊文聪
证据规则是关涉当事人程序价值和实体权利的重要制度,围绕专利无效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建立了较为清晰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和补充新证据规则,但法院司法实践却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立法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些典型案件中,为追求所谓“实质正义”、“效率优先”,忽视乃至漠视“程序正义”、“法的普适性、稳定性、权威性”以及“听证原则”、“案卷排他主义”、“避免审级损失”等诉讼法基本原理和价值理念,改变既有的共识,这一做法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新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表述笼统含糊,也有待司法解释的澄清。
专利无效诉讼 证据规则 公知常识 程序正义
引 言
证据规则是诉讼程序的脊髓,①参见李浩著:《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修订版序言第1页。然而在专利相关诉讼中,证据规则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法院突破既有法律规定的做法时常发生,学者们又仅仅探讨侵犯“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等某类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未形成体系化的关照。但在诉讼法学界,“证据”却是近几年的关键词。②参见胡学军:《从“抽象证明责任”到“具体举证责任”》,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霍海红:《证明责任配置裁量权之反思》,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巧的是,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在证据规则上有重大调整,而正在酝酿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也多处涉及证据问题。③参见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就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7/ id/1355331.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22日。本文希望结合立法动态和司法实践,并吸纳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对专利无效诉讼中的证据规则加以全面梳理与辨析。
一、专利无效诉讼举证责任辨析
依照我国现行《专利法》第45条,一项专利被授权后,任何人都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请求宣告该专利无效。专利复审委是一个既区别于专利审查部门,又区别于法院的独立法人机构,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审查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和对驳回专利申请决定不服的请求,并依法作出裁决。④依照中国专利复审委官网表述:专利复审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事业单位。参见http://www.sipo-reexam.gov. cn/zwgk/fsgk/fswjj/index.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22日。当事人如对此决定不服,则应以专利复审委为被告,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⑤自2014年11月3日起,专利无效一审行政案件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转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提起行政诉讼,从而进入司法程序。因此,虽然有学者指出专利授权、确权具有准司法性质,⑥参见梁志文:《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性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但无论是专利审查部门还是专利复审委,都无疑是代表公权力来划定专利这一私有财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边界,我国法院也一直是依照行政诉讼程序来审理专利无效纠纷。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32条,“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此法条中的“举证责任”,一般被认为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即当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让法官产生内心确信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⑦关于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的区别,可参见叶自强:《论不可逾越的“柴尔线”》,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此论点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得到印证,其第6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将专利无效纠纷特殊化,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将这一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落到实处。如在2009年的“陈镜钊”案⑧陈镜钊诉专利复审委、朱炽坡专利无效纠纷案,北京高院(2009)高行终字第643号。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二审认为,就案件某一待证事实,无效宣告请求人已尽到举证责任。专利复审委和专利权人如主张该事实不真实,应提供反证,即举证责任移转至专利复审委和专利权人。可见,法院将“举证责任”理解为提供证据责任,而非说服责任。然而在同一年另一起专利无效纠纷案(“胡德银”案⑨胡德银诉专利复审委、李芝雁专利无效纠纷案,北京高院(2009)高行终字第665号。)中,北京高院又认为原告在法律上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专利复审委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显然,法院又将“举证责任”界定为说服责任,而非提供证据责任。就笔者观察,在专利无效诉讼中,我国法院绝大多数情形是将举证责任理解为提供证据责任或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它可以在原被告之间来回移转,直到法官查明事实,产生内心确信。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很少出现在判决书的表述中,原因且待如下分析。
二、公知常识的举证责任
公知常识是否定一项技术方案具有创造性的重要依据,因此经常在专利无效诉讼中加以运用。然而,如何认定一项技术属于公知常识?是否需要举证?由谁举证?何时举证?……这些证据规则是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需要仔细解读。在“双鹤药业”案⑩北京双鹤药业公司诉专利复审委、湘北威尔曼公司专利无效纠纷案,最高院(2011)行提字第8号。这个经过一审、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再审,荣登最高院2011年度指导案例选的重要案件中,最高院开门见山指出:“本院系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对专利复审委决定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而非就有关证据是否影响涉案专利的创造性直接予以认定。”但最高院笔锋一转,接着又认为:“本案焦点在于:1、如何确定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2、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是否具有新颖性;3、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是否具有创造性。”判决书多处体现了这种内在矛盾,揭示了最高院对涉诉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及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等这些可专利性核心问题的直接判断,而对专利复审委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却反而成了一个副产品。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无效宣告请求人(双鹤药业公司)所主张的将“将舒巴坦与哌拉西林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合制成复方制剂”是否属于公知常识。专利复审委在其决定书中将此技术认定为公知常识,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公知常识是否可由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对此,《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1节第(7)项规定:“专利复审委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常识,并可以(粗体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可以”即“可以不”,也即专利复审委并不负有公知常识的举证义务。然而在实践中,法院对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公知常识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支持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如在“宋景尧”案①宋景尧诉专利复审委、营口驰远公司专利无效纠纷案,北京一中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525号。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多处对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某项技术特征为公知常识但不举证的做法予以否定。有法官强调:“在当事人未对引入的公知常识进行意见陈述,专利复审委也未对其所认定的公知常识进行举证的情况下,专利复审委的认定违反了无效审查程序中的听证原则。”②佟姝:《专利行政案件中几种特殊类型证据的认定》,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1年第4期。正因有此共识,北京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二审判决书中才特别指出:“专利复审委的决定没有就有关‘将舒巴坦与哌拉西林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合制成复方制剂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的认定提供相关的依据,其作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③北京双鹤药业公司诉专利复审委、湘北威尔曼公司专利无效纠纷案,北京高院(2007)高行终字第146号。法院的这一判定是有法律依据的,即上述提及的《行政诉讼法》第32条。
但令人不解的是,最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中对专利复审委在无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直接就公知常识做出认定的做法是否正当这一核心问题却只字未提,反而直接采信无效宣告请求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明确驳回了专利权人(湘北威尔曼公司)有关“未经专利复审委先行审查并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在本案中不能以双鹤药业公司提交的有关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主张。有法官指出:“为保障行政程序的稳定性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各国司法机关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多审慎地遵循着‘案卷排他主义’,即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只能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卷为依据,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本身的合法性。”④同注释② 。关于此点,法院在该案之前是有共识的,如北京高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专利复审和无效行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第10条规定,“在专利复审委的无效审理程序之后的行政诉讼程序中,无效请求人提出的新证据,原则上不应接受并认定,无效请求人可以依据新证据重新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有法官进一步指出:“如果确定要在诉讼阶段接收新的证据,法院所能做的工作也仅是在判决书中表示对这些新的证据要在审查程序中予以考虑,继而要求专利复审委结合这些新证据的内容重新进行无效审查,而绝不能在诉讼过程中直接对新证据的内容给予评述、认定。通过要求专利复审委在考虑新证据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审查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均回复到行政程序的原始状态之中,无论对重新作出的决定是否服从,当事人均有权再次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当事人可能因新证据的出现而遭受的审级损失。”⑤司法实践也印证了这一共识,如在2008年的“伊莱利利”案⑥伊莱利利公司诉专利复审委、甘李药业专利无效纠纷案,北京一中院(2008)一中行初字第 1290 号;北京高院(2009)高行终字第724 号。中,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证17是无效请求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该证据在无效程序中并未提交,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过程中也并未予以考虑,因此,一审法院主动引入该证据并不妥当,据此撤销一审判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11年的“双鹤药业”案中,最高院直接采信了无效请求人在行政再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终判决。不仅如此,在早些时候的“厦门联捷铸钢厂”案⑦厦门联捷铸钢厂诉专利复审委、福建多棱钢业、泉州金星公司专利无效纠纷案,最高院(2010)知行字第6号。中,最高院甚至明确指出,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以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受这些指导性案例的巨大影响,下级法院彻底放弃了之前的共识,如在2012年的“北京文通”案⑧北京文通公司诉专利复审委、深圳鼎识公司专利无效纠纷案,北京高院(2012)高行终字第959号。中,北京高院认为,“在专利权无效审查诉讼程序中,一般说来不应当考虑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但是,由于公知常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均知悉和了解的,因此在专利无效诉讼程序中,法院在无效宣告请求人自主决定的对比文件结合方式的基础上,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或者考虑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有关公
⑤ 同注释② 。知常识的证据,并在保障当事人就此发表意见的基础上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并未改变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对双方当事人来说亦无不公,且有助于避免专利无效程序的循环往复。”
三、法院采信新证据的正当性分析
法院在专利无效诉讼中主动引入或直接采信新证据的做法是否正当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2条对所谓“新证据”做出了限定,即仅仅包括三类:“(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对于这些新证据,是可以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进行质证的⑨参见《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第50条和第51条。。可见,在专利无效行政审查中未提交而在后续司法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那法院能否采信这类证据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2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第60条进一步指明:“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从这两条反推可知,对于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或收集的证据,是可以被法院采信的。在2010年的“重庆川东化工”案⑩重庆川东化工(集团)公司诉专利复审委、绵阳启明星磷化工公司专利无效纠纷案案,(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1220号。中,对于原告提交的用以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专家书面证词,一审法院认为:“因该证据系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依据授权文本能够得出与原申请公开文本记载内容相一致的结论,而该事实争议显系无效宣告审查期间的主要争议,是原告有能力提交而未予提交的证据,在其未能明确可以迟延提交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告可以不予质证,现被告不同意将该证据引入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予以准予。”该认定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不符,也因此没有被二审法院坚持。对于这一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和施行不久的新《行政诉讼法》第37条都加以了明确:“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
公知常识与其他证据一样,都是在纠纷发生前已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且任何证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作为补充证据的公知常识并不当然可以被法院采信,除非其是原告用来证明行政行为违法。在“双鹤药业”案中,专利复审委在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中认为,“在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其中给出的技术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花费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将舒巴坦与氧哌嗪青霉素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和制成复合物。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不具有创造性”,但并未给出“混合制成复合物”属于公知常识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肯定并维持了此行政无效决定。二审法院则认为专利复审委没有就其认定提供相关的依据,其作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而在再审过程中,最高院却直接采信了由专利无效请求人在再审程序中补充的、原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用以认定该行政行为合法的一系列证据,其理由是所谓的“实质公平”。实际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与此同时,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行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第1款、第67条规定,专利无效请求人的所有证据依法均应当在专利无效程序中提交,同时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专利无效请求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应当提供而未能提交的证据在诉讼程序中不予采纳,只能启动新的专利无效程序另行主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蒋利玮法官就指出:“由于受到《专利法实施细则》的限制,专利无效请求人不允许在行政诉讼中提交新证据。”①蒋利玮:《如何对待专利授确权行政案中的新证据》,载知产力:http://www.zhichanli.com/article/4601,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18日。
有研究者就“双鹤药业”案总结道:“最高院对双方在诉讼程序中补充的新证据体现了如下的采纳规则:第一,公知常识性证据予以采信;第二,现有技术证据谨慎参考 ;第三,其他证据一般不予接受 ;第四,适当给予专利权人补充证据补救权利的机会。”②毛琎、刘新蕾:《浅析创造性判断中相关证据的认定》,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2年第8期。但对此所谓的“证据规则”本文深表怀疑。首先,在上位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等)没有变更的前提下,最高院单就专利无效纠纷突破上位法的既有规定是否违法?其次,即使有必要做此突破,其正当化理由也不能是简单地追求所谓的“实质公平”。试问,难道前述上位法的规定就不追求“实质公平”吗?就算是存在所谓的“实质公平”、“效率优先”,在面对“程序正义”、“法的普适性、稳定性、权威性”以及“听证原则”、“案卷排他主义”、“避免审级损失”等诉讼法重要原理和价值时,法院又应如何取舍呢?最后,规则讲求清晰明确、一刀切,证据规则同样应如此。然而在“双鹤药业”案中,针对是否采信当事人补充的新证据这一关键问题,最高院采用“谨慎参考”、“一般”不予接受、“适当给予考虑”这样一种含蓄模糊、难以揣测的态度,视情形而变化,还能称之为“规则”吗?
有论者指出:“依据当事人在诉讼阶段提交的新证据直接得出实体结论判决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决定,应当认为是对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平衡之后的结果,即为了追求实体结果上的公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程序价值。如果不对新证据进行任何分析判断,只要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提交有价值的新证据,一律判决专利复审委根据新证据重新作出决定,则无异于鼓励当事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保留证据,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专利无效程序的价值,而且理论上可以连续不断地制造循环诉讼。”③同注释① 。实际上,前述法律规定已经体现了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的精巧平衡。其一,在专利无效诉讼中,当原告是专利无效请求人时,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其补充证据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自然不太可能出现法院是否需要对其新证据进行实质判断的问题。当然,若无效请求人确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无法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相关证据,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法院应准许其补充证据,并做实质判断,其法律依据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和新《行政诉讼法》第37条。当然,为了避免原告滥用诉权、故意制造证据突袭,法院应要求其提供之前行政程序环节无法提供证据存在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的充分证据。若作为专利权人的第三人在诉讼中补充证据,依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三)项,法院不能将此证据作为认定专利无效审查决定合法的依据。但依照新《行政诉讼法》第36条第2款,第三人又可以提出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经法院准许,行政机关也可以补充证据。此时,确实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冲突问题。考虑专利权人不可能向专利复审委请求宣告自己的专利无效,不会导致当事人的审级损失,法院应直接在诉讼中对此证据进行实质判断,而无需判令专利复审委重新审查。其二,当原告是专利权人时,因其作为无效宣告行政审查中的第三人并无举证义务,但显然有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责任和权利,法院应就这些证据作实质判断。此时不太可能产生审级损失或违背“案卷排他主义”,因为专利权人会在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穷尽一切证据来维护自身专利的效力。即使可能有某一证据因客观或主观原因未在行政程序中提出,也应准许其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提出并作实质判断,而不能判定专利复审委重新审查,因为就专利权人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审级损失或故意在行政审查中隐而不发。若作为无效请求人的第三人在诉讼中补充新证据(恰如“双鹤药业案”之情形),《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67条已经发挥了防范无效请求人故意制造证据突袭的作用,第三人如果依然提交新证据且无正当理由,则法院应不予采纳,其法律依据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三)项,而不能生硬照搬新《行政诉讼法》第36条第2款予以采信并作实质判断,否则很可能损害原告专利权人的程序价值,并助长恶意诉讼。当然,如果该补充的新证据属于决定裁判结果的关键事实,且的确是第三人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没能在前置行政审查环节提出,则法院应考虑为避免循环诉讼而予以采信并作实质判断。由此可见,最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中的错误就在于:第一,突破现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67条,《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第2款和第60条第(三)项),有刻意造法之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第二,退一步讲,即使采信第三人补充的新证据有一定的正当性(保证实质公平、效率优先),也应当要求第三人充分证明存在先前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之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并给予另一方当事人充分的质证机会和时间,但显然最高院并没有这么做。
结 语
综上可知,在目前我国专利无效行政诉讼中,清晰明确、稳定统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及是否采信并判定新证据的规则尚未建立起来。为了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效率优先”,最高人民法院忽视乃至漠视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理念,突破既有的法律规定,这种示范效应直接影响并改变了下级法院的裁判态度,也给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带来了不小的损害与困惑,这一做法应得到深刻反思与检讨。与此同时,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6条第2款由于笼统含混的表述,没有区分是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抑或是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更没有强调补充新证据须具备正当理由(令人费解的是,该条第1款却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延期提供证据的,需要证明存在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导致与现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存在适用上的矛盾冲突,而刚刚于2015年4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澄清和化解这一问题,着实有遗憾。
Rules of evidence are important mechanism on procedural interests and substantial rights of litigants. With respect to patent invalidity lawsuit, China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has established clear distribution rules on burdens of proof and new-evidence producing, while courts didn't follow the legislation strictly. In some typical cases, for chasing so-called substantial justice and priority to effi ciency, the Supreme Court overlooked basic principles and values of procedural law, such as due process; universality, stability and authority of law; right of a hearing; fi le exclusive principle; avoidance of trial-rank loss, and so on. This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discussed and rethinking deeply. The related article in forthcom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is sweeping and ambiguous, and a piece of clarify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s expectant.
patent invalidity lawsuit; rule of evidence; common knowledge; due process
熊文聪,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4T70412);“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