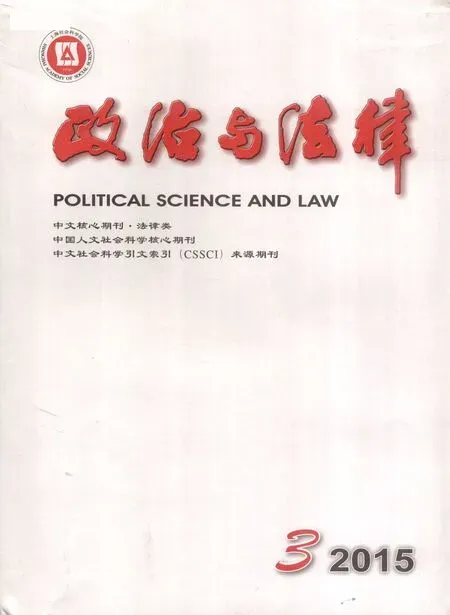论我国“单位犯罪”概念的摒弃
——以域外比较为切入点
2015-01-30黄晓亮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黄晓亮(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论我国“单位犯罪”概念的摒弃
——以域外比较为切入点
黄晓亮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近三十年的立法演进和司法实践使得我国逐步形成了单位犯罪的法律体系。由于立法技术不成熟和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等原因,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在罪名表述、犯罪主体认定标准等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在量刑和刑罚执行制度的规定上有缺失,给司法实践和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法典规定的不足与缺陷,但没有从实质层面对单位犯罪规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成熟完备的立法经验修改我国刑法,将单位犯罪彻底改为法人犯罪,将国家机关从法人范围内排除,并进一步完善刑罚制度。
单位犯罪;法人犯罪;外国刑法;修改法律
在我国,刑法与其他法律对单位犯罪的规定,经历了争论、确立、扩大三个历史阶段。①参见周振杰:《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8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修订《海关法》时增加单位犯走私罪的规定,这是我国以附属刑法方式将单位之危害行为犯罪化的最早尝试。之后,单位犯罪在有关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以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1997年刑法典生效后的刑法修正案中成为常态化的立法内容。迄今为止,单位犯罪在我国法律和刑法中的立法规定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近三十年的单位犯罪立法演进和司法实践,使得我国逐步形成了单位犯罪的法律体系。但是,我国单位犯罪之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未阻碍我国刑事法学界对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法律规定之种种不足的讨论,诸多学者扩展视野,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关于法人(机构)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和探讨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之规定的改进和完善的具体措施,使得我国在单位犯罪方面的规定与国际上法人犯罪的法律经验产生直接和充分的碰撞。相比而言,我国澳门地区关于法人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其司法适用在时间上晚于祖国大陆,相关规定因自身特色而与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国际组织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及其适用一起,成为反思和检讨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之规定的重要参照物。
一、我国单位犯罪立法模式的反思
我国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的第二章中专列一节,以第四节规定了“单位犯罪”,其包含了第30条、第31条。但这并不是我国刑法典关于单位犯罪的全部规定。我国刑法典分则、有关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还规定了各种具体的单位犯罪。对上述立法模式,在1997年刑法典生效实施以来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刑事法学界作了相当多的反思和检讨,②参见赵秉志:《单位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7页。但笔者仍感到其似乎有不够深刻之嫌。
(一)专节立法必要性的检讨
我国刑法典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以专节(第四节)规定了单位犯罪。对比我国刑法典第二章的其他内容可以发现,第一节“犯罪与刑事责任”就规定了犯罪成立的主体条件,即刑法典第17条、第18条、第19条。不过,这三个条文规定的是自然人类型的犯罪主体。有三个条文的自然人犯罪没有被我国刑法典以专节规定,而只有两个条文的单位犯罪却得到专节规定。有论者认为,这体现出立法者对单位犯罪的高度重视;不过,该论者对这种高度重视的方式妥当与否却持怀疑的态度。③参见赵秉志:《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总则之比较研究》,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第94页。从对比的角度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鲜有在刑法典中专门对法人犯罪作出规定的。例如,美国法典在第1条就规定可以构成犯罪的主体是“person”和“whoever”,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团体。连比较完备地规定法人犯罪的法国刑法典,也只不过是在通常被认为规定自然人犯罪的第121-1条之后以独立的一条即第121-2条规定法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澳门地区在其回归之前所颁布实施的刑法典中也是很简略地规定“仅自然人方负刑事责任,但另有规定者除外”(第10条)。即便是立足于我国刑法典来分析,其他比单位犯罪更重要的犯罪类型或者问题也并未以专节的形式作规定,如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在1997年3月6日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但他对此也没有特别阐述。那么,是否如有论者认为的那样,即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实为立法回应社会现实的仓卒之举,④参见郑延谱:《法国法人犯罪立法的演进》,《法制日报》2005年10月3日第2版。因而立法者未作深入考量便对单位犯罪予以专节规定呢?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我国1997年3月修订刑法典之前,单位犯罪已经出现于有关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理论界对单位犯罪或者法人犯罪的研讨也非常深入,我国刑法典规定单位犯罪并非仓促之举,之所以对单位犯罪以专节予以规定,纯粹是立法思路和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体现出立法者对刑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考虑,即因为过于重视,才考虑以专节规定单位犯罪,确立了一种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关于法人犯罪的立法例。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典第一编“总则”在第二章“犯罪”中其实没有必要以专节的形式规定单位犯罪,而是完全可以借鉴法国等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模式,将其与自然人对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一起作出规定即可。
(二)在刑法总则中位序的反思
我国刑法典在总则第二章“犯罪”最后一节中规定了单位犯罪。而前三节分别是“犯罪与刑事责任”、“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如前所述,关于自然人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处于第一节“犯罪与刑事责任”中,位于刑法典对主观罪过的规定之后。即便是加上该第一节的第一个条文、自然人犯罪主体之后的几个条文,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第一节主要规定了犯罪的构成要件,只不过该节最后两个条文(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内容,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消极的犯罪构成要件。⑤参见张永红:《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的新表述》,《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而我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第四节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其实也就是对单位这种类型的犯罪主体作出规定,即同样也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但是,该节却被置于我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的最后,让人费解。从将单位危害行为犯罪化是刑法典的重大突破这一角度考虑,以专节规定单位犯罪,或许是可以接受的立法形式。一直没有规定法人犯罪的俄罗斯,在有关部门于1994年12月向该国杜马提交的《刑法典草案》中虽设了“法人的刑事责任”专章,但并非孤立在外,而是与自然人负刑事责任的内容前后接续规定。⑥参见薛瑞林:《俄罗斯刑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于199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没有规定“法人的刑事责任”,因为俄罗斯杜马认为“法人无犯罪能力”。我国刑法典在总则第二章中将单位犯罪规定于最后一节,与其前面两节的规定(“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属于不同的内容,因为其前面两节规定的是对犯罪构成的修正问题,第四节(“单位犯罪”)规定的仍是基本犯罪构成的内容。这样的立法模式完全掩盖了作为犯罪主体类型之一的单位其实也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也割裂了单位与自然人同属犯罪主体的内在联系,因而在形式上破坏了刑法典总则第二章的体系性。相比之下,尽管含糊其辞,澳门地区刑法典对法人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却是紧随自然人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之后,即“仅自然人方负刑事责任,但另有规定者除外”(第10条)——除外的规定就是法人负刑事责任的情形。不同于我国刑法典中的规定,我国学者在有关著作或者教科书中都是在犯罪主体部分中讨论单位犯罪问题,且将该问题置于自然人犯罪的问题之后。⑦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法律条文立法涵义的思考
我国刑法典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文并没有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出界定,它是关于单位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规定。⑧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换言之,根据我国刑法典第30条的规定,不能准确地知晓单位犯罪的构成要素有哪些,而司法者单纯依赖上述条文的规定也并不能正确地认定某个单位的危害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当然,上述法律条文比某些国家或者地区刑法典的相应规定可能略胜一筹,例如,澳门地区刑法典第10条只是含糊地称“另有规定”之外非自然人也应负刑事责任,至于非自然人是否指法人,法人在何种情况下对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则完全付之阙如。但是,反观规定法人犯罪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刑事法,对法人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作出规定的立法例却占多数。例如,法国刑法典第121-2条规定:“除国家外,法人依第121-4条至第121-7条所定之区分,对其机关或者代表为其利益实行的犯罪负刑事责任。”⑨参见孙平:《试论法国法人犯罪的主体和法人负刑事责任的条件》,载李洁等:《和谐社会的刑法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而法国刑法典第121-4条至第121-7条规定了犯罪成立的行为条件、犯罪未遂、共犯的内容。根据法国刑法典的上述规定,法人的机关或者代表为法人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属于法人犯罪;显然,“法人机关或者代表”、“为法人利益”是法国刑法典所规定的法人成立犯罪的重要因素。在作为英美法系国家重要代表的美国,对联邦以及各州刑法立法有重要参考作用的《模范刑法典》在其第二章中以第7条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对法典分则的多数犯罪,若法人代理人以法人的名义在法人的业务范围内得到法人最高决策机构批准或者默许而实施,就成立法人犯罪,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少数犯罪则不需要法人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或者默许。这就意味着,根据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以法人的名义”、“在法人业务范围内”是所有法人构成犯罪所需要的条件,对大多数法人犯罪来说,还要求具备“得到法人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或者默许”这一条件。上述规定的情形还存在于其他在刑法典或者其他特别法中规定法人构成犯罪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或者地区(如我国香港特区)的法律中。通过上述对比性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刑法典第30条的规定完全没有揭示单位对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只是划定那些成立单位犯罪的主体的范围,也只具有宣示的作用。这种状况与刑事法理论界对单位(法人)犯罪的通常概念界定相差甚远。因为在规定单位犯罪的我国1997年刑法典通过和颁布实施之前,刑事法学界便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业务范围、为单位利益等问题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①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但立法者却避开对单位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使得第30条出现了规定单位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缺失,造成了一定的司法适用困境。对此困境,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纾解。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于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给出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即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
(四)关于“单位犯罪”之称谓的思考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典在总则第二章第四节以“单位犯罪”为标题通过两个条文规定了对非自然人的有关社会组织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而在理论上,对于非自然人之有关社会组织负刑事责任的问题,究竟是以法人犯罪指称,还是以单位犯罪指称,也有不大不小的争议。②参见刘生荣:《法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多数学者使用了“法人犯罪”的称谓。而从立法上看,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则》确立了法人可构成犯罪的原则,即其第110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同年1月22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我国《海关法》却使用了“单位”构成犯罪的表述,即其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自此之后,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都采用了“单位犯罪”的称谓。截至目前来看,对非自然人之社会组织负刑事责任的问题,究竟是采用“法人犯罪”的称谓,还是采用“单位犯罪”的表述,似乎已经成为不需要追问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单位犯罪”之称谓受到较为广泛的肯定,主要理由就是能够规范社会各个部门和实体的行为,对参与经济活动的非法人组织也能够予以规制。③参见陈鹏展:《单位犯罪司法实务问题释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但质疑者则认为,“单位”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不利于法治的统一,会造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④同前注③,赵秉志书,第95页。
在笔者看来,质疑者的看法似乎很有道理,却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在1987年《海关法》第47条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之前,单位亦能成立犯罪的观念已反映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有关文件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5年7月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其第2条第4项和第3条第3项中规定了“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行贿或者投机倒把而构成犯罪的情形,并规定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立足于当时的语境看,“企业事业单位”其实指的是国有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因为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尚未树立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国务院到1987年8月才发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到1988年6月才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而且,从上述具体表述中看,司法解释将“企业事业单位”置于“国家机关、团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其显然不包括私营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这一点在后来的《海关法》的起草过程中也存在。时任我国海关总署署长的戴杰于1986年11月1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草案)〉的说明》,其中指出:“为严格查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走私违法活动,《草案》规定,除对有关单位进行经济处罚外,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及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加上1987年《海关法》第47条第4款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国有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是当时社会的存在形式之一。而以“单位”概括城镇居民所属的社会组织,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社会观念,“单位”成为当时可能涉及经济犯罪的城镇社会“细胞”。针对城镇的居民(个人)而言,“单位”不仅仅发挥着经济支持的功能,更发挥了政治统合、思想管控、文化管理、治安管辖的社会秩序控制功能,成为我国的微化社会组织形式,因而其在经济性质上具有国有或者公有的特点。①参见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单位意识”也深刻和全面地影响生活在城镇中的每个人,以单位来指称某个城镇居民所属的工作实体便是人们自然而然的语言习惯。因而完全可以理解,即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也要用具有浓厚中国当代社会特色的“单位”一词,来概括对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各种形式社会组织。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依法保护,但并未改变“单位”一词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运用,相反,非国有公司、企业也逐渐承担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非国有单位”的说法颇为普遍。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遍览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可以发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在其刑事立法中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承担刑事责任的非自然人之社会组织的范围,但并不用“法人犯罪”或者“单位犯罪”这样的称谓来概括。例如,加拿大刑事法典修正案第2条规定,每人、人、所有人,及其类似用语,包括女王、公共团体、法人组织、社团、公司与郡县、郊区、城市及其他地区有权作为或者享有物权的居民,当负刑事责任。即便是用“法人”这样的术语的法国刑法典,也在其外规定了“地方行政部门”及他们的联合组织(第121-2条第2款)。但是,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刑事法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均以法人犯罪指称和概括非自然人之社会组织构成犯罪的情形。②See Andrew Weissmann: A NEW APPROACH TO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in the Vol. 44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p1319.在世界上(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民所归属的经济实体只是为该居民提供工作场合和职业发展平台,属于单一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具备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占社会组织数量最多的公司(company, corporation, firm)便成为极为重要的法律概念,其负刑事责任的情形具有代表性,可以概括和包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社会组织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即“法人犯罪(corporate crime)”。澳门地区的相应规定就很有代表性。澳门地区虽然在普通刑法典中没有直接规定法人犯罪,但在有关的特别刑法中以“法人的刑事责任”的表述规定了法人犯罪,而法人却不限于纯粹意义上的法人,还包括其他主体。③参见聂立泽:《港澳与内地刑事法律比较及刑事司法协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因此,在笔者看来,我国刑法典所采用的“单位犯罪”一词,在根本上与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格格不入。
二、我国单位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具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定,单位犯罪得以成为一个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范畴。④同前注⑧,高铭暄、马克昌书,第101页。不过,对于如何更为具体地认识和界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却仍然需要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研讨。
(一)负刑事责任之国家机关范围的界定
我国刑法典在其第30条中规定“国家机关”属于单位犯罪主体的一种,理论上肯定的认识和否定的观点针锋相对,相持不下。肯定者认为,从平等角度看,机关法人享有法人权利,故也应尽法人的义务,构成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机关判处罚金不等于对国家判处罚金,虽然有损威信,但从反面警告其不得实施犯罪行为;①参见周其华:《刑法典问题之全景揭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事实上看,国家机关也完全可以实施部分犯罪,以“‘立法机关犯罪’、‘行政执法机关’犯罪、‘司法机关犯罪’的说法不顺耳、说不过去”为由否认国家机关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并不合适。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然而,否定者则认为,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意志,不可能产生否定国家意志的犯罪意志;判处罚金,仍需由国家财政来承担,难以发挥刑罚效果;若造成国家职能的部分瘫痪,可能有损社会正义;我国从未有处罚国家机关的案例;缺乏可以借鉴的国外理论根据和立法例。③马克昌:《“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载李洁等:《和谐社会的刑法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笔者认为,与否定论者的理由相比,肯定论者的论据严重脱离单位犯罪的发生机制和防控规律,缺乏说服力,以立法规定不容否定为由的反驳也不妥当;不过,否定论者的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
首先,国外法律上并非没有国家机关成为犯罪主体的规定。应该承认,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其刑事法立法中确有将国家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形。例如,《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条第16项规定,该刑事法典所说的成立犯罪的“每人”、“人”、“所有人”及类似用语,包括女王、公共团体、法人组织、社团、公司与郡县、郊区、城市及其他地区有权作为或者享有物权的居民,而根据该条第37项的规定,“公共团体”是指加拿大政府的部门或者其分支机构、委员会、法人团体,或者在加拿大代表女王的其他团体。《法国刑法典》第121-2条在其第2款中也指出:“地方行政部门及其它们的联合组织仅对在从事可以订立公共事业委托协议的活动中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但是,需要注意,应当全面地看待上述规定,即也不能忽视上述规定并非规定全部国家机关成为犯罪的主体。按照《加拿大刑事法典》的规定,议会、法院、指控犯罪的检察机关就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按照《法国刑法典》的规定,仅地方行政部门及其联合组织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犯罪主体,议会、法院、中央政府及其部门、地方政府就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
其次,国外没有关于国家机关构成法人犯罪的理论阐述,不足以成为否定论的根据。在其他规定法人犯罪的国家或者地区,刑事法学界确实对国家机关构成法人犯罪的问题研讨不多,因而也缺乏完善的理论。但是,依笔者之见,在奉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较为完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消除了国家机关实施法人犯罪的机会,因为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法人犯罪本身就是指市场经济主体犯罪的情况,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只是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和竞争提供法律保障,已经退到市场经济经营和竞争活动之外,因而作为“裁判者”的国家机关不太可能触犯“运动员”的法律,如若有监管不力,违背公共管理职能等行为,国家机关的首脑就必须脱离“裁判者”的身份,遭受竞选失利等后果,而对于国家机关所控制的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的部门或者机构,则在其业务范围内承担提供低劣服务或者因服务不良侵犯公众权利的法律责任,若国家法律规定了刑事责任,则有关部门或者机构就要承担该刑事责任。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7条第4项指出,“‘法人’不包括执行政府计划的政府机构或者为执行政府计划而由政府机构设置的实体”。④参见刘仁文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我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形态上不具有上述特点,因而上述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国家机关成立法人犯罪之理论认识的看法也不足以成为我国否定国家机关构成犯罪的理由。
最后,以国外没有阐述国家机关构成法人犯罪的理论来否定我国国家机关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观点,不符合我国对此问题进行研讨的理论逻辑。我国刑法典总则第二章以“单位犯罪”作为第四节,且在该节的两个条文中明确地规定了哪些单位可构成单位犯罪和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问题。显然,我国某个社会组织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单位”的特征。而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司法机关,都将判断的标准相混淆,即不用是否属于单位的标准,而用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标准,去衡量非自然人的某个社会组织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典第30条所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9年6月18日通过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其第1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①该司法解释共有三条。其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不仅回避了如何认定国家机关构成单位犯罪的问题,而且,对何为单位的认定标准也非常地含糊:是否要求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具有法人资格,并未明示,似乎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不影响这些国有单位符合单位犯罪主体条件的认定;对非国有的单位,则要求是“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即需要具备法人资格。不过,两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似乎改变了该立场,其在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会谈纪要》中指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己所有,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据此规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也可以成立单位犯罪。独立资格或者法人资格不再是认定单位犯罪主体的标准。显然,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无法判定国家机关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也无法认定国家机关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单位犯罪,国外关于政府不构成法人犯罪的立法例也失去了可以借鉴的价值,而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否关于国家机关构成法人犯罪的理论,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针对这种困局,有论者尝试性地提出了国家机关构成单位犯罪的限定论,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若存在具体的相对人,且该机关存在具体的法律义务,国家机关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则可成立单位犯罪。②同前注①,周振杰书,第86-90页。笔者认为,这种修补式的论述虽说不是毫无意义,但也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何为单位。而认识该关键问题,有必要从我国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的立法背景入手来分析。有论者曾指出:“单位犯罪的增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现实司法实践的压力,‘为了单位利益且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在集体主义主导的上个世纪末的中国,如果单纯追究涉案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似乎有失公允。实际上,‘单位犯罪’在中国的出台,部分原因在于迎合‘为公’犯罪和‘为己’犯罪的刑罚差异性要求。”③参见于志刚:《刑法总则的扩张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该论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上述单位犯罪的立法折射出国家立法机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努力,国家立法机关认识到不应为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违法地压制和抹煞个人的合法权益,这对当时国家逐步建立法治、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来说,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专节形式以单位犯罪区别于自然人犯罪的立法模式,表明了国家立法机关内心浓厚的单位意识。1949年后逐步形成的单位制度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尤其是就职于国有单位的人。从法律上看,完备的国家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具体化为层级分明、井然有序的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从社会学上看,具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被安排在具体的工作单位中,党和国家通过单位将每个工作人员严格地控制起来,保证执行力量的集中和有序。①同前注⑤,周翼虎、杨晓民书,第103页。而在城镇生活的个人也通过单位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并自愿地将个人、家庭的利益与单位捆绑。只有从单位制度和单位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才能够理解国家立法机关为什么并不排斥国家机关也会成立单位犯罪的想法。在单位制度中,尽管每个单位在政治和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履行国家职责,但是,作为成员集体生存的社会共同体,单位在行使国家权力之外必须对成员承担经济和福利上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单位在其所履行的国家意志之外为了本单位成员的经济和福利而形成自我意志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实际上也不断发生。而处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的国家立法机关对此当然也是非常熟谙的,并且能够在单位之意志与所代表之国家意志、单位利益与成员个体利益之间做出区分,因而才希望通过立法将国有单位为本单位成员的小集团利益而形成的犯罪意志与其所代表或者贯彻执行的国家意志尽力剥离,将为单位全体成员之小集团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如私分国有资产)与单位成员为个体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如贪污)予以区别。而基于此种思维,国家机关作为单位而构成犯罪,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我国法律语境中也是法律平等的现实表现。在当前这种单位观念并未消失的情况下,以从法律层面维护国家威信为由否定国家机关属于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其实不具有正当性。以笔者之见,解决之道当然是修改法律,将单位犯罪彻底改为法人犯罪,用法人概念包含国家机关,并概括其他各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法人社会组织。
(二)依法负刑事责任之单位的范围扩大问题
我国刑法典第30条所规定的依法负刑事责任的单位具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以看出,该条其实采用了列举的方式来划定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不过,比较奇怪的是,不同于我国刑法典总则别处的列举性规定,国家立法机关在该条中没有以“等”或者“其他”来概括其他可能构成犯罪的单位。这样的规定很快就给司法机关造成了困扰。在司法实践中,一人公司、村民或者居民委员会、筹备中的公司企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设立后专门实施违法犯罪的公司等实施了我国刑法典分则罪刑条文所规定的单位可以构成的犯罪,能否对其按照相应的单位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呢?对此,虽然刑事法学界有着较大的争论,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还是积极地通过司法解释来试图解决上述争议问题。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将我国刑法典规定符合单位犯罪主体条件的单位限定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或者非国有单位,并排除了为实施非法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成立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会谈纪要》中又指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己所有,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也认为,符合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典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在我国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03年10月15日作出的《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而对于一人公司、村民或者居民委员会、没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的主体,目前尚没有司法文件出台。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尽管弥补了我国刑法典第30条在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上的缺陷和不足,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相关立法却从一开始就消除了上述疑难问题。澳门地区刑法典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法人犯罪,但在有关的特别刑法中却做出了一致规定,主体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容了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例如,澳门地区《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法律》第5条规定:“即使属于不合规范设立者,以及无法律人格的社团,须对贩卖人口犯罪负责。”有学者做出了总结,澳门特区法人犯罪的主体“法人”包括纯粹意义上的法人、合伙性质的经济组织(在民商法上不构成法人,但可称为法人犯罪的主体)、不合规范设立的组织(即某些组织的设立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客观上已在运作)、依照相关法律不享有法律人格的社团。①同前注④,聂立泽书,第84页。而这种立法风格并非仅为澳门地区刑法所有,在其他国家的刑事法中也存在。如前所述,《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条就将“法人组织”之外的“社团、公司”也列入犯罪主体的范围内。《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7条也规定法人、非法人团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②同前注②,刘仁文等译书,第35页。美国《组织体量刑指南》规定,其所适用的主体包括公司、合伙、团体、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信托公司、年金组织、非法人团体、政府、政党及非盈利法人等所有的组织体,③参见王世洲等译:《美国量刑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范围比模范刑法典的规定还要广。意大利2001年颁布的231/2001号法令规定了法人刑事责任的一般模式,即刑事责任可以适用于公司以及其他组织体,不论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人格”。④参见范红旗:《法人犯罪的国际法律控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当然,要求承担刑事责任的非自然人主体必须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外法律规定并非不存在。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仅法人这样的非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团体不承担刑事责任。尽管其该立法例的合理性有待分析,但是,在承担刑事责任之非自然人主体要否具备法人资格的问题上,其规定至少要比我国刑法典第30条明确一些。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典第30条所规定的可构成犯罪的单位不仅范围狭窄,且因为缺乏兜底性规定而造成了司法上的困扰。
三、我国单位犯罪处罚机制的考问
我国刑法典第31条规定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该原则在理论上被称为双罚制。但是,该条还允许特别法规定其他的处罚原则,即我国刑法典的“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国家机关坚持刑法统一性的实际情况,“其他法律”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⑤同前注⑧,高铭暄、马克昌书,第11页。单行刑法仅有一个,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刑法修正案截至目前共有八个。在我国刑法典分则和其他法律中,立法者对一些单位犯罪规定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该原则被称为“单罚制”。另外,关于单位在犯罪之后是否成立自首、立功、坦白、累犯,对单位犯罪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等问题,我国刑法典则没有规定,成为理论上争论的焦点。对此,笔者希望通过观察和分析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关于法人犯罪之刑罚制度的法律规定,来思考我国刑法典第31条中单位犯罪之刑罚制度的合理性。
(一)单罚制的规定欠缺立法价值
截至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实施之时,我国刑法典分则共规定了19种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情形,在规定模式上有两种表现。其一,明确犯罪主体是单位,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处罚。例如,我国刑法典第137条规定,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二,不明确规定犯罪主体是单位,仅对“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刑罚。例如,我国刑法典第244条之一第1款规定,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刑事法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笔者发现,双罚制才是对法人犯罪予以刑事处罚的基本原则。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7条第6项对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犯罪明确地规定了双罚制,即(a)以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名义或者代表其实施行为或者促使该行为实施时,行为人在法律上应承担相当于行为是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为了自己实施时一样的责任;(b)法律对于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规定有作为义务,如果轻率地未实施所要求的行为时,法人或者团体中对履行该义务负首要责任的代理人在法律上应承担相当于法律直接对自己施加该义务时一样的责任;(c)因对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被认定有罪时,该人应被处以自然人被认定同等级或者程度的犯罪时法律规定的刑罚。①同前注④,刘仁文书,第35页。有论者也指出,美国关于法人犯罪之立法新动向之一,就是强化对国内法人公司欺诈的惩罚,在对法人公司进行处罚的同时,强化对公司中直接责任人员的惩罚。②同前注④,范红旗书,第157-158页。不仅是美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较早和较全面规定法人犯罪的法国,经其司法部发布,于2005年12月31日生效实施关于法人刑事责任普遍化的2004年3月9日法律,且在其刑法典中以专节三目13个条文规定了对犯罪之法人的刑罚,因而在追究故意犯罪时,只要机关或者代表是为了法人的利益实施犯罪,就要同时追究自然人正犯、共犯和法人的刑事责任。③同前注⑨,孙平文,载同前注③,李洁等书,第177页。另外,同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较晚规定法人之刑事责任的意大利,其第231/2001号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国长期坚持的“法人不成立犯罪”的传统法律认识,对于有结构性疏忽的公司,须对公司首脑或者下属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从刑事程序的角度承担法律责任,即并未出现仅让代理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④同前注④,范红旗书,第302-305页。上述对法人犯罪之处罚规定双罚制的立法模式也为澳门地区刑法所采用。澳门地区特别刑法所规定的法人犯罪在处罚上均是双罚制,即法人,即使属于不合规范设立者,以及无法律人格的社团,须对相关犯罪负责;行为实体的责任并不排除有关行为人的个人责任。有论者还指出,有的特别刑法虽无此明确规定,但这一立法原则显然适用于所有的法人犯罪。⑤参见赵国强:《澳门刑法中法人犯罪之立法现状及其评析》,载同前注⑨,李洁等书,第609页。
对于我国刑法典所规定之单位犯罪的单罚制,有参与立法的论者认为:“由于单位犯罪的复杂性,其社会危害程度差别很大,一律适用双罚制原则,尚不能全面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符合犯罪的实际情况。”⑥参见李淳、王尚新:《中国刑法修订的背景与适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也有论者认为,在单位犯罪的情形下仅对责任人员定罪处罚,或者是为了保护单位利益(如我国刑法典第396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罚没财物罪),或者是为了避免损害无辜者的利益(如我国刑法典第161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或者是适应单位不存在的情形(如我国刑法典第161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⑦同前注②,赵秉志书,第167-168 页。笔者认为,这些理由不足以说明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规定单罚制的合理性。因为在个人责任与法人责任由法律明确划定的法治社会下,不可能存在单位犯罪却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例如,澳门地区相关特别刑法在对法人规定刑事责任时明确规定不排除有关行为人的个人责任,从相反的角度看,相关行为人承担个人责任,也不否定和抹煞法人本身的刑事责任。其实,对于我国刑法典所规定之上述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直接将直接责任人员规定为特定犯罪的犯罪主体,从技术上说并无困难,如我国刑法典第167条规定了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这里似乎就出现一个让人难以明白的问题——我国刑法典为什么要规定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呢?在笔者看来,根本原因还是国家立法机关(及其具体工作人员)所具有的单位意识。在单位制度的形态中,为了单位小集体的利益而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实施的犯罪,自然应当由实施该犯罪的直接负责之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承担责任,但其又不同于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在规定单位犯罪之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区分了三种责任:个人责任、为单位小集体的利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为属于社会分子之单位的利益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后两种利益重合的情况下,单位自然也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后两种利益不重合之时,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便不合情理,只需由个人承担责任。这非常明确地体现出在法人责任与个人责任关系上与前述美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澳门地区相关规定的不同特点。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刑事法的规定中,法人与其代表人、代理人或者下属人员在法人犯罪的场合下都要承担刑事责任,且互不替代。其实,在我国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单位犯罪的语境下,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滥用权力,违反法律的规定实施危害行为,已经脱离了单位利益和意志的范围,属于个人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因此,我国刑法典显然并无必要规定将近二十种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完全可以通过条文表述的调整而将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改为纯粹的自然人犯罪。
(二)单位犯罪之量刑和行刑制度尚属空白
不管是我国刑法典第31条前半段,还是该条后半段所称的“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在规定处罚原则之外,并没有对单位犯罪的其他刑罚制度作出规定。因而刑事法律界对单位能否成立自首、立功、坦白以及能否构成累犯,以及对单位犯罪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的问题,长期以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我国刑法学者越来越多地认同单位成立自首、立功、坦白以及构成累犯的观点,并呼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定。
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我国不少论者认为单位可以成立自首、立功,也构成累犯,主要的理由就是在我国刑法典关于自首、立功和累犯的规定中“犯罪分子”包括了单位。具体而言,有论者认为,单位在成立我国刑法典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刑法典第66条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若再犯该罪或者实施资助恐怖活动的犯罪(第120条之一),就有可能成立特殊累犯。①参见同前注④,陈鹏展书,第256页、第261页、第269页。还有论者指出,单位完全有可能经过集体决策后实施自首行为,因而既可以成立一般自首,又可以成立特殊自首。②参见高铭暄、吕华红:《论单位犯罪的自首》,《公民与法》2011年第2期。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似乎对此也持赞成态度,其于2002年7月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第21条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立自首,即“在办理单位走私案件中,对单位集体决定自首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的,应当认定单位自首”。2007年10月,关于单位自首、立功以及构成累犯的问题在我国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当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成为讨论焦点问题之一,③参见李洁、张军、贾宇:《和谐社会的刑法现实问题(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页以下。而肯定性的看法占据绝对多数,使得该问题似乎成为单位犯罪司法认定方面无需再行研讨的对象。但是,就上述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仍然有研讨的必要,且上述论者和司法文件的观点也站不住脚。
其一,不能确定“犯罪分子”的称谓包括“单位”。尽管我国刑法典关于自首、立功、坦白以及累犯的规定中将适用对象确定为犯罪分子,但对比整个我国刑法典中的规定,“犯罪分子”主要是指自然人的犯罪人,而不包括单位,否则,像我国刑法典关于缓刑、减刑、假释、减轻处罚等规定中的犯罪分子都要包括单位,但犯罪的单位显然不能适用这些规定;若在自首、立功、累犯的规定中承认犯罪分子包括单位,在缓刑、减刑、假释等规定中否认犯罪分子包括单位,就撕裂了刑法术语在内涵上的同一性,甚至造成选择性司法,破坏司法的公正性。
其二,我国刑法典并未就单位自首、立功、坦白以及成立累犯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对单位的刑罚,我国刑法典第31条仅规定“判处罚金”,没有提及是否适用相关的刑罚裁量制度,而我国刑法典总则第三章“刑罚”第六节“罚金”以两个条文(第52条、第53条)规定了罚金的裁量原则、缴纳方式,因而按照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对单位适用罚金不存在疑难问题;而且,我国刑法典第31条后半段还规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但是,关于对犯罪之单位能否认定自首、立功、坦白以及累犯的问题,我国刑法典分则和其他法律(如单行刑法)却并没有作出任何的规定。有论者甚至认为,犯罪之特定单位还可以成立我国刑法典第164条第3款规定的行贿人特别自首。①杨辉忠:《论单位自首的类型及其认定》,载同前注①,李洁等书,第420页。在笔者看来,上述认识以及前述《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纯粹是从逻辑和语义的角度所作的解释,仅限于个别的单位犯罪,缺乏单位犯罪成立自首(累犯等)的普遍性启示意义。而且,过多地牵强附会,就有可能突破我国刑法典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其三,关于犯罪之单位或者法人,只有在刑事法明确规定特定量刑和行刑制度的情况下,才有成立自首、立功以及构成累犯的可能,才可能享有刑罚执行中的权利。在此方面,法国刑法典对构成犯罪之法人的量刑和执行制度规定得较为详尽。法国刑法典除了从其第131-37条至第131-45条规定了适用于法人的刑种外,还规定了法人成立累犯的条件和处罚原则(第132-12条至第132-15条)、对法人适用缓刑的条件和效力(第132-30条至第132-39条)、对法人犯罪的刑罚消灭(第133-1条至第133-17条,其中有时效、特赦、大赦、复权)。相比之下,美国对法人犯罪规定的刑罚制度比较少,主要是缓刑制度。例如,美国量刑指南规定了非常广泛的法人缓刑适用条件,具体包括:(1)为了保证赔偿的支付、补偿令的执行和社区服务的完成;(2)为了保证该组织及时付清罚金及其他财产性惩罚;(3)为了督促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组织建立有效的防止与发现违法行为的制度;(4)为了保证对该组织的整顿以便降低再犯罪的可能性。这在《美国模范刑法典》也有反映(第6.4条第1项),即“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受有罪认定时,裁判所得犹豫其刑之宣告”。②同前注②,赵秉志书,第176页。这当然值得我国刑法典借鉴和吸收。不过,也有某些国家或者地区对犯罪的法人仅规定判处罚金、解散,没有规定量刑和刑罚执行制度,因而司法机关也就无需考虑犯罪之法人成立自首、坦白或者累犯的问题。例如,澳门地区特别刑法对法人犯罪仅仅规定了适用于法人的刑种及执行方式与适用于非法人团体的刑种及执行方式。③同前注③,聂立泽书,第85页。显然,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之量刑和刑罚执行制度完全没有提及,才造成了司法实务和理论上的纷纭争议。而澄清和解决这些争议,只有立法完善这一途径,单纯依靠司法解释,就有破坏法治之虞。
四、结 语
国家立法机关在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态的转型时期规定了单位犯罪,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走进市场经济社会的宏观决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计划经济形态下单位社会制度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规定随着其不断被适用而逐渐显现出内在的问题和缺陷,造成了诸多的司法困惑,在一定意义上说逐步落后于时代。对于这些问题和缺陷,我国刑事法学界却并未突破单位犯罪的范畴,仍在单位这一用语的语境中讨论单位犯罪的成立要件、司法适用、立法完善。尽管不能否定这些研讨的积极意义,但是,以笔者之见,不改变单位犯罪这样的表述,就无法彻底抛弃计划经济年代所形成的单位制度和单位意识,就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的现实需要,相反,在单位意识的影响下,对非自然人之社会组织(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参与经济竞争和社会生活所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思考,就有可能将作为市场经济基本主体的法人与计划经济时代权责不分、政企混合的单位相混淆,在本质上偏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目标。因而,不脱离单位这一术语所具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就无法准确地对我国所谓单位犯罪的内涵外延、完善刑罚制度作出合理的分析和界定。笔者在本文中的尝试,便是尽可能充分地参考和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在法人犯罪方面的立法经验,以检讨和反思我国刑法典关于单位犯罪之总则和分则规定的不足,寻求改进和完善的新路径,希冀国家立法机关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建构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人犯罪制度。
(责任编辑:杜小丽)
DF623
A
1005-9512(2015)03-0029-13
黄晓亮,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系赵国强教授主持之澳门基金会项目“中国内地与澳门法人犯罪之比较研究”[课题编号:MYRG22(Y1-L1)-FLL13-ZGQ]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