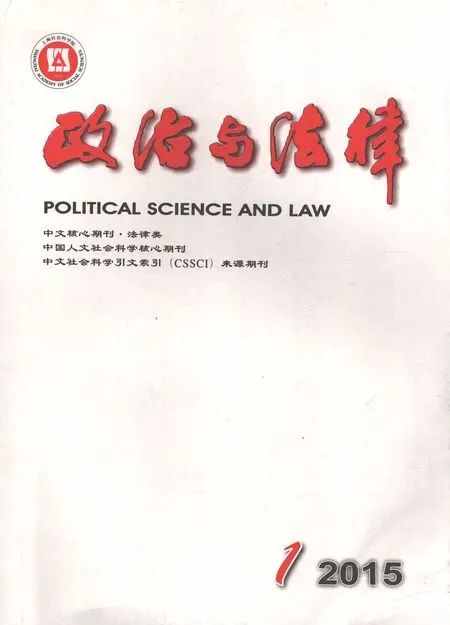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
2015-01-30尹建国
尹建国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
尹建国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合理、准确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是实现网络信息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立法规定和治理实践,尚存在粗放型、碎片化、不统一、不科学等不足。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应接受行政均衡、平等对待等法律原则指导,还应充分考察、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基于文化传统、法治现状等因素,可将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类型化为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网络有害私信息三类,并遵循从严到宽的解释口径,综合适用表达内容中立、明显而即刻危险、事后限制等判定标准。在理论论证和实践总结基础上,可对既有立法进行重述:制定统一的一般性条款,列举网络有害信息基本类型,辅之设计“三层次”的判断标准。实践中,可通过制定行政解释基准、创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库及发布司法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等形式,实现对网络有害信息的统一解释。
网络有害信息;网络信息治理法治化;表达自由;网络法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泄密、网络色情、网络欺诈、网络诽谤、网络煽动、网络恐怖主义等逐渐成为网络安全新的威胁因素。世界范围内,政府对传统媒体正从严格管制逐渐走向放宽管制;而网络媒体规范环境的发展趋势恰好相反,正从无人管制日益走向增加管制。①参见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法学》2001年第7期。政府管制网络信息,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突出难题:如何应对干预言论自由的质疑?如何在网络信息安全维护与网络表达自由保障间保持适度均衡?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政府如果疏于监管,将令互联网陷入混乱,最终将会影响并破坏现实世界之各项秩序。运用各种监管手段进行监管,弥足珍贵的言论自由、来之不易的民意表达渠道,又将处于公权侵害的阴影之下。面对错综复杂又满载希望的网络热土,政府既应发挥作用、践行职责,又应保持开明、有度。清晰、准确、合理判定“网络有害信息”之内涵与外延,不仅体现着一国网络信息规制的口径和网络权益保护的程度,也是一切后续治理行动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学界对网络有害信息之研究多围绕治理策略展开,对网络有害信息本身范围之判定反倒涉猎甚少,更未形成统一共识。既有立法虽作了相应规定,但缘于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规范位阶的不平等、条文设计的粗放型等特点,相关立法在统一性、合理性、明确性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欠缺,客观上也造成“同案不同判”、恣意解释、权力滥用、适用困难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对我国网络信息规制既有法律条文进行系统梳理基础上,结合对系列个案的实证分析和对域外法治实践、表达自由法理的比较观察,勉力为我国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类型建构、法律重述和统一解释等提出建议。
一、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现存问题
截至目前,我国仍未就网络信息治理制定统一立法,但涉及网络信息治理某一方面问题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却数量众多。其中,直接列举网络有害信息范围的规范条文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2条至第4条、《电信条例》第17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57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19条、《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第19条、《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9条等。综合上述规定,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法定类型主要包括14种。②此外,另有一些规范文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别立法色彩,所规定的往往是某个具体领域的社会治理问题,相应的网络信息也仅指涉该领域。例如,《国家安全法》第4条、《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8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4条至第6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等。这些条文主要存在于特别立法或特别法律条款之中,针对的对象特定,缺乏普遍代表性。
根据已有立法,主管机关渐次开展了针对网络有害信息的治理活动,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工作机制。整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操作策略:一是集中于某一特定时段推行运动式或专项式的集中整治活动。如公安部2012年会同九部门开展了整治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专项行动。③参见辛明:《九部门部署网络和手机“扫黄”专项行动》,《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28日。二是通过常规监管,对违法发布、传播网络有害信息的个人或组织,进行个案处罚、制裁。其中涉及的有害信息主要包括六类:(1)政治性有害信息,典型案件如任建宇案等;④参见朱巍:《希望任建宇获释不仅是个案的胜利》,《新京报》2012年11月20日。(2)网络谣言,典型案件如“秦火火”等传播网络谣言、非法经营案等;⑤参见黄庆畅:《网络谣言,如此炮制》,《人民日报》2013年8月22日。(3)色情、淫秽信息,典型案件如“奸夫淫妇导航”传播色情信息案等;⑥参见白炜:《一批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件宣判》,《中国文化报》2010年11月27日。(4)违反社会公德信息,典型案件如重庆女生地震后发表麻木感言案等;⑦参见苏显龙:《网络表达如何拒绝“暴力”》,《人民日报》2008年6月27日。(5)侵犯名誉权信息,典型案件如金山诉360董事长周鸿祎微博侵权案等;⑧参见杨清惠、梁小立:《国内“微博第一案”终审落槌》,《中国审判》2011年第10期。(6)泄密、侵犯隐私权信息,典型案件如王某、毛某泄露王立军侦察信息案等。⑨参见朱光泽:《成都一男子因泄露王立军案航班信息被拘留》,《成都日报》2012年10月13日。此外,在极其例外的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府也会采取全面的网络管制措施,从源头上限制网络使用,最典型表现是新疆2009年的“断网”事件。⑩参见《秦刚:暴力事件发生后新疆断网是维稳需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zuixinbaodao/200907/ 0707_7229_1238573.shtml,2014年2月18日访问。
总体而言,以既有立法为依托,我国网络有害信息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相关立法在统一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方面仍有欠缺,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标准仍不甚清晰。
第一,立法用语高度抽象,留有过宽的解释空间,易于导致适用困难和权力滥用。既有法律条文中,国家安全、党的安全、国家秘密、国家荣誉和利益、民族仇恨、民族风俗、民族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公德、邪教、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侮辱、诽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概念,均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既有可能因难以统一把握解释口径,导致“同案不同判”;也有可能被恣意进行扩大解释,限缩公民表达自由空间,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
第二,既有立法位阶偏低,各规定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统一现象,有损于法制的权威与统一性。我国现有相关规范文本,以法规、规章、政策文件等居多,没有法律层面的统一文本。这不仅滞后于网络法治发达国家,而且违背了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应由立法规定之“法律保留”原则的基本要求。同时,既有立法对网络有害信息之规定,仍存在较多不统一、不协调之处。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了9种网络有害信息类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增加为10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再增加为11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则完全打破既有立法体例,将网络有害信息界定为三大类共12种。其关于各类有害信息的表述内容及方式,与既有法规和规章等也有明显差别。显然,我国有关网络有害信息范围的立法呈现着较为明显的碎片化、差异化特点,这反映了相关立法在起草、审议等过程中所做的系统梳理、整合尚存不足。
第三,立法及实践中对政治性信息限制过多,易于堵塞监督政府、揭发检举、建言献策的民意渠道,有损于政府与民众间的互信与合作基础。网络是公民表达诉求、监督批评政府的重要渠道,但近年来,我国网络表达空间有被收窄的倾向。诸多关于政府、官员、时政的讨论、批评、揭示言论,或被屏蔽掉关键词,或被删除、禁发,消息发布、传播者有时甚至因之被不法拘禁。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部分政府沿袭威权治理思维、部分官员法律意识淡薄、网络服务商谨小慎微有一定关系,但立法对政治性信息本身的过多、过严限制,则为这种不合理行为提供了依据与便利。其典型表现是,现有立法规定的14种有害信息,其中8种都涉及国家利益、政治秩序、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问题,均或多或少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实践中的众多政治性言论审查案,更是广受质疑。例如,针对任建宇案,有学者评论称:“公民对公共事件的褒贬,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评价,乃至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或调侃,都应该属于正常表达自由的范畴。”①朱巍:《希望任建宇获释不仅是个案的胜利》,《新京报》2012年11月20日。整体而言,在网络政治性信息审查案中,各界对政府滥用权力、控制言论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明确反对态度。众多案件最终被纠正的结果,也客观印证公权力机关在判定此类网络有害信息过程中确实存在滥权风险。
第四,对侵犯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等私权的网络有害信息之判定及审查却力有不逮。从治理效果看,我国对网络诽谤、造谣、侵犯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等网络信息之治理,政府的可为空间、权力边界仍不清晰,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间如何形成配合与互补关系,也缺乏制度设计和法律调整。相关立法判断标准模糊、法律解释随机性、裁量余地过大的弊端,也增加了类似案件中的法律适用争议。例如,在杨某转贴夸大胶济铁路事故死亡人数案发生后,南都网曾组织网络投票,网友认为杨某不该被拘留的有1292票,认为他该被拘留的仅90票。②参见谭人玮:《“普通网友转帖被拘”追踪一张图导致被拘5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9日。
二、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指导原则与审查标准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表明,全面界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是维护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的必然需要。但尊重公众表达、知情等基本权益,严格界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则是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妥当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需在维护网络信息内容安全与公众表达自由等基本权益间保持均衡。为实现这种均衡目标,需接受宏观法律原则的指导并以微观的审查标准为工具。
(一)指导原则
从法理上讲,当两种不同权益发生冲突时,通过划定权益间“界限”的方式消解分歧,是传统做法。这种方法的理论前提,可追溯至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原理。按其观点,权利是交叉重叠的,在两个权利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界限,除非我们专断地认定一个界限并声称这就是互不侵犯的界限。③参见熊静波:《表达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与调和——从基本权利限制理论角度观察》,《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其方法论基础是:“由于我们不能够指望增加利益资源来解决大多数的权利冲突,于是,人们最为关注也是最常用的解决模式便是为各种权利设置相应的义务或者限制,从而界定各自的权利边界,以消除权利的冲突。”④李友根:《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初论》,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0-291页。该理论与方法,契合了均衡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与表达自由双重权益的现实需要。从正当性上看,国家干预言论自由,只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障言论自由本身的有效实施;二是当保障言论自由的价值与宪法保障的其它价值发生冲突时的一种取舍。⑤参见陈桃生:《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及其规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取舍之标准,则在于干预措施所保护法益与所限缩法益之间的衡量结果:若所限缩的法益重于所保护的法益,则干预措施不具有正当性;反之,干预就是可行的。⑥See 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trans.by Julian Riv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2.基于权益界限划分和法益衡量的理论与方法,判定网络有害信息应恪守之基本要求,可归结为行政均衡和平等对待两项指导原则。
首先,当判定网络有害信息之目的集中于保护国家安全、党和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民族团结、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社会秩序、社会公德、优秀传统等权益时,涉及的主要是公共利益与个人表达利益等的调整与均衡关系,应遵循行政均衡原则。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问题上,“公共利益超过个人利益”,⑦[法]马里旦:《人权与自然法》,倪建民译,载法学教材编辑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2页。“个人的眼前利益要服从集团的利益”。⑧[苏]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李光谟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由此,一般共识是,当网络信息危及公共利益时,应认定系属有害信息,应对相应私人表达加以限制。诚如有学者所总结的,“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人权的享有和保护往往让位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即便是在今天,任何国家公民良心和表达的享有都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⑨黎尔平:《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与表达自由》,《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1期。
然而,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不能成为漠视个人利益的绝对理由。现代行政法上的均衡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面对多种适合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相对人限制或损害最少手段;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行政目的的价值。⑩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60页。当网络有害信息涉嫌侵犯公益时,其一般属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范畴,这与侵犯私益有害信息主要可由被侵权人通过民事途径追责不同。一旦公权力介入对网络信息的治理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网络表达自由的“脆弱性”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另外,这类网络信息以政治性信息为典型代表,政府对其往往具有钳制的天然惯性,由此更易导致不良后果。对这类信息如果限定过宽、打击过重,将会造成禁言的恐惧。“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安定。”①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月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页。
在判定危及公共利益的网络有害信息范围时,应秉承最小侵害标准最大程度限缩其范围,此类网络有害信息不仅在立法中应做明确、具体和严格的限定,在具体适用时也要遵循严格解释原则,不得恣意做扩大解释。换言之,当网络信息涉嫌侵犯公益时,应受到监管,但这种网络有害信息本身之范围应受到立法的严格限制,相关条文的解释口径也应比危及私益之网络有害信息狭窄。
其次,当判定网络有害信息之目的指向平衡不同私益关系时,应遵循平等对待原则。平等对待要求行政机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或按比例对待”。②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据此,行政机关对信息发布、利用者的表达自由及信息指涉对象的私益等应同等对待,执法时力求中立。
在我国,涉及私益的网络有害信息,包括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网络侵权、诽谤和造谣等信息。这类信息的最大特点是,侵犯的是相对明确主体的私权益,而非抽象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这类信息政治敏感度低,对其限制往往也易于获得社会认可。所以,在立法及执法中,可加大对这类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一定程度上可通过完整、充分的立法规定,将可能侵权的信息充分涵盖在内。在具体个案中,则可通过执行科学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之一般原则,将网络信息是否有害的证明责任留给主张权利一方。在没有相对人提出异议情况下,行政机关一般不擅自臆断并直接限制该当信息。
简言之,立法对危及私益的网络有害信息范围之设定,应相对更全面一些,在解释此类网络有害信息时,则可遵循从宽原则。在该当信息的审查过程,发布者和异议者权利和义务对等,主管机关的地位和立场应是中立的。
(二)审查标准
为贯彻言论审查的上述原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逐渐发展出一系列微观操作标准,如恶劣倾向、明显而即刻危险、事后审查、表达内容中立、优先地位、法律保留、保障为主限制为辅等。③参见秦前红、陈道英:《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下),《信息网络安全》2006年第5期;王四新:《限制表达自由的原则》,《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杨君佐:《发达国家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模式》,《法学家》2009年第4期;尹建国:《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之启示》,《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其中,如下几项标准不仅内容明确、立足于现代法治共识,且比较吻合我国网络法治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原则立场,可考虑在我国予以借鉴与移植再造。
第一,“明显而即刻危险”。该标准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诉合众国”④See Schenck v.United States,249 U.S.47(1919).、“Abrams诉合众国”系列案件中创立。⑤See Abrams v.United States,250 U.S.616(1919).根据该原则,“只有政府证明明显而即刻的具体言论可能导致骚乱或其他严重的颠覆性犯罪,而这些都为政府所禁止,你才能受到惩罚”。⑥See James Macgregor Burns,etc.,Government by the People,4th edition,New Jersey:Prentice Hall College Div,2001,pp.136-137.该标准本身是严格的,但具有较大弹性。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政府结合经验据实确定。不过,也有学者对该标准提出质疑。例如,著名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批评该标准背离美国宪法,混淆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给予不同言论不同保护之立场,他认为给予公共性或政治性言论以绝对保护才是美国宪法的真实含义。⑦参见[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但世界范围内,“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一直广受讨论以致认可,其主要原因在于,相比其他标准,在正确理解与适用基础上,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可以较好地保护表达自由,又不至于置其他利益于无可保护之地。所以,在更加重视国家、集体利益的其他国家与地区,该标准深受推崇。
第二,事后限制。事后限制是相对于事前限制而言的,目的是防止言论审查者的主观臆测及专断蛮横。该标准主要通过“尼尔诉明尼苏达”案⑧See Near v.State of Minnesota Ex Rel.Olson,283 U.S.697(1931).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⑨See New York Times Co.v.United States,403 U.S.713(1971).等系列判例确立。其内涵是,政府对媒体和个人的不当言论,只能采用事后方式加以追惩,而不得意图以事先方式加以提前禁止。对表达加以事先限制的任何制度,都应强烈地推定其违宪。
第三,表达内容中立。该标准主要成型于“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⑩See Tinker v.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393 U.S.503(1969).指不对表达的内容本身进行限制,而仅对言论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作形式方面的审查与限制。至于何种时间、地点、方式符合限制标准,则需通过个案权衡的方式加以确立。例如,法院在“马丁诉斯特拉瑟斯”案中全面禁止到住宅游说、散发传单和拉顾客的行为;①See Martin v.Struthers 319 U.S.141(1943).在“贝瑟尔学区403号诉弗雷泽”案中确定学区可惩戒在学校会议上发表猥亵言论的学生等。②See Bethel School District No.403 v.Fraser,478 U.S.675(1986).
整体而言,域外国家针对言论限制的具体标准,虽存在随案变动差异,但基本共识正逐步形成。这些标准及理论,构成审查主体在个案中进行利益权衡时必须考量的基础。
三、网络有害信息范围的类型建构
从比较经验看,根据表达内容和目的之不同,对信息予以类型化,并依其属性,在法律上实施不同的保护和限制,是常见和有效的信息治理策略。如在美国,法律界倾向于把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公言论主要指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言论,典型形式是政治性言论;私言论指直接关系公民个人物质利益和人身权利的言论,主要包括商业言论及有关个人私生活的言论。③参见[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法律界多强调公言论享有绝对表达自由,应受宪法特殊保护。
我国现有立法未对网络公、私言论予以区别对待,实践中,对政治性言论则明显限制过多。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现行网络信息治理的行政法规、规章等,多由政府基于行政管理效率和社会控制目的制定,对政府审查权力的边界设定较宽,未能严格遵守有限政府的基本要求。另外,媒体被视为政府“喉舌”的传统媒体观并未得到根本扭转,政府未能以足够宽容、开明态度对待网络新媒体。④参见尹建国:《政府与网络新媒体相互关系的反思与重构》,《科技与法律》2013年第3期。在现代法治社会,对公共言论控制口径宽窄之争,形象地反映了政府与公众针对表达自由边界的不同认识:对政府而言,政权的稳定与权威不容挑战,基于政治安全需要可对表达自由予以限缩;对民众而言,自由地批评政府、表达诉求、反映心声,是法治、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不得专制、武断干涉表达自由。对任何国家而言,若要真正构建一套能同时满足政治需要,并符合民众期待的有害信息判定机制,均须正视上述分歧,并均衡兼顾两方面的需要。
从实施效果看,域外将言论分为公言论与私言论并予以区别对待的经典理论与方法,值得肯定与借鉴。同时,应在结合本国国情基础上,对上述二分法及相应审查标准作进一步细化与补充。诚如有学者所言:“将表达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就必须承认各国立法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植于各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的诸多不同。”⑤罗楚湘:《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及其限制——兼论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美国视言论自由为民主基石和现代宪政的起点,这是其坚持对公言论持宽松治理态度的制度前提和社会基础。在我国,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分结构,往往被作为讨论权力、权利、制度等现实问题的基本背景。⑥参见李拥军:《论市民社会的权利——对个人、社会、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王宝治:《社会权力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的辨证思考——基于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架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王淑芹:《国家、社会、个人:中国梦的价值主体》,《光明日报》2013年4月10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也强调: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是相对独立又辩证统一的,“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多被划分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且,相对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定优位性。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对私人利益进行一定限制的政府行为,客观上也往往获得相对较多的正当性支撑。基于对这一哲学观念和现实状况的认识和权衡,笔者建议在公、私言论二分基础上,按网络信息涉及权益之不同,进一步将其分为三类:网络政治性信息、网络社会性信息、网络私信息。⑧从语意讲,“信息”的内涵与外延要广于“言论”。言论主要指语言文字,信息则可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种形式。在网络上需规制的信息内容,既包括文字,也应包括图片、音视频等。本文在类型化时,倾向于使用“网络信息”一词。相应地,将网络有害信息类型化为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网络有害私信息三类,三者分别对应着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私益的侵犯与威胁。在类型化基础上,依次对三类有害信息适用从严到宽的判定标准。
(一)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
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指涉嫌危害国家政局稳定、国家统一、国家秘密、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荣誉等国家利益的网络信息。政治性信息特别受到政府关注。这既为人性本能使然,也有维护国家利益、时局稳定的客观考虑原因。不过,政府压制政治性信息,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国语·周语上》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在法治程度高度发达,追求民主、自由的当下,政府理应秉承开明姿态与胸怀,容纳不同甚至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因贫富差距、地域差异、民族隔阂、机会不等、受教育程度不同等原因引起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很容易被集中到对政府的批评、责难之上。此时,政府若动辄以触及政治敏感问题或稳定为由,对这些信息强加限制,不仅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序控制,还可能因堵塞建言献策、批评、宣泄渠道,积累更大的社会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政府不能因担心民众分享某种观念而作出有害行为,就对某种观念的传播采取干预行动。这是一种应当摒弃的家长制作风。”⑨Richard A.Epatein,E.Allan Farnsworth,Ronala J.Gilson,Constitutional Law,third edition,New York:Aspen Publishers, 1996,pp.1329-1330.换言之,“个人对政府的政策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相反,一个社会不能容忍反对派声音的出现说明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了沟通和交流……(政治性)表达自由权的拥有和维护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弥足珍重”。⑩黎尔平:《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与表达自由》,《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1期。
显然,对网络政治性信息理应秉持宽松治理立场,相应地,在判定政治性有害信息时则应坚持严格审查标准,为政治性信息松绑。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精义,也符合我国政府开创开明政治风气之长远需求。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倡导让人民看到希望、构筑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之执政理念。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表达环境,让人们能够自由批评、监督政府,实现国家权力的规范有序行使,则是“中国梦”的重要构成内容和保障。①参见《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7日。比较信息审查的各类标准,不触及实质内容审查的表达内容中立标准无疑最为契合该要求。遵循该标准,将不对政治性信息的内容本身进行限制,而仅对其发表时间、地点、方式等作形式方面的审查与限制。
(二)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
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指涉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信息,其处于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与网络有害私信息之间,与两者均有重合之处。例如,煽动非法集会的信息,涉嫌同时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处于社会性有害信息与政治性有害信息的交集。其对社会利益之破坏更直接和明显,故倾向于将其归为社会性有害信息。散布谣言的信息,既有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也有可能侵犯特定对象的私人利益,如为前者应被归为社会性有害信息,如为后者应被归为有害私信息,若同时侵犯了两方面的利益则宜将其归为社会性有害信息。因此,此时即便没有受害人提出主张,主管机关也可依职权主动审查该当信息。显然,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的外延较为宽泛,其判定及审查机制也应是多层次的。根据信息内容及危害程度之不同,可将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区分为两类:其一,涉嫌危害公序良俗的网络社会性信息,其主要指危害社会公德、文化传统、民族风俗、习惯的信息等。其二,含有其他立法明文禁止内容的网络社会性信息,其包括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等。
判定某类信息危害公序良俗,应采相对严格标准。一方面,涉及公序良俗之网络信息,包含着价值判断成分,而价值判断标准是多元的且具有历时变迁性,任何主体包括立法者和行政官员,都不能独自坚持只有自己的判断才是符合文化、传统或道德判准的。另一方面,法律不能禁止思想自由,不能强制人具有特定思想或道德观念。政府可通过教育、引导等手段,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倡导人们加强自律,却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去推动,否则便会模糊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边界,导致国家权力侵入公民思想自由和行为自治领域。因此,这类有害信息之判定标准,严格程度应不亚于政治性有害信息。基于此,笔者赞成对此类信息同样坚持表达内容中立标准,监管者仅在有充分理由情况下可以“限制”此类信息的发表时间、地点和方式,却不能“禁止”信息内容本身。
对含有其他立法明文禁止内容的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进行限制,则具有相对而言更多的正当性。这类有害信息侵犯的法益明确,且一般有在先的实然法为依据。对这类信息之判定,应遵循“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即仅在此类信息之危害同时满足“明显性”和“即刻性”两项标准时,方可对之予以限制。“明显”和“即刻”与否,应由执法者在个案中据实判定,但执法者在解释口径上拥有一定裁量权。例如,煽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信息具有相对更多政治色彩,与政治性信息更接近;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等信息则政治色彩弱,对其治理的社会认可度也更高。故在具体适用“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时,对前者应适用相对严格的解释口径,对后者则可适用相对宽松的解释口径。这种宽、严口径之把握,属执法者的行政裁量权范畴,②执法者在解释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应严格说明理由,需将进行裁量时所考虑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政策、道德、舆情及相应权衡取舍理由加以充分说明,以增强相对人的自觉接受性并便于法院的事后审查。参见尹建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说明理由》,《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法院也可进行事后审查与矫正。
(三)网络有害私信息
网络有害私信息指涉嫌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私益的网络侵权、诽谤、造谣等信息。这类信息最大特点是,其侵犯的是相对明确对象之权益,而非抽象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正因如此,这类信息的“有害性”理应以有被侵权人提出异议为前提。相对人提起异议,只是对该当信息进行限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是否真正有害,还需有权机关予以事后判定。此时,判定机关应居超然的中立地位,采取平等对待态度判定相应信息是否构成侵害私益。为保证判定机关的中立地位,防止权利人滥用异议权,有一项有效且成文的在先制度可供借鉴——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信息的认定及处理机制。具体而言,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规定了完整的处理网络著作权侵权信息的“通知——删除”规则,其要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著作权侵权通知后,应删除信息或链接并向信息提供者转送通知;但当接到否认侵权的反通知后,应恢复信息或链接,并转送反通知;接反通知后,权利人不得再通知删除,只能启动诉讼等公力救济程序。其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作品传播的中间环节,其对侵权损害主要承担补充责任,③参见张新宝主编:《互联网上侵权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自身也没有能力判断权利人与服务对象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无权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权利人若不服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民事纠纷。④参见张建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网络服务提供者需兼顾双方利益之立场与网络主管机关可谓高度一致。网络主管机关一方面应保护网络用户的表达自由等权益,另一方面也应该保护信息所指向相对人之名誉、隐私、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私益。兼顾双方利益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充当中立者,而不偏向、涉入任何一方。
参照上述制度,可构建适用于网络有害私信息的判定及处理机制。其一,对实名发布的私信息,权利人对此类信息提出侵权异议后,处理程序如下: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侵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信息并向信息发布者转送通知;信息发布者接通知后,若认为信息未侵权,可提交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反通知后,应恢复信息并转达反通知;权利人接反通知后,若不服可向法院起诉,通过侵权之诉解决民事纠纷;对于还需承担行政违法责任的事由,权利人可同时向行政机关举报、投诉,行政机关居间决定是否补充实施行政处罚。其二,对匿名或化名发布的私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因无法向权利人提供反通知和发言者的真实信息,可根据行业自律规则和企业精神、与用户缔结的经营协议等,自主决定是否删除信息。对其处理决定,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均有两种选择:一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被告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法律判定其是否应删除相关信息,并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向行政机关举报、投诉,行政机关若认为相关信息构成行政违法,可要求删除并处罚;若认为仅构成民事侵权,应告知举报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必要情况下,行政机关还可采取技术手段查明信息实际发布者,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任何一方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指令或处罚不服,应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建立信息发布、利用者和权利人间的身份披露机制,搭建双方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和鼓励司法求诉路径,可压缩政府的滥权风险,也可降低其涉入私益纠纷的法律风险,还可最大程度保护信息发布和利用者的合法权益。
四、网络有害信息范围的法律重述
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针对网络有害信息的判定与治理,我国本应制定更完善、系统的法律规范。但直至目前,我国相关立法仍存在位阶偏低、体系分散、内容不统一等问题。新形势下,有必要修订、完善既有各类规范的核心条款,并着手制定一部统一的《网络安全法》(或《网络信息安全法》)。在统一立法过程,重述网络有害信息立法的一般条款、具体类型、判定标准是工作重点和迫切任务。
(一)从限制和保护双重角度制定概括式的一般性条款
从立法学角度讲,立法模式一般有“概括式”和“列举式”两种基本模式。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采取了“概括肯定+列举否定”的混合立法模式,⑤参见应松年:《行政救济制度之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民法通则》在规定侵权行为及法律责任时则基本采用“全面一般条款+全面列举”立法模式。⑥参见张新宝:《侵权法立法模式:全面的一般条款+全面列举》,《法学家》2003年第4期。从效果看,概括式和列举式模式,各有优劣。前者涵盖范围全面,但相关条款可操作性一般不强;后者内容明确、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但往往因列举难以穷尽而出现遗漏。网络有害信息范围之判定,是开展一切后续治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故应首先设计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一般条款,以将其范围边界加以整体廓清。同时,考虑到立法规则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需要,也应尽量明确列举确有限制必要的有害信息类型。换言之,界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宜采取“一般概括条款+具体列举条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如此,能同时实现全面、明确、可操作性等多维目标。
以概括方式界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既有的立法和司法判决都有尝试。例如,1996年5月9日,公安部针对内蒙古公安厅请示作出《关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涉及的“有害数据”问题的批复》,认为有害信息(数据)指“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存储介质中存在、出现的,以计算机程序、图象、文字、声音等多种形式表示的,含有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破坏民族团结等危害国家安全内容的信息;含有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凶杀、教唆犯罪等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内容的信息,以及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和功能发挥,应用软件、数据可靠性、完整性和保密性,用于违法活动的计算机程序”。再如,在“陈堂发诉杭州博客信息公司”案中,我国法院首次在判决中对网络有害信息做出明确界定:网络系统中传播的对国家、社会或他人合法利益构成威胁或损害的不良资讯,包括危害国家利益、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连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资讯。⑦参见王建军:《首例博客告博客案原告一审胜诉》,《法制日报》2006年9月12日。
比较而言,公安部批复的界定,未能将破坏经济秩序、危害私人利益等有害信息包含在内,不尽全面。同时,界定方法也未能脱逸列举式的实质结构,仅是把列举的有害信息类型变换了表述方式而已。反观法院判决中阐述的定义,相对更概括、凝练,且同时涉及了三层次的有害信息类型,该界定方法与实体内容更值得肯定。前文曾论证将网络有害信息区分为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网络有害私信息之正当性,以此为基础,并借鉴个案中的上述界定方法,笔者建议将规定网络有害信息的概括立法条款设计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危害国家利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同时,为防止政府滥用审查权,侵犯表达自由等权益,需另设计一条专门针对该条款的限制条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滥用网络信息审查权力,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利用网络表达观点、思想的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
(二)统一列举具体类型
设计一般条款后,接下来应以列举方式将网络有害信息基本类型加以列明,以增强法条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在设计列举条款时,应系统梳理、整合已有规范文本中列举的各种类型,促成法制统一。
基于网络政治性信息、社会性信息和私信息的三分结构,建议在统一立法中,设计三项列举条款明确规定网络有害信息类型。其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发表含有以下内容、危害国家利益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党和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其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发表含有以下内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其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发表含有以下内容、危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的信息:侮辱或者散布谣言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暴露或者侵犯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侵犯他人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
(三)辅之设计“三层次”的判定标准
将网络有害信息划分为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网络有害私信息,并采用宽严不一审查标准的学理认识,也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固化。参考《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对“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⑧See Sandra Coliver,etc.,Secrecy and Liberty:National Security,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the Netherland: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9,pp.1-10.德国《多媒体法》对事后限制标准、⑨参见孟威:《宽容有度的德国网络内容监管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2月14日。美国司法判例对表达内容中立标准等之成文表述,⑩See Tinker v.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393 U.S.503(1969).可针对三类有害信息对应规定“三层次”的判定标准。其一,判定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遵循表达内容中立标准,条文建议设计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国家荣誉、国家统一等国家利益的网络信息,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对其发表时间、地点、形式等进行限制。其二,判定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区别适用表达内容中立和“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条文建议设计为:对于危害社会公德、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民族风俗、习惯等公序良俗的网络信息,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对其发表时间、地点、形式等进行限制;对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并有可能引起即刻暴力行为的网络信息,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进行限制。其三,判定网络有害私信息,遵循事后限制标准,同时贯彻平等对待原则,条文建议设计为:权利人认为网络信息存在侮辱、诽谤、侵犯个人名誉权、隐私权、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情形,有权向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异议,行政主管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双方意见,依照平等对待原则对争议信息进行处理(具体处理方法遵循前述“通知——删除”规则)。
五、网络有害信息范围的统一解释
网络有害信息之判定,究其本质乃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问题。基于立法的主动授权和语言的开放结构,无论在立法和学理上做何种努力,均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解法律适用者在具体化过程中的裁量空间。为最终解决“同案不同判”、裁量权恣意滥用等弊端,在系统化的立法努力外,还需确保法律概念适用中的统一解释。这种统一解释,在我国长期以来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完成。①例如,针对网络谣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连续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和《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4号)两份司法解释,对网络谣言的涵义、特征、定罪量刑标准等进行了细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网络谣言”这一具体类型网络有害信息的统一解释。但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较为漫长,具有一定滞后性,且不可能针对每一法律概念分别制定相应抽象解释文件,故还需跟进发展更为灵活、便捷并能迅速回应现实争议焦点的法律解释技术。根据行政法治经验,这种更为微观和及时的统一解释目标,可通过制定针对网络有害信息的解释基准、创建行政执法案例库、发布司法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等操作机制得以实现。
(一)建立行政解释基准制度
为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权,消解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我国行政法理论及实务界近年来大力推崇解释基准和裁量基准制度。②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在网络有害信息界定方面,解释基准制度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但在其他行政执法领域,解释基准制度已取得长足进步,积累了颇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广州市公安机关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第52条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一词进行了解释,《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赌博违法案件的量罚指导意见〉》第1条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赌资”一词进行了解释。③参见《广州市公安机关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穗公法〔2012〕49号)、《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赌博违法案件的量罚指导意见〉》(苏公规〔2010〕3号)。这些解释基准,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立法条文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统一指导了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
借鉴该制度与方法,笔者认为可由各级公安、国安、文化、电信、新闻等网络行政主管机关发布相应的解释基准制度,对网络有害信息相关立法条款中的国家安全、党的安全、国家秘密、国家荣誉和利益、民族仇恨、民族仇视、民族风俗、民族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公德、邪教、封建迷信、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侮辱、诽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进一步细化与具体化。各机关发布的解释基准,对本行业、本区域的同类执法活动,具有“自缚”的强制约束力。如此,可一定程度上统一法律适用效果,并为最终统一立法积累成文参照样本。
(二)创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库
对法律适用中的争议问题,建立执法案例库,是行政主体创新社会管理的另一项重要尝试。其典型表现如,2010年湖南省颁布《湖南省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办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实行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并对指导案例的遴选、发布、运用、法律效力等做了详细规定。④参见《湖南省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办法》(湘政发〔2010〕17号)。应松年教授曾这样评价行政指导案例的制度效果:“不管法律条文制定得多么细致,总没办法把现实情况解释清楚,但指导案例的出现,能提升行政执法的准确、公平和公正。”⑤张莹:《湖南又一次开创依法行政先河》,《潇湘晨报》2010年8月10日。
上述经验完全可适用于网络有害信息判定的微观执法领域。网络主管机关可通过发布典型指导案例,阐释行政主体在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过程中的考量因素,明晰对争议权益的衡量及取舍过程,正面回应相对人和公众质疑,将带有规律性、多发性、重复性的疑问,在个案中进行一并回应、释疑,以作为后续解释的参考。这种指导案例由网络行政主管部门遴选、制定,然后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审查。政府法制部门依法从专家、学者、实务部门资深工作人员中选定人员评审,对于通过评审的指导案例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发布。这种处理方法能够进一步弥补成文法及解释基准之不足,并极具可操作性,理应得到网络管理部门的重视和践行。
(三)发布司法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
行政主体针对网络有害信息的个案和抽象解释,均应接受司法的事后审查。一方面,根据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解释基准作为规范性文件对司法机关并不具有“依照”的强制约束力,而且法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一并审查其合法性,如认定不合法,应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法院对待行政解释,应持尊重态度,在其合法有效时应以自制的精神加以遵守,但在有正当理由情况下,也可依自身认识独立裁判。司法机关的这一审查权,为自身通过发布指导案例,再次修正、检视网络有害信息判定标准提供了可能。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中,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应“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同时,“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
根据发布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的上述制度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可遴选实践中有关网络有害信息判定的典型个案,对争议焦点进行条分缕析,尤其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个人私益与表达自由利益竞合时的考量因素、利益衡量取舍过程等,进行揭示与总结归纳,以作为后续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重要参考。上述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的建立,本身是开放的,可以不断添加更新,由此直面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焦点,弥补前述成文立法之不足。
(责任编辑:闻海)
D F31
A
1005-9512(2015)01-0102-12
尹建国,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有害信息政府治理的综合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CFX 033)及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W T0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