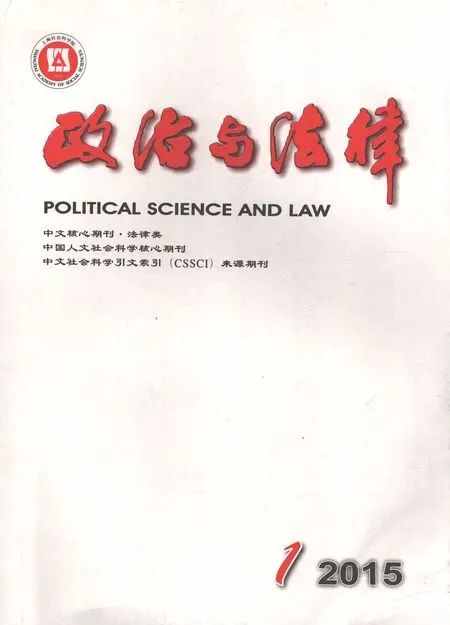论生命权法律性、权利性、神圣性的坚守
——对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的批判
2015-01-30郑琼现
郑琼现
(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论生命权法律性、权利性、神圣性的坚守
——对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的批判
郑琼现
(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生命权作为一项权利,主要性质是法律性而非道德性;其特征的主要是自由处分性而非处分的受限性,人的生命权是神圣的。在生命权的理论阐述和诠释中,盛行着生命权的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有人强调牺牲、奉献,在高扬权利道德性的同时放弃了权利的法律性;有人强调生命的义务,在聚焦人活着的责任的同时遗忘了人活着首先是一种权利;有人执着于人的生物属性,在呼吁人与动物平等和睦相处的同时抛弃了人类生命的特殊性和神圣性。这三类话语,将矛头直指生命权的法律性、独立性、排他性和生命权的神圣性,实有批判之必要。
生命权;生命权伦理化;生命权义务化;生命权生物化
康德说,人的生命“没有什么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因为世界上“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可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①[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6页。顺着这种思路考察生命权,可以说,对生命权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有学者曾经有点夸张地写道:“我们必须吸取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如果人的生命权长期被忽视或藐视,必然导致国家的灭亡;如果不能坚持以生命权为顶点的宪法价值秩序,由生命体的个人创造的现代文明也会成为地球上的一句神话。”②[韩]许营:《生命权的宪法考察》,转引自金柄禄:《生命权的若干问题》,载《公法研究》(韩国)第28辑第4期。的确,时至今日,已没有一个国家、政党或个人公然地反对或否定生命权的价值,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生命权的研究,中文期刊上发表了以“生命权”为主题的论文1264篇,可谓硕果累累,③期刊论文统计截止于2014年9月,其中1982年至1989年有10篇。最突出的例证,当为韩大元教授《生命权的宪法逻辑》和上官丕亮教授《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两部专著的出版。④上官丕亮:《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出版;韩大元:《生命权的宪法逻辑》,译林出版社2012年出版。生命权研究中的热闹非凡,彰显了学术界对生命权的极度关注。诚然,在这种极度关注中,诸多观点值得商榷:如许多论者主张生命权入宪,认为生命权不写进宪法,就不能彰显生命权的崇高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宪法权利泛滥的思维;如许多论者在讨论生命权的内容时,无限扩张生命权的内涵,声称生命权不仅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甚至是一种政治权利,大有将生命权内容泛化的意味。遗憾的是,因为这些话题游离了本文的主题,在此无法展开讨论。笔者关注的是,生命权作为一项权利,主要性质是法律性而非道德性,主要是自由处分性而非处分的受限性,人的生命权是神圣的。在生命权的理论阐述和诠释中,盛行着生命权的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或有人强调牺牲、奉献,在高扬权利道德性的同时放弃了权利的法律性;或有人强调生命的义务,在聚焦人活着的责任的同时遗忘了人活着首先是一种权利;或有人固守于人的生物属性,在呼吁人与动物平等和睦相处的同时抛弃了人类生命的特殊性和神圣性。这三类话语,将矛头直指生命权的法律性、独立性、排他性和生命权的神圣性,实有批判之必要。
一、生命权伦理化话语的批判
从弘扬高尚的道德风尚出发,学术界存在着鼓励自我抑制甚至牺牲权利的倾向,鼓励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利益抑制、牺牲个人的财产权,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例证。这种倾向也蔓延到了生命权的讨论之中,某些学者忽视了生命权与财产权等其他权利的重大区别,忽视了生命权的法律属性,强调生命权的道德性,强调生命权行使过程中对国家、社会、他人的价值和意义,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道德激情驱使下,呼吁献身、奉献和牺牲,将“小我”之生命权融入到“更高”、“更宏大”的价值体系之中,形塑了学术界的生命权伦理化话语。
(一)话语关键词:传统的“献身”与现代的“奉献”
也许是由于一向人口众多,因此“物多价贱”;也许是由于“舍生取义”、“十八年后又是好汉一条”的理念根深蒂固,中国文化传统中孕育了过重的“轻生”因子。死亡,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浪漫的字眼。娥皇、女英的死亡令人想起修长、灿烂、珍贵稀少的斑竹,梁山伯、祝英台的死亡让人想起花丛中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中国文化中虽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的古训,但那只是与“生命权神圣”相遇下的偶尔调情,她一见钟情的对象却是献身。为爱情献身,那是孔雀东南飞;为事业献身,那是“人固有一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国家民族献身,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总之,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生命权话语,很容易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吝啬于赞美生之灿烂,慷慨于悲歌死之美丽。时至今日,生命权在我国依然未能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小我”之生命权是如此渺小,以致在所谓国家、民族、集体、家庭甚至他人利益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以忽略不计。
1999年,张庆福教授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其中对“不可放弃的权利”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生命权是一种可以放弃的权利,“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也要求,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社会、国家利益,有必要由个人作出局部的利益牺牲,甚至是生命的牺牲”。⑤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8-619页。他论述道:“人们固然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绝不允许轻易抛弃自己生存的权利。但是,是否就因此可以说人的生命权就是一种绝对的权利?我们认为不是。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当国家或社会的利益遭到侵害,或当他人的生命发生危难时,道德要求人们应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挽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他人的生命。如那些跳进激流抢救落水者,那些扑入烈火抢救困在火中的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但还甘愿作出可能丧失生命的牺牲,这不是社会普遍称道和提倡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吗?相反,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见死不救,见危不助,不也是人们普遍厌恶和谴责的极卑劣的自私自利行为吗?至于在正义的战争中,许多军人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或者为了保全战友的生命,像黄继光等烈士那样,勇敢地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敌人的枪眼,或是用自己血肉之躯扫除地雷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不也是永远博得人们崇敬的英雄主义的行为吗?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抢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发扬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感人事例可以说举不胜举。”⑥同前注⑤,张庆福书,第617-618页。
相似的表述也曾出现在徐显明教授一篇以生命权为主题的论文中,⑦徐显明教授写道:“生命权是一种维护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固然重要,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存在。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宁肯牺牲生命也不愿屈辱地活着,更不接受外来统治者的高官厚禄,他们把人格尊严、民族气节和骨气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在他们的心目中,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要高于个人的生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有许多人为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保护他人的人身安全,奋不顾身地与犯罪分子博斗,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些见义勇为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的颂扬。反之,那些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出卖民族利益,甚至为虎作伥的人,都会受到人们的唾弃。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应在有限的时间里为社会作贡献,使自己生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徐显明:《生命权与人身安全权》,载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4页。其与前引张庆福教授的表述都堪称典型的生命权伦理化话语。奇怪的是,这种话语不是出于思想政治课的课堂,不是出自哲学伦理学的讲坛,而是出自法学的殿堂。在道德伦理领域,我们可以秉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尚情操,但在法律领域,我们不能无视“趋生避死”这一人的本能。人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需教导和训练的、天赋的、在人类进化路上所留下的一些行为和能力。霍布斯说:“如果一个人尽全力去保护他的身体和生命免遭死亡,这既不是荒诞不经的,也不应该受到指责,也不是与正确的理性相悖的。可以说,不与正确的理性相悖,就是按照正义和权利去行事。”⑧[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在法律领域,应秉持霍布斯式的最低道德要求对待生命权,任何超越人的理性和本能的法律要求,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我们有太多的法学家,热衷于弘扬道德风尚,而忘记了自己的专业视角和职业使命。10年前,法学界展开过一场关于乞讨问题的争论。在主流观点看来,乞讨不仅妨碍社会秩序和风尚,有碍市容等,而且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应当禁止。在非主流的观点看来,如果要从法律上否定公民的乞讨权利,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完全能够保障所有公民的生存条件,任何公民都可以从政府或政府指定的组织随时得到必要的维持生命需要的条件;二是对维护生命所需的条件能够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然而,至少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都难以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从法律上否定乞讨行为的条件还不成熟,但这并不排斥对乞讨行为进行管理,并积极创造条件减少和消灭乞讨行为。⑨参见谢鹏程:《公民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无论是主流观念还是非主流的观念,都未曾承认乞讨的权利是维持生命的权利的延伸,具有其正当性和不可剥夺性,或以妨碍市容的“面子”观念来剥夺维持生命权的这一有力手段,或将其看作暂时的、畸形的权利欲尽快消灭而后快。于是,在“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的古典情怀的强烈激励下,法律人和其他人一样,抛弃了生命权的至高地位。
(二)话语逻辑悖论:献身、奉献之愿与实现之艰
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某些特别的人的确有转让、奉献自己生命的愿望,当儿女、情人、父母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之际,有些人很愿意转让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所爱的人生命的延续;当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有些人牺牲了小我来拯救大我。可见,这种转让、奉献和牺牲往往发生在特别的时刻或者特别的人身上,是一种激情燃烧的结果,做出这种生命权处置的人,或被称为情圣,或被称为英雄。但法律不是为情圣和英雄所设立的,其对象是常人,法律调整的只是常人的理性。
从常人的理性或者说从法律人的理性来判断,生命权可以转让、牺牲和无私奉献吗?
首先,这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可能。抛弃或献出生命,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在生理和心理上超出了人类的能力。霍布斯论述道:“如果主权者命令某人把自己杀死、杀伤、弄成残废或对来攻击他的人不欲抵抗,或是命令他绝饮食、断呼吸、摒医药或放弃任何其他不用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这人就有自由不服从。”⑩[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9页。为什么可以不服从主权者要求生命权的主体抛弃或献出生命的命令呢?因为“当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或放弃他的权利时,那总是由于考虑到对方将某种权利回让给他,要不然就是因为他希望由此而得到某种别的好处。因为这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所以有些权利不论凭什么言辞或其他表示都不能认为人家已经捐弃或转让。首先,如果有人以武力攻击一个人,要夺去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放弃抵抗的权利,因为这样就不能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任何好处”。①同上注,霍布斯书,第100页。
其次,这在道德和理性上不可能。要求人抛弃或献出生命,类似于要求人抛弃良心或道德性。卢梭对于人抛弃自由和生命抱持一种深刻的批判:“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的。”②[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7页。他甚至认为,一个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只能说明献身的人没有健全的理智:“说一个人不求报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该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只因为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丧失了理智。”“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补偿的。这样做是不合人性的……”③Rousseau J.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Christopher Betts e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0.
也许,鼓励人们为了更高的公共利益而献出生命,是反对生命权绝对论的一种尝试。“在人权相对论者对绝对论者进行批评时,他们以经验中的权利冲突为事实依据,认为诸多不同种类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冲突或矛盾。而一旦权利之间发生冲突,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存在选择的问题时就必然意味着有权利是可以让渡的。而且,在冲突着的权利之间需要进行平衡,而平衡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要限制或牺牲另一种权利。”④赵雪纲:《从生命权角度看死刑存废之争》,《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生命权相对论者的出发点不外乎如是。但人权绝对论者之所以反对权利的相对论,是因为这种理论会带来的可能后果:有利于国家行为和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⑤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4,p33.所以,坚持生命权的绝对性自有其目标的合理性:任何人都不能以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将集体或团体利益优于个人生命,从而彻底架空生命权。就像德沃金所说的,“权利是这样一种资格,政府否认个人的这种资格就是错误的,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什么?德沃金解释道:“如果能够凭借多数人的权利剥夺个人的权利以实现政府的意志,那么现有的与政府有冲突的权利将会受到威胁。与政府相冲突的权利必须是即使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也可以做某事的权利,甚至这会使多数人处于更坏的境地。如果我们现在说为了公众的利益社会有权利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已经取消了(个人)权利。”⑥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269.对生命权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我们也要有类似的清醒。
(三)话语路径的吊诡:以生命奉献论始,以生命工具论终
生命权伦理化话语,核心是强调生命价值,与西方法社会学的生命价值论异曲同工。生命价值论认为,生命并不是无价的,生命的价值不是人人相等的常数,而取决于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只依赖于社会生活而不为社会做贡献,那他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⑦赵野田、潘月游:《论生命价值的道德支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在现实中,如果仅仅维持着生命的存在而无所事事,一味消耗着他人和社会的财富,这样的生命谈不上价值。而那些无恶不作、残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生命活动,不但是毫无价值可言,甚至是负价值。”⑧张勇、黄晓东:《对死亡和生命价值的哲学思考》,《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生命价值论强调贡献,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大,他的生命价值就大,没有贡献也就没有价值,生命之所以神圣,主要在于它的贡献价值,或称“社会价值”,“衡量生命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所作的贡献,生命活动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越大,其社会价值就越大”。⑨张谈生:《论生命价值》,《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由于对贡献的依赖,这种生命价值论与其说是在考察生命的价值,毋宁说是在考察生命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价值,“这种观点暗含了这样的前提:即把人置于客体的地位,考察的是这种客体对别的主体(他人、社会)的有用性,强调的是作为客体的人对别的主体的效用价值”。⑩万慧进:《论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人的生命价值概念质疑》,《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3期。手段和工具是可以选择和取舍的,没有用时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甚至就可以弃如敝履。将人的生命作为手段和工具的观点,早在康德时代就饱受质疑,康德批判道,人的本性就证明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有理性之物是以自己为目的而存在”,“无论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把它只当作工具”。①[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3页。的确,生命价值论存在着逻辑的悖论:仅仅把人的生命看作是满足他人和社会需要的工具,势必大大贬低生命权的价值,甚至取消个人生命权的独立性,最终,在倡导生命价值论的同时使生命价值荡然无存。
生命权伦理化话语存在着与生命价值论同样的逻辑悖论: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有时需要某些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需要限制和剥夺某些人的生命权,以保证所追求的“最大利益”这一结果,在“限制和剥夺某些人的生命权”的需要之下,生命权的地位就要作低调的处理。其实,这种理论不能解释献身、牺牲的对错,甚至无法说明杀人是错误的。赵雪纲曾经分析这种理论的逻辑缺陷:依这种理论推演,只有当波及他人的结果是负面的时候,杀人才是错误的,但是,杀人的结果不一定是负面的;“杀人是错误的”完全决定于该杀人行为是否真的产生波及他人的负面结果,假若此负面结果不出现,或者可以被“中和”,则没有理由反对该杀人行为;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杀人会带来波及他人的正面的结果,那么,这种理论就会提供杀人的正当理由。②同前注④,赵雪纲文。在生命权伦理化语境之中,如果牺牲或剥夺某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安全、秩序和其他多数人的幸福,则这种牺牲就是合理的、正义的,这种逻辑的结果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权都可能被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生命权伦理化语境之中,人的生命是相对的,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是可以被牺牲和奉献的,这种逻辑的结果是,个人的独立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绝对价值被消磨殆尽,“设若人的生命和生存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则我们就可以以一种任意和武断的方式对待人,由此,一个弱肉强食世界的建立也就不能被证明是荒谬和错误的”。③赵雪纲:《人权概念的正当性何在?——康德伦理学对人权概念(以生命权为例)之奠基性意义》,《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霍布斯说:“我们打量任何一个成人,都会看到,人的身体结构是多么脆弱,如果失去了它,人所有的力量、活力和智慧都会随之而去。”④同前注⑧,霍布斯书,第6页。法律和法学不能在本已脆弱的生命权躯体上再踏上致命的一脚,而应本着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的信条,去尊重和呵护人的生命权。以生命权是个人“小我”的信条去对待生命权,结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生命权话语伦理化的批判,其意义正在于此。
二、生命权义务化话语的批判
生命权义务化话语的批判,主要是为了反对生命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轻率、冒险、自杀、放弃生命等不负责任的行为。近来学界兴起了延续生命是一种义务的话语:活着,是一种权利,但更是一种义务,放弃生命权,就是放弃了对国家、社会、家庭甚至他人应尽的义务,因此生命权也是一种义务,处分权不能自由行使。这种话语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话语主题句:生命权的延续是一种义务
在我国的法学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提法:“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生命权在法学论著中的遭遇也可以用这句话来予以简单的概括。生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一方面,有人鼓励人们放弃生命权,如为了打击犯罪主张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和正当防卫权的泛化,为了计划生育鼓励堕胎;另一方面,将生存看作是人的一种义务,声称生命权不可放弃:“每个自然人作为法律主体,是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集权利和义务于一身,放弃了生命权,不仅享有的权利无法行使,必须履行的义务也不能再履行,如为人父母者不能尽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为人子女者不能尽赡养父母的义务,造成家庭残缺,义务履行对象的成长、生活陷于困境,使亲属蒙受巨大的精神痛苦。对生命的抛弃,不仅伤害了亲属的盛情,而且打击了每一个活着的人,是对人间最美好事物的亵渎。”⑤同前注⑦,李步云主编书,第464页。从“放弃了生命权,不仅享有的权利无法行使,必须履行的义务也不能再履行”之类的认识出发,生命权义务论者反对对生命权的自由处置,认为:“任何权利都以义务为界限;任何权利人既是自身利益的权利享有者,又是他人利益的义务承担者。就拿生命权来说,它是专属于权利人的,但该权利人的生命中同时还负担着他人的利益即对他人的义务,且该义务是以该权利人的生命存续为条件的,如对子女的抚养,对老人的赡养,对爱人的呵护等,没有生命的存续,这些义务难以履行。这说明,生命属于自己,但也不全是,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自己生命利益的处分权不能任意行使。否则会导致人们轻视生命,甚至将生命利益的处分权作为逃避责任的手段,这是法律万万不能认可的。”⑥李明华:《安乐死:生命的尊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0期。
(二)话语病灶之一:否定权利主体对客体的支配权
生命权义务化话语,其实质是否定生命权主体对生命的完全支配。生命权人是否拥有生命支配权?
经验是我们判断的重要根据。我们的经验是,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生命主体也经常要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需要独立抉择是否承担生命风险,甚至是否放弃生命,“我的生命我做主”,这是日常生活中行使生命权的应有之义。而生命权伦理化话语,近似于主张“我的生命他人做主”,实质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生命权主体对生命的支配。勇敢的激励驱使我们参加蹦极、跳伞、高空坠落等娱乐活动,我们这些活动依赖于他人的同意吗?冒险的冲动差遣我们去登山、攀岩、漂流,我们的这些活动仰仗他人的同意吗?好奇的天性引诱我们进入原始森林、酷寒极地、未开发的洞穴或荒蛮的无人区,我们的这些活动需要以他人的同意为前提吗?职业和爱好使我们以拳击、武术、赛车、杂技为业,健康的维持使我们无奈接受各种有风险乃至高风险的手术,每日例行的行路、乘车、驾车也会祸从天降……所有可能使我们失去生命的活动,只需要生命主体的自我决定、自我支配。因为,如果将他人的意志参和进来,甚至强调生命权人以外主体的同意,人就会失去或弱化勇敢、冒险、好奇等人的道德性,甚至使自身的工作、健康甚至日常生活都要受制于人。因此,在对生命权的支配和处置问题上,笔者支持这样的观点:“生命的风险几乎时时处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每一个生命的主体都有权也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心意思独立自主选择。这正是生命权人对自身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利的具体体现。”⑦邓河:《论生命权的本质与安乐死的选择》,《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
生命权主体对生命的支配程度,最有说服力的典型是对自杀的看法。“自杀曾在有的国家被认为是犯罪,那已成为历史的笑柄、早已不见了踪迹。”⑧张玉堂:《我们有死亡的权利吗?》,《法学》2001年第10期。在现代法学理论中,自杀属于“法律空白领域”之内的放任行为,⑨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属于“既不能适当地评价为合法的,也不能评价为违法的”行为。将自杀置之于“法律没有评价”的领域,⑩[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2页。在法学领域中部分论证了人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法律实践也秉持对自杀不予介入的态度,通过技术处理将自杀行为关闭在法律大门之外,既承认法律对自杀这种处分生命事实行为干预的无能和不能,又相信道德在法律缺席领域的应有功用。法律在自杀问题上的谦抑态度,表达了对生命权主体处置其生命的尊重,即使某些处置是“不道德”的,法律也谨慎地抱持回避心理,以免自身的过分张扬和肆意。笔者在此并不想轻率地认定生命权必定包含自杀权的内容,对生命权的支配也并非可以走向采取自杀行为的极端。笔者只是想指出,即使在道德领域,自杀之有无于生命权,都仍然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充满了赞同自杀与反对自杀的角力,法律领域中如果顽强地坚持生命义务论,那将情何以堪?
黑格尔说:“法定的权利不论是私人的或是国家、市镇等公共的,原先就称之为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①转引自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推理,生命权也是一种自由,生命权主体当然地具有对其生命的自由支配权,包括处分权。边沁认为,无论什么法律都是对自由的“违背”,而且,虽然某些类似的违背是必要的,但是,若要假装说它们根本就不是违背,那就是蒙昧主义的论调了。②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生命义务论者也许承认对生命权人支配生命的自由构成了“违背”,但其话语不足以解释这种违背是必要的。德沃金在谈到自由时说:“当我们制止一个人谈情说爱或做爱时,我们削减了他的自由,当我们制止他谋害或诽谤他人时,我们也削减了他的自由。虽然,后一方面的限制是可以有理由的,那也只是因为它们对于保护他人的自由和安全来讲是必要的妥协,而不是因为这些限制本身没有侵害自由的独立价值。”③同上注,罗纳德·德沃金书,第352页。生命义务论奢望用生命的义务来限制生命权的滥用,但这种限制已经走得太远了,因为这种限制已经侵害了支配生命自由的独立价值。
(三)话语病灶之二:混淆权利、义务概念
任何权利在设立时就已经自附了义务,权利的自附义务构成对权利的内在限制,生命权的设立也不例外。“人权的获得,由于从一开始就遵循着他人在同等条件下也能获得的原则,因之任何人的人权都必定与他人的人权和谐统一。”④徐显明:《论人权的界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如果生命权主体不履行生命权的自附义务、超越生命权内在限制的底线,那他就违背了他人在同等条件下也能获得生命权的原则,无法实现与他人生命权的和谐统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权的行使才可能超越“义务”和“限制”。生命权的自附义务是什么?生命权内在限制的底线何在?这需要联系生命权的位阶来回答。人们在行使生命权的时候需要接受他人生命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和自由的限制(譬如接受生命义务论者所言的子女被抚养权、老人被赡养权、爱人被抚养权、国家社会被回报权的限制)吗?不需要,因为这些权利、自由或利益对主体的生命权而言,都处于低位阶,而所有的权利只接受来自高位阶权利的限制。因为生命权位阶的最高性,因此只有他人的生命权是生命权的自附义务和内在限制,其他的全部是一种外在的限制。“人权只服从其内在限制而不需外在限制”,⑤徐显明:《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文化之解析》,《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如果说一定要明确生命权的义务的话,或者如果说一定要将生命权看作义务,那仅仅是指尊重他人生命权的义务,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义务。不能因为法律限制了自由就将自由等同为对自由的法律限制,同理,不能因为他人的生命权限制了我们的生命权就将我们的生命权当作义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否定生命权主体对生命的支配权出发,进而将生命权理解为个人对国家、父母、子女的一种义务,实有偷换权利和义务概念的嫌疑。
然而,生命权伦理化话语在这样的思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在这种话语之下,个人生命里面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之中;个人生命消失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和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个人结束自己生命有可能极大地损害社会利益,假如个人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自杀,这将严重破坏社会关系,对其他个人或社会造成损失。因此,“生命权归属的应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生命权。一切的重大关乎以上主体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抉择都必须经过以上这些主体的一致同意,不能忽略一个方面的主体”。⑥孟祥虎:《由生命权看安乐死》,法律图书馆网站,2014年6月18日访问。将生命定性为个人、国家、个人的主要亲属和重大利害关系人共有,将完整的生命权弄得支离破碎,将活着作为一种义务,在实践中必然意味着:国家、个人的主要亲属和重大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支配你的生命,都可以对你这一生命权人支配自己生命的行为进行合法的干预。这样生命权就失去了独立性和排他性,在抹杀了生命权绝对性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律设立和保障生命权的本旨。
三、生命权生物化话语的批判
从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只是万千生物中的一种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反对人的生命权神圣的浪潮:在权利的问题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人类自身意识到自己有生命权、生存权,相对于广阔的自然界来说,主张这种权利是毫无根据的,认为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动物歧视。这就是生命权的生物化话题。
(一)话语中心思想:人类不是神圣的
自然人生命的基本要义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如果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都不能存在,那自然人的生命又何谈其价值。这是生命的生物学基础。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被有的论者捕捉和放大,用以反对生命神圣的命题。因此便有了生命权生物化的话语:“如果我们接受生物进化论,把人类生命放到自然历史的演化之中,就会对人类生命产生一种更客观的理解。在这种客观理解中,假如人类生命是一个奇迹,那么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也是奇迹;假如大自然赋予人类以尊严,那么大自然也赋予了其他生命形式以尊严。在这种意义上,人类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类的特别是因为人类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同样,在这种意义上,人类不是神圣的,人类的神圣也是因为人类认为自己是神圣的。”⑦姚大志:《人类有权利克隆自己吗》,《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
生命权的生物化话语,目的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确,人类中心主义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包括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等。尽管这些流派在对权利主体范围的认识上有所区别,但却有着一种共识:各种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及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的“生存权利”;它们的这些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而非人类的利益)才是判断人们对它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的终极根据,对人的行为的善恶评价必须以此为标准。⑧杨通进:《动物权利论与生物中心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8期。正是在这种共识之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对人的生命神圣论发起了挑战。在生命神圣论肇始的西方社会,有人满怀义愤地向天赋生命权发问道:“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何以必然具有不可转让的权利?如果仅仅因为某种生物类别的成员身份,其它生物种类的成员为什么不能享有类似的权利?难道我们相信人权是‘同类’的一种非理性的选择?”⑨辛见:《关于人权概念的一场辩论》,《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的确,地球不仅仅是人的世界,也是所有生物同生共存的世界,人,只是构成地球生命的一分子、一个物种而已。在这种认识下,有了那条著名的彼得·辛格命题:“认为人类生命——并且惟有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乃是一种动物歧视。”⑩P.辛格:《动物解放》,孟祥森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主张对非人类存在物的保护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将人的权利与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相提并论,甚至以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来理解人权,那就危险了。
(二)话语危险之一:“人格”的“物格”化
这种话语的第一个危险是导致“人格”的“物格”化。如果自然、生态、动物等有权利,那就等于说它们与人具有相同的“品格”。也许,最初的人类在建构道德秩序时,通常以自然秩序为前提,自然秩序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差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基础,因此“人格”与“物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人格”与“物格”是两码事,自从自然的进化产生了人类以后,“人格”与“物格”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在“物格”领域,这样的命题不受质疑:我长得比你高比你壮,比你能打比你聪明,你必须按我的规矩生活,否则我将把你赶出我的地盘甚至剥夺你的生命。但在“人格”领域,依据个人智力、体能或类似事实性的差别来否定平等、主张特权,却一直不得人心。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5页。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使人成为道德、法律的主体,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是人具有道德资格的依据,从而在“人格”与“物格”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情况是,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至少是自然的管家,人永远是自然的主体,自然只能充当客体,自然只能人化,人不会去自然化的,最多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反之,从人是自然的产物出发,挖掘人与自然其他物种的相似性,其进路只能是“人格”的“物格”化。有人推测:“可能也是出于这种更高的智力和能力,人类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具有自恋的倾向。”②同前注⑦,姚大志文。在某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人类对自身“人格”的自豪,也许正是“自恋倾向”的结果,难道人类应该抛弃这种“自恋倾向”而彻底地“物格”化吗?“人格“的彻底“物格”化,结果只能是以自然界、动物界的规则来规则人类社会。在这种规则之下,就生死问题而言,人类应该像动植物那样听命环境、听命自然,排除人为干扰,特别是医学科技的干扰,在生病、受伤、年老、环境恶化之时,像动植物那样自行死亡,从而否定了人类的实践本性,将人降低为物,将人的生命简单等同于动植物的生命;在这种规则之下,“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移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页。
(三)话语危险之二:人的生命权的动物权化和动物权利的人权化
这种话语的第二个危险是导致“人的生命权的动物权化”和“动物权利的人权化”。所谓“人类没有什么特别的”④同前注37○,姚大志文。、“在存在权利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⑤刘湘溶、李培超:《论自然权利———关于生态伦理学的一个理论支点》,《求索》1997年第4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她)相对于广大的自然生物来说是没有权利可言的”⑥侯依成:《关于人的生存权的哲学思考》,《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凡此种种论调,无非是要打破人和动物的严格分野,主张动物权利与人权的平等。这种工作,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早就做了。动物解放论的代表人物辛格按照意识的发达程度,把生命依次划分为人格、有知觉的生命、无知觉的生命三个等级,“人格”包括正常人、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鲸鱼、海豚等有理性和自我意识的存在者;“有知觉的生命”包括许多非人动物、人类新生婴儿和一些严重智障的人;“无知觉的生命”包括植物、怀孕不满18周的胎儿、没有感觉能力的生命和所有无生命者。⑦Peter Singer.,Practical Ethics,Second e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01.在辛格的生命等级分类中,每一类中都既有人的生命也有物的生命,同一种的人的权利与物的权利都具有同质性和价值相等性,在强调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平等、打破人与动物分野的同时,实现了人权的物权化、人的生命权的动物化甚至植物化。人的生命权的动物化会推演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辛格推论道:“新生婴儿并不比猪、狗或黑猩猩等非人类动物更具有生命价值。”⑧同上注,p169.“杀死残疾婴儿与杀死人格在道德上是不相等同的;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这根本就不是错误的。”⑨同上注,p191.动物权利论的当代传人雷根则通过“救生艇案例”,实现了“动物权利的人权化”:救生艇只能容纳4个幸存者,现在有1只狗、3个正常的成年人和1个昏迷的人,某一个不能上船,否则会全体丧生。谁该被放弃?死亡没有给这个昏迷的人带来损失和伤害,但是会给其他三人和狗带来大于零的损失和伤害,此时就应牺牲这个昏迷者,来挽救其他三人和狗。⑩[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研究》,李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马克思说:“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他的价值不比别人大,也不比别人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5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论,人的价值就其自身来说是平等的,昏迷者的生命价值与清醒的正常人的价值是平等的。而在雷根的案例中,正常人生命的价值与狗的生命价值相等,而昏迷者的价值连狗都不如。
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的生命权生物化话语,表现了对动物、植物的关注,他们不仅主张动植物有不可侵犯的生命权,而且不遗余力地提升这种权利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方法不过是用对人的生命的贬低替代了过往对动植物生命的贬低,特别是贬低甚至否定了胎儿、婴儿、残障者、昏迷者、植物人等“劣质”生命的生存权。按照这种话语,只有手指能动而不能讲话行走、生活不能自理的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金,有维持生命权的合理性吗?按照这种思路深入,必将引来生命权大厦的坍塌,因为谁又能担保自己不会被驱赶到生命权保障的大门之外呢?
(责任编辑:郑平)
D F0
A
1005-9512(2015)01-0114-10
郑琼现,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